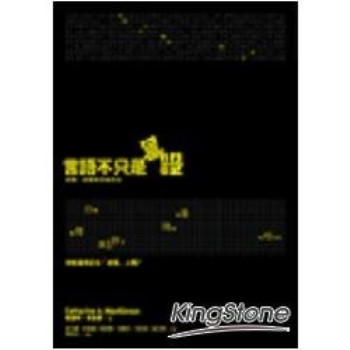第一篇 誹謗與歧視
想像一下,幾百年來,對妳影響最深的創傷、妳每天所受的折磨與痛苦、妳曾受過的虐待,以及在生活中如影隨行的恐懼都無法形諸言語,當然,並不是字面上的「說不出口」。在妳成長的過程中,妳父親按住妳並摀住妳的嘴,好讓另一個男人得以在妳的雙腿間,烙上那恐怖的痛楚。當妳再長大一些,妳的丈夫將妳緊縛在床上,在妳的乳頭滴上熱蠟,帶另一個男人進來觀賞,而且還要求妳保持微笑。醫生拒絕給妳那些明明是他使妳成癮的藥物,除非妳幫他口交。
妳無法告訴任何人這些事。當妳嘗試開口,他們就告訴妳它並未發生,這都是妳想像出來的,妳想要它而且妳樂在其中。書本就是這麼說,但是沒有一本書說出發生在妳身上的事;法律也這麼說,但沒有任何法律想像得到妳身上發生了什麼事,以及它們如何發生。妳的一生都生活在對妳的吶喊與言語毫無回應的文化之中。
在這千年的沉默中,相機與攝影機問世了,當這些事在妳身上發生時,也留下了影像。當妳被傷害時,妳聽到相機的快門聲和捲片聲,緊緊跟著妳痛苦的節奏。妳永遠都曉得那些影像存在於某處,人們販賣、交換、展示它,或只是把它放在抽屜。在這些照片中,那些施加在妳身上的事,將永遠存在。某個男人擁有它們,他可能是任何人,看過妳以那樣的方式存在。這令人無法忍受。透過這些照片,他觀看妳、利用妳時的感受,總是一再地被施行、經歷並感受,你的被侵犯引發了他的慾望,你的受虐成為他的歡愉。觀看妳,就是他將這一切施加在妳身上卻得以脫罪的方法:透過這些照片,他可以在任何時刻觀看妳,卻免於任何罪責。
隨著相機的問世,漸漸地,然後忽然間,妳心裡靈光一閃:也許現在人們會相信我了。妳找到了一個把事情說出來的可靠方法。也許,這些影像甚至可以作為強暴的證據。但妳發現,這些影像不但不能使這一切變得無可否認,甚至它們就是「性」的本身,是妳慾望與同意的證據。那些透過影像利用妳的人,所感受到的是他們自己的快樂。相較於那些觀看妳、傷害妳以製造這些影像的人,他們並不會更把妳的痛苦當作真正的痛苦看待。這些影像為一種虛假的私密與禁忌的特殊光環所環繞,而這些光環之所以是虛假的,是因為它們其實是公開的,而且並非真的違法。這些影像成為證明妳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權威證據,它們成為訴說妳經驗的文本,一個性的象徵,甚至是性的本身。這些影像十分真實地讓「性」成為性對於那些交互使用你以及你的影像的人所代表的意義,在那些人心目中,使用妳和使用妳的影像可以互換。這樣說來,這些照片和先前的色情文字或繪畫沒什麼差別,但是,透過相機利用妳更賦予這些影像一種特殊的可信度,使它成為一種更深刻而幾可亂真的事實,甚至是更強而有力的事實陳述,使得關於妳的一切無可否認,因為它們的確發生了,而且妳就在那裡。也正因為你對於這些影像而言是如此不可或缺,所以這些影像的供應者甚至有了另外一個理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妳。
最後,因為某種原因,妳發現了別的女人。她們的父親、丈夫、醫生看了那些影像,很喜歡,於是也對她們做了同樣的事,那些事是這些女人過去從未做過、也從未說她們想做的。這些女人也被壓住或綁起,或在檯上任人檢查,他們談論並指稱那些與妳的影像類似的影像:跟她做一樣的事,像她一樣享受它吧。那些強加於妳身上的行為,現在強加在她們身上,現在她們也被迫用當初妳被迫微笑的方式微笑著。妳發現,這一整個產業買賣著這些被控制著笑容的女人來生產影像,看起來彷彿她們就是喜歡這樣。
當她們之中任何一人試圖說出發生了什麼事,人們告訴她這事並沒有發生,是她想像出來的,是她自己想要的。她的「不」等同於「要」,影像就是證據,看,她明明就在微笑。除此之外,何必如此認真看待這些影像,它們不過是小小的人工產物,充其量不過是個微小的癥狀而已?即使真的有人對妳做了什麼不對的事,妳能有什麼樣的抽象隱痛呢?影像本身根本沒有對妳做出任何事。它們是一種理念的表達、一種討論、一種論辯、一種言說。妳能受到多大的壓迫?它們可是受到憲法保障的言論。
暫且不管這種從生活到法律的進展對人的現實意識、人身安全、社群中的地位,甚至法律體制的信心造成何種影響。思考一下它會對一個人和表達(包括語言、言論、思想與溝通的世界)之間的關係,造成什麼影響。妳開始明白其實語言並不屬於妳,妳無法運用它們說出妳所知道的事;妳開始明白知識並非妳在生活中所習得的;而且開始瞭解資訊並非基於妳的經驗而生;妳發現,「想」那些在妳身上發生的事情並不夠格稱為「思考」,但是「做」那些傷害妳的事卻顯然可以算是思考。妳開始發現屬於妳的真實存在於社會真實之外,這些真實暴露於外但人們看不見,尖叫著但人們聽不到,不斷地被想到但卻無法被思考,是一種「表達」但卻無法被表達,難以言語形容。妳開始明白,所謂「言論」並不是妳說的話,而是那些傷害者對妳做的事。
妳和言論的關係,就像是對著一部電影
想像一下,幾百年來,對妳影響最深的創傷、妳每天所受的折磨與痛苦、妳曾受過的虐待,以及在生活中如影隨行的恐懼都無法形諸言語,當然,並不是字面上的「說不出口」。在妳成長的過程中,妳父親按住妳並摀住妳的嘴,好讓另一個男人得以在妳的雙腿間,烙上那恐怖的痛楚。當妳再長大一些,妳的丈夫將妳緊縛在床上,在妳的乳頭滴上熱蠟,帶另一個男人進來觀賞,而且還要求妳保持微笑。醫生拒絕給妳那些明明是他使妳成癮的藥物,除非妳幫他口交。
妳無法告訴任何人這些事。當妳嘗試開口,他們就告訴妳它並未發生,這都是妳想像出來的,妳想要它而且妳樂在其中。書本就是這麼說,但是沒有一本書說出發生在妳身上的事;法律也這麼說,但沒有任何法律想像得到妳身上發生了什麼事,以及它們如何發生。妳的一生都生活在對妳的吶喊與言語毫無回應的文化之中。
在這千年的沉默中,相機與攝影機問世了,當這些事在妳身上發生時,也留下了影像。當妳被傷害時,妳聽到相機的快門聲和捲片聲,緊緊跟著妳痛苦的節奏。妳永遠都曉得那些影像存在於某處,人們販賣、交換、展示它,或只是把它放在抽屜。在這些照片中,那些施加在妳身上的事,將永遠存在。某個男人擁有它們,他可能是任何人,看過妳以那樣的方式存在。這令人無法忍受。透過這些照片,他觀看妳、利用妳時的感受,總是一再地被施行、經歷並感受,你的被侵犯引發了他的慾望,你的受虐成為他的歡愉。觀看妳,就是他將這一切施加在妳身上卻得以脫罪的方法:透過這些照片,他可以在任何時刻觀看妳,卻免於任何罪責。
隨著相機的問世,漸漸地,然後忽然間,妳心裡靈光一閃:也許現在人們會相信我了。妳找到了一個把事情說出來的可靠方法。也許,這些影像甚至可以作為強暴的證據。但妳發現,這些影像不但不能使這一切變得無可否認,甚至它們就是「性」的本身,是妳慾望與同意的證據。那些透過影像利用妳的人,所感受到的是他們自己的快樂。相較於那些觀看妳、傷害妳以製造這些影像的人,他們並不會更把妳的痛苦當作真正的痛苦看待。這些影像為一種虛假的私密與禁忌的特殊光環所環繞,而這些光環之所以是虛假的,是因為它們其實是公開的,而且並非真的違法。這些影像成為證明妳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權威證據,它們成為訴說妳經驗的文本,一個性的象徵,甚至是性的本身。這些影像十分真實地讓「性」成為性對於那些交互使用你以及你的影像的人所代表的意義,在那些人心目中,使用妳和使用妳的影像可以互換。這樣說來,這些照片和先前的色情文字或繪畫沒什麼差別,但是,透過相機利用妳更賦予這些影像一種特殊的可信度,使它成為一種更深刻而幾可亂真的事實,甚至是更強而有力的事實陳述,使得關於妳的一切無可否認,因為它們的確發生了,而且妳就在那裡。也正因為你對於這些影像而言是如此不可或缺,所以這些影像的供應者甚至有了另外一個理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妳。
最後,因為某種原因,妳發現了別的女人。她們的父親、丈夫、醫生看了那些影像,很喜歡,於是也對她們做了同樣的事,那些事是這些女人過去從未做過、也從未說她們想做的。這些女人也被壓住或綁起,或在檯上任人檢查,他們談論並指稱那些與妳的影像類似的影像:跟她做一樣的事,像她一樣享受它吧。那些強加於妳身上的行為,現在強加在她們身上,現在她們也被迫用當初妳被迫微笑的方式微笑著。妳發現,這一整個產業買賣著這些被控制著笑容的女人來生產影像,看起來彷彿她們就是喜歡這樣。
當她們之中任何一人試圖說出發生了什麼事,人們告訴她這事並沒有發生,是她想像出來的,是她自己想要的。她的「不」等同於「要」,影像就是證據,看,她明明就在微笑。除此之外,何必如此認真看待這些影像,它們不過是小小的人工產物,充其量不過是個微小的癥狀而已?即使真的有人對妳做了什麼不對的事,妳能有什麼樣的抽象隱痛呢?影像本身根本沒有對妳做出任何事。它們是一種理念的表達、一種討論、一種論辯、一種言說。妳能受到多大的壓迫?它們可是受到憲法保障的言論。
暫且不管這種從生活到法律的進展對人的現實意識、人身安全、社群中的地位,甚至法律體制的信心造成何種影響。思考一下它會對一個人和表達(包括語言、言論、思想與溝通的世界)之間的關係,造成什麼影響。妳開始明白其實語言並不屬於妳,妳無法運用它們說出妳所知道的事;妳開始明白知識並非妳在生活中所習得的;而且開始瞭解資訊並非基於妳的經驗而生;妳發現,「想」那些在妳身上發生的事情並不夠格稱為「思考」,但是「做」那些傷害妳的事卻顯然可以算是思考。妳開始發現屬於妳的真實存在於社會真實之外,這些真實暴露於外但人們看不見,尖叫著但人們聽不到,不斷地被想到但卻無法被思考,是一種「表達」但卻無法被表達,難以言語形容。妳開始明白,所謂「言論」並不是妳說的話,而是那些傷害者對妳做的事。
妳和言論的關係,就像是對著一部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