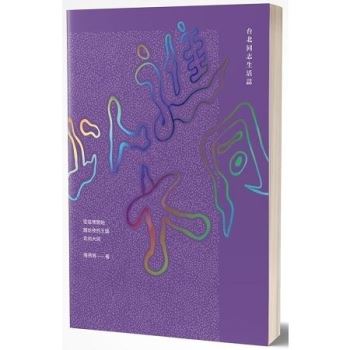◆今在此沿時間線徵友──打開同志徵友史(節錄)
◎陳栢青
「好兄弟,我十四歲便在公園裡出道。」白先勇《孽子》中小玉對阿青說道。「出道」被同志用來稱作進入圈子、認識友伴的開始,只是公園、酒吧固然是出道的首場見面會,早年訊息傳播管道有限,同志認識依賴口耳傳播,或經過報刊報導,才能得悉聚會場所。而時代並不友善,「同性戀加好奇心=愛滋病」,1991年《中國時報》仍可以見到這樣的標題,同志或憂慮他人眼光,或出於害羞,縱然知道同志聚會地點也不敢前往,那使得「出道」無期,認識朋友變得加倍困難。茫茫人海中如何尋找彼此?勇敢踏出一步,卻怕真心換絕情,「徵友」成了一次大冒險,透過各種方式現身,又達到隱身的效果,隔了一層,其實已經最暴露了。隱與現之間,也就成感情與慾望的引線。寫不完同志徵友史其實是同志生存史,希望認識別人,原來是接受自己的過程。
徵友欄
徵友欄不過方寸,對很多人而言,也就是天地了。訊息流通不方便的年代,刊物與雜誌上的筆友欄、徵友文是異性戀交友的重要管道,但春光藏不住,生命都會自己找到出路,八零年代《愛情青紅燈》雜誌號稱「軍中最紅的民間刊物」,傳之於軍旅,過手未必是異性戀男子,便多出幾雙同志的眼睛在其中暗眨,盼被看見。而《世界電影》雜誌帶來流行文化資訊,盛行於中產階級與學生族群中,徵友欄間或可見同志突圍足跡。至九零年代,於《愛情青紅燈》和《世界電影》雜誌上徵友竟成一股風潮。1995、1996年《世界電影》雜誌上每個月至少有四分之一徵友訊息或明示或暗示,同志在搶灘登陸。
八零年代《愛情青紅燈》設有「筆友(心情信箱)」,《世界電影》上則有「影迷俱樂部」, 但畢竟標榜「鼓勵未婚青年男女,開拓正常交友空間、寬闊思想生命為宗旨」,並且「對於違反本宗旨之函件,或詞語曖昧不當者,本來得以退件不刊出,或逕於刪修」,同志要隱藏其中,並同時顯露自身存在,「異中求同」變成求生策略。文字上偷渡,想方設法暗示,只有自己人知道。
徵友文可以古典,例如「小威,男,22歲。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獨我痴。願在青埂峰下,三生石畔,與你年年月月日日,期盼有志青年來信。」,文字用典,期盼有志青年來信,又與之月月日日。雖不明說,但身份也是天地可鑑了。
當然徵友也能很現代,「Kevin Lee,男,24歲,給我酷兒,其餘免談。」一句話表態。而隨著時代演進,不只同志認識彼此,徵友欄甚至能反過來看出同志內在自我的成形,無論「世人的眼裡,這是段不該有的畸戀,但我著實不願意就此放棄享受真愛的權利。」又或「宇宙觀的寬容是大愛,感情是自然表露,不分男女,沒有對錯,盼真誠相待,誠徵投緣的南部青少年為友。」那不只是自我介紹的引言,其實是世界觀的形成。從中可以看到同志怎樣看待自己,以及面對社會。
男找男。願與青年為友。但找的只是朋友,或者希望同類相吸引?徵友欄中字字珠磯,增加辨識度的方法,較為多見的方法如挪用同志 Icon: 「阿榮,男,十七歲,愛好:Madonna、瑪丹娜」,或將同志影視作品放入興趣嗜好中,例如「男,28歲。我聽黃耀明,熱愛與女朋友同言無忌,喜歡在公司裡掏心,卻一直苦無知音,來封信吧,保不定明朝我兩將相,信,相,依。」借流行元素與偶像傳心,迂迴撒下麵包屑,以供同類以逐字相尋。
徵友欄上的「同志」一詞成斷代,1991年金馬影展開設「同志專題」,「同志」同時指涉同性戀這樣的用法於台灣開始流行後,九零年代徵友欄上使用「同志」便多了一層寓意。「歡迎志同道合的青年來信交換彼此生活點滴」、「徵求志同道合者為友」、「尋覓有志青年為友」人們刻意在徵友文中箝入同志兩字,同志在徵友欄中既隱又現,光明正大隱藏。
隨著1994年《女朋友》雜誌創刊,1996年《熱愛》雜誌出現,專屬同志的雜誌上設有徵友欄,同志再無需遮掩,得以砲火全開。作家何景窗曾談到:「最早期女同志交朋友的方式,就是利用《女朋友》雜誌的徵友信箱,後來女書店的筆記本也變成認識朋友的一個管道。」而《熱愛》雜誌上徵友欄服務各族群,不只男找男,還有女找女。愛人啊來相會之外,更設有尋人欄位,足以容納心情故事,有人在上頭懺情,有人張貼尋人啟事,徵友文便不只朝向未來張貼,還要向過去召喚。
除了雜誌上徵友文,九零年代報紙分類小廣告上也見玄機。時可見「男男交友聯誼社」廣告,其運作類似婚友聯誼社,繳交經費後對方會依照條件與需求配給數則聯絡電話與地址。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之間」的會員克柔所成立的「迎芳軒」成為「第一個女同志電話信箱」,以付費會員方式,提供徵友交誼。「在我們之間處理信件的過程中發現,有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五的圈內人是為了找朋友,也就是找伴,我覺得女同性戀隱藏的人口數不清,檯面下的市場無窮無盡,我嘗試以迎芳軒來賺錢,有錢才有力量,才可能達到革命最終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