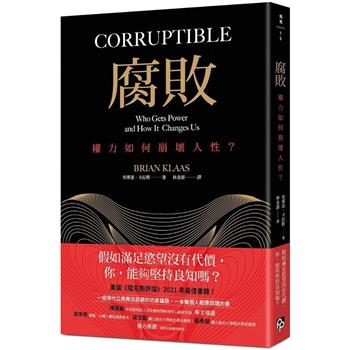第一章
引言
到底是權力使人腐化,或者腐敗的人受權力吸引?侵吞公款的企業家和殺人的警察是壞制度的必然結果,或者他們原本就是壞人?暴君是後天造就或生來如此?如果你被推上權力的寶座,中飽私囊或折磨你的敵人的新誘惑,是否會讓你心癢難耐而最終使你屈服?有點出人意料的是,我們可以從兩個被人遺忘的遙遠島嶼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遠在澳大利亞西部海岸外,有一小塊名為燈塔島(Beacon Island)的陸地勉強浮出於海面。島上覆蓋著矮小的青草,三角形的海岸線周圍是米黃色沙灘。如果你站在島上的某端,對著另一端投出棒球,它大概會落入海中。這似乎只是一座近岸處點綴著一些珊瑚,不值得注意的無人小島,但燈塔島藏著一個秘密。
一六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一艘長一百六十英尺的香料船「巴達維亞號」(Batavia)從荷蘭啟航。這艘貿易船隸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旗下的船隊,該公司帝國控制著全球貿易。「巴達維亞號」載著一大筆銀幣,準備用來交換現今印尼爪哇島上的香料和異國財富。船上有三百四十個人,其中一些是乘客,大多數是船員,還有一個心理病態的藥劑師。
船上事務按嚴明的階級制度進行規劃。「住宿條件方面,越靠近船首越簡陋。」船長在船尾處坐擁一個大艙房,他嘴裡嚼著醃肉,一面厲聲對著手下發號施令。在兩層甲板下,士兵們擠在通風不良、老鼠出沒,回程時用來儲存香料的爬行空間中。「巴達維亞號」上的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位階。
杰羅尼姆斯.科內利玆(Jeronimus Cornelisz)是比船長低幾個位階的資淺商人,一個窮困潦倒的前藥劑師。歷經一連串個人的不幸後,他在絕望之餘簽約到船上工作。啟航不久後,他著手進行一項翻身計畫。科內利玆與某位高級職員串通,密謀策劃一場叛變。他故意讓船偏離航道,準備在孤立的水域內奪取控制權。如果一切都按計畫發生,他將控制住「巴達維亞號」並展開豪奢的新生活,大肆揮霍手中的銀幣。
但事情沒有按計畫發生。
一六二九年六月四日在澳大利亞外海,「巴達維亞號」全速撞上低矮的阿布羅略斯群島(Abrolhos Islands)的珊瑚礁,木製的船身碎裂。其間沒有人發出警告,也沒有要求改變航道的呼叫。一看便知道,這艘船顯然已經在劫難逃。大多數的乘客和船員設法游到岸上。幾十個人溺斃,其他人試著攀附著「巴達維亞號」的殘骸。
船長明白除非獲得救援,否則無人能生還,他於是控制住緊急救生艇和搶救來的大部分物資。他和其他四十七個人出發前往爪哇島,其中包括領導階層的所有高級船員。他保證他們很快就會帶著救援隊回來。數百人被拋棄,沒有食物也幾乎沒有飲用水,只剩下期待某天有人回來拯救他們的一絲希望。貧瘠的島上沒有生長任何植物或棲息任何動物。情況很明顯:倖存者命在旦夕。
原本想要叛變的科內利玆也被留了下來。他已經沒有適於航海的船隻可以接管,但是他不會游泳,所以與其跳入水中、拚命地朝島上游去,站在沉沒中的「巴達維亞號」殘骸上似乎是更好的選擇。接連九天,包括科內利玆在內的七個男人佔據一片逐漸縮小的木頭乾燥區域。他們一面喝酒、一面盤算著不可避免的事。
六月十二日,「巴達維亞號」終於解體。在海浪的沖刷下,部分倖存者撞上鋒利的珊瑚而提早喪命,其餘的人不久之後跟著溺斃。科內利玆不知怎的活了下來,他最終「抓住一大塊浮木漂浮到島上,成為『巴達維亞號』的最後一名生還者」。
科內利玆來到位於現今燈塔島潮濕沙地上的避難處。在求生本能下的失序和混亂狀態,逐漸恢復成按階級和地位安排的既定秩序。雖然科內利玆被沖上岸時衣衫襤褸且虛弱,但他依舊是高級職員,意味著他是當家做主的人。「『巴達維亞號』是一個高度講求階級的社會。」歷史學家麥克.戴許(Mike Dash)說,「同樣的情況殘留在燈塔島。」受困在島上的幾百個人連忙過來幫助他們的上司。他們將會後悔這麼做,或者至少有些人會後悔。
一等到恢復健康和重振精神後,科內利玆迅速做了些盤算。情況非常惡劣:船隻失事後所剩的食物、飲水和酒維持不了多久。供給不會增加,他心想,因此必須降低需求。這些倖存者需要減少會張口吃飯的嘴。
科內利玆開始藉由消滅潛在的對手來鞏固自己的權力。有些人被派去進行有勇無謀的任務,然後被推出小船外落水溺斃。有些人被指控犯罪,這是用來判處他們死刑的藉口。可怕的處決行動確立了科內利玆的權威,同時也提供有用的忠誠測試。願意聽從科內利玆命令殺人的人,對他來說是有用的人,而拒絕聽命行事的人則是威脅。這些威脅一一被剷除,很快地,就連藉口都不需要了。為了試試看某把劍是否仍然鋒利,有一名男孩因此被斬首。兒童們無端被殺,這些殺戮都是按科內利玆的命令完成,但他本人沒有親自動手。他穿著從船上取得的華服,藉以展現他的支配力:「絲質長襪、滾上金邊的吊襪帶以及……諸如此類的裝飾品。」其他人穿著骯髒破爛的衣服等著依序被殺。第一章
引言
到底是權力使人腐化,或者腐敗的人受權力吸引?侵吞公款的企業家和殺人的警察是壞制度的必然結果,或者他們原本就是壞人?暴君是後天造就或生來如此?如果你被推上權力的寶座,中飽私囊或折磨你的敵人的新誘惑,是否會讓你心癢難耐而最終使你屈服?有點出人意料的是,我們可以從兩個被人遺忘的遙遠島嶼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遠在澳大利亞西部海岸外,有一小塊名為燈塔島(Beacon Island)的陸地勉強浮出於海面。島上覆蓋著矮小的青草,三角形的海岸線周圍是米黃色沙灘。如果你站在島上的某端,對著另一端投出棒球,它大概會落入海中。這似乎只是一座近岸處點綴著一些珊瑚,不值得注意的無人小島,但燈塔島藏著一個秘密。
一六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一艘長一百六十英尺的香料船「巴達維亞號」(Batavia)從荷蘭啟航。這艘貿易船隸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旗下的船隊,該公司帝國控制著全球貿易。「巴達維亞號」載著一大筆銀幣,準備用來交換現今印尼爪哇島上的香料和異國財富。船上有三百四十個人,其中一些是乘客,大多數是船員,還有一個心理病態的藥劑師。
船上事務按嚴明的階級制度進行規劃。「住宿條件方面,越靠近船首越簡陋。」船長在船尾處坐擁一個大艙房,他嘴裡嚼著醃肉,一面厲聲對著手下發號施令。在兩層甲板下,士兵們擠在通風不良、老鼠出沒,回程時用來儲存香料的爬行空間中。「巴達維亞號」上的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位階。
杰羅尼姆斯.科內利玆(Jeronimus Cornelisz)是比船長低幾個位階的資淺商人,一個窮困潦倒的前藥劑師。歷經一連串個人的不幸後,他在絕望之餘簽約到船上工作。啟航不久後,他著手進行一項翻身計畫。科內利玆與某位高級職員串通,密謀策劃一場叛變。他故意讓船偏離航道,準備在孤立的水域內奪取控制權。如果一切都按計畫發生,他將控制住「巴達維亞號」並展開豪奢的新生活,大肆揮霍手中的銀幣。
但事情沒有按計畫發生。
一六二九年六月四日在澳大利亞外海,「巴達維亞號」全速撞上低矮的阿布羅略斯群島(Abrolhos Islands)的珊瑚礁,木製的船身碎裂。其間沒有人發出警告,也沒有要求改變航道的呼叫。一看便知道,這艘船顯然已經在劫難逃。大多數的乘客和船員設法游到岸上。幾十個人溺斃,其他人試著攀附著「巴達維亞號」的殘骸。
船長明白除非獲得救援,否則無人能生還,他於是控制住緊急救生艇和搶救來的大部分物資。他和其他四十七個人出發前往爪哇島,其中包括領導階層的所有高級船員。他保證他們很快就會帶著救援隊回來。數百人被拋棄,沒有食物也幾乎沒有飲用水,只剩下期待某天有人回來拯救他們的一絲希望。貧瘠的島上沒有生長任何植物或棲息任何動物。情況很明顯:倖存者命在旦夕。
原本想要叛變的科內利玆也被留了下來。他已經沒有適於航海的船隻可以接管,但是他不會游泳,所以與其跳入水中、拚命地朝島上游去,站在沉沒中的「巴達維亞號」殘骸上似乎是更好的選擇。接連九天,包括科內利玆在內的七個男人佔據一片逐漸縮小的木頭乾燥區域。他們一面喝酒、一面盤算著不可避免的事。
六月十二日,「巴達維亞號」終於解體。在海浪的沖刷下,部分倖存者撞上鋒利的珊瑚而提早喪命,其餘的人不久之後跟著溺斃。科內利玆不知怎的活了下來,他最終「抓住一大塊浮木漂浮到島上,成為『巴達維亞號』的最後一名生還者」。
科內利玆來到位於現今燈塔島潮濕沙地上的避難處。在求生本能下的失序和混亂狀態,逐漸恢復成按階級和地位安排的既定秩序。雖然科內利玆被沖上岸時衣衫襤褸且虛弱,但他依舊是高級職員,意味著他是當家做主的人。「『巴達維亞號』是一個高度講求階級的社會。」歷史學家麥克.戴許(Mike Dash)說,「同樣的情況殘留在燈塔島。」受困在島上的幾百個人連忙過來幫助他們的上司。他們將會後悔這麼做,或者至少有些人會後悔。
一等到恢復健康和重振精神後,科內利玆迅速做了些盤算。情況非常惡劣:船隻失事後所剩的食物、飲水和酒維持不了多久。供給不會增加,他心想,因此必須降低需求。這些倖存者需要減少會張口吃飯的嘴。
科內利玆開始藉由消滅潛在的對手來鞏固自己的權力。有些人被派去進行有勇無謀的任務,然後被推出小船外落水溺斃。有些人被指控犯罪,這是用來判處他們死刑的藉口。可怕的處決行動確立了科內利玆的權威,同時也提供有用的忠誠測試。願意聽從科內利玆命令殺人的人,對他來說是有用的人,而拒絕聽命行事的人則是威脅。這些威脅一一被剷除,很快地,就連藉口都不需要了。為了試試看某把劍是否仍然鋒利,有一名男孩因此被斬首。兒童們無端被殺,這些殺戮都是按科內利玆的命令完成,但他本人沒有親自動手。他穿著從船上取得的華服,藉以展現他的支配力:「絲質長襪、滾上金邊的吊襪帶以及……諸如此類的裝飾品。」其他人穿著骯髒破爛的衣服等著依序被殺。
幾個月後,等到「巴達維亞號」船長帶著救援隊回來時,已經有一百多人遭到殺害。科內利玆最終嘗到他自己的島嶼正義:他獲判死刑。他被砍掉雙手並絞殺。但這個恐怖事件引發了一個令人感到不安的人性問題:倘若當時科內利玆不在船上,是否可以避免這場大屠殺?或者自然會有別人來領導他們做這件事?
燈塔島以東四千英里處,澳大利亞另一邊有一座隸屬於東加群島的荒島,名叫阿塔島(‘Ata)。一九六五年時,有六名十五至十七歲的男孩逃出寄宿學校,他們偷了一艘漁船向北航行。第一天他們只前進了五英里就決定下錨休息過夜。在他們試著入睡時,一陣暴風劇烈地搖晃他們那艘長二十四英尺的船,結果扯起船錨。超級強風很快就吹壞船帆,還摧毀掉船舵。等到天亮時,男孩們無法操縱船隻,也無法航行,只能隨著洋流漂浮。他們連續八天沿著海岸向南前進,完全不知道回家的方向。
當這六名青少年開始失去希望時,他們望見遠方有一片隱約的綠意。那是阿塔島,一座植被濃密的崎嶇島嶼。他們駕駛那艘只能有限度操縱的受損漁船,等到漂近岸邊時便棄船游泳上岸。在被沖進無情的汪洋之前,這是他們最後的機會。他們終於成功上岸,雖然被岩石割傷,但活了下來。
阿塔島周圍的峭壁使得登島變得困難,沒想到卻成為遭遇船難的男孩的生存助力。鋸齒狀的岩石是海鳥築巢棲息的完美場所,他們開始合作架設陷阱捕鳥。由於找不到淡水,他們只能隨機應變吸食海鳥血液。在新家四處搜尋後,他們升級到以椰子水解渴。最終他們的三餐從生食變成熟食,因為他們生起第一把火。男孩們商量好必須使餘火持續燃燒,絕不能讓它熄滅。他們於是輪流看顧餘火,一天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這條生命線讓他們得以烹煮魚肉、海鳥和甚至烏龜。
在通力合作下,男孩們的生活水準進一步提升。他們接連四天合力從島上大樹的根部一滴滴收集淡水。他們挖空樹幹來蒐集雨水,還用棕櫚葉搭建出一間簡陋的房屋。他們每件事都分工合作,沒有人當領導者。沒有鑲金邊的裝飾和長襪、沒有大聲下達的命令、沒有為了鞏固權力而策劃的陰謀,也沒有殺人事件。當他們征服這座島嶼時,成功和失敗都由大家平均分擔。
遭遇船難六個月後,當中一名男孩特維塔.法泰.拉杜(Tevita Fatai Latu)在每日例行獵捕海鳥時滑倒,結果摔斷了腿。其他五名男孩連忙過來幫助他,利用傳統東加方法,烤熱椰子樹莖製作出夾板,將骨頭固定復位。接下來的四個月,特維塔無法走路,但其他男孩一直照顧他,直到他能再度處理日常瑣事。
他們不時發生爭執。(六個人整天形影不離,菜單是一成不變的海鳥和烏龜肉,難免讓人偶爾脾氣失控。)然而一旦爆發衝突,男孩們會識相地分開。意見嚴重分歧的男孩會各自待在島上的不同地點,有時長達兩天,直到他們冷靜下來,可以再度合作求生存。過了一年多後,他們開始體認到這種新生活不是暫時的,因此得有長期安頓下來的打算,他們藉由製作粗陋的網球拍和舉行比賽、安排拳擊賽和一起健身來度日。為了避免耗盡海鳥存糧,他們同意限制每人每天的食物量並開始嘗試種植野生豆子。
在男孩們遭遇船難十五個月後,一個名叫彼得.華納(Peter Warner)的澳洲人開著他的漁船找尋捕捉螯蝦的地點。當他靠近一座無人居住的島嶼時,他發現一件不尋常的事。「我注意到峭壁上有燒焦的痕跡,這在熱帶地區並不尋常,因為在那麼潮濕的大氣環境中,不可能引發叢林野火。」現年八十九歲的華納回想。接下來,他看見令人驚奇的景象,一位留著十五個月的長髮的裸體男孩。男孩們大聲吶喊並揮舞著棕櫚葉,希望引起這艘船的注意。當船靠得夠近時,男孩們跳進海中,開始游向他們從沒想到會出現的救星。華納不確定發生了什麼事,他不知道這些男孩是否是被放逐到島上的囚犯,這項懲罰專門留給玻里尼西亞社會中最壞的壞蛋。「見到這些沒穿衣服、沒理髮,看起來健康的青少年,我有點驚慌。」他告訴我。華納將步槍裝上子彈,嚴陣以待。
當男孩來到船上時,他們客氣地解釋自己的身分。華納沒聽說有任何男孩失蹤,於是用無線電聯絡接線生,要他打電話到男孩在東加的學校證實他們的說法。二十分鐘後,流著淚的接線生告知華納,這些被認為已經死亡的男孩失蹤了一年多。「他們的葬禮已經舉行過。」接線生說。男孩被帶回東加與家人團圓。在他們獲救後,當中年紀最大的席歐內.法圖阿(Sione Fataua)說起他對生還返家的焦慮:「我們當中的幾個人有女朋友。或許她們已經不記得我們?」
如同荷蘭歷史學家羅格.布萊格曼(Rutger Bregman)所言,「真正的《蒼蠅王》是關於友誼和忠誠的故事,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如果能夠依賴彼此,我們會更加強大。」華納依舊定期和其中一位遭遇船難的男孩一起航海,他認為這整起事件「大大展現人性光輝」。
兩座荒島、兩種互相牴觸的人性洞察。其一,一個渴望權力的人鞏固對別人的控制,以便剝削和殺害他們。其二,講求平等的團隊合作佔上風,合作成為最高的原則。我們要如何解釋其間的差異?
燈塔島有結構、有秩序、有等級,最終釀成悲劇。另一方面,阿塔島到處是崎嶇聳立的岩石,但男孩們在十五個月裡所雕鑿出來的社會卻是一片平坦。兩個衝突的荒島故事引發不同的問題。我們是否因為壞人或壞的階級制度而注定被剝削?為什麼這世界上似乎有許多像科內利玆這樣的領導者在掌權,而像阿塔島男孩的人卻何其地少?
還有,如果你和同事被困在荒島上,你是否會推翻老闆,像東加男孩那樣平等合作來解決問題?或者像在燈塔島上,以血腥的方式奪取權力和支配力?你會怎麼做?
本書回答四個主要的問題。
第一,是否比較壞的人會獲得權力?
第二,權力是否使人變得更壞?
第三,我們為什麼讓那些顯然不該掌權的人控制我們?
第四,我們如何確保讓不會腐化的人掌權,並公正地行使權力?
過去十年來,我一直在世界各地研究這些問題,從白俄羅斯到英國、從象牙海岸到美國加州、泰國到突尼西亞以及澳大利亞到尚比亞。作為政治科學家的部分研究,我訪談了不同的人——主要是濫用他們的權力做壞事的壞人。我會晤教派領導者、戰犯、暴君、政變策劃者、刑求者、雇佣兵、將軍、鼓吹者、造反者、貪污的執行長以及被定罪的罪犯。我試著釐清是什麼讓他們發揮作用。了解他們,以及研究他們所處的體制——是阻止他們的關鍵。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瘋狂且殘忍,有些則仁慈和具有同情心。但他們有一個共通的特點:他們行使巨大的權力。
當你和一個犯下戰爭罪的叛軍指揮官握手,或者與折磨敵人、冷血無情的暴君共進早餐時,你會訝異於他們鮮少符合諷刺漫畫中的邪惡形象。他們往往很有魅力,會開玩笑且面露笑容。他們乍看之下並不像怪物,但有許多確實是惡人。
年復一年,我努力想解開這些揮之不去的謎題。刑求者和戰犯是否是全然不同的類型,或者他們只是我們偶爾會在辦公室或鄰里中遇見的小暴君的極端加強版?未來的惡人是否就藏身在我們之中?在適當的條件下,是否任何人都有可能變成惡人?果真如此的話,那麼我們從嗜殺的暴君身上所學到的教訓,能否用來減少社會上較小規模的濫權問題。這是一個尤其迫切需要解決的謎題,因為當權者不斷地令我們失望。當你告訴別人你是一個政治科學家,他們接下來往往會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有這麼多糟糕的人在掌權?」
但另一個謎題持續要求我們給予解答:這些人是否因為握有權力而變得糟糕?我自己也心存疑惑。另一個可能性在困擾著我:因為權力而變得更壞的人,他們是否只是冰山的一角。或許有更龐大、更嚴重的問題潛伏在波濤下,等待被發現,等著我們去解決。
讓我們先從傳統觀念說起。每個人都聽說過「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化」這句名言。大家普遍相信這句話,但事實是否果真如此?
幾年前我走訪了馬達加斯加,那是非洲海岸外一個紅土漫布的島嶼。人人都知道馬達加斯加有可愛的環尾狐猴,但它同樣也是一個有趣物種的產地:腐敗的政治人物。馬達加斯加主要由無賴統治,他們從地球上最貧窮的三千萬人身上榨取利益。在馬達加斯加,一份拿鐵咖啡加鬆餅就得花光一般人整週的所得。雪上加霜的是,有錢人往往剝削窮人。我在那裡遇見了馬達加斯加最富有的人之一:島上的優酪乳大亨拉瓦盧馬納納(Marc Ravalomanana)。
拉瓦盧馬納納出身貧寒。為了幫助家計,五歲的他會提著幾籃水田芥,向搭火車路過學校的乘客兜售。某天他交上意想不到的好運:鄰居送給他一輛腳踏車。年幼的拉瓦盧馬納納於是開始騎車到附近的農場,索討剩餘的牛奶並將它們變成自製的優酪乳。在生意剛起步時,他便試著回饋貧困的社區。他在當地教會當志工,或者在唱詩班裡唱歌,除此之外便是騎著那輛搖搖晃晃的破單車,一路叫賣優酪乳,一罐又一罐、年復一年發展出他的事業。
幾個月後,等到「巴達維亞號」船長帶著救援隊回來時,已經有一百多人遭到殺害。科內利玆最終嘗到他自己的島嶼正義:他獲判死刑。他被砍掉雙手並絞殺。但這個恐怖事件引發了一個令人感到不安的人性問題:倘若當時科內利玆不在船上,是否可以避免這場大屠殺?或者自然會有別人來領導他們做這件事?
燈塔島以東四千英里處,澳大利亞另一邊有一座隸屬於東加群島的荒島,名叫阿塔島(‘Ata)。一九六五年時,有六名十五至十七歲的男孩逃出寄宿學校,他們偷了一艘漁船向北航行。第一天他們只前進了五英里就決定下錨休息過夜。在他們試著入睡時,一陣暴風劇烈地搖晃他們那艘長二十四英尺的船,結果扯起船錨。超級強風很快就吹壞船帆,還摧毀掉船舵。等到天亮時,男孩們無法操縱船隻,也無法航行,只能隨著洋流漂浮。他們連續八天沿著海岸向南前進,完全不知道回家的方向。
當這六名青少年開始失去希望時,他們望見遠方有一片隱約的綠意。那是阿塔島,一座植被濃密的崎嶇島嶼。他們駕駛那艘只能有限度操縱的受損漁船,等到漂近岸邊時便棄船游泳上岸。在被沖進無情的汪洋之前,這是他們最後的機會。他們終於成功上岸,雖然被岩石割傷,但活了下來。
阿塔島周圍的峭壁使得登島變得困難,沒想到卻成為遭遇船難的男孩的生存助力。鋸齒狀的岩石是海鳥築巢棲息的完美場所,他們開始合作架設陷阱捕鳥。由於找不到淡水,他們只能隨機應變吸食海鳥血液。在新家四處搜尋後,他們升級到以椰子水解渴。最終他們的三餐從生食變成熟食,因為他們生起第一把火。男孩們商量好必須使餘火持續燃燒,絕不能讓它熄滅。他們於是輪流看顧餘火,一天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這條生命線讓他們得以烹煮魚肉、海鳥和甚至烏龜。
在通力合作下,男孩們的生活水準進一步提升。他們接連四天合力從島上大樹的根部一滴滴收集淡水。他們挖空樹幹來蒐集雨水,還用棕櫚葉搭建出一間簡陋的房屋。他們每件事都分工合作,沒有人當領導者。沒有鑲金邊的裝飾和長襪、沒有大聲下達的命令、沒有為了鞏固權力而策劃的陰謀,也沒有殺人事件。當他們征服這座島嶼時,成功和失敗都由大家平均分擔。
遭遇船難六個月後,當中一名男孩特維塔.法泰.拉杜(Tevita Fatai Latu)在每日例行獵捕海鳥時滑倒,結果摔斷了腿。其他五名男孩連忙過來幫助他,利用傳統東加方法,烤熱椰子樹莖製作出夾板,將骨頭固定復位。接下來的四個月,特維塔無法走路,但其他男孩一直照顧他,直到他能再度處理日常瑣事。
他們不時發生爭執。(六個人整天形影不離,菜單是一成不變的海鳥和烏龜肉,難免讓人偶爾脾氣失控。)然而一旦爆發衝突,男孩們會識相地分開。意見嚴重分歧的男孩會各自待在島上的不同地點,有時長達兩天,直到他們冷靜下來,可以再度合作求生存。過了一年多後,他們開始體認到這種新生活不是暫時的,因此得有長期安頓下來的打算,他們藉由製作粗陋的網球拍和舉行比賽、安排拳擊賽和一起健身來度日。為了避免耗盡海鳥存糧,他們同意限制每人每天的食物量並開始嘗試種植野生豆子。
在男孩們遭遇船難十五個月後,一個名叫彼得.華納(Peter Warner)的澳洲人開著他的漁船找尋捕捉螯蝦的地點。當他靠近一座無人居住的島嶼時,他發現一件不尋常的事。「我注意到峭壁上有燒焦的痕跡,這在熱帶地區並不尋常,因為在那麼潮濕的大氣環境中,不可能引發叢林野火。」現年八十九歲的華納回想。接下來,他看見令人驚奇的景象,一位留著十五個月的長髮的裸體男孩。男孩們大聲吶喊並揮舞著棕櫚葉,希望引起這艘船的注意。當船靠得夠近時,男孩們跳進海中,開始游向他們從沒想到會出現的救星。華納不確定發生了什麼事,他不知道這些男孩是否是被放逐到島上的囚犯,這項懲罰專門留給玻里尼西亞社會中最壞的壞蛋。「見到這些沒穿衣服、沒理髮,看起來健康的青少年,我有點驚慌。」他告訴我。華納將步槍裝上子彈,嚴陣以待。
當男孩來到船上時,他們客氣地解釋自己的身分。華納沒聽說有任何男孩失蹤,於是用無線電聯絡接線生,要他打電話到男孩在東加的學校證實他們的說法。二十分鐘後,流著淚的接線生告知華納,這些被認為已經死亡的男孩失蹤了一年多。「他們的葬禮已經舉行過。」接線生說。男孩被帶回東加與家人團圓。在他們獲救後,當中年紀最大的席歐內.法圖阿(Sione Fataua)說起他對生還返家的焦慮:「我們當中的幾個人有女朋友。或許她們已經不記得我們?」
如同荷蘭歷史學家羅格.布萊格曼(Rutger Bregman)所言,「真正的《蒼蠅王》是關於友誼和忠誠的故事,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如果能夠依賴彼此,我們會更加強大。」華納依舊定期和其中一位遭遇船難的男孩一起航海,他認為這整起事件「大大展現人性光輝」。
兩座荒島、兩種互相牴觸的人性洞察。其一,一個渴望權力的人鞏固對別人的控制,以便剝削和殺害他們。其二,講求平等的團隊合作佔上風,合作成為最高的原則。我們要如何解釋其間的差異?
燈塔島有結構、有秩序、有等級,最終釀成悲劇。另一方面,阿塔島到處是崎嶇聳立的岩石,但男孩們在十五個月裡所雕鑿出來的社會卻是一片平坦。兩個衝突的荒島故事引發不同的問題。我們是否因為壞人或壞的階級制度而注定被剝削?為什麼這世界上似乎有許多像科內利玆這樣的領導者在掌權,而像阿塔島男孩的人卻何其地少?
還有,如果你和同事被困在荒島上,你是否會推翻老闆,像東加男孩那樣平等合作來解決問題?或者像在燈塔島上,以血腥的方式奪取權力和支配力?你會怎麼做?
本書回答四個主要的問題。
第一,是否比較壞的人會獲得權力?
第二,權力是否使人變得更壞?
第三,我們為什麼讓那些顯然不該掌權的人控制我們?
第四,我們如何確保讓不會腐化的人掌權,並公正地行使權力?
過去十年來,我一直在世界各地研究這些問題,從白俄羅斯到英國、從象牙海岸到美國加州、泰國到突尼西亞以及澳大利亞到尚比亞。作為政治科學家的部分研究,我訪談了不同的人——主要是濫用他們的權力做壞事的壞人。我會晤教派領導者、戰犯、暴君、政變策劃者、刑求者、雇佣兵、將軍、鼓吹者、造反者、貪污的執行長以及被定罪的罪犯。我試著釐清是什麼讓他們發揮作用。了解他們,以及研究他們所處的體制——是阻止他們的關鍵。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瘋狂且殘忍,有些則仁慈和具有同情心。但他們有一個共通的特點:他們行使巨大的權力。
當你和一個犯下戰爭罪的叛軍指揮官握手,或者與折磨敵人、冷血無情的暴君共進早餐時,你會訝異於他們鮮少符合諷刺漫畫中的邪惡形象。他們往往很有魅力,會開玩笑且面露笑容。他們乍看之下並不像怪物,但有許多確實是惡人。
年復一年,我努力想解開這些揮之不去的謎題。刑求者和戰犯是否是全然不同的類型,或者他們只是我們偶爾會在辦公室或鄰里中遇見的小暴君的極端加強版?未來的惡人是否就藏身在我們之中?在適當的條件下,是否任何人都有可能變成惡人?果真如此的話,那麼我們從嗜殺的暴君身上所學到的教訓,能否用來減少社會上較小規模的濫權問題。這是一個尤其迫切需要解決的謎題,因為當權者不斷地令我們失望。當你告訴別人你是一個政治科學家,他們接下來往往會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有這麼多糟糕的人在掌權?」
但另一個謎題持續要求我們給予解答:這些人是否因為握有權力而變得糟糕?我自己也心存疑惑。另一個可能性在困擾著我:因為權力而變得更壞的人,他們是否只是冰山的一角。或許有更龐大、更嚴重的問題潛伏在波濤下,等待被發現,等著我們去解決。
讓我們先從傳統觀念說起。每個人都聽說過「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化」這句名言。大家普遍相信這句話,但事實是否果真如此?
幾年前我走訪了馬達加斯加,那是非洲海岸外一個紅土漫布的島嶼。人人都知道馬達加斯加有可愛的環尾狐猴,但它同樣也是一個有趣物種的產地:腐敗的政治人物。馬達加斯加主要由無賴統治,他們從地球上最貧窮的三千萬人身上榨取利益。在馬達加斯加,一份拿鐵咖啡加鬆餅就得花光一般人整週的所得。雪上加霜的是,有錢人往往剝削窮人。我在那裡遇見了馬達加斯加最富有的人之一:島上的優酪乳大亨拉瓦盧馬納納(Marc Ravalomanana)。
拉瓦盧馬納納出身貧寒。為了幫助家計,五歲的他會提著幾籃水田芥,向搭火車路過學校的乘客兜售。某天他交上意想不到的好運:鄰居送給他一輛腳踏車。年幼的拉瓦盧馬納納於是開始騎車到附近的農場,索討剩餘的牛奶並將它們變成自製的優酪乳。在生意剛起步時,他便試著回饋貧困的社區。他在當地教會當志工,或者在唱詩班裡唱歌,除此之外便是騎著那輛搖搖晃晃的破單車,一路叫賣優酪乳,一罐又一罐、年復一年發展出他的事業。
到了一九九○年代後期,拉瓦盧馬納納已經成為馬達加斯加的乳品業大亨,島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二○○二年,他成為拉瓦盧馬納納總統,在幾乎每個人都一窮二白的國家,身為精明的政治人物,他深諳白手起家的故事具有何等價值。擔任總統的拉瓦盧馬納納承諾帶來改變,起初,他履行了諾言。他的政府投資興建道路、取締貪污並以超高的經濟成長率根除貧窮。馬達加斯加變成全世界成長最快速的經濟體之一。這似乎是個成功的寓言故事,一個出身寒微的好人排除萬難,成為明智公正的統治者。
我決定去拜訪拉瓦盧馬納納。當我來到他那有如宮殿般的宅第時,他正穿著滾上白條紋的海軍藍Nike運動服走出前門。他滿面笑容地握住我的手,領著我入內。他帶我參觀他的訓練室,他從早上五點開始就一直在這裡做健身操。(「這是讓你保持敏銳的心智,以便做出重大決定的唯一辦法。」他告訴我。)接著他指向一座用來敬拜耶穌、裝飾華麗的定製神龕,這是某種火車模型版的伯利恆,上面有一具巨大的木製十字架俯臨著微型化的城鎮。我們走上樓,來到走廊盡頭時,他打開兩扇桃花心木製的大門。一張巨大的桌子出現在門後。桌面上擺滿食物、成堆的熱可頌麵包、以各種方式烹製的蛋、五種果汁,以及足夠餵飽他兒時村莊整整一星期的優酪乳。兜售水田芥的貧苦生活早已離他遠去。
儘管有拉瓦盧馬納納的幕僚長陪著我們,但只安排了兩個座位,一個給他,一個給我。我坐了下來,打開筆記本,伸手要拿筆,這才發現我忘了帶筆。
「沒問題。」拉瓦盧馬納納說,「我們或許貧窮,但並不缺筆。」他拿起叉子旁的小鈴鐺搖了起來。幾秒鐘後,兩名員工衝進房間,每個都希望搶先來到桌子旁。
「筆。」拉瓦盧馬納納厲聲說。
兩人匆忙離去,三十秒後回來,手上各抓著一支嶄新的原子筆,搶著得到讚美。動作比較慢、沒有獲得讚美的那個人看起來情緒低落。
這時拉瓦盧馬納納開始辦正事。他準備要在下次選舉中奪回總統寶座。他熱切地看著我。
「我從Google上得知你當過競選顧問。」他說,「告訴我,我應該怎麼做才能贏得選舉?」
這個問題讓我猝不及防。我去那裡是為了研究他,而不是當競選顧問。但我想要建立交情,只好臨場發揮。「我在明尼蘇達州幫忙處理州長競選活動時,我們想出一種有效的招數。我們在八十七天內走訪了全部八十七個郡,以顯示我們關心整個明尼蘇達州。馬達加斯加總共有一百十九個區,你不妨在一百十九天內走訪完這一百十九個區?」
他點點頭,示意我繼續說下去。
「你可以利用這個下鄉行程,搭配你的白手起家形象。你只需騎著腳踏車到每個城鎮,提醒人們你曾有過販售優酪乳的童年,藉以顯示你了解貧窮的滋味。」他點點頭,轉身對他的幕僚長說,「去買一百十九輛腳踏車。」
到了一九九○年代後期,拉瓦盧馬納納已經成為馬達加斯加的乳品業大亨,島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二○○二年,他成為拉瓦盧馬納納總統,在幾乎每個人都一窮二白的國家,身為精明的政治人物,他深諳白手起家的故事具有何等價值。擔任總統的拉瓦盧馬納納承諾帶來改變,起初,他履行了諾言。他的政府投資興建道路、取締貪污並以超高的經濟成長率根除貧窮。馬達加斯加變成全世界成長最快速的經濟體之一。這似乎是個成功的寓言故事,一個出身寒微的好人排除萬難,成為明智公正的統治者。
我決定去拜訪拉瓦盧馬納納。當我來到他那有如宮殿般的宅第時,他正穿著滾上白條紋的海軍藍Nike運動服走出前門。他滿面笑容地握住我的手,領著我入內。他帶我參觀他的訓練室,他從早上五點開始就一直在這裡做健身操。(「這是讓你保持敏銳的心智,以便做出重大決定的唯一辦法。」他告訴我。)接著他指向一座用來敬拜耶穌、裝飾華麗的定製神龕,這是某種火車模型版的伯利恆,上面有一具巨大的木製十字架俯臨著微型化的城鎮。我們走上樓,來到走廊盡頭時,他打開兩扇桃花心木製的大門。一張巨大的桌子出現在門後。桌面上擺滿食物、成堆的熱可頌麵包、以各種方式烹製的蛋、五種果汁,以及足夠餵飽他兒時村莊整整一星期的優酪乳。兜售水田芥的貧苦生活早已離他遠去。
儘管有拉瓦盧馬納納的幕僚長陪著我們,但只安排了兩個座位,一個給他,一個給我。我坐了下來,打開筆記本,伸手要拿筆,這才發現我忘了帶筆。
「沒問題。」拉瓦盧馬納納說,「我們或許貧窮,但並不缺筆。」他拿起叉子旁的小鈴鐺搖了起來。幾秒鐘後,兩名員工衝進房間,每個都希望搶先來到桌子旁。
「筆。」拉瓦盧馬納納厲聲說。
兩人匆忙離去,三十秒後回來,手上各抓著一支嶄新的原子筆,搶著得到讚美。動作比較慢、沒有獲得讚美的那個人看起來情緒低落。
這時拉瓦盧馬納納開始辦正事。他準備要在下次選舉中奪回總統寶座。他熱切地看著我。
「我從Google上得知你當過競選顧問。」他說,「告訴我,我應該怎麼做才能贏得選舉?」
這個問題讓我猝不及防。我去那裡是為了研究他,而不是當競選顧問。但我想要建立交情,只好臨場發揮。「我在明尼蘇達州幫忙處理州長競選活動時,我們想出一種有效的招數。我們在八十七天內走訪了全部八十七個郡,以顯示我們關心整個明尼蘇達州。馬達加斯加總共有一百十九個區,你不妨在一百十九天內走訪完這一百十九個區?」
他點點頭,示意我繼續說下去。
「你可以利用這個下鄉行程,搭配你的白手起家形象。你只需騎著腳踏車到每個城鎮,提醒人們你曾有過販售優酪乳的童年,藉以顯示你了解貧窮的滋味。」他點點頭,轉身對他的幕僚長說,「去買一百十九輛腳踏車。」
拉瓦盧馬納納對於如何出奇制勝打贏選戰並不陌生,他對打破規則也無所顧忌。二○○六年時,他雖然佔有再度當選的優勢,但他不願意冒任何風險。他運用了一個新奇的手法來操縱選舉:他迫使他的主要對手被流放,然後阻止他返回家鄉登記參選。每當他的對手設法想回到馬達加斯加,拉瓦盧馬納納就拿起電話,下令關閉島上所有機場,導致對手所搭乘的飛機掉頭返航。這個辦法奏效了。由於這個對手不准從海外登記參選,所以不在候選人名單中。拉瓦盧馬納納於是大獲全勝。
二○○八年,拉瓦盧馬納納,一個出身寒微,參加教堂唱詩班和當過慈善志工的人——變得貪婪。在掌權六年後,他的內心似乎已經被某種事物改變。在一個每人年平均所得只有幾百美元的國家,他花費六千萬美元的國家基金購買了一架總統專機(有點野心勃勃地命名為「空軍二號」)。他設法將這架飛機的牌照登記在自己名下,而非馬達加斯加政府。拉瓦盧馬納納年復一年地掌握權力,他腐化的程度似乎越來越嚴重。
最終這將證明是他垮台的原因。二○○九年,一名暴發的廣播節目主持人轉行從政,他組織了抗議拉瓦盧馬納納總統的活動。這位前主持人在廣播節目中慫恿和平抗議者遊行到總統府。在他們到達時,保護優酪乳大亨的士兵朝他們開火。數十人被射死,激起人們的憤怒。街道上的血跡剛被清洗掉不久,拉瓦盧馬納納便在政變中被推翻,接管政府的軍方擁立這位主持人上台。
或許傳統看法是對的:權力確實使人腐化。五歲時的拉瓦盧馬納納只夢想著從兜售水田芥晉級到販賣優酪乳,他規規矩矩地做生意,為人並不殘暴。他幫助的是別人而非自己。但掌控馬達加斯加似乎改變了他,使他變得更壞。但這或許不是拉瓦盧馬納納的錯。那位廣播節目主持人總統最終可能變得比他所取代的乳品業大亨更腐敗。假使你或我突然被擁立為這個以貪腐而聞名的島國總統,我們也可能會墮落。這只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然而傳統觀念有時錯得離譜。假使權力並不會讓我們變得更好或更壞呢?假使權力只吸引某些類型的人——而那些人恰恰是不應該掌權的人?也許最想要權力的人正好是最不適合掌握權力的人。也許渴望權力的人比較容易墮落。
如果你曾閱讀通俗的心理學書籍,你很可能聽說過一個惡名昭彰的研究,這個研究似乎暗示權力確實使人腐化。只是有個問題:關於這個研究,你以為你知道的一切其實是錯的。
一九七一年暮夏,史丹佛大學的研究者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心理學系的地下室搭建一座模擬監獄。他招募了十八名大學生參與一項準科學研究,目的在判定社會角色是否會改變一般人的行為到不像話的程度。這個假說相當簡單:人類行為變化莫測。我們會配合我們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說我們所穿的制服。
為了測試這個假說是否為真,津巴多隨機指派其中九名自願參與者為「守衛」,其他九名參與者則成為「囚犯」。為了為期兩週、每天十五美元的報酬,他們必須進行一場過於真實的刑事司法角色扮演。接下來發生的事,如今變得惡名昭彰。守衛幾乎立刻開始虐待囚犯。他們用滅火器攻擊囚犯,拿走囚犯的床墊並強迫他們睡在混凝土地板上。扮演守衛的大學生剝光同儕的衣服,只為了顯示誰是老大。權力似乎使他們變得可怕。
在喪失人身控制權後,原本自豪、外向開朗的大學生變得封閉保守和順從。一名守衛在虐待完他的大學同儕後,命令囚犯排好隊以便羞辱他們。
「以後我說什麼,你就做什麼。」
「謝謝你,矯正官。」一名囚犯回答。
「再說一遍。」
「謝謝你,矯正官。」
「說『上帝保佑你,矯正官』。」
「上帝保佑你,矯正官。」
這項研究原本要持續進行兩個星期,但當津巴多的女朋友來探訪這座模擬監獄,她被所目睹的境況給嚇壞了,六天後,她說服津巴多停止了實驗。研究結果發表之後,舉世震驚。有人為此製作紀錄片,也有人寫書。證據似乎相當明確:權力能召喚出我們每個人心中的惡魔。
但這當中藏了一個圈套。看似直截了當的史丹佛監獄實驗故事,不是這麼清楚明白——這已成為心理學的傳統看法。守衛之中只有一些人濫用權力。有些守衛拒絕濫用權力,並給予大學生囚犯尊重的對待。因此,即便權力真的使人腐化,是否有人比其他人更加不受影響?
此外,如今有些囚犯和守衛表示,他們當年只是在進行表演。他們相信研究人員想要看見一場表演,於是便給他們一場表演。近來被揭露的實驗準備階段錄音,已經讓人質疑這些參與者是否因為受到指示而對囚犯苛刻,並非自然而然變卑鄙。因此,情況比我們被引導去相信的還要撲朔迷離些。
但即便有這些提醒,這個實驗仍然教人感到心寒。一般人如果在合適的環境下,是否都有可能變得殘酷和邪惡?一旦我們控制了別人,我們是否全都是等著被揭下面具的虐待狂?
幸好答案可能不是如此。津巴多的結論並沒有考慮到該研究的一個重要層面:參與者的招募方式。研究人員為了找來囚犯和守衛,在當地報紙刊登了以下的廣告:
徵求男性大學生參與監獄生活的心理學研究。自八月十四日起,為期一至兩週,每日報酬十五美元。欲知詳情與應徵,請洽……
二○○七年,西肯塔基大學的研究人員注意到廣告中似乎微不足道的細節。他們感到納悶,這是否已經不慎使該研究產生偏差。為了找出答案,他們複製了這則廣告,只將十五美元改成七十美元(因應一九七○年代以來的通貨膨脹所作的調整)。除此之外,更新後的廣告中每個字都一模一樣。後來,他們又創造一個新廣告,除了一個關鍵的差異,其他部分都相同:「參與監獄生活的心理學研究」改成「參與心理學研究」。他們在某些大學城放置「監獄生活」廣告,在其他大學城放置「心理研究」廣告。其概念是讓一組人自願參加監獄實驗,而另一組參加一般心理學研究。回應這兩則廣告的人會有什麼差異嗎?
招募期結束後,研究人員要求未來的研究參與者接受心理篩選和徹底的人格評估。他們的發現十分驚人。相較於回應一般心理學研究廣告的人,那些回應監獄實驗廣告的人在「侵略性、獨裁主義、馬基維利主義、自戀和社會優勢」的測量項目獲得相當高的分數,而在「同理心和利他主義傾向項目的得分明顯偏低」。只不過是在廣告中包含了監獄這個用語,結果便招來不成比例的一批殘酷成性的學生。
這個發現可能翻轉了史丹佛監獄實驗的結論,在根本上改變我們對權力的了解。史丹佛監獄實驗並沒有證明被賦予權力的一般人會變得殘酷,而是可能證明了殘酷成性的人會尋求權力。或許我們倒因為果。或許權力只是一塊吸引壞人的磁鐵,而非使好人變壞的一種力量。依此構想,權力不會使人腐化——它吸引腐敗者。
但仍有另一個謎。即便不適合掌權的人被權力吸引,他們為何似乎很容易獲得權力?畢竟在現代社會中,大量的控制不是奪取來的,而是被給予。執行長不必與中階經理進行格鬥士般的戰鬥,就能進駐邊間辦公室。懦夫和腐敗的政客,至少在民主政體中,需要一般大眾支持他們掌權。近來所揭露關於史丹佛監獄實驗的事,提升了壞人受權力吸引的可能性。但我們又為什麼容易因為錯誤的理由,而將權力交給不對的人?
二○○八年,瑞士研究人員進行一項實驗來測試這個假說。他們招募了六百八十一名當地兒童,年齡介於五歲到十三歲之間。這些孩童被要求玩一個電腦模擬遊戲,他們必須為一艘即將出航的船做出相關的決定。每個孩童都得依據出現在螢幕上的兩張臉,為他們的數位船挑選一位船長。此外沒有其他資料。如此的設計是為了迫使這些孩童決定:對你而言誰看起來像是個好船長?誰似乎可以成為你想像中的船隻的有效領導者?
孩子們不知道的是,這兩個可能的船長人選並不是隨機搭配。他們是最近在法國國會選舉中競選的政治人物。成對的臉隨機分配給這些孩童,但他們所看見的每一對組合都包含了勝選者和第二高票。研究的結果相當驚人:孩子們挑選出來的船長,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一的機率是贏得選舉的候選人。當研究人員改以成人為對象,進行相同的實驗時,他們驚訝地發現近乎相同的結果。研究結果有兩方面值得我們注意。首先,連兒童都能光憑長相就準確辨識出勝選者,突顯出我們對於領導潛力的評估方式是多麼膚淺。第二,在挑選掌權者時,兒童和成人的認知歷程並無根本上的差異。此事賦予憑表象(at face value)相信人這個片語新的意義。進一步的證據指出,我們挑選領導者的能力是有問題的,其他幾項研究也顯示在群體討論中,更具攻擊性或表現粗野的人會被視為比更樂意合作或更溫順的人,看起來更有權力和更像領導者。
沒錯,事情越變越複雜。權力可能使好人腐化,但也可能吸引壞人。身為人類,不知怎的我們似乎因為壞的理由而被壞的領導者吸引。
不幸的是,這種複雜性才只是起點,還有另一個需要考量的難題。假使掌權者之所以做壞事,並非因為他們原本就是壞人,不是因為得到權力之後變壞,而是因為他們受困於壞的體制呢?這個想法非常有道理。畢竟奉公守法可能會讓你在挪威晉升,但保證你永遠無法在烏茲別克獲得權力。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某些位高權重者是真正的了不起——他們一心幫助別人而非幫助自己。因此權力的誘惑和掌握權力的影響可能得視背景而定。幸好,背景和體制是可以改變的。這帶給我們一些好消息:或許我們不是注定要活在一個無法避免科內利玆式濫權領導的世界。
在印度班加羅爾(Bangalore)所進行的研究為上述的樂觀看法提供了一些證據。研究人員想看看什麼類型的人會被公職吸引,當地公家部門是以貪污受賄而聞名。印度文官提供了合適的試驗場,因為他們的貪污腐敗可謂惡名昭彰。人人都知道在班加羅爾當公務員有機會獲得灰色收入。在這個由兩位經濟學家所設計的實驗中,數百名大學生被要求投標準的骰子四十二次並記錄結果。當然,投骰子的結果全憑運氣。然而在投骰子之前,他們被告知如果他們運氣好,投出更高的點數,會獲得更多報酬。投出更多的四點、五點和六點可以賺到更多現金。
但由於結果是自行報告,學生可以謊報他們投骰子的結果。許多人的確這麼做。投出六點的次數佔百分之二十五,而一點只有百分之十。藉由統計分析,研究人員可以確定,如此偏差的結果不可能是因為運氣。有些學生甚至厚顏無恥地宣稱他們接連投出四十二次的六點。但這些數據透露出蹊蹺:在實驗中作弊的學生,他們的職業志向不同於誠實記錄的學生。比起一般學生,自行報告出造假的高點數的學生,有更多人表示他們想要加入腐敗的印度文官體系。
丹麥的另一組研究人員也做了類似的實驗——這個國家的文官體系乾淨且透明,卻獲得相反的結果。誠實地自行報告點數的學生更想要擔任公務員,而說謊的學生尋求能讓他們以骯髒手段致富的職業。腐敗的體制吸引腐敗的學生,誠實的體制吸引誠實的學生。或許這無關權力使人改變,而是與背景有關。好的體制能創造出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追求權力的良性循環。壞的體制則創造出讓人們為了爬到最高位,樂於說謊、欺騙和偷竊的惡性循環。如果這是事實,那麼我們應該關切的不是掌握權力的個人,而是修補不健全的體制。
關於這些惱人的複雜謎題,我們有一系列可能的解答。第一,權力讓人變得更壞——權力使人腐化。水田芥變成優酪乳帝國,在你還會意不過來之前,你已經匆匆投入選戰,用不屬於自己的錢買飛機。第二,並非權力使人腐化,而是比較糟糕的人會被權力吸引——權力吸引腐敗的人。心理病態的藥劑師忍不住要在一艘注定滅亡的船上攀登到最高位,而虐待狂無法抗拒穿上制服,用警棍毆打囚犯的誘惑。第三,問題不在掌握權力或追求權力的人身上,而是我們因為壞的理由而被壞的領導者吸引,我們還傾向於授予他們權力。我們的船長是基於不理性的原因被挑選出來——不只是想像中的船。當他們帶領我們撞上礁岩時,我們只能怪罪自己。還有第四,我們不應該將重點放在個別的掌權者,因為一切都取決於體制。壞的體制產生壞的領導者,只要創造出正確的背景環境,權力就能使人淨化而非使人腐化。
這些假說是關於人類社會的兩個最基本問題的可能解釋:誰得到權力以及權力如何改變我們。本書會提供答案。
拉瓦盧馬納納對於如何出奇制勝打贏選戰並不陌生,他對打破規則也無所顧忌。二○○六年時,他雖然佔有再度當選的優勢,但他不願意冒任何風險。他運用了一個新奇的手法來操縱選舉:他迫使他的主要對手被流放,然後阻止他返回家鄉登記參選。每當他的對手設法想回到馬達加斯加,拉瓦盧馬納納就拿起電話,下令關閉島上所有機場,導致對手所搭乘的飛機掉頭返航。這個辦法奏效了。由於這個對手不准從海外登記參選,所以不在候選人名單中。拉瓦盧馬納納於是大獲全勝。
二○○八年,拉瓦盧馬納納,一個出身寒微,參加教堂唱詩班和當過慈善志工的人——變得貪婪。在掌權六年後,他的內心似乎已經被某種事物改變。在一個每人年平均所得只有幾百美元的國家,他花費六千萬美元的國家基金購買了一架總統專機(有點野心勃勃地命名為「空軍二號」)。他設法將這架飛機的牌照登記在自己名下,而非馬達加斯加政府。拉瓦盧馬納納年復一年地掌握權力,他腐化的程度似乎越來越嚴重。
最終這將證明是他垮台的原因。二○○九年,一名暴發的廣播節目主持人轉行從政,他組織了抗議拉瓦盧馬納納總統的活動。這位前主持人在廣播節目中慫恿和平抗議者遊行到總統府。在他們到達時,保護優酪乳大亨的士兵朝他們開火。數十人被射死,激起人們的憤怒。街道上的血跡剛被清洗掉不久,拉瓦盧馬納納便在政變中被推翻,接管政府的軍方擁立這位主持人上台。
或許傳統看法是對的:權力確實使人腐化。五歲時的拉瓦盧馬納納只夢想著從兜售水田芥晉級到販賣優酪乳,他規規矩矩地做生意,為人並不殘暴。他幫助的是別人而非自己。但掌控馬達加斯加似乎改變了他,使他變得更壞。但這或許不是拉瓦盧馬納納的錯。那位廣播節目主持人總統最終可能變得比他所取代的乳品業大亨更腐敗。假使你或我突然被擁立為這個以貪腐而聞名的島國總統,我們也可能會墮落。這只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然而傳統觀念有時錯得離譜。假使權力並不會讓我們變得更好或更壞呢?假使權力只吸引某些類型的人——而那些人恰恰是不應該掌權的人?也許最想要權力的人正好是最不適合掌握權力的人。也許渴望權力的人比較容易墮落。
如果你曾閱讀通俗的心理學書籍,你很可能聽說過一個惡名昭彰的研究,這個研究似乎暗示權力確實使人腐化。只是有個問題:關於這個研究,你以為你知道的一切其實是錯的。
一九七一年暮夏,史丹佛大學的研究者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心理學系的地下室搭建一座模擬監獄。他招募了十八名大學生參與一項準科學研究,目的在判定社會角色是否會改變一般人的行為到不像話的程度。這個假說相當簡單:人類行為變化莫測。我們會配合我們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說我們所穿的制服。
為了測試這個假說是否為真,津巴多隨機指派其中九名自願參與者為「守衛」,其他九名參與者則成為「囚犯」。為了為期兩週、每天十五美元的報酬,他們必須進行一場過於真實的刑事司法角色扮演。接下來發生的事,如今變得惡名昭彰。守衛幾乎立刻開始虐待囚犯。他們用滅火器攻擊囚犯,拿走囚犯的床墊並強迫他們睡在混凝土地板上。扮演守衛的大學生剝光同儕的衣服,只為了顯示誰是老大。權力似乎使他們變得可怕。
在喪失人身控制權後,原本自豪、外向開朗的大學生變得封閉保守和順從。一名守衛在虐待完他的大學同儕後,命令囚犯排好隊以便羞辱他們。
「以後我說什麼,你就做什麼。」
「謝謝你,矯正官。」一名囚犯回答。
「再說一遍。」
「謝謝你,矯正官。」
「說『上帝保佑你,矯正官』。」
「上帝保佑你,矯正官。」
這項研究原本要持續進行兩個星期,但當津巴多的女朋友來探訪這座模擬監獄,她被所目睹的境況給嚇壞了,六天後,她說服津巴多停止了實驗。研究結果發表之後,舉世震驚。有人為此製作紀錄片,也有人寫書。證據似乎相當明確:權力能召喚出我們每個人心中的惡魔。
但這當中藏了一個圈套。看似直截了當的史丹佛監獄實驗故事,不是這麼清楚明白——這已成為心理學的傳統看法。守衛之中只有一些人濫用權力。有些守衛拒絕濫用權力,並給予大學生囚犯尊重的對待。因此,即便權力真的使人腐化,是否有人比其他人更加不受影響?
此外,如今有些囚犯和守衛表示,他們當年只是在進行表演。他們相信研究人員想要看見一場表演,於是便給他們一場表演。近來被揭露的實驗準備階段錄音,已經讓人質疑這些參與者是否因為受到指示而對囚犯苛刻,並非自然而然變卑鄙。因此,情況比我們被引導去相信的還要撲朔迷離些。
但即便有這些提醒,這個實驗仍然教人感到心寒。一般人如果在合適的環境下,是否都有可能變得殘酷和邪惡?一旦我們控制了別人,我們是否全都是等著被揭下面具的虐待狂?
幸好答案可能不是如此。津巴多的結論並沒有考慮到該研究的一個重要層面:參與者的招募方式。研究人員為了找來囚犯和守衛,在當地報紙刊登了以下的廣告:
徵求男性大學生參與監獄生活的心理學研究。自八月十四日起,為期一至兩週,每日報酬十五美元。欲知詳情與應徵,請洽……
二○○七年,西肯塔基大學的研究人員注意到廣告中似乎微不足道的細節。他們感到納悶,這是否已經不慎使該研究產生偏差。為了找出答案,他們複製了這則廣告,只將十五美元改成七十美元(因應一九七○年代以來的通貨膨脹所作的調整)。除此之外,更新後的廣告中每個字都一模一樣。後來,他們又創造一個新廣告,除了一個關鍵的差異,其他部分都相同:「參與監獄生活的心理學研究」改成「參與心理學研究」。他們在某些大學城放置「監獄生活」廣告,在其他大學城放置「心理研究」廣告。其概念是讓一組人自願參加監獄實驗,而另一組參加一般心理學研究。回應這兩則廣告的人會有什麼差異嗎?
招募期結束後,研究人員要求未來的研究參與者接受心理篩選和徹底的人格評估。他們的發現十分驚人。相較於回應一般心理學研究廣告的人,那些回應監獄實驗廣告的人在「侵略性、獨裁主義、馬基維利主義、自戀和社會優勢」的測量項目獲得相當高的分數,而在「同理心和利他主義傾向項目的得分明顯偏低」。只不過是在廣告中包含了監獄這個用語,結果便招來不成比例的一批殘酷成性的學生。
這個發現可能翻轉了史丹佛監獄實驗的結論,在根本上改變我們對權力的了解。史丹佛監獄實驗並沒有證明被賦予權力的一般人會變得殘酷,而是可能證明了殘酷成性的人會尋求權力。或許我們倒因為果。或許權力只是一塊吸引壞人的磁鐵,而非使好人變壞的一種力量。依此構想,權力不會使人腐化——它吸引腐敗者。
但仍有另一個謎。即便不適合掌權的人被權力吸引,他們為何似乎很容易獲得權力?畢竟在現代社會中,大量的控制不是奪取來的,而是被給予。執行長不必與中階經理進行格鬥士般的戰鬥,就能進駐邊間辦公室。懦夫和腐敗的政客,至少在民主政體中,需要一般大眾支持他們掌權。近來所揭露關於史丹佛監獄實驗的事,提升了壞人受權力吸引的可能性。但我們又為什麼容易因為錯誤的理由,而將權力交給不對的人?
二○○八年,瑞士研究人員進行一項實驗來測試這個假說。他們招募了六百八十一名當地兒童,年齡介於五歲到十三歲之間。這些孩童被要求玩一個電腦模擬遊戲,他們必須為一艘即將出航的船做出相關的決定。每個孩童都得依據出現在螢幕上的兩張臉,為他們的數位船挑選一位船長。此外沒有其他資料。如此的設計是為了迫使這些孩童決定:對你而言誰看起來像是個好船長?誰似乎可以成為你想像中的船隻的有效領導者?
孩子們不知道的是,這兩個可能的船長人選並不是隨機搭配。他們是最近在法國國會選舉中競選的政治人物。成對的臉隨機分配給這些孩童,但他們所看見的每一對組合都包含了勝選者和第二高票。研究的結果相當驚人:孩子們挑選出來的船長,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一的機率是贏得選舉的候選人。當研究人員改以成人為對象,進行相同的實驗時,他們驚訝地發現近乎相同的結果。研究結果有兩方面值得我們注意。首先,連兒童都能光憑長相就準確辨識出勝選者,突顯出我們對於領導潛力的評估方式是多麼膚淺。第二,在挑選掌權者時,兒童和成人的認知歷程並無根本上的差異。此事賦予憑表象(at face value)相信人這個片語新的意義。進一步的證據指出,我們挑選領導者的能力是有問題的,其他幾項研究也顯示在群體討論中,更具攻擊性或表現粗野的人會被視為比更樂意合作或更溫順的人,看起來更有權力和更像領導者。
沒錯,事情越變越複雜。權力可能使好人腐化,但也可能吸引壞人。身為人類,不知怎的我們似乎因為壞的理由而被壞的領導者吸引。
不幸的是,這種複雜性才只是起點,還有另一個需要考量的難題。假使掌權者之所以做壞事,並非因為他們原本就是壞人,不是因為得到權力之後變壞,而是因為他們受困於壞的體制呢?這個想法非常有道理。畢竟奉公守法可能會讓你在挪威晉升,但保證你永遠無法在烏茲別克獲得權力。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某些位高權重者是真正的了不起——他們一心幫助別人而非幫助自己。因此權力的誘惑和掌握權力的影響可能得視背景而定。幸好,背景和體制是可以改變的。這帶給我們一些好消息:或許我們不是注定要活在一個無法避免科內利玆式濫權領導的世界。
在印度班加羅爾(Bangalore)所進行的研究為上述的樂觀看法提供了一些證據。研究人員想看看什麼類型的人會被公職吸引,當地公家部門是以貪污受賄而聞名。印度文官提供了合適的試驗場,因為他們的貪污腐敗可謂惡名昭彰。人人都知道在班加羅爾當公務員有機會獲得灰色收入。在這個由兩位經濟學家所設計的實驗中,數百名大學生被要求投標準的骰子四十二次並記錄結果。當然,投骰子的結果全憑運氣。然而在投骰子之前,他們被告知如果他們運氣好,投出更高的點數,會獲得更多報酬。投出更多的四點、五點和六點可以賺到更多現金。
但由於結果是自行報告,學生可以謊報他們投骰子的結果。許多人的確這麼做。投出六點的次數佔百分之二十五,而一點只有百分之十。藉由統計分析,研究人員可以確定,如此偏差的結果不可能是因為運氣。有些學生甚至厚顏無恥地宣稱他們接連投出四十二次的六點。但這些數據透露出蹊蹺:在實驗中作弊的學生,他們的職業志向不同於誠實記錄的學生。比起一般學生,自行報告出造假的高點數的學生,有更多人表示他們想要加入腐敗的印度文官體系。
丹麥的另一組研究人員也做了類似的實驗——這個國家的文官體系乾淨且透明,卻獲得相反的結果。誠實地自行報告點數的學生更想要擔任公務員,而說謊的學生尋求能讓他們以骯髒手段致富的職業。腐敗的體制吸引腐敗的學生,誠實的體制吸引誠實的學生。或許這無關權力使人改變,而是與背景有關。好的體制能創造出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追求權力的良性循環。壞的體制則創造出讓人們為了爬到最高位,樂於說謊、欺騙和偷竊的惡性循環。如果這是事實,那麼我們應該關切的不是掌握權力的個人,而是修補不健全的體制。
關於這些惱人的複雜謎題,我們有一系列可能的解答。第一,權力讓人變得更壞——權力使人腐化。水田芥變成優酪乳帝國,在你還會意不過來之前,你已經匆匆投入選戰,用不屬於自己的錢買飛機。第二,並非權力使人腐化,而是比較糟糕的人會被權力吸引——權力吸引腐敗的人。心理病態的藥劑師忍不住要在一艘注定滅亡的船上攀登到最高位,而虐待狂無法抗拒穿上制服,用警棍毆打囚犯的誘惑。第三,問題不在掌握權力或追求權力的人身上,而是我們因為壞的理由而被壞的領導者吸引,我們還傾向於授予他們權力。我們的船長是基於不理性的原因被挑選出來——不只是想像中的船。當他們帶領我們撞上礁岩時,我們只能怪罪自己。還有第四,我們不應該將重點放在個別的掌權者,因為一切都取決於體制。壞的體制產生壞的領導者,只要創造出正確的背景環境,權力就能使人淨化而非使人腐化。
這些假說是關於人類社會的兩個最基本問題的可能解釋:誰得到權力以及權力如何改變我們。本書會提供答案。
引言
到底是權力使人腐化,或者腐敗的人受權力吸引?侵吞公款的企業家和殺人的警察是壞制度的必然結果,或者他們原本就是壞人?暴君是後天造就或生來如此?如果你被推上權力的寶座,中飽私囊或折磨你的敵人的新誘惑,是否會讓你心癢難耐而最終使你屈服?有點出人意料的是,我們可以從兩個被人遺忘的遙遠島嶼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遠在澳大利亞西部海岸外,有一小塊名為燈塔島(Beacon Island)的陸地勉強浮出於海面。島上覆蓋著矮小的青草,三角形的海岸線周圍是米黃色沙灘。如果你站在島上的某端,對著另一端投出棒球,它大概會落入海中。這似乎只是一座近岸處點綴著一些珊瑚,不值得注意的無人小島,但燈塔島藏著一個秘密。
一六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一艘長一百六十英尺的香料船「巴達維亞號」(Batavia)從荷蘭啟航。這艘貿易船隸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旗下的船隊,該公司帝國控制著全球貿易。「巴達維亞號」載著一大筆銀幣,準備用來交換現今印尼爪哇島上的香料和異國財富。船上有三百四十個人,其中一些是乘客,大多數是船員,還有一個心理病態的藥劑師。
船上事務按嚴明的階級制度進行規劃。「住宿條件方面,越靠近船首越簡陋。」船長在船尾處坐擁一個大艙房,他嘴裡嚼著醃肉,一面厲聲對著手下發號施令。在兩層甲板下,士兵們擠在通風不良、老鼠出沒,回程時用來儲存香料的爬行空間中。「巴達維亞號」上的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位階。
杰羅尼姆斯.科內利玆(Jeronimus Cornelisz)是比船長低幾個位階的資淺商人,一個窮困潦倒的前藥劑師。歷經一連串個人的不幸後,他在絕望之餘簽約到船上工作。啟航不久後,他著手進行一項翻身計畫。科內利玆與某位高級職員串通,密謀策劃一場叛變。他故意讓船偏離航道,準備在孤立的水域內奪取控制權。如果一切都按計畫發生,他將控制住「巴達維亞號」並展開豪奢的新生活,大肆揮霍手中的銀幣。
但事情沒有按計畫發生。
一六二九年六月四日在澳大利亞外海,「巴達維亞號」全速撞上低矮的阿布羅略斯群島(Abrolhos Islands)的珊瑚礁,木製的船身碎裂。其間沒有人發出警告,也沒有要求改變航道的呼叫。一看便知道,這艘船顯然已經在劫難逃。大多數的乘客和船員設法游到岸上。幾十個人溺斃,其他人試著攀附著「巴達維亞號」的殘骸。
船長明白除非獲得救援,否則無人能生還,他於是控制住緊急救生艇和搶救來的大部分物資。他和其他四十七個人出發前往爪哇島,其中包括領導階層的所有高級船員。他保證他們很快就會帶著救援隊回來。數百人被拋棄,沒有食物也幾乎沒有飲用水,只剩下期待某天有人回來拯救他們的一絲希望。貧瘠的島上沒有生長任何植物或棲息任何動物。情況很明顯:倖存者命在旦夕。
原本想要叛變的科內利玆也被留了下來。他已經沒有適於航海的船隻可以接管,但是他不會游泳,所以與其跳入水中、拚命地朝島上游去,站在沉沒中的「巴達維亞號」殘骸上似乎是更好的選擇。接連九天,包括科內利玆在內的七個男人佔據一片逐漸縮小的木頭乾燥區域。他們一面喝酒、一面盤算著不可避免的事。
六月十二日,「巴達維亞號」終於解體。在海浪的沖刷下,部分倖存者撞上鋒利的珊瑚而提早喪命,其餘的人不久之後跟著溺斃。科內利玆不知怎的活了下來,他最終「抓住一大塊浮木漂浮到島上,成為『巴達維亞號』的最後一名生還者」。
科內利玆來到位於現今燈塔島潮濕沙地上的避難處。在求生本能下的失序和混亂狀態,逐漸恢復成按階級和地位安排的既定秩序。雖然科內利玆被沖上岸時衣衫襤褸且虛弱,但他依舊是高級職員,意味著他是當家做主的人。「『巴達維亞號』是一個高度講求階級的社會。」歷史學家麥克.戴許(Mike Dash)說,「同樣的情況殘留在燈塔島。」受困在島上的幾百個人連忙過來幫助他們的上司。他們將會後悔這麼做,或者至少有些人會後悔。
一等到恢復健康和重振精神後,科內利玆迅速做了些盤算。情況非常惡劣:船隻失事後所剩的食物、飲水和酒維持不了多久。供給不會增加,他心想,因此必須降低需求。這些倖存者需要減少會張口吃飯的嘴。
科內利玆開始藉由消滅潛在的對手來鞏固自己的權力。有些人被派去進行有勇無謀的任務,然後被推出小船外落水溺斃。有些人被指控犯罪,這是用來判處他們死刑的藉口。可怕的處決行動確立了科內利玆的權威,同時也提供有用的忠誠測試。願意聽從科內利玆命令殺人的人,對他來說是有用的人,而拒絕聽命行事的人則是威脅。這些威脅一一被剷除,很快地,就連藉口都不需要了。為了試試看某把劍是否仍然鋒利,有一名男孩因此被斬首。兒童們無端被殺,這些殺戮都是按科內利玆的命令完成,但他本人沒有親自動手。他穿著從船上取得的華服,藉以展現他的支配力:「絲質長襪、滾上金邊的吊襪帶以及……諸如此類的裝飾品。」其他人穿著骯髒破爛的衣服等著依序被殺。第一章
引言
到底是權力使人腐化,或者腐敗的人受權力吸引?侵吞公款的企業家和殺人的警察是壞制度的必然結果,或者他們原本就是壞人?暴君是後天造就或生來如此?如果你被推上權力的寶座,中飽私囊或折磨你的敵人的新誘惑,是否會讓你心癢難耐而最終使你屈服?有點出人意料的是,我們可以從兩個被人遺忘的遙遠島嶼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遠在澳大利亞西部海岸外,有一小塊名為燈塔島(Beacon Island)的陸地勉強浮出於海面。島上覆蓋著矮小的青草,三角形的海岸線周圍是米黃色沙灘。如果你站在島上的某端,對著另一端投出棒球,它大概會落入海中。這似乎只是一座近岸處點綴著一些珊瑚,不值得注意的無人小島,但燈塔島藏著一個秘密。
一六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一艘長一百六十英尺的香料船「巴達維亞號」(Batavia)從荷蘭啟航。這艘貿易船隸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旗下的船隊,該公司帝國控制著全球貿易。「巴達維亞號」載著一大筆銀幣,準備用來交換現今印尼爪哇島上的香料和異國財富。船上有三百四十個人,其中一些是乘客,大多數是船員,還有一個心理病態的藥劑師。
船上事務按嚴明的階級制度進行規劃。「住宿條件方面,越靠近船首越簡陋。」船長在船尾處坐擁一個大艙房,他嘴裡嚼著醃肉,一面厲聲對著手下發號施令。在兩層甲板下,士兵們擠在通風不良、老鼠出沒,回程時用來儲存香料的爬行空間中。「巴達維亞號」上的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位階。
杰羅尼姆斯.科內利玆(Jeronimus Cornelisz)是比船長低幾個位階的資淺商人,一個窮困潦倒的前藥劑師。歷經一連串個人的不幸後,他在絕望之餘簽約到船上工作。啟航不久後,他著手進行一項翻身計畫。科內利玆與某位高級職員串通,密謀策劃一場叛變。他故意讓船偏離航道,準備在孤立的水域內奪取控制權。如果一切都按計畫發生,他將控制住「巴達維亞號」並展開豪奢的新生活,大肆揮霍手中的銀幣。
但事情沒有按計畫發生。
一六二九年六月四日在澳大利亞外海,「巴達維亞號」全速撞上低矮的阿布羅略斯群島(Abrolhos Islands)的珊瑚礁,木製的船身碎裂。其間沒有人發出警告,也沒有要求改變航道的呼叫。一看便知道,這艘船顯然已經在劫難逃。大多數的乘客和船員設法游到岸上。幾十個人溺斃,其他人試著攀附著「巴達維亞號」的殘骸。
船長明白除非獲得救援,否則無人能生還,他於是控制住緊急救生艇和搶救來的大部分物資。他和其他四十七個人出發前往爪哇島,其中包括領導階層的所有高級船員。他保證他們很快就會帶著救援隊回來。數百人被拋棄,沒有食物也幾乎沒有飲用水,只剩下期待某天有人回來拯救他們的一絲希望。貧瘠的島上沒有生長任何植物或棲息任何動物。情況很明顯:倖存者命在旦夕。
原本想要叛變的科內利玆也被留了下來。他已經沒有適於航海的船隻可以接管,但是他不會游泳,所以與其跳入水中、拚命地朝島上游去,站在沉沒中的「巴達維亞號」殘骸上似乎是更好的選擇。接連九天,包括科內利玆在內的七個男人佔據一片逐漸縮小的木頭乾燥區域。他們一面喝酒、一面盤算著不可避免的事。
六月十二日,「巴達維亞號」終於解體。在海浪的沖刷下,部分倖存者撞上鋒利的珊瑚而提早喪命,其餘的人不久之後跟著溺斃。科內利玆不知怎的活了下來,他最終「抓住一大塊浮木漂浮到島上,成為『巴達維亞號』的最後一名生還者」。
科內利玆來到位於現今燈塔島潮濕沙地上的避難處。在求生本能下的失序和混亂狀態,逐漸恢復成按階級和地位安排的既定秩序。雖然科內利玆被沖上岸時衣衫襤褸且虛弱,但他依舊是高級職員,意味著他是當家做主的人。「『巴達維亞號』是一個高度講求階級的社會。」歷史學家麥克.戴許(Mike Dash)說,「同樣的情況殘留在燈塔島。」受困在島上的幾百個人連忙過來幫助他們的上司。他們將會後悔這麼做,或者至少有些人會後悔。
一等到恢復健康和重振精神後,科內利玆迅速做了些盤算。情況非常惡劣:船隻失事後所剩的食物、飲水和酒維持不了多久。供給不會增加,他心想,因此必須降低需求。這些倖存者需要減少會張口吃飯的嘴。
科內利玆開始藉由消滅潛在的對手來鞏固自己的權力。有些人被派去進行有勇無謀的任務,然後被推出小船外落水溺斃。有些人被指控犯罪,這是用來判處他們死刑的藉口。可怕的處決行動確立了科內利玆的權威,同時也提供有用的忠誠測試。願意聽從科內利玆命令殺人的人,對他來說是有用的人,而拒絕聽命行事的人則是威脅。這些威脅一一被剷除,很快地,就連藉口都不需要了。為了試試看某把劍是否仍然鋒利,有一名男孩因此被斬首。兒童們無端被殺,這些殺戮都是按科內利玆的命令完成,但他本人沒有親自動手。他穿著從船上取得的華服,藉以展現他的支配力:「絲質長襪、滾上金邊的吊襪帶以及……諸如此類的裝飾品。」其他人穿著骯髒破爛的衣服等著依序被殺。
幾個月後,等到「巴達維亞號」船長帶著救援隊回來時,已經有一百多人遭到殺害。科內利玆最終嘗到他自己的島嶼正義:他獲判死刑。他被砍掉雙手並絞殺。但這個恐怖事件引發了一個令人感到不安的人性問題:倘若當時科內利玆不在船上,是否可以避免這場大屠殺?或者自然會有別人來領導他們做這件事?
燈塔島以東四千英里處,澳大利亞另一邊有一座隸屬於東加群島的荒島,名叫阿塔島(‘Ata)。一九六五年時,有六名十五至十七歲的男孩逃出寄宿學校,他們偷了一艘漁船向北航行。第一天他們只前進了五英里就決定下錨休息過夜。在他們試著入睡時,一陣暴風劇烈地搖晃他們那艘長二十四英尺的船,結果扯起船錨。超級強風很快就吹壞船帆,還摧毀掉船舵。等到天亮時,男孩們無法操縱船隻,也無法航行,只能隨著洋流漂浮。他們連續八天沿著海岸向南前進,完全不知道回家的方向。
當這六名青少年開始失去希望時,他們望見遠方有一片隱約的綠意。那是阿塔島,一座植被濃密的崎嶇島嶼。他們駕駛那艘只能有限度操縱的受損漁船,等到漂近岸邊時便棄船游泳上岸。在被沖進無情的汪洋之前,這是他們最後的機會。他們終於成功上岸,雖然被岩石割傷,但活了下來。
阿塔島周圍的峭壁使得登島變得困難,沒想到卻成為遭遇船難的男孩的生存助力。鋸齒狀的岩石是海鳥築巢棲息的完美場所,他們開始合作架設陷阱捕鳥。由於找不到淡水,他們只能隨機應變吸食海鳥血液。在新家四處搜尋後,他們升級到以椰子水解渴。最終他們的三餐從生食變成熟食,因為他們生起第一把火。男孩們商量好必須使餘火持續燃燒,絕不能讓它熄滅。他們於是輪流看顧餘火,一天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這條生命線讓他們得以烹煮魚肉、海鳥和甚至烏龜。
在通力合作下,男孩們的生活水準進一步提升。他們接連四天合力從島上大樹的根部一滴滴收集淡水。他們挖空樹幹來蒐集雨水,還用棕櫚葉搭建出一間簡陋的房屋。他們每件事都分工合作,沒有人當領導者。沒有鑲金邊的裝飾和長襪、沒有大聲下達的命令、沒有為了鞏固權力而策劃的陰謀,也沒有殺人事件。當他們征服這座島嶼時,成功和失敗都由大家平均分擔。
遭遇船難六個月後,當中一名男孩特維塔.法泰.拉杜(Tevita Fatai Latu)在每日例行獵捕海鳥時滑倒,結果摔斷了腿。其他五名男孩連忙過來幫助他,利用傳統東加方法,烤熱椰子樹莖製作出夾板,將骨頭固定復位。接下來的四個月,特維塔無法走路,但其他男孩一直照顧他,直到他能再度處理日常瑣事。
他們不時發生爭執。(六個人整天形影不離,菜單是一成不變的海鳥和烏龜肉,難免讓人偶爾脾氣失控。)然而一旦爆發衝突,男孩們會識相地分開。意見嚴重分歧的男孩會各自待在島上的不同地點,有時長達兩天,直到他們冷靜下來,可以再度合作求生存。過了一年多後,他們開始體認到這種新生活不是暫時的,因此得有長期安頓下來的打算,他們藉由製作粗陋的網球拍和舉行比賽、安排拳擊賽和一起健身來度日。為了避免耗盡海鳥存糧,他們同意限制每人每天的食物量並開始嘗試種植野生豆子。
在男孩們遭遇船難十五個月後,一個名叫彼得.華納(Peter Warner)的澳洲人開著他的漁船找尋捕捉螯蝦的地點。當他靠近一座無人居住的島嶼時,他發現一件不尋常的事。「我注意到峭壁上有燒焦的痕跡,這在熱帶地區並不尋常,因為在那麼潮濕的大氣環境中,不可能引發叢林野火。」現年八十九歲的華納回想。接下來,他看見令人驚奇的景象,一位留著十五個月的長髮的裸體男孩。男孩們大聲吶喊並揮舞著棕櫚葉,希望引起這艘船的注意。當船靠得夠近時,男孩們跳進海中,開始游向他們從沒想到會出現的救星。華納不確定發生了什麼事,他不知道這些男孩是否是被放逐到島上的囚犯,這項懲罰專門留給玻里尼西亞社會中最壞的壞蛋。「見到這些沒穿衣服、沒理髮,看起來健康的青少年,我有點驚慌。」他告訴我。華納將步槍裝上子彈,嚴陣以待。
當男孩來到船上時,他們客氣地解釋自己的身分。華納沒聽說有任何男孩失蹤,於是用無線電聯絡接線生,要他打電話到男孩在東加的學校證實他們的說法。二十分鐘後,流著淚的接線生告知華納,這些被認為已經死亡的男孩失蹤了一年多。「他們的葬禮已經舉行過。」接線生說。男孩被帶回東加與家人團圓。在他們獲救後,當中年紀最大的席歐內.法圖阿(Sione Fataua)說起他對生還返家的焦慮:「我們當中的幾個人有女朋友。或許她們已經不記得我們?」
如同荷蘭歷史學家羅格.布萊格曼(Rutger Bregman)所言,「真正的《蒼蠅王》是關於友誼和忠誠的故事,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如果能夠依賴彼此,我們會更加強大。」華納依舊定期和其中一位遭遇船難的男孩一起航海,他認為這整起事件「大大展現人性光輝」。
兩座荒島、兩種互相牴觸的人性洞察。其一,一個渴望權力的人鞏固對別人的控制,以便剝削和殺害他們。其二,講求平等的團隊合作佔上風,合作成為最高的原則。我們要如何解釋其間的差異?
燈塔島有結構、有秩序、有等級,最終釀成悲劇。另一方面,阿塔島到處是崎嶇聳立的岩石,但男孩們在十五個月裡所雕鑿出來的社會卻是一片平坦。兩個衝突的荒島故事引發不同的問題。我們是否因為壞人或壞的階級制度而注定被剝削?為什麼這世界上似乎有許多像科內利玆這樣的領導者在掌權,而像阿塔島男孩的人卻何其地少?
還有,如果你和同事被困在荒島上,你是否會推翻老闆,像東加男孩那樣平等合作來解決問題?或者像在燈塔島上,以血腥的方式奪取權力和支配力?你會怎麼做?
本書回答四個主要的問題。
第一,是否比較壞的人會獲得權力?
第二,權力是否使人變得更壞?
第三,我們為什麼讓那些顯然不該掌權的人控制我們?
第四,我們如何確保讓不會腐化的人掌權,並公正地行使權力?
過去十年來,我一直在世界各地研究這些問題,從白俄羅斯到英國、從象牙海岸到美國加州、泰國到突尼西亞以及澳大利亞到尚比亞。作為政治科學家的部分研究,我訪談了不同的人——主要是濫用他們的權力做壞事的壞人。我會晤教派領導者、戰犯、暴君、政變策劃者、刑求者、雇佣兵、將軍、鼓吹者、造反者、貪污的執行長以及被定罪的罪犯。我試著釐清是什麼讓他們發揮作用。了解他們,以及研究他們所處的體制——是阻止他們的關鍵。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瘋狂且殘忍,有些則仁慈和具有同情心。但他們有一個共通的特點:他們行使巨大的權力。
當你和一個犯下戰爭罪的叛軍指揮官握手,或者與折磨敵人、冷血無情的暴君共進早餐時,你會訝異於他們鮮少符合諷刺漫畫中的邪惡形象。他們往往很有魅力,會開玩笑且面露笑容。他們乍看之下並不像怪物,但有許多確實是惡人。
年復一年,我努力想解開這些揮之不去的謎題。刑求者和戰犯是否是全然不同的類型,或者他們只是我們偶爾會在辦公室或鄰里中遇見的小暴君的極端加強版?未來的惡人是否就藏身在我們之中?在適當的條件下,是否任何人都有可能變成惡人?果真如此的話,那麼我們從嗜殺的暴君身上所學到的教訓,能否用來減少社會上較小規模的濫權問題。這是一個尤其迫切需要解決的謎題,因為當權者不斷地令我們失望。當你告訴別人你是一個政治科學家,他們接下來往往會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有這麼多糟糕的人在掌權?」
但另一個謎題持續要求我們給予解答:這些人是否因為握有權力而變得糟糕?我自己也心存疑惑。另一個可能性在困擾著我:因為權力而變得更壞的人,他們是否只是冰山的一角。或許有更龐大、更嚴重的問題潛伏在波濤下,等待被發現,等著我們去解決。
讓我們先從傳統觀念說起。每個人都聽說過「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化」這句名言。大家普遍相信這句話,但事實是否果真如此?
幾年前我走訪了馬達加斯加,那是非洲海岸外一個紅土漫布的島嶼。人人都知道馬達加斯加有可愛的環尾狐猴,但它同樣也是一個有趣物種的產地:腐敗的政治人物。馬達加斯加主要由無賴統治,他們從地球上最貧窮的三千萬人身上榨取利益。在馬達加斯加,一份拿鐵咖啡加鬆餅就得花光一般人整週的所得。雪上加霜的是,有錢人往往剝削窮人。我在那裡遇見了馬達加斯加最富有的人之一:島上的優酪乳大亨拉瓦盧馬納納(Marc Ravalomanana)。
拉瓦盧馬納納出身貧寒。為了幫助家計,五歲的他會提著幾籃水田芥,向搭火車路過學校的乘客兜售。某天他交上意想不到的好運:鄰居送給他一輛腳踏車。年幼的拉瓦盧馬納納於是開始騎車到附近的農場,索討剩餘的牛奶並將它們變成自製的優酪乳。在生意剛起步時,他便試著回饋貧困的社區。他在當地教會當志工,或者在唱詩班裡唱歌,除此之外便是騎著那輛搖搖晃晃的破單車,一路叫賣優酪乳,一罐又一罐、年復一年發展出他的事業。
幾個月後,等到「巴達維亞號」船長帶著救援隊回來時,已經有一百多人遭到殺害。科內利玆最終嘗到他自己的島嶼正義:他獲判死刑。他被砍掉雙手並絞殺。但這個恐怖事件引發了一個令人感到不安的人性問題:倘若當時科內利玆不在船上,是否可以避免這場大屠殺?或者自然會有別人來領導他們做這件事?
燈塔島以東四千英里處,澳大利亞另一邊有一座隸屬於東加群島的荒島,名叫阿塔島(‘Ata)。一九六五年時,有六名十五至十七歲的男孩逃出寄宿學校,他們偷了一艘漁船向北航行。第一天他們只前進了五英里就決定下錨休息過夜。在他們試著入睡時,一陣暴風劇烈地搖晃他們那艘長二十四英尺的船,結果扯起船錨。超級強風很快就吹壞船帆,還摧毀掉船舵。等到天亮時,男孩們無法操縱船隻,也無法航行,只能隨著洋流漂浮。他們連續八天沿著海岸向南前進,完全不知道回家的方向。
當這六名青少年開始失去希望時,他們望見遠方有一片隱約的綠意。那是阿塔島,一座植被濃密的崎嶇島嶼。他們駕駛那艘只能有限度操縱的受損漁船,等到漂近岸邊時便棄船游泳上岸。在被沖進無情的汪洋之前,這是他們最後的機會。他們終於成功上岸,雖然被岩石割傷,但活了下來。
阿塔島周圍的峭壁使得登島變得困難,沒想到卻成為遭遇船難的男孩的生存助力。鋸齒狀的岩石是海鳥築巢棲息的完美場所,他們開始合作架設陷阱捕鳥。由於找不到淡水,他們只能隨機應變吸食海鳥血液。在新家四處搜尋後,他們升級到以椰子水解渴。最終他們的三餐從生食變成熟食,因為他們生起第一把火。男孩們商量好必須使餘火持續燃燒,絕不能讓它熄滅。他們於是輪流看顧餘火,一天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這條生命線讓他們得以烹煮魚肉、海鳥和甚至烏龜。
在通力合作下,男孩們的生活水準進一步提升。他們接連四天合力從島上大樹的根部一滴滴收集淡水。他們挖空樹幹來蒐集雨水,還用棕櫚葉搭建出一間簡陋的房屋。他們每件事都分工合作,沒有人當領導者。沒有鑲金邊的裝飾和長襪、沒有大聲下達的命令、沒有為了鞏固權力而策劃的陰謀,也沒有殺人事件。當他們征服這座島嶼時,成功和失敗都由大家平均分擔。
遭遇船難六個月後,當中一名男孩特維塔.法泰.拉杜(Tevita Fatai Latu)在每日例行獵捕海鳥時滑倒,結果摔斷了腿。其他五名男孩連忙過來幫助他,利用傳統東加方法,烤熱椰子樹莖製作出夾板,將骨頭固定復位。接下來的四個月,特維塔無法走路,但其他男孩一直照顧他,直到他能再度處理日常瑣事。
他們不時發生爭執。(六個人整天形影不離,菜單是一成不變的海鳥和烏龜肉,難免讓人偶爾脾氣失控。)然而一旦爆發衝突,男孩們會識相地分開。意見嚴重分歧的男孩會各自待在島上的不同地點,有時長達兩天,直到他們冷靜下來,可以再度合作求生存。過了一年多後,他們開始體認到這種新生活不是暫時的,因此得有長期安頓下來的打算,他們藉由製作粗陋的網球拍和舉行比賽、安排拳擊賽和一起健身來度日。為了避免耗盡海鳥存糧,他們同意限制每人每天的食物量並開始嘗試種植野生豆子。
在男孩們遭遇船難十五個月後,一個名叫彼得.華納(Peter Warner)的澳洲人開著他的漁船找尋捕捉螯蝦的地點。當他靠近一座無人居住的島嶼時,他發現一件不尋常的事。「我注意到峭壁上有燒焦的痕跡,這在熱帶地區並不尋常,因為在那麼潮濕的大氣環境中,不可能引發叢林野火。」現年八十九歲的華納回想。接下來,他看見令人驚奇的景象,一位留著十五個月的長髮的裸體男孩。男孩們大聲吶喊並揮舞著棕櫚葉,希望引起這艘船的注意。當船靠得夠近時,男孩們跳進海中,開始游向他們從沒想到會出現的救星。華納不確定發生了什麼事,他不知道這些男孩是否是被放逐到島上的囚犯,這項懲罰專門留給玻里尼西亞社會中最壞的壞蛋。「見到這些沒穿衣服、沒理髮,看起來健康的青少年,我有點驚慌。」他告訴我。華納將步槍裝上子彈,嚴陣以待。
當男孩來到船上時,他們客氣地解釋自己的身分。華納沒聽說有任何男孩失蹤,於是用無線電聯絡接線生,要他打電話到男孩在東加的學校證實他們的說法。二十分鐘後,流著淚的接線生告知華納,這些被認為已經死亡的男孩失蹤了一年多。「他們的葬禮已經舉行過。」接線生說。男孩被帶回東加與家人團圓。在他們獲救後,當中年紀最大的席歐內.法圖阿(Sione Fataua)說起他對生還返家的焦慮:「我們當中的幾個人有女朋友。或許她們已經不記得我們?」
如同荷蘭歷史學家羅格.布萊格曼(Rutger Bregman)所言,「真正的《蒼蠅王》是關於友誼和忠誠的故事,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如果能夠依賴彼此,我們會更加強大。」華納依舊定期和其中一位遭遇船難的男孩一起航海,他認為這整起事件「大大展現人性光輝」。
兩座荒島、兩種互相牴觸的人性洞察。其一,一個渴望權力的人鞏固對別人的控制,以便剝削和殺害他們。其二,講求平等的團隊合作佔上風,合作成為最高的原則。我們要如何解釋其間的差異?
燈塔島有結構、有秩序、有等級,最終釀成悲劇。另一方面,阿塔島到處是崎嶇聳立的岩石,但男孩們在十五個月裡所雕鑿出來的社會卻是一片平坦。兩個衝突的荒島故事引發不同的問題。我們是否因為壞人或壞的階級制度而注定被剝削?為什麼這世界上似乎有許多像科內利玆這樣的領導者在掌權,而像阿塔島男孩的人卻何其地少?
還有,如果你和同事被困在荒島上,你是否會推翻老闆,像東加男孩那樣平等合作來解決問題?或者像在燈塔島上,以血腥的方式奪取權力和支配力?你會怎麼做?
本書回答四個主要的問題。
第一,是否比較壞的人會獲得權力?
第二,權力是否使人變得更壞?
第三,我們為什麼讓那些顯然不該掌權的人控制我們?
第四,我們如何確保讓不會腐化的人掌權,並公正地行使權力?
過去十年來,我一直在世界各地研究這些問題,從白俄羅斯到英國、從象牙海岸到美國加州、泰國到突尼西亞以及澳大利亞到尚比亞。作為政治科學家的部分研究,我訪談了不同的人——主要是濫用他們的權力做壞事的壞人。我會晤教派領導者、戰犯、暴君、政變策劃者、刑求者、雇佣兵、將軍、鼓吹者、造反者、貪污的執行長以及被定罪的罪犯。我試著釐清是什麼讓他們發揮作用。了解他們,以及研究他們所處的體制——是阻止他們的關鍵。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瘋狂且殘忍,有些則仁慈和具有同情心。但他們有一個共通的特點:他們行使巨大的權力。
當你和一個犯下戰爭罪的叛軍指揮官握手,或者與折磨敵人、冷血無情的暴君共進早餐時,你會訝異於他們鮮少符合諷刺漫畫中的邪惡形象。他們往往很有魅力,會開玩笑且面露笑容。他們乍看之下並不像怪物,但有許多確實是惡人。
年復一年,我努力想解開這些揮之不去的謎題。刑求者和戰犯是否是全然不同的類型,或者他們只是我們偶爾會在辦公室或鄰里中遇見的小暴君的極端加強版?未來的惡人是否就藏身在我們之中?在適當的條件下,是否任何人都有可能變成惡人?果真如此的話,那麼我們從嗜殺的暴君身上所學到的教訓,能否用來減少社會上較小規模的濫權問題。這是一個尤其迫切需要解決的謎題,因為當權者不斷地令我們失望。當你告訴別人你是一個政治科學家,他們接下來往往會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有這麼多糟糕的人在掌權?」
但另一個謎題持續要求我們給予解答:這些人是否因為握有權力而變得糟糕?我自己也心存疑惑。另一個可能性在困擾著我:因為權力而變得更壞的人,他們是否只是冰山的一角。或許有更龐大、更嚴重的問題潛伏在波濤下,等待被發現,等著我們去解決。
讓我們先從傳統觀念說起。每個人都聽說過「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化」這句名言。大家普遍相信這句話,但事實是否果真如此?
幾年前我走訪了馬達加斯加,那是非洲海岸外一個紅土漫布的島嶼。人人都知道馬達加斯加有可愛的環尾狐猴,但它同樣也是一個有趣物種的產地:腐敗的政治人物。馬達加斯加主要由無賴統治,他們從地球上最貧窮的三千萬人身上榨取利益。在馬達加斯加,一份拿鐵咖啡加鬆餅就得花光一般人整週的所得。雪上加霜的是,有錢人往往剝削窮人。我在那裡遇見了馬達加斯加最富有的人之一:島上的優酪乳大亨拉瓦盧馬納納(Marc Ravalomanana)。
拉瓦盧馬納納出身貧寒。為了幫助家計,五歲的他會提著幾籃水田芥,向搭火車路過學校的乘客兜售。某天他交上意想不到的好運:鄰居送給他一輛腳踏車。年幼的拉瓦盧馬納納於是開始騎車到附近的農場,索討剩餘的牛奶並將它們變成自製的優酪乳。在生意剛起步時,他便試著回饋貧困的社區。他在當地教會當志工,或者在唱詩班裡唱歌,除此之外便是騎著那輛搖搖晃晃的破單車,一路叫賣優酪乳,一罐又一罐、年復一年發展出他的事業。
到了一九九○年代後期,拉瓦盧馬納納已經成為馬達加斯加的乳品業大亨,島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二○○二年,他成為拉瓦盧馬納納總統,在幾乎每個人都一窮二白的國家,身為精明的政治人物,他深諳白手起家的故事具有何等價值。擔任總統的拉瓦盧馬納納承諾帶來改變,起初,他履行了諾言。他的政府投資興建道路、取締貪污並以超高的經濟成長率根除貧窮。馬達加斯加變成全世界成長最快速的經濟體之一。這似乎是個成功的寓言故事,一個出身寒微的好人排除萬難,成為明智公正的統治者。
我決定去拜訪拉瓦盧馬納納。當我來到他那有如宮殿般的宅第時,他正穿著滾上白條紋的海軍藍Nike運動服走出前門。他滿面笑容地握住我的手,領著我入內。他帶我參觀他的訓練室,他從早上五點開始就一直在這裡做健身操。(「這是讓你保持敏銳的心智,以便做出重大決定的唯一辦法。」他告訴我。)接著他指向一座用來敬拜耶穌、裝飾華麗的定製神龕,這是某種火車模型版的伯利恆,上面有一具巨大的木製十字架俯臨著微型化的城鎮。我們走上樓,來到走廊盡頭時,他打開兩扇桃花心木製的大門。一張巨大的桌子出現在門後。桌面上擺滿食物、成堆的熱可頌麵包、以各種方式烹製的蛋、五種果汁,以及足夠餵飽他兒時村莊整整一星期的優酪乳。兜售水田芥的貧苦生活早已離他遠去。
儘管有拉瓦盧馬納納的幕僚長陪著我們,但只安排了兩個座位,一個給他,一個給我。我坐了下來,打開筆記本,伸手要拿筆,這才發現我忘了帶筆。
「沒問題。」拉瓦盧馬納納說,「我們或許貧窮,但並不缺筆。」他拿起叉子旁的小鈴鐺搖了起來。幾秒鐘後,兩名員工衝進房間,每個都希望搶先來到桌子旁。
「筆。」拉瓦盧馬納納厲聲說。
兩人匆忙離去,三十秒後回來,手上各抓著一支嶄新的原子筆,搶著得到讚美。動作比較慢、沒有獲得讚美的那個人看起來情緒低落。
這時拉瓦盧馬納納開始辦正事。他準備要在下次選舉中奪回總統寶座。他熱切地看著我。
「我從Google上得知你當過競選顧問。」他說,「告訴我,我應該怎麼做才能贏得選舉?」
這個問題讓我猝不及防。我去那裡是為了研究他,而不是當競選顧問。但我想要建立交情,只好臨場發揮。「我在明尼蘇達州幫忙處理州長競選活動時,我們想出一種有效的招數。我們在八十七天內走訪了全部八十七個郡,以顯示我們關心整個明尼蘇達州。馬達加斯加總共有一百十九個區,你不妨在一百十九天內走訪完這一百十九個區?」
他點點頭,示意我繼續說下去。
「你可以利用這個下鄉行程,搭配你的白手起家形象。你只需騎著腳踏車到每個城鎮,提醒人們你曾有過販售優酪乳的童年,藉以顯示你了解貧窮的滋味。」他點點頭,轉身對他的幕僚長說,「去買一百十九輛腳踏車。」
到了一九九○年代後期,拉瓦盧馬納納已經成為馬達加斯加的乳品業大亨,島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二○○二年,他成為拉瓦盧馬納納總統,在幾乎每個人都一窮二白的國家,身為精明的政治人物,他深諳白手起家的故事具有何等價值。擔任總統的拉瓦盧馬納納承諾帶來改變,起初,他履行了諾言。他的政府投資興建道路、取締貪污並以超高的經濟成長率根除貧窮。馬達加斯加變成全世界成長最快速的經濟體之一。這似乎是個成功的寓言故事,一個出身寒微的好人排除萬難,成為明智公正的統治者。
我決定去拜訪拉瓦盧馬納納。當我來到他那有如宮殿般的宅第時,他正穿著滾上白條紋的海軍藍Nike運動服走出前門。他滿面笑容地握住我的手,領著我入內。他帶我參觀他的訓練室,他從早上五點開始就一直在這裡做健身操。(「這是讓你保持敏銳的心智,以便做出重大決定的唯一辦法。」他告訴我。)接著他指向一座用來敬拜耶穌、裝飾華麗的定製神龕,這是某種火車模型版的伯利恆,上面有一具巨大的木製十字架俯臨著微型化的城鎮。我們走上樓,來到走廊盡頭時,他打開兩扇桃花心木製的大門。一張巨大的桌子出現在門後。桌面上擺滿食物、成堆的熱可頌麵包、以各種方式烹製的蛋、五種果汁,以及足夠餵飽他兒時村莊整整一星期的優酪乳。兜售水田芥的貧苦生活早已離他遠去。
儘管有拉瓦盧馬納納的幕僚長陪著我們,但只安排了兩個座位,一個給他,一個給我。我坐了下來,打開筆記本,伸手要拿筆,這才發現我忘了帶筆。
「沒問題。」拉瓦盧馬納納說,「我們或許貧窮,但並不缺筆。」他拿起叉子旁的小鈴鐺搖了起來。幾秒鐘後,兩名員工衝進房間,每個都希望搶先來到桌子旁。
「筆。」拉瓦盧馬納納厲聲說。
兩人匆忙離去,三十秒後回來,手上各抓著一支嶄新的原子筆,搶著得到讚美。動作比較慢、沒有獲得讚美的那個人看起來情緒低落。
這時拉瓦盧馬納納開始辦正事。他準備要在下次選舉中奪回總統寶座。他熱切地看著我。
「我從Google上得知你當過競選顧問。」他說,「告訴我,我應該怎麼做才能贏得選舉?」
這個問題讓我猝不及防。我去那裡是為了研究他,而不是當競選顧問。但我想要建立交情,只好臨場發揮。「我在明尼蘇達州幫忙處理州長競選活動時,我們想出一種有效的招數。我們在八十七天內走訪了全部八十七個郡,以顯示我們關心整個明尼蘇達州。馬達加斯加總共有一百十九個區,你不妨在一百十九天內走訪完這一百十九個區?」
他點點頭,示意我繼續說下去。
「你可以利用這個下鄉行程,搭配你的白手起家形象。你只需騎著腳踏車到每個城鎮,提醒人們你曾有過販售優酪乳的童年,藉以顯示你了解貧窮的滋味。」他點點頭,轉身對他的幕僚長說,「去買一百十九輛腳踏車。」
拉瓦盧馬納納對於如何出奇制勝打贏選戰並不陌生,他對打破規則也無所顧忌。二○○六年時,他雖然佔有再度當選的優勢,但他不願意冒任何風險。他運用了一個新奇的手法來操縱選舉:他迫使他的主要對手被流放,然後阻止他返回家鄉登記參選。每當他的對手設法想回到馬達加斯加,拉瓦盧馬納納就拿起電話,下令關閉島上所有機場,導致對手所搭乘的飛機掉頭返航。這個辦法奏效了。由於這個對手不准從海外登記參選,所以不在候選人名單中。拉瓦盧馬納納於是大獲全勝。
二○○八年,拉瓦盧馬納納,一個出身寒微,參加教堂唱詩班和當過慈善志工的人——變得貪婪。在掌權六年後,他的內心似乎已經被某種事物改變。在一個每人年平均所得只有幾百美元的國家,他花費六千萬美元的國家基金購買了一架總統專機(有點野心勃勃地命名為「空軍二號」)。他設法將這架飛機的牌照登記在自己名下,而非馬達加斯加政府。拉瓦盧馬納納年復一年地掌握權力,他腐化的程度似乎越來越嚴重。
最終這將證明是他垮台的原因。二○○九年,一名暴發的廣播節目主持人轉行從政,他組織了抗議拉瓦盧馬納納總統的活動。這位前主持人在廣播節目中慫恿和平抗議者遊行到總統府。在他們到達時,保護優酪乳大亨的士兵朝他們開火。數十人被射死,激起人們的憤怒。街道上的血跡剛被清洗掉不久,拉瓦盧馬納納便在政變中被推翻,接管政府的軍方擁立這位主持人上台。
或許傳統看法是對的:權力確實使人腐化。五歲時的拉瓦盧馬納納只夢想著從兜售水田芥晉級到販賣優酪乳,他規規矩矩地做生意,為人並不殘暴。他幫助的是別人而非自己。但掌控馬達加斯加似乎改變了他,使他變得更壞。但這或許不是拉瓦盧馬納納的錯。那位廣播節目主持人總統最終可能變得比他所取代的乳品業大亨更腐敗。假使你或我突然被擁立為這個以貪腐而聞名的島國總統,我們也可能會墮落。這只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然而傳統觀念有時錯得離譜。假使權力並不會讓我們變得更好或更壞呢?假使權力只吸引某些類型的人——而那些人恰恰是不應該掌權的人?也許最想要權力的人正好是最不適合掌握權力的人。也許渴望權力的人比較容易墮落。
如果你曾閱讀通俗的心理學書籍,你很可能聽說過一個惡名昭彰的研究,這個研究似乎暗示權力確實使人腐化。只是有個問題:關於這個研究,你以為你知道的一切其實是錯的。
一九七一年暮夏,史丹佛大學的研究者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心理學系的地下室搭建一座模擬監獄。他招募了十八名大學生參與一項準科學研究,目的在判定社會角色是否會改變一般人的行為到不像話的程度。這個假說相當簡單:人類行為變化莫測。我們會配合我們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說我們所穿的制服。
為了測試這個假說是否為真,津巴多隨機指派其中九名自願參與者為「守衛」,其他九名參與者則成為「囚犯」。為了為期兩週、每天十五美元的報酬,他們必須進行一場過於真實的刑事司法角色扮演。接下來發生的事,如今變得惡名昭彰。守衛幾乎立刻開始虐待囚犯。他們用滅火器攻擊囚犯,拿走囚犯的床墊並強迫他們睡在混凝土地板上。扮演守衛的大學生剝光同儕的衣服,只為了顯示誰是老大。權力似乎使他們變得可怕。
在喪失人身控制權後,原本自豪、外向開朗的大學生變得封閉保守和順從。一名守衛在虐待完他的大學同儕後,命令囚犯排好隊以便羞辱他們。
「以後我說什麼,你就做什麼。」
「謝謝你,矯正官。」一名囚犯回答。
「再說一遍。」
「謝謝你,矯正官。」
「說『上帝保佑你,矯正官』。」
「上帝保佑你,矯正官。」
這項研究原本要持續進行兩個星期,但當津巴多的女朋友來探訪這座模擬監獄,她被所目睹的境況給嚇壞了,六天後,她說服津巴多停止了實驗。研究結果發表之後,舉世震驚。有人為此製作紀錄片,也有人寫書。證據似乎相當明確:權力能召喚出我們每個人心中的惡魔。
但這當中藏了一個圈套。看似直截了當的史丹佛監獄實驗故事,不是這麼清楚明白——這已成為心理學的傳統看法。守衛之中只有一些人濫用權力。有些守衛拒絕濫用權力,並給予大學生囚犯尊重的對待。因此,即便權力真的使人腐化,是否有人比其他人更加不受影響?
此外,如今有些囚犯和守衛表示,他們當年只是在進行表演。他們相信研究人員想要看見一場表演,於是便給他們一場表演。近來被揭露的實驗準備階段錄音,已經讓人質疑這些參與者是否因為受到指示而對囚犯苛刻,並非自然而然變卑鄙。因此,情況比我們被引導去相信的還要撲朔迷離些。
但即便有這些提醒,這個實驗仍然教人感到心寒。一般人如果在合適的環境下,是否都有可能變得殘酷和邪惡?一旦我們控制了別人,我們是否全都是等著被揭下面具的虐待狂?
幸好答案可能不是如此。津巴多的結論並沒有考慮到該研究的一個重要層面:參與者的招募方式。研究人員為了找來囚犯和守衛,在當地報紙刊登了以下的廣告:
徵求男性大學生參與監獄生活的心理學研究。自八月十四日起,為期一至兩週,每日報酬十五美元。欲知詳情與應徵,請洽……
二○○七年,西肯塔基大學的研究人員注意到廣告中似乎微不足道的細節。他們感到納悶,這是否已經不慎使該研究產生偏差。為了找出答案,他們複製了這則廣告,只將十五美元改成七十美元(因應一九七○年代以來的通貨膨脹所作的調整)。除此之外,更新後的廣告中每個字都一模一樣。後來,他們又創造一個新廣告,除了一個關鍵的差異,其他部分都相同:「參與監獄生活的心理學研究」改成「參與心理學研究」。他們在某些大學城放置「監獄生活」廣告,在其他大學城放置「心理研究」廣告。其概念是讓一組人自願參加監獄實驗,而另一組參加一般心理學研究。回應這兩則廣告的人會有什麼差異嗎?
招募期結束後,研究人員要求未來的研究參與者接受心理篩選和徹底的人格評估。他們的發現十分驚人。相較於回應一般心理學研究廣告的人,那些回應監獄實驗廣告的人在「侵略性、獨裁主義、馬基維利主義、自戀和社會優勢」的測量項目獲得相當高的分數,而在「同理心和利他主義傾向項目的得分明顯偏低」。只不過是在廣告中包含了監獄這個用語,結果便招來不成比例的一批殘酷成性的學生。
這個發現可能翻轉了史丹佛監獄實驗的結論,在根本上改變我們對權力的了解。史丹佛監獄實驗並沒有證明被賦予權力的一般人會變得殘酷,而是可能證明了殘酷成性的人會尋求權力。或許我們倒因為果。或許權力只是一塊吸引壞人的磁鐵,而非使好人變壞的一種力量。依此構想,權力不會使人腐化——它吸引腐敗者。
但仍有另一個謎。即便不適合掌權的人被權力吸引,他們為何似乎很容易獲得權力?畢竟在現代社會中,大量的控制不是奪取來的,而是被給予。執行長不必與中階經理進行格鬥士般的戰鬥,就能進駐邊間辦公室。懦夫和腐敗的政客,至少在民主政體中,需要一般大眾支持他們掌權。近來所揭露關於史丹佛監獄實驗的事,提升了壞人受權力吸引的可能性。但我們又為什麼容易因為錯誤的理由,而將權力交給不對的人?
二○○八年,瑞士研究人員進行一項實驗來測試這個假說。他們招募了六百八十一名當地兒童,年齡介於五歲到十三歲之間。這些孩童被要求玩一個電腦模擬遊戲,他們必須為一艘即將出航的船做出相關的決定。每個孩童都得依據出現在螢幕上的兩張臉,為他們的數位船挑選一位船長。此外沒有其他資料。如此的設計是為了迫使這些孩童決定:對你而言誰看起來像是個好船長?誰似乎可以成為你想像中的船隻的有效領導者?
孩子們不知道的是,這兩個可能的船長人選並不是隨機搭配。他們是最近在法國國會選舉中競選的政治人物。成對的臉隨機分配給這些孩童,但他們所看見的每一對組合都包含了勝選者和第二高票。研究的結果相當驚人:孩子們挑選出來的船長,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一的機率是贏得選舉的候選人。當研究人員改以成人為對象,進行相同的實驗時,他們驚訝地發現近乎相同的結果。研究結果有兩方面值得我們注意。首先,連兒童都能光憑長相就準確辨識出勝選者,突顯出我們對於領導潛力的評估方式是多麼膚淺。第二,在挑選掌權者時,兒童和成人的認知歷程並無根本上的差異。此事賦予憑表象(at face value)相信人這個片語新的意義。進一步的證據指出,我們挑選領導者的能力是有問題的,其他幾項研究也顯示在群體討論中,更具攻擊性或表現粗野的人會被視為比更樂意合作或更溫順的人,看起來更有權力和更像領導者。
沒錯,事情越變越複雜。權力可能使好人腐化,但也可能吸引壞人。身為人類,不知怎的我們似乎因為壞的理由而被壞的領導者吸引。
不幸的是,這種複雜性才只是起點,還有另一個需要考量的難題。假使掌權者之所以做壞事,並非因為他們原本就是壞人,不是因為得到權力之後變壞,而是因為他們受困於壞的體制呢?這個想法非常有道理。畢竟奉公守法可能會讓你在挪威晉升,但保證你永遠無法在烏茲別克獲得權力。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某些位高權重者是真正的了不起——他們一心幫助別人而非幫助自己。因此權力的誘惑和掌握權力的影響可能得視背景而定。幸好,背景和體制是可以改變的。這帶給我們一些好消息:或許我們不是注定要活在一個無法避免科內利玆式濫權領導的世界。
在印度班加羅爾(Bangalore)所進行的研究為上述的樂觀看法提供了一些證據。研究人員想看看什麼類型的人會被公職吸引,當地公家部門是以貪污受賄而聞名。印度文官提供了合適的試驗場,因為他們的貪污腐敗可謂惡名昭彰。人人都知道在班加羅爾當公務員有機會獲得灰色收入。在這個由兩位經濟學家所設計的實驗中,數百名大學生被要求投標準的骰子四十二次並記錄結果。當然,投骰子的結果全憑運氣。然而在投骰子之前,他們被告知如果他們運氣好,投出更高的點數,會獲得更多報酬。投出更多的四點、五點和六點可以賺到更多現金。
但由於結果是自行報告,學生可以謊報他們投骰子的結果。許多人的確這麼做。投出六點的次數佔百分之二十五,而一點只有百分之十。藉由統計分析,研究人員可以確定,如此偏差的結果不可能是因為運氣。有些學生甚至厚顏無恥地宣稱他們接連投出四十二次的六點。但這些數據透露出蹊蹺:在實驗中作弊的學生,他們的職業志向不同於誠實記錄的學生。比起一般學生,自行報告出造假的高點數的學生,有更多人表示他們想要加入腐敗的印度文官體系。
丹麥的另一組研究人員也做了類似的實驗——這個國家的文官體系乾淨且透明,卻獲得相反的結果。誠實地自行報告點數的學生更想要擔任公務員,而說謊的學生尋求能讓他們以骯髒手段致富的職業。腐敗的體制吸引腐敗的學生,誠實的體制吸引誠實的學生。或許這無關權力使人改變,而是與背景有關。好的體制能創造出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追求權力的良性循環。壞的體制則創造出讓人們為了爬到最高位,樂於說謊、欺騙和偷竊的惡性循環。如果這是事實,那麼我們應該關切的不是掌握權力的個人,而是修補不健全的體制。
關於這些惱人的複雜謎題,我們有一系列可能的解答。第一,權力讓人變得更壞——權力使人腐化。水田芥變成優酪乳帝國,在你還會意不過來之前,你已經匆匆投入選戰,用不屬於自己的錢買飛機。第二,並非權力使人腐化,而是比較糟糕的人會被權力吸引——權力吸引腐敗的人。心理病態的藥劑師忍不住要在一艘注定滅亡的船上攀登到最高位,而虐待狂無法抗拒穿上制服,用警棍毆打囚犯的誘惑。第三,問題不在掌握權力或追求權力的人身上,而是我們因為壞的理由而被壞的領導者吸引,我們還傾向於授予他們權力。我們的船長是基於不理性的原因被挑選出來——不只是想像中的船。當他們帶領我們撞上礁岩時,我們只能怪罪自己。還有第四,我們不應該將重點放在個別的掌權者,因為一切都取決於體制。壞的體制產生壞的領導者,只要創造出正確的背景環境,權力就能使人淨化而非使人腐化。
這些假說是關於人類社會的兩個最基本問題的可能解釋:誰得到權力以及權力如何改變我們。本書會提供答案。
拉瓦盧馬納納對於如何出奇制勝打贏選戰並不陌生,他對打破規則也無所顧忌。二○○六年時,他雖然佔有再度當選的優勢,但他不願意冒任何風險。他運用了一個新奇的手法來操縱選舉:他迫使他的主要對手被流放,然後阻止他返回家鄉登記參選。每當他的對手設法想回到馬達加斯加,拉瓦盧馬納納就拿起電話,下令關閉島上所有機場,導致對手所搭乘的飛機掉頭返航。這個辦法奏效了。由於這個對手不准從海外登記參選,所以不在候選人名單中。拉瓦盧馬納納於是大獲全勝。
二○○八年,拉瓦盧馬納納,一個出身寒微,參加教堂唱詩班和當過慈善志工的人——變得貪婪。在掌權六年後,他的內心似乎已經被某種事物改變。在一個每人年平均所得只有幾百美元的國家,他花費六千萬美元的國家基金購買了一架總統專機(有點野心勃勃地命名為「空軍二號」)。他設法將這架飛機的牌照登記在自己名下,而非馬達加斯加政府。拉瓦盧馬納納年復一年地掌握權力,他腐化的程度似乎越來越嚴重。
最終這將證明是他垮台的原因。二○○九年,一名暴發的廣播節目主持人轉行從政,他組織了抗議拉瓦盧馬納納總統的活動。這位前主持人在廣播節目中慫恿和平抗議者遊行到總統府。在他們到達時,保護優酪乳大亨的士兵朝他們開火。數十人被射死,激起人們的憤怒。街道上的血跡剛被清洗掉不久,拉瓦盧馬納納便在政變中被推翻,接管政府的軍方擁立這位主持人上台。
或許傳統看法是對的:權力確實使人腐化。五歲時的拉瓦盧馬納納只夢想著從兜售水田芥晉級到販賣優酪乳,他規規矩矩地做生意,為人並不殘暴。他幫助的是別人而非自己。但掌控馬達加斯加似乎改變了他,使他變得更壞。但這或許不是拉瓦盧馬納納的錯。那位廣播節目主持人總統最終可能變得比他所取代的乳品業大亨更腐敗。假使你或我突然被擁立為這個以貪腐而聞名的島國總統,我們也可能會墮落。這只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然而傳統觀念有時錯得離譜。假使權力並不會讓我們變得更好或更壞呢?假使權力只吸引某些類型的人——而那些人恰恰是不應該掌權的人?也許最想要權力的人正好是最不適合掌握權力的人。也許渴望權力的人比較容易墮落。
如果你曾閱讀通俗的心理學書籍,你很可能聽說過一個惡名昭彰的研究,這個研究似乎暗示權力確實使人腐化。只是有個問題:關於這個研究,你以為你知道的一切其實是錯的。
一九七一年暮夏,史丹佛大學的研究者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心理學系的地下室搭建一座模擬監獄。他招募了十八名大學生參與一項準科學研究,目的在判定社會角色是否會改變一般人的行為到不像話的程度。這個假說相當簡單:人類行為變化莫測。我們會配合我們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說我們所穿的制服。
為了測試這個假說是否為真,津巴多隨機指派其中九名自願參與者為「守衛」,其他九名參與者則成為「囚犯」。為了為期兩週、每天十五美元的報酬,他們必須進行一場過於真實的刑事司法角色扮演。接下來發生的事,如今變得惡名昭彰。守衛幾乎立刻開始虐待囚犯。他們用滅火器攻擊囚犯,拿走囚犯的床墊並強迫他們睡在混凝土地板上。扮演守衛的大學生剝光同儕的衣服,只為了顯示誰是老大。權力似乎使他們變得可怕。
在喪失人身控制權後,原本自豪、外向開朗的大學生變得封閉保守和順從。一名守衛在虐待完他的大學同儕後,命令囚犯排好隊以便羞辱他們。
「以後我說什麼,你就做什麼。」
「謝謝你,矯正官。」一名囚犯回答。
「再說一遍。」
「謝謝你,矯正官。」
「說『上帝保佑你,矯正官』。」
「上帝保佑你,矯正官。」
這項研究原本要持續進行兩個星期,但當津巴多的女朋友來探訪這座模擬監獄,她被所目睹的境況給嚇壞了,六天後,她說服津巴多停止了實驗。研究結果發表之後,舉世震驚。有人為此製作紀錄片,也有人寫書。證據似乎相當明確:權力能召喚出我們每個人心中的惡魔。
但這當中藏了一個圈套。看似直截了當的史丹佛監獄實驗故事,不是這麼清楚明白——這已成為心理學的傳統看法。守衛之中只有一些人濫用權力。有些守衛拒絕濫用權力,並給予大學生囚犯尊重的對待。因此,即便權力真的使人腐化,是否有人比其他人更加不受影響?
此外,如今有些囚犯和守衛表示,他們當年只是在進行表演。他們相信研究人員想要看見一場表演,於是便給他們一場表演。近來被揭露的實驗準備階段錄音,已經讓人質疑這些參與者是否因為受到指示而對囚犯苛刻,並非自然而然變卑鄙。因此,情況比我們被引導去相信的還要撲朔迷離些。
但即便有這些提醒,這個實驗仍然教人感到心寒。一般人如果在合適的環境下,是否都有可能變得殘酷和邪惡?一旦我們控制了別人,我們是否全都是等著被揭下面具的虐待狂?
幸好答案可能不是如此。津巴多的結論並沒有考慮到該研究的一個重要層面:參與者的招募方式。研究人員為了找來囚犯和守衛,在當地報紙刊登了以下的廣告:
徵求男性大學生參與監獄生活的心理學研究。自八月十四日起,為期一至兩週,每日報酬十五美元。欲知詳情與應徵,請洽……
二○○七年,西肯塔基大學的研究人員注意到廣告中似乎微不足道的細節。他們感到納悶,這是否已經不慎使該研究產生偏差。為了找出答案,他們複製了這則廣告,只將十五美元改成七十美元(因應一九七○年代以來的通貨膨脹所作的調整)。除此之外,更新後的廣告中每個字都一模一樣。後來,他們又創造一個新廣告,除了一個關鍵的差異,其他部分都相同:「參與監獄生活的心理學研究」改成「參與心理學研究」。他們在某些大學城放置「監獄生活」廣告,在其他大學城放置「心理研究」廣告。其概念是讓一組人自願參加監獄實驗,而另一組參加一般心理學研究。回應這兩則廣告的人會有什麼差異嗎?
招募期結束後,研究人員要求未來的研究參與者接受心理篩選和徹底的人格評估。他們的發現十分驚人。相較於回應一般心理學研究廣告的人,那些回應監獄實驗廣告的人在「侵略性、獨裁主義、馬基維利主義、自戀和社會優勢」的測量項目獲得相當高的分數,而在「同理心和利他主義傾向項目的得分明顯偏低」。只不過是在廣告中包含了監獄這個用語,結果便招來不成比例的一批殘酷成性的學生。
這個發現可能翻轉了史丹佛監獄實驗的結論,在根本上改變我們對權力的了解。史丹佛監獄實驗並沒有證明被賦予權力的一般人會變得殘酷,而是可能證明了殘酷成性的人會尋求權力。或許我們倒因為果。或許權力只是一塊吸引壞人的磁鐵,而非使好人變壞的一種力量。依此構想,權力不會使人腐化——它吸引腐敗者。
但仍有另一個謎。即便不適合掌權的人被權力吸引,他們為何似乎很容易獲得權力?畢竟在現代社會中,大量的控制不是奪取來的,而是被給予。執行長不必與中階經理進行格鬥士般的戰鬥,就能進駐邊間辦公室。懦夫和腐敗的政客,至少在民主政體中,需要一般大眾支持他們掌權。近來所揭露關於史丹佛監獄實驗的事,提升了壞人受權力吸引的可能性。但我們又為什麼容易因為錯誤的理由,而將權力交給不對的人?
二○○八年,瑞士研究人員進行一項實驗來測試這個假說。他們招募了六百八十一名當地兒童,年齡介於五歲到十三歲之間。這些孩童被要求玩一個電腦模擬遊戲,他們必須為一艘即將出航的船做出相關的決定。每個孩童都得依據出現在螢幕上的兩張臉,為他們的數位船挑選一位船長。此外沒有其他資料。如此的設計是為了迫使這些孩童決定:對你而言誰看起來像是個好船長?誰似乎可以成為你想像中的船隻的有效領導者?
孩子們不知道的是,這兩個可能的船長人選並不是隨機搭配。他們是最近在法國國會選舉中競選的政治人物。成對的臉隨機分配給這些孩童,但他們所看見的每一對組合都包含了勝選者和第二高票。研究的結果相當驚人:孩子們挑選出來的船長,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一的機率是贏得選舉的候選人。當研究人員改以成人為對象,進行相同的實驗時,他們驚訝地發現近乎相同的結果。研究結果有兩方面值得我們注意。首先,連兒童都能光憑長相就準確辨識出勝選者,突顯出我們對於領導潛力的評估方式是多麼膚淺。第二,在挑選掌權者時,兒童和成人的認知歷程並無根本上的差異。此事賦予憑表象(at face value)相信人這個片語新的意義。進一步的證據指出,我們挑選領導者的能力是有問題的,其他幾項研究也顯示在群體討論中,更具攻擊性或表現粗野的人會被視為比更樂意合作或更溫順的人,看起來更有權力和更像領導者。
沒錯,事情越變越複雜。權力可能使好人腐化,但也可能吸引壞人。身為人類,不知怎的我們似乎因為壞的理由而被壞的領導者吸引。
不幸的是,這種複雜性才只是起點,還有另一個需要考量的難題。假使掌權者之所以做壞事,並非因為他們原本就是壞人,不是因為得到權力之後變壞,而是因為他們受困於壞的體制呢?這個想法非常有道理。畢竟奉公守法可能會讓你在挪威晉升,但保證你永遠無法在烏茲別克獲得權力。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某些位高權重者是真正的了不起——他們一心幫助別人而非幫助自己。因此權力的誘惑和掌握權力的影響可能得視背景而定。幸好,背景和體制是可以改變的。這帶給我們一些好消息:或許我們不是注定要活在一個無法避免科內利玆式濫權領導的世界。
在印度班加羅爾(Bangalore)所進行的研究為上述的樂觀看法提供了一些證據。研究人員想看看什麼類型的人會被公職吸引,當地公家部門是以貪污受賄而聞名。印度文官提供了合適的試驗場,因為他們的貪污腐敗可謂惡名昭彰。人人都知道在班加羅爾當公務員有機會獲得灰色收入。在這個由兩位經濟學家所設計的實驗中,數百名大學生被要求投標準的骰子四十二次並記錄結果。當然,投骰子的結果全憑運氣。然而在投骰子之前,他們被告知如果他們運氣好,投出更高的點數,會獲得更多報酬。投出更多的四點、五點和六點可以賺到更多現金。
但由於結果是自行報告,學生可以謊報他們投骰子的結果。許多人的確這麼做。投出六點的次數佔百分之二十五,而一點只有百分之十。藉由統計分析,研究人員可以確定,如此偏差的結果不可能是因為運氣。有些學生甚至厚顏無恥地宣稱他們接連投出四十二次的六點。但這些數據透露出蹊蹺:在實驗中作弊的學生,他們的職業志向不同於誠實記錄的學生。比起一般學生,自行報告出造假的高點數的學生,有更多人表示他們想要加入腐敗的印度文官體系。
丹麥的另一組研究人員也做了類似的實驗——這個國家的文官體系乾淨且透明,卻獲得相反的結果。誠實地自行報告點數的學生更想要擔任公務員,而說謊的學生尋求能讓他們以骯髒手段致富的職業。腐敗的體制吸引腐敗的學生,誠實的體制吸引誠實的學生。或許這無關權力使人改變,而是與背景有關。好的體制能創造出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追求權力的良性循環。壞的體制則創造出讓人們為了爬到最高位,樂於說謊、欺騙和偷竊的惡性循環。如果這是事實,那麼我們應該關切的不是掌握權力的個人,而是修補不健全的體制。
關於這些惱人的複雜謎題,我們有一系列可能的解答。第一,權力讓人變得更壞——權力使人腐化。水田芥變成優酪乳帝國,在你還會意不過來之前,你已經匆匆投入選戰,用不屬於自己的錢買飛機。第二,並非權力使人腐化,而是比較糟糕的人會被權力吸引——權力吸引腐敗的人。心理病態的藥劑師忍不住要在一艘注定滅亡的船上攀登到最高位,而虐待狂無法抗拒穿上制服,用警棍毆打囚犯的誘惑。第三,問題不在掌握權力或追求權力的人身上,而是我們因為壞的理由而被壞的領導者吸引,我們還傾向於授予他們權力。我們的船長是基於不理性的原因被挑選出來——不只是想像中的船。當他們帶領我們撞上礁岩時,我們只能怪罪自己。還有第四,我們不應該將重點放在個別的掌權者,因為一切都取決於體制。壞的體制產生壞的領導者,只要創造出正確的背景環境,權力就能使人淨化而非使人腐化。
這些假說是關於人類社會的兩個最基本問題的可能解釋:誰得到權力以及權力如何改變我們。本書會提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