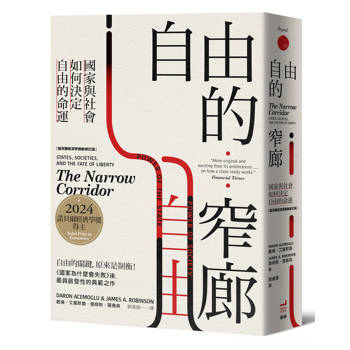有個常見論點認為,要建立國家的能力,必須徹底掌控安全與強大的武裝力量。很多人就是根據這種信念,主張中國可能是其他開發中國家(甚至可能是已開發國家)的模範,因為中國的國家機器能力這麼高強,原因之一是沒有人挑戰共產黨的宰制。但是,你更深入觀察時,會發現中國的國家巨靈雖然專制,擁有的能力卻不如美國或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國家,原因是中國沒有強而有力的社會可以逼迫國家、跟國家合作或跟國家的權力競爭。沒有這種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權力均衡時,紅皇后效應不會發揮作用,結果是產生能力比較差的國家巨靈。
要看出中國國家能力的成長性,你不必看得太深入,只需要看看教育體系。教育是很多國家重大施政中的重中之重,不僅因為受過教育的勞動力、會促使國家的發展比較成功,也是因為教育是把正確信念灌輸給公民的有效方法。因此,你會期望擁有強大能力的國家,應該能夠提供容易負擔的優質英才教育,動員公務員致力追求這種目標;但是,實情卻大不相同。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一切都可以出售,包括靠近黑板的前排座位和班長的位置。
趙華到北京一所小學替女兒註冊時,碰到區教育委員會的幾位官員,他們手中有一份名單,上面列出每個家庭必須繳交多少錢。這些官員並不經常出現在學校裡,但趙華卻必須在銀行裡存入四千八百美元進去,女兒才可以註冊。中小學教育是免費的,因此這些「費用」是非法的。從二○○五年起,政府已經下令禁止過五次(既然要禁五次,其中代表的意義就很明顯)。在北京的另一所菁英中學裡,家長每捐獻四千八百美元,學生的成績就會額外多得一分。如果你希望把小孩弄進頂尖的學校,例如跟北京著名的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送紅包的金額可能高達十三萬美元。老師也期望收禮—禮物愈多愈好。中國的新聞媒體報導指出,老師現在期望收的禮物包括設計師手錶、昂貴的高級茶葉、禮券,甚至是度假假期;比較積極的老師還歡迎附屬於銀行帳戶、全年可以補錢進去的轉帳卡。北京一位女企業家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說:「如果你不像其他家長那樣送好禮,你怕老師會比較不注意你的小孩。」
公務員怎麼可以這麼貪贓枉法?中國難道不是世界第一個用人唯賢的官僚制國家嗎?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們在第七章裡會發現,中國擁有歷史悠久的複雜、能幹官僚體系,但是貪腐橫行、用人唯親和買官鬻爵的歷史一樣悠長;這種歷史一直延續到今天。二○一五年內,一項針對三千六百七十一位共黨官員的訪調發現,高達三分之二的官員認為,獲得政府職位最重要的標準,是「政治忠誠」而非才能。一旦你聚攏親信,你就可以開始左右企業人士和公民,也可以藉著賣官創造聽話的下屬。政治學家貝敏新(Minxin Pei)分析二○○一年至二○一三年間,共黨官員涉貪定罪的五十個案例後,發現每一位官員平均賣了四十一個官位。底層賣官者包括安徽省五河縣的領導層張貴義和徐舍新,張貴義賣了十一個官位,平均價格為一萬二千元人民幣,折合美金的話,只有一千五百美元。徐舍新賣了五十八個職位。但是,在食物鏈比較上方,例如縣級單位,賣官所得高得多,有些官員在賣一個官位時,每個官位設法收取六萬美元。在貝敏新的研究裡,貪官靠著賣官,平均賺到十七萬美元。
張貴義和徐舍新只是小角色。鐵道部長劉志軍二○一一年遭到逮捕時,罪名是名下擁有三百五十棟公寓、現金超過一億美元。主因是中國的高鐵系統為貪污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良機,但是中國經濟擴張的其他絕大多數層面也一樣。劉志軍雖然垮臺了,其他人大都安然無恙。二○一二年內,中國一千位最富有的富人中,有一百六十位是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他們的財產淨值為二千二百一十億美元,大約是美國政府三權分立部門中六百六十位頂尖高官財產的二十倍,但是美國的人均所得是中國的七倍左右。所有這一切應該都不完全會令人驚訝,控制貪腐,不論是官僚體系還是教育體系中的貪腐,都需要社會的合作。國家機器需要信任人民會如實舉報,人民對國家機構的信任,必須到達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去舉報的程度;在專制國家巨靈的嚴厲凝視下,這種情形不會出現。
你可能認為,這點主要是貪腐問題,中國會不會是在國家機器能力高超的情況下,容忍貪腐呢?這種解釋不但牴觸中國國家持續打貪(卻只有少少成就)的企圖,也牴觸即使在貪腐之外,中國的國家機器難以勝任國家日常功能。就像我們討論黎巴嫩時說的那樣,讓社會瞭解國家機器似乎是任何自尊自重國家的首要任務,讓社會瞭解經濟狀況更是首要中的首要。的確如此,如果共產黨要證明自己宰制中國具有十足的理由,那麼,利用經濟成長來證明應該是其中關鍵。因此,對共黨而言,瞭解和精確衡量經濟活動一定是重點目標。但是,這種瞭解就像控制貪腐一樣,需要社會的合作;社會不合作時,問題就油然而生:企業會不會躲在非正式、沒有登記的部門中,尋求自保呢?個人會不會對自己不信任的國家隱匿消息呢?官僚會不會編造數據,以求升官發財呢?所有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在中國尤其如此。這點似乎是大家不相信中國國民所得統計的原因,連現任總理李克強在二○○七年升任總理前不久,都還形容中國的國民所得數字是「編造出來、不能相信」的東西,他建議避開官方的統計資料,注意電力消耗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放款,說這些資料更能衡量經濟狀況。既然如此,中國國家機器要說明經濟狀況的能力就不堪聞問了。
※※※
人們當然可以希望中國最後會變成對成長和秩序的焦慮比較少、比較自由、比較安全的社會。社會科學中有個叫做「現代化理論」的著名說法,認為國家富起來以後,會變得比較自由民主。我們是否能夠寄望中國出現這種轉變呢?答案是不大可能。將近二千五百年來,中國走在專制之路上,遠離自由窄廊,表示任何方向改變,都不可能一帆風順。寄望中國快速走到「歷史終結的盡頭」,也可能仍為虛無飄渺的幻想。
自由在專制政體中不容易萌芽,今天的中國也不例外。和中國極為貼近的臺灣和香港,雖然跟中國承襲相同的文化,卻創造出強力要求自由的社會,中國則走向不同的方向。
本書寫作之際,中國政府已經開始推動「社會信用制度」計畫,每一個中國人都會受到監視,獲得一個社會信用分數,政府會監視所有的線上活動,但是也要在全國各地,架設二億臺人臉辨識照相機,就像喬治.歐威爾在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中說的那樣:「老大哥正在監視你。」《一九八四》這本名著一九四九年出版時,上述做法在科技上是一種夢想,現在卻再也不是夢想了。擁有最高社會信用分數的人,在旅館和機場裡會得到優遇,優先進入菁英大學、找到最好的工作。如同這個計畫的宣傳文件所言:
守信者暢行天下,失信者寸步難行。
但是,究竟有多順暢自由呢?到超級市場買瓶烈酒是餿主意,你會失去幾分。如果親戚朋友做了當局不喜歡的事情,你也要扣分。你跟誰約會或結婚,也會影響你的分數。如果你做了共產黨不喜歡的決定,你會被排除在社會之外,不能旅行、租車或租屋,甚至找不到工作,這種事情聽來全都像牢籠,不是由社會規範創造的牢籠,而是由國家機器的監視器創造的牢籠。
社會信用心態及其對自由的意義,鮮明地表現在中國西部數百萬維吾爾族穆斯林家鄉的新疆省中。維吾爾族一直面對持續不斷的歧視、鎮壓、大規模囚禁,以及最嚴密的國家機器監偵技術的監視。現在他們必須忍受裝在自己家裡、監視自己一言一行的「老大哥和老大姐」們。
第一波這種社會監視器在二○一四年出現,當時中共大約派出二十萬共產黨員,前往新疆,「探視訪問人民、造福人民、收攬民心」,連他們也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下放到鄉下的都市居民一樣,受到維吾爾族的歡迎。到了二○一六年,第二波的十一萬臺監視器送到,作為「民族團結一家親」運動的先鋒,架設在家人遭到警察監禁或殺害的維吾爾族人家裡。第三波一百萬名共黨幹部於二○一七年抵達。這些大哥哥、大姐姐早上在地區中共黨部前面唱歌,勤奮地參加探討習主席「新中國」美夢的學習會。
維吾爾族不斷地遭到監視,為的是查驗他們忠誠與否,國語說得好不好?有沒有任何伊斯蘭拜墊或朝麥加跪拜的跡象?我是否聽到他們用阿拉伯語「祝你平安」(Assalamu alaikum)等伊斯蘭式問候語,跟別人打招呼?他們是否擁有一本《古蘭經》?齋月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對大部分人而言,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其實毫無自由。
要看出中國國家能力的成長性,你不必看得太深入,只需要看看教育體系。教育是很多國家重大施政中的重中之重,不僅因為受過教育的勞動力、會促使國家的發展比較成功,也是因為教育是把正確信念灌輸給公民的有效方法。因此,你會期望擁有強大能力的國家,應該能夠提供容易負擔的優質英才教育,動員公務員致力追求這種目標;但是,實情卻大不相同。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一切都可以出售,包括靠近黑板的前排座位和班長的位置。
趙華到北京一所小學替女兒註冊時,碰到區教育委員會的幾位官員,他們手中有一份名單,上面列出每個家庭必須繳交多少錢。這些官員並不經常出現在學校裡,但趙華卻必須在銀行裡存入四千八百美元進去,女兒才可以註冊。中小學教育是免費的,因此這些「費用」是非法的。從二○○五年起,政府已經下令禁止過五次(既然要禁五次,其中代表的意義就很明顯)。在北京的另一所菁英中學裡,家長每捐獻四千八百美元,學生的成績就會額外多得一分。如果你希望把小孩弄進頂尖的學校,例如跟北京著名的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送紅包的金額可能高達十三萬美元。老師也期望收禮—禮物愈多愈好。中國的新聞媒體報導指出,老師現在期望收的禮物包括設計師手錶、昂貴的高級茶葉、禮券,甚至是度假假期;比較積極的老師還歡迎附屬於銀行帳戶、全年可以補錢進去的轉帳卡。北京一位女企業家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說:「如果你不像其他家長那樣送好禮,你怕老師會比較不注意你的小孩。」
公務員怎麼可以這麼貪贓枉法?中國難道不是世界第一個用人唯賢的官僚制國家嗎?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們在第七章裡會發現,中國擁有歷史悠久的複雜、能幹官僚體系,但是貪腐橫行、用人唯親和買官鬻爵的歷史一樣悠長;這種歷史一直延續到今天。二○一五年內,一項針對三千六百七十一位共黨官員的訪調發現,高達三分之二的官員認為,獲得政府職位最重要的標準,是「政治忠誠」而非才能。一旦你聚攏親信,你就可以開始左右企業人士和公民,也可以藉著賣官創造聽話的下屬。政治學家貝敏新(Minxin Pei)分析二○○一年至二○一三年間,共黨官員涉貪定罪的五十個案例後,發現每一位官員平均賣了四十一個官位。底層賣官者包括安徽省五河縣的領導層張貴義和徐舍新,張貴義賣了十一個官位,平均價格為一萬二千元人民幣,折合美金的話,只有一千五百美元。徐舍新賣了五十八個職位。但是,在食物鏈比較上方,例如縣級單位,賣官所得高得多,有些官員在賣一個官位時,每個官位設法收取六萬美元。在貝敏新的研究裡,貪官靠著賣官,平均賺到十七萬美元。
張貴義和徐舍新只是小角色。鐵道部長劉志軍二○一一年遭到逮捕時,罪名是名下擁有三百五十棟公寓、現金超過一億美元。主因是中國的高鐵系統為貪污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良機,但是中國經濟擴張的其他絕大多數層面也一樣。劉志軍雖然垮臺了,其他人大都安然無恙。二○一二年內,中國一千位最富有的富人中,有一百六十位是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他們的財產淨值為二千二百一十億美元,大約是美國政府三權分立部門中六百六十位頂尖高官財產的二十倍,但是美國的人均所得是中國的七倍左右。所有這一切應該都不完全會令人驚訝,控制貪腐,不論是官僚體系還是教育體系中的貪腐,都需要社會的合作。國家機器需要信任人民會如實舉報,人民對國家機構的信任,必須到達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去舉報的程度;在專制國家巨靈的嚴厲凝視下,這種情形不會出現。
你可能認為,這點主要是貪腐問題,中國會不會是在國家機器能力高超的情況下,容忍貪腐呢?這種解釋不但牴觸中國國家持續打貪(卻只有少少成就)的企圖,也牴觸即使在貪腐之外,中國的國家機器難以勝任國家日常功能。就像我們討論黎巴嫩時說的那樣,讓社會瞭解國家機器似乎是任何自尊自重國家的首要任務,讓社會瞭解經濟狀況更是首要中的首要。的確如此,如果共產黨要證明自己宰制中國具有十足的理由,那麼,利用經濟成長來證明應該是其中關鍵。因此,對共黨而言,瞭解和精確衡量經濟活動一定是重點目標。但是,這種瞭解就像控制貪腐一樣,需要社會的合作;社會不合作時,問題就油然而生:企業會不會躲在非正式、沒有登記的部門中,尋求自保呢?個人會不會對自己不信任的國家隱匿消息呢?官僚會不會編造數據,以求升官發財呢?所有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在中國尤其如此。這點似乎是大家不相信中國國民所得統計的原因,連現任總理李克強在二○○七年升任總理前不久,都還形容中國的國民所得數字是「編造出來、不能相信」的東西,他建議避開官方的統計資料,注意電力消耗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放款,說這些資料更能衡量經濟狀況。既然如此,中國國家機器要說明經濟狀況的能力就不堪聞問了。
※※※
人們當然可以希望中國最後會變成對成長和秩序的焦慮比較少、比較自由、比較安全的社會。社會科學中有個叫做「現代化理論」的著名說法,認為國家富起來以後,會變得比較自由民主。我們是否能夠寄望中國出現這種轉變呢?答案是不大可能。將近二千五百年來,中國走在專制之路上,遠離自由窄廊,表示任何方向改變,都不可能一帆風順。寄望中國快速走到「歷史終結的盡頭」,也可能仍為虛無飄渺的幻想。
自由在專制政體中不容易萌芽,今天的中國也不例外。和中國極為貼近的臺灣和香港,雖然跟中國承襲相同的文化,卻創造出強力要求自由的社會,中國則走向不同的方向。
本書寫作之際,中國政府已經開始推動「社會信用制度」計畫,每一個中國人都會受到監視,獲得一個社會信用分數,政府會監視所有的線上活動,但是也要在全國各地,架設二億臺人臉辨識照相機,就像喬治.歐威爾在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中說的那樣:「老大哥正在監視你。」《一九八四》這本名著一九四九年出版時,上述做法在科技上是一種夢想,現在卻再也不是夢想了。擁有最高社會信用分數的人,在旅館和機場裡會得到優遇,優先進入菁英大學、找到最好的工作。如同這個計畫的宣傳文件所言:
守信者暢行天下,失信者寸步難行。
但是,究竟有多順暢自由呢?到超級市場買瓶烈酒是餿主意,你會失去幾分。如果親戚朋友做了當局不喜歡的事情,你也要扣分。你跟誰約會或結婚,也會影響你的分數。如果你做了共產黨不喜歡的決定,你會被排除在社會之外,不能旅行、租車或租屋,甚至找不到工作,這種事情聽來全都像牢籠,不是由社會規範創造的牢籠,而是由國家機器的監視器創造的牢籠。
社會信用心態及其對自由的意義,鮮明地表現在中國西部數百萬維吾爾族穆斯林家鄉的新疆省中。維吾爾族一直面對持續不斷的歧視、鎮壓、大規模囚禁,以及最嚴密的國家機器監偵技術的監視。現在他們必須忍受裝在自己家裡、監視自己一言一行的「老大哥和老大姐」們。
第一波這種社會監視器在二○一四年出現,當時中共大約派出二十萬共產黨員,前往新疆,「探視訪問人民、造福人民、收攬民心」,連他們也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下放到鄉下的都市居民一樣,受到維吾爾族的歡迎。到了二○一六年,第二波的十一萬臺監視器送到,作為「民族團結一家親」運動的先鋒,架設在家人遭到警察監禁或殺害的維吾爾族人家裡。第三波一百萬名共黨幹部於二○一七年抵達。這些大哥哥、大姐姐早上在地區中共黨部前面唱歌,勤奮地參加探討習主席「新中國」美夢的學習會。
維吾爾族不斷地遭到監視,為的是查驗他們忠誠與否,國語說得好不好?有沒有任何伊斯蘭拜墊或朝麥加跪拜的跡象?我是否聽到他們用阿拉伯語「祝你平安」(Assalamu alaikum)等伊斯蘭式問候語,跟別人打招呼?他們是否擁有一本《古蘭經》?齋月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對大部分人而言,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其實毫無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