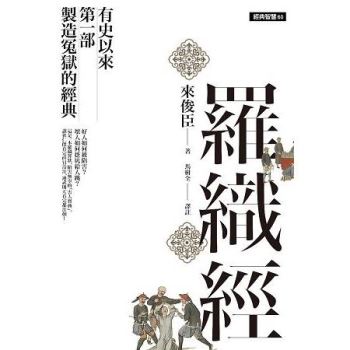原文
人皆可罪,罪人須定其人。罪不自昭,密而舉之則顯。
譯文
人都是可以定罪的,加罪於人必須先確定人選。罪行不會自動暴露,密告並檢舉他就會讓罪行顯現。
釋評
來俊臣、萬國俊之流,害人有一套完備的理論和方法,先確定人選,再由特務們向有關部門告密和寫檢舉信件,這便是他們害人的第一步驟。對象的確定是有學問的,他們不喜歡的人和皇上要排斥的人,自是對象之一;他們認為妨礙自己前途和有可能成為自己的對手的人,又是對象之二;至於那些德高望重和正直忠義的人,即使和他們無怨無仇,由於立場不同,自也是對象之三。如此只要他們能想像出來,任何人都可成為他們陷害的對象。
害人總要有些藉口,誣告和無中生有地揭發罪行,便為他們抓人作了很好的鋪墊。罪行屬實與否並不重要,只要是人落其手,他們便掌握了主動;只要人有了嫌疑,他們就有機可乘。這是輿論上的造勢,冤獄常便始於此處。
事典
狄仁傑的冤案
武則天當上女皇之後,重用武氏家族的人,以武承嗣為首的武姓宗戚一時人人顯貴,橫行朝野。宰相狄仁傑不肯諂媚他們,有時還頂撞武承嗣於朝堂之上,於是成了武承嗣等人的眼中釘,他們便思量陷害狄仁傑的毒計。
武承嗣找來來俊臣、萬國俊等酷吏商議此事,武承嗣先是罵了一頓狄仁傑,後說:「你們主管司法,明日便將他抓了,以解我心頭之氣。」
來俊臣不慌不忙地說:「大人此舉,怕是不妥。」
武承嗣把眼一橫,怒道:「你是為狄仁傑說情嗎?」
來俊臣忙道不敢,他諂媚說:「下官是為大人著想啊。那狄仁傑非比常人,皇上信賴於他,此人又頗有名望,如果沒有適當的罪名便貿然動手,皇上那裡都交待不了,又怎能置他於死地呢?依下官之見,我們還要廣造輿論,令其背上罪名,這樣下手就方便多了,皇上也不會再說什麼。」
武承嗣目現猶疑,萬國俊便在旁補充道:「來大人所言甚是。下官這就安排人手,告密、檢舉狄仁傑意圖謀反,大人再據此上奏皇上,這般雙管齊下,狄仁傑自是在劫難逃,大人也可不露痕跡了。」
武承嗣首肯此事,來俊臣、萬國俊便讓人到官府告密,給御史寫檢舉信。武承嗣拿著這些信件,上奏武則天。武則天將信將疑之下,便讓來俊臣、萬國俊等人審訊此案。
狄仁傑深知來俊臣等人的陰毒,為了麻痹他們,為自己贏得向武則天表白的時間,他竟在審訊時一口認下罪名,沒有一絲辯解。來俊臣等人十分驚訝,卻由此不再對他動用酷刑,只將他關在牢中,嚴加看管。
狄仁傑在獄中用血寫成鳴冤的表章,把它暗藏在棉衣裡面,讓獄吏送回家清洗。獄吏見是一件棉衣,沒有在意,便讓人送至其家。狄仁傑的兒子狄光遠,心知父親此刻送衣回家,必有緣故,他仔細拆開查看,於是拿出血書,直接上告到武則天那裡。武則天命人把狄仁傑押到她的面前,對他說:「你已招供,今又令子傳書,可是為何?」
狄仁傑連呼冤枉,口道:「當時酷吏在側,如我不招,必被其打死,又怎能面聖陳冤呢?他們造謠陷我,還請皇上明察。」
狄仁傑藉此又將酷吏的惡行講述一遍,武則天不置一詞;但因她憐惜狄仁傑之才,又有事倚重於他,這才將他釋放。
原文
人無不黨,罪一人可舉其眾;供必無缺,善修之毋違其真。事至此也,罪可成矣。
譯文
人沒有不結黨成群的,給一人定罪便可揭發出他的同夥;供狀必須沒有破綻,把被告供狀編撰修補,但又不違反真實的部分。事情做到這樣,罪名就可以成立了。
釋評
製造冤案、陷害無辜,酷吏們的手段不可不察。這裡既有他們的行事理論和思想,更有具體的實施方法和操作細節。認識了這些人們不僅從此看清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更重要的還是知己知彼,預防在先,以免受其害。許多人正是由於自恃身正無私,低估了酷吏興風作浪的能力才致禍的。更有人不識酷吏的「巧妙」手法和「瞞天」之術,往往在不知不覺中便被他們做成了「鐵案」,欺世盜名。
酷吏們借題發揮,把自己要打擊的人,硬是拉進一件與他們毫不相關的罪案中;然後又弄虛作假,讓所謂的口供完全合乎犯罪的邏輯和真實。如此一來,人證物證俱在,被陷害的人便在法律程式完備的情況下,被名正言順地定罪了。
事典
長孫無忌的誘供
長孫無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妻舅,深得李世民的信任。太子李承乾被廢後,李世民認為晉王李治懦弱寡斷,並不想立他為太子。李世民先是欲立魏王李泰,後因長孫無忌反對作罷;他一心想立吳王李恪,也因長孫無忌苦諫未果。為此,長孫無忌和二位王子都結下了仇怨,彼此為敵。
晉王李治後來登基即位,是為唐高宗。不久,魏王李泰去世,長孫無忌鬆了一口氣,便把目光集中在吳王李恪身上。他怕李恪一旦得勢,便會向他發洩不能成為太子和皇帝的怨恨,所以總想找機會把他除掉。
名相房玄齡之子房遺愛謀反案暴露後,長孫無忌負責審訊。他心中竊喜,信誓旦旦地對唐高宗說:「皇上所託,老臣決不辱命。以臣看來,房遺愛官小職微,恐不是真正的幕後元兇;如若審出要犯,事關皇上至親,還請皇上莫要仁慈,嚴加治罪,否則,老臣的命就不保了。」
高宗皇帝猜想這是長孫無忌或是為了行事方便,才會有如此要求,於是不暇思索地便答應下來。長孫無忌暗中得意,他之所以有此一說,原是早為他以後陷害吳王李恪打下伏筆,到時好讓高宗皇帝不以為驚,也可以堅持治他的罪,不使高宗皇帝有所偏袒。
房遺愛沒有其父的謀略和見識,他之所以心生反意,完全是受他那身為公主的夫人所惑。他的夫人淫蕩成性,廣招面首,後來醜事廣傳,夫人怕事發獲罪,於是鼓動房遺愛謀反。
長孫無忌接手此案,他先是對房遺愛動用重刑,後又對房遺愛說:「到了這個地步,你何必受皮肉之苦呢?你若招認,我也許還能幫你,求皇上法外施恩,免你一死。」
房遺愛受刑不住,又對長孫無忌心存幻想,便把同謀之人一一招出,不再抵賴。長孫無忌聽完,把臉一沉,厲聲喝道:「我如此對你,你卻不思立功贖罪,存心包庇奸臣,難道你真不想活了嗎?」
房遺愛連稱冤枉,他苦聲說:「大人關愛,罪人感激不盡,哪敢欺騙大人呢?就這些了,決無隱瞞。」
長孫無忌沉吟片刻,忽作一笑,他拍打了一下房遺愛的肩膀,低聲說:「你是個聰明人,自不會為別人開脫抵罪,自誤終生吧。吳王李恪一向自恃狂妄,他要當皇帝的野心日久,難道他就和此事無關?我勸你還是老實招認,有了幕後主謀,在皇上面前我才好為你說話呀。」
受此暗示,房遺愛為了自保脫罪,便信口胡說自己乃是受了吳王李恪的指使,他又東拉西扯,故意把事情編得有頭有尾。長孫無忌錄下口供,又反覆修改補充,直到此事編造得別人看不出虛假,他這才讓房遺愛簽字畫押,然後直接呈送給了高宗皇帝。
面對鐵證,高宗皇帝雖心有狐疑,卻不由得不信。結果此案中人皆被處死,吳王李恪卻是無罪冤死。長孫無忌見李恪已除,索性又把吳王的親信和他不滿的人,都牽進房遺愛的謀反案中,把他們統統發配嶺南。
人皆可罪,罪人須定其人。罪不自昭,密而舉之則顯。
譯文
人都是可以定罪的,加罪於人必須先確定人選。罪行不會自動暴露,密告並檢舉他就會讓罪行顯現。
釋評
來俊臣、萬國俊之流,害人有一套完備的理論和方法,先確定人選,再由特務們向有關部門告密和寫檢舉信件,這便是他們害人的第一步驟。對象的確定是有學問的,他們不喜歡的人和皇上要排斥的人,自是對象之一;他們認為妨礙自己前途和有可能成為自己的對手的人,又是對象之二;至於那些德高望重和正直忠義的人,即使和他們無怨無仇,由於立場不同,自也是對象之三。如此只要他們能想像出來,任何人都可成為他們陷害的對象。
害人總要有些藉口,誣告和無中生有地揭發罪行,便為他們抓人作了很好的鋪墊。罪行屬實與否並不重要,只要是人落其手,他們便掌握了主動;只要人有了嫌疑,他們就有機可乘。這是輿論上的造勢,冤獄常便始於此處。
事典
狄仁傑的冤案
武則天當上女皇之後,重用武氏家族的人,以武承嗣為首的武姓宗戚一時人人顯貴,橫行朝野。宰相狄仁傑不肯諂媚他們,有時還頂撞武承嗣於朝堂之上,於是成了武承嗣等人的眼中釘,他們便思量陷害狄仁傑的毒計。
武承嗣找來來俊臣、萬國俊等酷吏商議此事,武承嗣先是罵了一頓狄仁傑,後說:「你們主管司法,明日便將他抓了,以解我心頭之氣。」
來俊臣不慌不忙地說:「大人此舉,怕是不妥。」
武承嗣把眼一橫,怒道:「你是為狄仁傑說情嗎?」
來俊臣忙道不敢,他諂媚說:「下官是為大人著想啊。那狄仁傑非比常人,皇上信賴於他,此人又頗有名望,如果沒有適當的罪名便貿然動手,皇上那裡都交待不了,又怎能置他於死地呢?依下官之見,我們還要廣造輿論,令其背上罪名,這樣下手就方便多了,皇上也不會再說什麼。」
武承嗣目現猶疑,萬國俊便在旁補充道:「來大人所言甚是。下官這就安排人手,告密、檢舉狄仁傑意圖謀反,大人再據此上奏皇上,這般雙管齊下,狄仁傑自是在劫難逃,大人也可不露痕跡了。」
武承嗣首肯此事,來俊臣、萬國俊便讓人到官府告密,給御史寫檢舉信。武承嗣拿著這些信件,上奏武則天。武則天將信將疑之下,便讓來俊臣、萬國俊等人審訊此案。
狄仁傑深知來俊臣等人的陰毒,為了麻痹他們,為自己贏得向武則天表白的時間,他竟在審訊時一口認下罪名,沒有一絲辯解。來俊臣等人十分驚訝,卻由此不再對他動用酷刑,只將他關在牢中,嚴加看管。
狄仁傑在獄中用血寫成鳴冤的表章,把它暗藏在棉衣裡面,讓獄吏送回家清洗。獄吏見是一件棉衣,沒有在意,便讓人送至其家。狄仁傑的兒子狄光遠,心知父親此刻送衣回家,必有緣故,他仔細拆開查看,於是拿出血書,直接上告到武則天那裡。武則天命人把狄仁傑押到她的面前,對他說:「你已招供,今又令子傳書,可是為何?」
狄仁傑連呼冤枉,口道:「當時酷吏在側,如我不招,必被其打死,又怎能面聖陳冤呢?他們造謠陷我,還請皇上明察。」
狄仁傑藉此又將酷吏的惡行講述一遍,武則天不置一詞;但因她憐惜狄仁傑之才,又有事倚重於他,這才將他釋放。
原文
人無不黨,罪一人可舉其眾;供必無缺,善修之毋違其真。事至此也,罪可成矣。
譯文
人沒有不結黨成群的,給一人定罪便可揭發出他的同夥;供狀必須沒有破綻,把被告供狀編撰修補,但又不違反真實的部分。事情做到這樣,罪名就可以成立了。
釋評
製造冤案、陷害無辜,酷吏們的手段不可不察。這裡既有他們的行事理論和思想,更有具體的實施方法和操作細節。認識了這些人們不僅從此看清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更重要的還是知己知彼,預防在先,以免受其害。許多人正是由於自恃身正無私,低估了酷吏興風作浪的能力才致禍的。更有人不識酷吏的「巧妙」手法和「瞞天」之術,往往在不知不覺中便被他們做成了「鐵案」,欺世盜名。
酷吏們借題發揮,把自己要打擊的人,硬是拉進一件與他們毫不相關的罪案中;然後又弄虛作假,讓所謂的口供完全合乎犯罪的邏輯和真實。如此一來,人證物證俱在,被陷害的人便在法律程式完備的情況下,被名正言順地定罪了。
事典
長孫無忌的誘供
長孫無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妻舅,深得李世民的信任。太子李承乾被廢後,李世民認為晉王李治懦弱寡斷,並不想立他為太子。李世民先是欲立魏王李泰,後因長孫無忌反對作罷;他一心想立吳王李恪,也因長孫無忌苦諫未果。為此,長孫無忌和二位王子都結下了仇怨,彼此為敵。
晉王李治後來登基即位,是為唐高宗。不久,魏王李泰去世,長孫無忌鬆了一口氣,便把目光集中在吳王李恪身上。他怕李恪一旦得勢,便會向他發洩不能成為太子和皇帝的怨恨,所以總想找機會把他除掉。
名相房玄齡之子房遺愛謀反案暴露後,長孫無忌負責審訊。他心中竊喜,信誓旦旦地對唐高宗說:「皇上所託,老臣決不辱命。以臣看來,房遺愛官小職微,恐不是真正的幕後元兇;如若審出要犯,事關皇上至親,還請皇上莫要仁慈,嚴加治罪,否則,老臣的命就不保了。」
高宗皇帝猜想這是長孫無忌或是為了行事方便,才會有如此要求,於是不暇思索地便答應下來。長孫無忌暗中得意,他之所以有此一說,原是早為他以後陷害吳王李恪打下伏筆,到時好讓高宗皇帝不以為驚,也可以堅持治他的罪,不使高宗皇帝有所偏袒。
房遺愛沒有其父的謀略和見識,他之所以心生反意,完全是受他那身為公主的夫人所惑。他的夫人淫蕩成性,廣招面首,後來醜事廣傳,夫人怕事發獲罪,於是鼓動房遺愛謀反。
長孫無忌接手此案,他先是對房遺愛動用重刑,後又對房遺愛說:「到了這個地步,你何必受皮肉之苦呢?你若招認,我也許還能幫你,求皇上法外施恩,免你一死。」
房遺愛受刑不住,又對長孫無忌心存幻想,便把同謀之人一一招出,不再抵賴。長孫無忌聽完,把臉一沉,厲聲喝道:「我如此對你,你卻不思立功贖罪,存心包庇奸臣,難道你真不想活了嗎?」
房遺愛連稱冤枉,他苦聲說:「大人關愛,罪人感激不盡,哪敢欺騙大人呢?就這些了,決無隱瞞。」
長孫無忌沉吟片刻,忽作一笑,他拍打了一下房遺愛的肩膀,低聲說:「你是個聰明人,自不會為別人開脫抵罪,自誤終生吧。吳王李恪一向自恃狂妄,他要當皇帝的野心日久,難道他就和此事無關?我勸你還是老實招認,有了幕後主謀,在皇上面前我才好為你說話呀。」
受此暗示,房遺愛為了自保脫罪,便信口胡說自己乃是受了吳王李恪的指使,他又東拉西扯,故意把事情編得有頭有尾。長孫無忌錄下口供,又反覆修改補充,直到此事編造得別人看不出虛假,他這才讓房遺愛簽字畫押,然後直接呈送給了高宗皇帝。
面對鐵證,高宗皇帝雖心有狐疑,卻不由得不信。結果此案中人皆被處死,吳王李恪卻是無罪冤死。長孫無忌見李恪已除,索性又把吳王的親信和他不滿的人,都牽進房遺愛的謀反案中,把他們統統發配嶺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