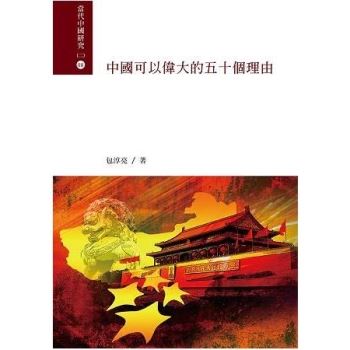葉鵬飛序
楚人遺弓,楚人得之——《中國可以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的臺灣視角
與淳亮兄相識,是被新加坡《聯合早報》派駐臺北期間(2003年至2005年)。若印象沒錯,我們初次見面,應該是在一場於北平路民主進步黨總部舉行的有關兩岸問題的座談會上。當時就微微感受到淳亮兄對於兩岸問題的關心。拜現代網絡科技之賜,離開臺北後,雖然沒能再見,但通過社交媒體,以及因負責《聯合早報》言論版之便,不時還有機會對他投來的大作先睹為快。如此以文會友,匆匆也有數年,故也對於淳亮兄這幾年就兩岸關係的觀察之細和用力之深,有了粗略的體會。
蒙他厚愛,請我為其時論文集《中國可以偉大的五十個理由》寫序。我自己在臺北報導了三年新聞,初到時正值「一邊一國」的提出,經歷了陳水扁總統時期兩岸關係緊張的年代,隨後在2005年轉駐北京,又逢《反分裂國家法》的訂立,算是分別在兩岸目睹了臺海當時的風起雲湧。在臺灣期間,開始對於「臺灣人主體性」有了感性的認識;在大陸時則觀察到其整體實力的不斷壯大,以及決策層的深謀遠慮。因此,在拜讀《五十個理由》時,感觸良多。
儘管作者在自序中表示,本書的預設讀者是中國人而非「外國人」,身為「習馬會」舉辦場所的新加坡人,在讀完這些篇章後,卻不由自主地聯想到「楚弓楚得」的典故。「楚王失弓」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讀,其中一種是關於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對比,因為孔子針對楚王「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的說法,提出了「人遺弓,人得之,何必楚也?」的反詰。我這裡並非就作者預設讀者對象而有所批評,只是認為《五十個理由》所收錄的文章,同時反映了作者清醒的立場意識,以及身為知識人的學術良心。
作者的立場,無疑是從臺灣的角度去觀察大陸。這種觀察也出自對臺灣未來利益的關懷。這在自序裡已經透露出來。作者表示,《五十個理由》的書名是針對2009年出版的《中國無法偉大的50個理由》,他不同意這本書的並非只是內容,更是立論的心態:「這類低估中國的書籍,只會使無視於現實的讀者繼續其鴕鳥心態,從而有害於自己、有害於社會,最終有害於世界。」
對於流行於臺灣社會輿論的這類心態,《五十個理由》裡的不少文章均一再提出批評,比如首篇〈以開放的態度認識中國〉,就開宗明義闡述了這個立場。作者對於一些因愛護臺灣,擔心被大陸併吞的臺灣人,選擇對大陸的發展不聞不問,或者一味「看衰」大陸的態度,做了必要的批判。他說:「只有先保持心靈的開放,保持一種自謙,才可能認識到不同的可能性,包括自己的偏見。然後再去檢驗前面提到的虛假、短暫、不義等假說,也許會發現那種種假說的不足。」
出於「同情理解」的態度,我相信自己能體會為何一些臺灣人會選擇對大陸的改變視而不見。大陸的不斷壯大所形成的威脅,的確會讓此消彼長之勢越來越明顯的臺灣社會,普遍感到無助。可是,這恰好也如作者所強調的那樣,對臺灣未來利益的關心,必須對大陸有清晰的認識,才能夠有趨吉避凶,自求多福的能力。(「樂觀看待中國的可能偉大,不僅是減少面對新世界時的挫敗感最好的方式,更是臺灣拯救自己的前提」——〈下一個世代的中國與世界〉)換一種較不客氣的說法,那些把大陸視為安全威脅的臺灣人,基於「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教訓,難道不更應該對「敵人」有細緻的了解嗎?
同理,這或許也是作者為何對中國大陸的前景樂觀,進而希望其「可以偉大」的原因。撇開「血濃於水」、「兄弟一家親」、「同文同種」等讓一些臺灣人感到不適的說法,從現實層面說,希望中國大陸穩定發展,並非僅是「與人為善」的道德情懷(從個人道德而言這自然也是應該的),更重要的是這符合臺灣的基本利益。新加坡人雖然不時會對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官方,在一些雙邊問題上偶爾表現出對小國的傲慢感到不滿,但是卻從來不會希望看到這兩個鄰國倒霉。道理很簡單,地緣政治的現實意味著唇亡齒寒的關係。從臺灣的立場思考,不穩定甚至陷入社會動亂的大陸,並非臺灣之福。所以,作者對於「中國可以偉大」的期待,完全是從臺灣也得以幸福的立場出發。
這個立場,可以從文集裡的不少篇章一窺究竟,最具代表性的首推〈「臺灣法」應該是什麼?〉。作者採取大陸「統一」的邏輯,理性地分析了為何北京必須言行一致,不能一方面宣稱臺灣屬於中國,卻又對「國民」實行差別待遇。義務必須同時有對等的權利,而且在操作上必須讓臺灣人先享有權利,才能要求他們履行義務。作者說:「如果大陸要將情感聯繫轉化為統一的基礎,則這種聯繫得有更明確的拘束力,以使臺灣人得以感受到其做為中國國民的身分。」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也是我以為這本書的讀者不應該只是大陸人,臺灣人更應該仔細參考的原因。
除了「楚人得之」的鮮明立場,作者並不缺乏「何必楚也」的普遍道德關懷。這也是我特別欣賞這本文集的另一個原因。這種知識人固有的學術良心,體現在作者從更大的角度,討論兩岸以外的國際課題。讓我印象深刻是關於金磚四國的崛起。作者認為與其擔心四國幾十億的總人口在經濟發展後,可能消耗更多自然資源、製造更多全球市場不易消化的廉價商品、提供發達國家員工難以競爭的廉價勞動力,不如思考解決之道。
他說:「金磚四國的發展,顯示『四、五十億發展遠遠落後的人口』的發展需要,對此學者有義務思考『怎麼辦』,回答『怎麼辦』。而其答案,絕不能是基於富國的自私、導向於遏制政策與保護政策、而終結於互相毀滅,而只能是基於道德公義、導向於自由貿易與自由遷徙,而最後促成『歷史的終結』。」這真是擲地有聲!
必須指出的是,在表達其「何必楚也」的普世關懷時,作者並沒有脫離他關注兩岸課題時的務實精神。對於知識人可能在思考時與現實脫節的危險,作者有著高度的自覺。他說:「公共知識分子的價值理性內涵不同於政治家,後者以國家遠景為念,前者則『我自一口真氣足』,以所受無上命令的道德關懷為起點。道德關懷碰上結構限制,就一心想打破之,但結構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客觀的經濟、物質生產力的問題,而公共知識分子卻往往無視於此。」(〈知識分子的藍圖與批判〉)
這種清醒的自覺,也表現在「敵人的敵人未必就是朋友」的觀察上。「這些進行著『陣地戰』的『反共』人士未必只是民間律師或具有堅定理想的志士,更可能是『披著紅旗反紅旗』、乃至於僅僅只是寄生於黨國體制中的各色機會主義者。後者的存在,意味著挖掘中共墳墓的各色人等的成功未必值得外界慶幸,他們許多甚至令人不恥。」(〈習近平肅貪:「歷史集團」向前行〉)
淳亮兄在委託我寫序時,希望我提出不同的意見,或者針鋒相對的批評。如果要吹毛求疵,我以為文集少選了從更大的歷史角度看待兩岸關係的文章。從文集的素材,我大概對淳亮兄的歷史觀能體察一二。但從說服臺灣讀者為何必須關心大陸發展的目的出發,這方面或許還是可以加強一些。法國的年鑒學派強調長時期的歷史視角,認為地理、物質等因素對歷史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套用這個史觀,則中國大陸的崛起,只是回復東亞的歷史常態。眼下南中國海的爭議,中國似乎被當成攪局的外來者。但是在很長的歷史時間裡,中國卻是區域的主角。由西方殖民主義者所建構的東亞地緣政治,只不過兩三百年時間。具備這樣的歷史眼光,或許有利於臺灣人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處境,更好地謀劃因應之道。
楚人遺弓,楚人得之——《中國可以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的臺灣視角
與淳亮兄相識,是被新加坡《聯合早報》派駐臺北期間(2003年至2005年)。若印象沒錯,我們初次見面,應該是在一場於北平路民主進步黨總部舉行的有關兩岸問題的座談會上。當時就微微感受到淳亮兄對於兩岸問題的關心。拜現代網絡科技之賜,離開臺北後,雖然沒能再見,但通過社交媒體,以及因負責《聯合早報》言論版之便,不時還有機會對他投來的大作先睹為快。如此以文會友,匆匆也有數年,故也對於淳亮兄這幾年就兩岸關係的觀察之細和用力之深,有了粗略的體會。
蒙他厚愛,請我為其時論文集《中國可以偉大的五十個理由》寫序。我自己在臺北報導了三年新聞,初到時正值「一邊一國」的提出,經歷了陳水扁總統時期兩岸關係緊張的年代,隨後在2005年轉駐北京,又逢《反分裂國家法》的訂立,算是分別在兩岸目睹了臺海當時的風起雲湧。在臺灣期間,開始對於「臺灣人主體性」有了感性的認識;在大陸時則觀察到其整體實力的不斷壯大,以及決策層的深謀遠慮。因此,在拜讀《五十個理由》時,感觸良多。
儘管作者在自序中表示,本書的預設讀者是中國人而非「外國人」,身為「習馬會」舉辦場所的新加坡人,在讀完這些篇章後,卻不由自主地聯想到「楚弓楚得」的典故。「楚王失弓」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讀,其中一種是關於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對比,因為孔子針對楚王「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的說法,提出了「人遺弓,人得之,何必楚也?」的反詰。我這裡並非就作者預設讀者對象而有所批評,只是認為《五十個理由》所收錄的文章,同時反映了作者清醒的立場意識,以及身為知識人的學術良心。
作者的立場,無疑是從臺灣的角度去觀察大陸。這種觀察也出自對臺灣未來利益的關懷。這在自序裡已經透露出來。作者表示,《五十個理由》的書名是針對2009年出版的《中國無法偉大的50個理由》,他不同意這本書的並非只是內容,更是立論的心態:「這類低估中國的書籍,只會使無視於現實的讀者繼續其鴕鳥心態,從而有害於自己、有害於社會,最終有害於世界。」
對於流行於臺灣社會輿論的這類心態,《五十個理由》裡的不少文章均一再提出批評,比如首篇〈以開放的態度認識中國〉,就開宗明義闡述了這個立場。作者對於一些因愛護臺灣,擔心被大陸併吞的臺灣人,選擇對大陸的發展不聞不問,或者一味「看衰」大陸的態度,做了必要的批判。他說:「只有先保持心靈的開放,保持一種自謙,才可能認識到不同的可能性,包括自己的偏見。然後再去檢驗前面提到的虛假、短暫、不義等假說,也許會發現那種種假說的不足。」
出於「同情理解」的態度,我相信自己能體會為何一些臺灣人會選擇對大陸的改變視而不見。大陸的不斷壯大所形成的威脅,的確會讓此消彼長之勢越來越明顯的臺灣社會,普遍感到無助。可是,這恰好也如作者所強調的那樣,對臺灣未來利益的關心,必須對大陸有清晰的認識,才能夠有趨吉避凶,自求多福的能力。(「樂觀看待中國的可能偉大,不僅是減少面對新世界時的挫敗感最好的方式,更是臺灣拯救自己的前提」——〈下一個世代的中國與世界〉)換一種較不客氣的說法,那些把大陸視為安全威脅的臺灣人,基於「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教訓,難道不更應該對「敵人」有細緻的了解嗎?
同理,這或許也是作者為何對中國大陸的前景樂觀,進而希望其「可以偉大」的原因。撇開「血濃於水」、「兄弟一家親」、「同文同種」等讓一些臺灣人感到不適的說法,從現實層面說,希望中國大陸穩定發展,並非僅是「與人為善」的道德情懷(從個人道德而言這自然也是應該的),更重要的是這符合臺灣的基本利益。新加坡人雖然不時會對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官方,在一些雙邊問題上偶爾表現出對小國的傲慢感到不滿,但是卻從來不會希望看到這兩個鄰國倒霉。道理很簡單,地緣政治的現實意味著唇亡齒寒的關係。從臺灣的立場思考,不穩定甚至陷入社會動亂的大陸,並非臺灣之福。所以,作者對於「中國可以偉大」的期待,完全是從臺灣也得以幸福的立場出發。
這個立場,可以從文集裡的不少篇章一窺究竟,最具代表性的首推〈「臺灣法」應該是什麼?〉。作者採取大陸「統一」的邏輯,理性地分析了為何北京必須言行一致,不能一方面宣稱臺灣屬於中國,卻又對「國民」實行差別待遇。義務必須同時有對等的權利,而且在操作上必須讓臺灣人先享有權利,才能要求他們履行義務。作者說:「如果大陸要將情感聯繫轉化為統一的基礎,則這種聯繫得有更明確的拘束力,以使臺灣人得以感受到其做為中國國民的身分。」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也是我以為這本書的讀者不應該只是大陸人,臺灣人更應該仔細參考的原因。
除了「楚人得之」的鮮明立場,作者並不缺乏「何必楚也」的普遍道德關懷。這也是我特別欣賞這本文集的另一個原因。這種知識人固有的學術良心,體現在作者從更大的角度,討論兩岸以外的國際課題。讓我印象深刻是關於金磚四國的崛起。作者認為與其擔心四國幾十億的總人口在經濟發展後,可能消耗更多自然資源、製造更多全球市場不易消化的廉價商品、提供發達國家員工難以競爭的廉價勞動力,不如思考解決之道。
他說:「金磚四國的發展,顯示『四、五十億發展遠遠落後的人口』的發展需要,對此學者有義務思考『怎麼辦』,回答『怎麼辦』。而其答案,絕不能是基於富國的自私、導向於遏制政策與保護政策、而終結於互相毀滅,而只能是基於道德公義、導向於自由貿易與自由遷徙,而最後促成『歷史的終結』。」這真是擲地有聲!
必須指出的是,在表達其「何必楚也」的普世關懷時,作者並沒有脫離他關注兩岸課題時的務實精神。對於知識人可能在思考時與現實脫節的危險,作者有著高度的自覺。他說:「公共知識分子的價值理性內涵不同於政治家,後者以國家遠景為念,前者則『我自一口真氣足』,以所受無上命令的道德關懷為起點。道德關懷碰上結構限制,就一心想打破之,但結構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客觀的經濟、物質生產力的問題,而公共知識分子卻往往無視於此。」(〈知識分子的藍圖與批判〉)
這種清醒的自覺,也表現在「敵人的敵人未必就是朋友」的觀察上。「這些進行著『陣地戰』的『反共』人士未必只是民間律師或具有堅定理想的志士,更可能是『披著紅旗反紅旗』、乃至於僅僅只是寄生於黨國體制中的各色機會主義者。後者的存在,意味著挖掘中共墳墓的各色人等的成功未必值得外界慶幸,他們許多甚至令人不恥。」(〈習近平肅貪:「歷史集團」向前行〉)
淳亮兄在委託我寫序時,希望我提出不同的意見,或者針鋒相對的批評。如果要吹毛求疵,我以為文集少選了從更大的歷史角度看待兩岸關係的文章。從文集的素材,我大概對淳亮兄的歷史觀能體察一二。但從說服臺灣讀者為何必須關心大陸發展的目的出發,這方面或許還是可以加強一些。法國的年鑒學派強調長時期的歷史視角,認為地理、物質等因素對歷史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套用這個史觀,則中國大陸的崛起,只是回復東亞的歷史常態。眼下南中國海的爭議,中國似乎被當成攪局的外來者。但是在很長的歷史時間裡,中國卻是區域的主角。由西方殖民主義者所建構的東亞地緣政治,只不過兩三百年時間。具備這樣的歷史眼光,或許有利於臺灣人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處境,更好地謀劃因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