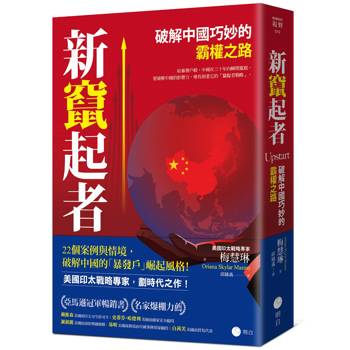導論 中國崛起,晉身強權俱樂部一員
三十年前,幾乎沒有人能夠想像中國可以在經濟、全球事務和軍事領域挑戰美國。冷戰結束後,美國不僅成為史上最強大的國家,還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並在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九年之間達成經濟成長率年平均四%。美國建立了廣泛的軍事聯盟網路,其國內生產毛額(GDP)超過中國十六倍以上。美國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主導建立了一系列國際組織,並透過這些組織與盟友維繫全球主導地位。
相較之下,二○○○年的中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局面。當時,中國的經濟僅占全球GDP的三%,甚至低於法國。同一年,中國的手機用戶不到總人口的七%,而網路使用者的比例甚至低於二%。雖然中國擁有約四百萬人的龐大軍隊,但這更多反映了其「落後」的現狀,而非「實力」。由於裝備過時、訓練不足,中國幾乎不算擁有真正的空軍和海軍。當時,中國飛行員無法在海上飛行,更無法應對夜間或惡劣天氣。一九九九年,中國的第四代戰鬥機僅占總數不到二%,符合當代標準的攻擊型潛艇不到四%,水面艦艇也完全不具備現代化水準。事實上,中國海軍更像是一支「放大版的海岸警衛隊」,因為艦艇缺乏防空系統,巡邏時只能貼近海岸行動。中國的核武系統主要依賴固定式的發射井並使用固體燃料,極易在先制攻擊中就被徹底摧毀。冷戰結束後,北京在國際上依然處於孤立狀態,無法參與像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樣的國際機構,也未與包括南韓在內的多個區域強權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本書的敘述由此展開──中國領導人意識到中美兩國之間巨大的實力差距,並希望縮小這一差距。在當時,美國處於無可挑戰的「單極」優勢地位,尤其在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美軍的軍事表現令人驚嘆,充分突顯出強大實力。自波斯灣戰爭以後,從江澤民到習近平,每一任的中國領導人都希望提高中國的實力,重塑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進而擺脫過去數十年來被強權壓制與羞辱的歷史。然而,對實力與影響力的追求並非中國行為的唯一動機──中國共產黨(中共)堅持以強有力的國家控制來維持其國內權力。同時,這種控制也塑造出獨特的「中國式競爭」,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以及中國自身均造成一些困境。在新千禧年的開端,中國因國內因素,突顯出採取謹慎戰略的重要性。唯有如此,北京才能在美國主導的世界中競逐權力與影響力,且不至於因為威脅到華盛頓的利益而遭到強烈反制。
接下來隨著時間演進,中國出乎意料地「脫胎換骨」。二○一○年,中國經濟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甚至已超過日本、印度和德國經濟的總和。從一九九○年到二○一○年間,北京擁有的國際組織會員總數翻了一倍,並在聯合國(UN)等組織中表現得更為積極主動。中國還在一九九○年代與二十八個國家實現了「關係正常化」。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間,中國從外交孤立蛻變成在全球舞台上擁有與美國相當的外交和政治影響力(根據某些衡量標準,甚至略為超越美國)。截至二○二一年,中國已成為一百二十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當中包含美國所有的印太地區盟友。
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同樣令人歎為觀止。這得益於從一九九二年到二○二○年間增長了七百九十%的國防預算,如今中國的軍事裝備多數已達到現代化水準,這意味著從戰鬥機到反衛星雷射技術的任何裝備都已足夠先進,足以對最尖端的技術構成威脅。換句話說,中國現在能對世界上最先進的軍隊構成威脅,並有信心不會因技術與裝備上的劣勢而在交戰中失利。中國的核武力量現在具備生存能力,即使遭遇先發制人的攻擊,仍能保有足夠的核彈頭與投射系統以進行報復性核子打擊。二○一○年十月,中國測試了全球首枚高超音速核子飛彈,成為首個進行此類測試的國家,此舉促使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麥利(Mark Milley)對外表示:「他們已經從一九七九年的一支龐大而落後的農民軍隊,成長為一支在所有領域都極具實力的現代化軍隊。」確實,中國目前的科學家人數比美國多出約二萬人,且在過去二十五年內,每年平均的研發支出成長率達到十五%(相較之下,美國僅為三%),因此,中國在許多與戰爭相關的新興技術領域被認為比美國更加先進,例如人工智慧、高超音速技術以及量子計算。
傳統軍事指標同樣顯示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進步幅度之大。過去,中國飛行員無法飛越距離中國海岸線僅約四十英里的台灣海峽中線,而如今他們幾乎每天都在進行此類飛行任務。從二○二○年九月至二○二一年九月,中國軍機在台灣防空識別區(ADIZ)內進行了二百五十天的飛行活動,且入侵次數與參與飛機架數均呈現上升趨勢。早期,中國艦艇很少遠離本土海岸進行活動,但如今已在南海、東海和印度洋巡航。中國尚未擁有「藍水海軍」──即能在遠離本土的全球水域運作的海軍力量,但憑藉著位於吉布地的軍事基地及例行性的港口巡航,中國已經展現出一定的全球存在感。中國海軍目前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海軍,擁有三百五十五艘各式艦艇(不過在總噸位上尚未達到美國海軍的水準)。中國還擁有全球最大且技術最先進的彈道飛彈和巡航飛彈工程計劃,包括一種能擊中海上移動目標的反艦彈道飛彈(ASBM),這是美國目前尚未具備的武器。
為了縮小在外交、經濟和軍事實力上的相對差距,中國的戰略不僅需要具備效能,還必須極具效率。如果效率不足,中國將無法成功追趕,甚至可能面臨內部崩潰的風險。北京還必須設法避免引發美國的強烈反應,因為這可能摧毀其努力,抬高成本,甚至可能導致內部危機或觸發一場終結中國崛起的預防性戰爭。中國需要在實力最大化、霸主國(美國)的反應、國內穩定與繁榮之間找到平衡,並且必須靈活應對不斷變化的國際與國內環境。答案在於一種「竄起者策略」。
竄起者策略
二○二一年三月,美國總統拜登的新任團隊前往阿拉斯加,首次與其中國對手會面。儘管會前雙方都抱持著高度期望,但此次會議的氣氛並不友好。中國方面無意聽取美國列舉中國在西藏、香港及新疆的人權以及外交政策上的一連串違反普世價值的行為。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更直接回嗆:「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以實力高人一等的姿態對中國說話。」
這場峰會中的表態雖然帶有一些表演性質,但楊潔篪的言論並非毫無根據。中美之間的相對實力差距已顯著縮小,甚至在某些領域,中國已經取得領先。如習近平在二○二二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所言:「我國發展具備了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在過去三十年中,中國是如何試圖建立實力和影響力的?是哪些因素決定了北京採取的策略?本書提出我的答案:「竄起者策略」。「竄起者」(upstart,在英文中同時也有暴發戶、新貴的意思)意指一個從低位突然迅速崛起,取得權力、財富或地位的實體。這一詞彙常帶有貶義,形容那些被認為自大、傲慢或咄咄逼人,最近剛開始從事某種活動並成功,卻未對前輩展現出應有尊重的人。然而,我所使用的這個術語並不完全是貶義,當「upstart」用來描述「新創公司」時,帶有中性意味。「竄起者策略」的靈感來自商業研究中的競爭理論。儘管在國際關係中新興勢力及重大衝突相對來說較為罕見,但在商業上以新興手法顛覆整個行業以及導致企業破產的案例卻屢見不鮮,因此商業研究中已有成熟的研究傳統,透過大量案例的測試與修正,探討新興企業如何擊敗並取代老牌成熟企業。
我的「竄起者策略」包括三個組成部分,以競爭領域和新興強權的行動模式來定義:模仿(emulation)、利用(exploitation)和創新(entrepreneurship),簡稱「三E策略」。模仿是指一個國家在現有競爭領域中,用和既有霸權相同的方式進行競爭。大多數現有文獻關注這種競爭形式,認為有志成為強權的國家會以已被證明有效的方法建立和運用實力。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利用,指新興強權在新的競爭領域採用類似於既有霸權的方法。例如,中國會在美國競爭力最弱的地方抓住機會──美國未積極參與或存在弱點的領域、國際秩序中的漏洞,或規範環境較弱的地方。最後一個組成部分是創新,涉及在新舊競爭領域中採取全新的方法。圖0.1中的維恩圖表示了這一策略的關係和區分。
探討商業競爭的文獻為每種方法的利弊提供了一些見解。例如,在某些領域,模仿可能是新興國家崛起最快且最有效的方式。模仿通常被視為「遵循既定規則」,這有助於新興國家在避免引發反彈或被其他強權制衡的情況下積累實力。然而,模仿也可能面臨高昂的成本且進展緩慢。在最壞的情況下,模仿可能因強權的競爭性反應而充滿風險。若新興國家在應對這些反應時欠缺競爭優勢,模仿策略可能最終成為徒勞的嘗試。
關於「竄起者策略」的第二個組成部分「利用」,商業領域中有些市占率低而企圖心強的競爭者,善加利用既有領導企業的盲點,擊敗他們而成為新的市場領導者。這樣的做法正是新興國家效法的對象。這一策略的實行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①存在可利用的盲點──既有霸權因忽視、欠缺能力或認為該領域增長空間有限而未積極參與競爭的領域;②新興國家在這些領域具有一定優勢。此時,新興國家便可採用已被證明有效的方式,但無需直接與既有霸權競爭。若新興國家在相關領域擁有競爭優勢,這是一種相對高效的實力構建方式。
最後一個組成部分──創新,也有其優勢。一種全新的方法可能不會被視為對既有霸權地位的直接挑戰,因此不會立即引發其他國家的制衡行動。儘管創新可能比模仿(已被驗證的方式)更具風險,但若成功,其崛起速度和效率可能遠比模仿更快。更具創意的策略還可能使新興國家在新的戰略領域獲得「先行者優勢」或充分利用其獨特的競爭優勢。成功挑戰領導者的競爭者往往能「以創意破壞根深蒂固的信念」,重新定義最佳建構與行使實力的方式。然而,創新並非毫無風險,這條道路並無明確的藍圖,採用不同尋常的策略也可能導致新興勢力的失敗。
從以上這項討論中,我們可以得出有五個主要因素會決定新興國家會採用「三E策略」中的哪一個:既有霸權策略的有效性、霸權對行為的最可能解讀、特定方法的效率(主要由競爭優勢塑造)、方法的侷限性以及是否存在差距與盲點。以中國的崛起而言,這意味著當中國評估美國的方法有效、模仿行為能使西方國家放心,且中國在相關領域具備競爭優勢以確保戰略效力時,往往會選擇模仿美國。例如,中國的外交推進、調解以及嘗試加入新的國際機構均屬於此類。當上述條件成立但中國因自身能力限制而無法直接參與競爭時,中國會意識到差距,並選擇在這些領域採行「利用盲點」策略。
新興策略的最後一個組成部分對中國的崛起最為關鍵。當中國認為美國的策略無效或是可能對黨造成風險,亦或採用美國的方法可能會引發強烈的負面威脅感時,中國便會尋求創新的實力建構途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會設計出一種新的方式來建立某種類型的實力,這種方式能夠充分利用中國的競爭優勢,並降低其弱點的影響。例如,中國建設商業港口設施,而非海外軍事基地,來保護其海外利益,或者訓練當地執法部門而非外國軍隊以謀求建立良好關係。
探討中國如何競逐強權地位
我們的敘述始於一九九○年代中期,這一時期通常被認為是中國地緣政治崛起的起點。在此期間中國領導人做出關鍵的戰略決策,將目光從單純追求國內經濟成長拓展到國際舞台,著手構建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本書試圖透過深入分析二十二個案例,探討中國領導人如何在這些情境中做出決策,以實現特定的戰略目標。
這三十年(約從一九九三年至二○二三年)也與中國對自身發展軌跡的認知相吻合。鄧小平曾將冷戰後的三十年稱為「追趕」的時期,並強調「抓住機遇」的重要性。知名中國學者鄭必堅在二○○○年初提出中國「和平崛起」的概念,而在二○○三年溫家寶總理於哈佛大學演講後,官方文本和講話中開始公開討論中國的崛起。到新冠疫情爆發前夕,官方和學術界的評估已經普遍接受中國成功的縮小了與美國的實力差距,可以被視為一個強權。
三十年前,幾乎沒有人能夠想像中國可以在經濟、全球事務和軍事領域挑戰美國。冷戰結束後,美國不僅成為史上最強大的國家,還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並在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九年之間達成經濟成長率年平均四%。美國建立了廣泛的軍事聯盟網路,其國內生產毛額(GDP)超過中國十六倍以上。美國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主導建立了一系列國際組織,並透過這些組織與盟友維繫全球主導地位。
相較之下,二○○○年的中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局面。當時,中國的經濟僅占全球GDP的三%,甚至低於法國。同一年,中國的手機用戶不到總人口的七%,而網路使用者的比例甚至低於二%。雖然中國擁有約四百萬人的龐大軍隊,但這更多反映了其「落後」的現狀,而非「實力」。由於裝備過時、訓練不足,中國幾乎不算擁有真正的空軍和海軍。當時,中國飛行員無法在海上飛行,更無法應對夜間或惡劣天氣。一九九九年,中國的第四代戰鬥機僅占總數不到二%,符合當代標準的攻擊型潛艇不到四%,水面艦艇也完全不具備現代化水準。事實上,中國海軍更像是一支「放大版的海岸警衛隊」,因為艦艇缺乏防空系統,巡邏時只能貼近海岸行動。中國的核武系統主要依賴固定式的發射井並使用固體燃料,極易在先制攻擊中就被徹底摧毀。冷戰結束後,北京在國際上依然處於孤立狀態,無法參與像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樣的國際機構,也未與包括南韓在內的多個區域強權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本書的敘述由此展開──中國領導人意識到中美兩國之間巨大的實力差距,並希望縮小這一差距。在當時,美國處於無可挑戰的「單極」優勢地位,尤其在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美軍的軍事表現令人驚嘆,充分突顯出強大實力。自波斯灣戰爭以後,從江澤民到習近平,每一任的中國領導人都希望提高中國的實力,重塑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進而擺脫過去數十年來被強權壓制與羞辱的歷史。然而,對實力與影響力的追求並非中國行為的唯一動機──中國共產黨(中共)堅持以強有力的國家控制來維持其國內權力。同時,這種控制也塑造出獨特的「中國式競爭」,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以及中國自身均造成一些困境。在新千禧年的開端,中國因國內因素,突顯出採取謹慎戰略的重要性。唯有如此,北京才能在美國主導的世界中競逐權力與影響力,且不至於因為威脅到華盛頓的利益而遭到強烈反制。
接下來隨著時間演進,中國出乎意料地「脫胎換骨」。二○一○年,中國經濟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甚至已超過日本、印度和德國經濟的總和。從一九九○年到二○一○年間,北京擁有的國際組織會員總數翻了一倍,並在聯合國(UN)等組織中表現得更為積極主動。中國還在一九九○年代與二十八個國家實現了「關係正常化」。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間,中國從外交孤立蛻變成在全球舞台上擁有與美國相當的外交和政治影響力(根據某些衡量標準,甚至略為超越美國)。截至二○二一年,中國已成為一百二十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當中包含美國所有的印太地區盟友。
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同樣令人歎為觀止。這得益於從一九九二年到二○二○年間增長了七百九十%的國防預算,如今中國的軍事裝備多數已達到現代化水準,這意味著從戰鬥機到反衛星雷射技術的任何裝備都已足夠先進,足以對最尖端的技術構成威脅。換句話說,中國現在能對世界上最先進的軍隊構成威脅,並有信心不會因技術與裝備上的劣勢而在交戰中失利。中國的核武力量現在具備生存能力,即使遭遇先發制人的攻擊,仍能保有足夠的核彈頭與投射系統以進行報復性核子打擊。二○一○年十月,中國測試了全球首枚高超音速核子飛彈,成為首個進行此類測試的國家,此舉促使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麥利(Mark Milley)對外表示:「他們已經從一九七九年的一支龐大而落後的農民軍隊,成長為一支在所有領域都極具實力的現代化軍隊。」確實,中國目前的科學家人數比美國多出約二萬人,且在過去二十五年內,每年平均的研發支出成長率達到十五%(相較之下,美國僅為三%),因此,中國在許多與戰爭相關的新興技術領域被認為比美國更加先進,例如人工智慧、高超音速技術以及量子計算。
傳統軍事指標同樣顯示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進步幅度之大。過去,中國飛行員無法飛越距離中國海岸線僅約四十英里的台灣海峽中線,而如今他們幾乎每天都在進行此類飛行任務。從二○二○年九月至二○二一年九月,中國軍機在台灣防空識別區(ADIZ)內進行了二百五十天的飛行活動,且入侵次數與參與飛機架數均呈現上升趨勢。早期,中國艦艇很少遠離本土海岸進行活動,但如今已在南海、東海和印度洋巡航。中國尚未擁有「藍水海軍」──即能在遠離本土的全球水域運作的海軍力量,但憑藉著位於吉布地的軍事基地及例行性的港口巡航,中國已經展現出一定的全球存在感。中國海軍目前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海軍,擁有三百五十五艘各式艦艇(不過在總噸位上尚未達到美國海軍的水準)。中國還擁有全球最大且技術最先進的彈道飛彈和巡航飛彈工程計劃,包括一種能擊中海上移動目標的反艦彈道飛彈(ASBM),這是美國目前尚未具備的武器。
為了縮小在外交、經濟和軍事實力上的相對差距,中國的戰略不僅需要具備效能,還必須極具效率。如果效率不足,中國將無法成功追趕,甚至可能面臨內部崩潰的風險。北京還必須設法避免引發美國的強烈反應,因為這可能摧毀其努力,抬高成本,甚至可能導致內部危機或觸發一場終結中國崛起的預防性戰爭。中國需要在實力最大化、霸主國(美國)的反應、國內穩定與繁榮之間找到平衡,並且必須靈活應對不斷變化的國際與國內環境。答案在於一種「竄起者策略」。
竄起者策略
二○二一年三月,美國總統拜登的新任團隊前往阿拉斯加,首次與其中國對手會面。儘管會前雙方都抱持著高度期望,但此次會議的氣氛並不友好。中國方面無意聽取美國列舉中國在西藏、香港及新疆的人權以及外交政策上的一連串違反普世價值的行為。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更直接回嗆:「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以實力高人一等的姿態對中國說話。」
這場峰會中的表態雖然帶有一些表演性質,但楊潔篪的言論並非毫無根據。中美之間的相對實力差距已顯著縮小,甚至在某些領域,中國已經取得領先。如習近平在二○二二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所言:「我國發展具備了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在過去三十年中,中國是如何試圖建立實力和影響力的?是哪些因素決定了北京採取的策略?本書提出我的答案:「竄起者策略」。「竄起者」(upstart,在英文中同時也有暴發戶、新貴的意思)意指一個從低位突然迅速崛起,取得權力、財富或地位的實體。這一詞彙常帶有貶義,形容那些被認為自大、傲慢或咄咄逼人,最近剛開始從事某種活動並成功,卻未對前輩展現出應有尊重的人。然而,我所使用的這個術語並不完全是貶義,當「upstart」用來描述「新創公司」時,帶有中性意味。「竄起者策略」的靈感來自商業研究中的競爭理論。儘管在國際關係中新興勢力及重大衝突相對來說較為罕見,但在商業上以新興手法顛覆整個行業以及導致企業破產的案例卻屢見不鮮,因此商業研究中已有成熟的研究傳統,透過大量案例的測試與修正,探討新興企業如何擊敗並取代老牌成熟企業。
我的「竄起者策略」包括三個組成部分,以競爭領域和新興強權的行動模式來定義:模仿(emulation)、利用(exploitation)和創新(entrepreneurship),簡稱「三E策略」。模仿是指一個國家在現有競爭領域中,用和既有霸權相同的方式進行競爭。大多數現有文獻關注這種競爭形式,認為有志成為強權的國家會以已被證明有效的方法建立和運用實力。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利用,指新興強權在新的競爭領域採用類似於既有霸權的方法。例如,中國會在美國競爭力最弱的地方抓住機會──美國未積極參與或存在弱點的領域、國際秩序中的漏洞,或規範環境較弱的地方。最後一個組成部分是創新,涉及在新舊競爭領域中採取全新的方法。圖0.1中的維恩圖表示了這一策略的關係和區分。
探討商業競爭的文獻為每種方法的利弊提供了一些見解。例如,在某些領域,模仿可能是新興國家崛起最快且最有效的方式。模仿通常被視為「遵循既定規則」,這有助於新興國家在避免引發反彈或被其他強權制衡的情況下積累實力。然而,模仿也可能面臨高昂的成本且進展緩慢。在最壞的情況下,模仿可能因強權的競爭性反應而充滿風險。若新興國家在應對這些反應時欠缺競爭優勢,模仿策略可能最終成為徒勞的嘗試。
關於「竄起者策略」的第二個組成部分「利用」,商業領域中有些市占率低而企圖心強的競爭者,善加利用既有領導企業的盲點,擊敗他們而成為新的市場領導者。這樣的做法正是新興國家效法的對象。這一策略的實行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①存在可利用的盲點──既有霸權因忽視、欠缺能力或認為該領域增長空間有限而未積極參與競爭的領域;②新興國家在這些領域具有一定優勢。此時,新興國家便可採用已被證明有效的方式,但無需直接與既有霸權競爭。若新興國家在相關領域擁有競爭優勢,這是一種相對高效的實力構建方式。
最後一個組成部分──創新,也有其優勢。一種全新的方法可能不會被視為對既有霸權地位的直接挑戰,因此不會立即引發其他國家的制衡行動。儘管創新可能比模仿(已被驗證的方式)更具風險,但若成功,其崛起速度和效率可能遠比模仿更快。更具創意的策略還可能使新興國家在新的戰略領域獲得「先行者優勢」或充分利用其獨特的競爭優勢。成功挑戰領導者的競爭者往往能「以創意破壞根深蒂固的信念」,重新定義最佳建構與行使實力的方式。然而,創新並非毫無風險,這條道路並無明確的藍圖,採用不同尋常的策略也可能導致新興勢力的失敗。
從以上這項討論中,我們可以得出有五個主要因素會決定新興國家會採用「三E策略」中的哪一個:既有霸權策略的有效性、霸權對行為的最可能解讀、特定方法的效率(主要由競爭優勢塑造)、方法的侷限性以及是否存在差距與盲點。以中國的崛起而言,這意味著當中國評估美國的方法有效、模仿行為能使西方國家放心,且中國在相關領域具備競爭優勢以確保戰略效力時,往往會選擇模仿美國。例如,中國的外交推進、調解以及嘗試加入新的國際機構均屬於此類。當上述條件成立但中國因自身能力限制而無法直接參與競爭時,中國會意識到差距,並選擇在這些領域採行「利用盲點」策略。
新興策略的最後一個組成部分對中國的崛起最為關鍵。當中國認為美國的策略無效或是可能對黨造成風險,亦或採用美國的方法可能會引發強烈的負面威脅感時,中國便會尋求創新的實力建構途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會設計出一種新的方式來建立某種類型的實力,這種方式能夠充分利用中國的競爭優勢,並降低其弱點的影響。例如,中國建設商業港口設施,而非海外軍事基地,來保護其海外利益,或者訓練當地執法部門而非外國軍隊以謀求建立良好關係。
探討中國如何競逐強權地位
我們的敘述始於一九九○年代中期,這一時期通常被認為是中國地緣政治崛起的起點。在此期間中國領導人做出關鍵的戰略決策,將目光從單純追求國內經濟成長拓展到國際舞台,著手構建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本書試圖透過深入分析二十二個案例,探討中國領導人如何在這些情境中做出決策,以實現特定的戰略目標。
這三十年(約從一九九三年至二○二三年)也與中國對自身發展軌跡的認知相吻合。鄧小平曾將冷戰後的三十年稱為「追趕」的時期,並強調「抓住機遇」的重要性。知名中國學者鄭必堅在二○○○年初提出中國「和平崛起」的概念,而在二○○三年溫家寶總理於哈佛大學演講後,官方文本和講話中開始公開討論中國的崛起。到新冠疫情爆發前夕,官方和學術界的評估已經普遍接受中國成功的縮小了與美國的實力差距,可以被視為一個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