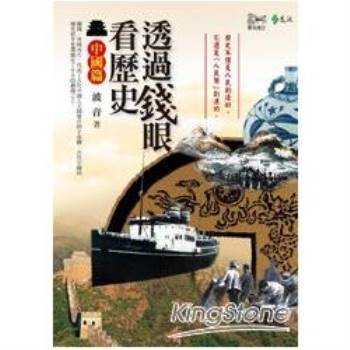第一篇
三千年的糧倉保衛戰
只有讀懂了中華大地上的糧食,我們才有可能真正讀懂中國的古代歷史。
有了糧食,人才有了賴以生存的條件,人得以生存了,才有了經濟的發展,才有了稅收。古代中國最大的經濟秘密是,稅收大多來自農民,億萬個自耕農上交的錢糧支撐起了中央王朝。
用狗尾巴草填飽肚子
要讀懂中國歷史,我們得從瞭解狗尾巴草開始。狗尾巴草和糧食能扯上什麼關係?其實人類馴化的各種農作物,不論是麥類、粟類、稻類,還是其他糧食作物,大都屬於禾本科,而禾本科植物中還包括了大量的野草。說句玩笑話,我們現在不是在吃飯,而是在吃草。
狗尾巴草是古代中國一種重要的農作物──粟的祖本植物,中國人馴化狗尾巴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近萬年前。粟,按照我們現在的通俗說法,就是穀子,我們早晨喝的香甜的小米粥就是用粟做的。反過來說,狗尾巴草是粟的野生種,也叫莠,在剛長出來的時候和粟的幼苗很難區分,所以我們的詞典裡有「良莠不分」的說法。
粟、黍和菽,是先秦時期中國古代最重要的農作物,它們的現代說法分別是穀子、黃米和大豆。從讀音上看,這三種作物名稱很相近,為什麼古人會如此稱呼這些農作物,是件有趣而令人費解的事情。三種作物最重要的相同之處是它們都是耐旱和耐貧瘠植物,而且生長期又比較短,非常適合中國北方旱地種植。而且,先秦時期農業技術很原始,可謂是刀耕火種,所以這三種非常皮實的作物就率先從百草中脫穎而出,被古代中國人篩選出來,作為當時的主要食物。
夏朝和商朝曾被人們稱為「粟文化」的王朝,可見這種家養狗尾巴草的重要地位。不過,當時人口還比較少,人口密度很低,天底下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沼澤,人們可以獲得的食物來源是相當多的。有人統計過取材先秦的詩歌集《詩經》,三○五篇詩歌中,有一四一篇四九二次提到動物,一四四篇五○五次提到植物,許多動植物都是當時人們的食物。就拿〈關雎〉一文來說,就有「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的句子。所謂「溫飽思淫欲」,吃不飽肚子,怎麼能有力氣唱歌彈琴追美女呢?
這種田園詩般的時代注定要遠逝,就像童年很美好,但終究要流逝一樣。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多,人們必須開墾更多的荒地,專門種植那些產量比較大的作物,以滿足大量人口的食物需求。
這其實就是有名的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的觀點,人口數量是以幾何級數上升的,1、2、4、8、16……而從環境中獲得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數量,是以算術級數上升的,1、2、3、4、5……人口總是增長得更快,這位英國經濟學家悲觀地認為,只有戰爭和疾病才能幹掉多餘的人口,解決人口和資源之間增長速度不一致的矛盾。
但是,如果打不贏別人,搶不到更多的地盤;又沒有爆發瘟疫導致非戰鬥減員百分之八十,人們總不能像北歐的旅鼠那樣,在鼠口爆炸的壓力下紛紛跳海自殺吧?尤其是土地變成了私人財產之後,人口和資源的矛盾更加突出了。除非遠遁山林,否則人們必須琢磨,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如何獲得更多的糧食,裝滿自己的糧倉。
在古代的農業社會中,人口數量的上限其實掌握在農作物的手中,農作物產量的高低,決定著人口數量的多寡。而面對一張張嗷嗷待哺的嘴,粟這種產量很低的作物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了。
小麥小麥我愛你
就在這時,小麥閃亮登場了,以其良好的口感和穩定的產量,席捲了中國北方地區,各地農民紛紛成為小麥的狂熱粉絲,擴大小麥的種植面積,減少其他作物的種植面積。
然而,小麥卻不是我國馴化的作物,它的故鄉在遙遠的西亞,那裡也是人類最早的農業起源地。距今約一萬年前,那裡的人們在平地上種小麥和大麥,在山坡上放牧山羊和綿羊。那時候的人們獲得一種新的農作物的喜悅之情,不亞於我們今天獲得一部蘋果新型掌上電腦(iPad)的感覺。此後,小麥的種子迅速地從西亞向四周蔓延。
小麥到達中國的時間不詳,不過我國境內最早的小麥遺物,是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溝墓地裡發現的,在古墓的一個草編的小簍中裝著小麥作為隨葬品,距今已經有三千八百年的歷史。當地遺址中還發現了大型磨麥器。新疆的發現提醒我們,小麥很可能是從西亞經過新疆傳入我國北方的。史書上也曾經記載,周穆王西巡,與西王母約會的時候,沿途部落紛紛向周穆王進獻小麥,可見當時小麥已經是全亞洲人民的大眾情人。
商、周時期,小麥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還不如粟,在宗廟祭祀的時候,以粟為尊貴之物,看來習慣的力量是巨大的。不過,嘴巴最終還是決定了腦袋,即使在古代原始的耕作制度下,單位面積小麥產量估計也是粟產量的兩倍以上,如果水肥得力,產量會更高。
到了戰國時期,小麥已經取代粟,開始在各國的糧倉中成為主角,特別是秦國。
戰國七雄之中,秦國位於西方,從地理上看,靠近西域,所以當地接觸到小麥這種作物的時間必然很早。而且,秦國擁有渭河沖積形成的關中平原,這裡的氣候和水文條件非常適宜種植小麥。所以秦國最後做大,並統一天下,是有著優良的環境基礎的。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無論秦國的軍隊有多彪悍,讓他們餓幾天肚子就沒有戰鬥力了。戰國後期秦軍能夠連年作戰,經濟基礎則是關中平原出產的小麥。
這一點,司馬遷看得很清楚,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談到,秦國所處的關中地區,土地不過天下的三分之一,民眾也大抵如此比例,但就其富庶程度,卻達到了天下總量的百分之六十。所以到了漢朝,國家的管理者非常重視關中平原,還有關中平原上的小麥。西漢的許多農學家兼官員就力挺在關中平原上大力推廣小麥種植。
在經歷了秦末的戰爭和漢初呂后專權的動蕩歲月後,到漢文帝和漢景帝期間,西漢迎來了所謂的「文景之治」。《漢書》記載,當時國家的糧倉逐漸豐盈,新糧壓在舊糧上面,一直堆積到了糧倉的外面;國家的庫府裡積攢了大量的銅錢,由於多年不用,穿錢的繩子爛掉了,散落在地上的銅錢數不勝數。
後人評價文景之治,大多歸功於戰亂平息後政治穩定、皇帝以身作則勤儉持家、減輕農民的賦稅負擔等因素。這些解釋固然都有道理,但我們應該關注更為主要的一個原因,那就是小麥的廣泛種植。中國各王朝的根基是農民,雖然農民也有許多種,有自耕農,有佃農,有農奴,但就古代中國來說,農民中的主力軍是億萬小自耕農。如果這些自耕農的土地上的糧食產量很低,僅能餬口,根本交不出皇糧,即使皇帝再勤儉節約,以德治國,一分錢掰成兩半花,恐怕也沒有多少稅收能夠存留下來。正是因為在文景時期,借助著和平年代的到來,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廣產量超過其他作物的小麥,才使得自耕農們秋收的時候能打下更多的糧食,於是可供上交的皇糧也就更多了。
中國史書中所記載的一些「盛世」,在那些以儒家思想為綱領的史官筆下,無一例外都是仁政的產物,是人品問題。但其實,有些「盛世」根本就是官樣文章,吹出來的,而有些「盛世」則另有原因,並不是用一句「皇上聖明」就能概括的。文景之治就是一例,兩個皇上並沒有推行什麼出色的政策,也就是節日的時候扶一扶鋤頭,擺個POSE而已。小麥才是文景之治真正的幕後推手。
三千年的糧倉保衛戰
只有讀懂了中華大地上的糧食,我們才有可能真正讀懂中國的古代歷史。
有了糧食,人才有了賴以生存的條件,人得以生存了,才有了經濟的發展,才有了稅收。古代中國最大的經濟秘密是,稅收大多來自農民,億萬個自耕農上交的錢糧支撐起了中央王朝。
用狗尾巴草填飽肚子
要讀懂中國歷史,我們得從瞭解狗尾巴草開始。狗尾巴草和糧食能扯上什麼關係?其實人類馴化的各種農作物,不論是麥類、粟類、稻類,還是其他糧食作物,大都屬於禾本科,而禾本科植物中還包括了大量的野草。說句玩笑話,我們現在不是在吃飯,而是在吃草。
狗尾巴草是古代中國一種重要的農作物──粟的祖本植物,中國人馴化狗尾巴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近萬年前。粟,按照我們現在的通俗說法,就是穀子,我們早晨喝的香甜的小米粥就是用粟做的。反過來說,狗尾巴草是粟的野生種,也叫莠,在剛長出來的時候和粟的幼苗很難區分,所以我們的詞典裡有「良莠不分」的說法。
粟、黍和菽,是先秦時期中國古代最重要的農作物,它們的現代說法分別是穀子、黃米和大豆。從讀音上看,這三種作物名稱很相近,為什麼古人會如此稱呼這些農作物,是件有趣而令人費解的事情。三種作物最重要的相同之處是它們都是耐旱和耐貧瘠植物,而且生長期又比較短,非常適合中國北方旱地種植。而且,先秦時期農業技術很原始,可謂是刀耕火種,所以這三種非常皮實的作物就率先從百草中脫穎而出,被古代中國人篩選出來,作為當時的主要食物。
夏朝和商朝曾被人們稱為「粟文化」的王朝,可見這種家養狗尾巴草的重要地位。不過,當時人口還比較少,人口密度很低,天底下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沼澤,人們可以獲得的食物來源是相當多的。有人統計過取材先秦的詩歌集《詩經》,三○五篇詩歌中,有一四一篇四九二次提到動物,一四四篇五○五次提到植物,許多動植物都是當時人們的食物。就拿〈關雎〉一文來說,就有「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的句子。所謂「溫飽思淫欲」,吃不飽肚子,怎麼能有力氣唱歌彈琴追美女呢?
這種田園詩般的時代注定要遠逝,就像童年很美好,但終究要流逝一樣。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多,人們必須開墾更多的荒地,專門種植那些產量比較大的作物,以滿足大量人口的食物需求。
這其實就是有名的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的觀點,人口數量是以幾何級數上升的,1、2、4、8、16……而從環境中獲得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數量,是以算術級數上升的,1、2、3、4、5……人口總是增長得更快,這位英國經濟學家悲觀地認為,只有戰爭和疾病才能幹掉多餘的人口,解決人口和資源之間增長速度不一致的矛盾。
但是,如果打不贏別人,搶不到更多的地盤;又沒有爆發瘟疫導致非戰鬥減員百分之八十,人們總不能像北歐的旅鼠那樣,在鼠口爆炸的壓力下紛紛跳海自殺吧?尤其是土地變成了私人財產之後,人口和資源的矛盾更加突出了。除非遠遁山林,否則人們必須琢磨,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如何獲得更多的糧食,裝滿自己的糧倉。
在古代的農業社會中,人口數量的上限其實掌握在農作物的手中,農作物產量的高低,決定著人口數量的多寡。而面對一張張嗷嗷待哺的嘴,粟這種產量很低的作物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了。
小麥小麥我愛你
就在這時,小麥閃亮登場了,以其良好的口感和穩定的產量,席捲了中國北方地區,各地農民紛紛成為小麥的狂熱粉絲,擴大小麥的種植面積,減少其他作物的種植面積。
然而,小麥卻不是我國馴化的作物,它的故鄉在遙遠的西亞,那裡也是人類最早的農業起源地。距今約一萬年前,那裡的人們在平地上種小麥和大麥,在山坡上放牧山羊和綿羊。那時候的人們獲得一種新的農作物的喜悅之情,不亞於我們今天獲得一部蘋果新型掌上電腦(iPad)的感覺。此後,小麥的種子迅速地從西亞向四周蔓延。
小麥到達中國的時間不詳,不過我國境內最早的小麥遺物,是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溝墓地裡發現的,在古墓的一個草編的小簍中裝著小麥作為隨葬品,距今已經有三千八百年的歷史。當地遺址中還發現了大型磨麥器。新疆的發現提醒我們,小麥很可能是從西亞經過新疆傳入我國北方的。史書上也曾經記載,周穆王西巡,與西王母約會的時候,沿途部落紛紛向周穆王進獻小麥,可見當時小麥已經是全亞洲人民的大眾情人。
商、周時期,小麥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還不如粟,在宗廟祭祀的時候,以粟為尊貴之物,看來習慣的力量是巨大的。不過,嘴巴最終還是決定了腦袋,即使在古代原始的耕作制度下,單位面積小麥產量估計也是粟產量的兩倍以上,如果水肥得力,產量會更高。
到了戰國時期,小麥已經取代粟,開始在各國的糧倉中成為主角,特別是秦國。
戰國七雄之中,秦國位於西方,從地理上看,靠近西域,所以當地接觸到小麥這種作物的時間必然很早。而且,秦國擁有渭河沖積形成的關中平原,這裡的氣候和水文條件非常適宜種植小麥。所以秦國最後做大,並統一天下,是有著優良的環境基礎的。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無論秦國的軍隊有多彪悍,讓他們餓幾天肚子就沒有戰鬥力了。戰國後期秦軍能夠連年作戰,經濟基礎則是關中平原出產的小麥。
這一點,司馬遷看得很清楚,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談到,秦國所處的關中地區,土地不過天下的三分之一,民眾也大抵如此比例,但就其富庶程度,卻達到了天下總量的百分之六十。所以到了漢朝,國家的管理者非常重視關中平原,還有關中平原上的小麥。西漢的許多農學家兼官員就力挺在關中平原上大力推廣小麥種植。
在經歷了秦末的戰爭和漢初呂后專權的動蕩歲月後,到漢文帝和漢景帝期間,西漢迎來了所謂的「文景之治」。《漢書》記載,當時國家的糧倉逐漸豐盈,新糧壓在舊糧上面,一直堆積到了糧倉的外面;國家的庫府裡積攢了大量的銅錢,由於多年不用,穿錢的繩子爛掉了,散落在地上的銅錢數不勝數。
後人評價文景之治,大多歸功於戰亂平息後政治穩定、皇帝以身作則勤儉持家、減輕農民的賦稅負擔等因素。這些解釋固然都有道理,但我們應該關注更為主要的一個原因,那就是小麥的廣泛種植。中國各王朝的根基是農民,雖然農民也有許多種,有自耕農,有佃農,有農奴,但就古代中國來說,農民中的主力軍是億萬小自耕農。如果這些自耕農的土地上的糧食產量很低,僅能餬口,根本交不出皇糧,即使皇帝再勤儉節約,以德治國,一分錢掰成兩半花,恐怕也沒有多少稅收能夠存留下來。正是因為在文景時期,借助著和平年代的到來,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廣產量超過其他作物的小麥,才使得自耕農們秋收的時候能打下更多的糧食,於是可供上交的皇糧也就更多了。
中國史書中所記載的一些「盛世」,在那些以儒家思想為綱領的史官筆下,無一例外都是仁政的產物,是人品問題。但其實,有些「盛世」根本就是官樣文章,吹出來的,而有些「盛世」則另有原因,並不是用一句「皇上聖明」就能概括的。文景之治就是一例,兩個皇上並沒有推行什麼出色的政策,也就是節日的時候扶一扶鋤頭,擺個POSE而已。小麥才是文景之治真正的幕後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