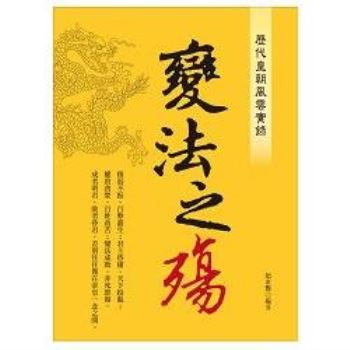洋務運動
張居正拯危救難的改革並沒有挽救危難之中的大明王朝,在農民起義的熊熊烈焰中明王朝銷聲匿跡了。然而,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不能承擔起統治全中國的重負,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的清王朝成了中原大地的主宰。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在延續了二百多年的封建社會之後,終於在十九世紀中葉走向了它最後的腐朽與沒落。
西元一八四○年,對於大清王朝乃至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都是一個極不尋常之年。英國的隆隆炮聲震撼了中國的海域,震撼了中國的南疆,也震撼了中國的心臟,中國的大門被打開了!這炮聲使守疆的戰士驚訝,使抗戰的愛國將帥驚訝,更使清廷的貴族老爺們驚訝,大清帝國不是世界強國、文明古國嗎?小小的蠻夷之國怎敢如此無理、如此膽大妄為?但事實就是事實。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以屈辱換來了「和平」。從此,香港割讓給英國,沿海港口開放,牟取暴利的鴉片也運了進來。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西元一八五六年,由英法聯合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打響了,結果中國損失慘重,迫不得已,與侵略者簽訂了《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以及中英、中法的《北京條約》。接著,又是割地、賠款、開放眾多城市、外國人開始大量湧入。隨後,號稱公正的美國人,也以十分「和平」的方式介入,取得了和英法同樣的在華利益。
面對屈辱的現實,人民開始逐漸覺醒,三元里人民在街頭巷尾,與敵人短兵相接,給予英國侵略者有力的打擊。香港、九龍的工人罷工、罷業、停水、停電,使整個城市處於癱瘓,外國人最後只好求救於高傲又卑賤的清朝政府,而腐朽無能的清政府只知道在屈辱退讓中苟延殘喘。
在地主階級的上層,有一些人開始意識到國家不能再這樣屈服下去了,再這樣下去,大清帝國就要滅亡了。而且當時來自於下層社會的太平天國運動已經風起雲湧,勢如浪潮,這更加重了他們的危機感。清朝政府要自救,然而自救的出路在哪裡?人們尋找著、探索著,終於發現自救的唯一方式就是學習能使外國人船堅炮利的先進西學。西元一八六一年之後,一場大規模、持續三十餘年之久的中學為本、西學為末的洋務運動開始了。
所謂洋務運動,就是由清政府內部一些進步人士為首而掀起的辦洋務熱潮,它是以西元一八六一年在北京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而開始的。
中國人辦洋務,這可不是一件簡單易行的事情!在閉關鎖國的封建時代,不僅僅是封建政府機構的官僚,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乃至士大夫知識分子們,他們也只知道四書五經,知道三綱五常封建禮義,知道宗教佛學。為民者以學好詩經、考取功名為榮,為官者以如何維護統治、效忠皇帝為尚。他們對外邊的世界知之甚少,只知道不同於自己的民族都是蠻夷,北方有蒙古、韃靼,沿海有倭寇,海外一定還有許多蠻夷。鴉片戰爭爆發前,沿海向朝廷告急。道光皇帝向大臣們問道:「英國是哪方夷人?地方幾許?與俄羅斯是否接壤?」如此驕傲與無知的清政府,將大清帝國與世界割裂,以為大清就是這個世界的主宰。二十年之後,清政府內部竟出現了洋務派,他們把辦洋務作為求強求富的必要手段,而且場面之大,規模之宏令人驚嘆不已。為什麼會有這樣質上的突飛猛進,為什麼封閉了幾千年的文明古國會迎接世界、走向世界呢?這一變化的關鍵來源於兩次戰爭對中國的撞擊,來源於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以及繼他之後魏源的思想啟蒙。
林則徐,以他虎門銷菸的威名流傳青史,盡人皆知。同時,他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瞭解西方,認識西方的先驅,范文瀾先生稱之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當英國人看準了中國這一市場,將鴉片源源不斷地帶到中國之後,身為湖廣總督的林則徐以欽差大臣之名義到廣州禁菸。那時,他就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願望,要瞭解英國,瞭解西方,知己知彼。林則徐大量蒐集外國書籍,找人翻譯,把西元一八三六年倫敦出版、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譯為《四洲志》,把《澳門新聞稿》譯為《澳門月報》,又把德庇時、地爾窪等人所著的《中國人》、《在中國做貿易罪過論》合譯為《華事夷言》。這些近代中國系統介紹西方各國地理歷史知識的書籍,使中國人瞭解了陌生的世界。鴉片戰爭時,面對英國人的堅船利炮,林則徐不是害怕屈服,而是勇敢地站起來進行抗爭,並主張把他們的船炮拿過來為自己所用,這就是林則徐的高明之處,是他不同於時人的遠見卓識,可謂慧眼獨具。當鴉片戰爭失敗後,林則徐總結失敗的教訓時說:「我覺得若想抗擊夷人,如不擁有夷人所有的新式船炮,建立水軍,那麼只能是自取失敗。只有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才能克敵制勝。」可以說,鴉片戰爭之後,林則徐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便形成了。
西元一八四一年林則徐因禁菸、抗戰而被革職充軍到新疆。林則徐去往新疆的途中路過京口,和正在京口的志同道合好友魏源相見後,便把《四洲志》的稿子交給魏源,囑咐他:「你要以此為藍本撰寫一本《海國圖志》,以便更有系統、更具體地介紹西方社會。」魏源沒有辜負林則徐的期望,於一八四四年完成了《海國圖志》的編纂。初始五十卷,後來又進行擴充,一八四七年補充到六十卷,一八四九年又擴編為一百卷。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不但詳細敘述了世界各國的沿革、地理,而且對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社會現象、對外開拓殖民地的社會本質,以及其技術水平、政治制度、風土人情等等都做了介紹,並加以評述。他是這樣描述英國的:英國並不看重宗教,只重視商業和武力,以此到世界各地去開拓殖民地。他指出,鴉片戰爭不是林則徐禁菸的結果,實際上是英國侵略者唯利是圖、唯威是畏的必然行為,以及清朝落後所造成的。他為林則徐申冤的同時,又指出必須學習西方長處。他大聲疾呼:「師夷長技以制夷。」
林則徐、魏源的啟蒙思想,促使中國士人更多地瞭解了西方,使中國知識界眼界大開,耳目一新,從而也引導了更多人來學習西方、學習西學。但是,林則徐、魏源對西方長技的認識還是相當淺層次的表面,所謂長技不外乎指船堅炮利而已,還沒有上升到西學這一高度。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他們,因為在萬民皆睡我獨醒的狀態下,能大聲發出吶喊,這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他們做出了自己應做的貢獻,更深層的認識只能靠後人來完成。事實也確實如此,洋務運動之所以能迅猛發展起來,後來的馮桂芬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著名的《校邠廬抗議》是馮桂芬的一部力著,其中《採西學議》和《製洋器議》集中反映了他學習西學的思想。馮桂芬把學習西方長技提高到了學習西學的高度,這是理論上的飛躍。他在《採西學議》中寫道:「在我國古代的一部天文歷算著作《周髀算經》中,有四極四合與半年為晝、半年為夜的說法,後人都不解其意。戰國時的陰陽家騶衍,說中國名為赤縣神州,而中國之外也如赤縣神州的還有九個,這在當時也被看做是荒唐之言。然而,他們說的並沒有錯,地球確實大無邊際,並不是舟車、人力所能到達的。據西人地圖所列,天下有百國。而這百國的書籍,在明末譯過來的僅意大利和英吉利兩國的書就有數十種之多,其中的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都十分具有科學性,是中國人遠不及的。這些對於我中華大一統之邦來說,難道不是中國學子的羞恥嗎?」
「今欲採西學,宜於廣東、上海設置翻譯公所,選附近十五歲以下聰穎易悟的童子,聘西人教他們各國語言文字,再聘內地名師教他們經史之學。一切西學都從算學開始,西人十歲以上無人不學算學,今欲採西學,自然不可不學算學,或者以西人為師,或者請內地知算學的人為師都可。我聽說香港英華書院、上海墨海書院藏書都很多,另外一八四七年俄國人送政府方略館的書籍也達千餘種,都可以有選擇地翻譯過來。這樣歷算之術、格致之理、製器尚象之法,無所不包,互為貫通,對中國將大有裨益。聽說西人發明了新的測量地動之術,與天行密切配合,可以報時。又聞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可以把它引來用以治水。又如農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機輪,用力少而收效大,可以學來以利民生。其他凡是有利於國計民生,我們不管他是什麼奇技淫巧,只管學來便是。這樣,三年之後,那些文童已能對外國書籍應口成誦,以此來補充本學;諸生中如有成績突出,具有真才實學的,可由通商大臣請示朝廷封他們為舉人。如前所議,中國多秀民,必有出之於夷而勝於夷之人,這實在是當今治學的第一要務。」
「愚以為在今日宜曰:『鑑諸國。』諸國同時並行於世,都能獨自達到富強,更何況我們對各方面做以比較,選擇其中最好的來學習呢!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是善之善者哉?」「夫御夷為當今天下第一要政,此議如能行,則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人必然多起來,則必然有正人君子、通達治體之人脫穎而出,然後得其要領而抵禦之。」
綜觀馮桂芬的思想,他已將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發展為「師夷善法而制夷」,提出了更廣泛學習西方的口號。他認為中國不僅僅在軍事技術上落後西方,而且在人才、地利、君民關係、名實必符等諸多方面都不如夷,所以要廣泛地學習,但必須是在以中學為本的前提下進行。他的這一中學為本、西學為末的思想對中國洋務運動時期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學習和掌握西方技術,是馮桂芬倡導自強之道的重要課題,這也成了洋務運動的初衷。他的《製洋器議》簡直就是一步一步地告訴洋務派如何去學西學,如何去製造洋器。馮桂芬將西學思想灌輸到人們的頭腦之中,只等著洋務派將他的思想付諸實施了。
西元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安徽合肥雖沒有北方的皚皚冰雪,但也是寒氣逼人,冷風瑟瑟。此時,在剛剛組建的淮軍總部,李鴻章正雙目緊閉,雙眉緊鎖,坐在那裡愁眉不展。左右見狀,不知為何,小心翼翼地問道:「大人已承曾總督相助,組建了淮軍,繳匪已勝利在望,大人還為何事憂慮?」李鴻章什麼話也沒說,他揮了揮手,示意左右退下。於是他們都再不敢言語,心懷疑慮地走了。
此時的李鴻章已奉兩江總督曾國藩之命建立了淮勇,面對士氣高漲的太平天國,他正待命準備開赴戰場,而且充滿了必勝的信心。那麼他究竟在想什麼呢?原來,這位二十四歲就中進士、曾是曾國藩幕僚的李鴻章,正為國事而憂慮、困惑。兩次鴉片戰爭失敗之後,農民起義又風起雲湧,大清王朝江河日下,危機四伏。太平天國勢在推翻清朝政府,英、法、美等國企圖主宰中華,這就是十九世紀六○年代的國情!十一月,慈禧太后發動宮廷政變,掌握了大清實權,並以恭親王奕訢為首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應付日益繁多的對外事宜。然而,這又能給人們帶來什麼希望呢?總理衙門只是為外國人在中國取得更大的利益大開方便之門罷了。李鴻章閉目思索著,心裡更增加了幾絲愁緒,眉間的皺紋更深了。
忽然,外面一片嘈雜聲使他從混亂的思緒中清醒過來,他睜開雙眼,看看究竟出了什麼事。原來是他的一個幕僚剛剛從蘇州回來,只見他興沖沖地來到李鴻章近前,「太令人振奮了,請大人看看這本書。」來人急不可耐地說。李鴻章接過來一看,是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翻開扉頁,再翻下去,繼續看下去,李鴻章越看越興奮,他不知不覺中熱血沸騰了,不禁大聲說道:「原來我所苦苦尋找的答案就在這裡啊!」是啊,這就是李鴻章所要找的答案,拯救危難中的中國,拯救搖搖欲墜的清政府,只有學習西學才是唯一的出路。李鴻章興奮著、欣喜著,他已不再困惑,不再猶豫,出路就在眼前,只要自己沿著別人給指的路向前走就行了。
與此同時,馮桂芬的書籍走出了他的家鄉蘇州,在合肥、上海、北京、湖南等地傳開了,恭親王奕訢看到了,兩江總督曾國藩看到了,無數的士人看到了。
此時的曾國藩,對農民起義自然是恨之入骨,但更使他痛心的是兩次鴉片戰爭失敗後的民族的劫難。他看到外國人肆意橫行於中國的沿海與沿江,他的心被一種不可言狀的憤怒與傷感所籠罩。他把這種愁苦心情寫在紙上,向他的日記傾訴,「大局已壞,令人心灰」,他無法沉默,無法忍讓,「扼腕久之,泫然有嗚咽之哀」。該如何擺脫這種苦痛呢?終於,他看到了一種新穎的思想。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七日,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余偶從朋友處得到馮氏之《校邠廬抗議》一書,如獲至寶,仔細研讀,實覺馮氏之論乃名儒之論矣。」讀罷馮氏之作,曾國藩茅塞頓開,有如撥開雲霧,看到了久違的希望和陽光。馮氏的西學之路,就是中國的自救之路,他終於明白了這個還不是眾多人都能明白的道理。曾國藩這位封建禮教的衛道士,在民族危難面前,選擇走在時代的最前端。
林則徐、魏源、馮桂芬,他們使矇昧了幾千年的中國人眼界大開,他們喚醒了沉睡中的人們,尤其是地主階級之上一些有識之士。這些有識之士開始學習西學、接受西學,並採納西學,洋務運動由此而產生了。《北京條約》簽訂之後,英、法、美等國侵略者大量湧入中國,並在北京派駐公使,中國外交事務逐漸繁重起來。過去承擔對外事務的理藩院已明顯不能應付目前這種局面,於是清政府便在北京成立了總理衙門,以總理外交事務。慈禧太后給予奕訢領導的總理衙門很大的權力,按軍機處的規模組建,除主管外交事務之外,還兼管各路軍務及海關等。但是,總理衙門一成立,便成了洋務派實行洋務運動的領導機構,這實在是清朝政府所始料不及的。
與洋人打交道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語言障礙,於是,總理衙門便把這一問題看成了頭等大事。西元一八六二年,以學習英語為首要任務的同文館成立,第二年又開設了法文館和俄文館,所屬同文館。
隨著總理衙門、同文館的設立,新的思想、新的觀念也在中華大地上勃然而生。大權在握的恭親王奕訢接受了新思想的陶冶,總理衙門事實上成了洋務運動的大本營。
此時,地方上的李鴻章等人也開始行動起來。西元一八六三年初春,被調到上海、已被提拔為江蘇巡撫的李鴻章終於將他久慕的馮桂芬請到自己帳下。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相差十幾歲的兩個人走在一起,並使他們成了師生、戰友和知己。李鴻章視馮桂芬為恩師,馮桂芬也更加深入而具體地把他的西學思想灌輸給李鴻章。由馮桂芬建議和擬稿,李鴻章依照同文館之例,奏准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廣方言館比北京同文館更加進步,其學生不但學習外國語言,而且還學習西方自然科學和製造技術,它同第二年兩廣總督瑞麟在廣州設立的同文館一樣,為培養洋務人才做出了突出貢獻。與此同時,各同文館大量地翻譯書籍,對打開中國風氣無疑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西元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已持續了十二年之久,清政府出於種種考慮,求救於外國人軍隊介入中國內戰之中。裝備精良的外國軍隊前所未見,使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大開眼界。外國有軍艦、輪船,中國卻只有帆篷舟楫;外國有來福槍,中國卻只有弓矢、工槍,相差實在太懸殊了。李鴻章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寫道:「鴻章經常到英法提督的兵船上去,看見其大砲之精純,彈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在不是中國所能比的。」正是因為這種懸殊差距,他們才想把外國人所有的拿過來據為己有。曾國藩曾說過:「目前借助於夷國軍隊,得以解一時之憂;而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才可期永遠之利。」李鴻章也曾強調說:「國家百用可省,只有練兵設備萬不可省。」他們二人都認為:如果中國軍器也能像西方的那樣精銳,那麼不但平定國內之亂有餘,而且抵禦外侮亦無不足。
西元一八六二年,曾國藩在安慶建立了軍械所。雖然規模較小,但是它卻是在中國試造新式武器的開始,它也是中國近代工業的始祖。之後不久,他又與李鴻章共同在上海創辦了洋務運動期間最大的軍事工業—江南機器製造局。曾到國外採辦機器的容閎後來追述:「自余由美國採購機器歸國以來,中國國家已籌備了千百萬現金,準備建廠,並希望能成為好望角以東之第一良好機器廠。故此廠實乃為一永久之碑,可以紀念曾文正之高識遠見。世無文正,則中國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機器廠否耶?」曾國藩、李鴻章引進機器生產軍備,以求自強,這在當時是最為先進之舉。
張居正拯危救難的改革並沒有挽救危難之中的大明王朝,在農民起義的熊熊烈焰中明王朝銷聲匿跡了。然而,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不能承擔起統治全中國的重負,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的清王朝成了中原大地的主宰。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在延續了二百多年的封建社會之後,終於在十九世紀中葉走向了它最後的腐朽與沒落。
西元一八四○年,對於大清王朝乃至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都是一個極不尋常之年。英國的隆隆炮聲震撼了中國的海域,震撼了中國的南疆,也震撼了中國的心臟,中國的大門被打開了!這炮聲使守疆的戰士驚訝,使抗戰的愛國將帥驚訝,更使清廷的貴族老爺們驚訝,大清帝國不是世界強國、文明古國嗎?小小的蠻夷之國怎敢如此無理、如此膽大妄為?但事實就是事實。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以屈辱換來了「和平」。從此,香港割讓給英國,沿海港口開放,牟取暴利的鴉片也運了進來。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西元一八五六年,由英法聯合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打響了,結果中國損失慘重,迫不得已,與侵略者簽訂了《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以及中英、中法的《北京條約》。接著,又是割地、賠款、開放眾多城市、外國人開始大量湧入。隨後,號稱公正的美國人,也以十分「和平」的方式介入,取得了和英法同樣的在華利益。
面對屈辱的現實,人民開始逐漸覺醒,三元里人民在街頭巷尾,與敵人短兵相接,給予英國侵略者有力的打擊。香港、九龍的工人罷工、罷業、停水、停電,使整個城市處於癱瘓,外國人最後只好求救於高傲又卑賤的清朝政府,而腐朽無能的清政府只知道在屈辱退讓中苟延殘喘。
在地主階級的上層,有一些人開始意識到國家不能再這樣屈服下去了,再這樣下去,大清帝國就要滅亡了。而且當時來自於下層社會的太平天國運動已經風起雲湧,勢如浪潮,這更加重了他們的危機感。清朝政府要自救,然而自救的出路在哪裡?人們尋找著、探索著,終於發現自救的唯一方式就是學習能使外國人船堅炮利的先進西學。西元一八六一年之後,一場大規模、持續三十餘年之久的中學為本、西學為末的洋務運動開始了。
所謂洋務運動,就是由清政府內部一些進步人士為首而掀起的辦洋務熱潮,它是以西元一八六一年在北京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而開始的。
中國人辦洋務,這可不是一件簡單易行的事情!在閉關鎖國的封建時代,不僅僅是封建政府機構的官僚,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乃至士大夫知識分子們,他們也只知道四書五經,知道三綱五常封建禮義,知道宗教佛學。為民者以學好詩經、考取功名為榮,為官者以如何維護統治、效忠皇帝為尚。他們對外邊的世界知之甚少,只知道不同於自己的民族都是蠻夷,北方有蒙古、韃靼,沿海有倭寇,海外一定還有許多蠻夷。鴉片戰爭爆發前,沿海向朝廷告急。道光皇帝向大臣們問道:「英國是哪方夷人?地方幾許?與俄羅斯是否接壤?」如此驕傲與無知的清政府,將大清帝國與世界割裂,以為大清就是這個世界的主宰。二十年之後,清政府內部竟出現了洋務派,他們把辦洋務作為求強求富的必要手段,而且場面之大,規模之宏令人驚嘆不已。為什麼會有這樣質上的突飛猛進,為什麼封閉了幾千年的文明古國會迎接世界、走向世界呢?這一變化的關鍵來源於兩次戰爭對中國的撞擊,來源於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以及繼他之後魏源的思想啟蒙。
林則徐,以他虎門銷菸的威名流傳青史,盡人皆知。同時,他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瞭解西方,認識西方的先驅,范文瀾先生稱之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當英國人看準了中國這一市場,將鴉片源源不斷地帶到中國之後,身為湖廣總督的林則徐以欽差大臣之名義到廣州禁菸。那時,他就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願望,要瞭解英國,瞭解西方,知己知彼。林則徐大量蒐集外國書籍,找人翻譯,把西元一八三六年倫敦出版、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譯為《四洲志》,把《澳門新聞稿》譯為《澳門月報》,又把德庇時、地爾窪等人所著的《中國人》、《在中國做貿易罪過論》合譯為《華事夷言》。這些近代中國系統介紹西方各國地理歷史知識的書籍,使中國人瞭解了陌生的世界。鴉片戰爭時,面對英國人的堅船利炮,林則徐不是害怕屈服,而是勇敢地站起來進行抗爭,並主張把他們的船炮拿過來為自己所用,這就是林則徐的高明之處,是他不同於時人的遠見卓識,可謂慧眼獨具。當鴉片戰爭失敗後,林則徐總結失敗的教訓時說:「我覺得若想抗擊夷人,如不擁有夷人所有的新式船炮,建立水軍,那麼只能是自取失敗。只有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才能克敵制勝。」可以說,鴉片戰爭之後,林則徐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便形成了。
西元一八四一年林則徐因禁菸、抗戰而被革職充軍到新疆。林則徐去往新疆的途中路過京口,和正在京口的志同道合好友魏源相見後,便把《四洲志》的稿子交給魏源,囑咐他:「你要以此為藍本撰寫一本《海國圖志》,以便更有系統、更具體地介紹西方社會。」魏源沒有辜負林則徐的期望,於一八四四年完成了《海國圖志》的編纂。初始五十卷,後來又進行擴充,一八四七年補充到六十卷,一八四九年又擴編為一百卷。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不但詳細敘述了世界各國的沿革、地理,而且對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社會現象、對外開拓殖民地的社會本質,以及其技術水平、政治制度、風土人情等等都做了介紹,並加以評述。他是這樣描述英國的:英國並不看重宗教,只重視商業和武力,以此到世界各地去開拓殖民地。他指出,鴉片戰爭不是林則徐禁菸的結果,實際上是英國侵略者唯利是圖、唯威是畏的必然行為,以及清朝落後所造成的。他為林則徐申冤的同時,又指出必須學習西方長處。他大聲疾呼:「師夷長技以制夷。」
林則徐、魏源的啟蒙思想,促使中國士人更多地瞭解了西方,使中國知識界眼界大開,耳目一新,從而也引導了更多人來學習西方、學習西學。但是,林則徐、魏源對西方長技的認識還是相當淺層次的表面,所謂長技不外乎指船堅炮利而已,還沒有上升到西學這一高度。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他們,因為在萬民皆睡我獨醒的狀態下,能大聲發出吶喊,這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他們做出了自己應做的貢獻,更深層的認識只能靠後人來完成。事實也確實如此,洋務運動之所以能迅猛發展起來,後來的馮桂芬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著名的《校邠廬抗議》是馮桂芬的一部力著,其中《採西學議》和《製洋器議》集中反映了他學習西學的思想。馮桂芬把學習西方長技提高到了學習西學的高度,這是理論上的飛躍。他在《採西學議》中寫道:「在我國古代的一部天文歷算著作《周髀算經》中,有四極四合與半年為晝、半年為夜的說法,後人都不解其意。戰國時的陰陽家騶衍,說中國名為赤縣神州,而中國之外也如赤縣神州的還有九個,這在當時也被看做是荒唐之言。然而,他們說的並沒有錯,地球確實大無邊際,並不是舟車、人力所能到達的。據西人地圖所列,天下有百國。而這百國的書籍,在明末譯過來的僅意大利和英吉利兩國的書就有數十種之多,其中的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都十分具有科學性,是中國人遠不及的。這些對於我中華大一統之邦來說,難道不是中國學子的羞恥嗎?」
「今欲採西學,宜於廣東、上海設置翻譯公所,選附近十五歲以下聰穎易悟的童子,聘西人教他們各國語言文字,再聘內地名師教他們經史之學。一切西學都從算學開始,西人十歲以上無人不學算學,今欲採西學,自然不可不學算學,或者以西人為師,或者請內地知算學的人為師都可。我聽說香港英華書院、上海墨海書院藏書都很多,另外一八四七年俄國人送政府方略館的書籍也達千餘種,都可以有選擇地翻譯過來。這樣歷算之術、格致之理、製器尚象之法,無所不包,互為貫通,對中國將大有裨益。聽說西人發明了新的測量地動之術,與天行密切配合,可以報時。又聞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可以把它引來用以治水。又如農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機輪,用力少而收效大,可以學來以利民生。其他凡是有利於國計民生,我們不管他是什麼奇技淫巧,只管學來便是。這樣,三年之後,那些文童已能對外國書籍應口成誦,以此來補充本學;諸生中如有成績突出,具有真才實學的,可由通商大臣請示朝廷封他們為舉人。如前所議,中國多秀民,必有出之於夷而勝於夷之人,這實在是當今治學的第一要務。」
「愚以為在今日宜曰:『鑑諸國。』諸國同時並行於世,都能獨自達到富強,更何況我們對各方面做以比較,選擇其中最好的來學習呢!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是善之善者哉?」「夫御夷為當今天下第一要政,此議如能行,則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人必然多起來,則必然有正人君子、通達治體之人脫穎而出,然後得其要領而抵禦之。」
綜觀馮桂芬的思想,他已將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發展為「師夷善法而制夷」,提出了更廣泛學習西方的口號。他認為中國不僅僅在軍事技術上落後西方,而且在人才、地利、君民關係、名實必符等諸多方面都不如夷,所以要廣泛地學習,但必須是在以中學為本的前提下進行。他的這一中學為本、西學為末的思想對中國洋務運動時期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學習和掌握西方技術,是馮桂芬倡導自強之道的重要課題,這也成了洋務運動的初衷。他的《製洋器議》簡直就是一步一步地告訴洋務派如何去學西學,如何去製造洋器。馮桂芬將西學思想灌輸到人們的頭腦之中,只等著洋務派將他的思想付諸實施了。
西元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安徽合肥雖沒有北方的皚皚冰雪,但也是寒氣逼人,冷風瑟瑟。此時,在剛剛組建的淮軍總部,李鴻章正雙目緊閉,雙眉緊鎖,坐在那裡愁眉不展。左右見狀,不知為何,小心翼翼地問道:「大人已承曾總督相助,組建了淮軍,繳匪已勝利在望,大人還為何事憂慮?」李鴻章什麼話也沒說,他揮了揮手,示意左右退下。於是他們都再不敢言語,心懷疑慮地走了。
此時的李鴻章已奉兩江總督曾國藩之命建立了淮勇,面對士氣高漲的太平天國,他正待命準備開赴戰場,而且充滿了必勝的信心。那麼他究竟在想什麼呢?原來,這位二十四歲就中進士、曾是曾國藩幕僚的李鴻章,正為國事而憂慮、困惑。兩次鴉片戰爭失敗之後,農民起義又風起雲湧,大清王朝江河日下,危機四伏。太平天國勢在推翻清朝政府,英、法、美等國企圖主宰中華,這就是十九世紀六○年代的國情!十一月,慈禧太后發動宮廷政變,掌握了大清實權,並以恭親王奕訢為首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應付日益繁多的對外事宜。然而,這又能給人們帶來什麼希望呢?總理衙門只是為外國人在中國取得更大的利益大開方便之門罷了。李鴻章閉目思索著,心裡更增加了幾絲愁緒,眉間的皺紋更深了。
忽然,外面一片嘈雜聲使他從混亂的思緒中清醒過來,他睜開雙眼,看看究竟出了什麼事。原來是他的一個幕僚剛剛從蘇州回來,只見他興沖沖地來到李鴻章近前,「太令人振奮了,請大人看看這本書。」來人急不可耐地說。李鴻章接過來一看,是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翻開扉頁,再翻下去,繼續看下去,李鴻章越看越興奮,他不知不覺中熱血沸騰了,不禁大聲說道:「原來我所苦苦尋找的答案就在這裡啊!」是啊,這就是李鴻章所要找的答案,拯救危難中的中國,拯救搖搖欲墜的清政府,只有學習西學才是唯一的出路。李鴻章興奮著、欣喜著,他已不再困惑,不再猶豫,出路就在眼前,只要自己沿著別人給指的路向前走就行了。
與此同時,馮桂芬的書籍走出了他的家鄉蘇州,在合肥、上海、北京、湖南等地傳開了,恭親王奕訢看到了,兩江總督曾國藩看到了,無數的士人看到了。
此時的曾國藩,對農民起義自然是恨之入骨,但更使他痛心的是兩次鴉片戰爭失敗後的民族的劫難。他看到外國人肆意橫行於中國的沿海與沿江,他的心被一種不可言狀的憤怒與傷感所籠罩。他把這種愁苦心情寫在紙上,向他的日記傾訴,「大局已壞,令人心灰」,他無法沉默,無法忍讓,「扼腕久之,泫然有嗚咽之哀」。該如何擺脫這種苦痛呢?終於,他看到了一種新穎的思想。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七日,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余偶從朋友處得到馮氏之《校邠廬抗議》一書,如獲至寶,仔細研讀,實覺馮氏之論乃名儒之論矣。」讀罷馮氏之作,曾國藩茅塞頓開,有如撥開雲霧,看到了久違的希望和陽光。馮氏的西學之路,就是中國的自救之路,他終於明白了這個還不是眾多人都能明白的道理。曾國藩這位封建禮教的衛道士,在民族危難面前,選擇走在時代的最前端。
林則徐、魏源、馮桂芬,他們使矇昧了幾千年的中國人眼界大開,他們喚醒了沉睡中的人們,尤其是地主階級之上一些有識之士。這些有識之士開始學習西學、接受西學,並採納西學,洋務運動由此而產生了。《北京條約》簽訂之後,英、法、美等國侵略者大量湧入中國,並在北京派駐公使,中國外交事務逐漸繁重起來。過去承擔對外事務的理藩院已明顯不能應付目前這種局面,於是清政府便在北京成立了總理衙門,以總理外交事務。慈禧太后給予奕訢領導的總理衙門很大的權力,按軍機處的規模組建,除主管外交事務之外,還兼管各路軍務及海關等。但是,總理衙門一成立,便成了洋務派實行洋務運動的領導機構,這實在是清朝政府所始料不及的。
與洋人打交道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語言障礙,於是,總理衙門便把這一問題看成了頭等大事。西元一八六二年,以學習英語為首要任務的同文館成立,第二年又開設了法文館和俄文館,所屬同文館。
隨著總理衙門、同文館的設立,新的思想、新的觀念也在中華大地上勃然而生。大權在握的恭親王奕訢接受了新思想的陶冶,總理衙門事實上成了洋務運動的大本營。
此時,地方上的李鴻章等人也開始行動起來。西元一八六三年初春,被調到上海、已被提拔為江蘇巡撫的李鴻章終於將他久慕的馮桂芬請到自己帳下。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相差十幾歲的兩個人走在一起,並使他們成了師生、戰友和知己。李鴻章視馮桂芬為恩師,馮桂芬也更加深入而具體地把他的西學思想灌輸給李鴻章。由馮桂芬建議和擬稿,李鴻章依照同文館之例,奏准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廣方言館比北京同文館更加進步,其學生不但學習外國語言,而且還學習西方自然科學和製造技術,它同第二年兩廣總督瑞麟在廣州設立的同文館一樣,為培養洋務人才做出了突出貢獻。與此同時,各同文館大量地翻譯書籍,對打開中國風氣無疑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西元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已持續了十二年之久,清政府出於種種考慮,求救於外國人軍隊介入中國內戰之中。裝備精良的外國軍隊前所未見,使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大開眼界。外國有軍艦、輪船,中國卻只有帆篷舟楫;外國有來福槍,中國卻只有弓矢、工槍,相差實在太懸殊了。李鴻章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寫道:「鴻章經常到英法提督的兵船上去,看見其大砲之精純,彈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在不是中國所能比的。」正是因為這種懸殊差距,他們才想把外國人所有的拿過來據為己有。曾國藩曾說過:「目前借助於夷國軍隊,得以解一時之憂;而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才可期永遠之利。」李鴻章也曾強調說:「國家百用可省,只有練兵設備萬不可省。」他們二人都認為:如果中國軍器也能像西方的那樣精銳,那麼不但平定國內之亂有餘,而且抵禦外侮亦無不足。
西元一八六二年,曾國藩在安慶建立了軍械所。雖然規模較小,但是它卻是在中國試造新式武器的開始,它也是中國近代工業的始祖。之後不久,他又與李鴻章共同在上海創辦了洋務運動期間最大的軍事工業—江南機器製造局。曾到國外採辦機器的容閎後來追述:「自余由美國採購機器歸國以來,中國國家已籌備了千百萬現金,準備建廠,並希望能成為好望角以東之第一良好機器廠。故此廠實乃為一永久之碑,可以紀念曾文正之高識遠見。世無文正,則中國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機器廠否耶?」曾國藩、李鴻章引進機器生產軍備,以求自強,這在當時是最為先進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