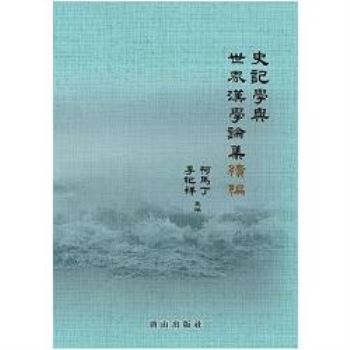節錄自〈《史記》裡的「作者」概念〉
柯馬丁(Martin Kern)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兼系主任
導言
據現有材料顯示,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下面提到的這些現象都發生在至多不到三代人之間:荷馬史詩開始廣為人知,並在許多希臘城邦被吟唱表演;書面文本開始超出他們的直接語境而流傳,而且新文本明確地作為書面作品被撰寫和閱讀;「詩人」(poet)和「吟誦者」(rhapsode)首次出現,分別指史詩的「創作者」(maker)和「表演者」(performer);「荷馬」之名出現在色諾芬(約前570年—約前475年)和赫拉克利特(約前535年—約前475年)的筆下,並很快被用為詩歌「創作者」的同義詞。換言之,文化裡典範性的文本、典範性的作者、書寫的普及、閱讀實踐以及作者和表演者之間的概念區分,這些現象相互關聯並共同湧現。因此,當《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成為泛希臘的文本時,他們同時也獲得了指名的作者,作為詩人(poet)的他「創作」了這些文本,正如「創作」陶器一樣(製作陶器是poieo一詞適用的最早的活動之一,正如六世紀以來製作了希臘花瓶的畫家和雕塑家在他們作品上簽名一樣)。隨著文學裡受到普遍尊敬的文本的出現,「作者」便應運而生了:不僅赫西俄德與荷馬被視為彼此競爭的對手,而且很快出現了諸如希羅多德(約前484年—約前425年)和修昔底德(約前460年—約前395年)這樣,於其作品開端就點明自己身分的作者。不妨看看下面兩段話。第一段是希羅多德《歷史》的開篇──這部作品後世被題為《希羅多德歷史》(Herodoti Historiae):
哈利卡那索斯的希羅多德在此發布他的研究,藉此,人類的成就將不被時間湮沒,而希臘和蠻族的豐功偉績都不會喪失其光彩;我特別要闡明的是這兩個民族的紛爭之源。古代中國的情況十分相似,但是並沒有發生在前一百年左右司馬遷(約前145年—約前85年)之前。眾所周知,和其希臘儕輩一樣,司馬遷告知我們,他曾如何四處遊歷尋訪來確認史實。但與希臘史家不同,他還強調自己的命運和遭遇賦予了他獨特的視角,和獲得歷史真實的特權,因為從個人經歷中,他深知道德和歷史在踐行正義上的失誤。因此,他對真實性的宣稱建立在兩項基礎上:首先,像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一樣,他聲言自己具有收集和評價歷史信息的能力,其次,與其不同的是,他本人「處於權利弱勢」的境地。 迫於宮刑的個人哀慟並沒有成為其明晰評價的阻礙,相反卻恰恰是其先決條件。然而,所有司馬遷作品詮釋中的張力,也都源自存在於司馬遷作為公正的資料收集者,以及司馬遷作為在提供史料之餘試圖融入自身憤懣的痛苦個體之間的根本二元對立。
柯馬丁(Martin Kern)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兼系主任
導言
據現有材料顯示,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下面提到的這些現象都發生在至多不到三代人之間:荷馬史詩開始廣為人知,並在許多希臘城邦被吟唱表演;書面文本開始超出他們的直接語境而流傳,而且新文本明確地作為書面作品被撰寫和閱讀;「詩人」(poet)和「吟誦者」(rhapsode)首次出現,分別指史詩的「創作者」(maker)和「表演者」(performer);「荷馬」之名出現在色諾芬(約前570年—約前475年)和赫拉克利特(約前535年—約前475年)的筆下,並很快被用為詩歌「創作者」的同義詞。換言之,文化裡典範性的文本、典範性的作者、書寫的普及、閱讀實踐以及作者和表演者之間的概念區分,這些現象相互關聯並共同湧現。因此,當《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成為泛希臘的文本時,他們同時也獲得了指名的作者,作為詩人(poet)的他「創作」了這些文本,正如「創作」陶器一樣(製作陶器是poieo一詞適用的最早的活動之一,正如六世紀以來製作了希臘花瓶的畫家和雕塑家在他們作品上簽名一樣)。隨著文學裡受到普遍尊敬的文本的出現,「作者」便應運而生了:不僅赫西俄德與荷馬被視為彼此競爭的對手,而且很快出現了諸如希羅多德(約前484年—約前425年)和修昔底德(約前460年—約前395年)這樣,於其作品開端就點明自己身分的作者。不妨看看下面兩段話。第一段是希羅多德《歷史》的開篇──這部作品後世被題為《希羅多德歷史》(Herodoti Historiae):
哈利卡那索斯的希羅多德在此發布他的研究,藉此,人類的成就將不被時間湮沒,而希臘和蠻族的豐功偉績都不會喪失其光彩;我特別要闡明的是這兩個民族的紛爭之源。古代中國的情況十分相似,但是並沒有發生在前一百年左右司馬遷(約前145年—約前85年)之前。眾所周知,和其希臘儕輩一樣,司馬遷告知我們,他曾如何四處遊歷尋訪來確認史實。但與希臘史家不同,他還強調自己的命運和遭遇賦予了他獨特的視角,和獲得歷史真實的特權,因為從個人經歷中,他深知道德和歷史在踐行正義上的失誤。因此,他對真實性的宣稱建立在兩項基礎上:首先,像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一樣,他聲言自己具有收集和評價歷史信息的能力,其次,與其不同的是,他本人「處於權利弱勢」的境地。 迫於宮刑的個人哀慟並沒有成為其明晰評價的阻礙,相反卻恰恰是其先決條件。然而,所有司馬遷作品詮釋中的張力,也都源自存在於司馬遷作為公正的資料收集者,以及司馬遷作為在提供史料之餘試圖融入自身憤懣的痛苦個體之間的根本二元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