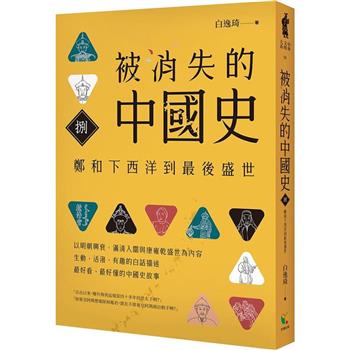第三章 閹黨、倭寇與滿清入關
●「留中不發」
滿州人崛起了,日本人打來了,巍峨的大明朝在做些什麼?當然還是一如往昔,沉浸在官僚政治的大染缸中,漸漸迷失方向。
朝廷裡唯一能夠超脫這套官僚體制的,就是高居萬物頂端的皇帝陛下。明神宗萬曆皇帝二十歲親政,在張居正的諄諄教誨中,年輕的皇帝滿腹經綸,衝勁十足,接手的是個有錢有勢的東亞第一強國,滿心想要有番大作為。
可是一連串的打擊卻讓萬曆皇帝心灰意冷。
無意之間發現了滿口仁義道德的張居正竟然家財萬貫,貪污不少銀兩,這讓他的情感受到傷害,他選擇以激烈手段來處理這件事:奪爵、抄家、子孫充軍,張居正過去的功業,被他一筆勾銷。
初掌大權的他,勵精圖治,不辭辛勞,萬曆十二年八月起,北京附近連月不雨,鬧了旱災,他親自率領文武百官,以步行方式往返二十里至京城南郊主持祭祀,太監勸他坐轎子,他不願意,走到腳底磨出水泡,只為了展現誠意。
萬曆十三年五月,山西、河南、山東、湖廣等地接連發生水災與蝗災,明神宗臨朝聽政之後,又召集閣臣商議因應對策,最後由他親自下詔,免去災區一年的田租稅糧。
同年,尚寶司丞徐貞明上表建議開發北方水利,增加糧食生產,明神宗看了奏表,頻頻點頭稱讚:「這的確是好辦法,應該讓他發揮。」他提拔徐貞明擔任少卿,兼任監察御史、墾田使,負起京畿農田治理之責,才花一年時間,就開墾三萬九千多畝土地。
對於臣下的建言,年輕的萬曆皇帝往往能虛心接受。萬曆十四年三月,禮部官員們討論政局,提出奏表指出:「如今天下尚不太平,原因乃是額外的徵收過多,不定時的勞役過繁,願陛下以身作則,力行節儉,以使百姓安居樂業。」
明神宗看完奏表,第二天上朝時當眾表示:「禮部的意見朕知道了,朕一定躬行節儉,絕不任意徵收稅賦勞役。」
想不到,這份勤勉與誠意竟然成為萬曆皇帝的絕響。
就在這一年,明神宗最寵愛的鄭貴妃生了一個兒子,取名朱常洵,明神宗欣喜非常,當下冊封鄭氏為皇貴妃。
這並不是一樁了不起的大事,皇帝愛封自己最愛的妃子,只要不廢皇后,那就理所當然,無關大局,但是,朝臣卻為這件事議論紛紛。原來,明神宗已經有過兩個兒子,次子早死,長子名叫朱常洛,是恭妃王氏所生,這個兒子雖非嫡長子,但從倫常秩序來看,理應立為太子,現在明神宗封鄭貴妃,豈非表示他有意封朱常洵為太子?
給事中姜應麟第一個跳出來說話,他上了一篇奏表,請求明神宗趕緊立朱常洛為東宮太子。
「朕立不立太子,那是朕的家務事,是這些奴才管得了的嗎?」明神宗憤怒異常,立刻下詔將姜應麟貶官。
誰知道過了不久,又有一個不怕死的吏部員外郎沈璟做出同樣的請求。明神宗依舊將他貶謫。
接連兩個要求立儲的官員被廢,似乎真的顯示出皇帝打算立朱常洵的企圖,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明神宗的智慧有限,在還沒立儲的情況下,他大可以不必這樣反應激烈,說不定不會讓那些以清流自居的臣子為了這種事吵翻了天。
結果,姜應麟、沈璟的被黜反而激起了群臣的喋喋不休,連首輔申時行為了順應眾朝臣的意見,也只好聯合閣臣請求萬曆皇帝明明白白的下令立儲。
「朕想把位子傳給誰,還得要聽這些老匹夫的話嗎?」明神宗問道。從前張居正教給他很多學問,這時候派上了用場,向來覺得自己就是天地至尊的他,仔細思索這個問題之後,赫然發現,貴為專制獨裁的皇帝,在官僚體系完備的情況下,竟然連決定繼承人的權力也沒有。
他長嘆一口氣,說道:「果真這樣的話,朕當這個皇帝還有什麼意思?」
明神宗沒有回應申時行的建議,只是第二天清晨,百官上朝之時,沒有看見皇帝的蹤影。「皇上龍體欠安,頭暈眼黑,今日暫且罷朝了。」負責傳話的小宦官說道。
百官面面相覷,申時行知道皇帝沒有生病,只是不想再和群臣辯論立儲的問題,但是有的時候,一群人的情緒要是起來了,就很難平撫下去,尤其是知識分子。
接連幾天,皇帝都沒有上朝,官員之中有人說話了:「皇上不願意見咱們,是不是因為他要立幼子為帝?我們身為朝廷忠臣,不能讓皇上犯下這種違背倫常之事!」
「皇上不上朝,還不是被鄭貴妃迷住了!」有人竟然這樣說道:「鄭貴妃要讓自己的兒子當儲君,怎不會在皇上面前猛灌迷湯!」
「皇上被奸人蒙蔽,太阿倒懸!」
激烈的言論紛紛出籠,抨擊聲浪極大,後來甚至連一些吏員也開始抨擊鄭貴妃,有些話甚至說得很難聽。這就是讀書人的風骨,皇帝操縱生殺大權是沒有錯,但是,只要讀書人面對這種「大節」之時,他們就會不怕死,不畏強權,捍衛自己心目中的「正義」與「道德」。
內閣首輔申時行是個好好先生,當初他帶頭上書請立儲君是為了平撫眾人意見洶洶,倒不是他真的認為立儲之事有那麼急迫,如今看見這些討論已經一發不可收拾,又轉而建議皇帝,希望他能下旨規定各部官員的議論僅止於自身職掌,並且不准那些不是言官的人擅自發表立儲的意見。
萬曆皇帝看了申時行的意見,點點頭,把奏章放在一旁,沒有任何指示。
這下子申時行連同僚都得罪了,言官們認為申時行蒙蔽皇上,紛紛上表彈劾,鬧得不可開交。
躲在後宮,不肯辦公,算是一種抗議,偏偏這種抗議很浪費錢,因為他總利用躲在後宮之時大肆享樂,動不動就下令將國庫中儲存的白銀挪到宮廷庫房之中好供他花用。這也算是一種報復,在他心中,朝中那些大臣都要和他作對,他就要多搶些大臣們辛苦賺來的銀子。
建議立儲的奏章不時送來,明神宗有時候看看奏表,有時候回應一下,有時候發怒起來重責一兩個官員。但他知道再怎麼重責也沒有用,這些官員書讀多了,腦袋和脖子都很硬,根本不怕死,堂堂的皇帝,也只好委婉的採取拖延策略,「皇后還沒生孩子哪!等皇后有了子嗣,再談立儲之事不遲。」
萬曆十七年,公元一五八九年十二月廿一日,大理寺評事雒于仁上了一篇《酒色財氣四箴疏》,嚴厲的筆調直指明神宗,說他整天躲在後宮喝酒,溺愛鄭貴妃,貪財好貨,意氣用事不與大臣見面,不理政事,不聽經筵,以致國勢日非,朝政敗壞。
這篇文章也許道出了明神宗的缺點,但是實在太不給皇帝面子,讓明神宗很難堪,也很生氣,不過他倒不是個暴虐的君主,並沒有立刻拿雒于仁開刀,一直撐到萬曆十八年元旦在毓德宮召見全體內閣大學士時,才把這份奏疏拿出來,遞給申時行。
「諸位先生們,這份奏疏直說朕酒色財氣兼而有之,你們替朕評一評。」萬曆皇帝說得很客氣。
申時行展開奏疏,才看了兩行,萬曆皇帝就忍不住說道:「他說朕好酒,誰不喝酒呢?朕喝酒後,從未有過失儀之事!他說朕好色,寵愛鄭貴妃,朕只因鄭貴妃勤勞,讓她隨時伺候著,恭妃王氏育有皇長子,朕讓她負起照管之責,母子相依,有何偏愛可言?」
大學士們只能頻頻點頭稱是。
萬曆皇帝命人把兩個皇子朱常洛與朱常洵找來,轉頭問申時行等人道:「你們覺得他們倆儀表如何?」
朱常洛不滿十歲,朱常洵不滿五歲,實在沒有什麼「儀表」可言,但是閣臣們仍然下拜稱頌。申時行說道:「皇長子龍鳳之姿,將來一定會成為有道之君;皇三子蘭芽玉質,將來一定也是皇室的驕傲。」
畢竟兩人都是萬曆皇帝生的,被這樣讚美,臉上的不岳漸漸退去。
大學士們察言觀色,王錫爵說道:「陛下,還是盡早冊立皇太子吧!免得議論紛紛。」
萬曆皇帝指著奏章說道:「這雒于仁的奏章是在詆毀朕躬,總該要嚴辦吧?」
申時行說道:「這份奏章言詞無理,固然不該,但也不可因此嚴辦,以免朝臣信以為真,恐將影響聖譽。」
「你說得很對。」萬曆皇帝道:「既然如此,朕就將這份奏章留中不發,你去和雒于仁說一聲,叫他稱病辭官吧!朕不想再見到這種人。」
「……臣等遵旨。」
「朕知道你們覺得不舒坦,朕又何嘗不是呢?只不過皇長子與皇三子均為朕所生,外人若想離間我父子之情,那就不是人臣之道,你們去和那些喜歡亂說話的人講一聲,要是明年不再為此爭論,則後年可以立儲,否則,就等皇長子十五歲的時候再說。」萬曆皇帝揮了揮手道:「你們跪安吧。」
此後,不只是議論立儲的奏疏,凡是任何有爭議、難以立刻決定的爭端,萬曆皇帝的處理方法就是「留中不發」,留中的意思,就是對這個問題既不允許,也不拒絕,不裁示,也不公布,直接擱置就算了事。
到後來,十份奏章有六七份都會留中,大學士葉向高感嘆地表示:「一事之請,難於拔山,一疏之行,曠然經歲……」皇帝不上朝,奏章不處理,重要大事沒辦法解決,如此政局,怎能清明?
日本攻打朝鮮,努爾哈赤橫掃東北,這兩件事雖然暫時轉移了部分朝臣議論的焦點,但是立儲之事,他們仍然沒有放棄。萬曆皇帝總是以皇后無子為理由,一再推託。
拖了十幾年,朝臣不但沒有放棄,態度反而更加堅決,明神宗曾經想用諸子同立為王的方式混淆視聽,但是騙不過精明的大臣們,皇帝迫於無奈,只好在萬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一年十月,皇長子朱常洛大婚之日,宣布立其為太子。
這場君臣之爭似乎以皇帝落敗收場,但是萬曆皇帝有辦法彌補心中的缺憾,比從前更貪財,更大手筆的從國庫調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