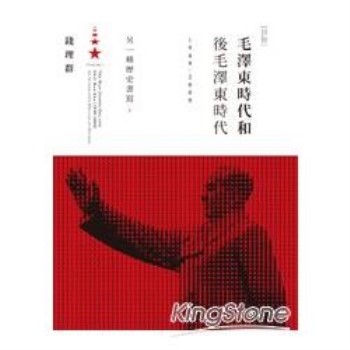第一講 建國初期1949-1955(2009年9月22日講)
今天是正式的第一講,我想完全按照歷史的順序講,所以第一講是建國初期,即1949-1955年。建國初期的問題首先在於,面對政權更替,一般老百姓該怎麼適應這種歷史的大變化,包括個人家庭命運的變化;第二,民眾當中特殊群體──知識分子,又如何適應這樣的變化,找到自己在新社會的位置;第三,執政者掌握政權後,要把中國帶往何處?
為了方便大家進入當時的歷史情境,我從個人經歷說起。
一、歷史交替時期我和我的家庭
1949年,我正好10歲,在上海迎接「解放」。當時我是上海幼兒師範附小五年級的學生。我記得大概在1949年6月23日,前一天晚上槍炮聲不斷,那天早上我和一位好朋友一起準時上學,走在大街上首先看到的,就是在沿街商鋪屋簷下躺著一排排大兵,這大概就是人們口耳相傳中已經相當神祕的「解放軍」了。解放軍為了不擾民,寧可露宿街頭,這使我這個小學生非常感動,許多上海市民也都是由這件小事認識了解放軍、共產黨和新政權的。對比國民黨的傷兵到處騷擾,我們都覺得這個世界真的變了。這個最初的印象十分深刻,一直到今天我都還記得。
現在想起來,其實,還沒有「解放」,我就已經處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了,只是我並不覺察而已。事情說起來還有點曲折。我是1948年從南京逃難到上海,原先預計再逃到台灣,但到了上海,我的外祖父和幾位在銀行供職的舅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共產黨的影響,一起勸說我母親不要走,所以我們就了留下來,我也在上海上小學。1949年上半年,那時秩序還算正常,我參加了上海市少年兒童的演講比賽,得了第三名。我記得自己講的是諾貝爾的故事,當時得第一名的小朋友講的是江亞輪沉船事件:1948年12月3日,上海吳淞港口江亞輪運輸大批人逃往台灣,卻發生沉船,失蹤1,600多人,當時很多人都覺得這是個象徵性事件,我後來在寫《1948:天地玄黃》時,就將其視為國民黨時代結束的一個象徵。那次我的演講引起一些成人的關注,上海當時有個少年兒童劇團,就把我吸收進去做業餘演員,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所領導的,我也就在實際上被納入共產黨的體制了。我們排了一幕話劇,我飾演一位報童,在街頭貼標語,撒傳單,迎接共產黨的到來。因此,上海一解放,我們就到各處的工廠、部隊、軍營去演出。
後來上海拍電影《三毛流浪記》也找了我。「三毛」是漫畫家張樂平(1910-1992)創造的一個流浪兒形象。這部電影於1948年拍攝,到1949年才拍完,恰好跨越了兩個時代。我在其中扮演了一個「闊少爺」的群眾角色,不知道為什麼在「演員表」上有我的名字,前幾年北大學生發現了,就用電腦技術,把電影上我的一個鏡頭定格了,發表在網上,也發給了我,算是一個紀念吧。這部電影公開放映大約是1950年初,我當時已從上海返回南京讀書。印象深刻的是,當時召開了一個座談會,討論三毛不幸命運的原因為何,我也發了言,認為這是戰爭造成的災難。沒想到我的發言遭到了其他大哥哥大姐姐的批判,他們都是共產黨員,或者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就批評我沒有階級觀點,不區別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共產黨的解放戰爭就是正義戰爭,是不能反對的。還有位大姐姐說,錢理群看來還需要學習及改造。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改造」這個詞,一直被要求改造到今天。
但「階級」在當時確實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特別我的家庭正是這場革命的對象。我後來在一篇文章中說到,共和國是一場革命的產物,革命是對原有社會結構、秩序的大顛倒,這導致原有階級、社會、人際關係的大變化。我們在歷史的敘述中都會討論到革命的意義,但很少考察這種大變動具體對每個人、每個家庭帶來的問題,以及他們心理的反應,這些都被歷史敘述所迴避,這樣的歷史是簡單化的。
這裡我想談談我的母親的反應。對於她來說,這確實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大變動,她原來是國民黨高官的貴夫人,一夜之間成了反革命家屬、反動官僚的家屬,所有人都用不屑的、敵視的眼光看著她,把她視作不可接觸的賤民。但我的母親卻以驚人的決斷和毅力適應了這樣的變化。她首先做的就是立刻把我父親所有的證件,包括蔣介石給他的勝利勛章,全部交給政府;然後她從此絕口不提和父親有關的任何事情,也絕口不提她過去的生活。既然這段歷史被視為罪惡,那就把住關口,從此不說。但她內心深處還保留著對父親的懷念,有兩件事可以看出,在她的臥房裡還掛著我父親的一幅畫像,過年過節時都要添一副碗筷來表示懷念。但後來連這都不被允許,因為我哥哥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家裡怎麼可以掛著反革命分子的畫像呢?後來這些外在的紀念形式都被取消了,思念也了無痕跡。本來她可以向我們傾訴以減輕精神的重負,但她閉口不言,就這麼沉默幾十年,至死也沒有隻言片語談及父親。她只保留了一張結婚照,並小心、頑固地斷絕和海峽對面的一切聯繫。最初兩邊還是有聯繫的,父親會通過香港的
今天是正式的第一講,我想完全按照歷史的順序講,所以第一講是建國初期,即1949-1955年。建國初期的問題首先在於,面對政權更替,一般老百姓該怎麼適應這種歷史的大變化,包括個人家庭命運的變化;第二,民眾當中特殊群體──知識分子,又如何適應這樣的變化,找到自己在新社會的位置;第三,執政者掌握政權後,要把中國帶往何處?
為了方便大家進入當時的歷史情境,我從個人經歷說起。
一、歷史交替時期我和我的家庭
1949年,我正好10歲,在上海迎接「解放」。當時我是上海幼兒師範附小五年級的學生。我記得大概在1949年6月23日,前一天晚上槍炮聲不斷,那天早上我和一位好朋友一起準時上學,走在大街上首先看到的,就是在沿街商鋪屋簷下躺著一排排大兵,這大概就是人們口耳相傳中已經相當神祕的「解放軍」了。解放軍為了不擾民,寧可露宿街頭,這使我這個小學生非常感動,許多上海市民也都是由這件小事認識了解放軍、共產黨和新政權的。對比國民黨的傷兵到處騷擾,我們都覺得這個世界真的變了。這個最初的印象十分深刻,一直到今天我都還記得。
現在想起來,其實,還沒有「解放」,我就已經處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了,只是我並不覺察而已。事情說起來還有點曲折。我是1948年從南京逃難到上海,原先預計再逃到台灣,但到了上海,我的外祖父和幾位在銀行供職的舅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共產黨的影響,一起勸說我母親不要走,所以我們就了留下來,我也在上海上小學。1949年上半年,那時秩序還算正常,我參加了上海市少年兒童的演講比賽,得了第三名。我記得自己講的是諾貝爾的故事,當時得第一名的小朋友講的是江亞輪沉船事件:1948年12月3日,上海吳淞港口江亞輪運輸大批人逃往台灣,卻發生沉船,失蹤1,600多人,當時很多人都覺得這是個象徵性事件,我後來在寫《1948:天地玄黃》時,就將其視為國民黨時代結束的一個象徵。那次我的演講引起一些成人的關注,上海當時有個少年兒童劇團,就把我吸收進去做業餘演員,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所領導的,我也就在實際上被納入共產黨的體制了。我們排了一幕話劇,我飾演一位報童,在街頭貼標語,撒傳單,迎接共產黨的到來。因此,上海一解放,我們就到各處的工廠、部隊、軍營去演出。
後來上海拍電影《三毛流浪記》也找了我。「三毛」是漫畫家張樂平(1910-1992)創造的一個流浪兒形象。這部電影於1948年拍攝,到1949年才拍完,恰好跨越了兩個時代。我在其中扮演了一個「闊少爺」的群眾角色,不知道為什麼在「演員表」上有我的名字,前幾年北大學生發現了,就用電腦技術,把電影上我的一個鏡頭定格了,發表在網上,也發給了我,算是一個紀念吧。這部電影公開放映大約是1950年初,我當時已從上海返回南京讀書。印象深刻的是,當時召開了一個座談會,討論三毛不幸命運的原因為何,我也發了言,認為這是戰爭造成的災難。沒想到我的發言遭到了其他大哥哥大姐姐的批判,他們都是共產黨員,或者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就批評我沒有階級觀點,不區別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共產黨的解放戰爭就是正義戰爭,是不能反對的。還有位大姐姐說,錢理群看來還需要學習及改造。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改造」這個詞,一直被要求改造到今天。
但「階級」在當時確實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特別我的家庭正是這場革命的對象。我後來在一篇文章中說到,共和國是一場革命的產物,革命是對原有社會結構、秩序的大顛倒,這導致原有階級、社會、人際關係的大變化。我們在歷史的敘述中都會討論到革命的意義,但很少考察這種大變動具體對每個人、每個家庭帶來的問題,以及他們心理的反應,這些都被歷史敘述所迴避,這樣的歷史是簡單化的。
這裡我想談談我的母親的反應。對於她來說,這確實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大變動,她原來是國民黨高官的貴夫人,一夜之間成了反革命家屬、反動官僚的家屬,所有人都用不屑的、敵視的眼光看著她,把她視作不可接觸的賤民。但我的母親卻以驚人的決斷和毅力適應了這樣的變化。她首先做的就是立刻把我父親所有的證件,包括蔣介石給他的勝利勛章,全部交給政府;然後她從此絕口不提和父親有關的任何事情,也絕口不提她過去的生活。既然這段歷史被視為罪惡,那就把住關口,從此不說。但她內心深處還保留著對父親的懷念,有兩件事可以看出,在她的臥房裡還掛著我父親的一幅畫像,過年過節時都要添一副碗筷來表示懷念。但後來連這都不被允許,因為我哥哥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家裡怎麼可以掛著反革命分子的畫像呢?後來這些外在的紀念形式都被取消了,思念也了無痕跡。本來她可以向我們傾訴以減輕精神的重負,但她閉口不言,就這麼沉默幾十年,至死也沒有隻言片語談及父親。她只保留了一張結婚照,並小心、頑固地斷絕和海峽對面的一切聯繫。最初兩邊還是有聯繫的,父親會通過香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