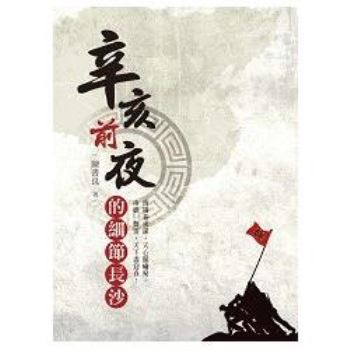第二章 華興公司
青年黃興一襲青衿,飄然東歸,在湘潭茶園鋪岩洞中與「龍頭大爺」馬福益用柴火煨雞,煮酒痛飲,徹夜縱談。在長沙西園僻巷,他會合群英成立華興會。會上黃興慷慨演講,其講演詞有諸葛亮〈隆中對〉之風概,其中「首義」、「起而應之」已經為七年後的辛亥革命所印證,不過由於事態的演變,「湘省」變為「鄂省」而已……
一
一九○三年秋天,一艘汽輪從漢口港開出,逆長江而上,過洞庭,入湘江,劈波斬浪,向南急駛。船頭站立著一位西裝革履、氣宇軒昂的青年。他就是日後震驚中外的辛亥革命的主將黃興。
不過,這時候他尚未改名為興。他名仁牧,一名軫,號杞園,字廑午,湖南善化縣(今長沙縣)人。父親黃炳昆,號筱村,青年時考取秀才,補府學廩生,起初在本鄉設館授徒,一度擔任過地方上的都總。後來到長沙城裡設館,家境漸寬裕,於是在涼塘購置了田產。
涼塘在善化縣龍喜鄉,即今長沙縣黃興鎮揚托村。此地處平疇沃土,四合大院座西朝東,有青瓦土磚房五十三間,頗有氣派,當地俗稱為「大屋」。
黃興五歲開始從父學習《論語》、唐詩宋詞等,八歲入私塾學習《詩經》、《楚辭》、《春秋》及八股文。到十四歲,轉為居家自修,並學習烏家拳術。二十二歲考中秀才。當年的太平軍啟動了愛國少年的勃勃雄心,據黃興後來追憶:「我革命的動機,是在少時讀太平天國雜史而起。」(李貽燕〈紀念黃克強先生〉,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西安《西北》)此時民族危機日益嚴重,隨之而來的日益高漲的湖南維新運動,異常活躍的進步知識界,給黃興以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一八九八年,他被長沙嶽麓書院保送到武昌兩湖書院學習以後,書院遵循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學方針,教育制度迅速向西方學制過渡。這樣,黃興在這裡接觸了西方的政治學說,並實習軍事,為其以後投身武裝革命準備了條件。他「文似東坡,字工北魏」,是兩湖的高材生。這時的黃廑午,是「瀏陽雙傑」譚嗣同、唐才常十足的粉絲。一九○○年夏,他甚至參與自立軍起事。後來,唐才常等遇害,這使「常存亡國亡種之心」的黃興在思想上發生了根本的轉變,經歷了從服膺維新轉向反清革命的歷程。他曾寫〈筆銘〉自勵:「朝作書,暮作書,雕蟲篆刻胡為乎?投筆方為大丈夫!」又作〈詠鷹〉詩一首:
獨立雄無敵,長空萬里風。
可憐此豪傑,豈肯困樊籠?
一去渡滄海,高揚摩碧穹。
秋深霜氣肅,木落萬山空。不過,儘管「豈肯困樊籠」,他表面上「沉默寡言」、「虛衷慎密」,深藏不露,因而並未引起書院當局的任何懷疑。
一九○二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從兩湖、經心、江漢三家書院選派學生三十餘人赴日本留學,其中湘籍一人,就是黃興。這是他走上民主革命的轉捩點。抵日後,黃興入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科,與留日學生楊篤生、樊錐、梁煥彝等創辦了《遊學譯編》雜誌,又設立湖南編譯社,介紹西方的社會政治學,宣傳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思想。革命老幹部李銳同志曾對我說過,他的父親其時亦與宋教仁等在日本留學,他父親說當時日本教科書說,橘子好吃,但橘子產地在哪裡呢?中國。當時的留學生憂國憂民,反清情緒日熾,李老的父親與宋教仁等都剪掉了辮子,然而黃興卻不顯山、不露水。當年同在弘文學院求學的魯迅曾以其生花妙筆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回憶:「黃克強在東京作師範學生時,就始終沒有斷髮,也未嘗大叫革命,所略顯其楚人的反抗的蠻性者,唯因日本學監誡學生不可赤膊,他卻偏光著上身,手挾洋瓷臉盆,從浴室經過大院子,搖搖擺擺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黃興熱心社會活動,富有組織才能,善於團結同志,成為留日學生中湖南學生和軍校學生的領袖。
關於黃興的領袖氣質與人格魅力,小他七歲的章士釗在〈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中記敍了切身感受:
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認為最難交者有三人:陳獨秀、章太炎、李根源。但吾與三人都保持始終,從無詬誶。吾持以論交之唯一武器,在「無爭」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強,則頓失憑依,手無寸鐵。何以言之?我以無爭往,而彼之無爭尤先於我,大於我。且彼無爭之外,尤一切任勞任怨而不辭,而我無有也。由是我之一生,凡與克強有涉之大小事故,都在對方涵蓋孕育之中,渾然不覺。因而我敢論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黃克強。
一九○三年,留日學生中的激進分子組織了軍國民教育會,該會決定了三種方法分頭進行活動:一、鼓吹,二、起義,三、暗殺。軍國民教育會對於吸收會員是絕對嚴格的,行動也完全祕密,「開會無定期,會場無定所」,會員的人數不多,活動從未中斷。被軍國民教育會推派回國,到各省去從事「運動」的,叫做「運動員」。黃興自告奮勇擔任軍國民教育會的「運動員」,回湘從事反清革命運動的策劃。
青年黃興一襲青衿,飄然東歸,在湘潭茶園鋪岩洞中與「龍頭大爺」馬福益用柴火煨雞,煮酒痛飲,徹夜縱談。在長沙西園僻巷,他會合群英成立華興會。會上黃興慷慨演講,其講演詞有諸葛亮〈隆中對〉之風概,其中「首義」、「起而應之」已經為七年後的辛亥革命所印證,不過由於事態的演變,「湘省」變為「鄂省」而已……
一
一九○三年秋天,一艘汽輪從漢口港開出,逆長江而上,過洞庭,入湘江,劈波斬浪,向南急駛。船頭站立著一位西裝革履、氣宇軒昂的青年。他就是日後震驚中外的辛亥革命的主將黃興。
不過,這時候他尚未改名為興。他名仁牧,一名軫,號杞園,字廑午,湖南善化縣(今長沙縣)人。父親黃炳昆,號筱村,青年時考取秀才,補府學廩生,起初在本鄉設館授徒,一度擔任過地方上的都總。後來到長沙城裡設館,家境漸寬裕,於是在涼塘購置了田產。
涼塘在善化縣龍喜鄉,即今長沙縣黃興鎮揚托村。此地處平疇沃土,四合大院座西朝東,有青瓦土磚房五十三間,頗有氣派,當地俗稱為「大屋」。
黃興五歲開始從父學習《論語》、唐詩宋詞等,八歲入私塾學習《詩經》、《楚辭》、《春秋》及八股文。到十四歲,轉為居家自修,並學習烏家拳術。二十二歲考中秀才。當年的太平軍啟動了愛國少年的勃勃雄心,據黃興後來追憶:「我革命的動機,是在少時讀太平天國雜史而起。」(李貽燕〈紀念黃克強先生〉,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西安《西北》)此時民族危機日益嚴重,隨之而來的日益高漲的湖南維新運動,異常活躍的進步知識界,給黃興以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一八九八年,他被長沙嶽麓書院保送到武昌兩湖書院學習以後,書院遵循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學方針,教育制度迅速向西方學制過渡。這樣,黃興在這裡接觸了西方的政治學說,並實習軍事,為其以後投身武裝革命準備了條件。他「文似東坡,字工北魏」,是兩湖的高材生。這時的黃廑午,是「瀏陽雙傑」譚嗣同、唐才常十足的粉絲。一九○○年夏,他甚至參與自立軍起事。後來,唐才常等遇害,這使「常存亡國亡種之心」的黃興在思想上發生了根本的轉變,經歷了從服膺維新轉向反清革命的歷程。他曾寫〈筆銘〉自勵:「朝作書,暮作書,雕蟲篆刻胡為乎?投筆方為大丈夫!」又作〈詠鷹〉詩一首:
獨立雄無敵,長空萬里風。
可憐此豪傑,豈肯困樊籠?
一去渡滄海,高揚摩碧穹。
秋深霜氣肅,木落萬山空。不過,儘管「豈肯困樊籠」,他表面上「沉默寡言」、「虛衷慎密」,深藏不露,因而並未引起書院當局的任何懷疑。
一九○二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從兩湖、經心、江漢三家書院選派學生三十餘人赴日本留學,其中湘籍一人,就是黃興。這是他走上民主革命的轉捩點。抵日後,黃興入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科,與留日學生楊篤生、樊錐、梁煥彝等創辦了《遊學譯編》雜誌,又設立湖南編譯社,介紹西方的社會政治學,宣傳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思想。革命老幹部李銳同志曾對我說過,他的父親其時亦與宋教仁等在日本留學,他父親說當時日本教科書說,橘子好吃,但橘子產地在哪裡呢?中國。當時的留學生憂國憂民,反清情緒日熾,李老的父親與宋教仁等都剪掉了辮子,然而黃興卻不顯山、不露水。當年同在弘文學院求學的魯迅曾以其生花妙筆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回憶:「黃克強在東京作師範學生時,就始終沒有斷髮,也未嘗大叫革命,所略顯其楚人的反抗的蠻性者,唯因日本學監誡學生不可赤膊,他卻偏光著上身,手挾洋瓷臉盆,從浴室經過大院子,搖搖擺擺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黃興熱心社會活動,富有組織才能,善於團結同志,成為留日學生中湖南學生和軍校學生的領袖。
關於黃興的領袖氣質與人格魅力,小他七歲的章士釗在〈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中記敍了切身感受:
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認為最難交者有三人:陳獨秀、章太炎、李根源。但吾與三人都保持始終,從無詬誶。吾持以論交之唯一武器,在「無爭」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強,則頓失憑依,手無寸鐵。何以言之?我以無爭往,而彼之無爭尤先於我,大於我。且彼無爭之外,尤一切任勞任怨而不辭,而我無有也。由是我之一生,凡與克強有涉之大小事故,都在對方涵蓋孕育之中,渾然不覺。因而我敢論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黃克強。
一九○三年,留日學生中的激進分子組織了軍國民教育會,該會決定了三種方法分頭進行活動:一、鼓吹,二、起義,三、暗殺。軍國民教育會對於吸收會員是絕對嚴格的,行動也完全祕密,「開會無定期,會場無定所」,會員的人數不多,活動從未中斷。被軍國民教育會推派回國,到各省去從事「運動」的,叫做「運動員」。黃興自告奮勇擔任軍國民教育會的「運動員」,回湘從事反清革命運動的策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