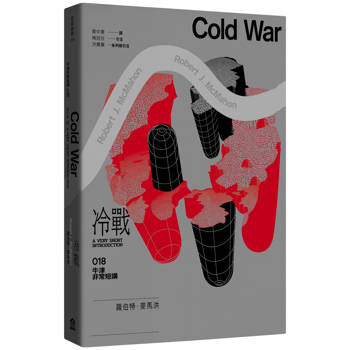【小標】第三章(節錄)
【小小標】共產黨拿下中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不只代表毛澤東(圖3)和二十年前遭國民黨擊潰、追殺、幾乎消滅的其他中共領袖的巨大勝利,也標誌著冷戰的性質和地點有了根本的轉變─對戰略、意識形態、國內政治影響甚大。
二戰期間,羅斯福政府以大量軍援、經援支持蔣介石政權,但始終無法令苛求的蔣介石滿意。羅斯福想要把中國軍隊打造成具有戰力的抗日部隊,把蔣介石政權打造成可靠的美國盟友,使其能在戰後亞洲事務上扮演促成穩定、制衡他方勢力的角色。為實現這些目標,一九四三年羅斯福於開羅和蔣介石會晤,就在中國領導人未獲邀參加的德黑蘭三巨頭高峰會前幾天。在開羅會談期間,這位美國總統把中國象徵性提升至大國地位,以討好蔣介石;接著羅斯福談到中國作為與美英蘇並列的「四警察」之一,將有助於維持戰後和平。他如此力捧中國,既為強化中美關係,也為彌補蔣介石所要求但華府未能提供的額外物資援助,還為使中國繼續參戰,防止中日單獨媾和,破壞大局。但不管是羅斯福的象徵性示好,還是他定期派至國民黨戰時首都重慶的軍事、外交代表團,都不足以說服蔣介石的軍隊在戰場上積極抗日。
到了一九四四年,美國駐華外交官已日益不看好深陷腐敗、貪污、無能泥淖的國民黨政權。國民黨政府則深信其生存的主要威脅,不是來自日本,而是來自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政府認為就算自身沒有大力相助,他們的美國盟友都會擊敗日本。在毛澤東高明的領導下,中共已在日本占領這幾年期間壯大為一股難以對付的軍事、政治力量,他們已控制華北、華中大部分地區。蔣介石和其親信未將更多兵力、作戰物資用於打入侵的日本人,而是選擇保留寶貴資源,留待戰後當他們免不了與共產黨攤牌之時。
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會議上,羅斯福指望一個不尋常的對象幫忙解決美國在中國的政策兩難。蔣介石不願全力抗戰,讓羅斯福徹底醒悟,於是羅斯福尋求蘇聯於歐戰結束三個月內加入對日作戰,並得到蘇聯應許。史達林為此提出的條件:羅斯福答應幫助蘇聯取回沙俄時代在中國東北和外蒙古的特許權,為美國總統所接受,畢竟,在太平洋戰爭的最後階段,死傷據認將會極慘重,這位美國總統盡可能減少美國人在此階段的傷亡。八月十四日,蔣介石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意給予蘇聯這些特許權,換取莫斯科承認國民政府的法定統治權。
出於同樣的意識形態,中共把史達林當成同志,因此,史達林與國民政府締約,自然令中共覺得遭同志出賣。史達林對俄羅斯國家利益的理性盤算,超越他對共產革命夥伴的任何感性忠誠。事實上,這位蘇聯統治者樂見中國孱弱分裂甚於強盛統一──不管中國由誰當家作主皆然。史達林希望中共依舊依賴且聽命於莫斯科,他察覺到若由民族主義氣息濃厚的團體掌權,可能致力於將全中國領土納入其統治,從而危害他所渴望建立的勢力範圍。這位打從骨子裡不喜歡冒風險的蘇聯獨裁者,也不想挑釁美國。能夠劫掠中國東北(蘇聯紅軍於一九四五年八月進入中國東北後就這麼做),並鞏固莫斯科剛在那裡和其他邊境地帶取得的商業利益,史達林就很滿足。在史達林眼中,毛澤東是個吵鬧、難以控制又不知天高地厚之徒,領導一群「人造奶油」共產黨人。在蘇聯本國的需要面前,毛澤東的需要只能晾在一邊。
日本投降後,中國國內政治情勢江河日下。一如蔣介石,毛澤東認為國共兩黨真誠攜手同心的可能性不大,內戰不可避免。在八月十一日的黨內指示中,他要中共幹部和軍事領導人「集中力量,準備打內戰」。整個一九四五年秋,國共兩黨軍隊在中國東北交火,蔣介石大舉動用美式裝備和運輸工具,欲將共軍逐出東北。
美國希望中國統一、和平、親美,但這份希望日益黯淡。一九四五年底,杜魯門總統派馬歇爾將軍赴華調停國共衝突。馬歇爾是他那一代最受敬重、戰功最彪炳的美國軍人。
一九四六年初,馬歇爾如願促成國共暫時停火,但不久戰火重燃。這位美國將軍誤以為建立國共聯合政府,讓國共共享權力可行,於是試圖打造出讓蔣毛都滿意的折衷方案。馬歇爾不偏向國共任一方,但兩黨之間難以消弭的歧見,使他的努力功敗垂成。國共兩黨互不信任,或不願與對方共享權力。到了一九四六年底,馬歇爾已斷定這場鬥爭只有靠武力才能解決,而且蔣介石無望取勝,情勢果如他所料。杜魯門政府繼續援助蔣介石政權(從日本投降至一九五○年共援助二十八億美元),但此舉的用意,在於保護杜魯門政府的側翼,使其免遭國會和媒體裡支持國民政府者(所謂的中國遊說團)攻擊,而非出於光靠美國支持就能使無能的國民黨軍隊打贏內戰的信念。到了一九四八年底,挫敗惡化為潰敗,蔣介石和其親信逃往台灣。一九四九年十月毛澤東從北京天安門豪氣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舉,只是把大部分了解中國情勢的觀察家老早就預料到的結果確立而已。
共產黨打贏中國內戰,主要是中國內部諸多錯綜複雜的因素所促成,但不可避免影響冷戰。儘管華府與蔣介石關係不穩且充滿猜忌,美國還是支持國民政府;儘管莫斯科與毛澤東關係不穩且充滿猜忌,蘇聯還是支持中共,而美國所支持的國民政府敗於蘇聯所支持的中共之手。亞洲、歐洲和其他關注此情勢的觀察家,立即把中國內戰的結果視為西方的一大挫敗、蘇聯和全世界共產勢力的劃時代勝利。美國國內批評杜魯門者也這麼認為,痛批這位總統思慮不周,甚至背信棄義,因而失去中國。杜魯門政府的計畫人員則對共黨拿下中國平靜看待,認為那是美國一次令人失望的挫敗,但非十足的戰略大敗。首先,國務卿艾奇遜和其國務院高階副手,並未把貧困、百廢待舉的中國視為整個世界均勢裡極重要的一環──至少短期來看不是如此。因此,在中國的失利,不能與在歐洲、日本、乃至在中東的失利相提並論。其次,他們推斷共產中國未必發展成鐵板一塊的中蘇反美集團。美國資深戰略家相信,扞格的地緣政治野心不利於史達林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結為緊密的夥伴。最後,他們樂觀認為北京亟需經濟援助一事,會給予美國分化這兩個共產強權所需的破口。
有些史學家相信美國其實有一個絕無僅有的機會,可以在這個重要關頭和中國發展出友好關係,或至少就事論事的務實關係,但未能把握住。中共政府裡有些人的確想與美國建立正面關係,以取得中國所需的重建援助,以免過度倚賴克里姆林宮。在美國這一方,艾奇遜認為一旦「塵埃落定」,華府可給予北京外交承認,從內戰後殘破的中國搶救出其所能搶救的東西。然而,晚近的證據意味著,這一「失去的機會」其實始終不存在。毛澤東決心改造中國,而且西方帝國主義者長久以來糟蹋中國,令其怒不可遏,為此更堅定改造中國之意。由於這一決心的驅使,加上需要一個外敵來幫忙動員人民支持其在國內的宏大革命抱負,毛澤東自然而然倒向蘇聯陣營。於是,下屬所提北京應向華府遞出橄欖枝的建議,他一概否決。這位中國領導人反而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前往莫斯科,儘管受到仍心存提防的史達林冷淡對待,毛澤東還是談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份中蘇條約載明若有一方受第三方攻擊,另一方必須出手援助。此時,冷戰已牢牢扎根於亞洲土壤,而此條約的問世或許是最讓人覺得不妙的冷戰象徵。
【小小標】共產黨拿下中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不只代表毛澤東(圖3)和二十年前遭國民黨擊潰、追殺、幾乎消滅的其他中共領袖的巨大勝利,也標誌著冷戰的性質和地點有了根本的轉變─對戰略、意識形態、國內政治影響甚大。
二戰期間,羅斯福政府以大量軍援、經援支持蔣介石政權,但始終無法令苛求的蔣介石滿意。羅斯福想要把中國軍隊打造成具有戰力的抗日部隊,把蔣介石政權打造成可靠的美國盟友,使其能在戰後亞洲事務上扮演促成穩定、制衡他方勢力的角色。為實現這些目標,一九四三年羅斯福於開羅和蔣介石會晤,就在中國領導人未獲邀參加的德黑蘭三巨頭高峰會前幾天。在開羅會談期間,這位美國總統把中國象徵性提升至大國地位,以討好蔣介石;接著羅斯福談到中國作為與美英蘇並列的「四警察」之一,將有助於維持戰後和平。他如此力捧中國,既為強化中美關係,也為彌補蔣介石所要求但華府未能提供的額外物資援助,還為使中國繼續參戰,防止中日單獨媾和,破壞大局。但不管是羅斯福的象徵性示好,還是他定期派至國民黨戰時首都重慶的軍事、外交代表團,都不足以說服蔣介石的軍隊在戰場上積極抗日。
到了一九四四年,美國駐華外交官已日益不看好深陷腐敗、貪污、無能泥淖的國民黨政權。國民黨政府則深信其生存的主要威脅,不是來自日本,而是來自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政府認為就算自身沒有大力相助,他們的美國盟友都會擊敗日本。在毛澤東高明的領導下,中共已在日本占領這幾年期間壯大為一股難以對付的軍事、政治力量,他們已控制華北、華中大部分地區。蔣介石和其親信未將更多兵力、作戰物資用於打入侵的日本人,而是選擇保留寶貴資源,留待戰後當他們免不了與共產黨攤牌之時。
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會議上,羅斯福指望一個不尋常的對象幫忙解決美國在中國的政策兩難。蔣介石不願全力抗戰,讓羅斯福徹底醒悟,於是羅斯福尋求蘇聯於歐戰結束三個月內加入對日作戰,並得到蘇聯應許。史達林為此提出的條件:羅斯福答應幫助蘇聯取回沙俄時代在中國東北和外蒙古的特許權,為美國總統所接受,畢竟,在太平洋戰爭的最後階段,死傷據認將會極慘重,這位美國總統盡可能減少美國人在此階段的傷亡。八月十四日,蔣介石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意給予蘇聯這些特許權,換取莫斯科承認國民政府的法定統治權。
出於同樣的意識形態,中共把史達林當成同志,因此,史達林與國民政府締約,自然令中共覺得遭同志出賣。史達林對俄羅斯國家利益的理性盤算,超越他對共產革命夥伴的任何感性忠誠。事實上,這位蘇聯統治者樂見中國孱弱分裂甚於強盛統一──不管中國由誰當家作主皆然。史達林希望中共依舊依賴且聽命於莫斯科,他察覺到若由民族主義氣息濃厚的團體掌權,可能致力於將全中國領土納入其統治,從而危害他所渴望建立的勢力範圍。這位打從骨子裡不喜歡冒風險的蘇聯獨裁者,也不想挑釁美國。能夠劫掠中國東北(蘇聯紅軍於一九四五年八月進入中國東北後就這麼做),並鞏固莫斯科剛在那裡和其他邊境地帶取得的商業利益,史達林就很滿足。在史達林眼中,毛澤東是個吵鬧、難以控制又不知天高地厚之徒,領導一群「人造奶油」共產黨人。在蘇聯本國的需要面前,毛澤東的需要只能晾在一邊。
日本投降後,中國國內政治情勢江河日下。一如蔣介石,毛澤東認為國共兩黨真誠攜手同心的可能性不大,內戰不可避免。在八月十一日的黨內指示中,他要中共幹部和軍事領導人「集中力量,準備打內戰」。整個一九四五年秋,國共兩黨軍隊在中國東北交火,蔣介石大舉動用美式裝備和運輸工具,欲將共軍逐出東北。
美國希望中國統一、和平、親美,但這份希望日益黯淡。一九四五年底,杜魯門總統派馬歇爾將軍赴華調停國共衝突。馬歇爾是他那一代最受敬重、戰功最彪炳的美國軍人。
一九四六年初,馬歇爾如願促成國共暫時停火,但不久戰火重燃。這位美國將軍誤以為建立國共聯合政府,讓國共共享權力可行,於是試圖打造出讓蔣毛都滿意的折衷方案。馬歇爾不偏向國共任一方,但兩黨之間難以消弭的歧見,使他的努力功敗垂成。國共兩黨互不信任,或不願與對方共享權力。到了一九四六年底,馬歇爾已斷定這場鬥爭只有靠武力才能解決,而且蔣介石無望取勝,情勢果如他所料。杜魯門政府繼續援助蔣介石政權(從日本投降至一九五○年共援助二十八億美元),但此舉的用意,在於保護杜魯門政府的側翼,使其免遭國會和媒體裡支持國民政府者(所謂的中國遊說團)攻擊,而非出於光靠美國支持就能使無能的國民黨軍隊打贏內戰的信念。到了一九四八年底,挫敗惡化為潰敗,蔣介石和其親信逃往台灣。一九四九年十月毛澤東從北京天安門豪氣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舉,只是把大部分了解中國情勢的觀察家老早就預料到的結果確立而已。
共產黨打贏中國內戰,主要是中國內部諸多錯綜複雜的因素所促成,但不可避免影響冷戰。儘管華府與蔣介石關係不穩且充滿猜忌,美國還是支持國民政府;儘管莫斯科與毛澤東關係不穩且充滿猜忌,蘇聯還是支持中共,而美國所支持的國民政府敗於蘇聯所支持的中共之手。亞洲、歐洲和其他關注此情勢的觀察家,立即把中國內戰的結果視為西方的一大挫敗、蘇聯和全世界共產勢力的劃時代勝利。美國國內批評杜魯門者也這麼認為,痛批這位總統思慮不周,甚至背信棄義,因而失去中國。杜魯門政府的計畫人員則對共黨拿下中國平靜看待,認為那是美國一次令人失望的挫敗,但非十足的戰略大敗。首先,國務卿艾奇遜和其國務院高階副手,並未把貧困、百廢待舉的中國視為整個世界均勢裡極重要的一環──至少短期來看不是如此。因此,在中國的失利,不能與在歐洲、日本、乃至在中東的失利相提並論。其次,他們推斷共產中國未必發展成鐵板一塊的中蘇反美集團。美國資深戰略家相信,扞格的地緣政治野心不利於史達林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結為緊密的夥伴。最後,他們樂觀認為北京亟需經濟援助一事,會給予美國分化這兩個共產強權所需的破口。
有些史學家相信美國其實有一個絕無僅有的機會,可以在這個重要關頭和中國發展出友好關係,或至少就事論事的務實關係,但未能把握住。中共政府裡有些人的確想與美國建立正面關係,以取得中國所需的重建援助,以免過度倚賴克里姆林宮。在美國這一方,艾奇遜認為一旦「塵埃落定」,華府可給予北京外交承認,從內戰後殘破的中國搶救出其所能搶救的東西。然而,晚近的證據意味著,這一「失去的機會」其實始終不存在。毛澤東決心改造中國,而且西方帝國主義者長久以來糟蹋中國,令其怒不可遏,為此更堅定改造中國之意。由於這一決心的驅使,加上需要一個外敵來幫忙動員人民支持其在國內的宏大革命抱負,毛澤東自然而然倒向蘇聯陣營。於是,下屬所提北京應向華府遞出橄欖枝的建議,他一概否決。這位中國領導人反而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前往莫斯科,儘管受到仍心存提防的史達林冷淡對待,毛澤東還是談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份中蘇條約載明若有一方受第三方攻擊,另一方必須出手援助。此時,冷戰已牢牢扎根於亞洲土壤,而此條約的問世或許是最讓人覺得不妙的冷戰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