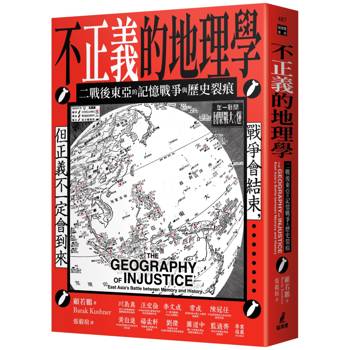臺灣版序言
臺灣戰後正義的悖論
二○二五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八十周年。然而,對於臺灣這座島嶼上的居民來說,當年那一時刻的意義卻是為另一段歷史,也就是為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揭幕。接下來的八十年可再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將近四十年,期間國民黨(在一九四九年退守臺灣與其他小島)以專制鐵腕統治臺灣,讓它在國際上的名號「自由中國」成為政治笑話。當國軍被中國共產黨打得兵敗如山倒,數百萬中國人因此割捨過去在大陸的人生,逃往這座小島;臺灣前文化部長龍應台所記述的老一輩人撤臺往事,以及楊孟軒的學術研究,都是字字血淚書寫這些人的悲慘故事。然後,在這八十年的後半段,中華民國開始轉向民主。國民黨自己把自己從一黨專制中解放;當政權易手,土生土長的「本省人」與家族從大陸移居來的「外省人」都以民選官員身分登上政壇。在臺灣人看來,從日帝國戰敗到今天,這段歷史是走過一條艱難的政治與文化之路。臺灣在一九四五年要被重新收歸中國統治,但當時的中國政權卻幾乎不願花心思去了解臺灣人民,了解這些人在過去半世紀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經歷的變化。相對於「中國人」,「臺灣人」到底是什麼?這是一個沒有被問出,也不被允許問出的問題。這種疑問會牴觸中國中央政權的基本信條,那就是全然相信「中國人」這個自我認知是深深刻在中華民族的骨子裡,與教育、地理或統治政府都無關,且絕對不會變更。中華民國從一個殖民地邊陲變成戰後國家,稍後又被宣告為「非國家」並喪失聯合國席位,這其中的百轉千迴都已被英語界與臺灣的學術研究者細細講明。正是因為這些事,因為這條通往政治合法性卻又失去政治合法性的崎嶇之路,所以歷史學家林孝庭才將他講述這場轉變的著作巧妙命名為《意外的國度》。
這座島嶼的政治認同也在過去四十年間有所變化,從堅持把「中華民國」的標籤利用到最後(且經常讓西方學生把它跟它的鄰居「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國大陸」搞混),變成現在以「臺灣」的稱呼比較盛行。接續林孝庭的分析,臺灣大學陳翠蓮教授以她挑動人心的研究檢驗臺灣政治史,暴露出這個幾乎從不曾存在過的「臺灣國」的脆弱源起。想當年,美國政府與軍方領袖認為國民黨既無能且腐敗,因此他們對於要不要讓國民黨取得臺灣島控制權一事的態度非常矛盾。此外,當時國際背景又讓臺灣問題變得更複雜。以英國官方為例,他們不認為臺灣應該立刻歸還中國,因為他們認為臺灣還處於託管狀態,只有在與日方簽訂和約後才能讓臺灣完全地、合法地交由中國統治。英國跟美國一樣,都覺得開羅宣言是一個「意向聲明」,但不是一個移交臺灣的「法律時刻」。陳翠蓮進一步引導讀者去看臺灣獨立運動至今猶未成功的歷史詳情,以及國民黨對此的反應;這件事極高程度塑造了蔣介石與其子蔣經國的政權,直到一九八七年解嚴為止。臺灣知名法律史學家王泰升言簡意賅表示,不管中華民國有多少革命性的政策、多少反攻大陸的計畫,它都無法輕易擺脫這片土地的歷史。王泰升寫道:「臺灣本地人花了將近五十年(一九四五到一九九二年)才從日本人遺留的政治框架裡脫離出來。」
殖民史vs.帝國史
這樣的二元性並不只存在於東亞各個前殖民地。數年前,阿爾及利亞作家達烏德寫下《默爾索案調查》這本小說,作為他對卡謬的名著《異鄉人》的回應,也揭露出我們是怎樣常被殖民史的「一面之詞」本質所蔽。《異鄉人》寫於一九四二年,卡謬在書中探索存在的無意義。除開法國,大部分在美國或英國受教育的學生在學校八成早晚都會讀到這本書;不幸的是,學校一般將這本書列為文學名著,但卻將它擺在歷史真空裡交給學生閱讀。除非學生另受指導,否則幾乎不會知道書中故事是如何反映出殖民偏見與帝國歷史。主人翁默爾索是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也就是歐陸來的白人移民),阿爾及利亞在一九六二年以前都正式屬於法國。故事情節曲折,只是這位法國主角最後殺了一名阿爾及利亞人,卻未受多少良心譴責。不過,我們對於被殺的阿爾及利亞人所知甚少,他連名字都沒有──他從頭到尾都不是情節裡的重要因素,只被用來象徵主角對人生的疏離。達烏德的反殖民版本是透過這位阿爾及利亞無名死者的弟弟,來檢驗《異鄉人》沒有寫出來的背景殖民故事。達烏德的目的是要探討卡謬故事中隱藏的部分,也就是殖民歷史的部分;他終究給了被害死者一個名字。這位阿爾及利亞作家的著作揭開了「重述帝國歷史」背後的政治問題,但他也表示自己必須使用征服者的語言來講故事。作者達烏德在小說開頭提出抱怨,說那個殺人犯(《異鄉人》主人翁)變得很出名,部分原因就是他能用自己的語言(法語)寫作。法語雖是阿爾及利亞官方語言,但當地主要人口與社會底層人民都說阿拉伯語。所以,達烏德告知我們,他要「代替那位死者來開口,這樣我才能為他續上他未盡的話語」。達烏德還寫道:「我要從殖民者留下的舊屋拆走石頭,一塊一塊拿,蓋我自己的屋,我自己的語言。」在他筆下的後殖民語言地景裡,這個國家「處處散落著再不屬於任何人的字句。你看見它們,在老鋪子的門面,在發黃的書頁、人的臉上,或是被去殖民化所製造的奇怪混合語言給變了樣」。
兩部文學作品鋪陳出一場殺人案與其背景故事,反映出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的歷史定位;如果我們從差不多的角度來看,那臺灣歷史也能被視為類似的鬥爭,對象是一個專制政權,它自外而來統治臺灣,用不同的語言(中國普通話相對於臺灣話或日語)將自身歷史版本強加給臺灣人民,並給過去賦予不同重點。臺灣人直到近年都像達烏德一樣,缺乏細說自身歷史認知、細說這些認知怎樣反映自身價值觀與情感的空間。情況正在改變,但如果放在全球史或甚至區域史裡,我們必須承認臺灣史通常被當作一個個別主題,很少被放進近代東亞史成為核心要素。讀者會看到,我雖然努力寫出臺灣在戰後這段正義不彰的故事裡所扮演角色的關鍵部分,但最後我大概還是寫得不夠。或許我可以拿出老生常談的辯護詞,說如果我把更多心力放到臺灣這裡,我這本書會「寫不完」;但可能很多人仍舊覺得這話只是藉口罷了。說到底,這也是為了避免把太多東西放在一起同時講,但臺灣的例子常在這種情況下被遺忘在歷史的漏洞裡(lost in the holes of history),就像吳濁流所寫的那樣。
從等式的兩端來思考歷史,一邊是帝國,另一邊是被殖民者;在這脈絡下,戰後東亞對日本軍人的戰罪審判也必須從多個角度加以審視。這裡我們面對的是比前述文學創作更引人深思的戲劇化情節,是一場各方爭奪歷史故事主講權的更大比賽,「追究正義」只是其下的一部分而已。這是敗者的歷史──是達烏德筆下殖民主義的敗者,是日本這個軍事與帝國的敗者,抑或是中國這個慘勝的一方。然而,因為這裡是東亞,所以又包括了夾在勝者與敗者之間第三者的故事──也就是發生在臺灣與朝鮮的事。我以本書提供讀者觀覽中日關係史的前排座位,從長時段看勝利者與敗戰者,以及夾在中間第三者敘事所產生的作用。這故事揭示三個層次的真相,一是帝國造成的影響,二是戰爭結束後軍方與市民社會的互動,最後則呈現帝國宣傳的影響力在勝利或敗戰後未必徹底化為雲煙。
《不正義的地理學》以我在中國河北省北疃村所做的一些訪問開頭,但我其實也能用臺灣霧社事件的悲劇做為開場白,畢竟這兩個地點都發生日本皇軍用化學武器攻擊平民的情況──霧社在一九三○年秋末,北疃則在一九四二年春。這兩個事件過後,日軍都否認當時有直接使用化學武器。在臺灣,日本皇軍在霧社屠殺日帝國臣民,小規模作戰從一九三○年十月底延伸到十一月初,期間並以空投的「軍武化毒氣」助威。臺灣原住民在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對日本軍人發動攻擊,在一場學校運動會上恣意殺戮,導致一百三十幾名日本人死亡;日本因此展開反擊。臺灣的中心性、日帝國的臺灣臣民,這兩方已經成為帝國的對話者,在日本人未能移民的地方代表日本。依據白根晴治的觀點,臺灣是日本練習帝國行政與統治的場所,開啟日本向東南亞拓展帝國的通道,因此臺灣最終變得對日本很重要。更何況,「臺灣是日本在亞洲太平洋戰爭中奮戰南進的樞紐門戶」。但臺灣還有另一點也同樣值得重視,那就是在二次大戰期間擔任日本帝國境內運輸盟軍戰俘的主要節點。
正如我在本書開頭所述,北疃小村也是像這樣發現自己原來有這種重要性。當日本更進一步擴大與西方同盟國的戰爭,北疃就被視為大華北地理的縮影。日方預定以該地區為防禦材料生產中心,於是日軍高層認為必須平定當地動亂,以保障物資、食物與人力的生產能在對西方的戰爭中有效開展。
臺灣與正義
在戰後東亞的複雜地景裡,以針對日本戰罪追究正義一事而論,臺灣占據一個獨特但常被忽略的地位。二次大戰結束時,這座島嶼既經歷敗戰也經歷勝利,那麼想當然耳,這種矛盾情況會讓當地人與統治者皆無所適從。臺灣人是日本這個昨日帝國的一部分嗎?還是回歸到某種中國政權的掌控下?他們可否同時擁有這兩重身分?放在東亞這個較宏觀的地理區域下,若要理解臺灣在戰後正義課題裡所扮演的角色,則前述問題正是核心。
中國國民黨取得臺灣是開羅宣言的協商結果,並在日本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投降後立刻付諸實踐,但它隨即面對一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一邊穩定自身內部、打贏大陸的國共內戰、鎮壓臺灣亂事,並同時向日本人追究正義。為了符合國際要求,國民黨必須接下這個多面向的挑戰,但此時的國民黨卻也正逐漸喪失日本戰敗所賦予中華民國的國際威權。冷戰的發展使事情更加扭曲,臺灣被捧成自由民主國家的一員,但臺灣的工業並未因此得到國際幫助強化,臺灣本身也進不了戰後強權殿堂。反過來,中華民國曾經的敵人日本卻成為西方最主要的關注與支持對象。
這條尋求合法性的不懈之路,代表臺灣戰後地位的悲劇性──同盟國在開羅向臺灣居民許諾一種未來,但戰後東亞秩序的現實又加諸他們另一種全然不同的未來。這座島嶼面對著最基本的定義問題,因為它並沒有進行去殖民化的過程。臺灣是在戰後從日本手中被拿走,由一個從未統治過臺灣的國民黨政權來「光復」。這種獨一無二的處境使我們必須發明新詞彙,以便適當描述像臺灣這種前日本殖民地所發生的事情。根基不穩的國民黨政權在此建立法治,然後拋棄法治,在「白色恐怖」的數十年間粗率執行判決、囚禁與死刑。我們選用來區辨國內暴政與國際暴行的語詞,以及我們理解後殖民、再殖民或是其他全新政治控制型態的方式,會顯示出更深刻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怎樣創造出自己對過去的敘事。
自從臺灣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後,特別是在實施自由公開選舉、更進一步拆解國民黨治下的專制國家之後,中華民國人民將政治動力投注在發掘中國國民黨治臺前四十年中不為人知的暴行與玩弄法治的行為。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人民裡的某些部分會更積極去闡明這段國民黨惡政歷史,而比較不想調查更早之前日本殖民與戰爭時期的憾事。對當代臺灣人來說,蔣介石與蔣經國搞出來的白色恐怖更牽動他們的日常生活,也更與他們自身和家人的經歷相關。此處我要再次強調,這不是臺灣人獨有的經驗,許多受過類似苦難的社會也是這樣自問:當他們曾經尊崇的領袖被揭開政治暴君的真面目,他們可還有一條往前的路?知名蘇維埃小說家格羅斯曼將納粹戰罪編年立史,但他的作品卻在蘇聯被禁,直到戈巴契夫的經濟改革時期為止;格羅斯曼曾發出疑問,問我們是否真有可能「既譴責加害者罪行,又同情他們身為人的缺陷」?
今天居住在首都臺北的很多居民並不知道,或者也不會在意,那座殖民時期被日本人所用(然後又被國民黨接管)監禁反政府政治犯的舊臺北監獄。戰後的戰罪審判也在該處舉行──就在臺北市中心。這座監獄因都市發展被拆除,原址蓋起高聳的中華電信辦公大樓,只剩下小小的碑文指出當年監獄圍牆遺跡所在。話說回來,現在關注國民黨濫刑之下在綠島所建的巨大政治犯監獄的民眾還比較多一些。這個歷史記憶的轉變反映出一個較廣泛的模式,呈現臺灣人如何在創傷與正義的多重層次裡掙扎奮鬥。
在戰後正義與和解的複雜性裡,當代臺灣是個獨特的研究案例。臺北與北京之間不尋常的歷史關係,導致臺灣並不是一個國家。然而,它卻以民主方式選舉自己的國家政府,擁有主權武力,印發自己的貨幣;臺灣護照的免簽證國家數量還超過其他不少國家。由於日本帝國當初那樣結束,再加上緊接著中國統治下的政治分裂,使得臺灣在任何國際組織裡都沒有代表。但臺灣的工業,特別是現在的半導體與其他珍稀商品,都證明臺灣在國際政治裡隱隱具備的份量。
本書所檢視的課題之一,是臺灣經驗如何揭露傳統「正義與和解」敘事在戰後東亞的受限所在。這座島嶼的故事告訴我們:這樣一個複雜的時刻,它不可以,也不應該用「敗戰」與「戰後」這種粗糙詞彙給輕易地歸類掉。如果能理解臺灣的獨特處境,我們就能更明白為什麼帝國控制的終結是戰後東亞誕生的必要前提,以及這樣的轉變導致什麼必然的後果。
當我們探索東亞全境的非正義地理,臺灣的例子就是個提醒,讓我們警覺正義與和解的變量從來就不是勝者與敗者這麼簡單。這其實是一場複雜的,關於認同、主權與歷史記憶的協商,直至今日仍在塑造區域政治。這裡可以用我的經驗舉例說明,我在二○一八年八月與臺灣著名小說家吳明益談話,當時吳明益是為宣傳新書《單車失竊記》而巡迴各地來到倫敦。這是一本引人入勝的小說,貫通臺灣的殖民時期與現代,且還附有吳明益親手繪製的精美插圖。作者的才華涵蓋太多領域,包含植物學與歷史;我因此開玩笑地問他說,難道他接下來的作品是要寫交響曲嗎!在新書發表會上,我向吳明益提問,問他覺得當代臺灣與中國文學是否有差異?是什麼差異?說到底,他用的是中文寫作,但也要知道臺灣教育直到晚近都在強調傳統的寫作元素,因而導致臺灣與大陸的文字風格和詞彙出現分歧。吳明益的回答是:雖然他小時候在臺灣長大,從沒去過大陸,但他學過很多與中國大陸有關的知識,熟知中國地理,包括他沒有看過且可能永遠不會去看的山川名稱。對比來說,他對自己住的地方,也就是臺灣的歷史,幾乎一無所知。吳明益並不是老一輩的人;直到近年,臺灣人都處於對自己這座島嶼歷史缺乏認知的狀態(地理則還是知道一些),很多人不認為自己是日本殖民主義的後代。這種情況在最近二十五年來有顯著改變,不僅有新的學術研究以臺灣自身過往為對象,將它與中國大陸和日本歷史區分開來,還有新設立的機構,如各種轉型正義組織,來協助平反舊日政治與社會冤屈。
一九八九年夏,身為美國國務院官員與蘭德智庫研究員的福山宣告人類已經抵達歷史終點,意即西方自由主義理想已經消滅所有敵對意識形態。這項宣言預言未來的準確程度並不如福山所料,但至少當年他所謂冷戰結束、自由民主大勝的觀點可是轟動一時。就在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後,才過幾個月,柏林圍牆這座橫亙在人類與世界和平之間、看似堅不可摧的障礙就被推倒。同一年,日本裕仁天皇過世;裕仁是惡棍,是聖人,是被廢黜的神,他在許多方面都象徵著日本戰爭時期的終結。然而,距離柏林數千公里以外,北緯三十八度線的非武裝區仍將朝鮮半島分割為南北。歷史在歐洲似乎抵達終點,但在遠東也是如此嗎?四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