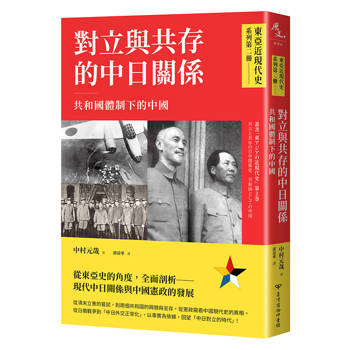第四節 革命再起──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革命
北京政府的苦鬥
從一九一○年代末到一九二○年代後半,中國國內政局分裂為兩個中央政府,一個是北京政府,另一個是廣東政府。就像聯省自治所象徵的那樣,制度的走向在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間搖擺不定。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鬥爭竟朝著武力衝突的方向發展,這種情形自然阻礙了社會經濟的活動,同時也迫使北京政府的財政逐漸走向崩潰。
北京政府在經歷過直系與皖系對立、直系與奉系對立後,黎元洪重回大總統的位子,一九二二年8月,再度召開舊國會,至此,基於舊約法的法統被恢復了。再啟的國會宣布「應該體認制憲工作是當前唯一的目標」(李強選編《北洋時期國會會議記錄彙編》第十三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一○年),展現了讓憲政回到軌道的企圖心。重視權力分立與自由保障,後來給中國憲政史發展帶來影響的王寵惠,於此時受命組閣,並欲落實胡適等人「憲政政府、公開政府、計面性政府」的政治信條。結果,廣東政府以維護舊約法為目標的行動陷入僵局,孫文的南方勢力於是再次走向革命。
而北京政府重建憲政的工作,也一再遭受打擊,重建憲政的工作可以說是困難重重。因為北京政府想以《天壇憲草》為基礎,再度展開制憲的行動,但是原本就有很多人對《天壇憲草》感到不滿,所以對北京政府此次制定憲法的行動採取抵制的態度。於是,北京政府不得不強行召開憲法會議。然而這種不顧外界看法,一意孤行的作為,反而擴大了社會對國會制定憲法的不信任感。
憲政的夭折
北京政府在苦苦尋求重建憲政之時,制憲出現了新的進展。一九二三年10月,曹錕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基礎,接受美國的支援,以大筆的金錢賄賂國會的議員,就任大總統,並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為了區別一九四六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這時制定的憲法在此稱為《曹錕憲法》──,試圖建立新的法統。
然而,賄選的行徑妨礙了憲政文化的確立,對後世有著不良的影響,所以《曹錕憲法》在當時便無法確保合法的法統地位。因此,在沒有合法的法統之下制定的《曹錕憲法》,即使將國會定位為最高的權力機關,以此來彰顯民主性,仍然受到嚴厲的批評。
不過,《曹錕憲法》並非完全没有其歷史性的意義。《曹錕憲法》的劃時代意義在於承認了條文中沒有明記的「其他」的自由和權利,即所謂的剩餘自由與權利。《曹錕憲法》沒有直接保障自由和權利(直接保障主義),而是像《大日本帝國憲法》一樣,保留了通過法律加以限制的其他自由與權利(間接保障主義),在中國憲法史上首次承認了剩餘自由和權利的存在,儘可能地維護了人權。人們經常誤解,以為憲法條款在北京政府時期退步了,其實問題出在制憲權力的不穩定。
進入一九二○年代後,人們對擁有制憲權的國會越發感到不信任,因此,由國民為全體來制定憲法的思潮高漲起來。一九二二年8月,以張君勱為中心,由省議會、商會、律師和媒體等人民團體組成的國是會議,制定了兩份憲法草案。隨後,在賄賂選舉徹底破壞了人們對國會的信任後,通過中間團體實現主權在民的氣勢更加高漲。孫文等人也在一九二四年的年底,展開了以職能代表制為基礎的國民會議運動。
就這樣,中華民國的法統一直沒有被恢復。而造成這種情形的決定性原因,在於一九二四年直系、皖系、奉系的再度對立,及包括溥儀在內的清室被逐出紫禁城。這次的北京政變不僅讓曹錕下台,原本民國對清朝皇室的禮遇,也被單方面地修改、廢除,讓已經變得貧困化的滿人社區走向崩潰,也推翻了作為民國起點的辛亥革命時所達成的協議事項。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國會制度本身也消失了。也就是說,舊約法的存在根據完全不見了,民國的合法法統地位,可以說是名實皆不存了。一九二五年2月召開的善後會議,是北京政府對重建憲政所做的最後努力,但由於憲法制定權還是由政府掌握,仍不足以使共和國體制的民國復活。該會議於同年4月解散。
從重建憲政到革命再起
此後,北京政府沒有進行任何重大的重建憲政的嘗試,因為無論在外交上還是在財政上,北京政府都已經無能為力了。
雖然說北京政府是構成華盛頓體系的成員,卻不一定能在這個體系內獲得好處。一九二五年10月,在擔心對華貿易有負面影響的日本的斡旋下,特別關稅會議通過了恢復關稅自主權的原則,並宣布將在幾年後廢除英國和美國要求的「釐金」,也就是地方政府徵收的「通行費」。然而,北京政府未能實施有效的財政重建措施,最終導至破產。相反的,國民黨的南方革命力量取代北京政府上台執政。一九二五年孫文逝世後,孫文的繼任者蔣介石成為領導的中心,國民黨於一九二六年發動了國民革命,以推翻北京政府、統一全國為目標,展開新的北伐戰爭。
另外,孫文的「大亞細亞主義」演講活動,也在此時展開了,這是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一幕。一九二四年11月,孫文以「大亞細亞主義」為題,在神戶高等女校舉辦的演講。演講的內容在直接面對當時中國境內日漸高漲的反日民族主義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向日本傳達了質問的信息。那句著名的提問「日本將成為西方霸權的看門狗?還是會成為東方王道主義的大本營?」,雖然是演講後補充上去的內容,但需要重視的是,他的演講也在呼籲,在中國重建共和的民族國家過程中,中日應該要合作。在中國,因為區別西方、東方與本國的世界觀並不強烈,要產生像日本那樣的亞洲主義的可能性一開始就不大,但孫文仍然敢貼近日本的亞洲主義,試圖對日本寄予一線希望。
筆者想把這個時期的中國政治過程中,認為對中國憲政史有重要意義的事實,歸納為以下五點。
第一點,在國民黨與共產黨這兩股革命力量的崛起的這個時期裡,出現了認為重燃革命之火優先於重建憲政的思潮。
事實上,蘇聯並沒有立即將所有特權交還給中國。然而,由於不公開細節的事實,有助於幫助蘇聯獨享在中國得到好的印象,也能幫助國民黨和共產黨重新崛起,成為新的革命力量。當然,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也各自參與了在中國的活動。因此,國民黨的孫文制定了「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政策,並在一九二四年1月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改變了恢復《臨時約法》和舊國會的既有目標,開始主張推翻帝國主義的勢力、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現三民主義。此外,國民黨允許共產黨員可以同時持有國民黨黨籍──後來這被稱為第一次國共合作──,並受到認為「少數人的暴力革命在所難免的列寧等人的社會主義路線」的影響,試圖建立政治和軍事一體化,以宣傳和動員的方式,來實踐革命的黨組織。簡而言之,國民黨也與共產黨一樣了,要採取民主集中制來作為黨的組織原則。
第二點,因為革命勢力的抬頭,人民日益意識到國家的自由和平等比個人的自由和平等更重要。
孫文透過召開跨黨派的國民會議,以求恢復民國的法統,這就是所謂的國民會議運動。然而,一九二五年3月,孫文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遺言,在北京逝世了。為了實現中國的自由與平等,他視廢除不平等條約為主要課題,晚年對給中國平等待遇的蘇聯寄以厚望,一再強調民族、國家的自由與平等,而非個人的自由與平等。他的這些言行是國家權利優先於個人權利的典型例子。
第三點,自一九二○年代中葉以來,與憲政應有的狀態及其確立息息相關目的民族主義風潮高漲。
中國各地的工人運動開始活躍起來,在上海,以大日本紡績為首的日本在華紡織廠,頻頻發生工人罷工的事件。一九二五年5月30日,以英國為中心的租界警察,對遊行示威的人群開槍,射殺了工人對此事件感到不滿的人們紛紛在各地組織罷工與遊行示威的活動,結果除了反日民族主義的運動外,也發展出了反英與反帝國主義的工人運動。這個被稱為五三○的運動,後來也延燒到英國統治下的廣州和香港,引發了激烈的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國民黨與共產黨為了支持這些運動,包括經濟援助在內,盡一切可能的手段動員和組織群眾,但工人運動的爆發,也受到在社會自發性和義憤填膺的心理等一系列複雜因素的推動。而承載著這樣社會運動的,正是工人、傭兵和流民匪賊等遊走於社會的流動性剩餘人口。來自這樣的社會運動而被發揚起來的民族主義,為推翻帝國主義勢力、廢除不平等條約,創造了國民革命的了條件。
以上三點,都是與實行憲政背道而馳的革命潮流。然而,即使在這樣的革命氛圍中,仍然潛藏著對中國憲政史後續發展至關重要的歷史事實。以下是第四點和第五點。
革命中的憲政
第四點,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如第一點所說的,都具有革命政黨的共通性,但它們其實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決定性的差異。
正如一九二四年4月國民黨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提出,在五權憲法的基礎上,中華民國的國家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司法、監察、人事(又稱「考試權」)等五項,然後依軍政、訓政、憲政的順序重建民國。所謂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就是首先以軍事的力量統一國家軍政,再進到國民黨推動建設民族國家的訓政,然後以憲法為基礎,實行主權在民的憲政。換言之,國民黨與共產黨不同,國民黨預先劃定了自己作為革命黨的時期。
孫文死後,國民黨內部出現意識形態的對立,一九二五年7月,國民黨左派的汪精衛(汪兆銘)成為廣州國民政府主席,但是作為日本通的國民黨右派元老戴季陶,提出國民黨不能接受階級鬥爭的主張。自此以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距離便擴大了。
第五點,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鴻溝越來越深,其內部也出現了分裂的情況,開始出現批評獨裁的聲浪。
以陳獨秀為中心組織起來的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召開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但是擔任第一屆委員長的陳獨秀後來因為與列夫.托洛斯基(Lev Davidovich Trotskiy)有共鳴,對共產國際與共產黨中央提出批評,結果在一九二九年時,陳獨秀被剝奪共產黨黨籍。陳獨秀發現蘇聯社會主義的非民主性體質,在中日戰爭期間寫下了「致西流」的信,進一步批評歐美民主主義的傳統。他所主張的無產階級民主,絕非擁護共產黨獨裁的主張(《陳獨秀選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九年)。
又,在共產黨創黨時期的成員之中,信仰馬克斯主義,對共產黨有大貢獻的李大釗,在一九二七年被奉系的張作霖殺害;曾經留學日本,在中日戰爭時期協調中日關係的周佛海,則被視為漢奸,在戰後死於獄中。如此看來,參加中共一大的十三個人中,除了陳公博之外的十二人中,只有毛澤東、董必武兩個人能夠保持較高的權勢,平安地迎接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南京國民政府統一中國
藉由國民革命,蔣介石鞏固了自己在國民黨內部的權力基礎。蔣介石曾任廣東的黃埔軍官學校校長,他以自己在日本的經驗,整頓軍隊,讓軍隊有了規律。國民革命軍後來成為中華民國國軍的主力,而支持蔣介石的,正是黃埔軍官學校的畢業生們。
國民革命具有反帝國主義的性格,也帶著反軍閥的性格,所以能夠博得來自社會的支持。但是,隨著國民革命軍的發展,汪精衛與孫文之子孫科擔心蔣介石的權力基礎擴大,於是把國民政府的所在地遷移到武漢。
這個武漢國民政府利用民眾與英國當局的衝突,以實力收回英國在漢口(武漢)與九江的租界。被收回租界的英國當然心有不甘,於是請求日本派兵干涉,但遭到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為由,拒絕派兵。這樣收回租界的成果,與擁蔣派或反蔣派無關,在外人的眼光中,那是國民革命的成果,而這樣的成果也激勵了在華的朝鮮人、越南人、印度人、緬甸和台灣的獨立運動家們。
之後,國民革命軍在這股反帝國主義運動推波助瀾下,陸續收回有著中國最大租界的上海, 和有諸多領事館與教會的南京。當蔣介石在上海鎮壓親共產黨的組織,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後,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的武漢國民政府,在不久後也和南京國民政府合流了。
就這樣,國民革命推翻了北京政府,在企圖建立一個新的全國政府的背景下,蔣介石的北伐順利往前推進。但是,日本的田中義一內閣不樂意見到中國有新的統一政權,所以三度出兵山東,想要藉此阻擾北伐。不過,由於蔣介石得到廣西的李宗仁與白崇禧,及山西的閻錫山等人支持,一九二八年6月,國民革命軍終於接收了北京政府,被日本關東軍炸死的張作霖之子張學良,也在同年12月帶領東北追隨蔣介石,至此,南京國民政府統一了全國,並且定南京為中華民國的首都。此時由於首都定在南京,北京便被改名為北平,而直隸省也改稱河北省,作為國家象徵的國旗,也由原來的五色旗,改為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加上代表三民主義理念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但是,南京國民政府卻沒能解决如何恢復中華民國的共和國法統這一重大課題。而且,為了恢復憲政,必須消除北京政府時期憲政失控的因素。國民黨方面的法學家們認識到,在警惕反立憲主義的社會主義憲政滲透的同時,也必須加速重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以控制軍權及確立穩定的中央財政。(張志本,《憲法論》,上海法學編譯社,一九三三年)。
然而,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入侵、共產黨作為國內反對力量不斷擴張的情況下,要怎麼樣做才能夠以上述的方式重建憲政呢?一九三○年代前半的民國,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迎來了讓共和國復甦的時代,也就是說迎來了作為共和國的民國抗戰時代。
北京政府的苦鬥
從一九一○年代末到一九二○年代後半,中國國內政局分裂為兩個中央政府,一個是北京政府,另一個是廣東政府。就像聯省自治所象徵的那樣,制度的走向在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間搖擺不定。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鬥爭竟朝著武力衝突的方向發展,這種情形自然阻礙了社會經濟的活動,同時也迫使北京政府的財政逐漸走向崩潰。
北京政府在經歷過直系與皖系對立、直系與奉系對立後,黎元洪重回大總統的位子,一九二二年8月,再度召開舊國會,至此,基於舊約法的法統被恢復了。再啟的國會宣布「應該體認制憲工作是當前唯一的目標」(李強選編《北洋時期國會會議記錄彙編》第十三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一○年),展現了讓憲政回到軌道的企圖心。重視權力分立與自由保障,後來給中國憲政史發展帶來影響的王寵惠,於此時受命組閣,並欲落實胡適等人「憲政政府、公開政府、計面性政府」的政治信條。結果,廣東政府以維護舊約法為目標的行動陷入僵局,孫文的南方勢力於是再次走向革命。
而北京政府重建憲政的工作,也一再遭受打擊,重建憲政的工作可以說是困難重重。因為北京政府想以《天壇憲草》為基礎,再度展開制憲的行動,但是原本就有很多人對《天壇憲草》感到不滿,所以對北京政府此次制定憲法的行動採取抵制的態度。於是,北京政府不得不強行召開憲法會議。然而這種不顧外界看法,一意孤行的作為,反而擴大了社會對國會制定憲法的不信任感。
憲政的夭折
北京政府在苦苦尋求重建憲政之時,制憲出現了新的進展。一九二三年10月,曹錕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基礎,接受美國的支援,以大筆的金錢賄賂國會的議員,就任大總統,並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為了區別一九四六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這時制定的憲法在此稱為《曹錕憲法》──,試圖建立新的法統。
然而,賄選的行徑妨礙了憲政文化的確立,對後世有著不良的影響,所以《曹錕憲法》在當時便無法確保合法的法統地位。因此,在沒有合法的法統之下制定的《曹錕憲法》,即使將國會定位為最高的權力機關,以此來彰顯民主性,仍然受到嚴厲的批評。
不過,《曹錕憲法》並非完全没有其歷史性的意義。《曹錕憲法》的劃時代意義在於承認了條文中沒有明記的「其他」的自由和權利,即所謂的剩餘自由與權利。《曹錕憲法》沒有直接保障自由和權利(直接保障主義),而是像《大日本帝國憲法》一樣,保留了通過法律加以限制的其他自由與權利(間接保障主義),在中國憲法史上首次承認了剩餘自由和權利的存在,儘可能地維護了人權。人們經常誤解,以為憲法條款在北京政府時期退步了,其實問題出在制憲權力的不穩定。
進入一九二○年代後,人們對擁有制憲權的國會越發感到不信任,因此,由國民為全體來制定憲法的思潮高漲起來。一九二二年8月,以張君勱為中心,由省議會、商會、律師和媒體等人民團體組成的國是會議,制定了兩份憲法草案。隨後,在賄賂選舉徹底破壞了人們對國會的信任後,通過中間團體實現主權在民的氣勢更加高漲。孫文等人也在一九二四年的年底,展開了以職能代表制為基礎的國民會議運動。
就這樣,中華民國的法統一直沒有被恢復。而造成這種情形的決定性原因,在於一九二四年直系、皖系、奉系的再度對立,及包括溥儀在內的清室被逐出紫禁城。這次的北京政變不僅讓曹錕下台,原本民國對清朝皇室的禮遇,也被單方面地修改、廢除,讓已經變得貧困化的滿人社區走向崩潰,也推翻了作為民國起點的辛亥革命時所達成的協議事項。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國會制度本身也消失了。也就是說,舊約法的存在根據完全不見了,民國的合法法統地位,可以說是名實皆不存了。一九二五年2月召開的善後會議,是北京政府對重建憲政所做的最後努力,但由於憲法制定權還是由政府掌握,仍不足以使共和國體制的民國復活。該會議於同年4月解散。
從重建憲政到革命再起
此後,北京政府沒有進行任何重大的重建憲政的嘗試,因為無論在外交上還是在財政上,北京政府都已經無能為力了。
雖然說北京政府是構成華盛頓體系的成員,卻不一定能在這個體系內獲得好處。一九二五年10月,在擔心對華貿易有負面影響的日本的斡旋下,特別關稅會議通過了恢復關稅自主權的原則,並宣布將在幾年後廢除英國和美國要求的「釐金」,也就是地方政府徵收的「通行費」。然而,北京政府未能實施有效的財政重建措施,最終導至破產。相反的,國民黨的南方革命力量取代北京政府上台執政。一九二五年孫文逝世後,孫文的繼任者蔣介石成為領導的中心,國民黨於一九二六年發動了國民革命,以推翻北京政府、統一全國為目標,展開新的北伐戰爭。
另外,孫文的「大亞細亞主義」演講活動,也在此時展開了,這是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一幕。一九二四年11月,孫文以「大亞細亞主義」為題,在神戶高等女校舉辦的演講。演講的內容在直接面對當時中國境內日漸高漲的反日民族主義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向日本傳達了質問的信息。那句著名的提問「日本將成為西方霸權的看門狗?還是會成為東方王道主義的大本營?」,雖然是演講後補充上去的內容,但需要重視的是,他的演講也在呼籲,在中國重建共和的民族國家過程中,中日應該要合作。在中國,因為區別西方、東方與本國的世界觀並不強烈,要產生像日本那樣的亞洲主義的可能性一開始就不大,但孫文仍然敢貼近日本的亞洲主義,試圖對日本寄予一線希望。
筆者想把這個時期的中國政治過程中,認為對中國憲政史有重要意義的事實,歸納為以下五點。
第一點,在國民黨與共產黨這兩股革命力量的崛起的這個時期裡,出現了認為重燃革命之火優先於重建憲政的思潮。
事實上,蘇聯並沒有立即將所有特權交還給中國。然而,由於不公開細節的事實,有助於幫助蘇聯獨享在中國得到好的印象,也能幫助國民黨和共產黨重新崛起,成為新的革命力量。當然,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也各自參與了在中國的活動。因此,國民黨的孫文制定了「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政策,並在一九二四年1月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改變了恢復《臨時約法》和舊國會的既有目標,開始主張推翻帝國主義的勢力、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現三民主義。此外,國民黨允許共產黨員可以同時持有國民黨黨籍──後來這被稱為第一次國共合作──,並受到認為「少數人的暴力革命在所難免的列寧等人的社會主義路線」的影響,試圖建立政治和軍事一體化,以宣傳和動員的方式,來實踐革命的黨組織。簡而言之,國民黨也與共產黨一樣了,要採取民主集中制來作為黨的組織原則。
第二點,因為革命勢力的抬頭,人民日益意識到國家的自由和平等比個人的自由和平等更重要。
孫文透過召開跨黨派的國民會議,以求恢復民國的法統,這就是所謂的國民會議運動。然而,一九二五年3月,孫文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遺言,在北京逝世了。為了實現中國的自由與平等,他視廢除不平等條約為主要課題,晚年對給中國平等待遇的蘇聯寄以厚望,一再強調民族、國家的自由與平等,而非個人的自由與平等。他的這些言行是國家權利優先於個人權利的典型例子。
第三點,自一九二○年代中葉以來,與憲政應有的狀態及其確立息息相關目的民族主義風潮高漲。
中國各地的工人運動開始活躍起來,在上海,以大日本紡績為首的日本在華紡織廠,頻頻發生工人罷工的事件。一九二五年5月30日,以英國為中心的租界警察,對遊行示威的人群開槍,射殺了工人對此事件感到不滿的人們紛紛在各地組織罷工與遊行示威的活動,結果除了反日民族主義的運動外,也發展出了反英與反帝國主義的工人運動。這個被稱為五三○的運動,後來也延燒到英國統治下的廣州和香港,引發了激烈的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國民黨與共產黨為了支持這些運動,包括經濟援助在內,盡一切可能的手段動員和組織群眾,但工人運動的爆發,也受到在社會自發性和義憤填膺的心理等一系列複雜因素的推動。而承載著這樣社會運動的,正是工人、傭兵和流民匪賊等遊走於社會的流動性剩餘人口。來自這樣的社會運動而被發揚起來的民族主義,為推翻帝國主義勢力、廢除不平等條約,創造了國民革命的了條件。
以上三點,都是與實行憲政背道而馳的革命潮流。然而,即使在這樣的革命氛圍中,仍然潛藏著對中國憲政史後續發展至關重要的歷史事實。以下是第四點和第五點。
革命中的憲政
第四點,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如第一點所說的,都具有革命政黨的共通性,但它們其實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決定性的差異。
正如一九二四年4月國民黨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提出,在五權憲法的基礎上,中華民國的國家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司法、監察、人事(又稱「考試權」)等五項,然後依軍政、訓政、憲政的順序重建民國。所謂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就是首先以軍事的力量統一國家軍政,再進到國民黨推動建設民族國家的訓政,然後以憲法為基礎,實行主權在民的憲政。換言之,國民黨與共產黨不同,國民黨預先劃定了自己作為革命黨的時期。
孫文死後,國民黨內部出現意識形態的對立,一九二五年7月,國民黨左派的汪精衛(汪兆銘)成為廣州國民政府主席,但是作為日本通的國民黨右派元老戴季陶,提出國民黨不能接受階級鬥爭的主張。自此以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距離便擴大了。
第五點,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鴻溝越來越深,其內部也出現了分裂的情況,開始出現批評獨裁的聲浪。
以陳獨秀為中心組織起來的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召開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但是擔任第一屆委員長的陳獨秀後來因為與列夫.托洛斯基(Lev Davidovich Trotskiy)有共鳴,對共產國際與共產黨中央提出批評,結果在一九二九年時,陳獨秀被剝奪共產黨黨籍。陳獨秀發現蘇聯社會主義的非民主性體質,在中日戰爭期間寫下了「致西流」的信,進一步批評歐美民主主義的傳統。他所主張的無產階級民主,絕非擁護共產黨獨裁的主張(《陳獨秀選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九年)。
又,在共產黨創黨時期的成員之中,信仰馬克斯主義,對共產黨有大貢獻的李大釗,在一九二七年被奉系的張作霖殺害;曾經留學日本,在中日戰爭時期協調中日關係的周佛海,則被視為漢奸,在戰後死於獄中。如此看來,參加中共一大的十三個人中,除了陳公博之外的十二人中,只有毛澤東、董必武兩個人能夠保持較高的權勢,平安地迎接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南京國民政府統一中國
藉由國民革命,蔣介石鞏固了自己在國民黨內部的權力基礎。蔣介石曾任廣東的黃埔軍官學校校長,他以自己在日本的經驗,整頓軍隊,讓軍隊有了規律。國民革命軍後來成為中華民國國軍的主力,而支持蔣介石的,正是黃埔軍官學校的畢業生們。
國民革命具有反帝國主義的性格,也帶著反軍閥的性格,所以能夠博得來自社會的支持。但是,隨著國民革命軍的發展,汪精衛與孫文之子孫科擔心蔣介石的權力基礎擴大,於是把國民政府的所在地遷移到武漢。
這個武漢國民政府利用民眾與英國當局的衝突,以實力收回英國在漢口(武漢)與九江的租界。被收回租界的英國當然心有不甘,於是請求日本派兵干涉,但遭到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為由,拒絕派兵。這樣收回租界的成果,與擁蔣派或反蔣派無關,在外人的眼光中,那是國民革命的成果,而這樣的成果也激勵了在華的朝鮮人、越南人、印度人、緬甸和台灣的獨立運動家們。
之後,國民革命軍在這股反帝國主義運動推波助瀾下,陸續收回有著中國最大租界的上海, 和有諸多領事館與教會的南京。當蔣介石在上海鎮壓親共產黨的組織,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後,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的武漢國民政府,在不久後也和南京國民政府合流了。
就這樣,國民革命推翻了北京政府,在企圖建立一個新的全國政府的背景下,蔣介石的北伐順利往前推進。但是,日本的田中義一內閣不樂意見到中國有新的統一政權,所以三度出兵山東,想要藉此阻擾北伐。不過,由於蔣介石得到廣西的李宗仁與白崇禧,及山西的閻錫山等人支持,一九二八年6月,國民革命軍終於接收了北京政府,被日本關東軍炸死的張作霖之子張學良,也在同年12月帶領東北追隨蔣介石,至此,南京國民政府統一了全國,並且定南京為中華民國的首都。此時由於首都定在南京,北京便被改名為北平,而直隸省也改稱河北省,作為國家象徵的國旗,也由原來的五色旗,改為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加上代表三民主義理念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但是,南京國民政府卻沒能解决如何恢復中華民國的共和國法統這一重大課題。而且,為了恢復憲政,必須消除北京政府時期憲政失控的因素。國民黨方面的法學家們認識到,在警惕反立憲主義的社會主義憲政滲透的同時,也必須加速重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以控制軍權及確立穩定的中央財政。(張志本,《憲法論》,上海法學編譯社,一九三三年)。
然而,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入侵、共產黨作為國內反對力量不斷擴張的情況下,要怎麼樣做才能夠以上述的方式重建憲政呢?一九三○年代前半的民國,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迎來了讓共和國復甦的時代,也就是說迎來了作為共和國的民國抗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