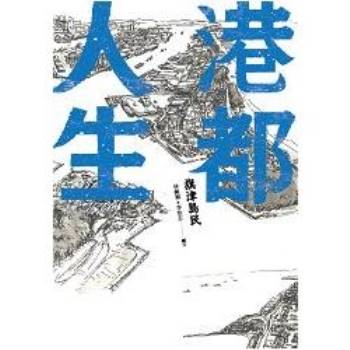3.掌中的經緯 莊碧飛
本來並不是討海的
一如往常,莊碧飛坐在門前編織漁具,他它熟稔地用爬滿皺紋的雙手,將尼龍線交叉出經緯。
莊碧飛是旗津著名的耆老,設計出許多耐用的網具。但他,本來並不是討海的。除了幼時父親在內港養殖石頭蚵外,他們在崩隙還有幾塊田園,種地瓜養豬維生。他的爺爺是日本時代的保正,在村裡有點名望,接受日本政府的指派,也受到特許,開了間雜貨店,販賣什貨等生活用品,他只消偶爾幫家裡顧店,其餘的時間就是上學唸書,生活過得不錯。
皇民化當時,全家改了日本姓「濱川」,莊碧飛說這是代表海邊的住民。他的長兄在二戰時擔任台籍日本陸軍志願兵,配有軍馬,在社里間受到敬重。美軍空襲時,每戶家庭在海岸邊挖掘防空壕避難,另一部分的人則疏開到鄉村。終戰後沒多久,他們已經得知,哥哥「濱川英雄」已經戰死在南洋,幾年後,輾轉多人,才由鄰居友人的手中接回他的指甲和頭髮。
戰後,大人們在港內抓魚。中洲漁港過去很大,沙地上能停放三、四十隻以上的竹筏,漁船並不多見,其中也有往返中國載運貨品的帆船。多數的漁民在外港牽罟,這種以地曳網作業是傳統的補魚方法,在臺灣西部沿海相當普遍,由於需要眾人合作,基本上多是具有一些經濟基礎的漁戶才能招工。莊碧飛記得,每當漁汛期,他的父親和兄長會站上竹筏上,由一個人撐向外海,另一個人將網撒出,環構成一個馬蹄狀的路徑,讓網沉至海中一些時間圍困漁群,灘上眾人腰間便勾著繩網,一齊向後拉即可收穫。莊碧飛至今仍忘不掉那時的景色:黃昏時,眾多的罟網在海上各自張開,錯落有致,加上江港歸帆,畫面美不勝收。他說,如果當時有攝影器材能記錄下來,那旗津一定是世界級的景點。
彼岸經緯
當了一年四個月的國民兵,莊碧飛才開始出海抓魚。當時兄弟還沒分開,三、四個一起賺食,有時候到台南、東港等處,一次數日或月餘。二、三十歲時後,他們也常跑到福建、汕頭等南方沿海作業,當時中國正歷經「大躍進」的時期,偶爾會見到公社專用的帆船,擠滿三、四十多個人。他記憶中裡對岸漁民的生活條件非常差,也不能靠近。
但有時候他們會從台灣帶一些舊衣,在海上遇見了個體漁民,就用塑膠袋包裹,會船時丟向他們的小船。
為了躲避颱風,莊碧飛和兄長也數次進出九龍。六○年代時,香港境內還沒有太多觀光客,港邊避風塘裡居住著在水上生活的蜑家漁民,岸上還有黑社會,搶劫頻繁,治安非常差,所以大約下午五、六點,路上的商店差不多都已經關門。莊碧飛說九龍與香港就像旗津和高雄一樣,港內是繁榮的市鎮,港外則是破落的漁村。
海上水路的經驗特別,越戰時,他們的船行經海南島附近,許多越南人從海上逃亡,他便親眼目睹難民用水缸和竹竿划滑到他們的船邊,其中一個人拿了軍用的指北針,問他們香港怎麼去,莊碧飛用手比了比方向,他們就趕路離開了。
此岸經緯
大概四、五十幾歲左右,莊碧飛結束了討海的生活,回到岸上。他和父親、哥哥開始作漁網販賣。
早期是以苧麻、棉線製作「苓仔」,但因為不耐鹽水,下水後需要曬網,使用壽命也僅有三年便需再製。,所以日治時期,即改成棉網,雖然較為耐水且耐用,不必次次曬網,但仍需要定期以一種類似番薯塊根的薯榔作染料,來增強拉力並延緩腐化。
他們向紗行批來棉絮,找來村裡的人工一起製做,這是在漁村裡極為普遍的技藝,多由女性負責,完成後便可賣到南部幾個漁港。戰後一段時間,才改成塑膠尼龍。
莊碧飛長年著一件棉質背心,深藍灰的西裝褲腰串著鑰匙,雖然現年已經八十三歲,但黝黑的薄皮膚下仍有寬厚的臂膀。他常坐在港邊自家的騎樓工作,椅子上放著竹製的梭子(編網針)、紡錘、網目尺、小刀、剪刀,和收納這些工具的油亮木盒。,莊碧飛坐在板凳上並著腳,默數著網目的尺寸,快速將繩結好手持漁網,或更費時的把線索撐開,穿過梭子,構成平整規律的交叉格狀,來加強護具的耐用性。
他走到住家隔壁的小儲藏間,解開鐵鎖瑣,推開刷成湖綠色的厚門,牆邊整齊不紊的擺放大小各異的手網,插在橘色、藍色的塑膠桶,一旁還堆放像壺狀漁簍的補蝦網具,莊碧飛用金屬增加幾層防脫設計,也是他的發明。
接著他莊碧飛又拿出一副寬大的手網,是專門用在每尾重達百斤的石斑大網。
其上的平口網圈,是以門前的鐵器折出來,這個設計可以讓網圈貼緊漁塭底層,魚群不至向弧形的兩邊逃脫;而扁狀木桿避免滑動,又減少手握的施力;上面的線繩接到網底的束口,因為在撈魚後,沉甸的重量不易傾倒,則可以控制開闔;網圍的尼龍繩更是鉤纏在不銹鋼網圈上的內側,沿線覆上剖開的塑膠管,防止作業時刮到壁岸及石塊而斷開。莊碧飛靠著多年的漁業知識與經驗,研究網距技術,改良繡法、網目,構法、耐水性和防刮等細節,許多養殖業者或海產店的攤商,都特別向他訂製作手持的撈網及容器護具,他也常受到政府及民間單位的表揚與關注。
黃昏時,莊碧飛坐在門口,隔一條水泥鋪成的馬路是中洲漁港,停靠的是玻璃纖維製的近海漁船。他說,過去叔叔將蚵殼傾倒在海岸,久而久之,囤出了這條路。偶爾,他會放下手邊的工具,規矩地收好,再沿著港邊這條小路,穿過漁民歇息的卡拉OK亭,回到旁邊紅磚造的祖厝看看。4.日曆紙上的旗津 魏祺峰
違建
魏祺峰的夾克和襯衫口袋,永遠放著鼓脹成饅頭狀的黑色皮夾,裡面收著一張張港務公司歲末聯歡的邀請名牌,還有幾張破爛變形、薄可透光的日曆紙。那是他反覆描繪的記憶,沒有間段地紀錄,隨時放在皮夾,數年累積。當他小心翼翼地攤開的日曆紙,那個用藍色原子筆來回塗寫的「東亞海運」字跡清晰可見。
「這裡都是違建。」魏祺峰步履緩緩,牽著腳踏車避開大街上的觀光客,沿著一條常走的小路徑,指著住家旁的兩側的屋厝說。也許新蓋的透天房對魏祺峰的記憶而言,都是違建。
西元一九二七年出生的魏祺峰,身體硬朗,鼻樑上掛著一副金邊寬大的舊式眼鏡,年邁的眼皮下垂,露出澄澈的雙眼。他獨居在旗津教會後方,一棟四十年左右的洗石子老屋,木門右上方有一塊板擦大小的木片,用石綠色填寫他的名字。屋內客廳的牆壁、頂端燈飾的圓形線板,白灰已經有好幾處剝落,後方廚房有石型磁磚砌成的洗手槽和廚具,雖然乾淨,但看得出來鮮少有客人。魏老從斗櫃裡拿出三合一咖啡,添加大量的砂糖沖泡。
記憶的圖像
二戰末期,美軍在台灣密集投彈的那兩年,高雄是受空襲次數最頻繁的城市。
魏祺峰在旗津的家被炸彈徹底地轟過,三合院出現一個偌大的窟窿,路也都被炸開,只有前方的教會沒倒。而魏老曾任職的「東亞海運株式會社」,則在他加入日本海軍志願兵訓練期間被炸毀,「當天正巧是會社的發薪日,同事當時都在現場。」魏祺峰因為受訓缺席,逃過一場浩劫,至今仍記憶猶存。
魏老喜歡畫圖,現在住的房子,是數十年前原址重建的三樓老屋。但他已經很少上二樓了。他改睡一樓的雅房,除了因為年邁退化的身子,另一個原因是在妻子過世後,他刻意保留的時間感。二樓幾乎維持原樣。
一樓通往二樓的牆上掛滿了許多書法字,是寫給自己勤勉的詩句,還有幾幅極為出色的水彩畫,雖然透明壓克板已經泛黃,仍可看出當時慎重地裱框。其中一幅神情優雅、姿態端莊的女人,是他為妻子所畫的肖像,用不透明水彩染上淡色,頭後方還有一輪像聖母般的暈黃光輝,在幾幅牆上的作品裡極為突出。
有一天,他用鑰匙打開深鎖的房門,玻璃窗掩著舊色的簾布,透進一點光照,細塵在空中亮晶晶地發閃,彷彿打開他的記憶。進到他們的房間,靠床的牆上,同樣擺了數件作品和照片,一件小尺幅的油彩自畫像,用古典式雕花的木框裱背,穩重的黃褐色調,表現了他青年時的自信與自持。
魏祺峰在床邊坐下來畫圖。
他說,阿祖從福建渡海,在這裡住了好幾代。父親在一八七四年出生時,一家子從苓仔寮搬到旗後,砲台剛因牡丹社事件的影響,由清政府修建好。他們靠「牽罟」、「篙排仔」及養貝維生。據說那時旗後還有一個清兵的哨營,但清朝統治重心不在台灣,所以治安狀況與衛生條件都非常差。他描述父親口中的旗後聚落。閩式漁村已是打狗當時最繁華的市街了,酒樓、洋行、領事、醫館和禮拜堂,都成為他原子筆下描繪的場景。
魏祺峰平日獨居,但這裡曾是全家族的回憶。他是父親第三個續絃的妻子所生,前兩任太太因故過世,所以他和父親的年紀相差懸殊。說著,魏祺峰翻開一頁旗後平和公學校卒業紀念冊,原版早就散失,現在彩色翻印是同窗借給他的。他指著裡面一個「糞萁」的名字,以原子筆重重劃掉,手寫改成「祺峰」。他沒有問過爸媽為什麼,但過去一些農家為了避災,常將小孩的名字起得粗魯。
他想起了一個早夭的妹妹,有一次犯了腸胃病,讓母親背到鹽埕給楊金虎醫生看診,父親還體貼地在媽祖廟前的市場買了昂貴的日本蜜桃,要慰勞可憐的小女兒,但她吃了幾口,晚上腹瀉脫水後便往生了。逃兵
魏祺峰的母親是基督徒,他們住在教會旁,小時候他在長老教會巴克禮牧師在旗津為高雄所創的第一所幼稚園「愛兒園」就讀,所以他會用羅馬字寫台語文。後來當他自公學校畢業,應徵上高雄港站前的「東亞海運株式會社」,當時他們停靠在高雄港的船舶就多達五、六十艘,是一座極具規模的海運公司。魏祺峰擔任船舶聯絡員,白天負責遞送文件,下午回到旗津,在國民學校附設青年學校進修。一九四三年,大東亞戰爭正熾,他加入警防團,在空襲時協助警消救護受傷人員與善後,戰爭末期,又成為台籍日本海軍志願兵。
「我是被迫的。」魏祺峰說,當時他曾眼睜睜地見證日本警察以長棍毆打台灣人,一個耳光下去,口中罵著「清國奴!清國奴!」年少血氣方剛,他有股衝動,想衝進警察署裡回擊,同歸於盡就罷了,但畢竟沒有。一九四五年,青年學校的教官強制魏祺峰等年輕人全部報考志願兵。體檢後他被選上,所以他乘著空襲的契機,假借要安頓母親疏開而逃兵,卻仍被發現,抓回從軍。
「臭油抽!」魏老憶起仍難掩憤慨,用當時罵日本人的髒話嚷著。
然而,對魏祺峰來說,加入戰爭卻也是萬幸,他逃過美軍空襲,也不像許多前期的台籍日本兵從高雄港出發,往南洋赴死。
透光的日曆紙
魏老騎著腳踏車在旗後行動。
每逢假日,此處人潮總是川流不息。他常在曾當過廟公的媽祖廟前和日本觀光客攀談,或在福壽宮的老人亭下唱歌。但或許,這座島於他而言,已經不再是過去的模樣,所以,魏老以筆用力記住每件要事。退休後,他在日曆紙背面開始畫畫,用原子筆反覆描繪記憶裡的港邊場景、被摧毀的老家、株式會社等等,沒有間段地描繪,隨時放在夾克口袋裡那個變形的皮夾,與數年累積的港務局名牌疊放在一起。因為薄得透光的紙,已經沒有完整的邊,更看得出筆跡的深度,像歷史在他生命的鑿痕。
魏祺峰見著人,便攤開左胸口袋皮夾內的日曆紙,說著時代的故事。5.港邊黑手
海上
潘顯德是金瓜石人,從東北角到基隆工作後,他決定在港邊討生活。
他先在報關行,二十歲歲那年當上海軍,先在海上待一段時間,退伍後就開始跑船。
剛開始他是不怕的,好望角到紅海,可倫坡到印度洋、盧安達、西非,跟所有船員一樣,他在船上的日子,遊歷了那些看起來很遙遠的點,小伙子膽子大,哪裡都願意去。
服役期間,軍中有習慣性毆打下屬的傳統。曾有士兵承受不住,直接跳海自殺。而他開始跑船之後,某次,船上起了爭執,有人為了面子單挑打架,他去當和事佬勸架,一不小心「公親變事主」,在一陣混亂中受了點小傷,他便開始思考船上這種封閉的日子,是否還要一直過下去。幾年後,又有朋友在行船期間離開人世,他形容「那是被海龍王抓去當女婿了」,說法竟然帶著點幽默,大概也是種跟老天爺比拚後的豁達。
這些情況,也讓年邁母親時不時叨唸擔心,深怕家中唯一的香火會不會就在海上斷了音訊。
某晚,風浪大作,船頭頂著浪,卻偏偏要往浪裡鑽。他原本還穿著救生衣站在甲板,看著比樓高的波濤層層襲來,正覺得怕,機器又壞了,為了修船,只能把救生衣脫掉,綁著繩索搖搖晃晃降到船邊工作。他一邊吐,一邊更換船隻的零件,濕濕黏黏的雨水和嘔吐物全攪和在一起。隔日,衣服一脫,只見身上佈滿數不盡的瘀青。
當下,他決定回到岸上討生活,那是船上生活的第十個年頭,他存足了一百萬,終於回到岸上。
輪機這一行
一回到陸地,他先訂下終身大事。由於太太是高雄人,他也跟著來到高雄開始新生活。婚後,他在修船廠工作七年,除了習得更熟練的技術,也順便了解港邊生態。到了一九八九年,他正式創業,開了自己的修船廠。
那年頭的修船廠在港邊可是熱門行業,哈瑪星哨船頭附近為船隻加油的油庫排滿船隻,急著要出港討海。每日在第一港口進出的漁船不時塞住港口,港邊相關輪機的廠店,大約接近百間。當時港邊一片榮景,身為其中一員,潘先生的造船廠,一個月要修十幾艘船,舊的船還沒修完,已經又有新進來的船在等待了。
談到修船,可說是一門不退流行的行業。只要港邊有船隻進出,就有船隻得修理。戰後,船隻噸位越來越大,百噸以上的大型貨船,每二十個小時就要航修,做定期檢測,這由船上的輪機人員負責;除此之外,大約每八千小時就要回陸地進廠保養,這就是修船廠的工作了。若是可以做上幾間大公司的生意,像是長榮、萬海或陽明,一個晚上保修所賺取的費用,幾乎就超越別人一整個月的薪水。
但這同時也是辛苦活,有時等船進港,一等就等到半夜。船一停好,船員各散,才是輪機檢修上工的時間。又或者船提早到了,不管是否熟睡,他都要頂著月光出門。要是遇上重大的問題,他則要領著師傅一起想對策。況且,船期是不等人的,每一艘船從進港的那一刻起,幾乎就是一次倒數計時,有限的時間內得完成必要整修,一方面要保證船隻能及時出發,一方面又要確定起程的平安,每一次都在跟時間賽跑。
輪機做為造船和拆船的中繼點,對於臺灣的整體造船工業,自然也有深刻的觀察。
終戰二十年後,臺灣開始出現大型船隻的需求,一方面是遠洋漁業的興起,一方面貨物進出口貿易也越來越頻繁。當時臺灣船公司會至日本神戶造船廠下訂,神戶的造船技術從戰前就開始發展,技術高階的主機,或者更高等級的潛水艇都可以製造,新船也有一定保固。臺灣造船公司在蔣經國主政的年代,培養了一批專家從美國和日本學到如何製造培林(軸承)、主機,臺灣一度擁有生產鏈的前端技術,那也是整個製船產業最核心也獲利最多的部分。但鄰近的韓國自一九六○年代以來,傾國家之力扶植造船業,九○年代後釜山的造船廠林立,以較便宜的價格日漸取代日本的地位。
那年代,工廠不時要找來日本的工程師維修,為了陪日本的客戶應酬,「還要特別買一臺賓士來接送客戶,至於停在門口的TOYOTA是平常開的」。港口光景
而臺灣所培育出的核心成員,則在這十年間被陸續挖角。
時至今日,臺灣的遊艇、造船工業,最無可取代的部分,不是高階的機械製造技術,反而是現年已經五十到六十歲左右的木工師傅,憑藉著優秀的裝潢與組裝技術,打造流利的船體。
臺灣的造船業仍處於後端的拼裝過程,仰賴進口他國的主機。現在的情況以裝潢組裝的「後端拼裝」技術為主,至於「造船、修船、拆船」的後端拆船產業,在一九九○年代後,臺灣也失去「拆船王國」的稱號,拆船的產業鏈移往中國、印尼、印度孟買。
這些年,港口的船隻壅塞的光景不再,過去新加坡、德國、希臘的航運公司在航線上原會「順路」經過臺灣。但現在,各國的船隻都會直接進到中國,譬如丹麥的快桅集團,才縮編了高雄港的組織,「對岸的港口,五十年免租的啊。」潘顯德一聲長嘆。相近的地點,一經比較,港口發展的消長就出現了。
快要六十歲的潘顯德,現在偶爾還會進現場。經歷一些人生的轉折,大部分的工作已經交給底下的年青人。他會參加扶輪社聽聽港邊不同的風聲,回海洋大學念二技,還被學校找去當業師,把一身的好功夫再傳承給新一代。他希望兒子能夠繼續將工廠經營下去,畢竟在港邊就有船,而有船,就會有輪機產業的位置。
本來並不是討海的
一如往常,莊碧飛坐在門前編織漁具,他它熟稔地用爬滿皺紋的雙手,將尼龍線交叉出經緯。
莊碧飛是旗津著名的耆老,設計出許多耐用的網具。但他,本來並不是討海的。除了幼時父親在內港養殖石頭蚵外,他們在崩隙還有幾塊田園,種地瓜養豬維生。他的爺爺是日本時代的保正,在村裡有點名望,接受日本政府的指派,也受到特許,開了間雜貨店,販賣什貨等生活用品,他只消偶爾幫家裡顧店,其餘的時間就是上學唸書,生活過得不錯。
皇民化當時,全家改了日本姓「濱川」,莊碧飛說這是代表海邊的住民。他的長兄在二戰時擔任台籍日本陸軍志願兵,配有軍馬,在社里間受到敬重。美軍空襲時,每戶家庭在海岸邊挖掘防空壕避難,另一部分的人則疏開到鄉村。終戰後沒多久,他們已經得知,哥哥「濱川英雄」已經戰死在南洋,幾年後,輾轉多人,才由鄰居友人的手中接回他的指甲和頭髮。
戰後,大人們在港內抓魚。中洲漁港過去很大,沙地上能停放三、四十隻以上的竹筏,漁船並不多見,其中也有往返中國載運貨品的帆船。多數的漁民在外港牽罟,這種以地曳網作業是傳統的補魚方法,在臺灣西部沿海相當普遍,由於需要眾人合作,基本上多是具有一些經濟基礎的漁戶才能招工。莊碧飛記得,每當漁汛期,他的父親和兄長會站上竹筏上,由一個人撐向外海,另一個人將網撒出,環構成一個馬蹄狀的路徑,讓網沉至海中一些時間圍困漁群,灘上眾人腰間便勾著繩網,一齊向後拉即可收穫。莊碧飛至今仍忘不掉那時的景色:黃昏時,眾多的罟網在海上各自張開,錯落有致,加上江港歸帆,畫面美不勝收。他說,如果當時有攝影器材能記錄下來,那旗津一定是世界級的景點。
彼岸經緯
當了一年四個月的國民兵,莊碧飛才開始出海抓魚。當時兄弟還沒分開,三、四個一起賺食,有時候到台南、東港等處,一次數日或月餘。二、三十歲時後,他們也常跑到福建、汕頭等南方沿海作業,當時中國正歷經「大躍進」的時期,偶爾會見到公社專用的帆船,擠滿三、四十多個人。他記憶中裡對岸漁民的生活條件非常差,也不能靠近。
但有時候他們會從台灣帶一些舊衣,在海上遇見了個體漁民,就用塑膠袋包裹,會船時丟向他們的小船。
為了躲避颱風,莊碧飛和兄長也數次進出九龍。六○年代時,香港境內還沒有太多觀光客,港邊避風塘裡居住著在水上生活的蜑家漁民,岸上還有黑社會,搶劫頻繁,治安非常差,所以大約下午五、六點,路上的商店差不多都已經關門。莊碧飛說九龍與香港就像旗津和高雄一樣,港內是繁榮的市鎮,港外則是破落的漁村。
海上水路的經驗特別,越戰時,他們的船行經海南島附近,許多越南人從海上逃亡,他便親眼目睹難民用水缸和竹竿划滑到他們的船邊,其中一個人拿了軍用的指北針,問他們香港怎麼去,莊碧飛用手比了比方向,他們就趕路離開了。
此岸經緯
大概四、五十幾歲左右,莊碧飛結束了討海的生活,回到岸上。他和父親、哥哥開始作漁網販賣。
早期是以苧麻、棉線製作「苓仔」,但因為不耐鹽水,下水後需要曬網,使用壽命也僅有三年便需再製。,所以日治時期,即改成棉網,雖然較為耐水且耐用,不必次次曬網,但仍需要定期以一種類似番薯塊根的薯榔作染料,來增強拉力並延緩腐化。
他們向紗行批來棉絮,找來村裡的人工一起製做,這是在漁村裡極為普遍的技藝,多由女性負責,完成後便可賣到南部幾個漁港。戰後一段時間,才改成塑膠尼龍。
莊碧飛長年著一件棉質背心,深藍灰的西裝褲腰串著鑰匙,雖然現年已經八十三歲,但黝黑的薄皮膚下仍有寬厚的臂膀。他常坐在港邊自家的騎樓工作,椅子上放著竹製的梭子(編網針)、紡錘、網目尺、小刀、剪刀,和收納這些工具的油亮木盒。,莊碧飛坐在板凳上並著腳,默數著網目的尺寸,快速將繩結好手持漁網,或更費時的把線索撐開,穿過梭子,構成平整規律的交叉格狀,來加強護具的耐用性。
他走到住家隔壁的小儲藏間,解開鐵鎖瑣,推開刷成湖綠色的厚門,牆邊整齊不紊的擺放大小各異的手網,插在橘色、藍色的塑膠桶,一旁還堆放像壺狀漁簍的補蝦網具,莊碧飛用金屬增加幾層防脫設計,也是他的發明。
接著他莊碧飛又拿出一副寬大的手網,是專門用在每尾重達百斤的石斑大網。
其上的平口網圈,是以門前的鐵器折出來,這個設計可以讓網圈貼緊漁塭底層,魚群不至向弧形的兩邊逃脫;而扁狀木桿避免滑動,又減少手握的施力;上面的線繩接到網底的束口,因為在撈魚後,沉甸的重量不易傾倒,則可以控制開闔;網圍的尼龍繩更是鉤纏在不銹鋼網圈上的內側,沿線覆上剖開的塑膠管,防止作業時刮到壁岸及石塊而斷開。莊碧飛靠著多年的漁業知識與經驗,研究網距技術,改良繡法、網目,構法、耐水性和防刮等細節,許多養殖業者或海產店的攤商,都特別向他訂製作手持的撈網及容器護具,他也常受到政府及民間單位的表揚與關注。
黃昏時,莊碧飛坐在門口,隔一條水泥鋪成的馬路是中洲漁港,停靠的是玻璃纖維製的近海漁船。他說,過去叔叔將蚵殼傾倒在海岸,久而久之,囤出了這條路。偶爾,他會放下手邊的工具,規矩地收好,再沿著港邊這條小路,穿過漁民歇息的卡拉OK亭,回到旁邊紅磚造的祖厝看看。4.日曆紙上的旗津 魏祺峰
違建
魏祺峰的夾克和襯衫口袋,永遠放著鼓脹成饅頭狀的黑色皮夾,裡面收著一張張港務公司歲末聯歡的邀請名牌,還有幾張破爛變形、薄可透光的日曆紙。那是他反覆描繪的記憶,沒有間段地紀錄,隨時放在皮夾,數年累積。當他小心翼翼地攤開的日曆紙,那個用藍色原子筆來回塗寫的「東亞海運」字跡清晰可見。
「這裡都是違建。」魏祺峰步履緩緩,牽著腳踏車避開大街上的觀光客,沿著一條常走的小路徑,指著住家旁的兩側的屋厝說。也許新蓋的透天房對魏祺峰的記憶而言,都是違建。
西元一九二七年出生的魏祺峰,身體硬朗,鼻樑上掛著一副金邊寬大的舊式眼鏡,年邁的眼皮下垂,露出澄澈的雙眼。他獨居在旗津教會後方,一棟四十年左右的洗石子老屋,木門右上方有一塊板擦大小的木片,用石綠色填寫他的名字。屋內客廳的牆壁、頂端燈飾的圓形線板,白灰已經有好幾處剝落,後方廚房有石型磁磚砌成的洗手槽和廚具,雖然乾淨,但看得出來鮮少有客人。魏老從斗櫃裡拿出三合一咖啡,添加大量的砂糖沖泡。
記憶的圖像
二戰末期,美軍在台灣密集投彈的那兩年,高雄是受空襲次數最頻繁的城市。
魏祺峰在旗津的家被炸彈徹底地轟過,三合院出現一個偌大的窟窿,路也都被炸開,只有前方的教會沒倒。而魏老曾任職的「東亞海運株式會社」,則在他加入日本海軍志願兵訓練期間被炸毀,「當天正巧是會社的發薪日,同事當時都在現場。」魏祺峰因為受訓缺席,逃過一場浩劫,至今仍記憶猶存。
魏老喜歡畫圖,現在住的房子,是數十年前原址重建的三樓老屋。但他已經很少上二樓了。他改睡一樓的雅房,除了因為年邁退化的身子,另一個原因是在妻子過世後,他刻意保留的時間感。二樓幾乎維持原樣。
一樓通往二樓的牆上掛滿了許多書法字,是寫給自己勤勉的詩句,還有幾幅極為出色的水彩畫,雖然透明壓克板已經泛黃,仍可看出當時慎重地裱框。其中一幅神情優雅、姿態端莊的女人,是他為妻子所畫的肖像,用不透明水彩染上淡色,頭後方還有一輪像聖母般的暈黃光輝,在幾幅牆上的作品裡極為突出。
有一天,他用鑰匙打開深鎖的房門,玻璃窗掩著舊色的簾布,透進一點光照,細塵在空中亮晶晶地發閃,彷彿打開他的記憶。進到他們的房間,靠床的牆上,同樣擺了數件作品和照片,一件小尺幅的油彩自畫像,用古典式雕花的木框裱背,穩重的黃褐色調,表現了他青年時的自信與自持。
魏祺峰在床邊坐下來畫圖。
他說,阿祖從福建渡海,在這裡住了好幾代。父親在一八七四年出生時,一家子從苓仔寮搬到旗後,砲台剛因牡丹社事件的影響,由清政府修建好。他們靠「牽罟」、「篙排仔」及養貝維生。據說那時旗後還有一個清兵的哨營,但清朝統治重心不在台灣,所以治安狀況與衛生條件都非常差。他描述父親口中的旗後聚落。閩式漁村已是打狗當時最繁華的市街了,酒樓、洋行、領事、醫館和禮拜堂,都成為他原子筆下描繪的場景。
魏祺峰平日獨居,但這裡曾是全家族的回憶。他是父親第三個續絃的妻子所生,前兩任太太因故過世,所以他和父親的年紀相差懸殊。說著,魏祺峰翻開一頁旗後平和公學校卒業紀念冊,原版早就散失,現在彩色翻印是同窗借給他的。他指著裡面一個「糞萁」的名字,以原子筆重重劃掉,手寫改成「祺峰」。他沒有問過爸媽為什麼,但過去一些農家為了避災,常將小孩的名字起得粗魯。
他想起了一個早夭的妹妹,有一次犯了腸胃病,讓母親背到鹽埕給楊金虎醫生看診,父親還體貼地在媽祖廟前的市場買了昂貴的日本蜜桃,要慰勞可憐的小女兒,但她吃了幾口,晚上腹瀉脫水後便往生了。逃兵
魏祺峰的母親是基督徒,他們住在教會旁,小時候他在長老教會巴克禮牧師在旗津為高雄所創的第一所幼稚園「愛兒園」就讀,所以他會用羅馬字寫台語文。後來當他自公學校畢業,應徵上高雄港站前的「東亞海運株式會社」,當時他們停靠在高雄港的船舶就多達五、六十艘,是一座極具規模的海運公司。魏祺峰擔任船舶聯絡員,白天負責遞送文件,下午回到旗津,在國民學校附設青年學校進修。一九四三年,大東亞戰爭正熾,他加入警防團,在空襲時協助警消救護受傷人員與善後,戰爭末期,又成為台籍日本海軍志願兵。
「我是被迫的。」魏祺峰說,當時他曾眼睜睜地見證日本警察以長棍毆打台灣人,一個耳光下去,口中罵著「清國奴!清國奴!」年少血氣方剛,他有股衝動,想衝進警察署裡回擊,同歸於盡就罷了,但畢竟沒有。一九四五年,青年學校的教官強制魏祺峰等年輕人全部報考志願兵。體檢後他被選上,所以他乘著空襲的契機,假借要安頓母親疏開而逃兵,卻仍被發現,抓回從軍。
「臭油抽!」魏老憶起仍難掩憤慨,用當時罵日本人的髒話嚷著。
然而,對魏祺峰來說,加入戰爭卻也是萬幸,他逃過美軍空襲,也不像許多前期的台籍日本兵從高雄港出發,往南洋赴死。
透光的日曆紙
魏老騎著腳踏車在旗後行動。
每逢假日,此處人潮總是川流不息。他常在曾當過廟公的媽祖廟前和日本觀光客攀談,或在福壽宮的老人亭下唱歌。但或許,這座島於他而言,已經不再是過去的模樣,所以,魏老以筆用力記住每件要事。退休後,他在日曆紙背面開始畫畫,用原子筆反覆描繪記憶裡的港邊場景、被摧毀的老家、株式會社等等,沒有間段地描繪,隨時放在夾克口袋裡那個變形的皮夾,與數年累積的港務局名牌疊放在一起。因為薄得透光的紙,已經沒有完整的邊,更看得出筆跡的深度,像歷史在他生命的鑿痕。
魏祺峰見著人,便攤開左胸口袋皮夾內的日曆紙,說著時代的故事。5.港邊黑手
海上
潘顯德是金瓜石人,從東北角到基隆工作後,他決定在港邊討生活。
他先在報關行,二十歲歲那年當上海軍,先在海上待一段時間,退伍後就開始跑船。
剛開始他是不怕的,好望角到紅海,可倫坡到印度洋、盧安達、西非,跟所有船員一樣,他在船上的日子,遊歷了那些看起來很遙遠的點,小伙子膽子大,哪裡都願意去。
服役期間,軍中有習慣性毆打下屬的傳統。曾有士兵承受不住,直接跳海自殺。而他開始跑船之後,某次,船上起了爭執,有人為了面子單挑打架,他去當和事佬勸架,一不小心「公親變事主」,在一陣混亂中受了點小傷,他便開始思考船上這種封閉的日子,是否還要一直過下去。幾年後,又有朋友在行船期間離開人世,他形容「那是被海龍王抓去當女婿了」,說法竟然帶著點幽默,大概也是種跟老天爺比拚後的豁達。
這些情況,也讓年邁母親時不時叨唸擔心,深怕家中唯一的香火會不會就在海上斷了音訊。
某晚,風浪大作,船頭頂著浪,卻偏偏要往浪裡鑽。他原本還穿著救生衣站在甲板,看著比樓高的波濤層層襲來,正覺得怕,機器又壞了,為了修船,只能把救生衣脫掉,綁著繩索搖搖晃晃降到船邊工作。他一邊吐,一邊更換船隻的零件,濕濕黏黏的雨水和嘔吐物全攪和在一起。隔日,衣服一脫,只見身上佈滿數不盡的瘀青。
當下,他決定回到岸上討生活,那是船上生活的第十個年頭,他存足了一百萬,終於回到岸上。
輪機這一行
一回到陸地,他先訂下終身大事。由於太太是高雄人,他也跟著來到高雄開始新生活。婚後,他在修船廠工作七年,除了習得更熟練的技術,也順便了解港邊生態。到了一九八九年,他正式創業,開了自己的修船廠。
那年頭的修船廠在港邊可是熱門行業,哈瑪星哨船頭附近為船隻加油的油庫排滿船隻,急著要出港討海。每日在第一港口進出的漁船不時塞住港口,港邊相關輪機的廠店,大約接近百間。當時港邊一片榮景,身為其中一員,潘先生的造船廠,一個月要修十幾艘船,舊的船還沒修完,已經又有新進來的船在等待了。
談到修船,可說是一門不退流行的行業。只要港邊有船隻進出,就有船隻得修理。戰後,船隻噸位越來越大,百噸以上的大型貨船,每二十個小時就要航修,做定期檢測,這由船上的輪機人員負責;除此之外,大約每八千小時就要回陸地進廠保養,這就是修船廠的工作了。若是可以做上幾間大公司的生意,像是長榮、萬海或陽明,一個晚上保修所賺取的費用,幾乎就超越別人一整個月的薪水。
但這同時也是辛苦活,有時等船進港,一等就等到半夜。船一停好,船員各散,才是輪機檢修上工的時間。又或者船提早到了,不管是否熟睡,他都要頂著月光出門。要是遇上重大的問題,他則要領著師傅一起想對策。況且,船期是不等人的,每一艘船從進港的那一刻起,幾乎就是一次倒數計時,有限的時間內得完成必要整修,一方面要保證船隻能及時出發,一方面又要確定起程的平安,每一次都在跟時間賽跑。
輪機做為造船和拆船的中繼點,對於臺灣的整體造船工業,自然也有深刻的觀察。
終戰二十年後,臺灣開始出現大型船隻的需求,一方面是遠洋漁業的興起,一方面貨物進出口貿易也越來越頻繁。當時臺灣船公司會至日本神戶造船廠下訂,神戶的造船技術從戰前就開始發展,技術高階的主機,或者更高等級的潛水艇都可以製造,新船也有一定保固。臺灣造船公司在蔣經國主政的年代,培養了一批專家從美國和日本學到如何製造培林(軸承)、主機,臺灣一度擁有生產鏈的前端技術,那也是整個製船產業最核心也獲利最多的部分。但鄰近的韓國自一九六○年代以來,傾國家之力扶植造船業,九○年代後釜山的造船廠林立,以較便宜的價格日漸取代日本的地位。
那年代,工廠不時要找來日本的工程師維修,為了陪日本的客戶應酬,「還要特別買一臺賓士來接送客戶,至於停在門口的TOYOTA是平常開的」。港口光景
而臺灣所培育出的核心成員,則在這十年間被陸續挖角。
時至今日,臺灣的遊艇、造船工業,最無可取代的部分,不是高階的機械製造技術,反而是現年已經五十到六十歲左右的木工師傅,憑藉著優秀的裝潢與組裝技術,打造流利的船體。
臺灣的造船業仍處於後端的拼裝過程,仰賴進口他國的主機。現在的情況以裝潢組裝的「後端拼裝」技術為主,至於「造船、修船、拆船」的後端拆船產業,在一九九○年代後,臺灣也失去「拆船王國」的稱號,拆船的產業鏈移往中國、印尼、印度孟買。
這些年,港口的船隻壅塞的光景不再,過去新加坡、德國、希臘的航運公司在航線上原會「順路」經過臺灣。但現在,各國的船隻都會直接進到中國,譬如丹麥的快桅集團,才縮編了高雄港的組織,「對岸的港口,五十年免租的啊。」潘顯德一聲長嘆。相近的地點,一經比較,港口發展的消長就出現了。
快要六十歲的潘顯德,現在偶爾還會進現場。經歷一些人生的轉折,大部分的工作已經交給底下的年青人。他會參加扶輪社聽聽港邊不同的風聲,回海洋大學念二技,還被學校找去當業師,把一身的好功夫再傳承給新一代。他希望兒子能夠繼續將工廠經營下去,畢竟在港邊就有船,而有船,就會有輪機產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