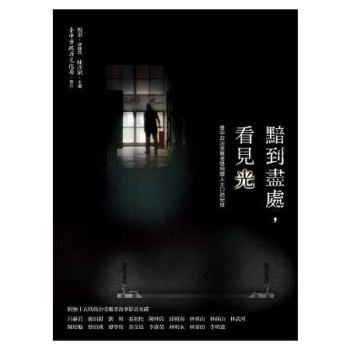謎樣的遺憾拼圖──呂赫若
受難者:呂赫若
現況:已歿
案件:1949~1950年「基隆中學」事件
案情概況:1949年爆發「基隆中學事件」,基隆中學校長也是《光明報》創辦人鍾浩東被舉報為匪諜被捕,時任《光明報》主編的呂赫若逃往臺北縣汐止石碇山區,蘇金英、陳春慶等人證實其於1950年於山區被毒蛇咬死,但始終未找到屍首。
受訪者:呂愛琴(呂赫若長女)、呂芳雄(呂赫若次子)
受訪時間:2016年4月15日(呂愛琴,自宅)
2016年4月18日(呂芳雄,自宅)
採訪、撰稿:魏吟冰
Story呂赫若
呂赫若,本名呂石堆,1914年生於臺中廳葫蘆墩支廳(豐原)潭仔墘區校栗林,父祖輩小有資產是當地頗具聲望的大戶人家。臺中師範學校畢業後,執教於新竹峨眉公學校及南投營盤公學校,期間即從事小說創作,後赴日本東京深造修習聲樂,返臺後曾任教於建國中學及北一女中,集「作家」、「聲樂家」、「劇作家」於一身,故有「臺灣第一才子」之封號。
呂赫若成名甚早,短篇小說〈牛車〉1935年刊登於日本《文學評論》的新年號,隨即受到臺灣及日本文壇重視。受左翼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甚深,作品多觸及「階級」與「性別」,對底層勞動者及封建社會桎梏的女性深有描述及同情。「呂赫若」筆名,日文之意是期許自己成為赫赫有名的年輕人。
1942年自日本返臺後,積極投入臺灣文壇活動,加入《臺灣文學》編輯,並擔任「臺灣文藝家協會」小說部理事,也為「臺灣演劇協會」撰寫大眾劇本及廣播劇。1943年更以短篇小說〈財子壽〉獲得第一回「臺灣文學賞」。終戰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後,1945年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並於次年一月擔任《人民導報》記者,1948年任《光明報》主編,對時局常有針砭,更變賣祖產成立「大安印版所」印行地下宣傳文件。
1949年發布戒嚴令,《光明報》創辦人鍾浩東被捕,呂赫若展開逃亡,躲在石碇山區,據當地人士證實1950年不幸於山區遭毒蛇咬死,走完熾熱卻短暫的一生。其妻、其子、其女則身受白色恐怖之苦。
受訪者:呂芳雄(呂赫若次子)
才子光環下的「冬夜」生活
我叫呂芳雄,1942年出生於臺中潭子校栗林曾祖父所建的「建義堂」。對父親的感受,如同我於〈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一文中文末所寫:「在熾熱又亮麗的『才子』光環下,父親走過他的人生,但卻留給他的家屬寒冷又黑暗的『冬夜』生活」。小時候大略知道父親是聲樂家,也寫過小說,但完全不知道父親有「臺灣第一才子」的稱號及在臺灣文壇的重要性。這些都是在我四十歲以後,接觸白色恐怖的田野訪查,參與研究父親的相關研討會、紀念活動後才陸續瞭解。我很尊敬父親在專業上的成就與貢獻,但作為他的子女要很真實的說:「父親一生最沒有付出的就是他的家庭」。
我的童年生活
1942年父親決定自日本返臺,母親在懷了身孕下顛簸坐船,回到臺灣在潭子生下了次子的我,我上有大哥芳卿、大姊愛琴、二姊田鶴及五歲因病過世的三姐緋沙子。下有芳傑、芳甫、芳伯、芳民四位弟弟。童年印象已模糊,在潭子生活的期間,叔公呂坤霖很喜歡抱我外出,遇到鄰人或朋友都會稱讚我長得很好。物質生活過得很優渥,雨天同齡小孩還在穿蓑衣時,我們已經穿雨衣了,在當時可說是相當罕見。
父親在家中絕口不提在外面從事的活動,雖然友人如音樂家呂泉生等也都來過家中,但朋友來時父親均不讓母親及小孩出來。所以,對於父親的朋友認識得極少。在潭子生活了一陣子就舉家搬到臺北,國小一年級唸的是臺北市的東門國小,1950年父親遇難時,我還不滿八歲,應該是國小二年級,八歲的小孩能有什麼記憶,只記得很快我們就搬回豐原社口的外婆家。之後,隱約記得聽人說過父親是被毒蛇咬死的,但從未聽母親提過。關於父親的很多事,都是後來才從舅舅林永南那得知。
1950年父親出事逃亡後,在那個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年代,除了舅舅林永南等少數幾人外,其他往來的親友幾乎不敢靠近。分別就讀北一女初中三年級的大姊,與讀成功初中二年級的大哥深受其害,不僅曾被情治人員拷問追查父親下落,兩人也皆斷送升學之路。舅舅林永南也無辜受到牽連,被關了將近一年才遭釋放。也因此,親友更是敬而遠之,每年過年農曆初二回娘家的日子,母親按例邀請父親的大姊到家裡來,我也曾經跟母親同往,印象中姑媽反應稍嫌冷淡,感覺就是應酬一下,當然也從未真正來過家裡,那個時代發生這種情形完全可以理解。這期間,舅舅林永南雖然也換來牢獄之災,但出獄後仍是無怨無悔照顧我們這一群年幼的外甥,尤其他從事藥品生意,經濟較過得去,資助我家生活及弟弟們的學費,這一路的不離不棄都令我們感念在心。
童年就在豐原社口外婆家渡過,初中考上豐原初級商業職業學校,那時情勢比較和緩了,沒遇到當初大哥從臺北成功中學要轉學臺中一中時沒人敢當保證人的慘況,姨丈做了我入學的保證人。畢業後,十六歲就隻身來臺北工作了。
三十二歲,尋訪的起始──鹿窟生死之謎
關於父親,在家裡就是禁忌,雖多少有聽過一些傳聞,但沒人會問也沒人會提。第一次尋找父親埋屍之地,是因三十二歲時接到姑丈劉興城的來信。劉興城是父親的妹妹──來于姑媽的先生,家中務農田產不少,因需人手幫忙,新聘一名長工,沒想到隨後軍方來抓人,指稱那人是二二八事件後的逃亡者。軍方誣指姑丈為同夥,1950年代期間也被抓入獄關了十年。獄中,姑丈剛好跟鹿窟事件被捕的蘇金英關在一起,蘇金英談到親眼目睹父親被毒蛇咬死的過程。出獄後,姑丈才會來信叫我去找蘇金英瞭解這一段過程。
還記得我騎了Vespa,獨自前往汐止石碇山區找蘇金英,當時他喝了點酒,跟他表明來意後,他打死也不承認認識我父親。我拿了姑丈寫的信,再把身分證拿出來讓他再三確認我的確是呂赫若的兒子,才願意跟我談起父親種種。石碇山區群山環繞,他指著隔著一條溪旁的山跟我說,父親就葬在那裡。他親口證實目睹父親被毒蛇龜殼花咬到,當時還找來陳春慶、王文山等人一起幫忙抬往山下就醫,但最後還是沒救回來。之後,他們找了一棵大樹把父親埋了,並找一塊大石頭作記號。那年代逃亡的人,沒有人敢用真名,據蘇金英的描述父親當時自稱「王仔」(註3)。事隔多年,四十歲左右(約1982、83年),認識了做白色恐怖田野調查的藍博洲,曾經開著我的雷諾九號到過好幾次鹿窟。之後,也跟大哥、四弟共同前去,那裡都是荒煙蔓草,也沒找到蘇金英所說為父親所立的大石頭。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確切的證據證實父親是被毒蛇咬死的,但在我心中90%相信父親是被毒蛇咬死的說法。
1998年的轉折──北京呂赫若研討會
雖然1980年代與藍博洲、陳映真等人接觸,開始瞭解父親的重要性,但仍僅止於聲樂家與作家的淺薄層次。直到1998年,接到陳映真的電話要我以家屬的身分去北京參加「呂赫若作品學術研討會」。當時,我不知道什麼是研討會?更沒有參加過研討會的經驗,還跟陳映真說:「我又不會寫論文去那裡要幹麼?」陳映真要我以家屬身分出席即可。研討會為期三天,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臺灣參加的人包括陳映真、藍博洲、在淡江大學教書的李昂之姐施淑、臺灣清華大學教授呂正惠、陳萬益,還有一位牙醫師曾健民等人。
研討會是在北京的民族飯店舉行,對父親認識不深又都沒經驗的我,第一天上台沒有邏輯性的胡亂講了一通。會場上遇到全國臺聯(註4)副會長石四皓,他還跟我說:「一般作家舉行兩天的研討會就很了不起了,對單一作家進行三天的研討會可說是絕無僅有。」什麼都不知道的我,那時還傻傻的以為全國臺聯是李登輝的那個臺聯。研討會晚上跟陳萬益老師住同一間房,又跟他多聊了父親的事。第二天,作家陳若曦女士特別來找我,表示願意將他論文發表挪出十分鐘讓給我,經過一番整理,我再一次上台發言。
回臺後,呂正惠老師鼓勵我把關於父親的東西寫下來。我還跟他說:「我不會寫,我來口述,拜託陳萬益老師博士班的學生寫下來。」但呂老師一再堅持這樣行不通,鼓勵我要自己把它寫出來。1998年北京研討會結束後,舅舅林永南的小女兒帶著子女移民澳洲,因她先生的診所在臺灣常需往返奔波,希望我能前往澳洲協助照料她的子女。就在1998到2000年往返臺灣一年多的時間中,慢慢地把追記父親的文章完成。期間,日本橫濱大學垂水千惠教授來信,打算以父親為主題,進行博士論文的撰寫,通信過程中也讓我更瞭解父親。近一萬五千字的文章完成後,第一個拿給陳萬益老師看,經由陳老師不著痕跡略為潤飾後,並由其協助將文章名稱定為〈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
父親日記的公開
父親遺留日記的公開過程則是有點曲折,大約也是1998到1999年期間,長期研究臺灣文學的張恆豪先生、日本橫濱東洋大學的野間信幸教授與清華大學的呂正惠教授等人,都希望父親遺留的日記能公開作為研究資產。當時,日記的原稿在大哥那裡,曾提供給特定學者研究。其他學術界人士覺得不盡公平,並認為日記未公開研究呂赫若就有如瞎子摸象。趁著清明回潭子掃墓,我跟母親還有大哥提起,願意用相機底片一張張將它翻拍公開。母親當時說:「不用那麼麻煩拿去影印就好。」我就帶回臺北影印裝訂成冊十本,分送給陳萬益、呂正惠等相關需要的教授,每一冊上面特別留有我的簽名,代表這是經過家屬的同意授權,不致產生版權上的問題。
之後,日記原稿曾由呂興昌教授策劃,匯集包含父親在內的五位作家,在南海路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2004年國立臺灣文學館將日記譯成中文,發行了〈呂赫若日記手稿本〉與〈呂赫若日記中譯本〉,讓更多研究者得以有更多的素材。目前,日記的原稿則保存在我這裡。
「赫若」筆名的由來
本名呂石堆的父親成名算很早,1935年就以「赫若」的筆名,在日本《文學評論》刊載第一篇發表的日文小說〈牛車〉。現對父親筆名「赫若」的詮釋多流傳一種說法,父親因嚮往社會主義,而各取朝鮮作家「張赫宙」的「赫」與中國左翼作家「郭沫若」的「若」作為筆名。但就我從六叔呂如鵬(父親很敬重的叔叔呂坤霖的兒子)口中得知並非如此。
關於父親的筆名「呂赫若」,六叔曾跟我提過,父親曾親口跟他說會以「赫若」作為筆名,是希望成為「赫赫有名的年輕人」。
六叔從小跟著坤瑞叔公移居爪哇,完全不懂日文,更不知道「赫赫有名的年輕人」就是「赫若」的日文字義。再者,父親也算成名得早,會取自同期間知名作家的名字作為筆名,在我看來並不合理。
我覺得很多事情要還原到那個年代的情境來看,不能理所當然的用我們現在的認知來推斷。外界也曾傳說,辜顏碧霞女士曾駕車載父親逃亡時,看到路旁有警察,辜顏女士就跟父親講說:「你趕快開我的車先跑。」這段坊間的傳聞,我個人覺得並不真實,還原到七十幾年前的情境,汽車是很稀有的東西,會開車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我不太相信父親會開車,跟舅舅、六叔等長輩聊過父親,從未聽他們說過父親會開車。
以上內容節錄自《黯到盡處,看見光:臺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紀錄》魏吟冰等採訪、撰稿.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受難者:呂赫若
現況:已歿
案件:1949~1950年「基隆中學」事件
案情概況:1949年爆發「基隆中學事件」,基隆中學校長也是《光明報》創辦人鍾浩東被舉報為匪諜被捕,時任《光明報》主編的呂赫若逃往臺北縣汐止石碇山區,蘇金英、陳春慶等人證實其於1950年於山區被毒蛇咬死,但始終未找到屍首。
受訪者:呂愛琴(呂赫若長女)、呂芳雄(呂赫若次子)
受訪時間:2016年4月15日(呂愛琴,自宅)
2016年4月18日(呂芳雄,自宅)
採訪、撰稿:魏吟冰
Story呂赫若
呂赫若,本名呂石堆,1914年生於臺中廳葫蘆墩支廳(豐原)潭仔墘區校栗林,父祖輩小有資產是當地頗具聲望的大戶人家。臺中師範學校畢業後,執教於新竹峨眉公學校及南投營盤公學校,期間即從事小說創作,後赴日本東京深造修習聲樂,返臺後曾任教於建國中學及北一女中,集「作家」、「聲樂家」、「劇作家」於一身,故有「臺灣第一才子」之封號。
呂赫若成名甚早,短篇小說〈牛車〉1935年刊登於日本《文學評論》的新年號,隨即受到臺灣及日本文壇重視。受左翼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甚深,作品多觸及「階級」與「性別」,對底層勞動者及封建社會桎梏的女性深有描述及同情。「呂赫若」筆名,日文之意是期許自己成為赫赫有名的年輕人。
1942年自日本返臺後,積極投入臺灣文壇活動,加入《臺灣文學》編輯,並擔任「臺灣文藝家協會」小說部理事,也為「臺灣演劇協會」撰寫大眾劇本及廣播劇。1943年更以短篇小說〈財子壽〉獲得第一回「臺灣文學賞」。終戰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後,1945年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並於次年一月擔任《人民導報》記者,1948年任《光明報》主編,對時局常有針砭,更變賣祖產成立「大安印版所」印行地下宣傳文件。
1949年發布戒嚴令,《光明報》創辦人鍾浩東被捕,呂赫若展開逃亡,躲在石碇山區,據當地人士證實1950年不幸於山區遭毒蛇咬死,走完熾熱卻短暫的一生。其妻、其子、其女則身受白色恐怖之苦。
受訪者:呂芳雄(呂赫若次子)
才子光環下的「冬夜」生活
我叫呂芳雄,1942年出生於臺中潭子校栗林曾祖父所建的「建義堂」。對父親的感受,如同我於〈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一文中文末所寫:「在熾熱又亮麗的『才子』光環下,父親走過他的人生,但卻留給他的家屬寒冷又黑暗的『冬夜』生活」。小時候大略知道父親是聲樂家,也寫過小說,但完全不知道父親有「臺灣第一才子」的稱號及在臺灣文壇的重要性。這些都是在我四十歲以後,接觸白色恐怖的田野訪查,參與研究父親的相關研討會、紀念活動後才陸續瞭解。我很尊敬父親在專業上的成就與貢獻,但作為他的子女要很真實的說:「父親一生最沒有付出的就是他的家庭」。
我的童年生活
1942年父親決定自日本返臺,母親在懷了身孕下顛簸坐船,回到臺灣在潭子生下了次子的我,我上有大哥芳卿、大姊愛琴、二姊田鶴及五歲因病過世的三姐緋沙子。下有芳傑、芳甫、芳伯、芳民四位弟弟。童年印象已模糊,在潭子生活的期間,叔公呂坤霖很喜歡抱我外出,遇到鄰人或朋友都會稱讚我長得很好。物質生活過得很優渥,雨天同齡小孩還在穿蓑衣時,我們已經穿雨衣了,在當時可說是相當罕見。
父親在家中絕口不提在外面從事的活動,雖然友人如音樂家呂泉生等也都來過家中,但朋友來時父親均不讓母親及小孩出來。所以,對於父親的朋友認識得極少。在潭子生活了一陣子就舉家搬到臺北,國小一年級唸的是臺北市的東門國小,1950年父親遇難時,我還不滿八歲,應該是國小二年級,八歲的小孩能有什麼記憶,只記得很快我們就搬回豐原社口的外婆家。之後,隱約記得聽人說過父親是被毒蛇咬死的,但從未聽母親提過。關於父親的很多事,都是後來才從舅舅林永南那得知。
1950年父親出事逃亡後,在那個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年代,除了舅舅林永南等少數幾人外,其他往來的親友幾乎不敢靠近。分別就讀北一女初中三年級的大姊,與讀成功初中二年級的大哥深受其害,不僅曾被情治人員拷問追查父親下落,兩人也皆斷送升學之路。舅舅林永南也無辜受到牽連,被關了將近一年才遭釋放。也因此,親友更是敬而遠之,每年過年農曆初二回娘家的日子,母親按例邀請父親的大姊到家裡來,我也曾經跟母親同往,印象中姑媽反應稍嫌冷淡,感覺就是應酬一下,當然也從未真正來過家裡,那個時代發生這種情形完全可以理解。這期間,舅舅林永南雖然也換來牢獄之災,但出獄後仍是無怨無悔照顧我們這一群年幼的外甥,尤其他從事藥品生意,經濟較過得去,資助我家生活及弟弟們的學費,這一路的不離不棄都令我們感念在心。
童年就在豐原社口外婆家渡過,初中考上豐原初級商業職業學校,那時情勢比較和緩了,沒遇到當初大哥從臺北成功中學要轉學臺中一中時沒人敢當保證人的慘況,姨丈做了我入學的保證人。畢業後,十六歲就隻身來臺北工作了。
三十二歲,尋訪的起始──鹿窟生死之謎
關於父親,在家裡就是禁忌,雖多少有聽過一些傳聞,但沒人會問也沒人會提。第一次尋找父親埋屍之地,是因三十二歲時接到姑丈劉興城的來信。劉興城是父親的妹妹──來于姑媽的先生,家中務農田產不少,因需人手幫忙,新聘一名長工,沒想到隨後軍方來抓人,指稱那人是二二八事件後的逃亡者。軍方誣指姑丈為同夥,1950年代期間也被抓入獄關了十年。獄中,姑丈剛好跟鹿窟事件被捕的蘇金英關在一起,蘇金英談到親眼目睹父親被毒蛇咬死的過程。出獄後,姑丈才會來信叫我去找蘇金英瞭解這一段過程。
還記得我騎了Vespa,獨自前往汐止石碇山區找蘇金英,當時他喝了點酒,跟他表明來意後,他打死也不承認認識我父親。我拿了姑丈寫的信,再把身分證拿出來讓他再三確認我的確是呂赫若的兒子,才願意跟我談起父親種種。石碇山區群山環繞,他指著隔著一條溪旁的山跟我說,父親就葬在那裡。他親口證實目睹父親被毒蛇龜殼花咬到,當時還找來陳春慶、王文山等人一起幫忙抬往山下就醫,但最後還是沒救回來。之後,他們找了一棵大樹把父親埋了,並找一塊大石頭作記號。那年代逃亡的人,沒有人敢用真名,據蘇金英的描述父親當時自稱「王仔」(註3)。事隔多年,四十歲左右(約1982、83年),認識了做白色恐怖田野調查的藍博洲,曾經開著我的雷諾九號到過好幾次鹿窟。之後,也跟大哥、四弟共同前去,那裡都是荒煙蔓草,也沒找到蘇金英所說為父親所立的大石頭。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確切的證據證實父親是被毒蛇咬死的,但在我心中90%相信父親是被毒蛇咬死的說法。
1998年的轉折──北京呂赫若研討會
雖然1980年代與藍博洲、陳映真等人接觸,開始瞭解父親的重要性,但仍僅止於聲樂家與作家的淺薄層次。直到1998年,接到陳映真的電話要我以家屬的身分去北京參加「呂赫若作品學術研討會」。當時,我不知道什麼是研討會?更沒有參加過研討會的經驗,還跟陳映真說:「我又不會寫論文去那裡要幹麼?」陳映真要我以家屬身分出席即可。研討會為期三天,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臺灣參加的人包括陳映真、藍博洲、在淡江大學教書的李昂之姐施淑、臺灣清華大學教授呂正惠、陳萬益,還有一位牙醫師曾健民等人。
研討會是在北京的民族飯店舉行,對父親認識不深又都沒經驗的我,第一天上台沒有邏輯性的胡亂講了一通。會場上遇到全國臺聯(註4)副會長石四皓,他還跟我說:「一般作家舉行兩天的研討會就很了不起了,對單一作家進行三天的研討會可說是絕無僅有。」什麼都不知道的我,那時還傻傻的以為全國臺聯是李登輝的那個臺聯。研討會晚上跟陳萬益老師住同一間房,又跟他多聊了父親的事。第二天,作家陳若曦女士特別來找我,表示願意將他論文發表挪出十分鐘讓給我,經過一番整理,我再一次上台發言。
回臺後,呂正惠老師鼓勵我把關於父親的東西寫下來。我還跟他說:「我不會寫,我來口述,拜託陳萬益老師博士班的學生寫下來。」但呂老師一再堅持這樣行不通,鼓勵我要自己把它寫出來。1998年北京研討會結束後,舅舅林永南的小女兒帶著子女移民澳洲,因她先生的診所在臺灣常需往返奔波,希望我能前往澳洲協助照料她的子女。就在1998到2000年往返臺灣一年多的時間中,慢慢地把追記父親的文章完成。期間,日本橫濱大學垂水千惠教授來信,打算以父親為主題,進行博士論文的撰寫,通信過程中也讓我更瞭解父親。近一萬五千字的文章完成後,第一個拿給陳萬益老師看,經由陳老師不著痕跡略為潤飾後,並由其協助將文章名稱定為〈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
父親日記的公開
父親遺留日記的公開過程則是有點曲折,大約也是1998到1999年期間,長期研究臺灣文學的張恆豪先生、日本橫濱東洋大學的野間信幸教授與清華大學的呂正惠教授等人,都希望父親遺留的日記能公開作為研究資產。當時,日記的原稿在大哥那裡,曾提供給特定學者研究。其他學術界人士覺得不盡公平,並認為日記未公開研究呂赫若就有如瞎子摸象。趁著清明回潭子掃墓,我跟母親還有大哥提起,願意用相機底片一張張將它翻拍公開。母親當時說:「不用那麼麻煩拿去影印就好。」我就帶回臺北影印裝訂成冊十本,分送給陳萬益、呂正惠等相關需要的教授,每一冊上面特別留有我的簽名,代表這是經過家屬的同意授權,不致產生版權上的問題。
之後,日記原稿曾由呂興昌教授策劃,匯集包含父親在內的五位作家,在南海路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2004年國立臺灣文學館將日記譯成中文,發行了〈呂赫若日記手稿本〉與〈呂赫若日記中譯本〉,讓更多研究者得以有更多的素材。目前,日記的原稿則保存在我這裡。
「赫若」筆名的由來
本名呂石堆的父親成名算很早,1935年就以「赫若」的筆名,在日本《文學評論》刊載第一篇發表的日文小說〈牛車〉。現對父親筆名「赫若」的詮釋多流傳一種說法,父親因嚮往社會主義,而各取朝鮮作家「張赫宙」的「赫」與中國左翼作家「郭沫若」的「若」作為筆名。但就我從六叔呂如鵬(父親很敬重的叔叔呂坤霖的兒子)口中得知並非如此。
關於父親的筆名「呂赫若」,六叔曾跟我提過,父親曾親口跟他說會以「赫若」作為筆名,是希望成為「赫赫有名的年輕人」。
六叔從小跟著坤瑞叔公移居爪哇,完全不懂日文,更不知道「赫赫有名的年輕人」就是「赫若」的日文字義。再者,父親也算成名得早,會取自同期間知名作家的名字作為筆名,在我看來並不合理。
我覺得很多事情要還原到那個年代的情境來看,不能理所當然的用我們現在的認知來推斷。外界也曾傳說,辜顏碧霞女士曾駕車載父親逃亡時,看到路旁有警察,辜顏女士就跟父親講說:「你趕快開我的車先跑。」這段坊間的傳聞,我個人覺得並不真實,還原到七十幾年前的情境,汽車是很稀有的東西,會開車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我不太相信父親會開車,跟舅舅、六叔等長輩聊過父親,從未聽他們說過父親會開車。
以上內容節錄自《黯到盡處,看見光:臺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紀錄》魏吟冰等採訪、撰稿.臺中市政府文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