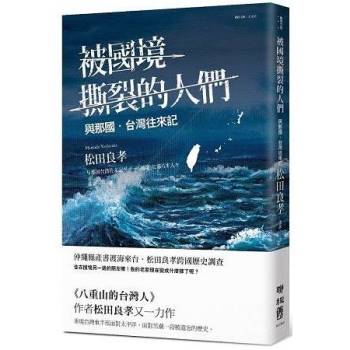第一章 往台灣
松川政良前往蘇澳南方之前,原本住在台北。他從與那國島渡海來到台北,投靠住在那裡的姊姊千代(1913年生)。憑藉著自己的力量,他開始找尋工作。當時的台北市中心原本是被城牆所環繞著,在城牆內側的地區,一般稱之為「城內」;政良就在城內的某處,發現了一家掛著「誠徵學徒」字樣的照相館。
台灣最大的都市—─台北,共有人口二十七萬六千人。千代在台北靠著幫傭過日子,並且將弟弟政良接了過來。
在與那國島上,可沒有什麼好工作的地方哪!除了村公所、郵局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地方是可以穩定工作拿薪水的,所以大家都是學校一畢業之後,就馬上跑去台灣;畢竟若是到台灣的話,不管怎樣總會有工作可做吧!於是,前輩們都陸陸續續跑過去(台灣)了吧?託他們的照料,我們也找到工作、並且定居下來了哪!
在島上讀完學業之後便前往台灣;在台灣那裡,有同樣出身自島上的哥哥姊姊、還有前輩。仰仗這些前輩照顧的弟弟妹妹以及晚輩,陸陸續續渡海前來。戰前的與那國島,就是這樣的一幅人群流動景象。
政良工作的照相館雖然沒給薪水也沒有零用錢,不過因為吃住免費的關係,生活還算過得去。至於衣服方面,也有千代幫忙張羅。只是,政良偶爾還是會想出門遠行。這時,他會試著跟老闆說「我想去基隆玩一趟」,然後老闆就會給他五十錢。按照政良的記憶,台北基隆間的火車票是單趟二十二錢,因此五十錢要用於往返,可說相當足夠了。老闆所提供的,就是這樣一筆五十錢。
從台北到基隆的距離是二十八點六公里。說起基隆,它的人口規模僅次於台北、台南,是台灣第三大的都市,人口在1933(昭和8年)年底,共有八萬一千人。
政良之所以想去基隆,其實是有理由的。「基隆有旅社和賓館,有很多朋友和親戚都在那裡。」為什麼與那國島的人會大量聚集在基隆呢?這點從方才政良所說的「與那國島沒什麼工作」,就可以得到解答。
在照相館裡落腳下來、並且開始工作的政良,為了送相片,必須要會騎腳踏車才行;可是,就在他努力練習著踩踏板的時候,卻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當時,新手上路的政良把自行車逆向騎上馬路,結果被一輛摩托車給撞飛了出去,所幸的是沒有生命危險,就連手腳也沒有骨折。
摩托車的駕駛破口大罵:
「人家在路上走,你從旁邊衝出來是怎樣啊!?」
「是我不對,因為我才剛學騎腳踏車、還不是很熟悉,真的很抱歉,是我不對……」
看見政良老實認錯後,摩托車也就自顧自地走掉了。
這時候的政良以現在來說,大概是國三到高一的年齡吧。照理想來,這個年紀才開始騎腳踏車似乎有點遲,不過想到政良在渡台之前,在與那國島上完全沒有看過腳踏車,這樣一想似乎又覺得不會太遲了。
這時期,在石垣島發行的報紙《先島朝日新聞》上,刊載了這樣兩則腳踏車店開店的廣告:
來自台灣、擁有長年經驗的熟練職人,秉持責任與忠誠,在此誠摯為您服務!(1934年6月21日刊)
來自台灣的專門熟練職人!這格外優秀的技術,請務必親身體驗一下!(1934年10月30日刊)
由上面可以清楚得知,在石垣島,「台灣」兩字可說是腳踏車店的一大「賣點」。政良就是在這樣的台灣,第一次遇見了腳踏車。
台灣經驗
那麼,從蘇澳南方回到與那國島祖納老家的政良,他後來又怎麼了呢?
政良現在住在石垣市大川,筆者曾經三度前往他的家中進行訪談。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2008年12月,當時周圍的人告訴我說「他有點重聽」;確實,在訪談過程中,筆者不時都得提高分貝才行。
不過,政良的聲音很洪亮、清晰,很容易聽得清楚。一想到他已經是超過九十歲的人瑞,筆者便不禁脫口而出:「您可真是活力充沛哪!」當我這樣說之後,政良便答道:「雖然有因為神經痛入院過一週啦,不過倒是沒因為內臟什麼的入過院;我可是很健康的唷!」政良在七十一歲那年、也就是1990年的6月,參加了第七屆九州Masters陸上競技選手權‧沖繩Masters十週年紀念大會的一百公尺競賽,跑出了十七秒八的成績,在70至74歲組中名列第一,體格依然健壯如昔。
這強而有力的說話聲,應該也是從年輕時候便一路持續至今的吧!緊接著,政良在訪談中,回想起自己服兵役時的樣子:
長官問說「有會騎腳踏車的人嗎!」的時候,應道「是」舉起手來的人,就只有我一個。
回到島上,跟父親津久利一起耕作的政良,在1936年,也就是二十歲的時候,遭到了徵兵。然後,長官問了這樣一句:「有會騎腳踏車的人嗎!」我想,當時政良回答的這聲「是」,一定也是洪亮而清晰的吧!那舉起的右手,一定也是堅定有力,讓人看得一清二楚吧!
可是,舉手答應後不久,政良心中立刻浮現起「這下麻煩大了」的念頭。舉起手的,就只有政良一個,其他一起從八重山出身的新兵,則全都沉默以對。「那時,我往後一看,發現沒有任何人跟著舉手,我就心想『哎呀,這下糟了,果然還是保持沉默比較好哪!』」出乎意料成為眾人焦點,總會讓人感到侷促不安。可是,政良只是笑著說:「這讓我莫名感覺自己好像生在大東京的人一樣,頗有地位哪!」完全沒有任何不好的感覺。
政良的回想又繼續下去。「那個時候,沖繩也好、八重山也好,都沒有腳踏車吧?所以,只有待過台灣的我會騎車。」事實上,雖然數量很少,但不能說就沒有腳踏車,只是在八重山要學會騎腳踏車,這機會可說是少之又少吧!
為大家提點一下記憶,政良學會騎腳踏車,是在他寄居台北市大和町市田照相館時候的事。對政良來說,這段「台灣經驗」,不只足以自豪,同時也是區分他與其他不曾去過台灣的人的深刻烙印。正因為這輛腳踏車,他在徵兵時才會如此響亮地回答「是」。
徵兵與殖民地台灣,在政良的心中,透過腳踏車連結在一起。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項連結兩者的東西,那就是公共運輸工具。
政良雖然被分配到熊本的部隊,但從與那國到那裡,必須歷經一段相當漫長的旅程。據政良自己的說法,「到熊本,得要花上一個月又好幾天的時間。」從與那國到石垣、沖繩本島、奄美大島、鹿兒島,沿路必須一再換船,然後還得搭火車前往熊本。在與那國島事先排好行程,買好船票和火車票才出發,根本是沒指望的事,只能到一站後,再找下一站的交通工具。等換搭的船一等就是幾天,也不是什麼稀罕的事。
就這樣,等政良好不容易抵達熊本、前去部隊報到時,才知道他所配屬的部隊,已經動身前往中國大陸了。
就在政良被徵兵的前一年,亦即1937年,爆發了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正式展開。大城正次因為蘆溝橋事變,被迫留在蘇澳南方;比他年長五歲的政良,則因為分毫之差,躲過了被派往戰地的命運。
熊本方面似乎做了判斷,認為不能只派政良一人前往戰地,所以政良不久之後,便帶著一筆旅費,踏上了返鄉之途。
回去的路上,政良並沒有循著來時的道路,而是從熊本一路北上。若是抵達門司,就能前往基隆。政良搭上了大阪商船的神戶—基隆定期船。他所搭乘的是客貨船「高千穗丸」(總噸數8154噸),1934年1月剛建造完成;九年後的1943年3月,它在基隆北方的彭佳嶼遭到魚雷擊沉,不過此時的政良,當然無從得知這艘船後來的命運。
從與那國經九州再往台灣的政良,對這趟大旅行是這樣說的:
我從鹿兒島到熊本,再從熊本到門司、下關。哎呀,那種電車(應為「列車」),老早就習慣了不是嗎?我從學校畢業之後,馬上就到了台灣、台北;搭交通工具的訓練,也是學校一畢業,馬上就在台北學到了。畢竟假日的時候,我總是台北基隆、基隆台北這樣來回遊玩嘛!
在台灣搭慣列車的經驗,結果在九州派上了用場。明明是出身和船淵源甚深的與那國島,但政良卻沒有特別提起海路,反而是說起了鐵路的事。
徵兵與殖民地台灣的體驗,在政良的心中,透過「列車」這種交通工具,密切地結合在一起。
第二章 蘇澳南方的琉球人
裡南方 消失的琉球人聚落
那麼,讓我們轉換話題,來談談「消失的琉球人聚落」吧!
這個聚落被稱為「裡南方」,它的痕跡一直到1955年都還留存在蘇澳南方的一角。當地有一座被稱為「猴猴池」的池子,沿著池子周圍有道路可通,家家戶戶就沿著道路兩旁林立。
我向兩位在裡南方出生長大的人物,詢問了當時琉球人聚落的樣貌。
上原吉助出生於1928年,是在裡南方經營雜貨店的父親吉三和母親阿夫的兒子。吉三和阿夫都是出身自現在的豐見城市平良地區。就在上原家位於裡南方的自宅附近,另外住著一位1929年出生的台灣人黃春生。現在,吉助住在那霸市,春生則留在蘇澳南方,兩人仍然保持著相當良好的友情。
「那邊有池子和道路,我家在這邊。這邊有片果樹園……」當我向春生詢問裡南方的模樣時,他一邊用筆記紙描繪著當時的情境,一邊不住說明著。對於果樹園,吉助也有很深的記憶:
我總是會進到黃先生的家中,偷吃他們家的蓮霧和龍眼。但是,對方(春生)的父母親從來沒有趕過我。我也會撿熟透了的香蕉來吃。其實不只是我,琉球人的孩子們都會這樣做,只是我做得比較過分就是了—當時真是承蒙他們關照了。
吉助也一邊說明,一邊描繪著裡南方的地圖。那片他常去偷蓮霧和龍眼的果園,是位在池子邊緣之處。沿著池子有道路可通,當地的家戶便是面向道路林立著。試著對照現在的景物後,我們可以發現,在逼近西側和北側之處,都是足以稱為崖壁的險峻地形;在這險坡和池子之間,主要居住著台灣人。池子的南側是丘陵,翻越丘陵就可以抵達海洋。從池子往北邊有一條蜿蜒小河,它的盡頭也是大海。
據說,來自沖繩的人們主要居住的地點是在池子的南側和東側。當舉出住在那裡的人們姓名時,可以發現「上原」、「渡慶次」、「與那嶺」、「玉城」之類的姓氏;這些都是沖繩地方相當普遍的姓氏。「沖繩的人,住在那裡的一定有十戶。」吉助如此回想著。
沖繩漁民村
在本書112至116頁中,我曾經為了獲知沖繩人在蘇澳南方的活動軌跡,而試著閱讀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以及加拿大出身的傳教士馬偕在殖民地時期以前所寫下的日記,但結果並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另一方面,針對居住在裡南方的沖繩相關人士做出證言的吉助和春生,則都是昭和誕生的人物。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試著從連結樺山/馬偕日記,到吉助/春生證言的這一時期,也就是殖民統治開始之後的明治、大正時期的蘇澳南方,來探尋沖繩出身者的影跡吧!
根據台北州蘇澳郡蘇澳庄於1935年發行的《蘇澳南方澳水道誌》所述,「領台後移居的三十餘戶沖繩漁民,在此地形成漁夫部落,但因部落中央有稱為『猴猴池』的水池,所以幾乎沒有耕地可言。」儘管詳細時期不明,不過確實記載了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之後,沖繩漁民居住於蘇澳南方的事實。從「漁夫部落」中央有池子這點,也可以清楚判斷此誌所指的正是裡南方。
從一份在太平洋戰爭結束一年前、亦即1944年所撰寫,有關蘇澳南方的報告中,也可以窺見在明治時期,確實有相當數量的沖繩出身者居住在裡南方地區。這份報告是由文化人類學者國分直一於同年9月執筆寫就,名為〈海邊民族雜記(一)—蘇澳郡南方澳〉。國分在1943年5月被聘任為台北師範學校本科教授,不過在第二年,亦即1944年3月,因為軍事訓練的緣故被動員到蘇澳。他利用訓練的空檔進行對蘇澳南方的調查,並將這份報告寄到了雜誌《民俗台灣》的四卷十二號上。
國分在這篇報告中,設下了一項名為「沖繩漁民村」的子題。在討論沖繩漁民時,他是這樣寫的:「在蘇澳郡南方澳,也有據稱是三十餘年前到來的漁民。」1944年的三十餘年前,指的就是1910年前後;換言之,在這個時候,沖繩的漁民就已經定居在蘇澳南方了。
蘇澳的沖繩漁民
1920年10月發行的《台灣水產雜誌》58號上,刊載了一篇以自沖繩移居蘇澳的漁民為主題的文章。這是在蘇澳興建成為漁港之前的大正時期,對當地沖繩出身者的珍貴記錄。由於內容相當有意思,故茲全文引用如下:
〈沖繩漁夫〉
在本島的鮮魚供給方面,沖繩人可說居功厥偉,特別是台灣東部的鮮魚,過半數都是由沖繩人所供給。記者某日前往蘇澳某先生的居所探訪,那是一間寬度不過兩、三間(譯註:即三、四公尺。)的陋屋,一家三四口人,正團聚在一起邊喝泡盛(譯註:沖繩產的燒酒。),邊打嘴鼓:
「嘿!咱每年都會寄上一百五、六十圓回老家哪!你問魚是嗎?咱們捕的魚都是些沒什麼好提的貨色哪!鮪魚、鯔魚、鰆魚、蝦、九孔,有什麼就捕什麼哪!
一天捕多少?就只有這樣一點點哪!多的時候二三十圓,少的時候只有兩三圓。就像你看到的,因為只能用那條小舟上場,所以天氣稍微壞一點,就只能在家裡邊咕嘟咕嘟喝泡盛,邊休息了哪!嘿!你問捕魚的場所嗎?那場所可了不起啦!在浪速的旁邊有片好淺灘,灘裡能捕到的鮪魚可多了哪!」
講到「我們」(私たち)時,用「咱們」(わっちたち)自稱的沖繩人,到現在還是很常見。當筆者在進行訪談時,裡面原本使用了很多沖繩的方言,不過我盡可能地將它們翻譯成共通語言,然後在做為小道具登場的泡盛助勢下,醞釀出那種屬於沖繩的獨特氛圍。海況不好就不出港打漁、躲起來喝泡盛的「海人」(譯註:原文為「ウミンチュ」,漢字寫做「海人」,是沖繩語對漁夫的稱呼。),這幅畫面難免會讓人感覺有些不太正經,但確實傳達了相當珍貴的情報。
松川政良前往蘇澳南方之前,原本住在台北。他從與那國島渡海來到台北,投靠住在那裡的姊姊千代(1913年生)。憑藉著自己的力量,他開始找尋工作。當時的台北市中心原本是被城牆所環繞著,在城牆內側的地區,一般稱之為「城內」;政良就在城內的某處,發現了一家掛著「誠徵學徒」字樣的照相館。
台灣最大的都市—─台北,共有人口二十七萬六千人。千代在台北靠著幫傭過日子,並且將弟弟政良接了過來。
在與那國島上,可沒有什麼好工作的地方哪!除了村公所、郵局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地方是可以穩定工作拿薪水的,所以大家都是學校一畢業之後,就馬上跑去台灣;畢竟若是到台灣的話,不管怎樣總會有工作可做吧!於是,前輩們都陸陸續續跑過去(台灣)了吧?託他們的照料,我們也找到工作、並且定居下來了哪!
在島上讀完學業之後便前往台灣;在台灣那裡,有同樣出身自島上的哥哥姊姊、還有前輩。仰仗這些前輩照顧的弟弟妹妹以及晚輩,陸陸續續渡海前來。戰前的與那國島,就是這樣的一幅人群流動景象。
政良工作的照相館雖然沒給薪水也沒有零用錢,不過因為吃住免費的關係,生活還算過得去。至於衣服方面,也有千代幫忙張羅。只是,政良偶爾還是會想出門遠行。這時,他會試著跟老闆說「我想去基隆玩一趟」,然後老闆就會給他五十錢。按照政良的記憶,台北基隆間的火車票是單趟二十二錢,因此五十錢要用於往返,可說相當足夠了。老闆所提供的,就是這樣一筆五十錢。
從台北到基隆的距離是二十八點六公里。說起基隆,它的人口規模僅次於台北、台南,是台灣第三大的都市,人口在1933(昭和8年)年底,共有八萬一千人。
政良之所以想去基隆,其實是有理由的。「基隆有旅社和賓館,有很多朋友和親戚都在那裡。」為什麼與那國島的人會大量聚集在基隆呢?這點從方才政良所說的「與那國島沒什麼工作」,就可以得到解答。
在照相館裡落腳下來、並且開始工作的政良,為了送相片,必須要會騎腳踏車才行;可是,就在他努力練習著踩踏板的時候,卻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當時,新手上路的政良把自行車逆向騎上馬路,結果被一輛摩托車給撞飛了出去,所幸的是沒有生命危險,就連手腳也沒有骨折。
摩托車的駕駛破口大罵:
「人家在路上走,你從旁邊衝出來是怎樣啊!?」
「是我不對,因為我才剛學騎腳踏車、還不是很熟悉,真的很抱歉,是我不對……」
看見政良老實認錯後,摩托車也就自顧自地走掉了。
這時候的政良以現在來說,大概是國三到高一的年齡吧。照理想來,這個年紀才開始騎腳踏車似乎有點遲,不過想到政良在渡台之前,在與那國島上完全沒有看過腳踏車,這樣一想似乎又覺得不會太遲了。
這時期,在石垣島發行的報紙《先島朝日新聞》上,刊載了這樣兩則腳踏車店開店的廣告:
來自台灣、擁有長年經驗的熟練職人,秉持責任與忠誠,在此誠摯為您服務!(1934年6月21日刊)
來自台灣的專門熟練職人!這格外優秀的技術,請務必親身體驗一下!(1934年10月30日刊)
由上面可以清楚得知,在石垣島,「台灣」兩字可說是腳踏車店的一大「賣點」。政良就是在這樣的台灣,第一次遇見了腳踏車。
台灣經驗
那麼,從蘇澳南方回到與那國島祖納老家的政良,他後來又怎麼了呢?
政良現在住在石垣市大川,筆者曾經三度前往他的家中進行訪談。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2008年12月,當時周圍的人告訴我說「他有點重聽」;確實,在訪談過程中,筆者不時都得提高分貝才行。
不過,政良的聲音很洪亮、清晰,很容易聽得清楚。一想到他已經是超過九十歲的人瑞,筆者便不禁脫口而出:「您可真是活力充沛哪!」當我這樣說之後,政良便答道:「雖然有因為神經痛入院過一週啦,不過倒是沒因為內臟什麼的入過院;我可是很健康的唷!」政良在七十一歲那年、也就是1990年的6月,參加了第七屆九州Masters陸上競技選手權‧沖繩Masters十週年紀念大會的一百公尺競賽,跑出了十七秒八的成績,在70至74歲組中名列第一,體格依然健壯如昔。
這強而有力的說話聲,應該也是從年輕時候便一路持續至今的吧!緊接著,政良在訪談中,回想起自己服兵役時的樣子:
長官問說「有會騎腳踏車的人嗎!」的時候,應道「是」舉起手來的人,就只有我一個。
回到島上,跟父親津久利一起耕作的政良,在1936年,也就是二十歲的時候,遭到了徵兵。然後,長官問了這樣一句:「有會騎腳踏車的人嗎!」我想,當時政良回答的這聲「是」,一定也是洪亮而清晰的吧!那舉起的右手,一定也是堅定有力,讓人看得一清二楚吧!
可是,舉手答應後不久,政良心中立刻浮現起「這下麻煩大了」的念頭。舉起手的,就只有政良一個,其他一起從八重山出身的新兵,則全都沉默以對。「那時,我往後一看,發現沒有任何人跟著舉手,我就心想『哎呀,這下糟了,果然還是保持沉默比較好哪!』」出乎意料成為眾人焦點,總會讓人感到侷促不安。可是,政良只是笑著說:「這讓我莫名感覺自己好像生在大東京的人一樣,頗有地位哪!」完全沒有任何不好的感覺。
政良的回想又繼續下去。「那個時候,沖繩也好、八重山也好,都沒有腳踏車吧?所以,只有待過台灣的我會騎車。」事實上,雖然數量很少,但不能說就沒有腳踏車,只是在八重山要學會騎腳踏車,這機會可說是少之又少吧!
為大家提點一下記憶,政良學會騎腳踏車,是在他寄居台北市大和町市田照相館時候的事。對政良來說,這段「台灣經驗」,不只足以自豪,同時也是區分他與其他不曾去過台灣的人的深刻烙印。正因為這輛腳踏車,他在徵兵時才會如此響亮地回答「是」。
徵兵與殖民地台灣,在政良的心中,透過腳踏車連結在一起。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項連結兩者的東西,那就是公共運輸工具。
政良雖然被分配到熊本的部隊,但從與那國到那裡,必須歷經一段相當漫長的旅程。據政良自己的說法,「到熊本,得要花上一個月又好幾天的時間。」從與那國到石垣、沖繩本島、奄美大島、鹿兒島,沿路必須一再換船,然後還得搭火車前往熊本。在與那國島事先排好行程,買好船票和火車票才出發,根本是沒指望的事,只能到一站後,再找下一站的交通工具。等換搭的船一等就是幾天,也不是什麼稀罕的事。
就這樣,等政良好不容易抵達熊本、前去部隊報到時,才知道他所配屬的部隊,已經動身前往中國大陸了。
就在政良被徵兵的前一年,亦即1937年,爆發了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正式展開。大城正次因為蘆溝橋事變,被迫留在蘇澳南方;比他年長五歲的政良,則因為分毫之差,躲過了被派往戰地的命運。
熊本方面似乎做了判斷,認為不能只派政良一人前往戰地,所以政良不久之後,便帶著一筆旅費,踏上了返鄉之途。
回去的路上,政良並沒有循著來時的道路,而是從熊本一路北上。若是抵達門司,就能前往基隆。政良搭上了大阪商船的神戶—基隆定期船。他所搭乘的是客貨船「高千穗丸」(總噸數8154噸),1934年1月剛建造完成;九年後的1943年3月,它在基隆北方的彭佳嶼遭到魚雷擊沉,不過此時的政良,當然無從得知這艘船後來的命運。
從與那國經九州再往台灣的政良,對這趟大旅行是這樣說的:
我從鹿兒島到熊本,再從熊本到門司、下關。哎呀,那種電車(應為「列車」),老早就習慣了不是嗎?我從學校畢業之後,馬上就到了台灣、台北;搭交通工具的訓練,也是學校一畢業,馬上就在台北學到了。畢竟假日的時候,我總是台北基隆、基隆台北這樣來回遊玩嘛!
在台灣搭慣列車的經驗,結果在九州派上了用場。明明是出身和船淵源甚深的與那國島,但政良卻沒有特別提起海路,反而是說起了鐵路的事。
徵兵與殖民地台灣的體驗,在政良的心中,透過「列車」這種交通工具,密切地結合在一起。
第二章 蘇澳南方的琉球人
裡南方 消失的琉球人聚落
那麼,讓我們轉換話題,來談談「消失的琉球人聚落」吧!
這個聚落被稱為「裡南方」,它的痕跡一直到1955年都還留存在蘇澳南方的一角。當地有一座被稱為「猴猴池」的池子,沿著池子周圍有道路可通,家家戶戶就沿著道路兩旁林立。
我向兩位在裡南方出生長大的人物,詢問了當時琉球人聚落的樣貌。
上原吉助出生於1928年,是在裡南方經營雜貨店的父親吉三和母親阿夫的兒子。吉三和阿夫都是出身自現在的豐見城市平良地區。就在上原家位於裡南方的自宅附近,另外住著一位1929年出生的台灣人黃春生。現在,吉助住在那霸市,春生則留在蘇澳南方,兩人仍然保持著相當良好的友情。
「那邊有池子和道路,我家在這邊。這邊有片果樹園……」當我向春生詢問裡南方的模樣時,他一邊用筆記紙描繪著當時的情境,一邊不住說明著。對於果樹園,吉助也有很深的記憶:
我總是會進到黃先生的家中,偷吃他們家的蓮霧和龍眼。但是,對方(春生)的父母親從來沒有趕過我。我也會撿熟透了的香蕉來吃。其實不只是我,琉球人的孩子們都會這樣做,只是我做得比較過分就是了—當時真是承蒙他們關照了。
吉助也一邊說明,一邊描繪著裡南方的地圖。那片他常去偷蓮霧和龍眼的果園,是位在池子邊緣之處。沿著池子有道路可通,當地的家戶便是面向道路林立著。試著對照現在的景物後,我們可以發現,在逼近西側和北側之處,都是足以稱為崖壁的險峻地形;在這險坡和池子之間,主要居住著台灣人。池子的南側是丘陵,翻越丘陵就可以抵達海洋。從池子往北邊有一條蜿蜒小河,它的盡頭也是大海。
據說,來自沖繩的人們主要居住的地點是在池子的南側和東側。當舉出住在那裡的人們姓名時,可以發現「上原」、「渡慶次」、「與那嶺」、「玉城」之類的姓氏;這些都是沖繩地方相當普遍的姓氏。「沖繩的人,住在那裡的一定有十戶。」吉助如此回想著。
沖繩漁民村
在本書112至116頁中,我曾經為了獲知沖繩人在蘇澳南方的活動軌跡,而試著閱讀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以及加拿大出身的傳教士馬偕在殖民地時期以前所寫下的日記,但結果並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另一方面,針對居住在裡南方的沖繩相關人士做出證言的吉助和春生,則都是昭和誕生的人物。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試著從連結樺山/馬偕日記,到吉助/春生證言的這一時期,也就是殖民統治開始之後的明治、大正時期的蘇澳南方,來探尋沖繩出身者的影跡吧!
根據台北州蘇澳郡蘇澳庄於1935年發行的《蘇澳南方澳水道誌》所述,「領台後移居的三十餘戶沖繩漁民,在此地形成漁夫部落,但因部落中央有稱為『猴猴池』的水池,所以幾乎沒有耕地可言。」儘管詳細時期不明,不過確實記載了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之後,沖繩漁民居住於蘇澳南方的事實。從「漁夫部落」中央有池子這點,也可以清楚判斷此誌所指的正是裡南方。
從一份在太平洋戰爭結束一年前、亦即1944年所撰寫,有關蘇澳南方的報告中,也可以窺見在明治時期,確實有相當數量的沖繩出身者居住在裡南方地區。這份報告是由文化人類學者國分直一於同年9月執筆寫就,名為〈海邊民族雜記(一)—蘇澳郡南方澳〉。國分在1943年5月被聘任為台北師範學校本科教授,不過在第二年,亦即1944年3月,因為軍事訓練的緣故被動員到蘇澳。他利用訓練的空檔進行對蘇澳南方的調查,並將這份報告寄到了雜誌《民俗台灣》的四卷十二號上。
國分在這篇報告中,設下了一項名為「沖繩漁民村」的子題。在討論沖繩漁民時,他是這樣寫的:「在蘇澳郡南方澳,也有據稱是三十餘年前到來的漁民。」1944年的三十餘年前,指的就是1910年前後;換言之,在這個時候,沖繩的漁民就已經定居在蘇澳南方了。
蘇澳的沖繩漁民
1920年10月發行的《台灣水產雜誌》58號上,刊載了一篇以自沖繩移居蘇澳的漁民為主題的文章。這是在蘇澳興建成為漁港之前的大正時期,對當地沖繩出身者的珍貴記錄。由於內容相當有意思,故茲全文引用如下:
〈沖繩漁夫〉
在本島的鮮魚供給方面,沖繩人可說居功厥偉,特別是台灣東部的鮮魚,過半數都是由沖繩人所供給。記者某日前往蘇澳某先生的居所探訪,那是一間寬度不過兩、三間(譯註:即三、四公尺。)的陋屋,一家三四口人,正團聚在一起邊喝泡盛(譯註:沖繩產的燒酒。),邊打嘴鼓:
「嘿!咱每年都會寄上一百五、六十圓回老家哪!你問魚是嗎?咱們捕的魚都是些沒什麼好提的貨色哪!鮪魚、鯔魚、鰆魚、蝦、九孔,有什麼就捕什麼哪!
一天捕多少?就只有這樣一點點哪!多的時候二三十圓,少的時候只有兩三圓。就像你看到的,因為只能用那條小舟上場,所以天氣稍微壞一點,就只能在家裡邊咕嘟咕嘟喝泡盛,邊休息了哪!嘿!你問捕魚的場所嗎?那場所可了不起啦!在浪速的旁邊有片好淺灘,灘裡能捕到的鮪魚可多了哪!」
講到「我們」(私たち)時,用「咱們」(わっちたち)自稱的沖繩人,到現在還是很常見。當筆者在進行訪談時,裡面原本使用了很多沖繩的方言,不過我盡可能地將它們翻譯成共通語言,然後在做為小道具登場的泡盛助勢下,醞釀出那種屬於沖繩的獨特氛圍。海況不好就不出港打漁、躲起來喝泡盛的「海人」(譯註:原文為「ウミンチュ」,漢字寫做「海人」,是沖繩語對漁夫的稱呼。),這幅畫面難免會讓人感覺有些不太正經,但確實傳達了相當珍貴的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