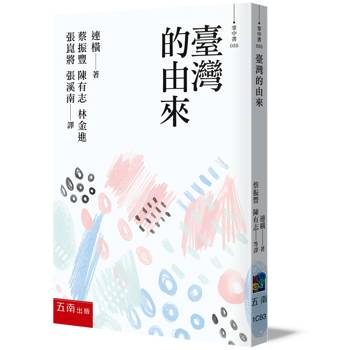一、開闢篇
臺灣原來是大陸東邊土番所居之處,地屬南方江漢蠻夷之境。其地形中間是層疊
的山巒,四面為海洋所環繞。自上古洪荒以來,此地與文明世界隔絕,土番頭上結著椎形的髮髻,千百人自成一個聚落,裸袒上身,以束腰的衣裙蔽體,射殺飛禽、追逐野獸,彷彿生活在上古遊牧的時代。以今日所出土的石器考古,文化的起源遠在五千年以前,而高山土番的生活方式,猶在原始的階段,由於沒有文獻可以考察徵引,所以飽學的知識分子也很難對臺灣有所說明。
古書中的臺灣依《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秦始皇曾命令徐福尋訪海上三神山,徐福出海後卻沒有回來。《史記.封禪書》也記載戰國時齊威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訪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三神山相傳在渤海中,訪求的人出海不久,就遇到了災難,船被海風牽引失去航向。據曾經到訪三神山的人所言,三神山上有許多仙人及不死的藥,所有的東西與禽獸都呈白色,而宮殿樓臺都以黃金白銀建造。從船上遠望,可以看到神山如雪白的雲;船靠近時,反而覺得神山處於水下;眼看快接近時,又有海風將船吹離,最後始終到達不了。由於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及,常使當世的君主心有不甘。至秦始皇併吞天下後,到過海上並提及三神山的方士,多到難以計算。秦始皇認為難以親自到達海上神山,所以使人帶著三百童男、童女作為贈禮,出海求訪三神山。出海的人都藉口說:船到海上受海風影響而無法駕馭,只能望見神山而無法到達。有人說:三神山中的蓬萊、方丈即是今日的日本、琉球,而瀛洲則是臺灣。這樣的話雖然空虛而沒有根據,但也有合理之處,因為古人的航海技術不夠精進,又少有人至海外探險,因此會將虛無飄渺的現象視為仙境,這是固陋寡識的結果。臺灣與日本、琉球的位置像三角形鼎立於東海。地理與氣候大致相同,山川秀美,有長春的鮮花與不枯的綠草,這在方士看來豈不就是仙境?徐福是否來過臺灣,這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可以判斷,但是日本及琉球各地都有徐福所領五百童男、童女移居的傳說,他們的後裔至今依然存在,由此推測秦代的童男、童女曾經來過臺灣,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又有人說:「澎湖」即是古代《列子》所說的「方壺」,而「臺灣」即是「岱
員」,這是由於二者的語音相近的原故。《列子.湯問》中記載夏革的話,說:「渤海的東方,不知幾億萬里遠的地方有大海,大海中有深不見底的谷地,由於海下無底,所以稱為歸虛。歸虛海中有五座山,分別叫做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
這五座山高低環繞一周,長有三萬里;山的頂端,高有九千里;山與山之間,相距有七萬里。由於這五座山的地基與地底不相連接,所以常隨波潮的上下、往還而浮動,即使在很短的時間內,也不能屹立在相同的位置上。山上的仙聖困擾於居所漂流不定,因此上訴於上帝。上帝也害怕五山漂蕩到極西之處,而使群聖無法在此居住,因此命令北方之神禺疆驅使十五隻巨鰲以頭頂著五山,巨鰲合力承受重量,經過三次才能一起負載五山,經過六萬年之後,五山才有固定不動的聳立位置。」澎湖與臺灣接近,周遭有大海相隔,黑潮流經,風浪波濤噴射湧起,瞬息萬變,其間有無底的海溝,如果遇颶風,航船像落入海底深陷之處不再回流,所以稱之為落漈;又海水向東流去,常使船隻難以控制而迷失航向,猶如被風引動,古書因此而說「風輒引去」。臺灣的山岳,最高有到海拔一萬三千六百餘尺,是東洋群山的高峰,山上長年積雪,
形狀如白玉,所以古書上說「望之如雲」。又有人說:臺灣是《漢書.地理志》所說的東鯷;《後漢書.東夷傳》說:「會稽郡(轄境約在今日江蘇省南部、上海市西部、浙江省、福建省地區)的外海有東鯷人,分布成二十多國。又有夷洲、澶洲等地方,相傳秦始皇命令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訪求蓬萊神仙,徐福因為找不到蓬萊山,害怕獲罪被殺,因此移居在這兩洲。曾有會稽東冶縣人(大約在今日福建福州巿),因為航行遭到海難,受風浪牽引漂流到澶洲。澶洲的位置距離會稽很遠,也難以指明所在的方向,因此難以往來。」由這些記載推測,認為「臺灣」是古書中的「瀛洲」、「東鯷」,「澎湖」是「方壺」的說法,也有可信之處,而澎湖有人定居,時間應該遠在秦朝、漢代之間。又有人說:戰國時楚國滅了越國,越國的子孫遷居於今日福建一帶,其中也有部分的人流落海上而居留於澎湖,依此而言,澎湖與中國有交通來往已有久遠的歷史,但一直到了隋代才看得到史書的記載。
《海防考》說:「隋文帝開皇年間 (五八一—六○○) ,曾命令虎賁郎將陳稜經
營澎湖。澎湖之島屹立在大海之中,有三十六個小島環繞本島,有如官員升堂前,衙役排班站立。居民的房舍有以茅草編織成的蓬蓋,他們推舉年紀大的長者治理地方事務,以打獵和捕魚營生。澎湖地表的植栽適宜放牧牛羊,牛羊散布在山谷之中,各家都在牛羊的耳毛上作記號,以區別是誰家的牛羊。陳稜雖然招撫澎湖的人民,但居留的時間不久就離開了。」這應該是中國經營治理澎湖最早的紀錄,也是中國東進臺灣的契機。當時,中國境內少有戰亂,南北方統合為一,國家的聲勢威靈,延伸到南蠻之地。澎湖因為距離福建不遠,經由海上交通,早上出發晚間可到,因此與漳州、泉州沿海的人民,早有來往,以耕耘、捕魚交互謀生,不起事端,互不侵擾,稱得上是怡然和樂的世代。但《海防考》的說法也有錯誤,陳稜官拜虎賁中郎將的時間在隋煬帝大業三年 (六○七) ,而《海防考》說在開皇年間,二者的說法相差幾十餘年,因此這可能只是追述的說法。如果要說陳稜經營治理臺灣的事,則《隋書.東夷傳.流求國》的紀錄最為詳盡。
臺灣原來是大陸東邊土番所居之處,地屬南方江漢蠻夷之境。其地形中間是層疊
的山巒,四面為海洋所環繞。自上古洪荒以來,此地與文明世界隔絕,土番頭上結著椎形的髮髻,千百人自成一個聚落,裸袒上身,以束腰的衣裙蔽體,射殺飛禽、追逐野獸,彷彿生活在上古遊牧的時代。以今日所出土的石器考古,文化的起源遠在五千年以前,而高山土番的生活方式,猶在原始的階段,由於沒有文獻可以考察徵引,所以飽學的知識分子也很難對臺灣有所說明。
古書中的臺灣依《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秦始皇曾命令徐福尋訪海上三神山,徐福出海後卻沒有回來。《史記.封禪書》也記載戰國時齊威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訪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三神山相傳在渤海中,訪求的人出海不久,就遇到了災難,船被海風牽引失去航向。據曾經到訪三神山的人所言,三神山上有許多仙人及不死的藥,所有的東西與禽獸都呈白色,而宮殿樓臺都以黃金白銀建造。從船上遠望,可以看到神山如雪白的雲;船靠近時,反而覺得神山處於水下;眼看快接近時,又有海風將船吹離,最後始終到達不了。由於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及,常使當世的君主心有不甘。至秦始皇併吞天下後,到過海上並提及三神山的方士,多到難以計算。秦始皇認為難以親自到達海上神山,所以使人帶著三百童男、童女作為贈禮,出海求訪三神山。出海的人都藉口說:船到海上受海風影響而無法駕馭,只能望見神山而無法到達。有人說:三神山中的蓬萊、方丈即是今日的日本、琉球,而瀛洲則是臺灣。這樣的話雖然空虛而沒有根據,但也有合理之處,因為古人的航海技術不夠精進,又少有人至海外探險,因此會將虛無飄渺的現象視為仙境,這是固陋寡識的結果。臺灣與日本、琉球的位置像三角形鼎立於東海。地理與氣候大致相同,山川秀美,有長春的鮮花與不枯的綠草,這在方士看來豈不就是仙境?徐福是否來過臺灣,這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可以判斷,但是日本及琉球各地都有徐福所領五百童男、童女移居的傳說,他們的後裔至今依然存在,由此推測秦代的童男、童女曾經來過臺灣,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又有人說:「澎湖」即是古代《列子》所說的「方壺」,而「臺灣」即是「岱
員」,這是由於二者的語音相近的原故。《列子.湯問》中記載夏革的話,說:「渤海的東方,不知幾億萬里遠的地方有大海,大海中有深不見底的谷地,由於海下無底,所以稱為歸虛。歸虛海中有五座山,分別叫做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
這五座山高低環繞一周,長有三萬里;山的頂端,高有九千里;山與山之間,相距有七萬里。由於這五座山的地基與地底不相連接,所以常隨波潮的上下、往還而浮動,即使在很短的時間內,也不能屹立在相同的位置上。山上的仙聖困擾於居所漂流不定,因此上訴於上帝。上帝也害怕五山漂蕩到極西之處,而使群聖無法在此居住,因此命令北方之神禺疆驅使十五隻巨鰲以頭頂著五山,巨鰲合力承受重量,經過三次才能一起負載五山,經過六萬年之後,五山才有固定不動的聳立位置。」澎湖與臺灣接近,周遭有大海相隔,黑潮流經,風浪波濤噴射湧起,瞬息萬變,其間有無底的海溝,如果遇颶風,航船像落入海底深陷之處不再回流,所以稱之為落漈;又海水向東流去,常使船隻難以控制而迷失航向,猶如被風引動,古書因此而說「風輒引去」。臺灣的山岳,最高有到海拔一萬三千六百餘尺,是東洋群山的高峰,山上長年積雪,
形狀如白玉,所以古書上說「望之如雲」。又有人說:臺灣是《漢書.地理志》所說的東鯷;《後漢書.東夷傳》說:「會稽郡(轄境約在今日江蘇省南部、上海市西部、浙江省、福建省地區)的外海有東鯷人,分布成二十多國。又有夷洲、澶洲等地方,相傳秦始皇命令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訪求蓬萊神仙,徐福因為找不到蓬萊山,害怕獲罪被殺,因此移居在這兩洲。曾有會稽東冶縣人(大約在今日福建福州巿),因為航行遭到海難,受風浪牽引漂流到澶洲。澶洲的位置距離會稽很遠,也難以指明所在的方向,因此難以往來。」由這些記載推測,認為「臺灣」是古書中的「瀛洲」、「東鯷」,「澎湖」是「方壺」的說法,也有可信之處,而澎湖有人定居,時間應該遠在秦朝、漢代之間。又有人說:戰國時楚國滅了越國,越國的子孫遷居於今日福建一帶,其中也有部分的人流落海上而居留於澎湖,依此而言,澎湖與中國有交通來往已有久遠的歷史,但一直到了隋代才看得到史書的記載。
《海防考》說:「隋文帝開皇年間 (五八一—六○○) ,曾命令虎賁郎將陳稜經
營澎湖。澎湖之島屹立在大海之中,有三十六個小島環繞本島,有如官員升堂前,衙役排班站立。居民的房舍有以茅草編織成的蓬蓋,他們推舉年紀大的長者治理地方事務,以打獵和捕魚營生。澎湖地表的植栽適宜放牧牛羊,牛羊散布在山谷之中,各家都在牛羊的耳毛上作記號,以區別是誰家的牛羊。陳稜雖然招撫澎湖的人民,但居留的時間不久就離開了。」這應該是中國經營治理澎湖最早的紀錄,也是中國東進臺灣的契機。當時,中國境內少有戰亂,南北方統合為一,國家的聲勢威靈,延伸到南蠻之地。澎湖因為距離福建不遠,經由海上交通,早上出發晚間可到,因此與漳州、泉州沿海的人民,早有來往,以耕耘、捕魚交互謀生,不起事端,互不侵擾,稱得上是怡然和樂的世代。但《海防考》的說法也有錯誤,陳稜官拜虎賁中郎將的時間在隋煬帝大業三年 (六○七) ,而《海防考》說在開皇年間,二者的說法相差幾十餘年,因此這可能只是追述的說法。如果要說陳稜經營治理臺灣的事,則《隋書.東夷傳.流求國》的紀錄最為詳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