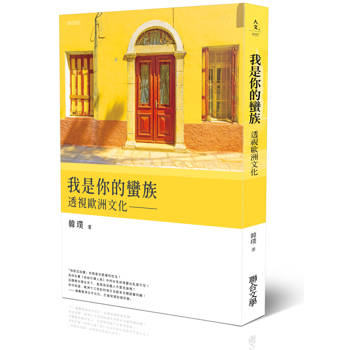來人啊,把這隻豬拖出去斬了!
故事,該從聖保羅在《羅馬書》(作於西元一世紀)第八章中的一句話說起:「萬物將掙脫腐敗的奴役,得享上帝子民的自由榮耀」。
有什麼問題嗎?
不但有,而且問題可大了!
一千三百多年後,中世紀許多神學家對著這一行字推敲琢磨,提出了一個大哉問:如果說「萬物」都是天主的子民,那麼天下除了人類之外,所有的動物也能上天堂嗎?如果有些動物可上天堂,那,有些是不是該下地獄呢?動物犯了錯該不該得到懲罰?是否應負起道德責任?牠們死後會重生嗎?
面對上述一連串提問,民間的想法可分為數派。有些學者相信除了人類以外,天堂只有鳥類(像天使一樣長了一對翅膀);有些人則認為「萬物」就是指天下所有的動物,他們回答:是的,動物有道德責任;是的,犯了錯就該受罰。基於後者的思維模式,十三至十六世紀間出現了不少審判動物的案件,法國境內有跡可循的文獻大約記載了六十起,其中又以一三八六年的法萊茲(Falaise)母豬事件最出名。
法萊茲位於諾曼第地區,十四世紀時已是一個中型城鎮,城裡有些居民自由放養家豬,隨牠們到處覓食。於是有一天悲劇發生了:一隻豬在城裡遊蕩時,咬死了一名襁褓中的新生兒。由於牠罪證確鑿,被逮捕後立即鋃鐺入獄,經過民事法庭審判後,被處以死刑。
行刑當日,法萊茲子爵親自擔任法官一職。刑台前除一般百姓之外,受害者的父親也被迫出席,藉機反省自己沒有好好保護嬰兒的過錯。許多養豬戶亦應邀帶著自家的豬群前來觀刑,以達到殺一儆百的教化作用。
由於母豬曾咬傷嬰兒的臉部和腿部,因此處決時,劊子手也秉持以牙還牙的原則,先把豬吻割下,帶上人臉面具,然後在豬腿上刺一刀,把牠倒掛在行刑台上,罪犯不久就因失血過多而死亡。行刑者隨後再象徵性地對屍體施以絞刑,拖屍繞行廣場,最後以焚屍作為了結。
法萊茲子爵為了紀錄此事,還下令在教堂中繪製大型壁畫,可惜該作在十九世紀時因翻修教堂而被粉刷銷毀了。
值得玩味的是,由於此類案件遵循聖保羅那句話的邏輯,認定動物也是道德主體,所以觸犯法律的是動物自己,失職的主人頂多罰款了事(處決動物對他來說已是一種損失)。曾有文獻明定:若某隻牛撞死路人,那麼牛主人無罪,犯法的是牛,應被亂石砸死,且其屍身不得被食用。法萊茲母豬本來是一隻肉豬,但因犯罪被判刑,所以也不能按豢養的初衷拿來食用。
審判動物的事件每幾年便發生一例,其中九成的被告均為家豬,可能因為當時豬群為數可觀,儘管各大城鎮三令五申,禁止養豬戶放任畜生在大街小巷閒逛,但是並沒起多少作用,因此家豬咬傷幼童或影響交通的事故層出不窮。十二世紀時,即將繼位的法國王儲在巴黎城中騎馬巡視,街上突然殺出一隻冒失的豬,把御駕撞得人仰馬翻,太子菲立普重傷不治而身亡,王室倉皇失措,不得不另立新的繼承人,整個法國的歷史也隨之改寫。這一切,都是因為一隻豬。
一般而言,家畜審判屬於民事,其他小型動物如老鼠、蒼蠅則歸教堂管轄。十六世紀初,某主教曾被請到巴黎東南方的一個小鎮,對著一群正在肆虐農田的蝗蟲提出嚴正警告,限牠們在六天之內全數離開,否則將……革除牠們的教籍。有效嗎?沒有,這群害蟲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沒理會這麼嚴重的威脅。
今天的我們可能會覺得這些故事很滑稽、覺得古代人真夠愚昧。其實,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係不斷在演變,每個時代的心態也不盡相同。中世紀的法國人之所以審判動物,是因為把牠們視為有道德責任的個體。到了十七世紀的啟蒙時代,理性主義的思想家一改原有立場,認為所有的動物都是沒有痛覺的生物,專供人類奴役剝削。
如今,人與動物的關係更為多元,法國當代人類學家Charles Stépanoff認為現今許多工業社會都有「動物原料」與「動物兒童」的並存現象:前者把動物視為物質原料,是人類餐盤中的肉食、身上穿的皮革毛料、實驗的對象與醫藥材料;後者把動物當成寵兒,將牠們擬人化、附屬於人類,像幼童一樣支配其生活行動。一般人大概都相信第二類動物最幸福,牠們得到人類的寵愛與呵護,每天吃飽喝足,有病痛還能就醫。事實上,這類寵物已無自主求生的本能,沒有與同類相處的社交生活,不是被強制結紮,就是無法自由養育後代,且有些品種經過「造型」改良,健康情況每下愈況(如哈巴狗的鼻子越「改良」越塌,生下來就有呼吸困難的症狀)。若站在動物的立場來看,中世紀的思維模式不見得更糟糕。審判動物的案件雖令人莞爾,但我們還是別急著嘲笑前人吧!誰知道幾百年後,未來的人類得知「二十一世紀的古人」竟給寵物穿衣戴帽,會不會也想揶揄幾句。
在此順帶提及幾年前的一則地方新聞。法國以西的Briollay小鎮曾在二○一八年夏天發布了一條市政命令,內容是「茲以昭告:即日起,本鎮嚴禁任何蚊子進入」。這是因為近年來氣候暖化經常引發蚊災,鎮民多有抱怨,束手無策的鎮長實在不勝其擾,乾脆以幽默諷刺的法令回應,與中世紀的嚴肅心態形成強烈的對照。
狼來了!狼來了!
無論是〈七隻小羊〉、〈三隻小豬〉、〈彼得與狼〉,或是〈小紅帽〉,狼在童話中永遠是同一個德性,牠面目猙獰,飢腸轆轆,想盡辦法要吃掉無辜的受害者。不過這位仁兄經常狼吞虎嚥,下了肚的人或動物往往還活著,剪開狼的肚皮後,就能把他們救出來。對聽故事的小朋友來說,狼這個角色實在太駭人了。殘忍的大人可能還會追加一句:「再不聽話,大野狼就來把你吃掉囉!」在童話的薰陶下,很多人從小就相信狼是既可怕又可恨的動物,但這種說法是否自古以來就放諸四海皆準?
當然不是,反例很多。比如創建羅馬的Romulus雙胞胎兄弟,據說就是由一頭母狼哺育長大,羅馬的城徽至今仍以「母狼乳嬰」作為畫面。各國民間也常有母狼養育人子的傳說,甚至有確切的史實紀錄。吉卜齡的小說〈叢林奇譚〉(即迪士尼的〈森林王子〉)與宮崎駿的〈魔法公主〉也都以「狼子」、「狼女」作為主人翁。可見從人的角度來看,狼也有慈眉善目的一面,扮演了兒童守護神的角色。
還有些民族自認與狼有親緣關係:蒙古人聲稱是蒼狼與白鹿的後代,美洲印地安人也把狼視為大地的兄弟。遠古的先民發現人類群居與狩獵的方式近似狼群,若干民族在出獵前會飲狼血、披狼皮、配戴狼牙,以從中獲取狼族勇猛的力量。但在喬裝成野獸的過程中,人與狼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甚至出現人類以狼自居的心理狀態。狼人的傳說是否從中演變而來……?根據記載,歐洲早在西元前五世紀,就已出現狼人之說。直到十九世紀,多數百姓仍相信狼人確實存在。
在集體的思維中,狼總是天生的壞胚子,人們習慣指定由狼來擔任負面角色。兒童心理學家Bruno Bettelheim曾在一九七六年的著作(台譯《童話的魅力》)中,以另一種角度解析〈小紅帽〉的故事:小紅帽可比天真無知的少女,受到情場老手大野狼的誘惑,而狼吞食小紅帽的劇情則有如一場性侵。大野狼在故事裡扮演的角色,與我們中文裡的「色狼」一詞不謀而合。牠是兇殘狡詐、愚昧好色的懦夫,也是巫術、地獄的基本成員。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牠的形象更和希特勒與納粹重疊,比如迪士尼動畫〈三隻小豬〉一九四一年的版本,就在大野狼的手臂別上納粹的十字徽章;法國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政治漫畫《畜生死了!》(La bête est morte !)也以嗜血的狼來代表納粹。
一千多年來,人類不斷舉行大型獵殺活動,立誓將狼族趕盡殺絕。為什麼我們如此厭恨狼呢?解釋有很多種,可能在於狼與人類在食物上有所競爭,而且教會長久以各種手段醜化遠古先民崇拜的動物,再加上古代狼群為數較多、攻擊性也勝過現代狼(根據研究指出,這可能是因為過去的狂犬病比今天猖獗),在在讓人類對牠咬牙切齒。至一九九○年代初,狼幾乎已在法國消失殆盡,後來少數族群從義大利山區輾轉遷入,成為如今民間積極保育的對象。
說到這裡,似乎不能不提十八世紀的「榭沃當怪獸」一案,此事至今仍是一個謎。話說一七六四年夏,法國中南部出現多起野獸咬死鄉民的慘案,民間認定罪魁禍首是一隻巨狼,但獵捕無果,鄉間死傷人數持續增加,地方政府不斷向上級求救,最後終於鬧到朝廷,由路易十五特派專人南下除害。軍隊下鄉期間還發生過一樁搞笑事件:副官長不知從哪裡聽說「公狼貪好人間女色」之說,為了吸引狼群上鉤,他要求士兵脫下軍服,全部男扮女裝。結果呢?一群花枝招展的阿兵哥在森林裡等啊等,卻連一隻狼都沒等到!
後來他們改變策略,陸續圍剿了許多狼窟,堅信大害已除。不料將官才剛打道回府,邪惡之獸馬上復出肆虐。怪就怪在牠只攻擊人類,卻對羊群、兔子等慣常食物無動於衷。這件事鬧了三年才平息,受害者多達百人,被殺的狼更達數百隻。兩個半世紀以後的今天,法國人一提到「榭沃當怪獸」,仍免不了把傳說、電影裡的劇情串上自己的想像力,重新加油添醋一番,繪聲繪影地把巨狼形容成連環殺人兇手,再次強化了「大惡狼」的形象。
事實上,榭沃當怪獸的行徑異於一般的狼,可能不是狼,也可能是經過人為訓練的動物。但事過境遷,求證已難,大家乾脆把這筆爛帳丟給狼。歷史學家指出:劫財或強暴案的受害者經常被棄屍荒野,警方無法破案時,總習慣推卸責任,以一句「又是狼的傑作」了事,讓無辜的狼揹上黑鍋。
狼真的吃人嗎?碰上戰爭、飢荒或傳染病,狼別無選擇時,才會拿人肉濫竽充數。別忘了對肉食動物而言,獵殺行動並非血腥暴力,而是單純的求生之舉。狼很殘暴、蛇最邪惡、小白兔溫馴可愛……這些說法都是從人的觀點出發,然而想像中的動物與實際往往有一大段差距。儘管人類早就是生物界的頭號殺手,但一見到自然界弱肉強食的情景,竟然還是習慣站在受害者的一方。而且我們常忘記一件事,那就是:物種互相牽制,不可能單一存在。
美國黃石公園的案例就是絕佳的證明。美國灰狼在一九二○年代消失於黃石公園,於一九九五年重新被引入。之前由於原產的馬鹿沒了天敵,數量與日俱增,遍布國家公園各處。狼群出現後,馬鹿不得不群聚生活,不敢再單獨出沒於河岸地帶。沿岸的植被因不再被啃食、踐踏,植株得以茂盛生長,有效地保育了河床水土,避免河岸持續變寬。林木的數量與種類隨之增加,不僅為鳥類提供築巢的空間,更吸引河狸前來建造水壩,進一步為其他物種提供多樣棲地。短短的二十多年間,國家公園的地貌變得更健康、生態更平衡、更多元,狼的功勞實在不小。
對了,台灣並沒有土生的狼。
你還怕狼嗎?
法國人的梳洗史:這個東西怎麼用?
第一次看到它是一九九四年在法國找房子期間,參觀公寓時在浴室裡和它打了一個照面。此物比馬桶略矮,但和洗臉池一樣裝了冷熱水龍頭和水槽塞。我問房東夫婦:「這怎麼用?」老太太一聽吃吃笑起來,老先生愣了兩秒,才牛頭不對馬嘴地答道:「這叫bidet。」「Bidet怎麼用?」房東先生似笑非笑地「哈」了一聲,二話不說轉身走回客廳。看來此物的用途只能意會不能言傳……
我後來才得知它是專門拿來清洗私處的坐浴池,原來與下體有關的事物都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話題。有人把它譯為「坐浴桶」,但常與免治馬桶混為一談(如維基百科頁),本文選用「坐浴池」。
坐浴池是法國十八世紀初的發明,古人沒有衛生紙這種奢侈品,最徹底的清潔方式還是用水洗。此物多以木材或銅板打造而成,僅見於條件優渥的上流社會,有時還裝了絨布背墊和扶手,宛如帝王寶座。拿破崙就擁有好幾個坐浴池,走到哪裡一定帶一個在身邊,可見在十九世紀初,此物仍然男女通用。
坐浴池在誕生之初,一直與性事有關。兩性開放的十八世紀留下了許多「關起房門欣賞」的淫穢版畫、油畫,內容常圍繞著坐浴池,畫中往往有一位清洗私處的女性。久而久之,此物變得像化妝台一樣,已成為女性專屬的用品。至十九世紀中期後,坐浴池已普及至民間,並且逐漸規格化,但僅見於城市地區。
抗生素發明前,民間一致相信男性若感染梅毒,一定是因為碰上不乾淨的妓女。為了讓顧客安心,每家妓院必備坐浴池。在避孕合法化之前(一九六七年),它一直是各地青樓不可或缺的設備,除了辦事前用來清潔私處之外,許多妓女亦以之進行避孕的陰道沖洗,已婚婦女亦將之視為最唾手可得的避孕工具。正因如此,教會對於坐浴池向來非常感冒,認為許多本有可能存在的小生命都被沖洗掉了。
二十世紀初,來到法國的觀光客第一次發現坐浴池,許多人如獲至寶,爭相引入本國。有人相信免治馬桶的發明正是從坐浴池中獲得靈感,從歐洲發展到美洲後,再於日本發揚光大。二次戰後,法國家家戶戶必備一兩個坐浴池,但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很多住家在整修浴室時,決定把它一一打掉,將騰出的位置改成淋浴間或接裝洗衣機,只有義大利與西班牙仍是它的忠實擁護者。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法國人已將坐浴池視為祖父母一代的骨董級設備,如果朋友得知你家裡還有一個,定會嘖嘖稱奇。此物雖然注定消失殆盡,但少數廠商仍不死心,揚言在日本免治馬桶、伊斯蘭小淨儀式的影響下,坐浴池不久即將捲土重來。
歷史學家在考究坐浴池時,發現它常與浣腸筒同時出現。浣腸法最早可上溯至古埃及,法國自十五世紀起重新掀起浣腸熱,揭開了長達好幾個世紀的黃金年代。人們相信此法可治百病,無論是便祕、消化不良、精神不濟,甚至憂鬱煩悶、臉色蒼白,都有對症下藥的處方,由專人以錫製浣腸筒注入五百c.c.的藥水,便可立竿見影。工匠在替坐浴池打造收藏櫃時,經常在櫃裡設計置放尿壺、海綿、香水瓶與浣腸用具的收藏格,讓坐浴成為一種兼具保健與享受的日常活動。路易十四本人對此也相當推崇,文獻紀錄他一生中曾浣腸四千次。不過浣腸並非上流社會的獨家專利,也廣見於中下階級。
很多民族都相當重視如廁的問題,比如古埃人怕便祕,留下了許多研討該症狀的文獻。十七、十八世紀的法國人也很關心排便問題,甚至把它視為一大養生重點,我們從法國人平時打招呼的用語中,便可略見端倪。若把法文的Comment allez-vous ? (你好嗎?)直譯成中文,就成了「你怎樣去?」怎麼看都顯得不太對勁。其實此話是從Comment allez-vous à la selle ?(排便還好嗎?)簡化而成的。當時的人們相信「便順人也安」,若要向人問好,還不如問他的便況。若對方答:「很好,你呢?」言下之意即「我大便很順暢,所以我很好。你呢?」當然,如今的法國人在問好時,並不見得知道此話的來源。無論如何,這和我們在台灣「你吃飽了嗎?」的問候方式著實大相逕庭。
法國人真的不洗澡嗎?
一般人常有這樣一個刻板印象:「法國香水之所以名聞天下,是因為法國人都不愛洗澡。」這是真的嗎?
在某種程度上,此話確實不假,只不過要看時代背景。
中世紀的法國人其實很愛乾淨,各大城裡均建有蒸浴池,鼓勵民眾常保清潔。話雖如此,有些場所樓下男女共浴,樓上公開賣淫,為此而備受教會指責。而且黑死病於十四世紀中期橫掃歐洲以後,整個社會都十分忌憚傳染病,很多學者相信:水,就是傳播病毒的媒介,因而大力譴責洗澡的行為。史上著名的外科醫生兼御醫Ambroise Paré(一五○九~一五九○年)就曾告誡道:「泡澡水會從毛孔滲入體內,造成猝死」。既然洗澡這麼可怕,那……何必冒這麼大的風險呢?醫學界當時的良心建議是:「洗手尚可,洗腳偶爾,洗澡萬萬行不得」。
從十七世紀開始,人們不但棄絕了「不文明」的泡浴,而且儘可能不接觸水,堅信水不但「傷眼傷牙,讓面部扁平,且令人冬天怕冷、夏天變黑」,他們寧可「乾洗」,也就是用白布(一定要是白色)擦拭身體,或每天更換潔淨的白色襯衣,認為乾洗的效果等同洗澡。當然,只有富裕的上流社會才有能力經常更衣,百姓平時頂多早晨洗臉、餐前洗手,其它部位就隨遇而安了。史上許多名人一生中沒洗過幾次澡,比如不拘小節的亨利四世非但從不碰水,而且最愛吃豬腸、咬大蒜,人還沒出現,臭氣就先到了。
十八世紀以後水源獲取較易,但人們梳洗時仍僅侷限於面部、手腳與下體。法國大革命之前,上流社會崇尚放蕩主義(libertinage,並為後世留下了許多情色文學作品),衛道人士因而把梳妝和縱慾劃上等號,認為好人家的女兒不必經常梳洗,倘若非洗不可的話,那最好閉上眼睛,不去觀賞自己的裸體,也不在鏡子前更衣。整個十九世紀,教會對洗滌之舉一直抱持敵意,相信常清洗陰部會造成不孕,並生怕洗浴會成為感官的享受,讓靈魂墮入地獄。為了避免浴池中的水太過清澈、一目了然,坊間還特別販售「池水混濁粉」。直到一九二五年,由修女管轄的女工宿舍(每兩週開一次澡堂)仍規定入浴者須穿著浴袍,且只准用肥皂搓洗,不可用手觸及自己的身體。
巴黎少數公寓早在一八七○年代,便已具備水管與瓦斯系統,讓住戶能輕易享用到熱水。但直到二十世紀初,城中裝設衛浴間的住宅仍只占百分之三,很多人認為早晨盥洗時拿毛巾擦拭就夠了,如有充足的預算,他們寧可接裝電話而不願買浴缸。而且「洗澡」之舉仍離不開治療的概念,在當時被稱為「水療」,只要醫生沒開水療的處方,沒事何必去洗什麼澡!法國第八任總統盧貝曾在一九○六年帶其繼任者參觀愛麗舍宮,介紹到浴室時,他對下一任總統說:「我們雖在總統府裡修建浴室,但內人和我從來不生病,所以我們一次也沒用過。」
幾個世紀當中,鑒於特殊的意識形態與設備條件,洗澡的法國人的確少之又少。但從二次大戰開始,絕大多數住家均擁有完善的衛浴設備。倘若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在問:「法國人真的都不洗澡嗎?」那你可能太輕信刻板印象了。
古人一向在開放的公共空間梳洗,比如月神黛安娜在池中沐浴時曾被獵人阿克泰翁撞見(中國民間故事與聊齋亦有諸多類似情節),古羅馬的浴場或中世紀的蒸浴池也都是公用設施。直到十七、十八世紀初為止,在中上層家庭裡,梳洗、更衣、如廁都有僕傭在旁伺候協助。有些人甚至把梳妝沐浴視為社交行為,選在此時接見訪客,不像我們今天將這些活動視為隱私。一般住家並沒有私人空間,寢室門不見得可上鎖,家人或僕役隨時可能進出。
法國史學家Vigarello提出一個有趣的論點,他認為「隱私」與「水」的關係相當密切。從十八世紀中期起,由於水成了較易取得的資源,坐浴池一類的盥洗用具日益普及,人們梳洗時開始與外界隔離。至十九世紀以後,連僕役也被關在房門之外了。衛浴設備因民間的需求而出現,逐漸成為人人不可或缺的空間。
這一轉變不僅是住宅格局的革命,也在人們內心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沒有隱私的時代,每個人平時只面對外界,與他人溝通互動。私密的空間出現後,個人首度能脫離外在世界,靜下來面對自己、照料自己的身體,並意識到自我的存在。生活空間的變化引發了新的思維模式,隱私的概念從而誕生,不僅之於梳洗如廁時分,也在於精神上的獨處。如今,「隱私」早已成為大部分人類的基本需求。
至於toilette這個常見的字,它大約出現在十七世紀,最早指包裹梳妝用品的精緻薄布,使用時先把它鋪在桌面,再把化妝品、香瓶、鏡子與首飾置於其上。到了十七世紀晚期,此字逐漸演變為梳妝更衣等活動,直到今天仍有衣裝、梳洗、清潔之意(如淡香水eau de toilette直譯就是「梳妝水」)。如果再加上一個s,就成了廁所,英文的toilet就是從這個法文字演變而來的。在中文裡,我們不是也把如廁的地點稱為「化妝間」嗎?
故事,該從聖保羅在《羅馬書》(作於西元一世紀)第八章中的一句話說起:「萬物將掙脫腐敗的奴役,得享上帝子民的自由榮耀」。
有什麼問題嗎?
不但有,而且問題可大了!
一千三百多年後,中世紀許多神學家對著這一行字推敲琢磨,提出了一個大哉問:如果說「萬物」都是天主的子民,那麼天下除了人類之外,所有的動物也能上天堂嗎?如果有些動物可上天堂,那,有些是不是該下地獄呢?動物犯了錯該不該得到懲罰?是否應負起道德責任?牠們死後會重生嗎?
面對上述一連串提問,民間的想法可分為數派。有些學者相信除了人類以外,天堂只有鳥類(像天使一樣長了一對翅膀);有些人則認為「萬物」就是指天下所有的動物,他們回答:是的,動物有道德責任;是的,犯了錯就該受罰。基於後者的思維模式,十三至十六世紀間出現了不少審判動物的案件,法國境內有跡可循的文獻大約記載了六十起,其中又以一三八六年的法萊茲(Falaise)母豬事件最出名。
法萊茲位於諾曼第地區,十四世紀時已是一個中型城鎮,城裡有些居民自由放養家豬,隨牠們到處覓食。於是有一天悲劇發生了:一隻豬在城裡遊蕩時,咬死了一名襁褓中的新生兒。由於牠罪證確鑿,被逮捕後立即鋃鐺入獄,經過民事法庭審判後,被處以死刑。
行刑當日,法萊茲子爵親自擔任法官一職。刑台前除一般百姓之外,受害者的父親也被迫出席,藉機反省自己沒有好好保護嬰兒的過錯。許多養豬戶亦應邀帶著自家的豬群前來觀刑,以達到殺一儆百的教化作用。
由於母豬曾咬傷嬰兒的臉部和腿部,因此處決時,劊子手也秉持以牙還牙的原則,先把豬吻割下,帶上人臉面具,然後在豬腿上刺一刀,把牠倒掛在行刑台上,罪犯不久就因失血過多而死亡。行刑者隨後再象徵性地對屍體施以絞刑,拖屍繞行廣場,最後以焚屍作為了結。
法萊茲子爵為了紀錄此事,還下令在教堂中繪製大型壁畫,可惜該作在十九世紀時因翻修教堂而被粉刷銷毀了。
值得玩味的是,由於此類案件遵循聖保羅那句話的邏輯,認定動物也是道德主體,所以觸犯法律的是動物自己,失職的主人頂多罰款了事(處決動物對他來說已是一種損失)。曾有文獻明定:若某隻牛撞死路人,那麼牛主人無罪,犯法的是牛,應被亂石砸死,且其屍身不得被食用。法萊茲母豬本來是一隻肉豬,但因犯罪被判刑,所以也不能按豢養的初衷拿來食用。
審判動物的事件每幾年便發生一例,其中九成的被告均為家豬,可能因為當時豬群為數可觀,儘管各大城鎮三令五申,禁止養豬戶放任畜生在大街小巷閒逛,但是並沒起多少作用,因此家豬咬傷幼童或影響交通的事故層出不窮。十二世紀時,即將繼位的法國王儲在巴黎城中騎馬巡視,街上突然殺出一隻冒失的豬,把御駕撞得人仰馬翻,太子菲立普重傷不治而身亡,王室倉皇失措,不得不另立新的繼承人,整個法國的歷史也隨之改寫。這一切,都是因為一隻豬。
一般而言,家畜審判屬於民事,其他小型動物如老鼠、蒼蠅則歸教堂管轄。十六世紀初,某主教曾被請到巴黎東南方的一個小鎮,對著一群正在肆虐農田的蝗蟲提出嚴正警告,限牠們在六天之內全數離開,否則將……革除牠們的教籍。有效嗎?沒有,這群害蟲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沒理會這麼嚴重的威脅。
今天的我們可能會覺得這些故事很滑稽、覺得古代人真夠愚昧。其實,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係不斷在演變,每個時代的心態也不盡相同。中世紀的法國人之所以審判動物,是因為把牠們視為有道德責任的個體。到了十七世紀的啟蒙時代,理性主義的思想家一改原有立場,認為所有的動物都是沒有痛覺的生物,專供人類奴役剝削。
如今,人與動物的關係更為多元,法國當代人類學家Charles Stépanoff認為現今許多工業社會都有「動物原料」與「動物兒童」的並存現象:前者把動物視為物質原料,是人類餐盤中的肉食、身上穿的皮革毛料、實驗的對象與醫藥材料;後者把動物當成寵兒,將牠們擬人化、附屬於人類,像幼童一樣支配其生活行動。一般人大概都相信第二類動物最幸福,牠們得到人類的寵愛與呵護,每天吃飽喝足,有病痛還能就醫。事實上,這類寵物已無自主求生的本能,沒有與同類相處的社交生活,不是被強制結紮,就是無法自由養育後代,且有些品種經過「造型」改良,健康情況每下愈況(如哈巴狗的鼻子越「改良」越塌,生下來就有呼吸困難的症狀)。若站在動物的立場來看,中世紀的思維模式不見得更糟糕。審判動物的案件雖令人莞爾,但我們還是別急著嘲笑前人吧!誰知道幾百年後,未來的人類得知「二十一世紀的古人」竟給寵物穿衣戴帽,會不會也想揶揄幾句。
在此順帶提及幾年前的一則地方新聞。法國以西的Briollay小鎮曾在二○一八年夏天發布了一條市政命令,內容是「茲以昭告:即日起,本鎮嚴禁任何蚊子進入」。這是因為近年來氣候暖化經常引發蚊災,鎮民多有抱怨,束手無策的鎮長實在不勝其擾,乾脆以幽默諷刺的法令回應,與中世紀的嚴肅心態形成強烈的對照。
狼來了!狼來了!
無論是〈七隻小羊〉、〈三隻小豬〉、〈彼得與狼〉,或是〈小紅帽〉,狼在童話中永遠是同一個德性,牠面目猙獰,飢腸轆轆,想盡辦法要吃掉無辜的受害者。不過這位仁兄經常狼吞虎嚥,下了肚的人或動物往往還活著,剪開狼的肚皮後,就能把他們救出來。對聽故事的小朋友來說,狼這個角色實在太駭人了。殘忍的大人可能還會追加一句:「再不聽話,大野狼就來把你吃掉囉!」在童話的薰陶下,很多人從小就相信狼是既可怕又可恨的動物,但這種說法是否自古以來就放諸四海皆準?
當然不是,反例很多。比如創建羅馬的Romulus雙胞胎兄弟,據說就是由一頭母狼哺育長大,羅馬的城徽至今仍以「母狼乳嬰」作為畫面。各國民間也常有母狼養育人子的傳說,甚至有確切的史實紀錄。吉卜齡的小說〈叢林奇譚〉(即迪士尼的〈森林王子〉)與宮崎駿的〈魔法公主〉也都以「狼子」、「狼女」作為主人翁。可見從人的角度來看,狼也有慈眉善目的一面,扮演了兒童守護神的角色。
還有些民族自認與狼有親緣關係:蒙古人聲稱是蒼狼與白鹿的後代,美洲印地安人也把狼視為大地的兄弟。遠古的先民發現人類群居與狩獵的方式近似狼群,若干民族在出獵前會飲狼血、披狼皮、配戴狼牙,以從中獲取狼族勇猛的力量。但在喬裝成野獸的過程中,人與狼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甚至出現人類以狼自居的心理狀態。狼人的傳說是否從中演變而來……?根據記載,歐洲早在西元前五世紀,就已出現狼人之說。直到十九世紀,多數百姓仍相信狼人確實存在。
在集體的思維中,狼總是天生的壞胚子,人們習慣指定由狼來擔任負面角色。兒童心理學家Bruno Bettelheim曾在一九七六年的著作(台譯《童話的魅力》)中,以另一種角度解析〈小紅帽〉的故事:小紅帽可比天真無知的少女,受到情場老手大野狼的誘惑,而狼吞食小紅帽的劇情則有如一場性侵。大野狼在故事裡扮演的角色,與我們中文裡的「色狼」一詞不謀而合。牠是兇殘狡詐、愚昧好色的懦夫,也是巫術、地獄的基本成員。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牠的形象更和希特勒與納粹重疊,比如迪士尼動畫〈三隻小豬〉一九四一年的版本,就在大野狼的手臂別上納粹的十字徽章;法國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政治漫畫《畜生死了!》(La bête est morte !)也以嗜血的狼來代表納粹。
一千多年來,人類不斷舉行大型獵殺活動,立誓將狼族趕盡殺絕。為什麼我們如此厭恨狼呢?解釋有很多種,可能在於狼與人類在食物上有所競爭,而且教會長久以各種手段醜化遠古先民崇拜的動物,再加上古代狼群為數較多、攻擊性也勝過現代狼(根據研究指出,這可能是因為過去的狂犬病比今天猖獗),在在讓人類對牠咬牙切齒。至一九九○年代初,狼幾乎已在法國消失殆盡,後來少數族群從義大利山區輾轉遷入,成為如今民間積極保育的對象。
說到這裡,似乎不能不提十八世紀的「榭沃當怪獸」一案,此事至今仍是一個謎。話說一七六四年夏,法國中南部出現多起野獸咬死鄉民的慘案,民間認定罪魁禍首是一隻巨狼,但獵捕無果,鄉間死傷人數持續增加,地方政府不斷向上級求救,最後終於鬧到朝廷,由路易十五特派專人南下除害。軍隊下鄉期間還發生過一樁搞笑事件:副官長不知從哪裡聽說「公狼貪好人間女色」之說,為了吸引狼群上鉤,他要求士兵脫下軍服,全部男扮女裝。結果呢?一群花枝招展的阿兵哥在森林裡等啊等,卻連一隻狼都沒等到!
後來他們改變策略,陸續圍剿了許多狼窟,堅信大害已除。不料將官才剛打道回府,邪惡之獸馬上復出肆虐。怪就怪在牠只攻擊人類,卻對羊群、兔子等慣常食物無動於衷。這件事鬧了三年才平息,受害者多達百人,被殺的狼更達數百隻。兩個半世紀以後的今天,法國人一提到「榭沃當怪獸」,仍免不了把傳說、電影裡的劇情串上自己的想像力,重新加油添醋一番,繪聲繪影地把巨狼形容成連環殺人兇手,再次強化了「大惡狼」的形象。
事實上,榭沃當怪獸的行徑異於一般的狼,可能不是狼,也可能是經過人為訓練的動物。但事過境遷,求證已難,大家乾脆把這筆爛帳丟給狼。歷史學家指出:劫財或強暴案的受害者經常被棄屍荒野,警方無法破案時,總習慣推卸責任,以一句「又是狼的傑作」了事,讓無辜的狼揹上黑鍋。
狼真的吃人嗎?碰上戰爭、飢荒或傳染病,狼別無選擇時,才會拿人肉濫竽充數。別忘了對肉食動物而言,獵殺行動並非血腥暴力,而是單純的求生之舉。狼很殘暴、蛇最邪惡、小白兔溫馴可愛……這些說法都是從人的觀點出發,然而想像中的動物與實際往往有一大段差距。儘管人類早就是生物界的頭號殺手,但一見到自然界弱肉強食的情景,竟然還是習慣站在受害者的一方。而且我們常忘記一件事,那就是:物種互相牽制,不可能單一存在。
美國黃石公園的案例就是絕佳的證明。美國灰狼在一九二○年代消失於黃石公園,於一九九五年重新被引入。之前由於原產的馬鹿沒了天敵,數量與日俱增,遍布國家公園各處。狼群出現後,馬鹿不得不群聚生活,不敢再單獨出沒於河岸地帶。沿岸的植被因不再被啃食、踐踏,植株得以茂盛生長,有效地保育了河床水土,避免河岸持續變寬。林木的數量與種類隨之增加,不僅為鳥類提供築巢的空間,更吸引河狸前來建造水壩,進一步為其他物種提供多樣棲地。短短的二十多年間,國家公園的地貌變得更健康、生態更平衡、更多元,狼的功勞實在不小。
對了,台灣並沒有土生的狼。
你還怕狼嗎?
法國人的梳洗史:這個東西怎麼用?
第一次看到它是一九九四年在法國找房子期間,參觀公寓時在浴室裡和它打了一個照面。此物比馬桶略矮,但和洗臉池一樣裝了冷熱水龍頭和水槽塞。我問房東夫婦:「這怎麼用?」老太太一聽吃吃笑起來,老先生愣了兩秒,才牛頭不對馬嘴地答道:「這叫bidet。」「Bidet怎麼用?」房東先生似笑非笑地「哈」了一聲,二話不說轉身走回客廳。看來此物的用途只能意會不能言傳……
我後來才得知它是專門拿來清洗私處的坐浴池,原來與下體有關的事物都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話題。有人把它譯為「坐浴桶」,但常與免治馬桶混為一談(如維基百科頁),本文選用「坐浴池」。
坐浴池是法國十八世紀初的發明,古人沒有衛生紙這種奢侈品,最徹底的清潔方式還是用水洗。此物多以木材或銅板打造而成,僅見於條件優渥的上流社會,有時還裝了絨布背墊和扶手,宛如帝王寶座。拿破崙就擁有好幾個坐浴池,走到哪裡一定帶一個在身邊,可見在十九世紀初,此物仍然男女通用。
坐浴池在誕生之初,一直與性事有關。兩性開放的十八世紀留下了許多「關起房門欣賞」的淫穢版畫、油畫,內容常圍繞著坐浴池,畫中往往有一位清洗私處的女性。久而久之,此物變得像化妝台一樣,已成為女性專屬的用品。至十九世紀中期後,坐浴池已普及至民間,並且逐漸規格化,但僅見於城市地區。
抗生素發明前,民間一致相信男性若感染梅毒,一定是因為碰上不乾淨的妓女。為了讓顧客安心,每家妓院必備坐浴池。在避孕合法化之前(一九六七年),它一直是各地青樓不可或缺的設備,除了辦事前用來清潔私處之外,許多妓女亦以之進行避孕的陰道沖洗,已婚婦女亦將之視為最唾手可得的避孕工具。正因如此,教會對於坐浴池向來非常感冒,認為許多本有可能存在的小生命都被沖洗掉了。
二十世紀初,來到法國的觀光客第一次發現坐浴池,許多人如獲至寶,爭相引入本國。有人相信免治馬桶的發明正是從坐浴池中獲得靈感,從歐洲發展到美洲後,再於日本發揚光大。二次戰後,法國家家戶戶必備一兩個坐浴池,但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很多住家在整修浴室時,決定把它一一打掉,將騰出的位置改成淋浴間或接裝洗衣機,只有義大利與西班牙仍是它的忠實擁護者。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法國人已將坐浴池視為祖父母一代的骨董級設備,如果朋友得知你家裡還有一個,定會嘖嘖稱奇。此物雖然注定消失殆盡,但少數廠商仍不死心,揚言在日本免治馬桶、伊斯蘭小淨儀式的影響下,坐浴池不久即將捲土重來。
歷史學家在考究坐浴池時,發現它常與浣腸筒同時出現。浣腸法最早可上溯至古埃及,法國自十五世紀起重新掀起浣腸熱,揭開了長達好幾個世紀的黃金年代。人們相信此法可治百病,無論是便祕、消化不良、精神不濟,甚至憂鬱煩悶、臉色蒼白,都有對症下藥的處方,由專人以錫製浣腸筒注入五百c.c.的藥水,便可立竿見影。工匠在替坐浴池打造收藏櫃時,經常在櫃裡設計置放尿壺、海綿、香水瓶與浣腸用具的收藏格,讓坐浴成為一種兼具保健與享受的日常活動。路易十四本人對此也相當推崇,文獻紀錄他一生中曾浣腸四千次。不過浣腸並非上流社會的獨家專利,也廣見於中下階級。
很多民族都相當重視如廁的問題,比如古埃人怕便祕,留下了許多研討該症狀的文獻。十七、十八世紀的法國人也很關心排便問題,甚至把它視為一大養生重點,我們從法國人平時打招呼的用語中,便可略見端倪。若把法文的Comment allez-vous ? (你好嗎?)直譯成中文,就成了「你怎樣去?」怎麼看都顯得不太對勁。其實此話是從Comment allez-vous à la selle ?(排便還好嗎?)簡化而成的。當時的人們相信「便順人也安」,若要向人問好,還不如問他的便況。若對方答:「很好,你呢?」言下之意即「我大便很順暢,所以我很好。你呢?」當然,如今的法國人在問好時,並不見得知道此話的來源。無論如何,這和我們在台灣「你吃飽了嗎?」的問候方式著實大相逕庭。
法國人真的不洗澡嗎?
一般人常有這樣一個刻板印象:「法國香水之所以名聞天下,是因為法國人都不愛洗澡。」這是真的嗎?
在某種程度上,此話確實不假,只不過要看時代背景。
中世紀的法國人其實很愛乾淨,各大城裡均建有蒸浴池,鼓勵民眾常保清潔。話雖如此,有些場所樓下男女共浴,樓上公開賣淫,為此而備受教會指責。而且黑死病於十四世紀中期橫掃歐洲以後,整個社會都十分忌憚傳染病,很多學者相信:水,就是傳播病毒的媒介,因而大力譴責洗澡的行為。史上著名的外科醫生兼御醫Ambroise Paré(一五○九~一五九○年)就曾告誡道:「泡澡水會從毛孔滲入體內,造成猝死」。既然洗澡這麼可怕,那……何必冒這麼大的風險呢?醫學界當時的良心建議是:「洗手尚可,洗腳偶爾,洗澡萬萬行不得」。
從十七世紀開始,人們不但棄絕了「不文明」的泡浴,而且儘可能不接觸水,堅信水不但「傷眼傷牙,讓面部扁平,且令人冬天怕冷、夏天變黑」,他們寧可「乾洗」,也就是用白布(一定要是白色)擦拭身體,或每天更換潔淨的白色襯衣,認為乾洗的效果等同洗澡。當然,只有富裕的上流社會才有能力經常更衣,百姓平時頂多早晨洗臉、餐前洗手,其它部位就隨遇而安了。史上許多名人一生中沒洗過幾次澡,比如不拘小節的亨利四世非但從不碰水,而且最愛吃豬腸、咬大蒜,人還沒出現,臭氣就先到了。
十八世紀以後水源獲取較易,但人們梳洗時仍僅侷限於面部、手腳與下體。法國大革命之前,上流社會崇尚放蕩主義(libertinage,並為後世留下了許多情色文學作品),衛道人士因而把梳妝和縱慾劃上等號,認為好人家的女兒不必經常梳洗,倘若非洗不可的話,那最好閉上眼睛,不去觀賞自己的裸體,也不在鏡子前更衣。整個十九世紀,教會對洗滌之舉一直抱持敵意,相信常清洗陰部會造成不孕,並生怕洗浴會成為感官的享受,讓靈魂墮入地獄。為了避免浴池中的水太過清澈、一目了然,坊間還特別販售「池水混濁粉」。直到一九二五年,由修女管轄的女工宿舍(每兩週開一次澡堂)仍規定入浴者須穿著浴袍,且只准用肥皂搓洗,不可用手觸及自己的身體。
巴黎少數公寓早在一八七○年代,便已具備水管與瓦斯系統,讓住戶能輕易享用到熱水。但直到二十世紀初,城中裝設衛浴間的住宅仍只占百分之三,很多人認為早晨盥洗時拿毛巾擦拭就夠了,如有充足的預算,他們寧可接裝電話而不願買浴缸。而且「洗澡」之舉仍離不開治療的概念,在當時被稱為「水療」,只要醫生沒開水療的處方,沒事何必去洗什麼澡!法國第八任總統盧貝曾在一九○六年帶其繼任者參觀愛麗舍宮,介紹到浴室時,他對下一任總統說:「我們雖在總統府裡修建浴室,但內人和我從來不生病,所以我們一次也沒用過。」
幾個世紀當中,鑒於特殊的意識形態與設備條件,洗澡的法國人的確少之又少。但從二次大戰開始,絕大多數住家均擁有完善的衛浴設備。倘若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在問:「法國人真的都不洗澡嗎?」那你可能太輕信刻板印象了。
古人一向在開放的公共空間梳洗,比如月神黛安娜在池中沐浴時曾被獵人阿克泰翁撞見(中國民間故事與聊齋亦有諸多類似情節),古羅馬的浴場或中世紀的蒸浴池也都是公用設施。直到十七、十八世紀初為止,在中上層家庭裡,梳洗、更衣、如廁都有僕傭在旁伺候協助。有些人甚至把梳妝沐浴視為社交行為,選在此時接見訪客,不像我們今天將這些活動視為隱私。一般住家並沒有私人空間,寢室門不見得可上鎖,家人或僕役隨時可能進出。
法國史學家Vigarello提出一個有趣的論點,他認為「隱私」與「水」的關係相當密切。從十八世紀中期起,由於水成了較易取得的資源,坐浴池一類的盥洗用具日益普及,人們梳洗時開始與外界隔離。至十九世紀以後,連僕役也被關在房門之外了。衛浴設備因民間的需求而出現,逐漸成為人人不可或缺的空間。
這一轉變不僅是住宅格局的革命,也在人們內心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沒有隱私的時代,每個人平時只面對外界,與他人溝通互動。私密的空間出現後,個人首度能脫離外在世界,靜下來面對自己、照料自己的身體,並意識到自我的存在。生活空間的變化引發了新的思維模式,隱私的概念從而誕生,不僅之於梳洗如廁時分,也在於精神上的獨處。如今,「隱私」早已成為大部分人類的基本需求。
至於toilette這個常見的字,它大約出現在十七世紀,最早指包裹梳妝用品的精緻薄布,使用時先把它鋪在桌面,再把化妝品、香瓶、鏡子與首飾置於其上。到了十七世紀晚期,此字逐漸演變為梳妝更衣等活動,直到今天仍有衣裝、梳洗、清潔之意(如淡香水eau de toilette直譯就是「梳妝水」)。如果再加上一個s,就成了廁所,英文的toilet就是從這個法文字演變而來的。在中文裡,我們不是也把如廁的地點稱為「化妝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