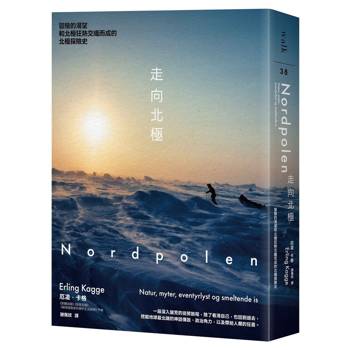【內文摘錄 1】
第一章 四個北極
「這趟旅程的目的地不是地理北極,而是每個人內心的北極。」
我的發現
一九七○年我生日那天,爸媽送給我人生中的第一顆地球儀。上面的金屬支架框住地球,從底部延伸到頂部。細線標出國界,其他細節以不同顏色呈現,彼此交織融合。海洋和河流是藍色,冰川是白色,山脈是棕色。海洋的顏色愈藍,表示愈深;山脈愈棕,表示愈高。那個小小的地球儀,幫助我更快理解大自然彼此相連,地球上的水、冰、土壤和石頭都是一體的。
地球儀的中間最寬,支架上刻著「0」,從那裡數字往上或往下最多達到「90」。研究過大半個世界之後,我的目光停在最上面那個點。頂端那一大片藍白色是什麼?它屬於哪個國家?怎麼樣才能抵達那裡?
七歲的我,就這樣發現了北極。
我仔細觀察那片藍白色區域。北極點被一個鉻合金小圓盤遮住。這個小圓盤將地球儀固定在連接支架的旋轉軸上。我很好奇圓盤底下是什麼?北極裡面藏了什麼?多虧這個地球儀,我才知道地球繞著軸心自轉;如果我把地球儀往右轉,它就往東,中間是北極。南北極似乎是地球的中心。當母親告訴我,在赤道地區,地球以每小時一千六百七十公里的速度自轉時,我試著要用這麼快的速度轉動地球儀,問題是要確認有沒有達到那個速度很難。於是我想到另一個點子。我站在房間中央,閉上眼睛,嘗試用每小時一千六百七十公里的速度轉圈圈。
七歲那一年,我發現的是地理上的北極。在那裡,羅盤上的指針永遠指向南;吹的風永遠是南風,即使從北邊吹過來也一樣;地球的離心力失去了作用;每年各只有一次日升和日落。北極在九月二十二日秋分這一天日落,要到三月二十一日春分這天,太陽才會再度升起。
「地理北極」是幾世紀以來各國探險家競相前往的地方,也是二十年後,我滑雪遠征的目標。
得到人生第一顆地球儀之後又過了好多年,我才知道,除了我最終抵達的北極之外,還有另外三個北極。四個北極彼此相關,但各自迥異。
「天球北極」位在北極的正上方。從南極到北極這條貫穿地球的軸線,若是直直往上延伸就是天球北極,而且也有充分的理由可視之為天空的中心。
「地磁北極」對海上和陸上導航都不可或缺,因為人類發現磁針都會指向北方。地磁北極是生死存亡的關鍵。
第四個北極不那麼廣為人知,也從未得到適當的名稱。我決定叫它「想像的北極」。那不是一個實體的地方,而是存在於人們心中的北極,受eventyrlyst(冒險的渴望)、令人驚奇的事物、想像力,有時還有口述歷史和文字記錄的啟發。
***
想像的北極
抵達北極之後,我才明白,歐洲、亞洲和北美洲的人幾千年來不斷探訪的是他們想像中的北極。我曾經為了抵達北極而走火入魔。有兩年多,我讀的每本書都跟前往北極的準備工作有關,開口閉口也離不開這個話題。等我回到挪威,熱情逐漸冷卻下來,我才發現北極不僅僅是一個遠征的目標,還有許許多多的面向值得探索。
北極的歷史大致可分成三段。第一段最長,從人類有史以來直到十六世紀。這段時間,北半球的人只能推測地平線盡頭以北是什麼樣的世界,無法實際前往,所以北極只存在人類的想像中。第二段是一五○○年到一九○○年前後,那時試圖前往北極的人很多都不敵冰雪,命喪途中。第三段是二十世紀至今,人類終於抵達北極。但根據頂尖科學家的看法,由於人類恣意妄為,導致全球溫度上升,如今北極冰層到了夏季將有融化之虞。
人類自古以來,一直在思考世界是如何相互連結、合而為一。哥白尼提出的理論,根據的觀察不會比前人更加可靠,畢竟當時尚未發明望遠鏡。然而,他跟同時代的人利用既有的觀察和理性的推論,提出開創性的理論。
最早的世界地圖之一,據說出自希臘天文學家及製圖師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西元前610-546)之手,但上面沒有北極。他成功說服同時代的人,接受兩個革命性的概念:一是這個世界飄浮在太空中,沒有固定在實體物質上;二是地表是彎曲的,因此天空在我們腳下延伸而去。阿那克西曼德得出的這兩個結論,比麥哲倫的維多利亞號環球一周,早了兩千多年,比太空人拍到地球飄浮在太空中的照片,早了兩千五百年。
人類的推測當然不一定準確,最早的北極探險就是很好的例子。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人類試著想像北極的樣貌,但從未完全預料到在那裡會遇到的洋流、酷寒、黑暗和冰雪。或許他們對自己太過自信,也有可能他們缺乏阿那克西曼德的好奇心。
(未完)
【內文摘錄 2】
第六章 英雄時代
你想是誰率先抵達北極?
有一些北極探險故事離奇到令人難以相信。但根據我的經驗,探險途中,沒有什麼事會離奇到令人難以相信。國家地理學會後來接受培利沒有真正抵達北極,只是相信自己到了北極。如果他離北極還有五十公里遠,我不認為他會相信自己已經抵達北極,但他可能認為離目標已經不遠。探險家俱樂部(The Explorers’ Club)(培利另一個早期贊助者)仍舊相信這次探險是抵達北極的第一支隊伍,「或至少很接近北極。」《紐約時報》比較坦白,在一九九八年直言:「今日多數的歷史學家認為兩名探險家都在說謊。」
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取決於怎麼樣才算抵達北極,但極點並沒有固定的定義。現在有GPS(衛星定位系統),在極點一公尺內才算抵達北極。問題是在極點很難停留很久,因為即使你站著不動,腳下的冰層也在動。大多數人都同意,一九○九年的北極點範圍應該比今日更加寬鬆。有人建議十公里內就算數。我認為這個標準有點嚴格,畢竟當時的自然誤差範圍可能更大。六分儀可以用來測量正確的位置,但一百多年前的時鐘不像現在那麼準確。北極海上方通常雲層密布,有時很難看見太陽,也就無法測出它離地平線有多高。再說,雪橇在凹凸不平的冰層上拖行好幾週,放在裡面的六分儀隨之顛簸搖晃,也可能產生非正常的誤差。此外,前後兩次測量之間,你可能已經漂離原點,導致兩次測得的位置不一致。在南極就簡單多了,因為你腳下的冰層固定在一塊大陸上。
如今,測量儀器愈來愈精準,未來我們或許有可能分毫不差地定義北極,而且你必須站在現場留下紀錄,才算抵達北極。當年我們抵達世界之頂時,極點位在一條開放水道裡,才搭好帳篷不過幾小時,我們就隨著冰層漂過了極點。我們到達了目標,當下卻無從得知我們是不是打敗了英國人,成為不靠補給站、發動機或雪橇犬抵達北極的第一批人。要是他們前一天就抵達,現在早就漂到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我們沒帶衛星電話,只有可跟附近飛過的飛機通話的VHF(特高頻)無線電,還有能把我們的位置和三個簡單的預設訊息(求救、緊急求救、抵達目標)傳給外界的發射器。
抵達後的第一天早上,我們一邊分配所剩無幾的食物,一邊等飛機來接我們,這時卻突然聽到引擎聲。正準備在冰上清出一條簡易跑道時,我轉向那個聲音,看見一架巨大的白色螺旋槳飛機飛得低低的,離我們不到一百公尺。機側印著「美國海軍」幾個字,但是沒裝滑雪板。後來我們才知道那是偵察機,負責飛到北極海的上空,往冰間水道投放探測器,以找出冰海下的俄羅斯潛艇。博格打開特高頻無線電(為了減輕重量,我們沒帶更大的無線電)。我用腳在雪裡踩出「FOOD」幾個大字。連上無線電之後,另一頭的美國人問我們是誰,博格用很重的挪威口音回答:「只是兩個徒步走向北極的挪威人。」下一個問題是:「你們需要食物嗎?」
美國人投下一箱食物和一箱讀物,但裡頭只有《閣樓雜誌》(Penthouse)和八卦雜誌《探詢者》(National Enquirer)。快累癱的時候,裸女照片是多餘的,所以我讀了八卦雜誌裡的每一篇文章。但我們更感興趣的是食物,即使一天攝取高達五千八百五十卡的熱量,體內的脂肪和肌肉還是消耗殆盡。抵達北極之後,我們開始管控每日攝取的熱量,因為不知道飛機何時才會來接我們。我們平分飛機投遞的食物,把分好的食物排在睡墊上,遵守我們每天早餐和晚餐所採用的方式:一個人分好食物,另一個先選他要的那一份。我記得從小我們家就是這樣分享甜點。那是永生難忘的一餐。以下是我的紀錄:
我正要抓起食物狼吞虎嚥,但博格建議我們等一下,不要立刻開動。靜靜觀察食物片刻。在腦中數到十再開始吃。展現我們共有的自制力。提醒彼此,滿足往往伴隨著犧牲。我很少像那一刻那樣覺得自己如此富有。停下來等待雖然感覺很怪,但食物因此嘗起來更加美味。
可以相當確定的是,培利確實曾經抵達北緯八十七度四十七分,這是巴伯.巴特列(Bob Bartlett)測到的位置。他是隊上除了培利以外,唯一會使用六分儀的人,而這是他被遣回之前做的最後一次測量。探險隊出發北上之前,巴特列告訴大半輩子都在北極地區獵海豹的父親:「下次出海,我要去北極。」
隊伍抵達北緯八十七度四十七分之前,巴特列走在前面為其他人開路,因此對這次探險貢獻很大。他認為培利答應過會讓他一路前往北極,卻出賣了他。被迫折返的前一天早上,他比所有人都早起,帶著裝備獨自往北走了一段。他承認自己掉了幾滴淚:「或許我哭了一下。」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就連培利和漢森也無法對誰先抵達北極達成共識。漢森說是他先到的。隊伍抵達北極的那一天,他走在前面探路,決定最佳路線。一抵達極點,漢森就表示自己是第一個到的人,終其一生也堅持這個說法。培利當然否定他的說法,真相為何,至今無人知曉。
據我所知,從來沒人問過另外四名因紐特人的看法。這對他們來說只是一份工作,即使成功歸來,他們也不會受人讚揚。我不確定當時有沒有任何一個因紐特人理解征服北極的意義何在。長久以來,只有歐美男性為此著迷。從很多方面來看,這都很像早期想攀登聖母峰的西方人跟雪巴人(Sherpas)之間的關係。尼泊爾登山家丹增.諾蓋(TenzingNorgay)的兒子詹姆林(Jamling),小時候曾經要求父親幫忙,讓他加入聖母峰探險隊。他父親回答:「我爬聖母峰是為了讓我的小孩不必去爬山,可以好好上學。」
培利跟漢森在自己的著作中,都不否認四名因紐特人是探險成敗的關鍵。最後一天,培利和漢森雙雙掉進水裡,多虧因紐特人,兩名美國人才撿回一條命。漢森形容這些事件是「北極探險的日常」。
一百多年後,比起是否抵達目標,或許更有趣的是往返極點的過程。無論目標有多遠大、結果有幾分真實,庫克、培利和其他七名隊員都令人敬佩。我懷疑真有一天,我們能百分之百解開誰先抵達北極之謎—如果兩人之中真有一人拔得頭籌的話。
但庫克、阿威拉和艾圖奇修最了不起的壯舉,發生在一九○八到○九年,從北極回程的途中。他們跟南森和約翰生當年一樣,被迫留下來過冬。太陽在十一月三日落下,隔年二月十一日才又升起。「我們因此注定要在我們的地洞,冬眠至少一百個極夜,黎明才會再度到來,打開我們的雙眼。」如同約翰生和南森,三人回到石器時代,靠安頓下來之前獵捕的海豹和北極熊肉及油脂存活。他們一起睡在石頭搭建的平台上,生活「沒有值得開心的理由。只能靠手工活和長時間的睡眠,避免精神崩潰和徹底瘋癲」。他們當然沒有足夠的火柴多撐一個冬天,所以每六小時一班輪流顧燈,以免火熄滅,順便趕走北極熊,並且「在單調乏味的生活中擠進一點樂趣」。約翰生和南森在過完冬天之後能很快地獲救,是純屬好運。庫克、艾圖奇修和阿拉威就沒那麼幸運了,不得不一路走到安諾阿托克。途中他們食物見底,只好吃兩種通常不會有人覺得能吃的東西,一個是用熱水融化的蠟燭,另一個是水煮海象皮。
三個人撐了十四個月才終於回到家,這是極地探險史上最了不起的壯舉之一。
北極探險的英雄時代並非一夕之間結束,但培利和庫克之間的爭執是結束的開始。大多數人都相信北極終於被征服,這場競賽也隨之落幕。
一次世界大戰的戰鼓愈敲愈響之際,大眾對兩名美國探險家的興趣逐漸消退。後來戰爭爆發,幾百萬年輕人在戰壕裡死的死、傷的傷,探險家沒完沒了的個人恩怨,以及為了抵達北極所做的各種嘗試,想必顯得荒謬又可笑。
一個新世界就在這個時候誕生了。
(未完)
第一章 四個北極
「這趟旅程的目的地不是地理北極,而是每個人內心的北極。」
我的發現
一九七○年我生日那天,爸媽送給我人生中的第一顆地球儀。上面的金屬支架框住地球,從底部延伸到頂部。細線標出國界,其他細節以不同顏色呈現,彼此交織融合。海洋和河流是藍色,冰川是白色,山脈是棕色。海洋的顏色愈藍,表示愈深;山脈愈棕,表示愈高。那個小小的地球儀,幫助我更快理解大自然彼此相連,地球上的水、冰、土壤和石頭都是一體的。
地球儀的中間最寬,支架上刻著「0」,從那裡數字往上或往下最多達到「90」。研究過大半個世界之後,我的目光停在最上面那個點。頂端那一大片藍白色是什麼?它屬於哪個國家?怎麼樣才能抵達那裡?
七歲的我,就這樣發現了北極。
我仔細觀察那片藍白色區域。北極點被一個鉻合金小圓盤遮住。這個小圓盤將地球儀固定在連接支架的旋轉軸上。我很好奇圓盤底下是什麼?北極裡面藏了什麼?多虧這個地球儀,我才知道地球繞著軸心自轉;如果我把地球儀往右轉,它就往東,中間是北極。南北極似乎是地球的中心。當母親告訴我,在赤道地區,地球以每小時一千六百七十公里的速度自轉時,我試著要用這麼快的速度轉動地球儀,問題是要確認有沒有達到那個速度很難。於是我想到另一個點子。我站在房間中央,閉上眼睛,嘗試用每小時一千六百七十公里的速度轉圈圈。
七歲那一年,我發現的是地理上的北極。在那裡,羅盤上的指針永遠指向南;吹的風永遠是南風,即使從北邊吹過來也一樣;地球的離心力失去了作用;每年各只有一次日升和日落。北極在九月二十二日秋分這一天日落,要到三月二十一日春分這天,太陽才會再度升起。
「地理北極」是幾世紀以來各國探險家競相前往的地方,也是二十年後,我滑雪遠征的目標。
得到人生第一顆地球儀之後又過了好多年,我才知道,除了我最終抵達的北極之外,還有另外三個北極。四個北極彼此相關,但各自迥異。
「天球北極」位在北極的正上方。從南極到北極這條貫穿地球的軸線,若是直直往上延伸就是天球北極,而且也有充分的理由可視之為天空的中心。
「地磁北極」對海上和陸上導航都不可或缺,因為人類發現磁針都會指向北方。地磁北極是生死存亡的關鍵。
第四個北極不那麼廣為人知,也從未得到適當的名稱。我決定叫它「想像的北極」。那不是一個實體的地方,而是存在於人們心中的北極,受eventyrlyst(冒險的渴望)、令人驚奇的事物、想像力,有時還有口述歷史和文字記錄的啟發。
***
想像的北極
抵達北極之後,我才明白,歐洲、亞洲和北美洲的人幾千年來不斷探訪的是他們想像中的北極。我曾經為了抵達北極而走火入魔。有兩年多,我讀的每本書都跟前往北極的準備工作有關,開口閉口也離不開這個話題。等我回到挪威,熱情逐漸冷卻下來,我才發現北極不僅僅是一個遠征的目標,還有許許多多的面向值得探索。
北極的歷史大致可分成三段。第一段最長,從人類有史以來直到十六世紀。這段時間,北半球的人只能推測地平線盡頭以北是什麼樣的世界,無法實際前往,所以北極只存在人類的想像中。第二段是一五○○年到一九○○年前後,那時試圖前往北極的人很多都不敵冰雪,命喪途中。第三段是二十世紀至今,人類終於抵達北極。但根據頂尖科學家的看法,由於人類恣意妄為,導致全球溫度上升,如今北極冰層到了夏季將有融化之虞。
人類自古以來,一直在思考世界是如何相互連結、合而為一。哥白尼提出的理論,根據的觀察不會比前人更加可靠,畢竟當時尚未發明望遠鏡。然而,他跟同時代的人利用既有的觀察和理性的推論,提出開創性的理論。
最早的世界地圖之一,據說出自希臘天文學家及製圖師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西元前610-546)之手,但上面沒有北極。他成功說服同時代的人,接受兩個革命性的概念:一是這個世界飄浮在太空中,沒有固定在實體物質上;二是地表是彎曲的,因此天空在我們腳下延伸而去。阿那克西曼德得出的這兩個結論,比麥哲倫的維多利亞號環球一周,早了兩千多年,比太空人拍到地球飄浮在太空中的照片,早了兩千五百年。
人類的推測當然不一定準確,最早的北極探險就是很好的例子。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人類試著想像北極的樣貌,但從未完全預料到在那裡會遇到的洋流、酷寒、黑暗和冰雪。或許他們對自己太過自信,也有可能他們缺乏阿那克西曼德的好奇心。
(未完)
【內文摘錄 2】
第六章 英雄時代
你想是誰率先抵達北極?
有一些北極探險故事離奇到令人難以相信。但根據我的經驗,探險途中,沒有什麼事會離奇到令人難以相信。國家地理學會後來接受培利沒有真正抵達北極,只是相信自己到了北極。如果他離北極還有五十公里遠,我不認為他會相信自己已經抵達北極,但他可能認為離目標已經不遠。探險家俱樂部(The Explorers’ Club)(培利另一個早期贊助者)仍舊相信這次探險是抵達北極的第一支隊伍,「或至少很接近北極。」《紐約時報》比較坦白,在一九九八年直言:「今日多數的歷史學家認為兩名探險家都在說謊。」
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取決於怎麼樣才算抵達北極,但極點並沒有固定的定義。現在有GPS(衛星定位系統),在極點一公尺內才算抵達北極。問題是在極點很難停留很久,因為即使你站著不動,腳下的冰層也在動。大多數人都同意,一九○九年的北極點範圍應該比今日更加寬鬆。有人建議十公里內就算數。我認為這個標準有點嚴格,畢竟當時的自然誤差範圍可能更大。六分儀可以用來測量正確的位置,但一百多年前的時鐘不像現在那麼準確。北極海上方通常雲層密布,有時很難看見太陽,也就無法測出它離地平線有多高。再說,雪橇在凹凸不平的冰層上拖行好幾週,放在裡面的六分儀隨之顛簸搖晃,也可能產生非正常的誤差。此外,前後兩次測量之間,你可能已經漂離原點,導致兩次測得的位置不一致。在南極就簡單多了,因為你腳下的冰層固定在一塊大陸上。
如今,測量儀器愈來愈精準,未來我們或許有可能分毫不差地定義北極,而且你必須站在現場留下紀錄,才算抵達北極。當年我們抵達世界之頂時,極點位在一條開放水道裡,才搭好帳篷不過幾小時,我們就隨著冰層漂過了極點。我們到達了目標,當下卻無從得知我們是不是打敗了英國人,成為不靠補給站、發動機或雪橇犬抵達北極的第一批人。要是他們前一天就抵達,現在早就漂到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我們沒帶衛星電話,只有可跟附近飛過的飛機通話的VHF(特高頻)無線電,還有能把我們的位置和三個簡單的預設訊息(求救、緊急求救、抵達目標)傳給外界的發射器。
抵達後的第一天早上,我們一邊分配所剩無幾的食物,一邊等飛機來接我們,這時卻突然聽到引擎聲。正準備在冰上清出一條簡易跑道時,我轉向那個聲音,看見一架巨大的白色螺旋槳飛機飛得低低的,離我們不到一百公尺。機側印著「美國海軍」幾個字,但是沒裝滑雪板。後來我們才知道那是偵察機,負責飛到北極海的上空,往冰間水道投放探測器,以找出冰海下的俄羅斯潛艇。博格打開特高頻無線電(為了減輕重量,我們沒帶更大的無線電)。我用腳在雪裡踩出「FOOD」幾個大字。連上無線電之後,另一頭的美國人問我們是誰,博格用很重的挪威口音回答:「只是兩個徒步走向北極的挪威人。」下一個問題是:「你們需要食物嗎?」
美國人投下一箱食物和一箱讀物,但裡頭只有《閣樓雜誌》(Penthouse)和八卦雜誌《探詢者》(National Enquirer)。快累癱的時候,裸女照片是多餘的,所以我讀了八卦雜誌裡的每一篇文章。但我們更感興趣的是食物,即使一天攝取高達五千八百五十卡的熱量,體內的脂肪和肌肉還是消耗殆盡。抵達北極之後,我們開始管控每日攝取的熱量,因為不知道飛機何時才會來接我們。我們平分飛機投遞的食物,把分好的食物排在睡墊上,遵守我們每天早餐和晚餐所採用的方式:一個人分好食物,另一個先選他要的那一份。我記得從小我們家就是這樣分享甜點。那是永生難忘的一餐。以下是我的紀錄:
我正要抓起食物狼吞虎嚥,但博格建議我們等一下,不要立刻開動。靜靜觀察食物片刻。在腦中數到十再開始吃。展現我們共有的自制力。提醒彼此,滿足往往伴隨著犧牲。我很少像那一刻那樣覺得自己如此富有。停下來等待雖然感覺很怪,但食物因此嘗起來更加美味。
可以相當確定的是,培利確實曾經抵達北緯八十七度四十七分,這是巴伯.巴特列(Bob Bartlett)測到的位置。他是隊上除了培利以外,唯一會使用六分儀的人,而這是他被遣回之前做的最後一次測量。探險隊出發北上之前,巴特列告訴大半輩子都在北極地區獵海豹的父親:「下次出海,我要去北極。」
隊伍抵達北緯八十七度四十七分之前,巴特列走在前面為其他人開路,因此對這次探險貢獻很大。他認為培利答應過會讓他一路前往北極,卻出賣了他。被迫折返的前一天早上,他比所有人都早起,帶著裝備獨自往北走了一段。他承認自己掉了幾滴淚:「或許我哭了一下。」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就連培利和漢森也無法對誰先抵達北極達成共識。漢森說是他先到的。隊伍抵達北極的那一天,他走在前面探路,決定最佳路線。一抵達極點,漢森就表示自己是第一個到的人,終其一生也堅持這個說法。培利當然否定他的說法,真相為何,至今無人知曉。
據我所知,從來沒人問過另外四名因紐特人的看法。這對他們來說只是一份工作,即使成功歸來,他們也不會受人讚揚。我不確定當時有沒有任何一個因紐特人理解征服北極的意義何在。長久以來,只有歐美男性為此著迷。從很多方面來看,這都很像早期想攀登聖母峰的西方人跟雪巴人(Sherpas)之間的關係。尼泊爾登山家丹增.諾蓋(TenzingNorgay)的兒子詹姆林(Jamling),小時候曾經要求父親幫忙,讓他加入聖母峰探險隊。他父親回答:「我爬聖母峰是為了讓我的小孩不必去爬山,可以好好上學。」
培利跟漢森在自己的著作中,都不否認四名因紐特人是探險成敗的關鍵。最後一天,培利和漢森雙雙掉進水裡,多虧因紐特人,兩名美國人才撿回一條命。漢森形容這些事件是「北極探險的日常」。
一百多年後,比起是否抵達目標,或許更有趣的是往返極點的過程。無論目標有多遠大、結果有幾分真實,庫克、培利和其他七名隊員都令人敬佩。我懷疑真有一天,我們能百分之百解開誰先抵達北極之謎—如果兩人之中真有一人拔得頭籌的話。
但庫克、阿威拉和艾圖奇修最了不起的壯舉,發生在一九○八到○九年,從北極回程的途中。他們跟南森和約翰生當年一樣,被迫留下來過冬。太陽在十一月三日落下,隔年二月十一日才又升起。「我們因此注定要在我們的地洞,冬眠至少一百個極夜,黎明才會再度到來,打開我們的雙眼。」如同約翰生和南森,三人回到石器時代,靠安頓下來之前獵捕的海豹和北極熊肉及油脂存活。他們一起睡在石頭搭建的平台上,生活「沒有值得開心的理由。只能靠手工活和長時間的睡眠,避免精神崩潰和徹底瘋癲」。他們當然沒有足夠的火柴多撐一個冬天,所以每六小時一班輪流顧燈,以免火熄滅,順便趕走北極熊,並且「在單調乏味的生活中擠進一點樂趣」。約翰生和南森在過完冬天之後能很快地獲救,是純屬好運。庫克、艾圖奇修和阿拉威就沒那麼幸運了,不得不一路走到安諾阿托克。途中他們食物見底,只好吃兩種通常不會有人覺得能吃的東西,一個是用熱水融化的蠟燭,另一個是水煮海象皮。
三個人撐了十四個月才終於回到家,這是極地探險史上最了不起的壯舉之一。
北極探險的英雄時代並非一夕之間結束,但培利和庫克之間的爭執是結束的開始。大多數人都相信北極終於被征服,這場競賽也隨之落幕。
一次世界大戰的戰鼓愈敲愈響之際,大眾對兩名美國探險家的興趣逐漸消退。後來戰爭爆發,幾百萬年輕人在戰壕裡死的死、傷的傷,探險家沒完沒了的個人恩怨,以及為了抵達北極所做的各種嘗試,想必顯得荒謬又可笑。
一個新世界就在這個時候誕生了。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