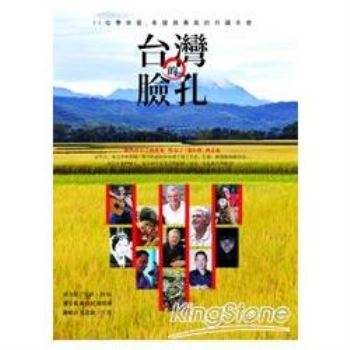用字紙與文字為貧民打造屋宇
來自法國的神父劉一峰 ◎須文蔚
玉里的天主教徒都知道,上帝隨時隨地會耐心傾聽人們的祈禱,劉一峰神父的手機從來不關機,天主堂的大門永遠是開著的。
【人物小傳】
劉一峰 (Yves Moal,一九四一年~),天主教玉里天主堂神父。
劉神父年輕時加入天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立下傳教的志願;二十五歲晉鐸後,因為曾經在一本書上看過台灣,便申請到台灣服務。劉神父在台灣的時間幾乎都在花蓮度過,一九九九年,創立「安德啟智中心」的顧超前神父過世後,服務於玉里天主堂的劉神父,接受教會指派成了中心負責人,接下顧神父照顧花東地區身心障礙者的棒子。二○○六年申請勞委會多元就業輔導,提供多名智能障礙者工作機會及協助職訓工作。二○○一年十一月六日,劉一峰神父回到祖國,在學術最高殿堂法蘭西學術院接受「第六屆中法文化獎」;二○○七年劉神父榮獲績優外籍宗教人士。二○一二年獲得行政院勞委會頒給「多元就業金旭獎」,表彰玉里天主堂以資源回收促進就業與公益的表現。
神父遲到的子夜彌撒
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玉里的子夜彌撒場地燈火輝煌,志工們忙進忙出,隆重準備慶祝耶誕節,教友紛紛來到,他們的臉上充滿著喜悅,要迎接耶穌基督誕生的福音。有人突然發現:駐堂的劉一峰神父不見了!
向來準時主持彌撒的劉神父竟然缺席,過了預定的時間依然不見蹤跡,大家開始不安,比較容易緊張的老人家碎碎唸:「千萬不要出什麼事才好。」
灰髮、削瘦與個子不高的劉一峰神父喘著氣,走進教堂,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也好奇地張望他。神父說:「很抱歉,我遲到了。」
大夥鬆了一口氣,繼續聽神父講:「剛剛一個單親家庭的小學生,家長又失業了,在平安夜餓得發慌,實在忍不住才哭著打電話給我。怎麼辦?就快要子夜彌撒了,要不要去呢?」
有個調皮的孩子大聲說:「神父一定會去的啦!」大家都哄堂大笑,孩子太清楚劉神父的風格。
「我覺得是耶穌在叫我,告訴我還有弱小的兄弟姊妹在餓肚子,所以我就趕去關心他,讓大家操心了!」神父還記掛著那孩子能否吃飽,能否安然度過耶誕節,像是一個父親沒有錢買晚餐回家般的負疚與難過。子夜彌撒就在劉一峰神父溫暖的話語聲中展開,每個人低頭祈禱時,都感覺自己是幸福無比的孩子,受到劉神父的照顧與關愛。
玉里的天主教徒都知道,上帝隨時隨地會耐心傾聽人們的祈禱,劉一峰神父的手機從來不關機,天主堂的大門永遠是開著的。有位精神狀況不好的孩子,一天情緒極度低潮,在自殺前向他求救,神父比消防隊先到現場,在血泊中簡單急救後,趕緊到醫院找救護車來處理。有人在教堂外喝酒鬧事、喧譁爭吵甚至鬥毆受傷,神父會挺身而出去勸架,把傷者帶回教堂包紮,最後一一把傷者或醉漢送回家。甚至玉里榮民醫院的精神病患出院了,家裡不接納,無所依歸的時候,社工會把劉神父的手機號碼給他們,好心的神父就到火車站接送,讓他們暫時有個安頓的地方。
協助神父超過十三年的社工李慧蘭說,劉一峰神父絕對不會拒絕任何的求救,所以他身邊總是有一批老老小小的「跟班」。
簡陋教堂中神父異常的跟班
劉一峰身邊的跟班不是帥氣的黑道小弟或保鏢,有剛出獄的更生人、逃學的中輟生、腦性麻痺的啟智兒或是酒精中毒的病患,他們把天主堂當作家,神父會照顧他們吃飯,甚至有時找臨時的工作讓他們自立。
玉里天主堂沒有宏偉的建築結構,連油漆剝落都靠志工自力救濟,維持外牆的潔白。神父的慈愛是教友最敬佩的,但是總有社工、信徒或其他神職人員會提醒神父:「你身邊的更生人或病患好像情緒不太穩定,我們會害怕。」也有人說:「天主堂收留太多像流浪漢的人,教友都不敢接近了,為了教堂好,一定要把他們都趕走!」劉神父總是笑而不答,他心裡頭一直掙扎著,其中他最放不下的是阿問和阿威(匿名)。
快要四十歲的阿問是「胎兒酒精綜合症」(Fetal alcohol syndrome, FAS)的患者,阿問的母親在妊娠期間酗酒,使他在胎兒階段就造成永久身心缺陷。和多數病患一樣,阿問在出生前中樞神經系統就遭到酒精無情破壞,他的神經細胞及腦部結構發育有障礙,成年後經常酗酒,更顯現出衝動、反應遲鈍、注意力不足及理解力差的精神狀況。因為自小在學校就是問題兒童,出社會也找不到工作,阿問誤入歧途過,從監獄出來後,成日酗酒,連家裡都待不下,就只有神父收容他。
阿問平日很沉默,看來有些傻乎乎,行動也不協調,但只要喝了一點酒,想起不如意的人生,或是心情莫名不好,就生龍活虎起來,經常對人咆哮。有時他在一樓罵人,在二樓主持彌撒的劉神父都不禁要皺眉頭,更讓教會的志工與教友感到頭疼。神父知道當阿問心情糟的時候,不要和他硬碰硬,理性的安撫也無法奏效。焦躁的阿問曾經幾度一面揮拳、一面對著神父吼叫:「我要錢買香菸啦!你給不給錢啊你?」
只見憂傷的神父從羞澀的阮囊中掏出一點錢:「阿問,去買菸!」藉由紙捲菸點燃的煙霧消散阿問的焦躁。
來自馬來西亞的志工黃婉秋說,不只阿問經常惹事,另一個更生人阿威也讓她和大家感到不安。阿威經常醉酒鬧事,和阿問一言不合就打起來,甚至作勢要攻擊對面國小的孩子。有一天晚上,阿威醉醺醺地坐在天主堂的院子裡,見到黃婉秋回來就拉著她的手:「婉秋,婉秋,我完了!你可以陪我講講話嗎?」
「怎麼了?」婉秋顫抖著聲音,把手掙脫。
「我可能因為疏忽照顧女兒,要再度回到監獄中,我完了!我完了!」阿威一直喃喃自語。
「我先回房放東西,等一會再來陪你。」婉秋急忙往樓上跑。
在房間中稍微穩定心情後,她到教堂內跟劉神父說:「神父,我很害怕,阿威又喝醉酒了,而且他很擔心又要回去坐牢。」
神父憂傷地說:「他又喝醉了,真糟糕!」
「為什麼不把他們送走,天主堂附近的鄰居也都不安心。」
「不可以!我沒辦法,如果把他們趕走,我的良心一定不安,會覺得……是不應該這樣。可是要把阿威送到戒酒中心,我手邊的錢也不夠。」
「可是,我會害怕。」
「不要害怕,我知道大家的恐懼,可是阿問和阿威本性都很善良,只要我花多點時間陪伴他們,多對他們付出關懷與愛心,最起碼他們不會發狠,不會做壞事,至少可以減少一些社會問題。」神父苦笑著,用眼神安慰婉秋,轉身去看顧阿威。
在李慧蘭眼中,就是因為劉神父一次又一次超乎常人的寬恕與包容,總是讓阿問和阿威覺得有家可歸,脾氣漸趨溫馴,甚至知道苦力不該由年長者承擔,會主動協助神父。他們跟在神父身邊,在彌撒時分派經書與歌本,擔任輔祭,甚至到安德啟智中心照顧腦性麻痺、唐氏症或身障的孩子。他們以能夠為神父分勞而感到驕傲,對照其他病弱的孩子,他們顯得身強體健,實在沒有悲觀的權利,慢慢振作了起來。
接下安德啟智院的千斤重擔
讓迷途羔羊重返正道固然備極艱辛,劉一峰神父還承擔了教養花東地區智障、殘障、遭棄養青少年的責任,管理安德啟智院,這是顧超前神父交給他的千斤重擔。
顧超前神父一九八○年在花蓮縣富里鄉傳教時,想起在法國的哥哥為了照顧家中一名智能不足的孩子,弄得身心俱疲,家庭陷入經濟困境。同樣悲慘的畫面也出現在他訪視過的許多弱勢家庭中。於是他創立了「安德啟智中心」,收容智商三十以下的中、重度先天性智障兒童,以及罹患腦性麻痺、自閉症等二至十八歲的兒童和青少年。以一對一的方式,依照孩子個別的差異,培養他們生活自理能力、感官知覺動作訓練、說話訓練、物理治療、體能活動,以及讀、寫、算、社會常識、美勞、律動等教學。
安德啟智中心創辦時,花東還是相當落後的農村,特殊教育得不到政府與企業的重視,顧超前神父積極向國外教會與企業募捐,幾乎半數的捐款都來自國外。一度經費不足,為了擴充教學設備,他還專程回到法國故鄉,變賣了自己的全部家產,讓弱勢與身心障礙有個學習的環境。顧神父堅信,殘障兒童需要家庭的溫暖和關懷。安德啟智中心的兒童,每天都要回家與家人團聚過夜,他不辭辛勞地接送,希望家人和孩子能緊密生活在一起,一起成長。
一九八二年九月,安德啟智中心遷移到人口更密集的玉里鎮現址。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六日,顧超前神父過世後,五十八歲的劉一峰神父接受教會指派,接下顧神父照顧花東地區身心障礙者的棒子。劉一峰很快就發現「安德」面臨了兩大挑戰:一是,「安德」的孩子經過近二十年的歲月,已經慢慢步入成年與中年,他們要如何獨立自主?二是,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外國的援助與捐款日漸減少,啟智中心的財務日益捉襟見肘,該怎麼辦?
面對日漸長大成人的「安德」院生,顧超前神父去世前一年的九月,已經在富里鄉東里村成立安德職訓部,可惜他來不及看到院生習得一技之長,就與世長辭。劉一峰知道,安德的孩子連生活自理都不容易,要能夠透過職業訓練習得工作技能,最終自給自足,是遙遠的夢想。但他和修女與同事們努力教導中重度障礙的院生製作竹掃把、木工、點心等等,目的不在貼補支出,而是希望藉由工作讓院生都有事情可做,為自己贏得更多尊嚴與他人的尊重。
一轉眼,劉一峰神父接手安德啟智中心也有十四年了,有三位院生已經超過四十歲,眼見很快就要超過法定收容四十五歲的上限。長年陪伴院生的社工李紅櫻說,由於身障者老化較快,加上部分智能不足或患有精神障礙者,長期依賴熟悉的社工、神職人員照顧,神父實在捨不得讓這些在安德成長與老去的院生離開,他們的家人也不放心。劉神父在鄉下買了塊地,期待興建「安德怡峰園」做為終生庇護所,讓年長院生得以安心地度過晚年。
劉一峰的責任愈來愈沉重,卻遭遇到經濟不景氣,國內外的捐贈日益萎縮,為了籌募經費,可讓他的頭髮愈來愈灰白。
來自法國的神父劉一峰 ◎須文蔚
玉里的天主教徒都知道,上帝隨時隨地會耐心傾聽人們的祈禱,劉一峰神父的手機從來不關機,天主堂的大門永遠是開著的。
【人物小傳】
劉一峰 (Yves Moal,一九四一年~),天主教玉里天主堂神父。
劉神父年輕時加入天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立下傳教的志願;二十五歲晉鐸後,因為曾經在一本書上看過台灣,便申請到台灣服務。劉神父在台灣的時間幾乎都在花蓮度過,一九九九年,創立「安德啟智中心」的顧超前神父過世後,服務於玉里天主堂的劉神父,接受教會指派成了中心負責人,接下顧神父照顧花東地區身心障礙者的棒子。二○○六年申請勞委會多元就業輔導,提供多名智能障礙者工作機會及協助職訓工作。二○○一年十一月六日,劉一峰神父回到祖國,在學術最高殿堂法蘭西學術院接受「第六屆中法文化獎」;二○○七年劉神父榮獲績優外籍宗教人士。二○一二年獲得行政院勞委會頒給「多元就業金旭獎」,表彰玉里天主堂以資源回收促進就業與公益的表現。
神父遲到的子夜彌撒
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玉里的子夜彌撒場地燈火輝煌,志工們忙進忙出,隆重準備慶祝耶誕節,教友紛紛來到,他們的臉上充滿著喜悅,要迎接耶穌基督誕生的福音。有人突然發現:駐堂的劉一峰神父不見了!
向來準時主持彌撒的劉神父竟然缺席,過了預定的時間依然不見蹤跡,大家開始不安,比較容易緊張的老人家碎碎唸:「千萬不要出什麼事才好。」
灰髮、削瘦與個子不高的劉一峰神父喘著氣,走進教堂,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也好奇地張望他。神父說:「很抱歉,我遲到了。」
大夥鬆了一口氣,繼續聽神父講:「剛剛一個單親家庭的小學生,家長又失業了,在平安夜餓得發慌,實在忍不住才哭著打電話給我。怎麼辦?就快要子夜彌撒了,要不要去呢?」
有個調皮的孩子大聲說:「神父一定會去的啦!」大家都哄堂大笑,孩子太清楚劉神父的風格。
「我覺得是耶穌在叫我,告訴我還有弱小的兄弟姊妹在餓肚子,所以我就趕去關心他,讓大家操心了!」神父還記掛著那孩子能否吃飽,能否安然度過耶誕節,像是一個父親沒有錢買晚餐回家般的負疚與難過。子夜彌撒就在劉一峰神父溫暖的話語聲中展開,每個人低頭祈禱時,都感覺自己是幸福無比的孩子,受到劉神父的照顧與關愛。
玉里的天主教徒都知道,上帝隨時隨地會耐心傾聽人們的祈禱,劉一峰神父的手機從來不關機,天主堂的大門永遠是開著的。有位精神狀況不好的孩子,一天情緒極度低潮,在自殺前向他求救,神父比消防隊先到現場,在血泊中簡單急救後,趕緊到醫院找救護車來處理。有人在教堂外喝酒鬧事、喧譁爭吵甚至鬥毆受傷,神父會挺身而出去勸架,把傷者帶回教堂包紮,最後一一把傷者或醉漢送回家。甚至玉里榮民醫院的精神病患出院了,家裡不接納,無所依歸的時候,社工會把劉神父的手機號碼給他們,好心的神父就到火車站接送,讓他們暫時有個安頓的地方。
協助神父超過十三年的社工李慧蘭說,劉一峰神父絕對不會拒絕任何的求救,所以他身邊總是有一批老老小小的「跟班」。
簡陋教堂中神父異常的跟班
劉一峰身邊的跟班不是帥氣的黑道小弟或保鏢,有剛出獄的更生人、逃學的中輟生、腦性麻痺的啟智兒或是酒精中毒的病患,他們把天主堂當作家,神父會照顧他們吃飯,甚至有時找臨時的工作讓他們自立。
玉里天主堂沒有宏偉的建築結構,連油漆剝落都靠志工自力救濟,維持外牆的潔白。神父的慈愛是教友最敬佩的,但是總有社工、信徒或其他神職人員會提醒神父:「你身邊的更生人或病患好像情緒不太穩定,我們會害怕。」也有人說:「天主堂收留太多像流浪漢的人,教友都不敢接近了,為了教堂好,一定要把他們都趕走!」劉神父總是笑而不答,他心裡頭一直掙扎著,其中他最放不下的是阿問和阿威(匿名)。
快要四十歲的阿問是「胎兒酒精綜合症」(Fetal alcohol syndrome, FAS)的患者,阿問的母親在妊娠期間酗酒,使他在胎兒階段就造成永久身心缺陷。和多數病患一樣,阿問在出生前中樞神經系統就遭到酒精無情破壞,他的神經細胞及腦部結構發育有障礙,成年後經常酗酒,更顯現出衝動、反應遲鈍、注意力不足及理解力差的精神狀況。因為自小在學校就是問題兒童,出社會也找不到工作,阿問誤入歧途過,從監獄出來後,成日酗酒,連家裡都待不下,就只有神父收容他。
阿問平日很沉默,看來有些傻乎乎,行動也不協調,但只要喝了一點酒,想起不如意的人生,或是心情莫名不好,就生龍活虎起來,經常對人咆哮。有時他在一樓罵人,在二樓主持彌撒的劉神父都不禁要皺眉頭,更讓教會的志工與教友感到頭疼。神父知道當阿問心情糟的時候,不要和他硬碰硬,理性的安撫也無法奏效。焦躁的阿問曾經幾度一面揮拳、一面對著神父吼叫:「我要錢買香菸啦!你給不給錢啊你?」
只見憂傷的神父從羞澀的阮囊中掏出一點錢:「阿問,去買菸!」藉由紙捲菸點燃的煙霧消散阿問的焦躁。
來自馬來西亞的志工黃婉秋說,不只阿問經常惹事,另一個更生人阿威也讓她和大家感到不安。阿威經常醉酒鬧事,和阿問一言不合就打起來,甚至作勢要攻擊對面國小的孩子。有一天晚上,阿威醉醺醺地坐在天主堂的院子裡,見到黃婉秋回來就拉著她的手:「婉秋,婉秋,我完了!你可以陪我講講話嗎?」
「怎麼了?」婉秋顫抖著聲音,把手掙脫。
「我可能因為疏忽照顧女兒,要再度回到監獄中,我完了!我完了!」阿威一直喃喃自語。
「我先回房放東西,等一會再來陪你。」婉秋急忙往樓上跑。
在房間中稍微穩定心情後,她到教堂內跟劉神父說:「神父,我很害怕,阿威又喝醉酒了,而且他很擔心又要回去坐牢。」
神父憂傷地說:「他又喝醉了,真糟糕!」
「為什麼不把他們送走,天主堂附近的鄰居也都不安心。」
「不可以!我沒辦法,如果把他們趕走,我的良心一定不安,會覺得……是不應該這樣。可是要把阿威送到戒酒中心,我手邊的錢也不夠。」
「可是,我會害怕。」
「不要害怕,我知道大家的恐懼,可是阿問和阿威本性都很善良,只要我花多點時間陪伴他們,多對他們付出關懷與愛心,最起碼他們不會發狠,不會做壞事,至少可以減少一些社會問題。」神父苦笑著,用眼神安慰婉秋,轉身去看顧阿威。
在李慧蘭眼中,就是因為劉神父一次又一次超乎常人的寬恕與包容,總是讓阿問和阿威覺得有家可歸,脾氣漸趨溫馴,甚至知道苦力不該由年長者承擔,會主動協助神父。他們跟在神父身邊,在彌撒時分派經書與歌本,擔任輔祭,甚至到安德啟智中心照顧腦性麻痺、唐氏症或身障的孩子。他們以能夠為神父分勞而感到驕傲,對照其他病弱的孩子,他們顯得身強體健,實在沒有悲觀的權利,慢慢振作了起來。
接下安德啟智院的千斤重擔
讓迷途羔羊重返正道固然備極艱辛,劉一峰神父還承擔了教養花東地區智障、殘障、遭棄養青少年的責任,管理安德啟智院,這是顧超前神父交給他的千斤重擔。
顧超前神父一九八○年在花蓮縣富里鄉傳教時,想起在法國的哥哥為了照顧家中一名智能不足的孩子,弄得身心俱疲,家庭陷入經濟困境。同樣悲慘的畫面也出現在他訪視過的許多弱勢家庭中。於是他創立了「安德啟智中心」,收容智商三十以下的中、重度先天性智障兒童,以及罹患腦性麻痺、自閉症等二至十八歲的兒童和青少年。以一對一的方式,依照孩子個別的差異,培養他們生活自理能力、感官知覺動作訓練、說話訓練、物理治療、體能活動,以及讀、寫、算、社會常識、美勞、律動等教學。
安德啟智中心創辦時,花東還是相當落後的農村,特殊教育得不到政府與企業的重視,顧超前神父積極向國外教會與企業募捐,幾乎半數的捐款都來自國外。一度經費不足,為了擴充教學設備,他還專程回到法國故鄉,變賣了自己的全部家產,讓弱勢與身心障礙有個學習的環境。顧神父堅信,殘障兒童需要家庭的溫暖和關懷。安德啟智中心的兒童,每天都要回家與家人團聚過夜,他不辭辛勞地接送,希望家人和孩子能緊密生活在一起,一起成長。
一九八二年九月,安德啟智中心遷移到人口更密集的玉里鎮現址。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六日,顧超前神父過世後,五十八歲的劉一峰神父接受教會指派,接下顧神父照顧花東地區身心障礙者的棒子。劉一峰很快就發現「安德」面臨了兩大挑戰:一是,「安德」的孩子經過近二十年的歲月,已經慢慢步入成年與中年,他們要如何獨立自主?二是,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外國的援助與捐款日漸減少,啟智中心的財務日益捉襟見肘,該怎麼辦?
面對日漸長大成人的「安德」院生,顧超前神父去世前一年的九月,已經在富里鄉東里村成立安德職訓部,可惜他來不及看到院生習得一技之長,就與世長辭。劉一峰知道,安德的孩子連生活自理都不容易,要能夠透過職業訓練習得工作技能,最終自給自足,是遙遠的夢想。但他和修女與同事們努力教導中重度障礙的院生製作竹掃把、木工、點心等等,目的不在貼補支出,而是希望藉由工作讓院生都有事情可做,為自己贏得更多尊嚴與他人的尊重。
一轉眼,劉一峰神父接手安德啟智中心也有十四年了,有三位院生已經超過四十歲,眼見很快就要超過法定收容四十五歲的上限。長年陪伴院生的社工李紅櫻說,由於身障者老化較快,加上部分智能不足或患有精神障礙者,長期依賴熟悉的社工、神職人員照顧,神父實在捨不得讓這些在安德成長與老去的院生離開,他們的家人也不放心。劉神父在鄉下買了塊地,期待興建「安德怡峰園」做為終生庇護所,讓年長院生得以安心地度過晚年。
劉一峰的責任愈來愈沉重,卻遭遇到經濟不景氣,國內外的捐贈日益萎縮,為了籌募經費,可讓他的頭髮愈來愈灰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