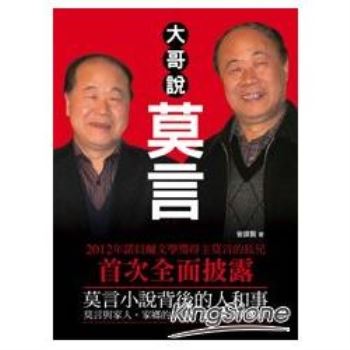一、莫言和他的小說
莫言小說中的人和事
莫言成名之後,尤其是電影《紅高粱》在柏林得獎之後,人們對莫言及其作品的研究很是熱鬧了一陣子。有人稱莫言為「怪才」。似乎莫言本身就是一個謎,一夜之間不知從哪裏冒出來殺上了文壇。也有人把小說與現實混為一談,憑主觀想像或道聽塗說,把小說中某些情節強加在我們家庭成員的頭上寫成論文發表,使得我們這樣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農民家庭蒙上了一層神奇的色彩。這幾年來,國內外一些文學界的朋友甚至不遠萬里來我們家鄉考察。其實,莫言是極普通的一個農民的兒子,甚至可以說直到現在他還是一個農民。他愛農民之所愛,恨農民之所恨,與農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作品,不管怎麼「現代」,如何「魔幻」,在我看來都是再現實不過的東西。它既不是歷史,更不是神話,都是普通的真正的小說。莫言的作品多用第一人稱來寫,其中不但有「我爺爺」、「我奶奶」、「父親」、「母親」、「小姑」,而且有時竟將真人姓名寫進作品中去,如《紅高粱》中的曹夢九、王文義,《築路》中的來書,《草鞋窨子》中的于大身、轆子張球,《生死疲勞》中的單幹戶……我曾經提醒過他不要用真人姓名以免引起糾紛,他的解釋是,用真人姓名在寫作時便於很快進入角色,易於發揮。從近兩年的作品看,莫言已經注意了這個問題,把真人姓名寫入作品的事已不多見了。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莫言作品中有時用了真人的姓名,但往往是真名之下無真事(歷史人物除外),真事往往用假名。人與事之間張冠李戴,移花接木,或乾脆「無中生有」,純乎是聯想或想像而已。總之,小說只能是小說,絕不能把小說當作歷史或報告文學來看。
為了給研究莫言作品的同志們提供一點資料,也為了澄清一些事實,特寫此文。
爺 爺
我們的爺爺管遵義,字居正,又字嵩峰,以此字行於世。生於1895年,1978年病故,享年84歲。我們的爺爺既沒有《秋水》、《紅高粱》裏爺爺那般傳奇式的英雄豪氣和壯舉,更沒有那般痛快淋漓的風流韻事。我們的爺爺是一個忠厚老實、勤儉持家、聰明靈巧的農民,與《大風》中的爺爺庶幾近之。爺爺一生務農,又會木匠手藝,種田是一把高手,木匠活也做得漂亮。不管多麼複雜的家什,只要看了樣子,他都能照樣做出來。過去用的木輪車,檀木軸斷了,柿木車耳子(軸套)破了,人們都喜歡到爺爺這裏來換新的,因為他換過的車子推起來吱吜吱吜叫得特別好聽。農村用的風箱,爺爺原來沒做過,後來,照樣做了一個,把出風口幾經改進,風箱嗚嗚地叫,聲音悅耳動聽。於是,人們都願意來找他做。
爺爺一生樂善好施,親友、鄰居來借錢、糧、柴草,有求必應,而且從來不登門討帳。最多到年關時對奶奶說:「某某還欠著什麼什麼沒還呢!」有很多就是白送。人家要還,他就說:「算了吧!多少年了,還提它做什麼?」小時我有一個印象,似乎那些找爺爺借東西的,壓根兒就不想還。加上還要撫養我三爺爺三奶奶死後留下的三個孤兒(我們的三叔、四叔、六叔),又經常接濟窮親戚窮朋友,日子也總是富不起來,土改時被定為中農。爺爺是文盲,但卻十分聰明,稱得上博聞強記。他能打一手好算盤,再複雜的帳目也可算清。過去村人買賣土地,不管地塊多複雜,他能很快算出它的面積。從三皇五帝至明清民國的歷史變遷,改朝換代的名人軼事,他可以一樁樁一件件講個頭頭是道。不少詩詞戲文他能夠背誦。更令人奇怪的是,他雖不識字,卻可以對照藥方從大爺爺(爺爺的哥哥)的藥櫥裏為病人抓藥。至於那滿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名人名勝的傳說,更是子孫輩夏日河堤上、冬季炕頭上百聽不厭的精神食糧。我有時候想,爺爺要是有文化,沒準也會當作家。準確地說,爺爺才是莫言的第一個老師。莫言作品中絕大多數故事傳說都是從爺爺那兒聽來的,如《球狀閃電》裏舉子趕考救螞蟻,《爆炸》裏狐狸煉丹,《金髮嬰兒》裏八個泥瓦匠廟裏避雨,《草鞋窨子》裏兩個姑娘乘涼、笤帚疙瘩成精,《紅高粱》裏綦翰林出殯等等。如果把爺爺講過的故事單獨回憶整理出來,怕是要出一本厚厚的《民間故事集》呢!
爺爺性格柔中有剛。他很少發火,從來不打罵孩子,罵人從不帶髒字。但他說話很有分量,批評的話,讓你一輩子忘不了,高興的話,讓你忍俊不禁。他曾說:「人生在世,誰都有春風得意的時候,但得意不要張狂;誰都會有倒楣不走運的時候,但跌倒了就要爬起來。越是有人看笑話,越是不能草雞了!」他還說:「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沒有受不了的罪。」這些話在我看來都是真理,讓我終生難忘,受益匪淺。
爺爺其實是很有情趣的。他有一桿鳥槍,有一張漁網,會打鳥打兔子,會打魚摸螃蟹。有什麼莊稼瓜菜新品種,他喜歡試種試栽。
爺爺的脾氣耿直抗上,很少有讓他服氣的人和事。對於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他老人家甚至一輩子都沒有叫過一聲「毛主席」。在家裏開口閉口都是「老毛」如何如何(同樣,提到蔣介石也是一口一個「老蔣」)。在那個年代,嚇得我們恨不得跑上去捂住他的嘴巴,要他小聲說,別叫人聽見。他說:「怕什麼?他和我年紀差不多,叫他『老毛』怎麼了?」後來,尤其是到了上世紀60年代,人們把「毛主席萬歲」喊得震天響,他才恍然大悟似地說:「老毛當皇上了,人能活一萬歲嗎?萬歲就是皇上啊!」
對於新生事物,他不大接受。開國之初,講中蘇友好,全國上下成立了中蘇友好協會。那時好像人人都是會員,發一個徽章戴著,一面小紅旗,上邊是毛澤東和史達林頭像。還有一支歌,人人會唱:「毛澤東,史達林,像太陽在天空照,紅旗在前面飄,全世界人民心一條,爭取人民民主,爭取世界和平……」他聽了很不以為然,說:「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天上怎麼會有兩個太陽?中蘇本是兩國,兩國如同兩人,現在好成什麼樣,將來就會打成什麼樣!」當時,我們稱蘇聯為「老大哥」,他也有看法,甚至說:「朝裏是不是出了秦檜?真給中國人丟臉!」這些話,當時是百分之百的「反動言論」。家人一起反對他,讓他別說。他說:「我又不到外邊去說。我說的對與不對,今後看!」
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他斷定用土爐子煉不出鐵,更煉不出鋼,純粹是浪費東西,禍害人民。農業生產「放衛星」,廣播喇叭裏說某地小麥畝產萬斤,他堅決不信。他說:「一市畝地,就那麼一點點地方,不用說長麥子,就是把麥子打好,光把麥粒鋪在那一畝地裏,一萬斤得鋪多厚?這肯定有假!」甚至反問我:「你不是說老毛是種地的出身,小時候還幹過農活嗎?一畝地能打多少糧食,他不知道?朝裏肯定出了奸臣了!」我沒見過畝產萬斤的小麥,也只好閉口無言。他曾預言,人民公社不是好折騰,折騰來折騰去,非餓死人不可。果然,三年困難接踵而來,村裏人人浮腫,天天死人,爺爺一手拉扯大為其成了家的三叔因饑餓而病死。生產隊裏只有幹不完的活,卻分不到足夠的糧。一家人靠爺爺度過荒年。當時他已年過六十,不去隊裏幹活,冒險偷偷地去邊遠地方開小塊荒地種地瓜。夏秋兩季,他去田野割草,曬乾後,等第二年春天送到農場,換回大豆、地瓜乾。剛剛四五歲的莫言因野菜難以下嚥而圍著飯桌哭鬧時,爺爺弄來的地瓜乾,無疑是比今日之蛋糕餅乾更為甘美的食品,給他幼小的心靈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爺爺一生務農,對土地有著深厚的感情。直到入社那一年,他為了幫一個親戚度過生活難關,還花高價把他的五畝地買過來。他相信世界大同,卻不贊成合作化,他說:「一家子親兄弟還要分家,張、王、李、趙湊在一塊,能有好嗎?」他對入社是極力反對的。為此,他氣得不吃不喝,要帶著我分家單幹,急得父親沒辦法,只好去西王家苓芝把他的姑父、爺爺的姐夫請了來做他的工作。最後達成協定,同意入社,但約法三章:一,爺爺永遠不去農業社裏幹活;二,農業社要他幹木匠活,送到家裏來,要現錢;三,農業社一旦垮了台,土地、牲口、農具原樣退回來。這約法三章真正落實了的,只有第一條,第二條是父親自掏腰包解決的。第三條一直到他臨終,「文革」」已經結束,公社也將撤銷,但農具早已毀壞,牲口早在困難時期就餓死了。
爺爺去世時,莫言給我寫信說:「祖父的死,使我感到心痛。他老人家一生含辛茹苦,農忙時辛勞耕作於田間,農閒時又持斧操鋸在作坊。他以剛直不阿的性格和嫺熟的木工工藝博得了鄉里的眾望,他為我們留下了很多值得學習的品質和精神。我至今不能忘記祖父帶我去割草的情景,以及他用青筋暴露的手揮動斧鑿的形象。他這種吃苦耐勞的精神,正是我缺乏的……前幾年我在家時,經常地和他拉一拉,故意請他講些古今軼事,所以頗得他的歡心,我也受益匪淺……」
爺爺19歲,奶奶20歲才成的親。這在當時已是晚婚年齡。二人艱苦創業,勤儉持家,勞作一生,生有一女二男(我們的父親和五叔),在鄉里有很高的威望。
奶 奶
我們的奶奶姓戴,如同舊社會的勞動婦女一樣,沒有自己的大名,在世時,農業社的社員名冊,稱她管戴氏。奶奶比爺爺大一歲,1971年去世,終年77歲。
儘管《紅高粱》裏的「奶奶」也姓戴,但我們的奶奶卻遠沒有九兒那般潑辣風流,也沒有《老槍》裏的「奶奶」那般殺伐決斷。我們的奶奶是一位極普通的老式家庭婦女。奶奶的娘家也是極普通的農民,因為她的父兄會竹器手藝,所以生活過得比一般農戶強。小時候曾聽奶奶發牢騷說,她和爺爺成親後,爺爺的以及後來子女們的衣服全是奶奶家負責的,我們家一概不管。奶奶雖然極普通,但確實很能幹。直至去世,奶奶是我們家實際上的大總管。那時父親和叔父沒有分家,一家十幾口人的吃穿,全由奶奶安排,儘管那些年月生活極艱難,奶奶勤儉持家,精打細算,一家人也未受凍餓之苦。奶奶的手極巧,我不只一次地聽我的大爺爺、外祖父誇她做的飯菜好吃,針線活漂亮。村裏有人家結婚,窗花、饅頭花常找她剪;喪事也找她去操辦。奶奶還會接生,新中國成立後雖說新式接生已經推行,但找她接生的仍很多。可以說,我們村現在60歲左右的人有一半是她老人家接到這個世界上來的。
奶奶膽子比爺爺大。聽奶奶說,有一年來日本鬼子,鬼子在外邊砸門,爺爺去開門,鬼子進門一腳將爺爺踢倒,刺刀對準爺爺胸口,嗚哇一叫,嚇得爺爺面如土色。倒是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爺爺。爺爺出門想跑,那鬼子一勾槍機,子彈從爺爺耳邊飛過。從此,只要聽說鬼子來了,鬼子影未見,爺爺就先跑了,往往是奶奶留守。我問奶奶當時怕不怕,奶奶說:「怎麼不怕?一有動靜就想上茅房!」即使如此,凡與兵們打交道的事爺爺再不敢出面,哪怕後來的八路軍、解放軍來了,開大會都是奶奶去。
奶奶一生未出過遠門,一生未見過樓房。上世紀60年代,我到上海讀大學。放假回來告訴她我們住在樓上,她不只一次問我:人怎樣上得去?用梯子嗎?我當然回答不是,並且給她解釋怎樣一層層走上去,還說高層樓可乘電梯等等。誰知奶奶越聽越糊塗,歎口氣道:「看不到真樓,越聽越不明白!」當時,整個高密縣只有縣城有兩座二層小樓,鄉下一律是平房,所以她老人家至死也沒弄明白樓是怎麼回事。
父 親
我們的父親管貽範,生於1923年。舊社會上過四年私塾,在我們鄉下已經算是知識份子了。所以,家鄉一解放就擔任了各種社會工作,記帳、掃盲,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到生產大隊,到國有農場耕作區,再到生產大隊,一直擔任會計,1982年才退休。幾十年的會計當下來,積累的帳冊、單據成捆成箱。他可以自豪地向村裏的老老少少說,他沒貪污過一分錢,沒有錯過一筆帳,沒有用過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辦過一次事,連記帳用的一支竹竿圓珠筆都是通過書記批准才買的。父親擔任大隊會計二十多年,一年四季白天和社員一起幹重活,下雨陰天和晚上記帳。每逢大隊偶爾擺酒席,他總是藉故推辭,拒不參加。
父親教育子侄十分嚴厲,子侄們,甚至他的同輩都怕他。我們小時,稍有差錯,非打即罵,有時到了蠻橫不講理的地步。他擔心我們「學問不成,莊戶不能」,對我們的學習抓得很緊。我讀小學時,父親經常檢查我的學習。有一次居然要我將一冊語文書倒背出來,背不出就打。等我讀了中學,一方面離家遠,每周回家一次,另一方面我讀的東西他也不懂了,所以不再檢查我的學習,但每學期的成績單必看。三年困難時期,我讀高中,同學中有的餓死,有的逃往東北。我也想去闖關東,回家一說,父親大怒,說:「供你上了十年學,什麼結果也沒有,要走,就別再回來!」父親希望我們走正道,望子成龍心切,加上生活困難,心情不好,所以很少給子女笑臉。莫言小時候頑皮,自然少不了挨打。有一次小莫言下地幹活,餓極了,偷了一個蘿蔔吃,被罰跪在毛主席像前。父親知道了,回家差一點把他打死,幸虧六嬸去請了爺爺來才解了圍。父親自己清正廉潔,容不得子侄們沾染不良習氣,敗壞管家門風。有一年,我叔父的二兒子十來歲時,去隊裏瓜地裏偷了幾個小瓜。雖然偷瓜摸棗是農村孩子常幹的事,而且又是侄兒,父親對他也是一頓好揍。後來我的這個叔兄弟不但考上了大學,而且研究生畢業,獲得碩士學位,後到美國留學,現已在美國定居。
父親不是黨員,但一直跟黨走,在鄉里很有威信。他孝敬爺爺奶奶,愛護弟弟(我們的五叔)。我們的五叔在供銷社棉花站工作。當年,區裏讓我父親脫產出來工作,父親把機會讓給五叔。嬸嬸和叔叔的四個孩子在家裏和父母一起生活,直到奶奶去世才分家。分家後,父親還像過去一樣照顧叔叔的孩子,還不時寄錢去資助上大學的。
父親今年已經90歲了,至今仍在鄉下。地裏的活已幹不動了,木匠活也不做了,但他仍然幫二弟家做點家務,種種小菜園,一刻也閒不住。
母 親
我母親姓高,1922年生於河崖鎮小高家莊(現名北高家)。大名高淑娟,但一輩子沒用過,公社化時生產隊裏的記工冊以及我們填表都寫管高氏。母親纏足,典型的農村婦女,沒有文化,因勞累過度,患有哮喘、肺氣腫等多種疾病,於1994年1月病故。母親是17歲嫁到我們家的。母親的親生母親在母親兩歲時就去世了。她來到我們家五十多年,當媳婦的時間比當婆婆的時間長,一直沒過上好日子,及至過上好日子,又老生病,母親常歎自己命苦。
母親生過七八個子女,活下來的只有我們兄妹四人。除我之外,莫言還有一位二哥和姐姐,莫言是母親最小的孩子。到莫言出生時,我們這個大家庭已有四個孩子。後來,我嬸嬸又生了三個兒子。莫言在家裏的位置無足輕重。本來窮人的孩子就如小豬小狗一般,這樣,莫言就不如路邊的一棵草了。母愛是有的,但要懂事的孩子自己去體會。天下父母哪有不愛自己孩子的?但母親為了這個大家庭,為了顧全大局,必須將愛藏在心底。記得困難時期,全家吃野菜,莫言和他堂姐(我叔父的女兒,僅比莫言大半歲)吃不下,有時母親單獨為他倆煮兩個地瓜或蒸一個不加野菜或加少量野菜的玉米麵餅子,小莫言飯量大,但他也只能和姐姐平分秋色。半個餅子姐姐吃了已飽,可小莫言卻不飽。儘管如此,母親也不能多分給莫言,結果莫言是吃不飽還要挨罵。
莫言小說中的人和事
莫言成名之後,尤其是電影《紅高粱》在柏林得獎之後,人們對莫言及其作品的研究很是熱鬧了一陣子。有人稱莫言為「怪才」。似乎莫言本身就是一個謎,一夜之間不知從哪裏冒出來殺上了文壇。也有人把小說與現實混為一談,憑主觀想像或道聽塗說,把小說中某些情節強加在我們家庭成員的頭上寫成論文發表,使得我們這樣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農民家庭蒙上了一層神奇的色彩。這幾年來,國內外一些文學界的朋友甚至不遠萬里來我們家鄉考察。其實,莫言是極普通的一個農民的兒子,甚至可以說直到現在他還是一個農民。他愛農民之所愛,恨農民之所恨,與農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作品,不管怎麼「現代」,如何「魔幻」,在我看來都是再現實不過的東西。它既不是歷史,更不是神話,都是普通的真正的小說。莫言的作品多用第一人稱來寫,其中不但有「我爺爺」、「我奶奶」、「父親」、「母親」、「小姑」,而且有時竟將真人姓名寫進作品中去,如《紅高粱》中的曹夢九、王文義,《築路》中的來書,《草鞋窨子》中的于大身、轆子張球,《生死疲勞》中的單幹戶……我曾經提醒過他不要用真人姓名以免引起糾紛,他的解釋是,用真人姓名在寫作時便於很快進入角色,易於發揮。從近兩年的作品看,莫言已經注意了這個問題,把真人姓名寫入作品的事已不多見了。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莫言作品中有時用了真人的姓名,但往往是真名之下無真事(歷史人物除外),真事往往用假名。人與事之間張冠李戴,移花接木,或乾脆「無中生有」,純乎是聯想或想像而已。總之,小說只能是小說,絕不能把小說當作歷史或報告文學來看。
為了給研究莫言作品的同志們提供一點資料,也為了澄清一些事實,特寫此文。
爺 爺
我們的爺爺管遵義,字居正,又字嵩峰,以此字行於世。生於1895年,1978年病故,享年84歲。我們的爺爺既沒有《秋水》、《紅高粱》裏爺爺那般傳奇式的英雄豪氣和壯舉,更沒有那般痛快淋漓的風流韻事。我們的爺爺是一個忠厚老實、勤儉持家、聰明靈巧的農民,與《大風》中的爺爺庶幾近之。爺爺一生務農,又會木匠手藝,種田是一把高手,木匠活也做得漂亮。不管多麼複雜的家什,只要看了樣子,他都能照樣做出來。過去用的木輪車,檀木軸斷了,柿木車耳子(軸套)破了,人們都喜歡到爺爺這裏來換新的,因為他換過的車子推起來吱吜吱吜叫得特別好聽。農村用的風箱,爺爺原來沒做過,後來,照樣做了一個,把出風口幾經改進,風箱嗚嗚地叫,聲音悅耳動聽。於是,人們都願意來找他做。
爺爺一生樂善好施,親友、鄰居來借錢、糧、柴草,有求必應,而且從來不登門討帳。最多到年關時對奶奶說:「某某還欠著什麼什麼沒還呢!」有很多就是白送。人家要還,他就說:「算了吧!多少年了,還提它做什麼?」小時我有一個印象,似乎那些找爺爺借東西的,壓根兒就不想還。加上還要撫養我三爺爺三奶奶死後留下的三個孤兒(我們的三叔、四叔、六叔),又經常接濟窮親戚窮朋友,日子也總是富不起來,土改時被定為中農。爺爺是文盲,但卻十分聰明,稱得上博聞強記。他能打一手好算盤,再複雜的帳目也可算清。過去村人買賣土地,不管地塊多複雜,他能很快算出它的面積。從三皇五帝至明清民國的歷史變遷,改朝換代的名人軼事,他可以一樁樁一件件講個頭頭是道。不少詩詞戲文他能夠背誦。更令人奇怪的是,他雖不識字,卻可以對照藥方從大爺爺(爺爺的哥哥)的藥櫥裏為病人抓藥。至於那滿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名人名勝的傳說,更是子孫輩夏日河堤上、冬季炕頭上百聽不厭的精神食糧。我有時候想,爺爺要是有文化,沒準也會當作家。準確地說,爺爺才是莫言的第一個老師。莫言作品中絕大多數故事傳說都是從爺爺那兒聽來的,如《球狀閃電》裏舉子趕考救螞蟻,《爆炸》裏狐狸煉丹,《金髮嬰兒》裏八個泥瓦匠廟裏避雨,《草鞋窨子》裏兩個姑娘乘涼、笤帚疙瘩成精,《紅高粱》裏綦翰林出殯等等。如果把爺爺講過的故事單獨回憶整理出來,怕是要出一本厚厚的《民間故事集》呢!
爺爺性格柔中有剛。他很少發火,從來不打罵孩子,罵人從不帶髒字。但他說話很有分量,批評的話,讓你一輩子忘不了,高興的話,讓你忍俊不禁。他曾說:「人生在世,誰都有春風得意的時候,但得意不要張狂;誰都會有倒楣不走運的時候,但跌倒了就要爬起來。越是有人看笑話,越是不能草雞了!」他還說:「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沒有受不了的罪。」這些話在我看來都是真理,讓我終生難忘,受益匪淺。
爺爺其實是很有情趣的。他有一桿鳥槍,有一張漁網,會打鳥打兔子,會打魚摸螃蟹。有什麼莊稼瓜菜新品種,他喜歡試種試栽。
爺爺的脾氣耿直抗上,很少有讓他服氣的人和事。對於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他老人家甚至一輩子都沒有叫過一聲「毛主席」。在家裏開口閉口都是「老毛」如何如何(同樣,提到蔣介石也是一口一個「老蔣」)。在那個年代,嚇得我們恨不得跑上去捂住他的嘴巴,要他小聲說,別叫人聽見。他說:「怕什麼?他和我年紀差不多,叫他『老毛』怎麼了?」後來,尤其是到了上世紀60年代,人們把「毛主席萬歲」喊得震天響,他才恍然大悟似地說:「老毛當皇上了,人能活一萬歲嗎?萬歲就是皇上啊!」
對於新生事物,他不大接受。開國之初,講中蘇友好,全國上下成立了中蘇友好協會。那時好像人人都是會員,發一個徽章戴著,一面小紅旗,上邊是毛澤東和史達林頭像。還有一支歌,人人會唱:「毛澤東,史達林,像太陽在天空照,紅旗在前面飄,全世界人民心一條,爭取人民民主,爭取世界和平……」他聽了很不以為然,說:「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天上怎麼會有兩個太陽?中蘇本是兩國,兩國如同兩人,現在好成什麼樣,將來就會打成什麼樣!」當時,我們稱蘇聯為「老大哥」,他也有看法,甚至說:「朝裏是不是出了秦檜?真給中國人丟臉!」這些話,當時是百分之百的「反動言論」。家人一起反對他,讓他別說。他說:「我又不到外邊去說。我說的對與不對,今後看!」
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他斷定用土爐子煉不出鐵,更煉不出鋼,純粹是浪費東西,禍害人民。農業生產「放衛星」,廣播喇叭裏說某地小麥畝產萬斤,他堅決不信。他說:「一市畝地,就那麼一點點地方,不用說長麥子,就是把麥子打好,光把麥粒鋪在那一畝地裏,一萬斤得鋪多厚?這肯定有假!」甚至反問我:「你不是說老毛是種地的出身,小時候還幹過農活嗎?一畝地能打多少糧食,他不知道?朝裏肯定出了奸臣了!」我沒見過畝產萬斤的小麥,也只好閉口無言。他曾預言,人民公社不是好折騰,折騰來折騰去,非餓死人不可。果然,三年困難接踵而來,村裏人人浮腫,天天死人,爺爺一手拉扯大為其成了家的三叔因饑餓而病死。生產隊裏只有幹不完的活,卻分不到足夠的糧。一家人靠爺爺度過荒年。當時他已年過六十,不去隊裏幹活,冒險偷偷地去邊遠地方開小塊荒地種地瓜。夏秋兩季,他去田野割草,曬乾後,等第二年春天送到農場,換回大豆、地瓜乾。剛剛四五歲的莫言因野菜難以下嚥而圍著飯桌哭鬧時,爺爺弄來的地瓜乾,無疑是比今日之蛋糕餅乾更為甘美的食品,給他幼小的心靈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爺爺一生務農,對土地有著深厚的感情。直到入社那一年,他為了幫一個親戚度過生活難關,還花高價把他的五畝地買過來。他相信世界大同,卻不贊成合作化,他說:「一家子親兄弟還要分家,張、王、李、趙湊在一塊,能有好嗎?」他對入社是極力反對的。為此,他氣得不吃不喝,要帶著我分家單幹,急得父親沒辦法,只好去西王家苓芝把他的姑父、爺爺的姐夫請了來做他的工作。最後達成協定,同意入社,但約法三章:一,爺爺永遠不去農業社裏幹活;二,農業社要他幹木匠活,送到家裏來,要現錢;三,農業社一旦垮了台,土地、牲口、農具原樣退回來。這約法三章真正落實了的,只有第一條,第二條是父親自掏腰包解決的。第三條一直到他臨終,「文革」」已經結束,公社也將撤銷,但農具早已毀壞,牲口早在困難時期就餓死了。
爺爺去世時,莫言給我寫信說:「祖父的死,使我感到心痛。他老人家一生含辛茹苦,農忙時辛勞耕作於田間,農閒時又持斧操鋸在作坊。他以剛直不阿的性格和嫺熟的木工工藝博得了鄉里的眾望,他為我們留下了很多值得學習的品質和精神。我至今不能忘記祖父帶我去割草的情景,以及他用青筋暴露的手揮動斧鑿的形象。他這種吃苦耐勞的精神,正是我缺乏的……前幾年我在家時,經常地和他拉一拉,故意請他講些古今軼事,所以頗得他的歡心,我也受益匪淺……」
爺爺19歲,奶奶20歲才成的親。這在當時已是晚婚年齡。二人艱苦創業,勤儉持家,勞作一生,生有一女二男(我們的父親和五叔),在鄉里有很高的威望。
奶 奶
我們的奶奶姓戴,如同舊社會的勞動婦女一樣,沒有自己的大名,在世時,農業社的社員名冊,稱她管戴氏。奶奶比爺爺大一歲,1971年去世,終年77歲。
儘管《紅高粱》裏的「奶奶」也姓戴,但我們的奶奶卻遠沒有九兒那般潑辣風流,也沒有《老槍》裏的「奶奶」那般殺伐決斷。我們的奶奶是一位極普通的老式家庭婦女。奶奶的娘家也是極普通的農民,因為她的父兄會竹器手藝,所以生活過得比一般農戶強。小時候曾聽奶奶發牢騷說,她和爺爺成親後,爺爺的以及後來子女們的衣服全是奶奶家負責的,我們家一概不管。奶奶雖然極普通,但確實很能幹。直至去世,奶奶是我們家實際上的大總管。那時父親和叔父沒有分家,一家十幾口人的吃穿,全由奶奶安排,儘管那些年月生活極艱難,奶奶勤儉持家,精打細算,一家人也未受凍餓之苦。奶奶的手極巧,我不只一次地聽我的大爺爺、外祖父誇她做的飯菜好吃,針線活漂亮。村裏有人家結婚,窗花、饅頭花常找她剪;喪事也找她去操辦。奶奶還會接生,新中國成立後雖說新式接生已經推行,但找她接生的仍很多。可以說,我們村現在60歲左右的人有一半是她老人家接到這個世界上來的。
奶奶膽子比爺爺大。聽奶奶說,有一年來日本鬼子,鬼子在外邊砸門,爺爺去開門,鬼子進門一腳將爺爺踢倒,刺刀對準爺爺胸口,嗚哇一叫,嚇得爺爺面如土色。倒是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爺爺。爺爺出門想跑,那鬼子一勾槍機,子彈從爺爺耳邊飛過。從此,只要聽說鬼子來了,鬼子影未見,爺爺就先跑了,往往是奶奶留守。我問奶奶當時怕不怕,奶奶說:「怎麼不怕?一有動靜就想上茅房!」即使如此,凡與兵們打交道的事爺爺再不敢出面,哪怕後來的八路軍、解放軍來了,開大會都是奶奶去。
奶奶一生未出過遠門,一生未見過樓房。上世紀60年代,我到上海讀大學。放假回來告訴她我們住在樓上,她不只一次問我:人怎樣上得去?用梯子嗎?我當然回答不是,並且給她解釋怎樣一層層走上去,還說高層樓可乘電梯等等。誰知奶奶越聽越糊塗,歎口氣道:「看不到真樓,越聽越不明白!」當時,整個高密縣只有縣城有兩座二層小樓,鄉下一律是平房,所以她老人家至死也沒弄明白樓是怎麼回事。
父 親
我們的父親管貽範,生於1923年。舊社會上過四年私塾,在我們鄉下已經算是知識份子了。所以,家鄉一解放就擔任了各種社會工作,記帳、掃盲,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到生產大隊,到國有農場耕作區,再到生產大隊,一直擔任會計,1982年才退休。幾十年的會計當下來,積累的帳冊、單據成捆成箱。他可以自豪地向村裏的老老少少說,他沒貪污過一分錢,沒有錯過一筆帳,沒有用過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辦過一次事,連記帳用的一支竹竿圓珠筆都是通過書記批准才買的。父親擔任大隊會計二十多年,一年四季白天和社員一起幹重活,下雨陰天和晚上記帳。每逢大隊偶爾擺酒席,他總是藉故推辭,拒不參加。
父親教育子侄十分嚴厲,子侄們,甚至他的同輩都怕他。我們小時,稍有差錯,非打即罵,有時到了蠻橫不講理的地步。他擔心我們「學問不成,莊戶不能」,對我們的學習抓得很緊。我讀小學時,父親經常檢查我的學習。有一次居然要我將一冊語文書倒背出來,背不出就打。等我讀了中學,一方面離家遠,每周回家一次,另一方面我讀的東西他也不懂了,所以不再檢查我的學習,但每學期的成績單必看。三年困難時期,我讀高中,同學中有的餓死,有的逃往東北。我也想去闖關東,回家一說,父親大怒,說:「供你上了十年學,什麼結果也沒有,要走,就別再回來!」父親希望我們走正道,望子成龍心切,加上生活困難,心情不好,所以很少給子女笑臉。莫言小時候頑皮,自然少不了挨打。有一次小莫言下地幹活,餓極了,偷了一個蘿蔔吃,被罰跪在毛主席像前。父親知道了,回家差一點把他打死,幸虧六嬸去請了爺爺來才解了圍。父親自己清正廉潔,容不得子侄們沾染不良習氣,敗壞管家門風。有一年,我叔父的二兒子十來歲時,去隊裏瓜地裏偷了幾個小瓜。雖然偷瓜摸棗是農村孩子常幹的事,而且又是侄兒,父親對他也是一頓好揍。後來我的這個叔兄弟不但考上了大學,而且研究生畢業,獲得碩士學位,後到美國留學,現已在美國定居。
父親不是黨員,但一直跟黨走,在鄉里很有威信。他孝敬爺爺奶奶,愛護弟弟(我們的五叔)。我們的五叔在供銷社棉花站工作。當年,區裏讓我父親脫產出來工作,父親把機會讓給五叔。嬸嬸和叔叔的四個孩子在家裏和父母一起生活,直到奶奶去世才分家。分家後,父親還像過去一樣照顧叔叔的孩子,還不時寄錢去資助上大學的。
父親今年已經90歲了,至今仍在鄉下。地裏的活已幹不動了,木匠活也不做了,但他仍然幫二弟家做點家務,種種小菜園,一刻也閒不住。
母 親
我母親姓高,1922年生於河崖鎮小高家莊(現名北高家)。大名高淑娟,但一輩子沒用過,公社化時生產隊裏的記工冊以及我們填表都寫管高氏。母親纏足,典型的農村婦女,沒有文化,因勞累過度,患有哮喘、肺氣腫等多種疾病,於1994年1月病故。母親是17歲嫁到我們家的。母親的親生母親在母親兩歲時就去世了。她來到我們家五十多年,當媳婦的時間比當婆婆的時間長,一直沒過上好日子,及至過上好日子,又老生病,母親常歎自己命苦。
母親生過七八個子女,活下來的只有我們兄妹四人。除我之外,莫言還有一位二哥和姐姐,莫言是母親最小的孩子。到莫言出生時,我們這個大家庭已有四個孩子。後來,我嬸嬸又生了三個兒子。莫言在家裏的位置無足輕重。本來窮人的孩子就如小豬小狗一般,這樣,莫言就不如路邊的一棵草了。母愛是有的,但要懂事的孩子自己去體會。天下父母哪有不愛自己孩子的?但母親為了這個大家庭,為了顧全大局,必須將愛藏在心底。記得困難時期,全家吃野菜,莫言和他堂姐(我叔父的女兒,僅比莫言大半歲)吃不下,有時母親單獨為他倆煮兩個地瓜或蒸一個不加野菜或加少量野菜的玉米麵餅子,小莫言飯量大,但他也只能和姐姐平分秋色。半個餅子姐姐吃了已飽,可小莫言卻不飽。儘管如此,母親也不能多分給莫言,結果莫言是吃不飽還要挨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