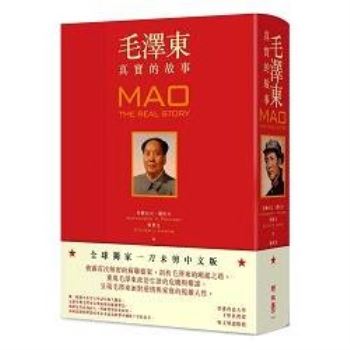第三十二章 「海瑞罷官」
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六月回到北京,又碰上騷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絕大多數黨組織中都發現可恥的「資產階級墮落」的例證。至少有半數黨組織,已被「階級敵人」奪了權。自從一九六四年底,效忠毛澤東的幹部已經向他報告地方層級出現此一有威脅的情勢,現在則更加嚴重。這一點是無可避免的,因為每個黨官員都能揣摩偉大的舵手的情緒,只往上呈報毛澤東愛聽的消息。這就是毛澤東本人創造的極權主義制度。出於命運的諷刺,他成為這套制度最大的受害人。
他所活著的可怕的幻象世界,激發他要有實際行動。即使他已年逾七旬,他仍然不像孔子的「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這還不是毛澤東和這位偉大聖人唯一不同的地方,孔子也說過:「六十而耳順」。1毛主席直到嚥氣都做不到這一點。
回到北京,他和江青就文化事務有一番長談。早先,她已經說服他需要揭發吳晗所寫的《海瑞罷官》歷史劇的「反革命」性質。吳晗這本劇本寫於一九六一年一月,隨即在中國向少數觀眾公演。它講的是十六世紀一位勇敢的清官海瑞敢犯顏直諫腐敗的明朝皇帝。劇中的海瑞向皇帝說:「過去您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您現在在幹什麼?趕快改正您的錯誤!讓老百姓過幸福的日子。您已經犯了太多錯誤,可是還認為自己永遠是對的,聽不進所有的批評。」江青認為吳晗是「以古諷今」,拿海瑞來暗喻彭德懷。他那「惡毒」的劇本意在打擊偉大舵手的權威。可是,中國的看戲者卻沒有感覺到這齣戲的「犯罪」意圖,不以為忠實
追隨毛澤東的吳晗有任何不忠誠。
江青早早就質疑這份劇本,但是起初毛澤東或任何人都不支持她。連康生也對江青的主張存疑。大家都曉得,毛澤東喜歡海瑞。他從海瑞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一個誠實、正直的革命家」,力抗墮落階級的惡行。一九六一年底,毛澤東還題字送給吳晗一本《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然而,到了一九六五年,毛澤東開始覺得草木皆兵,到處都是敵人;現在江青終於成功地引起他對吳晗的疑懼。這位學者兼劇作家也是北京市副市長,算得上是彭真的直接部屬。而彭真又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親信副手。在毛主席發脹的腦子裡,吳晗、彭真、劉少奇和鄧小平這四個人組成一支「邪惡的樂隊」。
一九六四年底,毛澤東在政治局全國會議上宣泄他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不滿。他之所以發作是因為會議前夕,鄧小平建議毛澤東不用參加開會。這個建議並沒有不尋常,因為毛澤東當時身體不適。毛澤東還是出現在議事廳,照舊大談階級鬥爭。他甚至說,目前農村的主要矛盾出在一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另一方是廣大的群眾。劉少奇試圖反駁這個觀點,因為他長久以來即擔心反修正主義的鬥爭會無限上綱,而他本人可能成為目標。他意識到主席的矛頭已經轉向他。毛澤東非常生氣,決定大鬧一場。隔了幾天,他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黨章來到會場,向同志們喧嚷大叫,他手上這兩本書都賦與他身為公民、身為黨員,有權利發表意見。毛澤東聲稱:「現在,你們一個不讓我參加黨的會議(指鄧小平),違反黨章;一個不讓我發言(指劉少奇),違反憲法。」
不久之後,他想到江青對吳晗的評論。現在,一切都明白了。吳晗奉彭真、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命令寫劇本,夢想粉碎我!若干年後他告訴史諾,換下劉少奇的決定是一九六五年一月即有的想法,因為劉少奇「強烈反對」正在展開的剷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史諾根據毛澤東的說
法寫下:當時「許多權力—各省及地方黨委、尤其是北京市委之內的宣傳工作權力—都不在他控制下」。因此,他決定「更需要搞個人崇拜,以便鼓勵群眾解散反毛的黨官僚」。(待續) 一九六五年二月,毛澤東派江青到上海,「安排發表批判《海瑞罷官》歷史劇的一篇文章」。江青在當地黨報編輯姚文元協助下進行任務。江青和上海的左派張春橋派專差秘密送到北京給毛澤東過目,更動十一次文稿。6一直要到夏末,他才覺得「大致滿意」。他把定稿交還給江青,建議讓中央其他領導人也過目,但是江青表示,「文章就這樣發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來同志、康生同志看了。」江青怕的是,如果周恩來和康生拿到文稿,劉少奇和鄧小平也會要求讀它。他們決定照江青建議進行。文章刊登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掀起了旋即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場新的群眾運動。
毛澤東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讀了江青的盟友、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一份報告,對文化情勢有悲觀的描繪時,即有在文化領域發動激烈革命的想法。毛澤東當時擬了一項決議文,聲稱文藝界的「流氓」正在宣傳封建和資產階級的價值、而非社會主義的價值。8他原先就表示憂心有創意的知識分子、包括有些是黨員,迴避階級鬥爭。然而,直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初,他才要求中共中央成立一個五人小組負責文化革命事務。「溫和派」不欲和主席衝突,支持這個主意;五人小組由劉少奇倚重的彭真主持,康生則代表強硬路線的毛派。不過,毛澤東並不滿意這個小組。彭真及其同夥想藉由組織學術討論,限制黨對文化領域的干預。毛澤東則深信非得要在文藝界進行階級清洗不可。
整個夏天,毛澤東對派人撰文、準備批判吳晗這件事守口如瓶。他不打算在北京發表這篇文章,因為他還不想引爆公開衝突。他打算悄悄地攻打吳晗、彭真以及他們背後的支持者劉少奇和鄧小平。劉少奇和鄧小平似乎沒有察覺偉大舵手的情緒,也可能覺得自己不是全無招架之力。九月底,彭真在五人小組會議上宣布:「人人平等,不問他們是否中央委員或主席。」
毛澤東絕對不能原諒他這樣說。他立刻示意姚文元發表文章。姚文元譴責吳晗的劇本是資產階級在反無產階級專政及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之一項武器。在毛澤東治下的中國,這樣的指控等同於宣判死刑。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章發表後兩天,毛澤東取道天津、濟南、徐州、蚌埠(安徽省)和南京,前往上海這個左派大本營。他很不滿意沿路所見的地方領導人。人人熱切於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達成的「重大成功」。沒有人關切反修正主義的鬥爭或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只有到了上海,空氣中才充滿了激進主義。可是他不能鬆懈。從北京傳來的消息,令他心存警戒。彭真對於《文匯報》刊出的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初步反應是不准中央的報刊雜誌轉載,並且把針對劇本的討論框限在學術領域內。吳晗針對上海方面的批評,其反應就是指出《文匯報》這篇文章有許多不符
史實的引述。吳晗寫說:「姚文元這樣批評我,我也不怕。不過我覺得這樣牽強附會的批評,亂扣帽子,這種風氣很不好,誰還敢寫東西,誰還敢寫歷史?」
讀完這個回應後,毛澤東失眠了。彭真和北京市委控制了中央報刊雜誌,不肯投降。鬥爭要升高。毛澤東日後回想說:「我在北京無能為力。」彭真和他的支持者不曉得姚文元背後的靠山是誰。但是周恩來介入了。他告訴彭真,如果北京的傳媒繼續置之不理,毛澤東打算把姚文元的文章出單行本。《人民日報》終於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轉載這篇惡意攻訐的文章,但是又加上評論文字,秉持彭真精神,指它是學者之間的論戰。
毛澤東樂了,寫了一首詩,描述一頭大鳥思念風暴。
鯤鵬展翅九萬里,
翻起扶搖羊角。
背負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民城郭。
炮火連天,彈痕遍地。
嚇倒蓬間雀,怎麼得了。
哎呀,我想飛躍。
借問你去何方?
雀兒答道,
有仙山瓊閣,
不見前年秋月朗,
訂了三家條約。
還有吃的,
土豆燒熟了,
再添牛肉。
不須放屁,
試看天地翻覆。
的確,在毛澤東居住的世界,已經天翻地覆。他希望把全國鬧得天翻地覆。(待續) 毛澤東精神一振,又從上海跑到杭州,來到寧靜的西里湖畔,他終於可以放輕鬆了。現在一切都順心如意。然而,過了十天之後,他又坐不住了,再次上路。他渴望作戰。到了上海,他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然後回到杭州;陳伯達、康生和其他親信等著他,聽取指示。然後他又跑到廬山、廣州和南寧,再於新年後回到杭州。二月初,他經長沙,往武漢去。
他住進武漢東湖邊的東湖賓館,在這裡召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四名成員:彭真、康生、陸定一(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和吳冷西(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他們帶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有一位與會者描述會議進行情況:
毛澤東問彭真一個問題:「吳晗真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嗎?」彭真還來不及回答,康生已插嘴說,吳晗的作品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毒草」。沒有人敢出言反駁。毛澤東打破沉默說:「當然,任何人有不同的觀點,都應該說出來。」……最後,彭真發言。他要為他帶來的文件辯護。
彭真說:「學術問題還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陸定一支持彭真。毛澤東總結說:「你們去寫,我不看了。」
彭真、陸定一和吳冷西都以為毛澤東核准他們的報告,沒察覺這是陷阱。他們向主席報告後,就輕鬆地逛武昌和漢口聞名的善本古書書肆。隔了幾天,中央通過、並分發此一劃為「絕密」的文件。
現在,毛澤東鬥志昂揚,發起行動。五月中旬,毛澤東氣憤彭真,核定了江青所起草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報告;這是經林彪批准,於二月解放軍召開一項會議所做出的結論。和彭真等人那份報告不一樣,這份報告談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反對毛澤東思想,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即由文藝官員在鼓吹、宣傳。<紀要>強調:「『寫真實』論……就是他們的代表性論點。」它主張「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三月中旬,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邀請劉少奇、周恩來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出席。某些中央委員也參加會議。許多人對他們聽到的話大為震驚。毛澤東不僅攻擊彭真、吳晗和吳冷西散布資產階級文化,他也號召在全國大、中、小學發動階級鬥爭。「讓學生們……大鬧一番。我們不需要盲目的信念或束縳。我們需要新的知識分子、新的論點、新的創造。我們需要的是,讓學生推翻教授。」
一星期之後,毛澤東在杭州對江青、康生等最親信的人士說,北京市委和中央宣傳部替壞分子辯護、沒有支持左派。他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他再度把吳晗貼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標籤。他也批評《人民日報》前任總編輯鄧拓,和北京市委統戰部前任部長廖沫沙,指責他們在首都報紙發表雜文諷刺時政,而他們文章的共同作者不是別人、正是吳晗。
在毛澤東施壓下,中共中央把江青的︿紀要﹀報告發下去。六天後,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要求將彭真的報告作廢、並解散文革五人小組,換上另一個新小組,直屬政治局常委會。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出席會議,在日記中記下毛澤東憤怒地表示:「出修正主義,不止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
毛澤東這時候無意回北京,因此他要求劉少奇等人在中南海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執行這些決定。他對副手們說:「﹃西風吹渭水,落葉下長安﹄,灰塵不掃不少。」劉少奇為了自保,出賣彭真;五月間,他這個忠心的副手被免除一切職務,並被指控散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種「資產階級」口號。四月底,彭真已遭到軟禁。(待續) 陸定一同時也遭罷黜,原因還不只因為他在武漢討論四月報告時支持彭真。一九六六年初,林彪的太太葉群發現她素來視為「戰友」的陸定一太太嚴慰冰,竟然十分痛恨她。嚴慰冰究竟是因為嫉妒、還是其他什麼原因仇恨葉群,我們並不清楚(陸定一後來說他太太有精神分裂症)。從一九六○年起,就在「葉同志」成為她丈夫在國防部的辦公廳主任之後,「嚴同志」開始向她及林彪其他家人濫發匿名信。大半的信說葉群生性淫蕩,一再讓林彪戴綠帽子。嚴慰冰發給林彪女兒豆豆的信,一口咬定葉群不是她的親生母親。
葉群和林彪大怒,要求有關單位嚴懲散布謠言者,把數十封匿名信交給公安部調查。公安部後來移送陸定一的太太。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嚴慰冰被捕,罪名是從事「反革命活動」。隔了幾天,倒楣的陸定一也和彭真同一命運,遭到軟禁。
在毛澤東堅持下,他們兩人和總參謀長羅瑞卿、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一起湊成一個「反黨集團」;羅、楊兩人稍早即因完全不相干的理由遭到免職。把他們湊在一起,是要顯示正在展開的文化大革命不僅針對文宣部門官僚,也要對付其他「滲透進入黨、政、軍的資產階級代表」,換句話說,要對付「準備伺機奪權,把無產階級專政改成資產階級專政」的任何人。
五月十六日,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厲聲質問陸定一:「你和你太太已經陰謀活動了許久,毀謗葉群同志和我全家,灌爆一大堆匿名信。你究竟想幹什麼?說!」
在場人人轉頭看陸定一。會議開始前,人人桌上已擺了一張林彪親筆寫的聲明書:「我證明:(一)葉群和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二)葉群與王實味根本沒有戀愛過;(三)老虎、豆豆(指林立果、林立衡)是我與葉群親生的子女;(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的一切全係造謠。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嚇得渾身發抖的陸定一趕緊跟他愛妻劃分界線:「嚴慰冰﹝的確﹞寫了匿名信,但是我完全不知情。她沒有和我商量過、沒有給我看過,我也沒有起疑過。」
林彪暴跳如雷,用拳捶桌:「你胡說!你怎麼會不知道你太太在做什麼?」
陸定一好不容易才回了一句:「先生不曉得他們太太在做什麼,有那麼不尋常嗎?」他根本不曉得他說了什麼。
人人都僵住了。林彪則氣瘋了,咆哮:「我要斃了你!」康生立刻做出裁決:「陸定一是間諜。」
康生也指控「四個反黨分子」為首的彭真是間諜,聲稱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一直和蔣介石的特務維持秘密聯繫。他也把彭真的岳父列為「大叛徒」。
五月十六日,同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通過下達全國各級黨委組織的特別公告,宣布解散五人小組,另成立直屬政治局常委會的中央文革小組。這份公告首次號召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
公告有幾段話,包括另成立直屬政治局常委會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那一段,由毛澤東本人親自撰寫。它最重要的部分是: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份公告邀請全民參與文化大革命,這是它最鮮明的特色。在此之前,黨內的清算鬥爭全都門戶森嚴、關起門來進行。現在主席賦與人民權力評斷「修正主義分子」,包括「大黨閥」在內。可是沒有人曉得,偉大的舵手在講,像赫魯雪夫這類的人「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究竟指的是誰。(待續) 人人皆知毛澤東的接班人是劉少奇,但沒有人料想他是叛徒—或許,毛主席身邊少數圈內人士除外。康生回憶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強調,修正主義者、反動派和叛徒躲在我們身邊、受到我們友人的信任。當時,許多幹部不瞭解毛主席的意思,認為影射的是羅﹝瑞卿﹞、彭﹝真﹞。但是,事實上,彭真已經暴露。沒有人敢亂猜誰是我們之中的叛徒。」康生又說:「我沒有意識到指的是劉少奇,對於毛主席這項重要指示只有很膚淺的瞭解。」
上海左派人物張春橋也有同樣說法:「運動開始時,很少人瞭解主席的話,尤其是有關『像赫魯雪夫這類的人還躲在我們身邊』這一段—因此反應也非常遲緩。當時,我不瞭解這段話。我只想到彭真,完全沒料到是劉少奇。」
毛澤東認為他有關「中國的赫魯雪夫」這一段是公告的重點,立刻就告訴康生和陳伯達。他要這份公告不僅「炸」黨、還要「炸」整個社會。
康生被毛澤東提示,後來解釋說:
文化大革命起源自社會主義陣營裡仍然存在階級鬥爭的意念。這個意念既是理論又是實踐。經驗已證明,就是在列寧的故鄉—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布爾什維克黨已成為修正主義者。我們二十多年來在建設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經驗,特別是最近發生在東歐的事件,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已在那裡復辟了,由此使我們提出在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一場革命的方式是什麼的問題。為
了解決這個問題,毛主席發動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根據康生的說法,偉大的舵手原本提議以三年的時間搞文化大革命。第一年(一九六六年六月至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任務是「動員人民」;第二年(一九六七年六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是「取得重大勝利」;第三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六月)是「完成革命」。這位毛澤東的忠心追隨者聲稱:「以這麼大的革命來說,三年不算太長的時間。」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一項重要報告。他首次暗示批評劉少奇「從來沒有提倡毛澤東思想」。康生提議把「毛澤東思想」這個詞語改為「毛澤東主義」,但是,毛澤東再次反對更改。
中國陷入混亂,但是毛澤東根本不介意。他反而還添油加醋。很顯然,年邁的主席因為指揮群眾運動而恢復活力。他覺得遭到敵人包圍,因此把所有賭注壓在這一寶上面。為了粉碎「陰謀者」,他再度轉向人民訴求。這一次他向沒有經驗、可又狂熱效忠他的年輕人—大學及技術學院,以及中等學校學生—發出訴求。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他已經認定,學生應該「打倒他們的教授」。現在,既已「揭發」了彭真及其他黨內「走資派」,他清楚地意識到青年學生的熱情比往常都更加高昂。他只要發出訊號,革命怒火即可席捲教育學府。他每天收到無所不在的公安機關、張春橋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上海分部,以及學運分子的報告。有個學生(湊巧是某個幹部的兒子)寫說:「誰能料想到彭真、羅瑞卿這樣的老幹部,其實是危險人物?現在我覺得我們只能信賴毛主席、只能信賴黨中央,我們必須懷疑每一個人。如果有人不執行毛主席的指示,那個人就要被攻打。」這個砲手將成為他的新衛兵。沒有一個「走資派」官僚抵擋得住他們強大的壓力。
他思索把年輕人更深地引入「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需要,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他認為「階級鬥爭」是重點,而高等學府裡教的課程大部分都有害。因此,教室授課時數應該大幅減少,不再讓學生聽一大堆廢話,要讓他們花時間積極參與「階級鬥爭」。他憤慨地認為,「現在的﹝教育﹞方法有害才智、有害青年。我不贊成。必須停止讀太多書!」他也不喜歡學科考試這套制度。他說:「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他指的是刻板依據規定舉行考試的方法。「這無非是你會我不會,你寫了我再抄一遍,也可以。」他說,有些考試根本全該廢了。他在文革之前兩年多、就在一次會議上說過:「目前的教育制度、課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全得改,因為它們困住人。」(待續) 他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即政治局公告展開文化大革命之前九天,也在信中向林彪談到這個主題。總而言之,從教育機構中清除「走資派」,並動員青年參加「階級鬥爭」,是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任務之一。毛澤東指派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副組長,康生出任小組的顧問。
康生派他太太到北京大學,找她認識的聶元梓。聶元梓擔任北大哲學系黨組書記。康生太太鼓勵聶元梓動員幾個學生批評北京市委及北大領導人。四十五歲的聶元梓立刻行動,於五月二十五日偕同六個學生在餐廳牆上張貼大字報。她攻擊北京市委高教工作部幾個領導,以及北大校長(他也是北大黨委書記),「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以當時的政治規矩來說,這是造反。但是,聶元梓和她的學校當然不怕;他們有中央文革小組撐腰。
康生一讀到大字報全文,立刻將它整理出來,送呈人在杭州的毛澤東。毛澤東立刻稱讚這段胡說八道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並且命令康生和陳伯達透過大眾傳媒廣為發表。他下條子說:「康生與伯達同志!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毛澤東。六月一日。」幾個小時後,他又打電話到北京給這兩個副手,強調這份大字報是一九六○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比起巴黎公社宣言還更重要」。這時,陳伯達已派出一支所謂的工作組,接管了《人民日報》編輯部。毛澤東早就不滿意《人民日報》,指責它受到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的控制,大家不應該讀它。現在,它已經和新華社一樣,都回到正統毛派的控制下。因此陳伯達毫無困難,立即執行主席的指示。
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多位政治局領導人不曉得該如何處理。主席不在,他們亂了手腳,不知該怎麼辦。由於毛澤東要求加調公安部兩個師的警力加強防衛首都,而林彪也下令不准對抗革命學生;這下子他們更加狼狽,不知如何是好。
武裝部隊全力支持主席,左派青年肆無忌憚。
這時候,劉少奇和鄧小平也慢慢改組北京市委、撤換北大校長。這些行動立刻在全國引起回響。許多高教機構學生效法聶元梓,也攻擊他們的校長和黨委。大學陷入大字報流感、學生停止上課。
六月九日,稍微忙了過來的劉少奇、鄧小平,偕同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新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陶鑄,前往杭州,勸毛澤東回北京。但是毛澤東一口就拒絕。然後他們徵求他同意,黨要派工作組到全國所有大學「恢復秩序」,參加談話的陳伯達反對此一建議。毛澤東未置可否。他就像在武漢接見彭真時一樣,讓人莫測高深地表示:「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
他和以前一樣,要誘使「敵人」完全亮相。他還是一個老方法,「讓那些討厭的東西全部爬出來,否則牠們若只爬出來一半,隨時又可以躲起來」。奇怪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這樣經驗老到的政客竟然沒看穿他的伎倆。
他們迷迷糊糊地回到北京,立即採取了兩個相互矛盾的決定:一方面,全國各級學校「暫時」停課「六個月」,取消考試;另一方面,他們承認派工作組到所有大學去「恢復秩序」是正確的。他們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不久,上萬個人被編組為工作組,派到北京及全國各地去。
他們犯了絕大的錯誤。毛澤東正是希望他們這樣做,他才好指控「敵人」「壓迫」群眾。他明白,只要工作組出現在校園,那些已被挑激起來的左派分子一定會挑釁,雙方的衝突勢必發展為流血對抗。他坐在高山上俯視情勢發展,欣喜若狂:「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待續) 他在六月中旬離開杭州,回韶山老家,不過只逗留了十一天。六月底,他又到了武漢,照舊下榻於東湖邊的東湖賓館。在櫻桃樹下享受著清涼的微風,他在平靜的環境下思索,終於決定該出手對「潛伏在共產黨領導圈中的走資派黑幫」予以決定性的重擊。七月八日,他在給江青的信中透露他的想法: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多次掃除。
他把這封信寄到北京給江青,然後決定再給中國人民、甚至全世界一個大驚奇。七十二歲的他決定再次下長江游泳。
他在七月十六日下水。當然他沒有要游渡長江,而是和往常一樣順流而下,浮游了約九英里,全程費時一小時又五分鐘。但是它讓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民興奮莫名。新華社報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中國人民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主席在宜人的風浪下於長江游泳。一小時又五分鐘,他游了約十五公里……這則令人欣喜的消息……很快就傳遍武漢。全市歡欣鼓舞,消息口耳相傳。人人都說:『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是那麼健康,這是全中華民族最大的福氣。這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最大的福氣。』」
在毛澤東下水游泳這一天 —
揚子江畔旗海飄揚、掛出大型海報,人群萬頭攢動,擴音器播放雄偉的<東方紅>曲調,唱出對我們敬愛的毛主席的讚美……歡呼如雷聲般響起,與笛號匯為一聲。毛主席神采奕奕,站在汽艇甲板……在水面上,你可以看到紅旗飄揚,許多布條貼出毛主席的訓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要時刻提高警惕」、「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毛主席向熱情的群眾揮手……他高聲喊出:「同志們,大家好!」有一隊兩百多人的年輕泳將、小學生,特別吸引毛主席注意。這些八到十四歲的少年先鋒隊(人在水中、高舉牌子)亮出「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標語,並且唱著「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歌,充分展現毛澤東時代少年先鋒隊的熱情……快艇靠近武昌岸邊。毛主席下水游泳,時間上午十一點整。夏天時,長江水流湍急。毛主席先游自由式,接著換上仰式、側式……當時鐘指向已經過了一小時又五分鐘……毛主席爬上岸;他精神奕奕,毫無倦容。
毛澤東英勇壯舉的新聞,也令國外許多人震驚。但不是人人都相信中國的宣傳:七十二歲的毛澤東以一小時多的時間游了九英里!根本沒有人提毛澤東其實是順流漂浮。
職業游泳好手特別拿這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來調侃。國際游泳總會(International Swimming Association)會長威廉.柏吉.菲力浦斯(William Berge Phillips︶甚至發函邀請毛澤東參加在加拿大的兩場比賽。他尖酸刻薄地寫說:「我們聽說閣下在七月十六日,以非常了不起的一小時五分鐘成績游了九英里。由於十英里游泳的世界記錄於去年在魁北克一項傳統比賽中,由世界最快的游泳好手之一、德國籍的賀曼.威廉斯(Herman Willemse) 所締造,那是四小時又三十五分鐘。您已經合格,可參加這兩項比賽。」菲力浦斯會長進一步指出,義大利泳將吉里歐.特拉瓦吉里歐(Giulio Travaglio)一九六六年二月在阿根廷的艾
爾桂連湖(Lake El Quillén)已經刷新記錄,但是他的成績三小時五十六分鐘,和毛主席一比還是望塵莫及。毛澤東的成績顯示,他平均速度是每百碼二四.六秒;可是迄今世界上尚無人可在平均四五.六秒內完成這項紀錄。菲力浦斯尖舌辣嘴地寫說:「或許毛主席在轉為職業選手之前,願意代表紅色中國參加下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但是如果他想要輕鬆賺點錢,我建議他今年夏天參加職業游泳比賽,好好給威廉斯、特拉瓦吉里歐及其他人上一課,他們連替他舉蠟燭都不夠看。」
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回到北京,立刻給劉少奇和鄧小平顏色看。他一回到北京,先住進西郊的釣魚台賓館,故意不回中南海住—因為劉少奇和鄧小平住在中南海。劉少奇立刻趕到釣魚台賓館,但是毛澤東不肯接見。毛澤東的秘書告訴大驚失色的劉少奇:「主席已經休息了。」其實,毛澤東正和康生、陳伯達闢室密談;他們兩人當然藉機抹黑劉少奇和鄧小平。劉少奇一直要到第二天夜裡才見到毛澤東。對於劉少奇而言,這場談話非常不愉快。毛澤東連珠砲般痛罵,劉少奇的「工作組不行,前市委爛了,中宣部爛了,文化部爛了,高教部也爛了,《人民日報》也不好」。劉少奇像熱鍋上的螞蟻。同時,毛澤東步步進逼,技巧地以眾人辜負他的期望之姿出現。他在八天內召開七次會議,要求召回「起了阻礙作用、幫助反革命」的工作組。他痛罵說:「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我們不應該限制群眾……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暴跳如雷的毛主席指控政治局領導人破壞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壓力下,劉少奇和鄧小平得到周恩來及北京市委新領導班子的協助,七月二十九日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召開大規模的學運分子會議。參加者逾一萬人。劉少奇和鄧小平試圖說明他們的行動,但是結結巴巴說不清楚。劉少奇尤其可憐;他承認說:「我……坦白說……不知道……如何推動『文化大革命』。」大會堂陷入一片死寂。鄧小平的女兒也在現場,不禁落淚。
然而,「敵人」「像小孩般的喃喃之語」只讓毛澤東更為生氣,他現在嗅到了血腥味。劉少奇講話的時候,毛澤東隱身坐在幕後。鄧小平和忠心的周恩來發言時,他還是沒有現身。等到人人都說完了,他才掀開布幕,在眾人驚呼中走向講台。學生們著魔似地狂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澤東在台上走前走後,頻頻揮手。
偉大的表演者正在做他最精彩的演出。灰頭土臉的鄧小平和劉少奇沒有辦法,只能參加這一幕演出,拚命地和大家一起向折磨他們的這個人鼓掌。
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六月回到北京,又碰上騷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絕大多數黨組織中都發現可恥的「資產階級墮落」的例證。至少有半數黨組織,已被「階級敵人」奪了權。自從一九六四年底,效忠毛澤東的幹部已經向他報告地方層級出現此一有威脅的情勢,現在則更加嚴重。這一點是無可避免的,因為每個黨官員都能揣摩偉大的舵手的情緒,只往上呈報毛澤東愛聽的消息。這就是毛澤東本人創造的極權主義制度。出於命運的諷刺,他成為這套制度最大的受害人。
他所活著的可怕的幻象世界,激發他要有實際行動。即使他已年逾七旬,他仍然不像孔子的「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這還不是毛澤東和這位偉大聖人唯一不同的地方,孔子也說過:「六十而耳順」。1毛主席直到嚥氣都做不到這一點。
回到北京,他和江青就文化事務有一番長談。早先,她已經說服他需要揭發吳晗所寫的《海瑞罷官》歷史劇的「反革命」性質。吳晗這本劇本寫於一九六一年一月,隨即在中國向少數觀眾公演。它講的是十六世紀一位勇敢的清官海瑞敢犯顏直諫腐敗的明朝皇帝。劇中的海瑞向皇帝說:「過去您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您現在在幹什麼?趕快改正您的錯誤!讓老百姓過幸福的日子。您已經犯了太多錯誤,可是還認為自己永遠是對的,聽不進所有的批評。」江青認為吳晗是「以古諷今」,拿海瑞來暗喻彭德懷。他那「惡毒」的劇本意在打擊偉大舵手的權威。可是,中國的看戲者卻沒有感覺到這齣戲的「犯罪」意圖,不以為忠實
追隨毛澤東的吳晗有任何不忠誠。
江青早早就質疑這份劇本,但是起初毛澤東或任何人都不支持她。連康生也對江青的主張存疑。大家都曉得,毛澤東喜歡海瑞。他從海瑞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一個誠實、正直的革命家」,力抗墮落階級的惡行。一九六一年底,毛澤東還題字送給吳晗一本《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然而,到了一九六五年,毛澤東開始覺得草木皆兵,到處都是敵人;現在江青終於成功地引起他對吳晗的疑懼。這位學者兼劇作家也是北京市副市長,算得上是彭真的直接部屬。而彭真又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親信副手。在毛主席發脹的腦子裡,吳晗、彭真、劉少奇和鄧小平這四個人組成一支「邪惡的樂隊」。
一九六四年底,毛澤東在政治局全國會議上宣泄他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不滿。他之所以發作是因為會議前夕,鄧小平建議毛澤東不用參加開會。這個建議並沒有不尋常,因為毛澤東當時身體不適。毛澤東還是出現在議事廳,照舊大談階級鬥爭。他甚至說,目前農村的主要矛盾出在一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另一方是廣大的群眾。劉少奇試圖反駁這個觀點,因為他長久以來即擔心反修正主義的鬥爭會無限上綱,而他本人可能成為目標。他意識到主席的矛頭已經轉向他。毛澤東非常生氣,決定大鬧一場。隔了幾天,他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黨章來到會場,向同志們喧嚷大叫,他手上這兩本書都賦與他身為公民、身為黨員,有權利發表意見。毛澤東聲稱:「現在,你們一個不讓我參加黨的會議(指鄧小平),違反黨章;一個不讓我發言(指劉少奇),違反憲法。」
不久之後,他想到江青對吳晗的評論。現在,一切都明白了。吳晗奉彭真、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命令寫劇本,夢想粉碎我!若干年後他告訴史諾,換下劉少奇的決定是一九六五年一月即有的想法,因為劉少奇「強烈反對」正在展開的剷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史諾根據毛澤東的說
法寫下:當時「許多權力—各省及地方黨委、尤其是北京市委之內的宣傳工作權力—都不在他控制下」。因此,他決定「更需要搞個人崇拜,以便鼓勵群眾解散反毛的黨官僚」。(待續) 一九六五年二月,毛澤東派江青到上海,「安排發表批判《海瑞罷官》歷史劇的一篇文章」。江青在當地黨報編輯姚文元協助下進行任務。江青和上海的左派張春橋派專差秘密送到北京給毛澤東過目,更動十一次文稿。6一直要到夏末,他才覺得「大致滿意」。他把定稿交還給江青,建議讓中央其他領導人也過目,但是江青表示,「文章就這樣發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來同志、康生同志看了。」江青怕的是,如果周恩來和康生拿到文稿,劉少奇和鄧小平也會要求讀它。他們決定照江青建議進行。文章刊登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掀起了旋即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場新的群眾運動。
毛澤東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讀了江青的盟友、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一份報告,對文化情勢有悲觀的描繪時,即有在文化領域發動激烈革命的想法。毛澤東當時擬了一項決議文,聲稱文藝界的「流氓」正在宣傳封建和資產階級的價值、而非社會主義的價值。8他原先就表示憂心有創意的知識分子、包括有些是黨員,迴避階級鬥爭。然而,直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初,他才要求中共中央成立一個五人小組負責文化革命事務。「溫和派」不欲和主席衝突,支持這個主意;五人小組由劉少奇倚重的彭真主持,康生則代表強硬路線的毛派。不過,毛澤東並不滿意這個小組。彭真及其同夥想藉由組織學術討論,限制黨對文化領域的干預。毛澤東則深信非得要在文藝界進行階級清洗不可。
整個夏天,毛澤東對派人撰文、準備批判吳晗這件事守口如瓶。他不打算在北京發表這篇文章,因為他還不想引爆公開衝突。他打算悄悄地攻打吳晗、彭真以及他們背後的支持者劉少奇和鄧小平。劉少奇和鄧小平似乎沒有察覺偉大舵手的情緒,也可能覺得自己不是全無招架之力。九月底,彭真在五人小組會議上宣布:「人人平等,不問他們是否中央委員或主席。」
毛澤東絕對不能原諒他這樣說。他立刻示意姚文元發表文章。姚文元譴責吳晗的劇本是資產階級在反無產階級專政及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之一項武器。在毛澤東治下的中國,這樣的指控等同於宣判死刑。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章發表後兩天,毛澤東取道天津、濟南、徐州、蚌埠(安徽省)和南京,前往上海這個左派大本營。他很不滿意沿路所見的地方領導人。人人熱切於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達成的「重大成功」。沒有人關切反修正主義的鬥爭或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只有到了上海,空氣中才充滿了激進主義。可是他不能鬆懈。從北京傳來的消息,令他心存警戒。彭真對於《文匯報》刊出的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初步反應是不准中央的報刊雜誌轉載,並且把針對劇本的討論框限在學術領域內。吳晗針對上海方面的批評,其反應就是指出《文匯報》這篇文章有許多不符
史實的引述。吳晗寫說:「姚文元這樣批評我,我也不怕。不過我覺得這樣牽強附會的批評,亂扣帽子,這種風氣很不好,誰還敢寫東西,誰還敢寫歷史?」
讀完這個回應後,毛澤東失眠了。彭真和北京市委控制了中央報刊雜誌,不肯投降。鬥爭要升高。毛澤東日後回想說:「我在北京無能為力。」彭真和他的支持者不曉得姚文元背後的靠山是誰。但是周恩來介入了。他告訴彭真,如果北京的傳媒繼續置之不理,毛澤東打算把姚文元的文章出單行本。《人民日報》終於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轉載這篇惡意攻訐的文章,但是又加上評論文字,秉持彭真精神,指它是學者之間的論戰。
毛澤東樂了,寫了一首詩,描述一頭大鳥思念風暴。
鯤鵬展翅九萬里,
翻起扶搖羊角。
背負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民城郭。
炮火連天,彈痕遍地。
嚇倒蓬間雀,怎麼得了。
哎呀,我想飛躍。
借問你去何方?
雀兒答道,
有仙山瓊閣,
不見前年秋月朗,
訂了三家條約。
還有吃的,
土豆燒熟了,
再添牛肉。
不須放屁,
試看天地翻覆。
的確,在毛澤東居住的世界,已經天翻地覆。他希望把全國鬧得天翻地覆。(待續) 毛澤東精神一振,又從上海跑到杭州,來到寧靜的西里湖畔,他終於可以放輕鬆了。現在一切都順心如意。然而,過了十天之後,他又坐不住了,再次上路。他渴望作戰。到了上海,他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然後回到杭州;陳伯達、康生和其他親信等著他,聽取指示。然後他又跑到廬山、廣州和南寧,再於新年後回到杭州。二月初,他經長沙,往武漢去。
他住進武漢東湖邊的東湖賓館,在這裡召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四名成員:彭真、康生、陸定一(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和吳冷西(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他們帶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有一位與會者描述會議進行情況:
毛澤東問彭真一個問題:「吳晗真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嗎?」彭真還來不及回答,康生已插嘴說,吳晗的作品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毒草」。沒有人敢出言反駁。毛澤東打破沉默說:「當然,任何人有不同的觀點,都應該說出來。」……最後,彭真發言。他要為他帶來的文件辯護。
彭真說:「學術問題還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陸定一支持彭真。毛澤東總結說:「你們去寫,我不看了。」
彭真、陸定一和吳冷西都以為毛澤東核准他們的報告,沒察覺這是陷阱。他們向主席報告後,就輕鬆地逛武昌和漢口聞名的善本古書書肆。隔了幾天,中央通過、並分發此一劃為「絕密」的文件。
現在,毛澤東鬥志昂揚,發起行動。五月中旬,毛澤東氣憤彭真,核定了江青所起草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報告;這是經林彪批准,於二月解放軍召開一項會議所做出的結論。和彭真等人那份報告不一樣,這份報告談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反對毛澤東思想,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即由文藝官員在鼓吹、宣傳。<紀要>強調:「『寫真實』論……就是他們的代表性論點。」它主張「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三月中旬,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邀請劉少奇、周恩來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出席。某些中央委員也參加會議。許多人對他們聽到的話大為震驚。毛澤東不僅攻擊彭真、吳晗和吳冷西散布資產階級文化,他也號召在全國大、中、小學發動階級鬥爭。「讓學生們……大鬧一番。我們不需要盲目的信念或束縳。我們需要新的知識分子、新的論點、新的創造。我們需要的是,讓學生推翻教授。」
一星期之後,毛澤東在杭州對江青、康生等最親信的人士說,北京市委和中央宣傳部替壞分子辯護、沒有支持左派。他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他再度把吳晗貼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標籤。他也批評《人民日報》前任總編輯鄧拓,和北京市委統戰部前任部長廖沫沙,指責他們在首都報紙發表雜文諷刺時政,而他們文章的共同作者不是別人、正是吳晗。
在毛澤東施壓下,中共中央把江青的︿紀要﹀報告發下去。六天後,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要求將彭真的報告作廢、並解散文革五人小組,換上另一個新小組,直屬政治局常委會。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出席會議,在日記中記下毛澤東憤怒地表示:「出修正主義,不止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
毛澤東這時候無意回北京,因此他要求劉少奇等人在中南海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執行這些決定。他對副手們說:「﹃西風吹渭水,落葉下長安﹄,灰塵不掃不少。」劉少奇為了自保,出賣彭真;五月間,他這個忠心的副手被免除一切職務,並被指控散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種「資產階級」口號。四月底,彭真已遭到軟禁。(待續) 陸定一同時也遭罷黜,原因還不只因為他在武漢討論四月報告時支持彭真。一九六六年初,林彪的太太葉群發現她素來視為「戰友」的陸定一太太嚴慰冰,竟然十分痛恨她。嚴慰冰究竟是因為嫉妒、還是其他什麼原因仇恨葉群,我們並不清楚(陸定一後來說他太太有精神分裂症)。從一九六○年起,就在「葉同志」成為她丈夫在國防部的辦公廳主任之後,「嚴同志」開始向她及林彪其他家人濫發匿名信。大半的信說葉群生性淫蕩,一再讓林彪戴綠帽子。嚴慰冰發給林彪女兒豆豆的信,一口咬定葉群不是她的親生母親。
葉群和林彪大怒,要求有關單位嚴懲散布謠言者,把數十封匿名信交給公安部調查。公安部後來移送陸定一的太太。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嚴慰冰被捕,罪名是從事「反革命活動」。隔了幾天,倒楣的陸定一也和彭真同一命運,遭到軟禁。
在毛澤東堅持下,他們兩人和總參謀長羅瑞卿、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一起湊成一個「反黨集團」;羅、楊兩人稍早即因完全不相干的理由遭到免職。把他們湊在一起,是要顯示正在展開的文化大革命不僅針對文宣部門官僚,也要對付其他「滲透進入黨、政、軍的資產階級代表」,換句話說,要對付「準備伺機奪權,把無產階級專政改成資產階級專政」的任何人。
五月十六日,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厲聲質問陸定一:「你和你太太已經陰謀活動了許久,毀謗葉群同志和我全家,灌爆一大堆匿名信。你究竟想幹什麼?說!」
在場人人轉頭看陸定一。會議開始前,人人桌上已擺了一張林彪親筆寫的聲明書:「我證明:(一)葉群和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二)葉群與王實味根本沒有戀愛過;(三)老虎、豆豆(指林立果、林立衡)是我與葉群親生的子女;(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的一切全係造謠。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嚇得渾身發抖的陸定一趕緊跟他愛妻劃分界線:「嚴慰冰﹝的確﹞寫了匿名信,但是我完全不知情。她沒有和我商量過、沒有給我看過,我也沒有起疑過。」
林彪暴跳如雷,用拳捶桌:「你胡說!你怎麼會不知道你太太在做什麼?」
陸定一好不容易才回了一句:「先生不曉得他們太太在做什麼,有那麼不尋常嗎?」他根本不曉得他說了什麼。
人人都僵住了。林彪則氣瘋了,咆哮:「我要斃了你!」康生立刻做出裁決:「陸定一是間諜。」
康生也指控「四個反黨分子」為首的彭真是間諜,聲稱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一直和蔣介石的特務維持秘密聯繫。他也把彭真的岳父列為「大叛徒」。
五月十六日,同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通過下達全國各級黨委組織的特別公告,宣布解散五人小組,另成立直屬政治局常委會的中央文革小組。這份公告首次號召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
公告有幾段話,包括另成立直屬政治局常委會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那一段,由毛澤東本人親自撰寫。它最重要的部分是: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份公告邀請全民參與文化大革命,這是它最鮮明的特色。在此之前,黨內的清算鬥爭全都門戶森嚴、關起門來進行。現在主席賦與人民權力評斷「修正主義分子」,包括「大黨閥」在內。可是沒有人曉得,偉大的舵手在講,像赫魯雪夫這類的人「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究竟指的是誰。(待續) 人人皆知毛澤東的接班人是劉少奇,但沒有人料想他是叛徒—或許,毛主席身邊少數圈內人士除外。康生回憶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強調,修正主義者、反動派和叛徒躲在我們身邊、受到我們友人的信任。當時,許多幹部不瞭解毛主席的意思,認為影射的是羅﹝瑞卿﹞、彭﹝真﹞。但是,事實上,彭真已經暴露。沒有人敢亂猜誰是我們之中的叛徒。」康生又說:「我沒有意識到指的是劉少奇,對於毛主席這項重要指示只有很膚淺的瞭解。」
上海左派人物張春橋也有同樣說法:「運動開始時,很少人瞭解主席的話,尤其是有關『像赫魯雪夫這類的人還躲在我們身邊』這一段—因此反應也非常遲緩。當時,我不瞭解這段話。我只想到彭真,完全沒料到是劉少奇。」
毛澤東認為他有關「中國的赫魯雪夫」這一段是公告的重點,立刻就告訴康生和陳伯達。他要這份公告不僅「炸」黨、還要「炸」整個社會。
康生被毛澤東提示,後來解釋說:
文化大革命起源自社會主義陣營裡仍然存在階級鬥爭的意念。這個意念既是理論又是實踐。經驗已證明,就是在列寧的故鄉—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布爾什維克黨已成為修正主義者。我們二十多年來在建設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經驗,特別是最近發生在東歐的事件,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已在那裡復辟了,由此使我們提出在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一場革命的方式是什麼的問題。為
了解決這個問題,毛主席發動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根據康生的說法,偉大的舵手原本提議以三年的時間搞文化大革命。第一年(一九六六年六月至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任務是「動員人民」;第二年(一九六七年六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是「取得重大勝利」;第三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六月)是「完成革命」。這位毛澤東的忠心追隨者聲稱:「以這麼大的革命來說,三年不算太長的時間。」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一項重要報告。他首次暗示批評劉少奇「從來沒有提倡毛澤東思想」。康生提議把「毛澤東思想」這個詞語改為「毛澤東主義」,但是,毛澤東再次反對更改。
中國陷入混亂,但是毛澤東根本不介意。他反而還添油加醋。很顯然,年邁的主席因為指揮群眾運動而恢復活力。他覺得遭到敵人包圍,因此把所有賭注壓在這一寶上面。為了粉碎「陰謀者」,他再度轉向人民訴求。這一次他向沒有經驗、可又狂熱效忠他的年輕人—大學及技術學院,以及中等學校學生—發出訴求。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他已經認定,學生應該「打倒他們的教授」。現在,既已「揭發」了彭真及其他黨內「走資派」,他清楚地意識到青年學生的熱情比往常都更加高昂。他只要發出訊號,革命怒火即可席捲教育學府。他每天收到無所不在的公安機關、張春橋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上海分部,以及學運分子的報告。有個學生(湊巧是某個幹部的兒子)寫說:「誰能料想到彭真、羅瑞卿這樣的老幹部,其實是危險人物?現在我覺得我們只能信賴毛主席、只能信賴黨中央,我們必須懷疑每一個人。如果有人不執行毛主席的指示,那個人就要被攻打。」這個砲手將成為他的新衛兵。沒有一個「走資派」官僚抵擋得住他們強大的壓力。
他思索把年輕人更深地引入「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需要,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他認為「階級鬥爭」是重點,而高等學府裡教的課程大部分都有害。因此,教室授課時數應該大幅減少,不再讓學生聽一大堆廢話,要讓他們花時間積極參與「階級鬥爭」。他憤慨地認為,「現在的﹝教育﹞方法有害才智、有害青年。我不贊成。必須停止讀太多書!」他也不喜歡學科考試這套制度。他說:「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他指的是刻板依據規定舉行考試的方法。「這無非是你會我不會,你寫了我再抄一遍,也可以。」他說,有些考試根本全該廢了。他在文革之前兩年多、就在一次會議上說過:「目前的教育制度、課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全得改,因為它們困住人。」(待續) 他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即政治局公告展開文化大革命之前九天,也在信中向林彪談到這個主題。總而言之,從教育機構中清除「走資派」,並動員青年參加「階級鬥爭」,是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任務之一。毛澤東指派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副組長,康生出任小組的顧問。
康生派他太太到北京大學,找她認識的聶元梓。聶元梓擔任北大哲學系黨組書記。康生太太鼓勵聶元梓動員幾個學生批評北京市委及北大領導人。四十五歲的聶元梓立刻行動,於五月二十五日偕同六個學生在餐廳牆上張貼大字報。她攻擊北京市委高教工作部幾個領導,以及北大校長(他也是北大黨委書記),「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以當時的政治規矩來說,這是造反。但是,聶元梓和她的學校當然不怕;他們有中央文革小組撐腰。
康生一讀到大字報全文,立刻將它整理出來,送呈人在杭州的毛澤東。毛澤東立刻稱讚這段胡說八道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並且命令康生和陳伯達透過大眾傳媒廣為發表。他下條子說:「康生與伯達同志!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毛澤東。六月一日。」幾個小時後,他又打電話到北京給這兩個副手,強調這份大字報是一九六○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比起巴黎公社宣言還更重要」。這時,陳伯達已派出一支所謂的工作組,接管了《人民日報》編輯部。毛澤東早就不滿意《人民日報》,指責它受到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的控制,大家不應該讀它。現在,它已經和新華社一樣,都回到正統毛派的控制下。因此陳伯達毫無困難,立即執行主席的指示。
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多位政治局領導人不曉得該如何處理。主席不在,他們亂了手腳,不知該怎麼辦。由於毛澤東要求加調公安部兩個師的警力加強防衛首都,而林彪也下令不准對抗革命學生;這下子他們更加狼狽,不知如何是好。
武裝部隊全力支持主席,左派青年肆無忌憚。
這時候,劉少奇和鄧小平也慢慢改組北京市委、撤換北大校長。這些行動立刻在全國引起回響。許多高教機構學生效法聶元梓,也攻擊他們的校長和黨委。大學陷入大字報流感、學生停止上課。
六月九日,稍微忙了過來的劉少奇、鄧小平,偕同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新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陶鑄,前往杭州,勸毛澤東回北京。但是毛澤東一口就拒絕。然後他們徵求他同意,黨要派工作組到全國所有大學「恢復秩序」,參加談話的陳伯達反對此一建議。毛澤東未置可否。他就像在武漢接見彭真時一樣,讓人莫測高深地表示:「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
他和以前一樣,要誘使「敵人」完全亮相。他還是一個老方法,「讓那些討厭的東西全部爬出來,否則牠們若只爬出來一半,隨時又可以躲起來」。奇怪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這樣經驗老到的政客竟然沒看穿他的伎倆。
他們迷迷糊糊地回到北京,立即採取了兩個相互矛盾的決定:一方面,全國各級學校「暫時」停課「六個月」,取消考試;另一方面,他們承認派工作組到所有大學去「恢復秩序」是正確的。他們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不久,上萬個人被編組為工作組,派到北京及全國各地去。
他們犯了絕大的錯誤。毛澤東正是希望他們這樣做,他才好指控「敵人」「壓迫」群眾。他明白,只要工作組出現在校園,那些已被挑激起來的左派分子一定會挑釁,雙方的衝突勢必發展為流血對抗。他坐在高山上俯視情勢發展,欣喜若狂:「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待續) 他在六月中旬離開杭州,回韶山老家,不過只逗留了十一天。六月底,他又到了武漢,照舊下榻於東湖邊的東湖賓館。在櫻桃樹下享受著清涼的微風,他在平靜的環境下思索,終於決定該出手對「潛伏在共產黨領導圈中的走資派黑幫」予以決定性的重擊。七月八日,他在給江青的信中透露他的想法: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多次掃除。
他把這封信寄到北京給江青,然後決定再給中國人民、甚至全世界一個大驚奇。七十二歲的他決定再次下長江游泳。
他在七月十六日下水。當然他沒有要游渡長江,而是和往常一樣順流而下,浮游了約九英里,全程費時一小時又五分鐘。但是它讓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民興奮莫名。新華社報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中國人民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主席在宜人的風浪下於長江游泳。一小時又五分鐘,他游了約十五公里……這則令人欣喜的消息……很快就傳遍武漢。全市歡欣鼓舞,消息口耳相傳。人人都說:『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是那麼健康,這是全中華民族最大的福氣。這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最大的福氣。』」
在毛澤東下水游泳這一天 —
揚子江畔旗海飄揚、掛出大型海報,人群萬頭攢動,擴音器播放雄偉的<東方紅>曲調,唱出對我們敬愛的毛主席的讚美……歡呼如雷聲般響起,與笛號匯為一聲。毛主席神采奕奕,站在汽艇甲板……在水面上,你可以看到紅旗飄揚,許多布條貼出毛主席的訓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要時刻提高警惕」、「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毛主席向熱情的群眾揮手……他高聲喊出:「同志們,大家好!」有一隊兩百多人的年輕泳將、小學生,特別吸引毛主席注意。這些八到十四歲的少年先鋒隊(人在水中、高舉牌子)亮出「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標語,並且唱著「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歌,充分展現毛澤東時代少年先鋒隊的熱情……快艇靠近武昌岸邊。毛主席下水游泳,時間上午十一點整。夏天時,長江水流湍急。毛主席先游自由式,接著換上仰式、側式……當時鐘指向已經過了一小時又五分鐘……毛主席爬上岸;他精神奕奕,毫無倦容。
毛澤東英勇壯舉的新聞,也令國外許多人震驚。但不是人人都相信中國的宣傳:七十二歲的毛澤東以一小時多的時間游了九英里!根本沒有人提毛澤東其實是順流漂浮。
職業游泳好手特別拿這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來調侃。國際游泳總會(International Swimming Association)會長威廉.柏吉.菲力浦斯(William Berge Phillips︶甚至發函邀請毛澤東參加在加拿大的兩場比賽。他尖酸刻薄地寫說:「我們聽說閣下在七月十六日,以非常了不起的一小時五分鐘成績游了九英里。由於十英里游泳的世界記錄於去年在魁北克一項傳統比賽中,由世界最快的游泳好手之一、德國籍的賀曼.威廉斯(Herman Willemse) 所締造,那是四小時又三十五分鐘。您已經合格,可參加這兩項比賽。」菲力浦斯會長進一步指出,義大利泳將吉里歐.特拉瓦吉里歐(Giulio Travaglio)一九六六年二月在阿根廷的艾
爾桂連湖(Lake El Quillén)已經刷新記錄,但是他的成績三小時五十六分鐘,和毛主席一比還是望塵莫及。毛澤東的成績顯示,他平均速度是每百碼二四.六秒;可是迄今世界上尚無人可在平均四五.六秒內完成這項紀錄。菲力浦斯尖舌辣嘴地寫說:「或許毛主席在轉為職業選手之前,願意代表紅色中國參加下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但是如果他想要輕鬆賺點錢,我建議他今年夏天參加職業游泳比賽,好好給威廉斯、特拉瓦吉里歐及其他人上一課,他們連替他舉蠟燭都不夠看。」
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回到北京,立刻給劉少奇和鄧小平顏色看。他一回到北京,先住進西郊的釣魚台賓館,故意不回中南海住—因為劉少奇和鄧小平住在中南海。劉少奇立刻趕到釣魚台賓館,但是毛澤東不肯接見。毛澤東的秘書告訴大驚失色的劉少奇:「主席已經休息了。」其實,毛澤東正和康生、陳伯達闢室密談;他們兩人當然藉機抹黑劉少奇和鄧小平。劉少奇一直要到第二天夜裡才見到毛澤東。對於劉少奇而言,這場談話非常不愉快。毛澤東連珠砲般痛罵,劉少奇的「工作組不行,前市委爛了,中宣部爛了,文化部爛了,高教部也爛了,《人民日報》也不好」。劉少奇像熱鍋上的螞蟻。同時,毛澤東步步進逼,技巧地以眾人辜負他的期望之姿出現。他在八天內召開七次會議,要求召回「起了阻礙作用、幫助反革命」的工作組。他痛罵說:「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我們不應該限制群眾……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暴跳如雷的毛主席指控政治局領導人破壞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壓力下,劉少奇和鄧小平得到周恩來及北京市委新領導班子的協助,七月二十九日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召開大規模的學運分子會議。參加者逾一萬人。劉少奇和鄧小平試圖說明他們的行動,但是結結巴巴說不清楚。劉少奇尤其可憐;他承認說:「我……坦白說……不知道……如何推動『文化大革命』。」大會堂陷入一片死寂。鄧小平的女兒也在現場,不禁落淚。
然而,「敵人」「像小孩般的喃喃之語」只讓毛澤東更為生氣,他現在嗅到了血腥味。劉少奇講話的時候,毛澤東隱身坐在幕後。鄧小平和忠心的周恩來發言時,他還是沒有現身。等到人人都說完了,他才掀開布幕,在眾人驚呼中走向講台。學生們著魔似地狂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澤東在台上走前走後,頻頻揮手。
偉大的表演者正在做他最精彩的演出。灰頭土臉的鄧小平和劉少奇沒有辦法,只能參加這一幕演出,拚命地和大家一起向折磨他們的這個人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