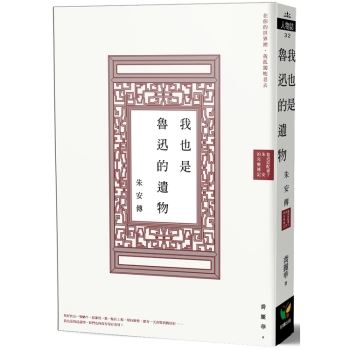【母親的禮物】
獨守──婚後的處境
「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
一九○九年八月,在母親的催促下,魯迅結束了長達七年之久的留日生涯,回到故鄉。一別三年,魯迅終於歸來,這無疑給了朱安一絲希望,然而,魯迅的態度很快就讓她心涼了。
魯迅回紹興一個月後,就去杭州擔任了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員,一九一○年六月,他辭職回到紹興,就任紹興府中學堂教師,並兼任監學。辛亥革命後,他接受紹興都督王金發的委任,擔任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校長),直至一九一二年二月離開紹興。也就是說,只有一年半的時間他們夫婦同處一個屋簷下。
這一時期魯迅沒有留下日記,我們所瞭解的都是他的社會活動,對於他的家庭生活知之甚少。一般的說法是,由於魯迅忙於學校的事情,所以他常住在學校裡,就是回家也總是很晚。據說他晚上總是獨自睡一屋。他於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寫給許壽裳的信中寫道:「僕荒落殆盡,手不觸書,惟搜採植物,不殊囊日,又翻類書,薈集古逸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他白天教書會友,晚上用抄寫古籍來打發漫漫長夜,來代替他心目中的美酒和女人,這些應該都是事實。不過,即使再怎麼回避,畢竟還是要常常碰面,還要維持著夫妻的名分,這反而更令雙方痛苦。何況,周家和朱家的長輩們一定也會唇焦舌敝,勸說他們夫婦和好,希望他們多接觸,漸漸親密起來,而決不會坐視不管。
然而,這些努力顯然都白費了。據魯老太太多年後回憶,她發現「他們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時不多說話,但沒有感情,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她不明白,為什麼他們總是好不起來,於是問兒子:「她有什麼不好?」魯迅只是搖搖頭,說:「和她談不來。」魯老太太問他怎麼談不來,他的回答是:和她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要自作聰明。他舉了個例子說: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就是全中國也沒有,她怎麼能吃到?這樣,談不下去了。談話不是對手,沒趣味,不如不談……(1)
天天低頭不見抬頭見,魯迅也曾試圖跟朱安有所交流,可是朱安一開口,就讓他感到話不投機半句多,從此再也不願意跟她說話。他希望的是「談話的對手」,可是在他面前,朱安的自卑感太深了,她除了對丈夫唯唯諾諾,連連附和,又說得出什麼呢?其實,這也怪不得朱安,魯迅剛從日本回來,談的都是外面的事,都是朱安所不熟悉的,如果談些熟悉的事,也許不至於如此吧。
魯迅對母親所說的理由,或許也只是一種敷衍之辭。如果他對朱安的感情不是那麼淡漠的話,也不至於為了說錯一句話就反感。原指望魯迅回來後夫妻關係能改善,可是實際的情況是「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這種日子無異於精神的苦刑,對彼此都是一種折磨。魯老太太眼看「他們兩人好像越來越疏遠,精神上都很痛苦」,可她也無能為力了。
這一時期魯迅屢次在信中向許壽裳訴說心中的苦悶,一再地表示對故鄉人事的不滿,希望老友能在外給他謀一個職位,在一九一○年八月十五日的信中他寫道:「他處可有容足者不?僕不願居越中也,留以年杪(年底)為度。」一九一一年三月七日的信中寫道:「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當較善乎?」又七月三十一日信中再一次請求老友為其覓一職位:「僕頗欲在他處得一地位,雖遠無害,有機會時,尚希代圖之。」他在故鄉感覺到的只有憋悶,煩惱,他是下了決心要拋開故鄉的一切,決意去過一個人的生活—只要能離開,「雖遠無害」。
一九一二年初,魯迅終於如願以償,離開了令他失望的故鄉和家庭。二月,他離開紹興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擔任部員,五月初與許壽裳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員。從此,朱安又開始了長達七年的獨居生活。
魯迅到北京後,住在位於宣武門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今天我們看到紹興會館儼然已經成了一個湫隘的大雜院,裡面搭建了很多小平房,住了幾十戶人家。當年的紹興縣館規模很大,原名山邑會館,係由紹興府轄的山陰、會稽兩縣在京做官的人出錢建立的,凡有同鄉舉人到京應試,或是同鄉官員到京候補都借住在這裡。魯迅先是住在會館西部的藤花館,後來移到東部的補樹書屋,這是個很安靜的院子,〈吶喊.自序〉中曾寫道:「相傳是往昔在院子裡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他在這裡過著近乎於獨身的寂寞生活,一直到一九一九年。
一個人在北京,魯迅與二弟周作人共同語言最多,通信也最勤,與三弟周建人、信子、芳子的通信也十分頻繁,日記中常有記載。不僅如此,他與東京的羽太家裡通信也很勤,羽太信子的母親羽太近、弟弟重久、妹妹福子都和他通過信。日記中多次有他匯款給羽太家的記錄,如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後赴打磨廠保商銀行易日幣。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羽太家信並日銀五十元……」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九日:「晨至交民巷日郵局寄羽太家信,附與福子箋一枚,銀二十五圓,內十五元為年末之用也。」
魯迅日記裡給羽太家匯款的記載不少,使人覺得他與羽太家,特別是與羽太信子關係不一般,但這很可能是因紹興匯兌不便,周作人託大哥替他往岳家匯款。周作人作為羽太家的女婿,在紹興期間的日記裡,從沒有匯款給日本的記錄,這一點似也可證明。至於這錢究竟是誰出,當時三兄弟沒有分家,也就無所謂了。
相比於這濃濃的兄弟情,魯迅對朱安及其娘家人就顯得格外冷淡。他一個人在北京的這幾年裡,幾乎不與丁家弄朱家通信。倒是朱家人曾給他寫過信,可是他也沒回信。一次是一九一三年四月四日他收到朱安弟弟朱可銘的信:「四日,曇。上午得朱可銘信,南京發。」雖然日記中有朱可銘來信的記載,卻沒有魯迅回信的記載。一般來說,他收到信都會馬上回覆並記在日記裡,對朱可銘的信他卻置之不理。另一次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他收到朱安的信:「二十六日……下午得婦來書,二十二日從丁家弄朱宅發,頗謬。」這是日記裡唯一一次記載收到朱安的信,朱安不識字,大概是託娘家人代筆的。朱安此信寫了什麼?有人做過一些猜測,下文中還會做一些分析,這裡先擱下不提。「得婦來書」,魯迅非但不感到高興,反而說她「頗謬」,可見其對這位舊式太太的反感。
魯迅除一九一九年返鄉接家人去北京之外,僅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六年兩次回紹興探親。但在回鄉期間的日記裡,他隻字不提朱安。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七日,他在紹興住了一個多月,可是看他的日記,彷彿根本不存在這樣一位太太。不過,字裡行間仔細體會,也能看出一些跡象。如七月二日的日記裡:「午前陳子英來。夜不能睡,坐至曉。」魯迅為什麼一夜不睡,坐到天亮?是不是在母親或族人的竭力勸說下,他被迫晚上來到朱安的房中,卻寧可獨自坐到天亮?又七月十一日那天記載:「下午朱可銘來。」這位小舅子上門,對魯迅而言也不是愉快的事吧?
至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魯迅回到紹興,主要是為母親祝壽。這年舊曆十一月十九日為魯老太太六十歲大壽,一連三天家中親朋滿座,連著兩天請來戲班唱戲,祭祖、祀神,賀客盈門,場面十分熱鬧。魯迅這次回家不到一個月,這期間他去了朱安娘家一次:「二十八日曇。……下午往朱宅。晚雨雪。夜陳子英來。」日記中沒有說明是否與朱安同去,他這次出於禮節拜訪了岳家,在朱家逗留的時間也不長。
從魯迅冷冷的態度中,我們能感受到朱安婚後的處境是很可悲的,後面的日子也越來越沒有了指望。據孫伏園說,有一次魯迅回紹興探親,朱安備席款待親友。席間朱安當著親友指責魯迅種種不是。魯迅聽之任之,一言不發,因此,平安無事。事後魯迅對孫伏園說:「她是有意挑釁,我如答辯,就會中了她的計而鬧得一塌糊塗;置之不理,她也就無計可施了。」(2)孫伏園沒有說具體的年份,大概不是一九一三年就是一九一六年。如果真的像孫伏園所說,那麼一向忍讓順從的朱安也終於爆發了,而這並不能挽回什麼,反而使兩人的關係更僵罷了。
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在這七年間,朱安以似棄婦非棄婦的不確定身分留守在周家新台門裡,沒有人知道,遭受這麼多年的冷落,她的心理是什麼狀態,她有什麼想法。
很多研究者指出,魯迅在北京紹興會館那些年埋頭抄古碑的生活,就像是個獨身者或苦行僧,精神上很頹唐。其實,朱安這種等於守活寡的日子一定也很難過,只是今天我們已聽不到她內心的聲音,也不知道她以何種方式排遣心底的苦悶。從有些親友的回憶可知,朱安在北京時,在閒下來的時間裡常常默默地一個人抽著水煙袋。沒有記載說她是什麼時候開始抽水煙的,很可能是婚後因為寂寞苦悶而養成了這種習慣。清代婦女吸煙相當普遍,金學詩《無所用心齋瑣語》中就描述過蘇州一帶官紳之家女子吸煙之狀。《秋平新語》記載靜海呂氏之妻作戲詠長煙袋詩,詩云:「這個長煙袋,妝台放不開;伸時窗紙破,鉤進月光來。」寫得夠幽默的。張愛玲《金鎖記》裡曹七巧的女兒長白是吸鴉片的,儘管時間已經是二十世紀了。
(1)俞芳〈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第一百四十三至一百四十四頁。
(2)〈朱安與魯迅的一次衝突〉,《魯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四年第十一期。
獨守──婚後的處境
「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
一九○九年八月,在母親的催促下,魯迅結束了長達七年之久的留日生涯,回到故鄉。一別三年,魯迅終於歸來,這無疑給了朱安一絲希望,然而,魯迅的態度很快就讓她心涼了。
魯迅回紹興一個月後,就去杭州擔任了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員,一九一○年六月,他辭職回到紹興,就任紹興府中學堂教師,並兼任監學。辛亥革命後,他接受紹興都督王金發的委任,擔任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校長),直至一九一二年二月離開紹興。也就是說,只有一年半的時間他們夫婦同處一個屋簷下。
這一時期魯迅沒有留下日記,我們所瞭解的都是他的社會活動,對於他的家庭生活知之甚少。一般的說法是,由於魯迅忙於學校的事情,所以他常住在學校裡,就是回家也總是很晚。據說他晚上總是獨自睡一屋。他於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寫給許壽裳的信中寫道:「僕荒落殆盡,手不觸書,惟搜採植物,不殊囊日,又翻類書,薈集古逸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他白天教書會友,晚上用抄寫古籍來打發漫漫長夜,來代替他心目中的美酒和女人,這些應該都是事實。不過,即使再怎麼回避,畢竟還是要常常碰面,還要維持著夫妻的名分,這反而更令雙方痛苦。何況,周家和朱家的長輩們一定也會唇焦舌敝,勸說他們夫婦和好,希望他們多接觸,漸漸親密起來,而決不會坐視不管。
然而,這些努力顯然都白費了。據魯老太太多年後回憶,她發現「他們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時不多說話,但沒有感情,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她不明白,為什麼他們總是好不起來,於是問兒子:「她有什麼不好?」魯迅只是搖搖頭,說:「和她談不來。」魯老太太問他怎麼談不來,他的回答是:和她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要自作聰明。他舉了個例子說: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就是全中國也沒有,她怎麼能吃到?這樣,談不下去了。談話不是對手,沒趣味,不如不談……(1)
天天低頭不見抬頭見,魯迅也曾試圖跟朱安有所交流,可是朱安一開口,就讓他感到話不投機半句多,從此再也不願意跟她說話。他希望的是「談話的對手」,可是在他面前,朱安的自卑感太深了,她除了對丈夫唯唯諾諾,連連附和,又說得出什麼呢?其實,這也怪不得朱安,魯迅剛從日本回來,談的都是外面的事,都是朱安所不熟悉的,如果談些熟悉的事,也許不至於如此吧。
魯迅對母親所說的理由,或許也只是一種敷衍之辭。如果他對朱安的感情不是那麼淡漠的話,也不至於為了說錯一句話就反感。原指望魯迅回來後夫妻關係能改善,可是實際的情況是「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這種日子無異於精神的苦刑,對彼此都是一種折磨。魯老太太眼看「他們兩人好像越來越疏遠,精神上都很痛苦」,可她也無能為力了。
這一時期魯迅屢次在信中向許壽裳訴說心中的苦悶,一再地表示對故鄉人事的不滿,希望老友能在外給他謀一個職位,在一九一○年八月十五日的信中他寫道:「他處可有容足者不?僕不願居越中也,留以年杪(年底)為度。」一九一一年三月七日的信中寫道:「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當較善乎?」又七月三十一日信中再一次請求老友為其覓一職位:「僕頗欲在他處得一地位,雖遠無害,有機會時,尚希代圖之。」他在故鄉感覺到的只有憋悶,煩惱,他是下了決心要拋開故鄉的一切,決意去過一個人的生活—只要能離開,「雖遠無害」。
一九一二年初,魯迅終於如願以償,離開了令他失望的故鄉和家庭。二月,他離開紹興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擔任部員,五月初與許壽裳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員。從此,朱安又開始了長達七年的獨居生活。
魯迅到北京後,住在位於宣武門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今天我們看到紹興會館儼然已經成了一個湫隘的大雜院,裡面搭建了很多小平房,住了幾十戶人家。當年的紹興縣館規模很大,原名山邑會館,係由紹興府轄的山陰、會稽兩縣在京做官的人出錢建立的,凡有同鄉舉人到京應試,或是同鄉官員到京候補都借住在這裡。魯迅先是住在會館西部的藤花館,後來移到東部的補樹書屋,這是個很安靜的院子,〈吶喊.自序〉中曾寫道:「相傳是往昔在院子裡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他在這裡過著近乎於獨身的寂寞生活,一直到一九一九年。
一個人在北京,魯迅與二弟周作人共同語言最多,通信也最勤,與三弟周建人、信子、芳子的通信也十分頻繁,日記中常有記載。不僅如此,他與東京的羽太家裡通信也很勤,羽太信子的母親羽太近、弟弟重久、妹妹福子都和他通過信。日記中多次有他匯款給羽太家的記錄,如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後赴打磨廠保商銀行易日幣。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羽太家信並日銀五十元……」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九日:「晨至交民巷日郵局寄羽太家信,附與福子箋一枚,銀二十五圓,內十五元為年末之用也。」
魯迅日記裡給羽太家匯款的記載不少,使人覺得他與羽太家,特別是與羽太信子關係不一般,但這很可能是因紹興匯兌不便,周作人託大哥替他往岳家匯款。周作人作為羽太家的女婿,在紹興期間的日記裡,從沒有匯款給日本的記錄,這一點似也可證明。至於這錢究竟是誰出,當時三兄弟沒有分家,也就無所謂了。
相比於這濃濃的兄弟情,魯迅對朱安及其娘家人就顯得格外冷淡。他一個人在北京的這幾年裡,幾乎不與丁家弄朱家通信。倒是朱家人曾給他寫過信,可是他也沒回信。一次是一九一三年四月四日他收到朱安弟弟朱可銘的信:「四日,曇。上午得朱可銘信,南京發。」雖然日記中有朱可銘來信的記載,卻沒有魯迅回信的記載。一般來說,他收到信都會馬上回覆並記在日記裡,對朱可銘的信他卻置之不理。另一次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他收到朱安的信:「二十六日……下午得婦來書,二十二日從丁家弄朱宅發,頗謬。」這是日記裡唯一一次記載收到朱安的信,朱安不識字,大概是託娘家人代筆的。朱安此信寫了什麼?有人做過一些猜測,下文中還會做一些分析,這裡先擱下不提。「得婦來書」,魯迅非但不感到高興,反而說她「頗謬」,可見其對這位舊式太太的反感。
魯迅除一九一九年返鄉接家人去北京之外,僅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六年兩次回紹興探親。但在回鄉期間的日記裡,他隻字不提朱安。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七日,他在紹興住了一個多月,可是看他的日記,彷彿根本不存在這樣一位太太。不過,字裡行間仔細體會,也能看出一些跡象。如七月二日的日記裡:「午前陳子英來。夜不能睡,坐至曉。」魯迅為什麼一夜不睡,坐到天亮?是不是在母親或族人的竭力勸說下,他被迫晚上來到朱安的房中,卻寧可獨自坐到天亮?又七月十一日那天記載:「下午朱可銘來。」這位小舅子上門,對魯迅而言也不是愉快的事吧?
至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魯迅回到紹興,主要是為母親祝壽。這年舊曆十一月十九日為魯老太太六十歲大壽,一連三天家中親朋滿座,連著兩天請來戲班唱戲,祭祖、祀神,賀客盈門,場面十分熱鬧。魯迅這次回家不到一個月,這期間他去了朱安娘家一次:「二十八日曇。……下午往朱宅。晚雨雪。夜陳子英來。」日記中沒有說明是否與朱安同去,他這次出於禮節拜訪了岳家,在朱家逗留的時間也不長。
從魯迅冷冷的態度中,我們能感受到朱安婚後的處境是很可悲的,後面的日子也越來越沒有了指望。據孫伏園說,有一次魯迅回紹興探親,朱安備席款待親友。席間朱安當著親友指責魯迅種種不是。魯迅聽之任之,一言不發,因此,平安無事。事後魯迅對孫伏園說:「她是有意挑釁,我如答辯,就會中了她的計而鬧得一塌糊塗;置之不理,她也就無計可施了。」(2)孫伏園沒有說具體的年份,大概不是一九一三年就是一九一六年。如果真的像孫伏園所說,那麼一向忍讓順從的朱安也終於爆發了,而這並不能挽回什麼,反而使兩人的關係更僵罷了。
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在這七年間,朱安以似棄婦非棄婦的不確定身分留守在周家新台門裡,沒有人知道,遭受這麼多年的冷落,她的心理是什麼狀態,她有什麼想法。
很多研究者指出,魯迅在北京紹興會館那些年埋頭抄古碑的生活,就像是個獨身者或苦行僧,精神上很頹唐。其實,朱安這種等於守活寡的日子一定也很難過,只是今天我們已聽不到她內心的聲音,也不知道她以何種方式排遣心底的苦悶。從有些親友的回憶可知,朱安在北京時,在閒下來的時間裡常常默默地一個人抽著水煙袋。沒有記載說她是什麼時候開始抽水煙的,很可能是婚後因為寂寞苦悶而養成了這種習慣。清代婦女吸煙相當普遍,金學詩《無所用心齋瑣語》中就描述過蘇州一帶官紳之家女子吸煙之狀。《秋平新語》記載靜海呂氏之妻作戲詠長煙袋詩,詩云:「這個長煙袋,妝台放不開;伸時窗紙破,鉤進月光來。」寫得夠幽默的。張愛玲《金鎖記》裡曹七巧的女兒長白是吸鴉片的,儘管時間已經是二十世紀了。
(1)俞芳〈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第一百四十三至一百四十四頁。
(2)〈朱安與魯迅的一次衝突〉,《魯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四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