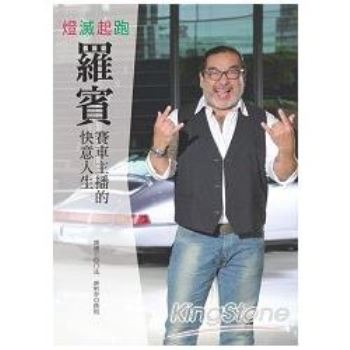CHAPTER 11 瀟灑走一回
開啟我製作賽車節目的契機,是有天和一位健身房認識的老兄閒聊,他向我提到:「我有個朋友在做汽車節目,但是都找不到合適的主持人。老龔啊,拜託你可不可以給我個面子,去見見他呢?」我就前往朋友口中的製作公司,拜訪了製作人「周哥」周一鳴。
當時菸商雖然有許多預算,但囿於法規限制,禁止在媒體上打廣告,唯一有可能做的,就是投入汽車或賽車節目(賽車迷對賽車上貼有各家菸商logo 的畫面應該都不陌生)。這間製作公司從菸商那裡拿到經費,卻沒有規劃節目的具體方向,不知道從何著手,於是我提出建議:「可以將F1、WRC、MotoGP 等賽事精華加以介紹,做成綜合性賽事報導的節目。」
主持賽車節目不是光念稿子就可以,重點是還要從旁講評。在那個沒有網路的年代,賽事的帶子送過來,也不像現在可以即時上網找資料、做功課。老一輩的車迷大概了解,八○年代末期在台灣做賽車節目,僅有的資訊來源,就是一些在台販售的香港汽車雜誌之類的刊物,其中大部分內容主要還是以市售車為主,只有小部分的賽事報導。
因此,我要求菸商的公關公司,至少要幫我弄來諸如車隊發行的刊物,或車隊提供給媒體的資料。這就是專業與否的差別,因為我夠專業,知道可以和人「要什麼」;否則公關公司只負責出錢,其餘你自己想辦法搞定。我告知公關公司可索取的項目,例如F1、WRC、MotoGP 賽季開始前都會發行車手或車隊資料,以及觀戰指南之類的東西。所幸公關公司很配合,照我的交代收齊了資料。就這樣,我開始做第一個賽車節目──《大賽車》。由於這類節目在預算消化完之後,往往只能「下台一鞠躬」,等找到經費,又可重起爐灶,在各台「借屍還魂」。我們這個團隊就像打游擊一般,先主持台視的《旋風大賽車》,後來是華視的《飛越地平線》,陸陸續續讓足跡踏遍各電視台。
做賽車節目期間,我在青春網的處境也日漸緊張。由於我是個喜歡遊走灰色地帶、衝到極限的人,高層對我十分感冒,常氣到快抓狂。這就是媒體界冷酷和現實的一面:一個新媒體成立時,總會希望有個標新立異,可以炒話題的招牌充作號召;也許是我的作風很酷,節目點播率很高,曾經是青春網的當紅炸子雞。可是一旦過了蜜月期,剩下來的固然是每晚陪我一起熬夜的忠實聽眾,問題是單靠這些鐵桿粉絲支持,最終也未必能吸引和留住贊助商;就像八點檔連續劇熱門時段一樣,廠商在廣播看中的也是晚間的黃金時段。說白一點,節目很紅、很熱門是一回事,能不能藉此賺到錢又是另一回事;廣播電台畢竟是營利單位,上頭不免認為:「羅賓你愛搞冷僻偏鋒,行走懸崖邊上,不少人或許認為你很屌,問題是一般廠商都對你和你的節目敬而遠之。」
我只能說:「要麼我太笨,要麼我聰明過頭,永遠想跑在人家前面。」陶曉清夾在中間,肩頭上擔了巨大壓力,又猶豫著該如何告訴我:「你被公司炒了。」便坦率對她表明:「很簡單。陶姊,妳就直說上面的『遊戲規則』改變了,我會了解的。」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可以瀟灑地就此離開。
說真的,後來青春網的遊戲規則變得愈來愈奇怪,例如每個鐘頭規定要播幾首語歌曲,但這和我的節目風格大相逕庭,我還得努力找些在當時寥寥可數的搖滾曲風國語歌,開始覺得愈來愈沒意思。
CHAPTER12騎虎難下
邀請我製作日月潭鐵人三項節目的老蔡,是一位香港人,他也是替人做事,背後實際的負責人是台中一家鋼構公司的老闆。我做事有個原則:可以不賺錢,但絕不賠錢。眼見活動開始前兩、三天,老蔡那邊的資金竟還沒到位,我當即向他表明:「不管是負責音響器材的夥伴,請來表演的幻眼樂隊,還有在各個項目幫忙的好友,這些都是我的好哥們;大家看在我面子上,報出來的價錢都是友情價。所以不論如何,在還沒開工前,一定要先把酬勞給人家。」這類活動或演出若不先拿錢,等事情結束後往往根本拿不到錢,血淋淋的例子實在太多了。果不其然,合約簽了之後,錢卻只拿到一半,我先全數支付給好友們,自己被積欠的部分例如製作人費等項目則同意先欠著。結果,直到活動辦完,欠我的款項始終沒付清,他們送我遊艇俱樂部的永久會員當補償,只是後來遊艇俱樂部也倒了。這段往事其實牽涉到我日後的職涯發展。原來老蔡回香港聯絡了Star TV,該台要播出我們製作的日月潭鐵人三項的帶子。當時Star TV 的體育台還叫Prime Sports,完全是老外的天下,根本沒有中文部。我們把帶子剪好,找了我在ICRT 的好友把旁白錄好,一切準備就緒,只需要確定播出日期。
老蔡跟Star TV 交涉過程中,對方要求隨附製作人履歷。由於只要交出帶子、確認播出日期後,就可以拿到一筆款項,儘管我覺得要我的履歷很奇怪,基於「能收回多少錢是多少」的心態,仍趕緊做了一份傳過去。兩、三天之後,Star TV 突然來電, 轉達老闆RickJamison 希望和我見面。起初我狐疑:「只不過製作個節
目,你們那邊的『眉眉角角』和要求怎麼這麼多?」便故意推說:「沒空!下週再說。」不料對方並沒有打退堂鼓,回覆道:「沒關係,我們老闆正好下週要到台灣,您何時方便和他碰面呢?」由於隔週剛好是英國搖滾詩人Sting 來台,要在來來飯店舉行記者會,由我負責主持。對方表示那就安排他們老闆入住來來,待記者會結束後,可以順道會面。
畢竟不清楚對方的來意,原本我還單純地想:「帶著剪好的帶子、錄放影機等器材,讓對方把內容看完,覺得OK 的話,訂好播出日期,這樣我就可以拿到欠款了。」怎料,會面當天,我一踏進Rick Jamison 的房間,他劈頭第一句就說:「我們找你很久了!」我聽完一愣,還以為他是要找我談播出日期。他接著道:「我們在香港久聞你的大名,卻始終找不到你。一提到做賽車節目,所有
人第一個想到和推薦的就是你,你有沒有興趣來香港幫助我們?」
我這輩子最討厭的地方之一就是香港,非常不喜歡那種到處人擠人的鬱悶感,每次去都待不到兩天就想走人,便直接以沒興趣來回絕。Rick Jamison 轉而動之以情:「大家都說台灣的賽車節目是你製作和主持的,我們知道你會做賽車節目。StarTV 的體育頻道打算開闢中文部,希望有指標性的節目來發揮帶頭作用。我們發現台灣有很多摩托車,又是亞洲除日本以外最大的汽車市場,想主打賽車運動,卻一直找不到適合的華語製作人,始終無法開展⋯⋯」原先打算三十分鐘搞定的會面,一聊卻是一個多小時。Rick Jamison 最後結論:「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你留在台灣,要做節目或播賽事時才飛到香港;另一種是舉家搬到香港。
依我們看,建構中文部和製作節目等各方面的事務,一開始勢必得付出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不大可能容許你採取第一種方式。你可以回去考慮一下嗎?」。
回家後,我和母親及太太討論,大家一致覺得還是算了。當年離九七大限剩不到四年,香港民心浮動,何況當地消費又十分高昂。我開柯達沖印店,扣除成本一個月可賺十幾萬,加上我在廣播電台主持節目,以及其他的業外收入,加總起來一個月收入少說也有三十萬元以上。何況住家裡還不花錢,吃飽撐著才跟你搬去香港。
我當時的想法是:「假如你們真的要找我的話,條件待遇一定要比我原本在台灣的工作優渥。」畢竟要轉往香港工作,各種開銷相當可觀,便故意開出了應該會讓他們知難而退的價碼,想要打發掉他們。到了耶誕節前夕,我抱著愉悅的心情在台北電台錄製一些節目存檔,準備要帶家人去美國度假。那時我在台北
電台主持一個晚間七至八點的節目,有天我正要前往電台時接到Rick Jamison 的來電,他轉達董事會同意接受我開的條件,問我最快何時能夠開始?對方急著敲定的原因,在於當時已經是十二月底,賽季是隔年三月開始,但負責轉播賽事的部門迄今尚未建置完成。衛視希望在1994 年新賽季能馬上在台灣、港澳和其
他亞洲各地的華語地區開播,特別是台灣被視為最主要的市場。
台灣的有線電視,當年正處於開始蓬勃發展的階段,媒體自由度在華語區亦是最好的,他們希望盡快從台灣出發,也可以藉此收到一筆相當可觀的費用。總之,雖然有點騎虎難下的味道,我仍答應了衛視的邀約。事後回顧,或許是我對台灣當時的媒體環境不太滿意,下意識地驅策出換個環境也不錯的想法。對我來說,這份工作有一個很大的誘因,是我可以帶領自己的團隊,自行製作F1 和MotoGP 的現場報導。對於任何車迷來說,這都是實現夢想再好不過的機會了。我趕在跨年前幾天把相關文件簽好,快遞給衛視,衛視則通知我最遲一月底就要過去,因為報到日期是二月一日。於是,我便在過完農曆春節後不久,帶著太太和當時
才一歲多的大女兒Kiki,舉家搬往香港,待一切安頓好,我如期向新公司報到。
CHAPTER13 創業維艱
衛視辦公室位於紅磡的維港中心,這裡是工業區,建築設計也呈現濃濃的工業風。第一天前往辦公室,眼前景況讓我楞在當場。前前後後逛了一圈,我發現辦公室空空如也,根本沒看到製作部之類的單位。過去我待在中廣或老三台,深悉一個組織健全的廣播電台或電視公司,皆會有節目部、製作部、業務部等分工詳細的單位。我觀察到這個隸屬衛視的體育頻道,似乎除了英文部和負責行銷的業務部,完全沒有其他部門。
所幸當時的美籍總監Mike Diamond 人不錯,和我在溝通方面很順利;簽下我的澳洲人Rick Jamison 負責的是整個頻道的推廣發展,我們也相處愉快。我對Rick 表明,自己一向不喜歡大公司裡的派系之分,更不擅長應付瑣碎的行政事務。他對我承諾不必管這些,只要搞定我負責的部分就好了。
我們公司早先已設有英文部,當時以F1 和MotoGP 兩大賽事為主打,英文主播是英國人Jonathan Green。我剛進公司時,上司引見我和他相互認識,察覺他不是個友善的人,當主管介紹我是被延攬來建構中文部的賽車轉播和節目時,他臉上立即閃現不以為然的表情,彷彿在說:「你一個華人懂賽車嗎?」
我一點兒也不怪他有這種反應,就如同我在美國經歷過的。當地流傳不少華人駕車的惡劣笑話,在賽車場上遇到的老美,總是一臉看不起華人的態度。剛開始,公司只配給我一位名叫Ramon Lau 的人,他會一點國語,人相當熱心。我問他:「我們的製作團隊在哪?」他回答:「就我們兩個。」我一聽不禁憂心忡忡,
幸好在我報到後的一個月間,其他同仁也陸續加入,例如過去任職TVB 體育組的陳尚來(阿來,Owen Chen)。他報到那天,我就和他講好:「我在這裡只負責專業和技術的部分,我的個性不愛搞政治,所以你可能要分擔這方面
的事情。」於是我埋頭幹自己分內的工作,他則負責行政和管理相關的事務。簽約時, 我的頭銜和職務是資深製作人(SeniorProducer)兼主持人,因為公司告知我,在我未替他們找到主持人和車評前,必須自己上陣播報和講評。當時我覺得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沒想到一做下去就度過了整整二十個寒暑。
中文部草創時,我們真的遇到很多困難。由於公司欠缺相關硬體設備,僅有的幾台電腦只用在文書處理,配備網路的電腦更是寥寥可數,最常使用的還是傳真機和Telex電報機。賽季開始時,「理論上」公司會發給我們一人一本年鑑,上頭載明FIA 和車隊的管理階層是些何方神聖的資料。車手方面的年鑑,則是由車隊交給FOCA 統籌印製,內容就像我們今天在車隊官網上看到的車隊資料。
照理說,整個公司會保留兩份年鑑資料,奇怪的是總有一份不知流落何方?而另一份就在Jonathan 手上,鎖在英文部的檔案櫃,我們還得去拜託他,借來弄一份影印本留在中文部。即使只是影本,我們仍然寶貝得不得了。在我的F1 主播生涯裡,每次只是在棚內挑選新聞加以評述,是因為我沒有太多的選擇,畢竟素材就是這些。二十年後的今天再回首,一路走來真是「一步一腳印,滴滴血淚」。當然,觀眾是不會知道背後這些辛酸。在草創時期很多觀眾──特別是一些身處在歐美賽車資訊比較發達的地方的車迷──對我的批評非常嚴厲,我也只能「眼
淚往肚裡吞」。那個網路不發達的年代,獲得資訊的速度是如此牛步化。歐洲的Sky TV 會在週六排位賽開始前二小時,電傳過來一份暫訂的參賽車隊與車手的名單,以歐洲賽事為例,在香港時間大約五、六點左右,我們會收到資料,但往往一到傳真機那邊,東西卻消失得無影無蹤。原來,資料早被英文部的製作人一聲不吭地拿走了,我遍尋不著只好找他們要,他們才會敷衍致歉,擺明就是欺負我們中文部。這樣的情況延續了半個賽季,等英文部的人終於明白我是真的精通賽車運動,整個態度才改觀。
中文部與英文部之間的矛盾,更表現在公司高層的差別待遇和歧視心態,每次都把英文部該做的事務、該給的資源搞定後,最後才來問我們的需求。或許因為中文部其他同事都是香港人,在成長過程或文化上,已經習慣對英國人或白種人逆來順受,很多時候他們都不表示意見。但我不同,我旅美時就不會對白種人唯命是從,況且我天生反骨叛逆,敢於直接發出不平之鳴,並且向高層爭取資源。阿來有時候會勸我:「算了,別跟他們去爭。」但我仍不輕易妥協。
1995 年,有回我和公司一個交情很好的老外要賽事資料,平常他都給得很爽快,那天不知道是心情不好還是怎樣,竟賞了我一頓排頭。我意識到老是要依賴別人也不是辦法,就自己花錢買了套486 電腦,因為當時住在離島,光請人來裝網路就等了好幾天。
開啟我製作賽車節目的契機,是有天和一位健身房認識的老兄閒聊,他向我提到:「我有個朋友在做汽車節目,但是都找不到合適的主持人。老龔啊,拜託你可不可以給我個面子,去見見他呢?」我就前往朋友口中的製作公司,拜訪了製作人「周哥」周一鳴。
當時菸商雖然有許多預算,但囿於法規限制,禁止在媒體上打廣告,唯一有可能做的,就是投入汽車或賽車節目(賽車迷對賽車上貼有各家菸商logo 的畫面應該都不陌生)。這間製作公司從菸商那裡拿到經費,卻沒有規劃節目的具體方向,不知道從何著手,於是我提出建議:「可以將F1、WRC、MotoGP 等賽事精華加以介紹,做成綜合性賽事報導的節目。」
主持賽車節目不是光念稿子就可以,重點是還要從旁講評。在那個沒有網路的年代,賽事的帶子送過來,也不像現在可以即時上網找資料、做功課。老一輩的車迷大概了解,八○年代末期在台灣做賽車節目,僅有的資訊來源,就是一些在台販售的香港汽車雜誌之類的刊物,其中大部分內容主要還是以市售車為主,只有小部分的賽事報導。
因此,我要求菸商的公關公司,至少要幫我弄來諸如車隊發行的刊物,或車隊提供給媒體的資料。這就是專業與否的差別,因為我夠專業,知道可以和人「要什麼」;否則公關公司只負責出錢,其餘你自己想辦法搞定。我告知公關公司可索取的項目,例如F1、WRC、MotoGP 賽季開始前都會發行車手或車隊資料,以及觀戰指南之類的東西。所幸公關公司很配合,照我的交代收齊了資料。就這樣,我開始做第一個賽車節目──《大賽車》。由於這類節目在預算消化完之後,往往只能「下台一鞠躬」,等找到經費,又可重起爐灶,在各台「借屍還魂」。我們這個團隊就像打游擊一般,先主持台視的《旋風大賽車》,後來是華視的《飛越地平線》,陸陸續續讓足跡踏遍各電視台。
做賽車節目期間,我在青春網的處境也日漸緊張。由於我是個喜歡遊走灰色地帶、衝到極限的人,高層對我十分感冒,常氣到快抓狂。這就是媒體界冷酷和現實的一面:一個新媒體成立時,總會希望有個標新立異,可以炒話題的招牌充作號召;也許是我的作風很酷,節目點播率很高,曾經是青春網的當紅炸子雞。可是一旦過了蜜月期,剩下來的固然是每晚陪我一起熬夜的忠實聽眾,問題是單靠這些鐵桿粉絲支持,最終也未必能吸引和留住贊助商;就像八點檔連續劇熱門時段一樣,廠商在廣播看中的也是晚間的黃金時段。說白一點,節目很紅、很熱門是一回事,能不能藉此賺到錢又是另一回事;廣播電台畢竟是營利單位,上頭不免認為:「羅賓你愛搞冷僻偏鋒,行走懸崖邊上,不少人或許認為你很屌,問題是一般廠商都對你和你的節目敬而遠之。」
我只能說:「要麼我太笨,要麼我聰明過頭,永遠想跑在人家前面。」陶曉清夾在中間,肩頭上擔了巨大壓力,又猶豫著該如何告訴我:「你被公司炒了。」便坦率對她表明:「很簡單。陶姊,妳就直說上面的『遊戲規則』改變了,我會了解的。」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可以瀟灑地就此離開。
說真的,後來青春網的遊戲規則變得愈來愈奇怪,例如每個鐘頭規定要播幾首語歌曲,但這和我的節目風格大相逕庭,我還得努力找些在當時寥寥可數的搖滾曲風國語歌,開始覺得愈來愈沒意思。
CHAPTER12騎虎難下
邀請我製作日月潭鐵人三項節目的老蔡,是一位香港人,他也是替人做事,背後實際的負責人是台中一家鋼構公司的老闆。我做事有個原則:可以不賺錢,但絕不賠錢。眼見活動開始前兩、三天,老蔡那邊的資金竟還沒到位,我當即向他表明:「不管是負責音響器材的夥伴,請來表演的幻眼樂隊,還有在各個項目幫忙的好友,這些都是我的好哥們;大家看在我面子上,報出來的價錢都是友情價。所以不論如何,在還沒開工前,一定要先把酬勞給人家。」這類活動或演出若不先拿錢,等事情結束後往往根本拿不到錢,血淋淋的例子實在太多了。果不其然,合約簽了之後,錢卻只拿到一半,我先全數支付給好友們,自己被積欠的部分例如製作人費等項目則同意先欠著。結果,直到活動辦完,欠我的款項始終沒付清,他們送我遊艇俱樂部的永久會員當補償,只是後來遊艇俱樂部也倒了。這段往事其實牽涉到我日後的職涯發展。原來老蔡回香港聯絡了Star TV,該台要播出我們製作的日月潭鐵人三項的帶子。當時Star TV 的體育台還叫Prime Sports,完全是老外的天下,根本沒有中文部。我們把帶子剪好,找了我在ICRT 的好友把旁白錄好,一切準備就緒,只需要確定播出日期。
老蔡跟Star TV 交涉過程中,對方要求隨附製作人履歷。由於只要交出帶子、確認播出日期後,就可以拿到一筆款項,儘管我覺得要我的履歷很奇怪,基於「能收回多少錢是多少」的心態,仍趕緊做了一份傳過去。兩、三天之後,Star TV 突然來電, 轉達老闆RickJamison 希望和我見面。起初我狐疑:「只不過製作個節
目,你們那邊的『眉眉角角』和要求怎麼這麼多?」便故意推說:「沒空!下週再說。」不料對方並沒有打退堂鼓,回覆道:「沒關係,我們老闆正好下週要到台灣,您何時方便和他碰面呢?」由於隔週剛好是英國搖滾詩人Sting 來台,要在來來飯店舉行記者會,由我負責主持。對方表示那就安排他們老闆入住來來,待記者會結束後,可以順道會面。
畢竟不清楚對方的來意,原本我還單純地想:「帶著剪好的帶子、錄放影機等器材,讓對方把內容看完,覺得OK 的話,訂好播出日期,這樣我就可以拿到欠款了。」怎料,會面當天,我一踏進Rick Jamison 的房間,他劈頭第一句就說:「我們找你很久了!」我聽完一愣,還以為他是要找我談播出日期。他接著道:「我們在香港久聞你的大名,卻始終找不到你。一提到做賽車節目,所有
人第一個想到和推薦的就是你,你有沒有興趣來香港幫助我們?」
我這輩子最討厭的地方之一就是香港,非常不喜歡那種到處人擠人的鬱悶感,每次去都待不到兩天就想走人,便直接以沒興趣來回絕。Rick Jamison 轉而動之以情:「大家都說台灣的賽車節目是你製作和主持的,我們知道你會做賽車節目。StarTV 的體育頻道打算開闢中文部,希望有指標性的節目來發揮帶頭作用。我們發現台灣有很多摩托車,又是亞洲除日本以外最大的汽車市場,想主打賽車運動,卻一直找不到適合的華語製作人,始終無法開展⋯⋯」原先打算三十分鐘搞定的會面,一聊卻是一個多小時。Rick Jamison 最後結論:「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你留在台灣,要做節目或播賽事時才飛到香港;另一種是舉家搬到香港。
依我們看,建構中文部和製作節目等各方面的事務,一開始勢必得付出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不大可能容許你採取第一種方式。你可以回去考慮一下嗎?」。
回家後,我和母親及太太討論,大家一致覺得還是算了。當年離九七大限剩不到四年,香港民心浮動,何況當地消費又十分高昂。我開柯達沖印店,扣除成本一個月可賺十幾萬,加上我在廣播電台主持節目,以及其他的業外收入,加總起來一個月收入少說也有三十萬元以上。何況住家裡還不花錢,吃飽撐著才跟你搬去香港。
我當時的想法是:「假如你們真的要找我的話,條件待遇一定要比我原本在台灣的工作優渥。」畢竟要轉往香港工作,各種開銷相當可觀,便故意開出了應該會讓他們知難而退的價碼,想要打發掉他們。到了耶誕節前夕,我抱著愉悅的心情在台北電台錄製一些節目存檔,準備要帶家人去美國度假。那時我在台北
電台主持一個晚間七至八點的節目,有天我正要前往電台時接到Rick Jamison 的來電,他轉達董事會同意接受我開的條件,問我最快何時能夠開始?對方急著敲定的原因,在於當時已經是十二月底,賽季是隔年三月開始,但負責轉播賽事的部門迄今尚未建置完成。衛視希望在1994 年新賽季能馬上在台灣、港澳和其
他亞洲各地的華語地區開播,特別是台灣被視為最主要的市場。
台灣的有線電視,當年正處於開始蓬勃發展的階段,媒體自由度在華語區亦是最好的,他們希望盡快從台灣出發,也可以藉此收到一筆相當可觀的費用。總之,雖然有點騎虎難下的味道,我仍答應了衛視的邀約。事後回顧,或許是我對台灣當時的媒體環境不太滿意,下意識地驅策出換個環境也不錯的想法。對我來說,這份工作有一個很大的誘因,是我可以帶領自己的團隊,自行製作F1 和MotoGP 的現場報導。對於任何車迷來說,這都是實現夢想再好不過的機會了。我趕在跨年前幾天把相關文件簽好,快遞給衛視,衛視則通知我最遲一月底就要過去,因為報到日期是二月一日。於是,我便在過完農曆春節後不久,帶著太太和當時
才一歲多的大女兒Kiki,舉家搬往香港,待一切安頓好,我如期向新公司報到。
CHAPTER13 創業維艱
衛視辦公室位於紅磡的維港中心,這裡是工業區,建築設計也呈現濃濃的工業風。第一天前往辦公室,眼前景況讓我楞在當場。前前後後逛了一圈,我發現辦公室空空如也,根本沒看到製作部之類的單位。過去我待在中廣或老三台,深悉一個組織健全的廣播電台或電視公司,皆會有節目部、製作部、業務部等分工詳細的單位。我觀察到這個隸屬衛視的體育頻道,似乎除了英文部和負責行銷的業務部,完全沒有其他部門。
所幸當時的美籍總監Mike Diamond 人不錯,和我在溝通方面很順利;簽下我的澳洲人Rick Jamison 負責的是整個頻道的推廣發展,我們也相處愉快。我對Rick 表明,自己一向不喜歡大公司裡的派系之分,更不擅長應付瑣碎的行政事務。他對我承諾不必管這些,只要搞定我負責的部分就好了。
我們公司早先已設有英文部,當時以F1 和MotoGP 兩大賽事為主打,英文主播是英國人Jonathan Green。我剛進公司時,上司引見我和他相互認識,察覺他不是個友善的人,當主管介紹我是被延攬來建構中文部的賽車轉播和節目時,他臉上立即閃現不以為然的表情,彷彿在說:「你一個華人懂賽車嗎?」
我一點兒也不怪他有這種反應,就如同我在美國經歷過的。當地流傳不少華人駕車的惡劣笑話,在賽車場上遇到的老美,總是一臉看不起華人的態度。剛開始,公司只配給我一位名叫Ramon Lau 的人,他會一點國語,人相當熱心。我問他:「我們的製作團隊在哪?」他回答:「就我們兩個。」我一聽不禁憂心忡忡,
幸好在我報到後的一個月間,其他同仁也陸續加入,例如過去任職TVB 體育組的陳尚來(阿來,Owen Chen)。他報到那天,我就和他講好:「我在這裡只負責專業和技術的部分,我的個性不愛搞政治,所以你可能要分擔這方面
的事情。」於是我埋頭幹自己分內的工作,他則負責行政和管理相關的事務。簽約時, 我的頭銜和職務是資深製作人(SeniorProducer)兼主持人,因為公司告知我,在我未替他們找到主持人和車評前,必須自己上陣播報和講評。當時我覺得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沒想到一做下去就度過了整整二十個寒暑。
中文部草創時,我們真的遇到很多困難。由於公司欠缺相關硬體設備,僅有的幾台電腦只用在文書處理,配備網路的電腦更是寥寥可數,最常使用的還是傳真機和Telex電報機。賽季開始時,「理論上」公司會發給我們一人一本年鑑,上頭載明FIA 和車隊的管理階層是些何方神聖的資料。車手方面的年鑑,則是由車隊交給FOCA 統籌印製,內容就像我們今天在車隊官網上看到的車隊資料。
照理說,整個公司會保留兩份年鑑資料,奇怪的是總有一份不知流落何方?而另一份就在Jonathan 手上,鎖在英文部的檔案櫃,我們還得去拜託他,借來弄一份影印本留在中文部。即使只是影本,我們仍然寶貝得不得了。在我的F1 主播生涯裡,每次只是在棚內挑選新聞加以評述,是因為我沒有太多的選擇,畢竟素材就是這些。二十年後的今天再回首,一路走來真是「一步一腳印,滴滴血淚」。當然,觀眾是不會知道背後這些辛酸。在草創時期很多觀眾──特別是一些身處在歐美賽車資訊比較發達的地方的車迷──對我的批評非常嚴厲,我也只能「眼
淚往肚裡吞」。那個網路不發達的年代,獲得資訊的速度是如此牛步化。歐洲的Sky TV 會在週六排位賽開始前二小時,電傳過來一份暫訂的參賽車隊與車手的名單,以歐洲賽事為例,在香港時間大約五、六點左右,我們會收到資料,但往往一到傳真機那邊,東西卻消失得無影無蹤。原來,資料早被英文部的製作人一聲不吭地拿走了,我遍尋不著只好找他們要,他們才會敷衍致歉,擺明就是欺負我們中文部。這樣的情況延續了半個賽季,等英文部的人終於明白我是真的精通賽車運動,整個態度才改觀。
中文部與英文部之間的矛盾,更表現在公司高層的差別待遇和歧視心態,每次都把英文部該做的事務、該給的資源搞定後,最後才來問我們的需求。或許因為中文部其他同事都是香港人,在成長過程或文化上,已經習慣對英國人或白種人逆來順受,很多時候他們都不表示意見。但我不同,我旅美時就不會對白種人唯命是從,況且我天生反骨叛逆,敢於直接發出不平之鳴,並且向高層爭取資源。阿來有時候會勸我:「算了,別跟他們去爭。」但我仍不輕易妥協。
1995 年,有回我和公司一個交情很好的老外要賽事資料,平常他都給得很爽快,那天不知道是心情不好還是怎樣,竟賞了我一頓排頭。我意識到老是要依賴別人也不是辦法,就自己花錢買了套486 電腦,因為當時住在離島,光請人來裝網路就等了好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