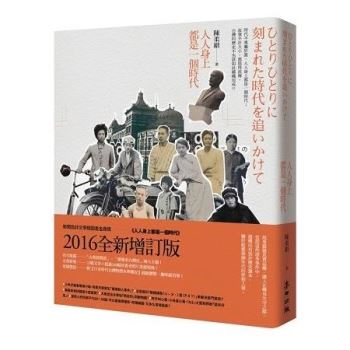那時候的公車會「犁田」
台北市有載客巴士,始於一九一三年,如養不良的初生兒,一年即夭折。真正粗具公車系統規模,已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此後十來年,姑且稱為台北公車的幼稚園期,那時的單純,如你我三歲流著鼻涕、四歲拉著媽媽衣角、五歲抱著小狗,想來可愛。
那時候,公車屬私人經營,車小到比現在的小巴還小。以一九二○年所見的公車來說,底盤高,輪胎比現在瘦。乘客坐左右兩邊,面對面,每邊應該擠不進四個人。說是車,又沒有「車廂」;乘客非置身可封閉的空間,車沒有窗戶,頂上罩布棚,彷彿坐敞篷車。
那時候,公車上還有一個現在已消失的職人,稱之「車掌」。戰後,有一段很長時間,公車都有車掌,負責收賣車票,下車信號也由她們吹哨子。我寫「她們」,因為中年以上兩、三代台灣人遇見的車掌,全是小姐。但是,台北公車的「幼稚園小班」時期,車掌都由男性擔任。
男車掌有點自毀前程。一九二○年,曾有讀者投書爆料,指來往大稻埕與艋舺間的公車,女乘客多中學女學生和護士,她們上車要買票,姓王的和姓葉的兩個男車掌故意不賣,色迷迷的,等停車或下車,再手來腳來,「調戲」這些少女。兩年後,車公司也覺得設車掌的弊害太多,就把男車掌廢了。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台北公車才起用六位女車掌,其中四位是台灣小姐。
當初,還有一個專屬舊時代的公車風景。
一九二四年八月,颱風剛掃過,到處水災。公館到新店之間,沿途牛車、拉車,晝夜絡繹不絕,搬運重建需用的材料。二十四日晚上八點半左右,天色漆暗,車牌號「50」的公車載了十三位乘客從新店往北來,幾乎可說是摸黑前進。駛到景美的番婆厝(今萬隆集應廟一帶),二十二歲的廖姓司機看到牛車時已來不及,還好只是擦撞,車有點損壞,便想到有燈的地方修理。沒想到,往前開開開,到今萬盛街那邊,忽然,才轉一下把手,車就栽進田裡了。災情反而比撞牛車嚴重,報紙說,車體「全部粉碎」,車上的日本警察光田撞到鼻樑,流著血,其他七位台灣籍乘客輕重傷都有。
現在公車都走在大馬路上,穿梭在大樓與樓房之間,八、九十年前大不同,公車一出大稻埕、艋舺和城中區,四處盡是農田,道路又窄,稍有車況,方向盤稍偏,動不動就,「犁田」了。
一九三一年,還發生一種現在幾乎不可能發生的公車之禍。一樣是二十出頭的年輕司機,駕駛台北市營公車,從中崙往台北車站開,來到善導寺(當時為淨土宗別院),那裡有個公車牌,郭姓司機正準備停車。故事說到這裡,必須插入一個說明,日本時代,陸上交通一律靠左行,因此,郭運將準備停車的位置為路的南邊。這時,從今天紹興南街駛出一部市役所(市政府)的「糞屎運搬車」,像溜冰一樣,無遮阻地撞上公車的左後側。公車玻璃窗全破了,一位日本籍乘客割傷頭,一位台灣人乘客割傷臉。更恐怖的是,他們還被潑到穢物,搞得搭個公車好像遇見仇人似的。
不過,報紙編輯可能為了補償他們受創的心靈,標題下得文雅,說是公車撞糞尿車,乘客負傷,「有沐黃金汁者」。
小象闖進高級料亭了
小熊貓「圓仔」連睡個覺都那麼卡哇衣,惹人愛憐,成為台北動物園的新明星。時間往前推,戰後幾十年,圓仔的前輩是大象林旺,再往前推到日本時代,那就屬「麻──將」最紅了。
「麻──將」是一隻母象,大家暱稱牠「マーちゃん」,可以譯成「小瑪」,但念起來的聲音則像中文的「麻將」,叫起來頗順口,姑且就這樣寫。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麻將先搭船到基隆,轉搭貨運列車,抵達台北火車站。民眾已經聞風而來,圍觀等待者有戴斗笠的、有穿台灣衫褲的,明顯是台灣人。報紙如拿刀刻木,要把歷史上不可忘卻的時間牢牢記著,午後兩點十二分,麻將小象從貨物車的小斜坡走下來,終於踏上台灣的土地,同一秒,新聞記者拚命按下快門。
然後,麻將如何從台北火車站到她的新家圓山動物園呢?用走的。動物園的人餵她樹葉和水,誘騙她慢慢往前。從現在忠孝西路靠左側開始走,第一個轉彎,走進今天的中山北路。路口的行政院,以前是台北市役所(市政府),市尹(市長)太田吾一鼻下蓄著髭,和一堆公務員跑出來歡迎。市長出迎的熱鬧沒過幾秒,麻將走一走,明明有鐵鍊圈住脖子,仍然拉不住,突然就衝進旁邊的日式高級酒宴料亭「梅屋敷」,即今天的國父史蹟紀念館。一個小時後,好不容易才入住圓山新家。
之後,麻將就變成圓山動物園的「人氣者」,大人小孩抱著好奇去,看牠用鼻子吃飯,興味盎然。麻將一整天要吃五顆鳳梨、甘蔗葉一百斤、一些普通青草、一斗的水,再加上刺刺的鳳梨葉五十斤,非常驚人。
有一次,中部的原住民小孩到動物園修學旅行,他們在山上看過許多動物,對大象卻很陌生。雖然麻將還是小母象,只有一千公斤左右,他們仍覺得大得可怕。麻將的象腿,在他們眼裡,很像部落的石臼。初看到麻將的象鼻,他們皺眉不解,為什麼象臉上會長出一隻腳來。
日本時代,去動物園已是孩童普遍的活動。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在回憶錄裡說,小學時,老師帶他們到圓山動物園遠足,前一晚他興奮得睡不著覺。隔天搭火車從基隆出發,下了台北火車站,再走路到動物園,花了大半天,雖然只剩半日遊,也很高興滿足。張榮發生於一九二七年,小學時期到動物園遠足,應該看過人氣印度象「麻將」。
三○年代,麻將是圓山動物園的第一女主角,她塊頭大,存在感十足,能聽命做動作,每年「動物祭」,動物園準備米、地瓜、蜜柑、甘蔗、香蕉和柿子等供品,祭拜死去的動物同伴,感謝牠們的付出,此時,麻將就會身披彩衣登場,代表園內所有動物屈膝祭拜。
同在園內,猩猩「一郎君」也很受歡迎,身高一二八公分、體重六十八公斤,是全日本第一大的猩猩。不過,日本時代,圓山動物園歷經兩次大門改裝,一九三九年底那回的新門,入口正上方還是畫了兩頭大象,那可說是麻將的勳章,證明牠不容動搖的一姐地位。
麻將向來溫馴,還是闖了一次禍,一位叫蔡誘丁的動物園工人,靠近餵食,「被象鼻舐其頰」,蔡桑的臉被這致命一吻,竟然就受傷了,而且還要好幾天才能痊癒。
猛雄藏了十個月的祕密
二○一三年,給貓熊「圓仔」取個好名字的活動,熱烈進行,進入第二階段,有六個名字開放網路投票。
日本時代,不乏動物明星,不乏有響亮的小名暱稱,但是,為明星動物舉辦命名徵選,只有過一次。主角既非孔雀、雲豹,也非猩猩、大象,而是一對老虎夫婦。
一九八六年,台北動物園才由圓山搬到木柵現址,圓山動物園則早在一九一○年代中期就開幕了。開園之初,便有一隻印度虎,身長六尺,年齡五歲,每天跺著步,咆嘯稱霸。
雖說老虎的壽命可以超過二十年,但是,早期圓山動物園的老虎,不敵三、五年,便要歸天。又死了一隻老虎之後,養育主任大江常四郎哀嘆說,園內的老虎因為年幼,胃非常虛弱,養老虎好像跟養老人一樣,雞肉都要先搗碎成細末,再拌入雞血。
抱怨歸抱怨,動物園沒有老虎,還能號稱是動物園嗎?一九二○年春天,大江常四郎奉命前往新加坡買虎去。本來預定出差往返要花七十天,但大江先生一去無返,不幸病逝新加坡。之後幾年,動物園改向日本的動物商人購買老虎。
一九三五年,圓山動物園又從九州門司的商人那邊買了兩隻馬來虎。四月多,鳳山丸駛進基隆港,載來這一對新客,給動物園注入活力。接下來的五月五日為日本的「子供日」(兒童節),園方靈光一閃,決定那天要給兩隻老虎新生辦個盛大的「命名式」。
徵募虎名的辦法,因兩隻老虎雌雄各一,園方就定位為「虎夫婦」,希望市民大家一起來幫忙取個簡潔、好叫、有夫妻感的名字。應徵者要用空白明信片寫上意愛的名字,活動到四月三十日截止,入選者將送老虎寫真照當獎品。
結果,短短幾天,有一百八十五張明信片飛來,跟現在運用網路,動輒萬人參與,無法相提並論,但是,無礙於選出好名字。五月五日那天,進動物園的遊客都可以拿到印刷漂亮的老虎卡片。下午一點半,市長代表人宣布虎君夫婦名字為「猛雄」和「破魔子」,聽起來,虎先生很生猛,虎太太也是不可輕侮之輩。大象接著揮舞長鼻,向新到的虎朋友致恭賀之意。最後,還打煙火,閃閃火花從空中絢爛灑下,整個動物園內更顯得熱鬧滾滾。
猛雄和破魔子的命名秀,可謂盛大收場,十個月後,卻有個烏龍的結局。
猛雄入住圓山不到一年,也難脫厄運,突發怪病暴斃。動物園解剖死體,全部人都嚇了一大跳,猛雄不是男的,牠是一隻母老虎。回想前一年的虎夫婦命名活動,好不尷尬。
這下怎麼辦?動物園只能馬上向遠在門司的動物商人「提出嚴重抗議」,然後,動物園也不能沒有一隻雄糾糾的老虎,於是又跟原廠商簽了一張買賣契約。不過,這回為了避免相同錯誤,交涉時特別強調,我們要買一隻「確實」是男生的老虎。
狗狗的日本時代
日本幕末,一位荷蘭人的家僕帶一隻外國狗狗,從長崎踏上東瀛土地。接著一八六○年代末期,也就是明治初年,日本門戶向西方大開之際,一隻腳很長、尾巴很細、毛短耳垂的pointer獵犬,跟著牠的英國主人,移居橫濱,開始牠的東方見聞錄。
台灣因中國簽訂天津條約而開放港口,從一八六○年底開始有外國領事到台南。茶商紛至,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西洋傳教師、神父接踵而來。據筆者眼力所及,還未讀到相關資料,證明他們帶著狗兒一起東來。
但是,日本統治台灣後第三年,也就是距今一百零九年前的一八九七年九月初,一個在洋行工作、名叫「保羅」的洋人,在報紙上連登三天一則稀奇罕見的尋狗啟事。說是要找「小洋犬一頭」。大概保羅的狗不怎麼像所謂的西洋狗,廣告說了一個「但是」;「但是,白色狗狗有黑點,尾巴還被剪得很短」。當然,就像現在心急如焚的主人一樣,絕不會虧待幫忙找回愛犬的善心人士,保羅也在廣告之末表明會致贈謝禮。
登載這則尋找愛犬廣告的《臺灣新報》,是日治第一份現代化報紙,一八九六年六月才創刊。即使保羅的白狗不算是台灣第一洋犬,保羅應該還是台灣第一個刊登尋狗啟事的狗主人。
一百多年前,台灣不僅不是沒有小狗蹤影,而且還是滿布市街,很容易讓外國人感受到牠們的存在。把台灣烏龍茶輸出國際的重要英籍茶商陶德(John Dodd)曾幽默說,台灣的狗本來對洋人極不友善,會咆哮追咬洋人,但一八八四到八五年,法國軍隊佔領基隆那段期間,被法軍一寵,幼犬已經會搖尾巴,「跟隨陌生人東晃西晃」了。
其實台灣土狗不僅對洋人懷抱疑懼,日本的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六月初從基隆上岸履任,七月有一天,自己單獨在西門外散步,也曾被一群黑色台灣土狗包圍狂吠。樺山一氣,隔天就命令部下大舉掃蕩野狗。這下台灣土狗惹到的可不是手無寸鐵的英國茶商紳士,而是揮著刀的日本軍人,旋即慘遭斬首報復。
接下去幾年,日本基於衛生考慮,防制狂犬等傳染疾病,非常努力撲殺野狗。養狗既要抽稅,營救野狗還要罰錢。臺北廳並公布法令,要求家犬要繫鑑札,否則一律視為流浪野狗,撲殺勿論。
但是,野狗和家犬只以掛在脖子上的「鑑札」(執照、許可證)來區別,誤殺事件頻傳。一九○七年,終於出現一位主人,挺身為愛犬爭取正義。《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指出,酒商葉瑞,住台北大稻埕日新街(今延平北路和涼州街口東南一側),他的狗領有第五百十七號鑑札。家住日新街西市的葉家狗,一朝跑到南市閒逛,捕狗大隊的日本人高野也晃到南市,報紙說,高野「乍見該犬。即從而銃殺之」。報紙沒說葉瑞傷心悲憤,抑或頗有法律概念,反正他就告官了。他跟法院主張,狗以六十錢買入,之後每天花飼料費十五錢,養了十六個月,共花七十二圓,所以請求高野應賠償他七十二圓六十錢。
狗綁著鑑札,仍被撲殺的何只葉家狗一樁,報紙說,但要求賠償的「殆百無一二焉。葉瑞可謂飼犬人中之錚錚者矣。」
從葉瑞的新聞來看,上個世紀初,似乎不少台灣人會花錢買狗養狗,然而既不關在家裡,也不拉鐵鍊散步,似乎還不到現在養寵物的程度。
到一九一○年代,台灣對遛狗還很陌生。那時有份雜誌《台灣愛國婦人》,常登載各類國際趣聞。一九一五年有一段文章,把賣狗店說成「倫敦最奇者」,「紳士淑女偶一散步。無不率犬而行。每以金環箝其首。區區一犬。雖四五百金至千金,亦所不靳。」靳是古文「吝嗇」之意。倫敦人對狗那般大方,教台灣人很是驚奇。
一九一○年代的台灣社會,倒已不乏飼養西洋犬的人。一九一四年,也有個姓「菅沼」的日本人登廣告尋找愛犬,說他的狗有「白黑斑」,屬「フォックステリア種」,即英文的Fox terrier,台灣稱「雪納瑞」的英國犬。
而寵若兒女的飼主也已經大有人在。葉榮鐘(一九○○年生,報人、政治運動家)十四歲那年,在家鄉鹿港當小藥劑生,受僱於日本人片岡醫生。片岡太太高頭大馬、圓臉有酒窩。葉榮鐘猜她大概沒有生育,「所以養一條捲毛的黑狗,一天到晚抱起抱倒」。
「店狗」也現身了,可惜不怎討喜。一九一五年三月底,春花正開,台北大書店新高堂裡,有個年輕男人正在看書。本來畫面很安恬的,老闆的狗兒卻猛然發飆,咬了這位客人的右腳踝。
在西方世界,一九二○年代開始的兩任美國總統哈定和柯立芝,都曾公開抱著愛犬,大展笑容。一九三○年代廣告上,時尚摩登女郎常戴著鐘形帽,和狗兒一起演出。
戰前就有「狗是奢侈的家庭動物」的說法,當時台灣是否有養寵物狗的流行,並不明顯。不過,中山北路宮前町的煤商張聰明家裡,就有一隻外國臉孔的狗,據稱是他的兒子帶回來的莫斯科犬,他們給牠取了一個洋名「Charlie」(查理)。從一九四○年左右拍攝的舊照上看,查理依偎在坐著的小主人腿邊,頷下的鐵鍊隨意橫過小主人的小腿,顯得安逸而愉快,就跟當今萬家愛犬所受的待遇一般。
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在日本時代擔任高等官員,待遇優渥,他家也養狗,取名「吉姆」。和張家愛犬一樣,都取洋名。
當年,「エス」(唸音同S)似乎頗流行的狗名。在台北靜修女中的刊物裡,有兩篇女學生作文談家裡愛犬,兩隻備受寵愛的狗都叫「エス」。戰後日本還有很長時間,「エス」是日本狗界的「菜市仔名」,漫畫裡常有叫「エス」的狗狗。
從靜修兩位日籍女學生的作文也可以看出,戰前應該沒有專門特製的狗食,一般家犬常吃味噌湯泡飯,非常日本風。當然,也吃生肉、豬肉汁和家裡前晚剩下的菜。
台北市有載客巴士,始於一九一三年,如養不良的初生兒,一年即夭折。真正粗具公車系統規模,已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此後十來年,姑且稱為台北公車的幼稚園期,那時的單純,如你我三歲流著鼻涕、四歲拉著媽媽衣角、五歲抱著小狗,想來可愛。
那時候,公車屬私人經營,車小到比現在的小巴還小。以一九二○年所見的公車來說,底盤高,輪胎比現在瘦。乘客坐左右兩邊,面對面,每邊應該擠不進四個人。說是車,又沒有「車廂」;乘客非置身可封閉的空間,車沒有窗戶,頂上罩布棚,彷彿坐敞篷車。
那時候,公車上還有一個現在已消失的職人,稱之「車掌」。戰後,有一段很長時間,公車都有車掌,負責收賣車票,下車信號也由她們吹哨子。我寫「她們」,因為中年以上兩、三代台灣人遇見的車掌,全是小姐。但是,台北公車的「幼稚園小班」時期,車掌都由男性擔任。
男車掌有點自毀前程。一九二○年,曾有讀者投書爆料,指來往大稻埕與艋舺間的公車,女乘客多中學女學生和護士,她們上車要買票,姓王的和姓葉的兩個男車掌故意不賣,色迷迷的,等停車或下車,再手來腳來,「調戲」這些少女。兩年後,車公司也覺得設車掌的弊害太多,就把男車掌廢了。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台北公車才起用六位女車掌,其中四位是台灣小姐。
當初,還有一個專屬舊時代的公車風景。
一九二四年八月,颱風剛掃過,到處水災。公館到新店之間,沿途牛車、拉車,晝夜絡繹不絕,搬運重建需用的材料。二十四日晚上八點半左右,天色漆暗,車牌號「50」的公車載了十三位乘客從新店往北來,幾乎可說是摸黑前進。駛到景美的番婆厝(今萬隆集應廟一帶),二十二歲的廖姓司機看到牛車時已來不及,還好只是擦撞,車有點損壞,便想到有燈的地方修理。沒想到,往前開開開,到今萬盛街那邊,忽然,才轉一下把手,車就栽進田裡了。災情反而比撞牛車嚴重,報紙說,車體「全部粉碎」,車上的日本警察光田撞到鼻樑,流著血,其他七位台灣籍乘客輕重傷都有。
現在公車都走在大馬路上,穿梭在大樓與樓房之間,八、九十年前大不同,公車一出大稻埕、艋舺和城中區,四處盡是農田,道路又窄,稍有車況,方向盤稍偏,動不動就,「犁田」了。
一九三一年,還發生一種現在幾乎不可能發生的公車之禍。一樣是二十出頭的年輕司機,駕駛台北市營公車,從中崙往台北車站開,來到善導寺(當時為淨土宗別院),那裡有個公車牌,郭姓司機正準備停車。故事說到這裡,必須插入一個說明,日本時代,陸上交通一律靠左行,因此,郭運將準備停車的位置為路的南邊。這時,從今天紹興南街駛出一部市役所(市政府)的「糞屎運搬車」,像溜冰一樣,無遮阻地撞上公車的左後側。公車玻璃窗全破了,一位日本籍乘客割傷頭,一位台灣人乘客割傷臉。更恐怖的是,他們還被潑到穢物,搞得搭個公車好像遇見仇人似的。
不過,報紙編輯可能為了補償他們受創的心靈,標題下得文雅,說是公車撞糞尿車,乘客負傷,「有沐黃金汁者」。
小象闖進高級料亭了
小熊貓「圓仔」連睡個覺都那麼卡哇衣,惹人愛憐,成為台北動物園的新明星。時間往前推,戰後幾十年,圓仔的前輩是大象林旺,再往前推到日本時代,那就屬「麻──將」最紅了。
「麻──將」是一隻母象,大家暱稱牠「マーちゃん」,可以譯成「小瑪」,但念起來的聲音則像中文的「麻將」,叫起來頗順口,姑且就這樣寫。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麻將先搭船到基隆,轉搭貨運列車,抵達台北火車站。民眾已經聞風而來,圍觀等待者有戴斗笠的、有穿台灣衫褲的,明顯是台灣人。報紙如拿刀刻木,要把歷史上不可忘卻的時間牢牢記著,午後兩點十二分,麻將小象從貨物車的小斜坡走下來,終於踏上台灣的土地,同一秒,新聞記者拚命按下快門。
然後,麻將如何從台北火車站到她的新家圓山動物園呢?用走的。動物園的人餵她樹葉和水,誘騙她慢慢往前。從現在忠孝西路靠左側開始走,第一個轉彎,走進今天的中山北路。路口的行政院,以前是台北市役所(市政府),市尹(市長)太田吾一鼻下蓄著髭,和一堆公務員跑出來歡迎。市長出迎的熱鬧沒過幾秒,麻將走一走,明明有鐵鍊圈住脖子,仍然拉不住,突然就衝進旁邊的日式高級酒宴料亭「梅屋敷」,即今天的國父史蹟紀念館。一個小時後,好不容易才入住圓山新家。
之後,麻將就變成圓山動物園的「人氣者」,大人小孩抱著好奇去,看牠用鼻子吃飯,興味盎然。麻將一整天要吃五顆鳳梨、甘蔗葉一百斤、一些普通青草、一斗的水,再加上刺刺的鳳梨葉五十斤,非常驚人。
有一次,中部的原住民小孩到動物園修學旅行,他們在山上看過許多動物,對大象卻很陌生。雖然麻將還是小母象,只有一千公斤左右,他們仍覺得大得可怕。麻將的象腿,在他們眼裡,很像部落的石臼。初看到麻將的象鼻,他們皺眉不解,為什麼象臉上會長出一隻腳來。
日本時代,去動物園已是孩童普遍的活動。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在回憶錄裡說,小學時,老師帶他們到圓山動物園遠足,前一晚他興奮得睡不著覺。隔天搭火車從基隆出發,下了台北火車站,再走路到動物園,花了大半天,雖然只剩半日遊,也很高興滿足。張榮發生於一九二七年,小學時期到動物園遠足,應該看過人氣印度象「麻將」。
三○年代,麻將是圓山動物園的第一女主角,她塊頭大,存在感十足,能聽命做動作,每年「動物祭」,動物園準備米、地瓜、蜜柑、甘蔗、香蕉和柿子等供品,祭拜死去的動物同伴,感謝牠們的付出,此時,麻將就會身披彩衣登場,代表園內所有動物屈膝祭拜。
同在園內,猩猩「一郎君」也很受歡迎,身高一二八公分、體重六十八公斤,是全日本第一大的猩猩。不過,日本時代,圓山動物園歷經兩次大門改裝,一九三九年底那回的新門,入口正上方還是畫了兩頭大象,那可說是麻將的勳章,證明牠不容動搖的一姐地位。
麻將向來溫馴,還是闖了一次禍,一位叫蔡誘丁的動物園工人,靠近餵食,「被象鼻舐其頰」,蔡桑的臉被這致命一吻,竟然就受傷了,而且還要好幾天才能痊癒。
猛雄藏了十個月的祕密
二○一三年,給貓熊「圓仔」取個好名字的活動,熱烈進行,進入第二階段,有六個名字開放網路投票。
日本時代,不乏動物明星,不乏有響亮的小名暱稱,但是,為明星動物舉辦命名徵選,只有過一次。主角既非孔雀、雲豹,也非猩猩、大象,而是一對老虎夫婦。
一九八六年,台北動物園才由圓山搬到木柵現址,圓山動物園則早在一九一○年代中期就開幕了。開園之初,便有一隻印度虎,身長六尺,年齡五歲,每天跺著步,咆嘯稱霸。
雖說老虎的壽命可以超過二十年,但是,早期圓山動物園的老虎,不敵三、五年,便要歸天。又死了一隻老虎之後,養育主任大江常四郎哀嘆說,園內的老虎因為年幼,胃非常虛弱,養老虎好像跟養老人一樣,雞肉都要先搗碎成細末,再拌入雞血。
抱怨歸抱怨,動物園沒有老虎,還能號稱是動物園嗎?一九二○年春天,大江常四郎奉命前往新加坡買虎去。本來預定出差往返要花七十天,但大江先生一去無返,不幸病逝新加坡。之後幾年,動物園改向日本的動物商人購買老虎。
一九三五年,圓山動物園又從九州門司的商人那邊買了兩隻馬來虎。四月多,鳳山丸駛進基隆港,載來這一對新客,給動物園注入活力。接下來的五月五日為日本的「子供日」(兒童節),園方靈光一閃,決定那天要給兩隻老虎新生辦個盛大的「命名式」。
徵募虎名的辦法,因兩隻老虎雌雄各一,園方就定位為「虎夫婦」,希望市民大家一起來幫忙取個簡潔、好叫、有夫妻感的名字。應徵者要用空白明信片寫上意愛的名字,活動到四月三十日截止,入選者將送老虎寫真照當獎品。
結果,短短幾天,有一百八十五張明信片飛來,跟現在運用網路,動輒萬人參與,無法相提並論,但是,無礙於選出好名字。五月五日那天,進動物園的遊客都可以拿到印刷漂亮的老虎卡片。下午一點半,市長代表人宣布虎君夫婦名字為「猛雄」和「破魔子」,聽起來,虎先生很生猛,虎太太也是不可輕侮之輩。大象接著揮舞長鼻,向新到的虎朋友致恭賀之意。最後,還打煙火,閃閃火花從空中絢爛灑下,整個動物園內更顯得熱鬧滾滾。
猛雄和破魔子的命名秀,可謂盛大收場,十個月後,卻有個烏龍的結局。
猛雄入住圓山不到一年,也難脫厄運,突發怪病暴斃。動物園解剖死體,全部人都嚇了一大跳,猛雄不是男的,牠是一隻母老虎。回想前一年的虎夫婦命名活動,好不尷尬。
這下怎麼辦?動物園只能馬上向遠在門司的動物商人「提出嚴重抗議」,然後,動物園也不能沒有一隻雄糾糾的老虎,於是又跟原廠商簽了一張買賣契約。不過,這回為了避免相同錯誤,交涉時特別強調,我們要買一隻「確實」是男生的老虎。
狗狗的日本時代
日本幕末,一位荷蘭人的家僕帶一隻外國狗狗,從長崎踏上東瀛土地。接著一八六○年代末期,也就是明治初年,日本門戶向西方大開之際,一隻腳很長、尾巴很細、毛短耳垂的pointer獵犬,跟著牠的英國主人,移居橫濱,開始牠的東方見聞錄。
台灣因中國簽訂天津條約而開放港口,從一八六○年底開始有外國領事到台南。茶商紛至,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西洋傳教師、神父接踵而來。據筆者眼力所及,還未讀到相關資料,證明他們帶著狗兒一起東來。
但是,日本統治台灣後第三年,也就是距今一百零九年前的一八九七年九月初,一個在洋行工作、名叫「保羅」的洋人,在報紙上連登三天一則稀奇罕見的尋狗啟事。說是要找「小洋犬一頭」。大概保羅的狗不怎麼像所謂的西洋狗,廣告說了一個「但是」;「但是,白色狗狗有黑點,尾巴還被剪得很短」。當然,就像現在心急如焚的主人一樣,絕不會虧待幫忙找回愛犬的善心人士,保羅也在廣告之末表明會致贈謝禮。
登載這則尋找愛犬廣告的《臺灣新報》,是日治第一份現代化報紙,一八九六年六月才創刊。即使保羅的白狗不算是台灣第一洋犬,保羅應該還是台灣第一個刊登尋狗啟事的狗主人。
一百多年前,台灣不僅不是沒有小狗蹤影,而且還是滿布市街,很容易讓外國人感受到牠們的存在。把台灣烏龍茶輸出國際的重要英籍茶商陶德(John Dodd)曾幽默說,台灣的狗本來對洋人極不友善,會咆哮追咬洋人,但一八八四到八五年,法國軍隊佔領基隆那段期間,被法軍一寵,幼犬已經會搖尾巴,「跟隨陌生人東晃西晃」了。
其實台灣土狗不僅對洋人懷抱疑懼,日本的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六月初從基隆上岸履任,七月有一天,自己單獨在西門外散步,也曾被一群黑色台灣土狗包圍狂吠。樺山一氣,隔天就命令部下大舉掃蕩野狗。這下台灣土狗惹到的可不是手無寸鐵的英國茶商紳士,而是揮著刀的日本軍人,旋即慘遭斬首報復。
接下去幾年,日本基於衛生考慮,防制狂犬等傳染疾病,非常努力撲殺野狗。養狗既要抽稅,營救野狗還要罰錢。臺北廳並公布法令,要求家犬要繫鑑札,否則一律視為流浪野狗,撲殺勿論。
但是,野狗和家犬只以掛在脖子上的「鑑札」(執照、許可證)來區別,誤殺事件頻傳。一九○七年,終於出現一位主人,挺身為愛犬爭取正義。《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指出,酒商葉瑞,住台北大稻埕日新街(今延平北路和涼州街口東南一側),他的狗領有第五百十七號鑑札。家住日新街西市的葉家狗,一朝跑到南市閒逛,捕狗大隊的日本人高野也晃到南市,報紙說,高野「乍見該犬。即從而銃殺之」。報紙沒說葉瑞傷心悲憤,抑或頗有法律概念,反正他就告官了。他跟法院主張,狗以六十錢買入,之後每天花飼料費十五錢,養了十六個月,共花七十二圓,所以請求高野應賠償他七十二圓六十錢。
狗綁著鑑札,仍被撲殺的何只葉家狗一樁,報紙說,但要求賠償的「殆百無一二焉。葉瑞可謂飼犬人中之錚錚者矣。」
從葉瑞的新聞來看,上個世紀初,似乎不少台灣人會花錢買狗養狗,然而既不關在家裡,也不拉鐵鍊散步,似乎還不到現在養寵物的程度。
到一九一○年代,台灣對遛狗還很陌生。那時有份雜誌《台灣愛國婦人》,常登載各類國際趣聞。一九一五年有一段文章,把賣狗店說成「倫敦最奇者」,「紳士淑女偶一散步。無不率犬而行。每以金環箝其首。區區一犬。雖四五百金至千金,亦所不靳。」靳是古文「吝嗇」之意。倫敦人對狗那般大方,教台灣人很是驚奇。
一九一○年代的台灣社會,倒已不乏飼養西洋犬的人。一九一四年,也有個姓「菅沼」的日本人登廣告尋找愛犬,說他的狗有「白黑斑」,屬「フォックステリア種」,即英文的Fox terrier,台灣稱「雪納瑞」的英國犬。
而寵若兒女的飼主也已經大有人在。葉榮鐘(一九○○年生,報人、政治運動家)十四歲那年,在家鄉鹿港當小藥劑生,受僱於日本人片岡醫生。片岡太太高頭大馬、圓臉有酒窩。葉榮鐘猜她大概沒有生育,「所以養一條捲毛的黑狗,一天到晚抱起抱倒」。
「店狗」也現身了,可惜不怎討喜。一九一五年三月底,春花正開,台北大書店新高堂裡,有個年輕男人正在看書。本來畫面很安恬的,老闆的狗兒卻猛然發飆,咬了這位客人的右腳踝。
在西方世界,一九二○年代開始的兩任美國總統哈定和柯立芝,都曾公開抱著愛犬,大展笑容。一九三○年代廣告上,時尚摩登女郎常戴著鐘形帽,和狗兒一起演出。
戰前就有「狗是奢侈的家庭動物」的說法,當時台灣是否有養寵物狗的流行,並不明顯。不過,中山北路宮前町的煤商張聰明家裡,就有一隻外國臉孔的狗,據稱是他的兒子帶回來的莫斯科犬,他們給牠取了一個洋名「Charlie」(查理)。從一九四○年左右拍攝的舊照上看,查理依偎在坐著的小主人腿邊,頷下的鐵鍊隨意橫過小主人的小腿,顯得安逸而愉快,就跟當今萬家愛犬所受的待遇一般。
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在日本時代擔任高等官員,待遇優渥,他家也養狗,取名「吉姆」。和張家愛犬一樣,都取洋名。
當年,「エス」(唸音同S)似乎頗流行的狗名。在台北靜修女中的刊物裡,有兩篇女學生作文談家裡愛犬,兩隻備受寵愛的狗都叫「エス」。戰後日本還有很長時間,「エス」是日本狗界的「菜市仔名」,漫畫裡常有叫「エス」的狗狗。
從靜修兩位日籍女學生的作文也可以看出,戰前應該沒有專門特製的狗食,一般家犬常吃味噌湯泡飯,非常日本風。當然,也吃生肉、豬肉汁和家裡前晚剩下的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