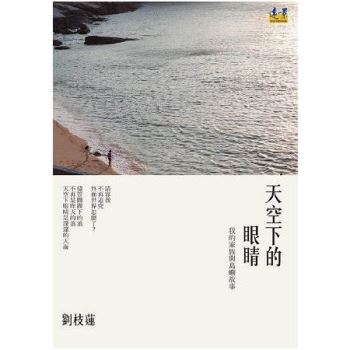父親討海日子(一九五八~一九七○)
那時,我們家有一隻黃貓,牠總懶洋洋,找個定錨點,直睜睜看著人們,重複、單一動作,有時候是一個晌午。小時候,我也喜歡一個人坐在階梯上,直睜睜,看著金正叔叔他們,如何重複整理漁網,從打開、抖落、摺疊;或者他們以強勁的手,搖轉呀搖轉,從這頭到那頭,編製著「繩索」。他們有時對著一塊如鐵石木頭,不斷鑿洞,每天就這麼丁點木屑,連拿起掃帚都嫌少。至於我為什麼會對這盲目與單調視覺感到興趣,連自己也不懂,或許有一世,我也是貓,一隻孤僻的貓。
那些年,我們這大房子,總是好多人,金正叔叔、國興伯伯、金暖表哥、嬤珠表舅、珠弟哥哥、立義姨丈、典露叔叔、孟大表哥……,還有從香港來的廣東人伯伯,他們一高一矮,其中一位白髮,聽長輩說,他們是來馬祖研發白力魚(梅香魚)。記憶中,他們住在三樓,很少聽他們二個開口說話,是語言不通?我不了解。金正叔叔他們是爸爸找來的工作伙伴,是蝦皮豐收一起慶祝、婚喪喜慶一起幫忙、遇到困難會互相包容、彼此扶持的另類家人。
一九五八年機動舢舨「中興一號」下水啟用。它不僅取代傳統「搖櫓」捕魚方式,也為馬祖漁民打開新的視野。一九五九年,父親嗅到將要遍地開花的漁耕方式,主動邀約牛角村國興伯伯、典露叔叔等六人合股,一起造新船。他們六人之中,以親兄弟搭檔「下江」、「討海」為一組,六股十二人,姜伯伯為技術股,不出資。其實大夥都不出資,都由父親全權處理,包括資金。一九六一年新船「建新號」落水啟用,它不只改變了「一柄櫓槳下大洋」牧漁方式,也跨過了「家族海耕」形態,轉型成了鄰里「伙伴關係」。
父親是出資者,對外代表船公司;國興伯伯則管理營運,對內負管理經營責任;舅舅曹典詠管理財務、金正叔是船長、姜伯伯負責打樁技能、「鴉片鬼」卡叔負責膳食。一切就定位,隨著衝上天際鞭炮聲,一九六一年新房子完工,股東與我們同步遷入新家,這兒成了大夥築夢的來處,是休息也是出發的地方。
四○、五○年代蝦皮(或稱毛蝦、小蝦)、黃魚並列馬祖主要漁獲。蝦皮移動方向主要在南竿、北竿。若要與黃魚相遇,那麼就要選擇東引島。「建新號」以追逐蝦皮為主,也曾遠赴東引追捕黃魚。而捕蝦皮要用「起斗」(定置網)製作材料如稻草等,都得從臺灣購買,由於在季節開始前準備購料,漁民通常稱這樣的採購為「辦季頭」。
│辦季頭│
馬祖列島位處閩江口。閩江,是河水與海水交錯碰撞水質環境,適合浮游生物生存,而浮游生物孕育了「蝦皮」。「蝦皮」在食物鏈追逐下,每年農曆十一月至次年四、五月之間,便會成群聚集在島的沿海。其實馬祖豐富蝦皮資源,在清朝就吸引了大陸福建沿海漁民,尤其是梅花鎮的漁民。這批聞汛期而來的漁民,雖然帶走海上豐富資源,也帶來了漁船在海上圍捕蝦皮技術,俗稱「繒網」,「建新號」技術入股的姜伯伯,就曾為梅花鎮漁民打工,是最好例證。
這個固定「網」的製作,包括斗、樁、繩、輪板、窗……主要元件,都得漁民手工完成,而這些元件所需要材料,包括稻草、竹皮、孟宗竹、桂竹、網尾、棉線繩、洋麻、薯榔、紅柴、硬木等都是由漁會出面招標,登記地點是彰化市第一旅社,為維護漁民權益,每年會指派漁民代表四至六人,到竹山等現地監督或接收相關物料,父親便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小看這「招標」採購過程,那就大錯特錯了。姑且不論,以當時物價,每季二十、三十萬交易,可是個龐大經濟活動,其中孟宗竹是管制物件,需要總統府來核定。我的父親不識字、普通話也不輪轉,他是如何扛了二十、三十萬現金,來到既陌生又偏僻山間,以漁民代表身分來監督採購,我造訪林內趙炆山先生。
趙叔,趙炆山,一九三三年出生,是提供孟宗竹給漁民的廠商之一。與其他廠商相較,是當時年紀最輕的供應商。也因為這樣理由,父親以對廟宇(連興宮)僅有的記憶,高齡九十歲,在竹山與趙叔上演五十年之後,重逢的悸動。當趙家二哥說:「我父親(趙叔)站在門口等著他的老友,那紋風不動只是身軀,遠遠的,我聽到他顫抖的心……。」那段英雄重逢竊喜戲碼上演時,感動了雙方陪同造訪的晚輩,我雖然無法參與那一次盛會,當趙家二哥為我打開電腦螢幕時,我動容了,抑制要落下來的眼淚,噙在眼眶打轉;那夜,我執意編織著父親與故友──臺鐵林內車站站長、麵攤柯姓老闆、照片中外省女子以及我父親想要認養的男孩,他們與父親的故事。
趙叔說:「林內,是竹子故鄉,當時有許多人衝著竹子而來,商場難免有應酬,林內酒家林立,有些來辦採購的人,會要求去酒家尋歡,你們父親不菸、不酒、從不上酒家,工作認真負責,將民雄、林內、竹東將要交接木材、竹子劃上紅線、點上記號,送到林內火車站,轉運至基隆上船。平常飲食多數在車站旁邊柯姓麵攤解決,為方便往返,也就落腳在車站附近的民生旅店或永大旅社……。」趙叔表述的父親,我沒有驚訝,這本就是我父親真實樣貌。
或許趙叔不知道,那幾年,父親每次臺灣回來,總會扛著一籮筐一籮筐的水果、孩子衣物、家庭用品。表姊說:「有一次,姑爹買了一麻袋球鞋,先讓我家小朋友挑,竟然出現兩隻同腳鞋。當時,回力牌球鞋可珍貴,我的弟弟中,有一位同腳鞋,也穿了許久……。」我好奇的是,為什麼是一麻袋?「以前,每家孩子都能自成一個籃球隊,妳們家、我們家,還有……姑爹對一堆大、小孩,無法判斷尺寸,就隨性買下,我家挑好再到妳家……。」表姊這般回應我說。
原來如此,記憶中孩提時,我有時會穿過膝的洋裝、過小而綁腳的皮鞋。這不打緊,因為對光著腳的孩子而言,「皮鞋」、「洋裝」已經是從來沒見過的奢侈品。沒錯,那些年,不只小孩沒見過這些奢侈品,一般婦女身著鬆緊帶粗褲,上衣為開襟式,並以布做紐扣,有時還光著腳丫,上山種菜、抬魚貨。多數漁民,即便是冬季下海捕魚,沒有雨鞋,打著赤腳,那如鱷魚皮般的腳皮,成了他們的印記。父親不到臺灣,多年都穿著,唯一破棉襖,黑色,七分袖,那寬鬆褲子,還露出小腿肚,除了方便漁事工作,大部有省些布料的意味。
由於爸爸勤奮與能幹,有記憶中的我從沒餓著,偶爾有一些特別如鋼筆之類東西,這大概是拜爸爸到臺灣「辦季頭」之賜吧!那些年,每當父親從臺灣回來,扛著各式水果,剛進入村口,大澳街上正在玩耍的小朋友,總會一路跟到我家;那物資缺乏的年代,小朋友對西瓜、鳳梨、糖果、瓜子……,充滿好奇與期待,而我父母親從不會讓大家失望。有一年,年幼的弟弟與妹妹索性跑到村口候著爸爸,正逢中秋節,怕月餅未到家,在途中已分享其他小朋友了。
四○年代到臺灣是讓人羨慕的經驗。一次,我路過大澳街口,看見從臺灣回來J叔叔,穿起西服、皮鞋,還戴著黑白電影才看到的帽子,時髦地與街坊鄰居說著,讓人羨慕的經驗。父親從不,他不但沒有穿著西裝、襯衫,還肩上扛著、手上擰著一籮筐一籮筐的水果,徒步爬過一重一重好漢坡,不只為了家人,還包括街坊鄰里與親友。父親為了扛物資回家,必須脫掉磨腳的皮鞋,成了「只愛赤腳,不愛穿鞋」的土包子意象,也成了長輩逗弄我的話題。少小時,聽到別人誇大說著父親如何捲起褲管、脫掉皮鞋情節時,我總想要辯駁。長大一點,我覺得父親非常了不起;當紳士,尤其是假紳士,很容易,要能負重,很困難;表象有什麼重要的呢!
「與人分享」是我們家每位成員必修家庭學分。大姊同學芳姊說,那年,她們小四,她到我們家等姊姊上學,媽媽招呼她,裝飯吃,那是她人生第一次有米飯拌豬油,即便過了六十年,口齒仍然留香……。這等連大姊都忘了的事,芳姊卻說得有滋有味。動亂年代,大家都窮,多數家庭以「地瓜籤」為主食,白米與豬油對我們而言,也只是剛好而已吧!或許媽媽當天自己以其它食物替代了豬油拌飯,這樣的媽媽我們很熟悉,即便與女兒吃飯、逛街也搶要付錢。
偶有,我父親帶著我,沿著牛角陂上山,大抵造訪朋友。我們路過兩旁房屋,都住著不同面孔,但他們都會與父親寒暄,說些無關緊要的事。我最常聽到是:「年關不好,沒米煮飯」或「依清哥,我想借米」之類的話語,這時我父親總笑呵呵地說:「好,好,到我家去拿,我家很多。」大嬸們吆喝她家孩子拿著臉盆到我家取米,有時我們返家,媽媽會說:「沒米下鍋。」這樣情況久了,次數多了,我們知道家裡米缸空的理由,沒有人嘟嘴、抱怨,視為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的事。
父母親不識字,沒有很多大道理,也不喜歡說教,他們以身教來教育我們。
記得,有一年,過年,我帶著弟弟妹妹,將一顆很大的橘子,從上端挖個小洞,將內裡的肉吃掉,從中填入瓜子殼,然後丟在路中,惡作劇躲在窗口觀看撿到的人反應。從不對我嚴厲的爸爸,那次訓斥我一頓,並告訴我:「吃這樣水果、住這樣大房子,只不過是我們運氣好……。」那年,我小二。
一九六三年小弟「一國」出生,對重男輕女社會,毫無疑問,小弟出生是值得期待。那年,媽媽已是三十六歲高齡。父親對哥哥姊姊很嚴厲,即便我從沒看到父親打小孩,他只需看一眼、開口說話,大家就已經嚇得夠厲害,尤其對長子建華,父親認為男孩需要肩膀,可以打罵,而大哥在父親面前也顯得畏縮,即便當了爺,一樣敬畏父親。但我父親替我哥哥許親大嫂,是家中唯一口無遮攔、敢頂撞父親的人,即便是大年初二。或許是晚年得子,父親對弟弟不會如此約束他,「一國」從小就展現領導人特質,品學兼優。
那時,我們家有一隻黃貓,牠總懶洋洋,找個定錨點,直睜睜看著人們,重複、單一動作,有時候是一個晌午。小時候,我也喜歡一個人坐在階梯上,直睜睜,看著金正叔叔他們,如何重複整理漁網,從打開、抖落、摺疊;或者他們以強勁的手,搖轉呀搖轉,從這頭到那頭,編製著「繩索」。他們有時對著一塊如鐵石木頭,不斷鑿洞,每天就這麼丁點木屑,連拿起掃帚都嫌少。至於我為什麼會對這盲目與單調視覺感到興趣,連自己也不懂,或許有一世,我也是貓,一隻孤僻的貓。
那些年,我們這大房子,總是好多人,金正叔叔、國興伯伯、金暖表哥、嬤珠表舅、珠弟哥哥、立義姨丈、典露叔叔、孟大表哥……,還有從香港來的廣東人伯伯,他們一高一矮,其中一位白髮,聽長輩說,他們是來馬祖研發白力魚(梅香魚)。記憶中,他們住在三樓,很少聽他們二個開口說話,是語言不通?我不了解。金正叔叔他們是爸爸找來的工作伙伴,是蝦皮豐收一起慶祝、婚喪喜慶一起幫忙、遇到困難會互相包容、彼此扶持的另類家人。
一九五八年機動舢舨「中興一號」下水啟用。它不僅取代傳統「搖櫓」捕魚方式,也為馬祖漁民打開新的視野。一九五九年,父親嗅到將要遍地開花的漁耕方式,主動邀約牛角村國興伯伯、典露叔叔等六人合股,一起造新船。他們六人之中,以親兄弟搭檔「下江」、「討海」為一組,六股十二人,姜伯伯為技術股,不出資。其實大夥都不出資,都由父親全權處理,包括資金。一九六一年新船「建新號」落水啟用,它不只改變了「一柄櫓槳下大洋」牧漁方式,也跨過了「家族海耕」形態,轉型成了鄰里「伙伴關係」。
父親是出資者,對外代表船公司;國興伯伯則管理營運,對內負管理經營責任;舅舅曹典詠管理財務、金正叔是船長、姜伯伯負責打樁技能、「鴉片鬼」卡叔負責膳食。一切就定位,隨著衝上天際鞭炮聲,一九六一年新房子完工,股東與我們同步遷入新家,這兒成了大夥築夢的來處,是休息也是出發的地方。
四○、五○年代蝦皮(或稱毛蝦、小蝦)、黃魚並列馬祖主要漁獲。蝦皮移動方向主要在南竿、北竿。若要與黃魚相遇,那麼就要選擇東引島。「建新號」以追逐蝦皮為主,也曾遠赴東引追捕黃魚。而捕蝦皮要用「起斗」(定置網)製作材料如稻草等,都得從臺灣購買,由於在季節開始前準備購料,漁民通常稱這樣的採購為「辦季頭」。
│辦季頭│
馬祖列島位處閩江口。閩江,是河水與海水交錯碰撞水質環境,適合浮游生物生存,而浮游生物孕育了「蝦皮」。「蝦皮」在食物鏈追逐下,每年農曆十一月至次年四、五月之間,便會成群聚集在島的沿海。其實馬祖豐富蝦皮資源,在清朝就吸引了大陸福建沿海漁民,尤其是梅花鎮的漁民。這批聞汛期而來的漁民,雖然帶走海上豐富資源,也帶來了漁船在海上圍捕蝦皮技術,俗稱「繒網」,「建新號」技術入股的姜伯伯,就曾為梅花鎮漁民打工,是最好例證。
這個固定「網」的製作,包括斗、樁、繩、輪板、窗……主要元件,都得漁民手工完成,而這些元件所需要材料,包括稻草、竹皮、孟宗竹、桂竹、網尾、棉線繩、洋麻、薯榔、紅柴、硬木等都是由漁會出面招標,登記地點是彰化市第一旅社,為維護漁民權益,每年會指派漁民代表四至六人,到竹山等現地監督或接收相關物料,父親便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小看這「招標」採購過程,那就大錯特錯了。姑且不論,以當時物價,每季二十、三十萬交易,可是個龐大經濟活動,其中孟宗竹是管制物件,需要總統府來核定。我的父親不識字、普通話也不輪轉,他是如何扛了二十、三十萬現金,來到既陌生又偏僻山間,以漁民代表身分來監督採購,我造訪林內趙炆山先生。
趙叔,趙炆山,一九三三年出生,是提供孟宗竹給漁民的廠商之一。與其他廠商相較,是當時年紀最輕的供應商。也因為這樣理由,父親以對廟宇(連興宮)僅有的記憶,高齡九十歲,在竹山與趙叔上演五十年之後,重逢的悸動。當趙家二哥說:「我父親(趙叔)站在門口等著他的老友,那紋風不動只是身軀,遠遠的,我聽到他顫抖的心……。」那段英雄重逢竊喜戲碼上演時,感動了雙方陪同造訪的晚輩,我雖然無法參與那一次盛會,當趙家二哥為我打開電腦螢幕時,我動容了,抑制要落下來的眼淚,噙在眼眶打轉;那夜,我執意編織著父親與故友──臺鐵林內車站站長、麵攤柯姓老闆、照片中外省女子以及我父親想要認養的男孩,他們與父親的故事。
趙叔說:「林內,是竹子故鄉,當時有許多人衝著竹子而來,商場難免有應酬,林內酒家林立,有些來辦採購的人,會要求去酒家尋歡,你們父親不菸、不酒、從不上酒家,工作認真負責,將民雄、林內、竹東將要交接木材、竹子劃上紅線、點上記號,送到林內火車站,轉運至基隆上船。平常飲食多數在車站旁邊柯姓麵攤解決,為方便往返,也就落腳在車站附近的民生旅店或永大旅社……。」趙叔表述的父親,我沒有驚訝,這本就是我父親真實樣貌。
或許趙叔不知道,那幾年,父親每次臺灣回來,總會扛著一籮筐一籮筐的水果、孩子衣物、家庭用品。表姊說:「有一次,姑爹買了一麻袋球鞋,先讓我家小朋友挑,竟然出現兩隻同腳鞋。當時,回力牌球鞋可珍貴,我的弟弟中,有一位同腳鞋,也穿了許久……。」我好奇的是,為什麼是一麻袋?「以前,每家孩子都能自成一個籃球隊,妳們家、我們家,還有……姑爹對一堆大、小孩,無法判斷尺寸,就隨性買下,我家挑好再到妳家……。」表姊這般回應我說。
原來如此,記憶中孩提時,我有時會穿過膝的洋裝、過小而綁腳的皮鞋。這不打緊,因為對光著腳的孩子而言,「皮鞋」、「洋裝」已經是從來沒見過的奢侈品。沒錯,那些年,不只小孩沒見過這些奢侈品,一般婦女身著鬆緊帶粗褲,上衣為開襟式,並以布做紐扣,有時還光著腳丫,上山種菜、抬魚貨。多數漁民,即便是冬季下海捕魚,沒有雨鞋,打著赤腳,那如鱷魚皮般的腳皮,成了他們的印記。父親不到臺灣,多年都穿著,唯一破棉襖,黑色,七分袖,那寬鬆褲子,還露出小腿肚,除了方便漁事工作,大部有省些布料的意味。
由於爸爸勤奮與能幹,有記憶中的我從沒餓著,偶爾有一些特別如鋼筆之類東西,這大概是拜爸爸到臺灣「辦季頭」之賜吧!那些年,每當父親從臺灣回來,扛著各式水果,剛進入村口,大澳街上正在玩耍的小朋友,總會一路跟到我家;那物資缺乏的年代,小朋友對西瓜、鳳梨、糖果、瓜子……,充滿好奇與期待,而我父母親從不會讓大家失望。有一年,年幼的弟弟與妹妹索性跑到村口候著爸爸,正逢中秋節,怕月餅未到家,在途中已分享其他小朋友了。
四○年代到臺灣是讓人羨慕的經驗。一次,我路過大澳街口,看見從臺灣回來J叔叔,穿起西服、皮鞋,還戴著黑白電影才看到的帽子,時髦地與街坊鄰居說著,讓人羨慕的經驗。父親從不,他不但沒有穿著西裝、襯衫,還肩上扛著、手上擰著一籮筐一籮筐的水果,徒步爬過一重一重好漢坡,不只為了家人,還包括街坊鄰里與親友。父親為了扛物資回家,必須脫掉磨腳的皮鞋,成了「只愛赤腳,不愛穿鞋」的土包子意象,也成了長輩逗弄我的話題。少小時,聽到別人誇大說著父親如何捲起褲管、脫掉皮鞋情節時,我總想要辯駁。長大一點,我覺得父親非常了不起;當紳士,尤其是假紳士,很容易,要能負重,很困難;表象有什麼重要的呢!
「與人分享」是我們家每位成員必修家庭學分。大姊同學芳姊說,那年,她們小四,她到我們家等姊姊上學,媽媽招呼她,裝飯吃,那是她人生第一次有米飯拌豬油,即便過了六十年,口齒仍然留香……。這等連大姊都忘了的事,芳姊卻說得有滋有味。動亂年代,大家都窮,多數家庭以「地瓜籤」為主食,白米與豬油對我們而言,也只是剛好而已吧!或許媽媽當天自己以其它食物替代了豬油拌飯,這樣的媽媽我們很熟悉,即便與女兒吃飯、逛街也搶要付錢。
偶有,我父親帶著我,沿著牛角陂上山,大抵造訪朋友。我們路過兩旁房屋,都住著不同面孔,但他們都會與父親寒暄,說些無關緊要的事。我最常聽到是:「年關不好,沒米煮飯」或「依清哥,我想借米」之類的話語,這時我父親總笑呵呵地說:「好,好,到我家去拿,我家很多。」大嬸們吆喝她家孩子拿著臉盆到我家取米,有時我們返家,媽媽會說:「沒米下鍋。」這樣情況久了,次數多了,我們知道家裡米缸空的理由,沒有人嘟嘴、抱怨,視為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的事。
父母親不識字,沒有很多大道理,也不喜歡說教,他們以身教來教育我們。
記得,有一年,過年,我帶著弟弟妹妹,將一顆很大的橘子,從上端挖個小洞,將內裡的肉吃掉,從中填入瓜子殼,然後丟在路中,惡作劇躲在窗口觀看撿到的人反應。從不對我嚴厲的爸爸,那次訓斥我一頓,並告訴我:「吃這樣水果、住這樣大房子,只不過是我們運氣好……。」那年,我小二。
一九六三年小弟「一國」出生,對重男輕女社會,毫無疑問,小弟出生是值得期待。那年,媽媽已是三十六歲高齡。父親對哥哥姊姊很嚴厲,即便我從沒看到父親打小孩,他只需看一眼、開口說話,大家就已經嚇得夠厲害,尤其對長子建華,父親認為男孩需要肩膀,可以打罵,而大哥在父親面前也顯得畏縮,即便當了爺,一樣敬畏父親。但我父親替我哥哥許親大嫂,是家中唯一口無遮攔、敢頂撞父親的人,即便是大年初二。或許是晚年得子,父親對弟弟不會如此約束他,「一國」從小就展現領導人特質,品學兼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