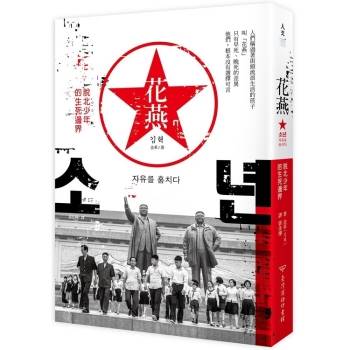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我因為非法越境(意指脫北)的嫌疑,被拘留在咸鏡北道穩城的某個安全部裡。在接受審判前的八個月我都在那裡度過,然後被依非法越境一年、買賣貨幣一年、走私一年的罪名,在法庭被宣告三年有期徒刑。直到大赦令頒布之前,自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年七月六日為止,我在咸鏡北道會寧的全巨里第十二教化所度過了八個月。
第一次被拘留時,大約是晚上九點左右,戒護員送來我的晚餐,是難以下嚥的玉米糠飯。即使那是剛用完餐的時間,其他囚犯卻爭先恐後地對我說如果不吃就拿給他們吃。一看,大家都彷彿只剩下一副骨頭,力氣只夠在監獄地板爬行。看著他們我真的吃不下飯,於是我把飯給了一個看起來最虛弱的人。
裡頭大約七、八成的犯人都是因非法越境罪入獄,其他的兩、三成則是經濟犯或殺人犯。牢房總共有十個,每間可以收容十到二十名犯人。
四月八日下午,戒護員傳喚我的名字。我曾聽說,十七歲要出獄的可能性還很高,因此抱著一絲的期待起身。但是,事情卻不如我的預期,他遞給我一把剪刀,要我剪頭髮。剪頭髮其實有特別的原因:過去監獄裡經常充斥著頭蝨、頭蝨卵和跳蚤這些小東西,有時它們給囚犯帶來的痛苦,比戒護員的教化還要大上許多倍。
在監獄裡基本上不容許有「動作」。囚犯必須坐好,並將雙手放在膝蓋上乖乖地待著。若因為抓了身上那些恣意橫行的跳蚤或頭蝨,身體動了一下,就必須被戒護員處罰一整天,甚至還要挨棍子。那時我才知道,不是只有見血才叫做殘忍的拷問。一整天乖乖地坐著不動,還得受害蟲折磨的痛苦,沒經歷過的人根本插不上嘴。人們因此變得越來越虛弱,不少人都因為受不了肉體和心靈的雙重痛苦而想尋死。
為了擺脫害蟲折磨,人人都想剪頭髮。只不過,削髮也成了一道證據,告訴世人「我現在是囚犯,被剝奪人權了」。我覺得眼前一片黯淡又難受。真的沒辦法避開這條路了嗎?難道,我就得去接受審判,然後去那個被詛咒的人間煉獄了嗎?削髮的人被認為是有罪、必須接受審判的人,大家戲稱他們是即將前往教化所的「桌球」。監獄裡的規定非常嚴苛,沒有任何一件事是自由的:早上六點起床,七點結束用餐後就開始一天的教化行程。其中最辛苦的,莫過於跳蚤和頭蝨的教化帶給肉體的百般苦痛。大約晚間七點結束用餐後,九點半左右就寢,頭絕對不能躺在床鋪上面;若沒有確實整理乾淨也不能睡覺。每當此時我就會想起家裡的地炕,至少還能溫暖、舒服地躺著睡覺。有幾個夜晚,我也在黑暗裡獨自哭泣,以前從來沒有一次那麼迫切地思念過父母親。每當我難受又痛苦時,只要一想到父母,悲傷的感覺就會越發膨脹。有時,還真想一頭撞上牆角或鐵窗一死了得。這個痛苦彷彿看不見終點。
只要在監獄裡稍微做錯一點事,或者讓戒護員稍不滿意,囚犯就會馬上受罰,處罰的重點在肉體的痛苦。戒護員會不出聲音地貼在牆上,注意誰做了他們覺得刺眼的行動,只要被他們盯上,馬上就會被叫起來教化。他們讓囚犯手往鐵欄杆外伸,然後拿來槍架或是一種五乘五格的木塊,不分青紅皂白地打下去,囚犯的手會變成黑青色腫起來,然後流血。因此,戒護員和被收監的囚犯之間總是瀰漫一股緊繃的氛圍。
那時,在我們監獄裡有一名茂山人,經常遭到戒護員毆打和欺負。戒護員每天都可以挑出小缺失揍他、懲罰他。據說他原先性格就高傲又不懂得屈服,經常和戒護員槓上。戒護員越是不給他飯吃、越是欺負他,他就更加頑強地反抗。他用頭拚命撞鐵欄杆,最後一片血肉模糊地昏了過去。
我也曾經做了幾次遭禁止的行為然後被戒護員發現。有一次,我用打火機的鐵片做成刀子,結果被裡頭最壞的戒護員抓到。他將我的左手臂抓出鐵欄杆外,用我做的刀硬是從我的左手臂上直直劃了下去,纖細的手腕裡流出好多血。又有一次我做了銅針,正當我做到第十二根針時,被戒護員發現了。戒護員用那些針亂刺我的手,針尖穿過我的手背,從手掌心出來。他一直刺著,直到心滿意足後,才又去了別間牢房。雖然我很想抗議,但最終還是忍了下來。每當視線移到那雙被針任意戳爛的手,就不禁想著為什麼這雙手會被戳得泛黑、發青?為什麼我得受這種詛咒?實在好冤枉!第一次見到她,是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左右,她在我看守的玉米田裡偷了玉米。那個女人流著淚說她的孩子們已經餓了好幾天,而她自己也已經餓了兩天了。我就這樣放走了那個女人,但是她又再次回來找我。女人哭訴她那當國境守衛隊的丈夫去世後,她就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生活。她向我提議,若我沒有下榻的地方,可以在她家過夜。餓得精疲力盡的女人和孩子讓我感到十分不忍,那個女人以在她家睡覺作為交換條件,提出兩個要求:一是我得幫忙找來糧食,另一個則是幫忙砍柴。我稱呼三十多歲、接近四十歲的她為姐姐。
當天晚上,我開始在農場的玉米田裡偷竊。七歲女孩和五歲男孩因長期飢餓變得消瘦,但自從我給兩個孩子食物後,他們的臉上開始有了血色。對我而言,偷農場作物是維持生命的最後一種手段。現在,人們已不再像以前一樣,認為餓死的人很可憐。現今世態,餓死的人反而會被認為是傻瓜,沒人會給予同情。就算偷了糧食,人們也不再認為那是偷竊,我也同樣沒有選擇的餘地。也在那時候,我才明白在飢餓這個人類最原始的本能面前談論道德或倫理,甚至是犯罪行為,都沒有任何意義。
不知不覺秋天過去,初冬已經慢慢到來。天氣越來越冷,樹葉都已飄落,只剩下那枯瘦的枝幹。我每天辛苦在農場裡偷來的數百公斤玉米,都用來幫忙她還債。雖然辛苦得來的糧食就這樣消失著實令我心痛,但我是真心想幫助她,因此盡量去克制那種感受。我不希望女人和她的孩子們在她遇見下一任丈夫前必須一直挨餓,也不希望她被債務纏身。但是,就在不久之後,那不期待任何回報的真心卻被無情地踐踏。
在初冬的某一天,我跟著她到了中國。那裡的朝鮮族會給我們一些舊物,附近也有許多被丟棄的衣服或鞋子等,只要把那些東西帶回去賣,可以換得錢或是糧食。之後,她和一名三十出頭的國境守衛隊軍官交往。接著有一天,那個軍官叫我去賺錢,一天若沒賺到一定的錢就別回家──要我滾出去的意思。過去是我盡全力為餓壞的女人和孩子們找來糧食,又幫他們砍柴,現在居然要我出去?
離開女人家的那天,大雪紛飛。我沒有方向,只是一直走著。我一無所有,身邊僅剩的只有一樣,那就是「希望」。
第一次被拘留時,大約是晚上九點左右,戒護員送來我的晚餐,是難以下嚥的玉米糠飯。即使那是剛用完餐的時間,其他囚犯卻爭先恐後地對我說如果不吃就拿給他們吃。一看,大家都彷彿只剩下一副骨頭,力氣只夠在監獄地板爬行。看著他們我真的吃不下飯,於是我把飯給了一個看起來最虛弱的人。
裡頭大約七、八成的犯人都是因非法越境罪入獄,其他的兩、三成則是經濟犯或殺人犯。牢房總共有十個,每間可以收容十到二十名犯人。
四月八日下午,戒護員傳喚我的名字。我曾聽說,十七歲要出獄的可能性還很高,因此抱著一絲的期待起身。但是,事情卻不如我的預期,他遞給我一把剪刀,要我剪頭髮。剪頭髮其實有特別的原因:過去監獄裡經常充斥著頭蝨、頭蝨卵和跳蚤這些小東西,有時它們給囚犯帶來的痛苦,比戒護員的教化還要大上許多倍。
在監獄裡基本上不容許有「動作」。囚犯必須坐好,並將雙手放在膝蓋上乖乖地待著。若因為抓了身上那些恣意橫行的跳蚤或頭蝨,身體動了一下,就必須被戒護員處罰一整天,甚至還要挨棍子。那時我才知道,不是只有見血才叫做殘忍的拷問。一整天乖乖地坐著不動,還得受害蟲折磨的痛苦,沒經歷過的人根本插不上嘴。人們因此變得越來越虛弱,不少人都因為受不了肉體和心靈的雙重痛苦而想尋死。
為了擺脫害蟲折磨,人人都想剪頭髮。只不過,削髮也成了一道證據,告訴世人「我現在是囚犯,被剝奪人權了」。我覺得眼前一片黯淡又難受。真的沒辦法避開這條路了嗎?難道,我就得去接受審判,然後去那個被詛咒的人間煉獄了嗎?削髮的人被認為是有罪、必須接受審判的人,大家戲稱他們是即將前往教化所的「桌球」。監獄裡的規定非常嚴苛,沒有任何一件事是自由的:早上六點起床,七點結束用餐後就開始一天的教化行程。其中最辛苦的,莫過於跳蚤和頭蝨的教化帶給肉體的百般苦痛。大約晚間七點結束用餐後,九點半左右就寢,頭絕對不能躺在床鋪上面;若沒有確實整理乾淨也不能睡覺。每當此時我就會想起家裡的地炕,至少還能溫暖、舒服地躺著睡覺。有幾個夜晚,我也在黑暗裡獨自哭泣,以前從來沒有一次那麼迫切地思念過父母親。每當我難受又痛苦時,只要一想到父母,悲傷的感覺就會越發膨脹。有時,還真想一頭撞上牆角或鐵窗一死了得。這個痛苦彷彿看不見終點。
只要在監獄裡稍微做錯一點事,或者讓戒護員稍不滿意,囚犯就會馬上受罰,處罰的重點在肉體的痛苦。戒護員會不出聲音地貼在牆上,注意誰做了他們覺得刺眼的行動,只要被他們盯上,馬上就會被叫起來教化。他們讓囚犯手往鐵欄杆外伸,然後拿來槍架或是一種五乘五格的木塊,不分青紅皂白地打下去,囚犯的手會變成黑青色腫起來,然後流血。因此,戒護員和被收監的囚犯之間總是瀰漫一股緊繃的氛圍。
那時,在我們監獄裡有一名茂山人,經常遭到戒護員毆打和欺負。戒護員每天都可以挑出小缺失揍他、懲罰他。據說他原先性格就高傲又不懂得屈服,經常和戒護員槓上。戒護員越是不給他飯吃、越是欺負他,他就更加頑強地反抗。他用頭拚命撞鐵欄杆,最後一片血肉模糊地昏了過去。
我也曾經做了幾次遭禁止的行為然後被戒護員發現。有一次,我用打火機的鐵片做成刀子,結果被裡頭最壞的戒護員抓到。他將我的左手臂抓出鐵欄杆外,用我做的刀硬是從我的左手臂上直直劃了下去,纖細的手腕裡流出好多血。又有一次我做了銅針,正當我做到第十二根針時,被戒護員發現了。戒護員用那些針亂刺我的手,針尖穿過我的手背,從手掌心出來。他一直刺著,直到心滿意足後,才又去了別間牢房。雖然我很想抗議,但最終還是忍了下來。每當視線移到那雙被針任意戳爛的手,就不禁想著為什麼這雙手會被戳得泛黑、發青?為什麼我得受這種詛咒?實在好冤枉!第一次見到她,是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左右,她在我看守的玉米田裡偷了玉米。那個女人流著淚說她的孩子們已經餓了好幾天,而她自己也已經餓了兩天了。我就這樣放走了那個女人,但是她又再次回來找我。女人哭訴她那當國境守衛隊的丈夫去世後,她就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生活。她向我提議,若我沒有下榻的地方,可以在她家過夜。餓得精疲力盡的女人和孩子讓我感到十分不忍,那個女人以在她家睡覺作為交換條件,提出兩個要求:一是我得幫忙找來糧食,另一個則是幫忙砍柴。我稱呼三十多歲、接近四十歲的她為姐姐。
當天晚上,我開始在農場的玉米田裡偷竊。七歲女孩和五歲男孩因長期飢餓變得消瘦,但自從我給兩個孩子食物後,他們的臉上開始有了血色。對我而言,偷農場作物是維持生命的最後一種手段。現在,人們已不再像以前一樣,認為餓死的人很可憐。現今世態,餓死的人反而會被認為是傻瓜,沒人會給予同情。就算偷了糧食,人們也不再認為那是偷竊,我也同樣沒有選擇的餘地。也在那時候,我才明白在飢餓這個人類最原始的本能面前談論道德或倫理,甚至是犯罪行為,都沒有任何意義。
不知不覺秋天過去,初冬已經慢慢到來。天氣越來越冷,樹葉都已飄落,只剩下那枯瘦的枝幹。我每天辛苦在農場裡偷來的數百公斤玉米,都用來幫忙她還債。雖然辛苦得來的糧食就這樣消失著實令我心痛,但我是真心想幫助她,因此盡量去克制那種感受。我不希望女人和她的孩子們在她遇見下一任丈夫前必須一直挨餓,也不希望她被債務纏身。但是,就在不久之後,那不期待任何回報的真心卻被無情地踐踏。
在初冬的某一天,我跟著她到了中國。那裡的朝鮮族會給我們一些舊物,附近也有許多被丟棄的衣服或鞋子等,只要把那些東西帶回去賣,可以換得錢或是糧食。之後,她和一名三十出頭的國境守衛隊軍官交往。接著有一天,那個軍官叫我去賺錢,一天若沒賺到一定的錢就別回家──要我滾出去的意思。過去是我盡全力為餓壞的女人和孩子們找來糧食,又幫他們砍柴,現在居然要我出去?
離開女人家的那天,大雪紛飛。我沒有方向,只是一直走著。我一無所有,身邊僅剩的只有一樣,那就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