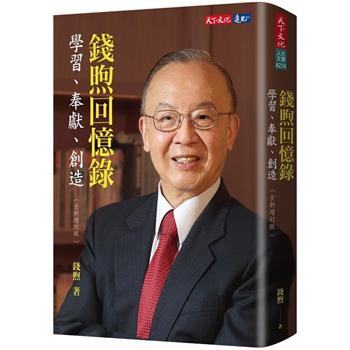受長輩的薰陶
我在哥大讀博士的時候常去胡婆婆家,和胡適校長(胡公公)常有機會見面。我和匡政結婚後生美儀之前,在他們紐約市東八十一街家裡住了一年。胡公公是中國近代最傑出的哲學家和教育家,學問淵廣,博古通今。他非常平易近人,喜歡提攜後進,我從他那裡學到許多為人處事的原則。他教我很多研究的奧祕,例如選擇題目、尋找資料、綜結知識、創新構思以及如何善用時間、追求卓越、流暢寫作和積極完成等。
在和他的談話中,我領悟到他很多名言的真諦。例如「為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和「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等。胡公公不但教我如何做學問,也教我如何為人處事,特別是如何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人交往。我們固然要保持發揚中華文化,但同時也要盡力增強英語說寫表達的能力,要吸收學習西方習俗理念,要能互相了解、增進友誼、共求世界大同。這些教導對我後來能在各項學會組織參與主流社會極有幫助。
胡婆婆雖然不會說英文,但她知事明理,在紐約過得很好。她常去朋友家打牌,每次帶一張紙出門,上面寫著朋友家的地址,可以用來叫計程車;另外也帶一張回家的紙。雖然朋友大多會接送,但她有備無患。
事實上胡婆婆也知道紐約的公共汽車路線。有一次她教我如何搭公車去一個地方,不坐公車的胡公公聽了很著急,怕這路線不對,輕輕用英文跟我說不要聽她的。我出門後照胡婆婆指點的方向去搭公車,居然順利到達。
胡婆婆對小輩非常關照,每次都給我們做很多好吃的菜,吃不完就分給大家帶回去。有一次她給我和匡政帶一鍋蘿蔔湯,裝在一個袋子裡帶回去。我們坐在公車最後一排,把這個袋子放在腳前。沒想到一個緊急剎車,那個鍋子就從袋子裡翻出來,沿著中間走道一直滾向司機位置。我們急忙起來盡量把蘿蔔撿起,用所有的紙巾手帕拚命擦地,但味道就沒有辦法了。當我們大致清理到車前端時,正好到站。我們臉紅耳赤,含糊地說了些道歉的話就匆匆下車了。這件事我們始終不敢告訴胡婆婆。
我真是非常幸運,能夠從三位我最敬佩的長輩(父親、傅校長和胡公公)受到直接教誨,這對我一生的思想行為有極大影響。此外,我也很有幸能受到很多位其他長者大師的教導,例如袁家騮和吳健雄院士夫婦,他們是華人科學家中的神仙眷侶。袁先生在紐約長島布魯克黑文國立實驗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工作,而吳院士是哥大物理系教授,我和她見面的機會較多。她在核子物理有世界頂級的成就,被稱為「中國居里夫人」。她的實驗室做核子物理最尖端的研究,規模極大。她親自對每一位研究人員給予個別的指導,幾乎晝夜不分。她潛心研究、熱誠教導的風格,給我很大的影響。
在實驗室之外,她則像平常人一樣,做家事,和朋友學生聊天,沒有任何架子,令人覺得如沐春風。除了以身作則,給我很多榜樣之外,吳院士也給我很多直接鼓勵。每次我得到一些對她來說應該是微不足道的獎譽時,她都會親筆寫賀函給我,這對我來說比獎譽本身更有意義,更有價值。她對匡政也極為愛護,一九八七年她在義大利帕多瓦(Padua)大學榮獲Elena Lucrezia Cornaro Piscopia獎章,紀念全義大利第一位女性獲得博士學位三百週年,那是一個極高的榮譽。因為匡政是一位醫師,吳院士回到紐約後便把那可貴的獎章贈送給她,讚揚鼓勵匡政熱忱的醫學服務,使我們萬分感動。
我在紐約以及台灣有幸跟很多父執長輩學習做人做事,包括梅貽琦校長、葉公超大使,和後文提到的吳大猷院長和李國鼎先生及大舅父張茲闓;他們給我很多啟發和指示。我在小學讀書時,曾經寫過一篇題目為「我最敬佩的人」的作文,我選擇了王雲五先生。他從小沒有進學校,可是努力自修讀書求學,寫了很多好文章,並且發明了「四角號碼」。後來我就讀台灣大學醫學院,他的幼子王學善是我最熟的同班同學,還是乒乓球雙打的夥伴,因此常常有機會和王雲五先生見面,才知道他每天清晨不到四點鐘就起床,到我們起床的時候,他已經寫了好幾千字。成功不是偶然的,這對我有很大的啟發。
前面說過,王世濬院士是父親的小學同學,又是我在哥大的老師,教給我很多生理學的學理知識和研究技術。王院士在神經生理學和藥理學領域是國際領先的學者,造就很多傑出的神經科學家,蔡作雍院士是他的博士學生,方懷時院士、彭明聰院士都在他研究室從事過合作研究。王夫人郭煥煒為人處事謙和溫厚,是紐約康乃爾大學醫學院護理教授,中華醫藥促進基金會(ABMAC)以她為名建立了一個基金,資助台灣護理人員赴美參加進階訓練或修習學位。他們的大女兒菲麗(Phyllis Wise)繼承父業,是一位傑出神經科學家,曾任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校長。王夫人建立了林王獎學金,紀念王院士和他的老師林可勝院士,這獎學金的目的是獎勵台灣傑出的神經、生理及藥理青年科學家出國深造。二○一五年四月,菲麗和我應李小媛之邀,在台北參加林王學術基金會首屆研討會。
我在哥大讀博士的時候常去胡婆婆家,和胡適校長(胡公公)常有機會見面。我和匡政結婚後生美儀之前,在他們紐約市東八十一街家裡住了一年。胡公公是中國近代最傑出的哲學家和教育家,學問淵廣,博古通今。他非常平易近人,喜歡提攜後進,我從他那裡學到許多為人處事的原則。他教我很多研究的奧祕,例如選擇題目、尋找資料、綜結知識、創新構思以及如何善用時間、追求卓越、流暢寫作和積極完成等。
在和他的談話中,我領悟到他很多名言的真諦。例如「為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和「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等。胡公公不但教我如何做學問,也教我如何為人處事,特別是如何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人交往。我們固然要保持發揚中華文化,但同時也要盡力增強英語說寫表達的能力,要吸收學習西方習俗理念,要能互相了解、增進友誼、共求世界大同。這些教導對我後來能在各項學會組織參與主流社會極有幫助。
胡婆婆雖然不會說英文,但她知事明理,在紐約過得很好。她常去朋友家打牌,每次帶一張紙出門,上面寫著朋友家的地址,可以用來叫計程車;另外也帶一張回家的紙。雖然朋友大多會接送,但她有備無患。
事實上胡婆婆也知道紐約的公共汽車路線。有一次她教我如何搭公車去一個地方,不坐公車的胡公公聽了很著急,怕這路線不對,輕輕用英文跟我說不要聽她的。我出門後照胡婆婆指點的方向去搭公車,居然順利到達。
胡婆婆對小輩非常關照,每次都給我們做很多好吃的菜,吃不完就分給大家帶回去。有一次她給我和匡政帶一鍋蘿蔔湯,裝在一個袋子裡帶回去。我們坐在公車最後一排,把這個袋子放在腳前。沒想到一個緊急剎車,那個鍋子就從袋子裡翻出來,沿著中間走道一直滾向司機位置。我們急忙起來盡量把蘿蔔撿起,用所有的紙巾手帕拚命擦地,但味道就沒有辦法了。當我們大致清理到車前端時,正好到站。我們臉紅耳赤,含糊地說了些道歉的話就匆匆下車了。這件事我們始終不敢告訴胡婆婆。
我真是非常幸運,能夠從三位我最敬佩的長輩(父親、傅校長和胡公公)受到直接教誨,這對我一生的思想行為有極大影響。此外,我也很有幸能受到很多位其他長者大師的教導,例如袁家騮和吳健雄院士夫婦,他們是華人科學家中的神仙眷侶。袁先生在紐約長島布魯克黑文國立實驗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工作,而吳院士是哥大物理系教授,我和她見面的機會較多。她在核子物理有世界頂級的成就,被稱為「中國居里夫人」。她的實驗室做核子物理最尖端的研究,規模極大。她親自對每一位研究人員給予個別的指導,幾乎晝夜不分。她潛心研究、熱誠教導的風格,給我很大的影響。
在實驗室之外,她則像平常人一樣,做家事,和朋友學生聊天,沒有任何架子,令人覺得如沐春風。除了以身作則,給我很多榜樣之外,吳院士也給我很多直接鼓勵。每次我得到一些對她來說應該是微不足道的獎譽時,她都會親筆寫賀函給我,這對我來說比獎譽本身更有意義,更有價值。她對匡政也極為愛護,一九八七年她在義大利帕多瓦(Padua)大學榮獲Elena Lucrezia Cornaro Piscopia獎章,紀念全義大利第一位女性獲得博士學位三百週年,那是一個極高的榮譽。因為匡政是一位醫師,吳院士回到紐約後便把那可貴的獎章贈送給她,讚揚鼓勵匡政熱忱的醫學服務,使我們萬分感動。
我在紐約以及台灣有幸跟很多父執長輩學習做人做事,包括梅貽琦校長、葉公超大使,和後文提到的吳大猷院長和李國鼎先生及大舅父張茲闓;他們給我很多啟發和指示。我在小學讀書時,曾經寫過一篇題目為「我最敬佩的人」的作文,我選擇了王雲五先生。他從小沒有進學校,可是努力自修讀書求學,寫了很多好文章,並且發明了「四角號碼」。後來我就讀台灣大學醫學院,他的幼子王學善是我最熟的同班同學,還是乒乓球雙打的夥伴,因此常常有機會和王雲五先生見面,才知道他每天清晨不到四點鐘就起床,到我們起床的時候,他已經寫了好幾千字。成功不是偶然的,這對我有很大的啟發。
前面說過,王世濬院士是父親的小學同學,又是我在哥大的老師,教給我很多生理學的學理知識和研究技術。王院士在神經生理學和藥理學領域是國際領先的學者,造就很多傑出的神經科學家,蔡作雍院士是他的博士學生,方懷時院士、彭明聰院士都在他研究室從事過合作研究。王夫人郭煥煒為人處事謙和溫厚,是紐約康乃爾大學醫學院護理教授,中華醫藥促進基金會(ABMAC)以她為名建立了一個基金,資助台灣護理人員赴美參加進階訓練或修習學位。他們的大女兒菲麗(Phyllis Wise)繼承父業,是一位傑出神經科學家,曾任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校長。王夫人建立了林王獎學金,紀念王院士和他的老師林可勝院士,這獎學金的目的是獎勵台灣傑出的神經、生理及藥理青年科學家出國深造。二○一五年四月,菲麗和我應李小媛之邀,在台北參加林王學術基金會首屆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