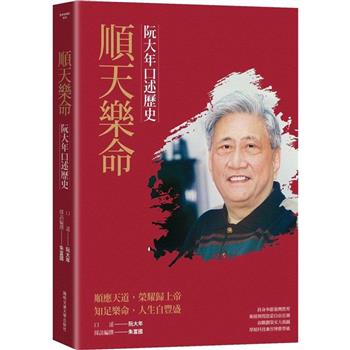節錄自〈第四章 大膽衝撞制度—從中原到教育部〉
愛護稀有動物
我在中原大學服務這麼多年,對教育當然還是很感興趣,加上政務次長不需要公務人員資格,我很願意去幫他。李國鼎先生當時人在國外,我就用電話和他聯繫,他說這是個難得的機會,他會尊重我的決定。巧合的是,科技顧問組前任執行秘書、同時也是交大校友的吳伯楨身體復原了,正好可以回來接替我的工作,不會有青黃不接的問題,我最後就決定到教育部服務,6 月11 日宣誓就任。
教育部有三位次長,兩位常務次長負責學術和事務性的工作,一位政務次長負責政策相關事務,一般的公文我會先批掉,需要部長批示的公文我會先寫建議再上呈。他外面事情很多,部裡事情盡量都讓我管,算是放手讓我發揮,對我很信任。
因為柯先生紀小姐電視節目的關係,我當時也算政府裡面的明星,除了當政務次長,還擔任教育部發言人說明政策。李煥部長不大習慣上電視,大家覺得他有點神秘,有些人還誤以為我是部長。我一開始對記者也沒有防備,有次跟記者閒聊,我說我在上海小學五年級就學開始英語,我覺得很好,可是我也沒有講要實施;結果記者報導說教育部準備要開放小學教英語,最後李煥部長還自己出來澄清。
後來李煥部長私底下跟我說,雖然這是很好的事,可是我們現在還沒能力實施,政務次長講話要小心慎言,對記者也不要講太多個人意見,談教育部意見就好。但是他也沒有不讓我做發言人,基本上他同意我的觀念,有時候也需要透過我放個氣球,測試一下社會輿論風向。
例如以前有些人沒服兵役就偷偷出國留學,畢業後又不敢回來,怕被抓到要補役期,有一陣子社會就在討論重新開放高中畢業生出國留學。我認為如果高中畢業生已經先盡完服兵役義務,政府沒有理由禁止他們留學,當時卻一定要大學畢業,還要通過留學考,真的管太多了。而且有些人會用當廚師或護士的名義申請出國工作,實際上是去讀書,高中畢業生服完兵役想去留學卻不可以,這個真的講不通,出國唸書也沒什麼不好啊!
我是很講求理性思考的人,很多政府禁止的理由,仔細想想其實沒道理,後來也確實開放了,只是過猶不及,最後連國中生都可以留學。我大女兒後來到加拿大生活,她發現很多高中生不上學、整天都在外面混,像這些孩子還不夠成熟又沒有家長管,這樣真的不太好,所以我並不贊成「小留學生」。
總之,不管小學上英語課或者高中生出國留學,這些政策後來都做到了,只是我那時候講得太早了,雖然講的是個人意見也是實話,可惜先知通常都不受歡迎。有些記者說要好好保護我這個「稀有動物」,其實他們才不會保護我!
不再為頭髮哭泣
1971 年回國時,我的大女兒文薏已經6 歲,在中原服務期間二女兒文芯、三女兒文薆和小兒子慕光陸續出生。我常常覺得有點對不起文薏,因為臺灣就學環境跟美國很不一樣。比方在美國托兒所畫畫,畫什麼老師都說好棒,畫紅色樹葉也可以;但是在臺灣,樹幹一定要棕色,樹葉一定要綠色。還有一次小學考試,題目是用「橋、這座、天上、彩虹、像」組成一個句子,我女兒寫「這座橋像天上的彩虹」,雖然不是標準答案,老師也不應該說她寫錯了,後來她一直不大習慣臺灣的教學方式。
文薏的數學不算好,有一次我就說她是美國人,所以數學不好,可是為什麼這麼簡單的題目都不會?弄到她很難過地說:「對,我就是笨、我就是笨!」有陣子她也不太想上學。我真的要跟她說聲對不起,不應該傷她的心,就是因為從小被我罵她笨,才會不喜歡在臺灣讀書。
我到教育部的時候,文薏已經讀高二準備要考大學,隔年大學聯考她意外落了榜。有人問我女兒考上哪所大學?我回答沒考上,一開始他們還以為我亂講,後來居然還說:「證明大學聯考真的很公平!」聯考當然公平啊,可是很多人認為做官的都有問題,就算聯考也有內幕。我是真的清清白白,唯一我比別人多知道的,就是作文的題目,因為政務次長要先看過題目,同意之後再從兩個題目中挑選一個,但是我也不可能告訴我的女兒。
沒考上大學,原本文薏也沒那麼在乎,她說:「考不上無所謂,可是也不必全國都知道!」被媒體一渲染後,她連夜間部也不考了,就去唸了一年基督書院,後來出國唸服裝設計。聯考這件事,文薏也算是「被害人」,她深受其害的還有國、高中男生要剃光頭,女生也要剪成「清湯掛麵頭」的「髮禁」。
1986 年底有一次教育部行政會議,我提出臨時動議,我說美國的青少年每天早上最在乎的事情就是吹頭髮,想要展現自己的特點,美國人還有不同的髮色,臺灣人都是黑頭髮,又要剪成「清湯掛麵」或者剃光頭,女生和男生心情都很不好;而且我四個小孩,前兩個女兒到國中要剪頭髮的時候,都會大哭一場,希望第三個女兒不要再哭了。
部長原本覺得「有那麼嚴重嗎?」詢問其他同事,大家都認為解除髮禁很困難,來自教官和學校的阻力會很大。最後部長裁示,既然我有興趣,就交給我去推動。會後我就跟記者講,教育部要推動解除髮禁,我認為「教育的重點在於頭皮以下,不是頭皮以上!」記者也很同意我的看法。後來部長也有點緊張,我怎麼這麼快就宣布了?果然很多保守的人群起而攻之,一大堆人打電話到教育部罵人。
記得有位老太太打電話給我:「阮次長,我很喜歡你的柯先生紀小姐節目,可是這件事情你做錯了,以後國中生、高中生留個長髮,那跟酒家女有什麼分別呢?」我說:「謝謝提供建議,可是如果照您的看法,是不是要提倡現在開始纏小腳?這樣就更走不到酒吧去了!」她大概覺得我不可理喻,也沒話講,就掛掉電話了。
1987 年 1 月教育部跟省市教育廳局開會以後,決定不再用行政命令管制學生髮型,把決定權交還給學校。「髮禁」解除已經超過三十五年了,雖然現在有些私立學校希望繼續維持傳統,對於學生頭髮還是有些規定,但起碼不像當年那麼嚴格了。也因為我推動很多改革,很多人還以為我的後臺很硬:當時政壇流行一種說法,把陳履安、錢復、沈君山和連戰稱為「四公子」,很多人搞不清楚,還說不要得罪阮大年,因為我是四公子之一。我也懶得解釋,真的是哭笑不得。
愛護稀有動物
我在中原大學服務這麼多年,對教育當然還是很感興趣,加上政務次長不需要公務人員資格,我很願意去幫他。李國鼎先生當時人在國外,我就用電話和他聯繫,他說這是個難得的機會,他會尊重我的決定。巧合的是,科技顧問組前任執行秘書、同時也是交大校友的吳伯楨身體復原了,正好可以回來接替我的工作,不會有青黃不接的問題,我最後就決定到教育部服務,6 月11 日宣誓就任。
教育部有三位次長,兩位常務次長負責學術和事務性的工作,一位政務次長負責政策相關事務,一般的公文我會先批掉,需要部長批示的公文我會先寫建議再上呈。他外面事情很多,部裡事情盡量都讓我管,算是放手讓我發揮,對我很信任。
因為柯先生紀小姐電視節目的關係,我當時也算政府裡面的明星,除了當政務次長,還擔任教育部發言人說明政策。李煥部長不大習慣上電視,大家覺得他有點神秘,有些人還誤以為我是部長。我一開始對記者也沒有防備,有次跟記者閒聊,我說我在上海小學五年級就學開始英語,我覺得很好,可是我也沒有講要實施;結果記者報導說教育部準備要開放小學教英語,最後李煥部長還自己出來澄清。
後來李煥部長私底下跟我說,雖然這是很好的事,可是我們現在還沒能力實施,政務次長講話要小心慎言,對記者也不要講太多個人意見,談教育部意見就好。但是他也沒有不讓我做發言人,基本上他同意我的觀念,有時候也需要透過我放個氣球,測試一下社會輿論風向。
例如以前有些人沒服兵役就偷偷出國留學,畢業後又不敢回來,怕被抓到要補役期,有一陣子社會就在討論重新開放高中畢業生出國留學。我認為如果高中畢業生已經先盡完服兵役義務,政府沒有理由禁止他們留學,當時卻一定要大學畢業,還要通過留學考,真的管太多了。而且有些人會用當廚師或護士的名義申請出國工作,實際上是去讀書,高中畢業生服完兵役想去留學卻不可以,這個真的講不通,出國唸書也沒什麼不好啊!
我是很講求理性思考的人,很多政府禁止的理由,仔細想想其實沒道理,後來也確實開放了,只是過猶不及,最後連國中生都可以留學。我大女兒後來到加拿大生活,她發現很多高中生不上學、整天都在外面混,像這些孩子還不夠成熟又沒有家長管,這樣真的不太好,所以我並不贊成「小留學生」。
總之,不管小學上英語課或者高中生出國留學,這些政策後來都做到了,只是我那時候講得太早了,雖然講的是個人意見也是實話,可惜先知通常都不受歡迎。有些記者說要好好保護我這個「稀有動物」,其實他們才不會保護我!
不再為頭髮哭泣
1971 年回國時,我的大女兒文薏已經6 歲,在中原服務期間二女兒文芯、三女兒文薆和小兒子慕光陸續出生。我常常覺得有點對不起文薏,因為臺灣就學環境跟美國很不一樣。比方在美國托兒所畫畫,畫什麼老師都說好棒,畫紅色樹葉也可以;但是在臺灣,樹幹一定要棕色,樹葉一定要綠色。還有一次小學考試,題目是用「橋、這座、天上、彩虹、像」組成一個句子,我女兒寫「這座橋像天上的彩虹」,雖然不是標準答案,老師也不應該說她寫錯了,後來她一直不大習慣臺灣的教學方式。
文薏的數學不算好,有一次我就說她是美國人,所以數學不好,可是為什麼這麼簡單的題目都不會?弄到她很難過地說:「對,我就是笨、我就是笨!」有陣子她也不太想上學。我真的要跟她說聲對不起,不應該傷她的心,就是因為從小被我罵她笨,才會不喜歡在臺灣讀書。
我到教育部的時候,文薏已經讀高二準備要考大學,隔年大學聯考她意外落了榜。有人問我女兒考上哪所大學?我回答沒考上,一開始他們還以為我亂講,後來居然還說:「證明大學聯考真的很公平!」聯考當然公平啊,可是很多人認為做官的都有問題,就算聯考也有內幕。我是真的清清白白,唯一我比別人多知道的,就是作文的題目,因為政務次長要先看過題目,同意之後再從兩個題目中挑選一個,但是我也不可能告訴我的女兒。
沒考上大學,原本文薏也沒那麼在乎,她說:「考不上無所謂,可是也不必全國都知道!」被媒體一渲染後,她連夜間部也不考了,就去唸了一年基督書院,後來出國唸服裝設計。聯考這件事,文薏也算是「被害人」,她深受其害的還有國、高中男生要剃光頭,女生也要剪成「清湯掛麵頭」的「髮禁」。
1986 年底有一次教育部行政會議,我提出臨時動議,我說美國的青少年每天早上最在乎的事情就是吹頭髮,想要展現自己的特點,美國人還有不同的髮色,臺灣人都是黑頭髮,又要剪成「清湯掛麵」或者剃光頭,女生和男生心情都很不好;而且我四個小孩,前兩個女兒到國中要剪頭髮的時候,都會大哭一場,希望第三個女兒不要再哭了。
部長原本覺得「有那麼嚴重嗎?」詢問其他同事,大家都認為解除髮禁很困難,來自教官和學校的阻力會很大。最後部長裁示,既然我有興趣,就交給我去推動。會後我就跟記者講,教育部要推動解除髮禁,我認為「教育的重點在於頭皮以下,不是頭皮以上!」記者也很同意我的看法。後來部長也有點緊張,我怎麼這麼快就宣布了?果然很多保守的人群起而攻之,一大堆人打電話到教育部罵人。
記得有位老太太打電話給我:「阮次長,我很喜歡你的柯先生紀小姐節目,可是這件事情你做錯了,以後國中生、高中生留個長髮,那跟酒家女有什麼分別呢?」我說:「謝謝提供建議,可是如果照您的看法,是不是要提倡現在開始纏小腳?這樣就更走不到酒吧去了!」她大概覺得我不可理喻,也沒話講,就掛掉電話了。
1987 年 1 月教育部跟省市教育廳局開會以後,決定不再用行政命令管制學生髮型,把決定權交還給學校。「髮禁」解除已經超過三十五年了,雖然現在有些私立學校希望繼續維持傳統,對於學生頭髮還是有些規定,但起碼不像當年那麼嚴格了。也因為我推動很多改革,很多人還以為我的後臺很硬:當時政壇流行一種說法,把陳履安、錢復、沈君山和連戰稱為「四公子」,很多人搞不清楚,還說不要得罪阮大年,因為我是四公子之一。我也懶得解釋,真的是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