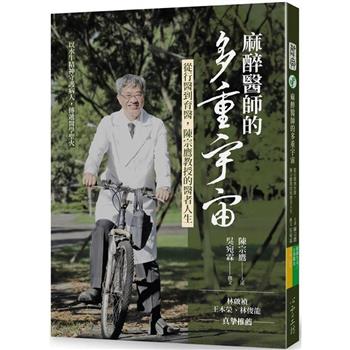☆摘文一 在田間和工廠長大的少年
小學五、六年級時,陳宗鷹常常跟著父親陳森林在田間工作,晚餐過後,則跟著爸爸到南投名間鄉的松柏嶺一座供奉「帝爺」的廟宇「受天宮」上香參拜,或者到彰化田中鎮赤水崎頂的北天宮去問事。受天宮香火鼎盛,是當地民間信仰的中心,而北天宮則是當時民間解惑問事的重要地點。陳宗鷹知道,每當父親有煩惱時,就會去請示神明。他總是看著爸爸的側臉,爸爸虔誠地對神明喃喃訴說,神桌上鋪著米糠,接著有兩人抬著神轎,乩童被神明附身之後,神轎開始晃動,並在前方的竹子上寫字,此時廟方有人出來解讀神明的旨意,為迷惘的眾生指點迷津。
一九六二年,陳宗鷹出生在彰化縣田中鎮。家中七個孩子,他剛好排在中間,是第四個小孩,上面有兩個姊姊、一個哥哥,在他之下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他每次自我介紹,覺得最符合自己的形容就是「我有兄弟姊妹」。
他的爸爸陳森林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丁,上有三個姊姊。陳森林七歲的時候,父親就過世了,家中的孩子全靠母親一個人撫養長大。陳森林國小畢業後,就去學裁縫、做學徒,從小就必須自力更生。陳森林學成後,自己經營布莊,和妻子陳巫玉蘭在彰化縣田中市場裡賣布,並在攤位上層隔了一個小房間,全家就住在裡面。
布莊生意還不錯,有了一點積蓄,孩子們陸續出生,陳森林希望能給家人更好的生活空間,在同樣位於斗中路、距離田中市場大約一公里的地方買下一塊土地蓋房子。蓋房子必須花一大筆錢,妻子陳巫玉蘭非常反對,認為布莊在市場才有人潮有生意,但陳森林相當堅持,想要有自己的房子。誰知布莊搬至新房子之後,因為距離市場遠,生意一落千丈,再加上建屋時建築材料價格漲得厲害,所有積蓄都花光了,甚至還負債,經濟頓時陷入困境。除了節流,陳森林想要開源,當時聽說鳳梨和薑的價格很好,想起自己在南投縣名間鄉弓鞋村還有兩分地,若再承租陳氏祖先的兩甲地來耕作,應該可以增加收入。
鳳梨、金紙和襪子:童年打工記憶
不過,務農也沒有想像的簡單。在資訊不發達的年代,常常聽人說種某種作物價格很好,便趕緊跟風,但經過口耳相傳後,其實價格都已從高峰往下走,最後往往慘賠收場。原本因為蓋新房和搬布莊就已經負債,再加上務農的慘賠、家中食指浩繁,生活越發拮据辛苦。陳森林很希望可以改善經濟狀況,神明指示祖墳風水不好需要重修,他就重修;聽說種什麼好,他就種什麼,只希望能找到讓妻小好好生活的轉機。這時候孩子都還小,長子陳宗位從田中國小第一名畢業後,就讀田中國中,每次考試都霸占著第一名的位置。看長子書讀得好,期待他認真讀好書,不用再幫忙家務,盼望長子出人頭地,是陳森林最大的希望。大女兒(令珠)國中畢業後,馬上投入工作,到公路局客運金馬號擔任車掌小姐,二女兒(姚色)國中畢業為了分攤家計,在家門口擺攤賣檳榔、山上種植的果物,也賣寶島、長壽菸賺一些價差,或批發一些抽抽樂給小學生玩。排行老四的二兒子陳宗鷹當時還年幼,就讀田中國小高年級,適逢國內棒球風氣興盛,他喜歡打棒球,因此獲選進入彰化縣棒球隊,集訓期間有棒球隊供應吃住,也減輕家中一點負擔。但在練球和讀書的空檔,陳宗鷹(十二歲)常常和兩個妹妹(姚里十歲及姚光八歲)也在晚上及假日到住家對面製作金紙的工廠打工賺錢。
在過去,臺灣民眾大多信奉民間信仰,幾乎家家戶戶都會燒香祭拜以及燒金紙奉納神明與祖先。金紙上面需要蓋一個四四方方的紅色印章,還要在正中間貼上銀色或金色的錫箔紙。金紙從工廠一疊一疊生產出來後,陳家三兄妹就排隊去做手工,負責嵌金和蓋章。在做這些步驟前,為了避免金紙散落,必須先在每一疊金紙的一角用電鑽鑽個洞,穿線綁起來。由於電鑽很重,一個沒拿好,可能就讓金紙歪掉、鑽破,甚至手會受傷,於是就由五年級的陳宗鷹負責這個工作,鑽完洞、固定好,再交給小妹姚光一張一張蓋印,她的兩隻小手常常沾到染劑,從紅變黑。蓋完印,他再跟大妹接手貼細部的錫箔。因為很多人搶著打工,金紙紙質又參差不齊,紙質比較好、比較厚的容易做,比較薄的紙容易黏在一起,工作效率較差,所以陳宗鷹總是帶著妹妹先去工廠排隊,搶比較好的紙多做一些。做好十二疊就算一捆,一捆可以拿到五毛的工資,每個月累積的工資一次發放。把賺的錢拿回家給媽媽之前,兄妹三人會先彎去附近雜貨店去買糖廠出產的健素糖,五毛錢可以買到一大把。他們最喜歡沒有加糖衣的健素糖那香香的味道,含在嘴裡吃,愈嚼愈香,是三人童年裡最幸福的味道。
陳宗鷹大一些之後,就開始當爸爸的左右手,假日跟著父親到山上的農園工作。他記得有一陣子家裡種鳳梨,有一甲地都是鳳梨田,他在田間穿梭,兩隻腳被鳳梨刺得傷痕累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午在田邊的小工寮休息,跟父親一起煮泡麵吃。傍晚,爸爸挑著扁擔,將收成的鳳梨、香蕉或荔枝運下山,再走一段路到公車站,兩人搭最後一班公車回到田中,將農產交給二姊放在攤子賣。辛苦種鳳梨的記憶太深刻,深刻到讓陳宗鷹在外求學時幾乎不買鳳梨。他並不是不愛吃,而是會想起以前父親挑著重重的鳳梨下山,收購鳳梨的商人卻只給非常低廉的價格,因此每次看到市場上鳳梨的標價,他都覺得實在昂貴得買不下手!
就在全家人務農、布莊、擺攤和家庭代工的各種努力下,讓家中孩子可以繼續讀書。後來父母親決定把房子賣掉,搬往更遠的區域居住,用賣掉房子的錢償還債務,家中經濟才稍稍改善。
☆摘文二 第一次為連體嬰麻醉
二〇一〇年,陳宗鷹接到菲律賓分會轉介來一對臀部相連的連體嬰要到花蓮慈濟醫院進行分割手術的訊息。雖然很高興可以參與麻醉專業生涯中難得的學習機會和經驗,但另一方面,這也是以前從未處理過、超罕見的特殊個案,他內心嚴陣以待。
這對姊妹被慈濟志工發現時已經三個月大,臀部相連,共用一個直腸和肛門,健康狀況良好,無特殊疾病,因為名字裡都有Rose,所以被暱稱為「玫瑰姊妹」。小兒外科的彭海祁主任先啟程到菲律賓,評估姊妹倆的健康狀況。同時,陳宗鷹並請王章勉和李佳玲兩位學生,做文獻回顧與各項器材準備。
早在二〇〇三年,石明煌院長就曾率領麻醉團隊,成功幫助第一對連體嬰成功分割,所以特別提醒陳宗鷹要注意兩位小病人的用藥劑量與個人標記一定要區分清楚,才能確保手術安全。
手術房團隊既緊張又期待,隨即進行萬全的準備,就連兩臺麻醉機、兩個手術臺,擺放的位置和動線也仔細斟酌,甚至還將兩個洋娃娃臀部黏在一起操作演練。當準備分割的小姊妹抵達慈院,醫療團隊見到這麼漂亮可愛又天真無邪的孩子,更決心一定要幫助她們。手術前的各項檢查,是麻醉醫師和玫瑰姊妹的初次接觸。由於要進行MRI核磁共振造影,必須讓小嬰兒靜止才能準確攝影,因此由麻醉團隊負責麻醉。
一開始,大家手忙腳亂,當第一劑麻醉藥物從姊姊的靜脈點滴注射進去,每個人都屏氣凝神注視、並猜測到底是哪位會睡著?還是兩位都睡著?或是都不會睡著?看著姊姊逐漸睡著,妹妹還在哭鬧,陳宗鷹心中放下一塊大石頭──這表示兩姊妹的血液循環沒有大量的血液流量交叉的影響。接著,注射藥物也讓妹妹睡著,才順利完成檢查。
團隊在檢討MRI的麻醉經驗時,發現有可能會將兩姊妹的數值記錄寫相反,為了避免失誤,麻醉團隊在兩姊妹身上要用到的點滴、心電圖、血氧飽和度與呼吸管路等,每一條管線都用紅色、藍色分別標記來做區隔。
分割前腸造口與組織擴張的手術非常順利,手術結束甦醒時,陳宗鷹和麻醉團隊也更篤定兩姊妹的麻醉藥物不會互相影響,讓他們對分割時更有信心。實際分割手術時,兩姊妹需要一百八十度的翻身,團隊再次使用兩個洋娃娃做練習。為了預防手術時萬一需要輸血、尋找管路,麻醉團隊也使用超音波評估兩姊妹內頸靜脈的位置、大小,以備下次分割手術時的不時之需。
正式分割大挑戰
儘管已有前次檢查成功麻醉的經驗,但是正式分割才是真正挑戰的開始。陳宗鷹前一天與開刀房護理團隊及麻醉團隊,仔細的從頭演練並模擬各種狀況。
分割當日,早上七點便進開刀房準備,八點鐘準時為兩姊妹分別了進行麻醉誘導,每一個小細節,包括氣管內管如何黏貼、姊妹倆頭部怎麼擺、小手如何用棉捲包紮保溫與保護等等,大家戰戰兢兢的做好每一個步驟。在彭海祁主任所領導外科團隊精湛的技術下,小姊妹的身體正式分開了。緊接著,另外兩個外科團隊小心翼翼的個別進行後續修補的工作。
麻醉團隊也隨時注意各種狀況與因應。雖然,在神經外科團隊為小姊妹分割後的尾椎,進行神經修補時,因脊髓液流失,姊妹倆的血壓稍微下降,但在麻醉醫師馬上補充水分並處理升壓後,血壓隨即回復平穩。手術前後將近十個小時,時間雖長,陳宗鷹還是時刻守護在姊妹倆身旁。直到最後一次的手術麻醉,兩姊妹終於可以個別進行手術,幫姊妹做完腸造口的關閉送到恢復室時,陳宗鷹看到媽媽不知道要照顧哪一個孩子的這一幕,內心激動起來,對姊妹這一路以來的艱辛與大家的付出,非常感動。他疼惜孩子的心仍一如往昔,看到她們恢復健康,同時期待她們能平安長大,擁有各自燦爛的玫瑰人生,就是最無價滿足的回報。
☆摘文三 遇到麻醉醫師最大的惡夢
這一天清晨,開刀房如常運作,每個人依循著一套有秩序的流程,忙碌準備著。陳宗鷹這時還是臺灣南部某醫學中心的麻醉科醫師,他已經看完今天要手術的個案資料,第一臺刀是眼科手術,一位三歲的小男孩,即將被送進開刀房準備做疏通鼻淚管的手術。
鼻淚管位在眼頭靠近鼻腔處,多餘的淚水會由鼻淚管流至鼻子內排出。鼻淚管的末端有一層薄薄的瓣膜,通常嬰兒出生時,會自行打開。如果沒有打開,眼科醫師只要進行「淚管探針術」疏通,大約半個小時就可以完成。
為小男孩麻醉
對麻醉醫師而言,手術沒有大小之分,每一次都要讓病人安全接受麻醉、並舒適平安的甦醒。喜歡小孩的陳宗鷹,雖不能說在開刀房看到小孩會很開心,畢竟進入開刀房治療並不是什麼好事;但如果看到小孩,陳宗鷹頓時會覺得心情柔軟起來。曾經,他想過要當兒科醫師,成為麻醉科醫師之後,他也對自己承諾要在手術室裡守護孩子的生命。
小兒麻醉誘導最常使用吸入性的麻醉劑,他拿著面罩配合著安撫的話語,扣住小病人胖胖圓圓的臉頰,隨著麻醉監測儀器滴滴滴的聲音,小男孩沉沉的睡去。眼科醫師開始幫小病人清潔消毒,大約才過十五分鐘,手術都還沒開始,陳宗鷹發現小男孩的心跳在下降,血壓也下降,立即仔細檢查麻醉機、藥物和各種監測的生命數值狀況,一時找不出原因,但隱隱覺得不安,眼前雖然看似平靜,陳宗鷹還是請眼科醫師暫時先不要動刀。
陳宗鷹飛速打開所有腦中的資料庫,想找出原因時,小男孩竟突然發生心跳停止!醫護團隊緊急搶救,陳宗鷹趕緊打入強心劑,不斷進行心肺復甦術,一陣手忙腳亂之後,陳宗鷹覺得自己被嚇得心跳也快要停止,小男孩終於恢復了心跳。
最難防的「惡性高熱症」
陳宗鷹決定請眼科醫師取消這次的手術,先送病童到恢復室觀察。一到恢復室量體溫,發現小男孩體溫飆高,他還正在納悶,不一會兒,小男孩體溫又再升高一度。他正想釐清體溫的變化,沒想到,小男孩開始痙攣,「怎麼會這樣?」他都仔細確認過每個步驟都沒有問題,一個大膽的猜測,在陳宗鷹腦中跳出,他懷疑發生在這個小男孩身上的,正是「麻醉醫師的惡夢」──亞洲人臨床非常少見的「惡性高熱症」(MH)。臺灣大部分的醫師,都只在教科書裡讀到,幾乎沒有真正遇過惡性高熱發作的病人。
惡性高熱真正的發生原因仍不清楚,但與基因有關,比較盛行於歐美。歐美接受麻醉引發惡性高熱的發生率,是五萬至十萬分之一到五千分之一,在亞洲、臺灣的發生率更低。惡性高熱是由於肌漿鈣不受控制的升高,會讓肌肉釋放大量鈣離子,使體內二氧化碳濃度上升,病人就像用高速跑了一整天的馬拉松一樣,導致體溫過高(每五分鐘上升攝氏1至2度 ,中心體溫甚至超過44度)、酸中毒和肌肉收縮,甚至因ATP(三磷酸腺苷)耗盡,肌膜完整性受到損害,導致高血鉀症和橫紋肌溶解症。就算盡力搶救,百分之十的病人仍可能因心跳停止、腦傷、內出血,或器官衰竭而死亡;存活者也可能遺留腦部損傷、腎臟衰竭、肌肉損傷或重要器官功能不全等併發症。
惡性高熱症,也被稱為「麻醉醫師的惡夢」。惡性高熱可怕之處,在如今醫療科技進步的時代,僅僅接受一個小手術,仍可能因為一系列的反應,而導致病人突然死亡的悲劇,不僅家屬不能理解,醫師也遭受嚴重打擊。
這個小男孩的各種症狀,都像是惡性高熱症的表現,必須趕快治療,同時做肌肉切片給病理科檢驗,才能確認是否為惡性高熱。此時,困難又出現了,一是家長不願意孩子再進開刀房切一刀,再者,因為在美國發生病例較多,總共有八家醫學中心可以做切片檢查,但臺灣卻沒有一家醫學中心的病理科可以做,所以最後只能以「疑似」惡性高熱來診斷。還好當時惡性高熱症已經有解藥(Dantrolene),然而因為病例稀少,藥品保存期短、藥價昂貴,又是知名的「孤兒藥」──只有惡性高熱一種疾病會使用,幾乎很少醫院會準備。
使盡全力照顧
極為幸運的是,陳宗鷹當時服務的醫院是濁水溪以南唯一備有這種藥品的醫學中心,他向藥局拿到解藥,在恢復室即刻給予起始劑量(Loading Dose),小男孩的體溫不再升高,逐漸下降,病況馬上有了起色。之後,他將小男孩轉入小兒加護病房,持續治療,原本想委託在小兒科的學弟幫忙照顧,但學弟說他也沒遇過惡性高熱症的病人,陳宗鷹只好自己照顧,他待在小兒加護病房,整整七天照顧小病患,終於讓小男孩恢復,轉出加護病房並順利出院。
一個健康活潑的三歲小男孩,只是接受一個簡單的鼻淚管疏通手術,卻遭遇這種折磨,併發肌溶解症,差點連命都沒了。孩子的父母相當不諒解,甚至找了其他外科醫師,並跑到陳宗鷹的疼痛門診,質疑他是不是麻醉藥物用錯、或是劑量不對,才讓原本活活潑潑的孩子癱軟的躺在床上。陳宗鷹雖然耐心的解釋,是基因的問題加上吸入性麻醉藥物才誘發這樣的狀況,但在場包括其他麻醉科醫師、外科醫師,大家都只在教科書上讀過,也確實不曾有人見過這種狀況,因此沒有人可以再解釋什麼,只能期待小男孩能順利恢復健康!
除了每天盡心盡力的照顧這位小病人,陳宗鷹也到處找資料,並寫信到美國的惡性高熱學會詢問,陳宗鷹心想,「臺灣對這個疾病確實比較陌生,我乾脆自己翻譯成中文,讓更多人知道。」雖然,這件事讓他焦頭爛額,但他還是覺得應該把這件事當成案例,讓更多人知道,所以又花了時間把美國惡性高熱學會回覆的內容翻譯成中文,寫成科普文章。
小病人母親原本因為這件事,對陳宗鷹相當不諒解,看到陳宗鷹不但救回孩子,每天很認真照顧她的孩子,加上惡性高熱使用的特效藥非常昂貴,陳宗鷹為了幫家屬節省醫療開支,幫家屬向健保局申請給付,與健保局數次交涉往返,證明必須使用唯一而昂貴的「孤兒藥」才可治療,最後也獲得同意。最後出院時,小病人的母親已經不再怪罪陳宗鷹,不但不提告,反而是謝謝他一路以來的照顧。雖然,孩子出院時,只恢復了部分大肌肉功能,僅僅可以坐起來,還不能走路。不過,三個月後,陳宗鷹收到小兒科的好消息,原來他們透過在臺南鄉間開設診所的兒科醫師,得知小病人已經恢復健康,可以跑跑跳跳,讓陳宗鷹終於放下心來。
小學五、六年級時,陳宗鷹常常跟著父親陳森林在田間工作,晚餐過後,則跟著爸爸到南投名間鄉的松柏嶺一座供奉「帝爺」的廟宇「受天宮」上香參拜,或者到彰化田中鎮赤水崎頂的北天宮去問事。受天宮香火鼎盛,是當地民間信仰的中心,而北天宮則是當時民間解惑問事的重要地點。陳宗鷹知道,每當父親有煩惱時,就會去請示神明。他總是看著爸爸的側臉,爸爸虔誠地對神明喃喃訴說,神桌上鋪著米糠,接著有兩人抬著神轎,乩童被神明附身之後,神轎開始晃動,並在前方的竹子上寫字,此時廟方有人出來解讀神明的旨意,為迷惘的眾生指點迷津。
一九六二年,陳宗鷹出生在彰化縣田中鎮。家中七個孩子,他剛好排在中間,是第四個小孩,上面有兩個姊姊、一個哥哥,在他之下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他每次自我介紹,覺得最符合自己的形容就是「我有兄弟姊妹」。
他的爸爸陳森林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丁,上有三個姊姊。陳森林七歲的時候,父親就過世了,家中的孩子全靠母親一個人撫養長大。陳森林國小畢業後,就去學裁縫、做學徒,從小就必須自力更生。陳森林學成後,自己經營布莊,和妻子陳巫玉蘭在彰化縣田中市場裡賣布,並在攤位上層隔了一個小房間,全家就住在裡面。
布莊生意還不錯,有了一點積蓄,孩子們陸續出生,陳森林希望能給家人更好的生活空間,在同樣位於斗中路、距離田中市場大約一公里的地方買下一塊土地蓋房子。蓋房子必須花一大筆錢,妻子陳巫玉蘭非常反對,認為布莊在市場才有人潮有生意,但陳森林相當堅持,想要有自己的房子。誰知布莊搬至新房子之後,因為距離市場遠,生意一落千丈,再加上建屋時建築材料價格漲得厲害,所有積蓄都花光了,甚至還負債,經濟頓時陷入困境。除了節流,陳森林想要開源,當時聽說鳳梨和薑的價格很好,想起自己在南投縣名間鄉弓鞋村還有兩分地,若再承租陳氏祖先的兩甲地來耕作,應該可以增加收入。
鳳梨、金紙和襪子:童年打工記憶
不過,務農也沒有想像的簡單。在資訊不發達的年代,常常聽人說種某種作物價格很好,便趕緊跟風,但經過口耳相傳後,其實價格都已從高峰往下走,最後往往慘賠收場。原本因為蓋新房和搬布莊就已經負債,再加上務農的慘賠、家中食指浩繁,生活越發拮据辛苦。陳森林很希望可以改善經濟狀況,神明指示祖墳風水不好需要重修,他就重修;聽說種什麼好,他就種什麼,只希望能找到讓妻小好好生活的轉機。這時候孩子都還小,長子陳宗位從田中國小第一名畢業後,就讀田中國中,每次考試都霸占著第一名的位置。看長子書讀得好,期待他認真讀好書,不用再幫忙家務,盼望長子出人頭地,是陳森林最大的希望。大女兒(令珠)國中畢業後,馬上投入工作,到公路局客運金馬號擔任車掌小姐,二女兒(姚色)國中畢業為了分攤家計,在家門口擺攤賣檳榔、山上種植的果物,也賣寶島、長壽菸賺一些價差,或批發一些抽抽樂給小學生玩。排行老四的二兒子陳宗鷹當時還年幼,就讀田中國小高年級,適逢國內棒球風氣興盛,他喜歡打棒球,因此獲選進入彰化縣棒球隊,集訓期間有棒球隊供應吃住,也減輕家中一點負擔。但在練球和讀書的空檔,陳宗鷹(十二歲)常常和兩個妹妹(姚里十歲及姚光八歲)也在晚上及假日到住家對面製作金紙的工廠打工賺錢。
在過去,臺灣民眾大多信奉民間信仰,幾乎家家戶戶都會燒香祭拜以及燒金紙奉納神明與祖先。金紙上面需要蓋一個四四方方的紅色印章,還要在正中間貼上銀色或金色的錫箔紙。金紙從工廠一疊一疊生產出來後,陳家三兄妹就排隊去做手工,負責嵌金和蓋章。在做這些步驟前,為了避免金紙散落,必須先在每一疊金紙的一角用電鑽鑽個洞,穿線綁起來。由於電鑽很重,一個沒拿好,可能就讓金紙歪掉、鑽破,甚至手會受傷,於是就由五年級的陳宗鷹負責這個工作,鑽完洞、固定好,再交給小妹姚光一張一張蓋印,她的兩隻小手常常沾到染劑,從紅變黑。蓋完印,他再跟大妹接手貼細部的錫箔。因為很多人搶著打工,金紙紙質又參差不齊,紙質比較好、比較厚的容易做,比較薄的紙容易黏在一起,工作效率較差,所以陳宗鷹總是帶著妹妹先去工廠排隊,搶比較好的紙多做一些。做好十二疊就算一捆,一捆可以拿到五毛的工資,每個月累積的工資一次發放。把賺的錢拿回家給媽媽之前,兄妹三人會先彎去附近雜貨店去買糖廠出產的健素糖,五毛錢可以買到一大把。他們最喜歡沒有加糖衣的健素糖那香香的味道,含在嘴裡吃,愈嚼愈香,是三人童年裡最幸福的味道。
陳宗鷹大一些之後,就開始當爸爸的左右手,假日跟著父親到山上的農園工作。他記得有一陣子家裡種鳳梨,有一甲地都是鳳梨田,他在田間穿梭,兩隻腳被鳳梨刺得傷痕累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午在田邊的小工寮休息,跟父親一起煮泡麵吃。傍晚,爸爸挑著扁擔,將收成的鳳梨、香蕉或荔枝運下山,再走一段路到公車站,兩人搭最後一班公車回到田中,將農產交給二姊放在攤子賣。辛苦種鳳梨的記憶太深刻,深刻到讓陳宗鷹在外求學時幾乎不買鳳梨。他並不是不愛吃,而是會想起以前父親挑著重重的鳳梨下山,收購鳳梨的商人卻只給非常低廉的價格,因此每次看到市場上鳳梨的標價,他都覺得實在昂貴得買不下手!
就在全家人務農、布莊、擺攤和家庭代工的各種努力下,讓家中孩子可以繼續讀書。後來父母親決定把房子賣掉,搬往更遠的區域居住,用賣掉房子的錢償還債務,家中經濟才稍稍改善。
☆摘文二 第一次為連體嬰麻醉
二〇一〇年,陳宗鷹接到菲律賓分會轉介來一對臀部相連的連體嬰要到花蓮慈濟醫院進行分割手術的訊息。雖然很高興可以參與麻醉專業生涯中難得的學習機會和經驗,但另一方面,這也是以前從未處理過、超罕見的特殊個案,他內心嚴陣以待。
這對姊妹被慈濟志工發現時已經三個月大,臀部相連,共用一個直腸和肛門,健康狀況良好,無特殊疾病,因為名字裡都有Rose,所以被暱稱為「玫瑰姊妹」。小兒外科的彭海祁主任先啟程到菲律賓,評估姊妹倆的健康狀況。同時,陳宗鷹並請王章勉和李佳玲兩位學生,做文獻回顧與各項器材準備。
早在二〇〇三年,石明煌院長就曾率領麻醉團隊,成功幫助第一對連體嬰成功分割,所以特別提醒陳宗鷹要注意兩位小病人的用藥劑量與個人標記一定要區分清楚,才能確保手術安全。
手術房團隊既緊張又期待,隨即進行萬全的準備,就連兩臺麻醉機、兩個手術臺,擺放的位置和動線也仔細斟酌,甚至還將兩個洋娃娃臀部黏在一起操作演練。當準備分割的小姊妹抵達慈院,醫療團隊見到這麼漂亮可愛又天真無邪的孩子,更決心一定要幫助她們。手術前的各項檢查,是麻醉醫師和玫瑰姊妹的初次接觸。由於要進行MRI核磁共振造影,必須讓小嬰兒靜止才能準確攝影,因此由麻醉團隊負責麻醉。
一開始,大家手忙腳亂,當第一劑麻醉藥物從姊姊的靜脈點滴注射進去,每個人都屏氣凝神注視、並猜測到底是哪位會睡著?還是兩位都睡著?或是都不會睡著?看著姊姊逐漸睡著,妹妹還在哭鬧,陳宗鷹心中放下一塊大石頭──這表示兩姊妹的血液循環沒有大量的血液流量交叉的影響。接著,注射藥物也讓妹妹睡著,才順利完成檢查。
團隊在檢討MRI的麻醉經驗時,發現有可能會將兩姊妹的數值記錄寫相反,為了避免失誤,麻醉團隊在兩姊妹身上要用到的點滴、心電圖、血氧飽和度與呼吸管路等,每一條管線都用紅色、藍色分別標記來做區隔。
分割前腸造口與組織擴張的手術非常順利,手術結束甦醒時,陳宗鷹和麻醉團隊也更篤定兩姊妹的麻醉藥物不會互相影響,讓他們對分割時更有信心。實際分割手術時,兩姊妹需要一百八十度的翻身,團隊再次使用兩個洋娃娃做練習。為了預防手術時萬一需要輸血、尋找管路,麻醉團隊也使用超音波評估兩姊妹內頸靜脈的位置、大小,以備下次分割手術時的不時之需。
正式分割大挑戰
儘管已有前次檢查成功麻醉的經驗,但是正式分割才是真正挑戰的開始。陳宗鷹前一天與開刀房護理團隊及麻醉團隊,仔細的從頭演練並模擬各種狀況。
分割當日,早上七點便進開刀房準備,八點鐘準時為兩姊妹分別了進行麻醉誘導,每一個小細節,包括氣管內管如何黏貼、姊妹倆頭部怎麼擺、小手如何用棉捲包紮保溫與保護等等,大家戰戰兢兢的做好每一個步驟。在彭海祁主任所領導外科團隊精湛的技術下,小姊妹的身體正式分開了。緊接著,另外兩個外科團隊小心翼翼的個別進行後續修補的工作。
麻醉團隊也隨時注意各種狀況與因應。雖然,在神經外科團隊為小姊妹分割後的尾椎,進行神經修補時,因脊髓液流失,姊妹倆的血壓稍微下降,但在麻醉醫師馬上補充水分並處理升壓後,血壓隨即回復平穩。手術前後將近十個小時,時間雖長,陳宗鷹還是時刻守護在姊妹倆身旁。直到最後一次的手術麻醉,兩姊妹終於可以個別進行手術,幫姊妹做完腸造口的關閉送到恢復室時,陳宗鷹看到媽媽不知道要照顧哪一個孩子的這一幕,內心激動起來,對姊妹這一路以來的艱辛與大家的付出,非常感動。他疼惜孩子的心仍一如往昔,看到她們恢復健康,同時期待她們能平安長大,擁有各自燦爛的玫瑰人生,就是最無價滿足的回報。
☆摘文三 遇到麻醉醫師最大的惡夢
這一天清晨,開刀房如常運作,每個人依循著一套有秩序的流程,忙碌準備著。陳宗鷹這時還是臺灣南部某醫學中心的麻醉科醫師,他已經看完今天要手術的個案資料,第一臺刀是眼科手術,一位三歲的小男孩,即將被送進開刀房準備做疏通鼻淚管的手術。
鼻淚管位在眼頭靠近鼻腔處,多餘的淚水會由鼻淚管流至鼻子內排出。鼻淚管的末端有一層薄薄的瓣膜,通常嬰兒出生時,會自行打開。如果沒有打開,眼科醫師只要進行「淚管探針術」疏通,大約半個小時就可以完成。
為小男孩麻醉
對麻醉醫師而言,手術沒有大小之分,每一次都要讓病人安全接受麻醉、並舒適平安的甦醒。喜歡小孩的陳宗鷹,雖不能說在開刀房看到小孩會很開心,畢竟進入開刀房治療並不是什麼好事;但如果看到小孩,陳宗鷹頓時會覺得心情柔軟起來。曾經,他想過要當兒科醫師,成為麻醉科醫師之後,他也對自己承諾要在手術室裡守護孩子的生命。
小兒麻醉誘導最常使用吸入性的麻醉劑,他拿著面罩配合著安撫的話語,扣住小病人胖胖圓圓的臉頰,隨著麻醉監測儀器滴滴滴的聲音,小男孩沉沉的睡去。眼科醫師開始幫小病人清潔消毒,大約才過十五分鐘,手術都還沒開始,陳宗鷹發現小男孩的心跳在下降,血壓也下降,立即仔細檢查麻醉機、藥物和各種監測的生命數值狀況,一時找不出原因,但隱隱覺得不安,眼前雖然看似平靜,陳宗鷹還是請眼科醫師暫時先不要動刀。
陳宗鷹飛速打開所有腦中的資料庫,想找出原因時,小男孩竟突然發生心跳停止!醫護團隊緊急搶救,陳宗鷹趕緊打入強心劑,不斷進行心肺復甦術,一陣手忙腳亂之後,陳宗鷹覺得自己被嚇得心跳也快要停止,小男孩終於恢復了心跳。
最難防的「惡性高熱症」
陳宗鷹決定請眼科醫師取消這次的手術,先送病童到恢復室觀察。一到恢復室量體溫,發現小男孩體溫飆高,他還正在納悶,不一會兒,小男孩體溫又再升高一度。他正想釐清體溫的變化,沒想到,小男孩開始痙攣,「怎麼會這樣?」他都仔細確認過每個步驟都沒有問題,一個大膽的猜測,在陳宗鷹腦中跳出,他懷疑發生在這個小男孩身上的,正是「麻醉醫師的惡夢」──亞洲人臨床非常少見的「惡性高熱症」(MH)。臺灣大部分的醫師,都只在教科書裡讀到,幾乎沒有真正遇過惡性高熱發作的病人。
惡性高熱真正的發生原因仍不清楚,但與基因有關,比較盛行於歐美。歐美接受麻醉引發惡性高熱的發生率,是五萬至十萬分之一到五千分之一,在亞洲、臺灣的發生率更低。惡性高熱是由於肌漿鈣不受控制的升高,會讓肌肉釋放大量鈣離子,使體內二氧化碳濃度上升,病人就像用高速跑了一整天的馬拉松一樣,導致體溫過高(每五分鐘上升攝氏1至2度 ,中心體溫甚至超過44度)、酸中毒和肌肉收縮,甚至因ATP(三磷酸腺苷)耗盡,肌膜完整性受到損害,導致高血鉀症和橫紋肌溶解症。就算盡力搶救,百分之十的病人仍可能因心跳停止、腦傷、內出血,或器官衰竭而死亡;存活者也可能遺留腦部損傷、腎臟衰竭、肌肉損傷或重要器官功能不全等併發症。
惡性高熱症,也被稱為「麻醉醫師的惡夢」。惡性高熱可怕之處,在如今醫療科技進步的時代,僅僅接受一個小手術,仍可能因為一系列的反應,而導致病人突然死亡的悲劇,不僅家屬不能理解,醫師也遭受嚴重打擊。
這個小男孩的各種症狀,都像是惡性高熱症的表現,必須趕快治療,同時做肌肉切片給病理科檢驗,才能確認是否為惡性高熱。此時,困難又出現了,一是家長不願意孩子再進開刀房切一刀,再者,因為在美國發生病例較多,總共有八家醫學中心可以做切片檢查,但臺灣卻沒有一家醫學中心的病理科可以做,所以最後只能以「疑似」惡性高熱來診斷。還好當時惡性高熱症已經有解藥(Dantrolene),然而因為病例稀少,藥品保存期短、藥價昂貴,又是知名的「孤兒藥」──只有惡性高熱一種疾病會使用,幾乎很少醫院會準備。
使盡全力照顧
極為幸運的是,陳宗鷹當時服務的醫院是濁水溪以南唯一備有這種藥品的醫學中心,他向藥局拿到解藥,在恢復室即刻給予起始劑量(Loading Dose),小男孩的體溫不再升高,逐漸下降,病況馬上有了起色。之後,他將小男孩轉入小兒加護病房,持續治療,原本想委託在小兒科的學弟幫忙照顧,但學弟說他也沒遇過惡性高熱症的病人,陳宗鷹只好自己照顧,他待在小兒加護病房,整整七天照顧小病患,終於讓小男孩恢復,轉出加護病房並順利出院。
一個健康活潑的三歲小男孩,只是接受一個簡單的鼻淚管疏通手術,卻遭遇這種折磨,併發肌溶解症,差點連命都沒了。孩子的父母相當不諒解,甚至找了其他外科醫師,並跑到陳宗鷹的疼痛門診,質疑他是不是麻醉藥物用錯、或是劑量不對,才讓原本活活潑潑的孩子癱軟的躺在床上。陳宗鷹雖然耐心的解釋,是基因的問題加上吸入性麻醉藥物才誘發這樣的狀況,但在場包括其他麻醉科醫師、外科醫師,大家都只在教科書上讀過,也確實不曾有人見過這種狀況,因此沒有人可以再解釋什麼,只能期待小男孩能順利恢復健康!
除了每天盡心盡力的照顧這位小病人,陳宗鷹也到處找資料,並寫信到美國的惡性高熱學會詢問,陳宗鷹心想,「臺灣對這個疾病確實比較陌生,我乾脆自己翻譯成中文,讓更多人知道。」雖然,這件事讓他焦頭爛額,但他還是覺得應該把這件事當成案例,讓更多人知道,所以又花了時間把美國惡性高熱學會回覆的內容翻譯成中文,寫成科普文章。
小病人母親原本因為這件事,對陳宗鷹相當不諒解,看到陳宗鷹不但救回孩子,每天很認真照顧她的孩子,加上惡性高熱使用的特效藥非常昂貴,陳宗鷹為了幫家屬節省醫療開支,幫家屬向健保局申請給付,與健保局數次交涉往返,證明必須使用唯一而昂貴的「孤兒藥」才可治療,最後也獲得同意。最後出院時,小病人的母親已經不再怪罪陳宗鷹,不但不提告,反而是謝謝他一路以來的照顧。雖然,孩子出院時,只恢復了部分大肌肉功能,僅僅可以坐起來,還不能走路。不過,三個月後,陳宗鷹收到小兒科的好消息,原來他們透過在臺南鄉間開設診所的兒科醫師,得知小病人已經恢復健康,可以跑跑跳跳,讓陳宗鷹終於放下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