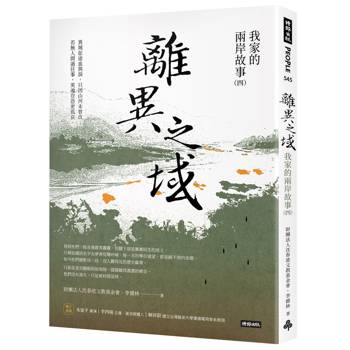輯一 緣起
前言
二○○八的夏天,隨著「帕黨溫暖之家」育幼院創辦人錢秋華女士的腳步,我第一次踏上泰北清萊的一座山村美斯樂(Mae Salong)。「美斯樂」原本是一座山岳的名稱,山麓下海拔高度一二六○公尺的這處村落一帶,大抵就是大家所稱的「異域」。
那天抵達時已是晚間十點多,整座村落早已闃無人聲,一路上聽多了異域戰火頻仍、犧牲壯烈的故事,這樣的寂然非但無法讓人好好體會山城的靜謐,反而感到一絲不安。
果然,翌日清晨天空微微透出亮光,一行人就被急促的砲彈聲驚醒,定神後,從小小的木窗格向外張望,才發現村民正拉起長長的紅色鞭炮歡迎我們的到來,不絕於耳的鞭炮聲響徹整個「美斯樂」……。
和大多數初訪異域的人一樣,我們對於「孤軍」所知有限。
美斯樂當地「同胞」(這樣稱呼是因為他們曾同屬中華民國國民,只是當年被共軍逼殺至此)帶著鄉音輕描淡寫地說:「異域,指的是當年中國雲南與緬甸之間尚未清楚劃定國界的模糊地帶,我們這一支屢敗屢戰的殘存軍隊就是利用軍事、政治上的模糊,讓大家有了趁隙轉進、伺機反攻,求取一息尚存的機會。儘管,有時候甚至不知道我們這一群早已彈盡糧絕、乏人聞問,隨時得面臨生死交迫、瀕臨瓦解的人,還能否稱得上是軍隊。」
時間回溯到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間,緬甸政府軍曾聯手共軍發動?滅性的圍剿,同時向聯合國施壓引發國際輿論,迫使駐守在滇緬一帶的邊區游擊隊撤軍;剩餘孤軍殘部便在李文煥、段希文二位軍長(第三軍、第五軍)率領下進入泰北山區,為來日的反攻續命。然而,這群殘士傷兵輾轉到泰北落腳之後,最終成為一支不被承認、被遺忘的「孤軍」……。
根據文獻史料記載,三、五兩軍不願意退的原因並不盡相同。
其中,第三軍早在撤退行動定案前便已下定決心不會隨部隊撤退至臺灣。由於第三軍的班底是早年在雲南成立的「鎮康縣自衛大隊」,同袍之間不但有同鄉、同學情誼,也有著更密切的宗親、姻親關係,彼此凝聚力、向心力都特別強;加上軍長李文煥並非軍系正規背景出身,「因為沒有軍人資歷或者軍校學歷,其官階在正規體系中均將遭到核降,因此李文煥所率的三軍選擇留在異域不願意撤臺。」
至於段希文將軍所統率的第五軍,則是在離開雲南之後才招兵買馬組成,部隊的共同意向並不一致,但憑軍長的判斷與決定。
軍長段希文雖然在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第一次撤退時即主張不撤,然而此次「國雷演習」,總統蔣介石已明確下令全面撤退,否則將不再提供補給。考量到部隊往後龐大開銷與生存問題,加上第五軍的軍官大部分皆為軍系出身,回到臺灣後不致面臨失業或降階,因此在接獲撤退命令後即已決定全撤。
「然而就在撤退前夕,段希文接到由情報局傳達而來的密令,請求五軍續留滇緬邊境伺機待命。」
為了生存並取得永久居留的機會,他們訓練泰軍,並七度出征協助泰國政府掃蕩企圖解放泰北的苗共(泰共);其中,考科考牙一役堪稱是孤軍能否苟存於泰北最為決定性的一場戰役。
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二月,由第三軍、第五軍編組而成的孤軍應泰國政府的請求,聯手出擊圍剿考科考牙山區的泰共游擊隊,經過廿二天的日夜攻打,成功收復考科考牙山區,阻止共產武裝勢力擴大,也避免泰國因共產勢力侵入遭一分為二的命運。這場戰役是泰國近代傷亡最為慘烈的戰爭,日後泰國政府於共軍的大本營設立紀念碑,高聳的紀念碑下刻著一位位陣亡將士的名字,只不過全都是以泰文鑴刻,已經找不到任何一個孤軍的中文姓名。
「在別人的土地上打勝仗,一點都不光彩啊,那是因為中華民國不要我們了嘛,所以我們才去幫忙泰皇打共軍;為了留下來呀,因為中華民國不要我們了嘛……。」
「也有臺灣的同袍弟兄不斷招手要我們回去啊,但中華民國已經不承認我們,我們根本回不去了;而且去臺灣有什麼好?要做什麼?我們除了會打仗什麼都不會啊。」
受訪的泰北孤軍們異口同聲地回應著。
確實,當時的國民政府在面對詭譎的國際情勢與龐大的國際輿論壓力下,曾向國際宣告:此後留滯當地的軍人不會再有任何軍事行動,就算有,也再與中華民國政府無關。這段歷史的始末就容我在後面慢慢訴說。
只如今,五軍軍長段希文將軍墓園座落於可以俯瞰整個美斯樂的山區,也成為造訪華人必訪的景點,雖仍有一位段將軍傳令兵的後代穿著國軍軍服看守著墓園,但已鮮少有人登高祭拜。
而三軍軍長李文煥之墓則位於泰國清邁省差巴干縣熱水塘新村的山腳下,後代曾在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重修新墓。其子女在李將軍的墓誌銘上寫著:
父親告訴我們: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家。
在這漫長無情的歲月裡,
父親為一群被遭忘的人,
苦苦尋求一片自力更生的土地,
並能在這片溫暖的土地上,
擁有自由呼吸的空間、建立自己的家園。
接下來要說的故事,發生地點不在中國內陸,而是靠近泰、緬邊境的西南「異域」……。
國共內戰不斷退守 反共部隊流離失所
關於異域孤軍如何從槍林彈雨中逃出生天的故事,要屬作家柏楊在《異域》裡描寫得最為深入、刻骨。
一九六一年,柏楊以「鄧克保」第一人稱的角度,在《自立晚報》發表連載小說,原書名為《血戰異域十一年》。當中觸及的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間,國共內戰時從雲南敗退到中、緬、泰邊界的國軍,如何歷經大大小的峽谷戰役、叢林游擊戰等,一路抵抗窮追不捨的共軍與誓言將外部勢力阻絕於境外的緬甸政府軍,又因國際政治利益折衝最終遭到「祖國」(指的是中華民國)遺棄的經過。
故事經由報紙連載後獲得廣大迴響,不少人讀來熱淚盈眶,而這些連載短篇也很快集結成書出版,一時間成了最為暢銷的戰爭(反共)文學作品(另於一九九○年拍攝成同名電影作品《異域》);這也讓身處異域的孤軍遭遇獲得社會的正視與關注。
之所以會有「異域孤軍」,還是要從國民政府遷來臺灣的這段歷史,也就是民國卅八年(一九四九)前後說起(或許現在多習慣以西元紀年,但深植於受訪老兵心中的那些記憶,仍然是以民國紀年的方式深刻銘印著;這點,也容在後續的敘事中適時加註。)。
(未完)
前言
二○○八的夏天,隨著「帕黨溫暖之家」育幼院創辦人錢秋華女士的腳步,我第一次踏上泰北清萊的一座山村美斯樂(Mae Salong)。「美斯樂」原本是一座山岳的名稱,山麓下海拔高度一二六○公尺的這處村落一帶,大抵就是大家所稱的「異域」。
那天抵達時已是晚間十點多,整座村落早已闃無人聲,一路上聽多了異域戰火頻仍、犧牲壯烈的故事,這樣的寂然非但無法讓人好好體會山城的靜謐,反而感到一絲不安。
果然,翌日清晨天空微微透出亮光,一行人就被急促的砲彈聲驚醒,定神後,從小小的木窗格向外張望,才發現村民正拉起長長的紅色鞭炮歡迎我們的到來,不絕於耳的鞭炮聲響徹整個「美斯樂」……。
和大多數初訪異域的人一樣,我們對於「孤軍」所知有限。
美斯樂當地「同胞」(這樣稱呼是因為他們曾同屬中華民國國民,只是當年被共軍逼殺至此)帶著鄉音輕描淡寫地說:「異域,指的是當年中國雲南與緬甸之間尚未清楚劃定國界的模糊地帶,我們這一支屢敗屢戰的殘存軍隊就是利用軍事、政治上的模糊,讓大家有了趁隙轉進、伺機反攻,求取一息尚存的機會。儘管,有時候甚至不知道我們這一群早已彈盡糧絕、乏人聞問,隨時得面臨生死交迫、瀕臨瓦解的人,還能否稱得上是軍隊。」
時間回溯到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間,緬甸政府軍曾聯手共軍發動?滅性的圍剿,同時向聯合國施壓引發國際輿論,迫使駐守在滇緬一帶的邊區游擊隊撤軍;剩餘孤軍殘部便在李文煥、段希文二位軍長(第三軍、第五軍)率領下進入泰北山區,為來日的反攻續命。然而,這群殘士傷兵輾轉到泰北落腳之後,最終成為一支不被承認、被遺忘的「孤軍」……。
根據文獻史料記載,三、五兩軍不願意退的原因並不盡相同。
其中,第三軍早在撤退行動定案前便已下定決心不會隨部隊撤退至臺灣。由於第三軍的班底是早年在雲南成立的「鎮康縣自衛大隊」,同袍之間不但有同鄉、同學情誼,也有著更密切的宗親、姻親關係,彼此凝聚力、向心力都特別強;加上軍長李文煥並非軍系正規背景出身,「因為沒有軍人資歷或者軍校學歷,其官階在正規體系中均將遭到核降,因此李文煥所率的三軍選擇留在異域不願意撤臺。」
至於段希文將軍所統率的第五軍,則是在離開雲南之後才招兵買馬組成,部隊的共同意向並不一致,但憑軍長的判斷與決定。
軍長段希文雖然在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第一次撤退時即主張不撤,然而此次「國雷演習」,總統蔣介石已明確下令全面撤退,否則將不再提供補給。考量到部隊往後龐大開銷與生存問題,加上第五軍的軍官大部分皆為軍系出身,回到臺灣後不致面臨失業或降階,因此在接獲撤退命令後即已決定全撤。
「然而就在撤退前夕,段希文接到由情報局傳達而來的密令,請求五軍續留滇緬邊境伺機待命。」
為了生存並取得永久居留的機會,他們訓練泰軍,並七度出征協助泰國政府掃蕩企圖解放泰北的苗共(泰共);其中,考科考牙一役堪稱是孤軍能否苟存於泰北最為決定性的一場戰役。
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二月,由第三軍、第五軍編組而成的孤軍應泰國政府的請求,聯手出擊圍剿考科考牙山區的泰共游擊隊,經過廿二天的日夜攻打,成功收復考科考牙山區,阻止共產武裝勢力擴大,也避免泰國因共產勢力侵入遭一分為二的命運。這場戰役是泰國近代傷亡最為慘烈的戰爭,日後泰國政府於共軍的大本營設立紀念碑,高聳的紀念碑下刻著一位位陣亡將士的名字,只不過全都是以泰文鑴刻,已經找不到任何一個孤軍的中文姓名。
「在別人的土地上打勝仗,一點都不光彩啊,那是因為中華民國不要我們了嘛,所以我們才去幫忙泰皇打共軍;為了留下來呀,因為中華民國不要我們了嘛……。」
「也有臺灣的同袍弟兄不斷招手要我們回去啊,但中華民國已經不承認我們,我們根本回不去了;而且去臺灣有什麼好?要做什麼?我們除了會打仗什麼都不會啊。」
受訪的泰北孤軍們異口同聲地回應著。
確實,當時的國民政府在面對詭譎的國際情勢與龐大的國際輿論壓力下,曾向國際宣告:此後留滯當地的軍人不會再有任何軍事行動,就算有,也再與中華民國政府無關。這段歷史的始末就容我在後面慢慢訴說。
只如今,五軍軍長段希文將軍墓園座落於可以俯瞰整個美斯樂的山區,也成為造訪華人必訪的景點,雖仍有一位段將軍傳令兵的後代穿著國軍軍服看守著墓園,但已鮮少有人登高祭拜。
而三軍軍長李文煥之墓則位於泰國清邁省差巴干縣熱水塘新村的山腳下,後代曾在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重修新墓。其子女在李將軍的墓誌銘上寫著:
父親告訴我們: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家。
在這漫長無情的歲月裡,
父親為一群被遭忘的人,
苦苦尋求一片自力更生的土地,
並能在這片溫暖的土地上,
擁有自由呼吸的空間、建立自己的家園。
接下來要說的故事,發生地點不在中國內陸,而是靠近泰、緬邊境的西南「異域」……。
國共內戰不斷退守 反共部隊流離失所
關於異域孤軍如何從槍林彈雨中逃出生天的故事,要屬作家柏楊在《異域》裡描寫得最為深入、刻骨。
一九六一年,柏楊以「鄧克保」第一人稱的角度,在《自立晚報》發表連載小說,原書名為《血戰異域十一年》。當中觸及的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間,國共內戰時從雲南敗退到中、緬、泰邊界的國軍,如何歷經大大小的峽谷戰役、叢林游擊戰等,一路抵抗窮追不捨的共軍與誓言將外部勢力阻絕於境外的緬甸政府軍,又因國際政治利益折衝最終遭到「祖國」(指的是中華民國)遺棄的經過。
故事經由報紙連載後獲得廣大迴響,不少人讀來熱淚盈眶,而這些連載短篇也很快集結成書出版,一時間成了最為暢銷的戰爭(反共)文學作品(另於一九九○年拍攝成同名電影作品《異域》);這也讓身處異域的孤軍遭遇獲得社會的正視與關注。
之所以會有「異域孤軍」,還是要從國民政府遷來臺灣的這段歷史,也就是民國卅八年(一九四九)前後說起(或許現在多習慣以西元紀年,但深植於受訪老兵心中的那些記憶,仍然是以民國紀年的方式深刻銘印著;這點,也容在後續的敘事中適時加註。)。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