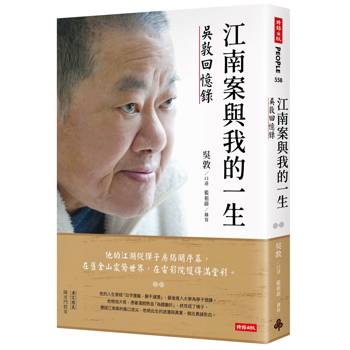序曲 殺手的眼神
聽見樓梯腳步聲,我舉起了黑色的0.38左輪。
槍不沉不重,來舊金山前才在洛杉磯的靶場試過,好使得很。我在心中反覆告訴自己:「你是特級射手。三軍四校聯合開學典禮上表揚過的特級射手。」
車庫沒亮燈,加州陽光很豔,門外天光儘管只射到日產「達特桑(DATSUN)」跑車的車後燈,但已經夠讓我和小董(董桂森)看清楚車庫方位,我左他右,站定身,擺好陣勢,等他從樓上下來。
車庫裡頭很靜,左手邊的熱水爐??響著電磁聲。樓上有男女對話,夾雜著腳步聲、馬桶沖水聲。「不是該上班了嗎?」大約等了十分鐘,一直不見人影,我忍不住嘀咕起來。比較輕的腳步聲明明都走近了,卻又旋了回去,大概有東西忘了。
屏著呼吸,我等待。漫長的十多分鐘,這種安靜,我很熟悉。
三十年前,我也這樣等待過。
當時,還在讀小學,身高不到一五○公分的我,懷裡裡著武士刀和飯盒,乘著傍晚天色昏暗,一溜煙鑽進「狗弟」家樓梯下的小空隙裡。那是我的攻擊基地,就等著「狗弟」返家。
「狗弟」就是個最會仗勢欺人的屁,個頭跟我差不多,人一多就喳呼喧鬧,落單就靜得像老鼠,眼睛骨溜溜轉。本事沒有,就是一張嘴又賤又臭屁。他們幾位念初中的混在一起,有幾個大個兒有一點肌肉,滿能打的,號稱「幸安聯盟」,相互照應,囂張的很。
我就讀的台北市幸安國小那時還有國軍駐紮,幾位老芋仔在街角開了間彈子房,兩盞黃燈掛兩張球檯上,幾排板凳和兩塊黑板,設備簡陋得很,但吸引年輕人,「幸安聯盟」是常客,一來就霸著不放。他們很精,要比拳頭前會先比人數,就算是個頭高大的高中生進來,只要人數比他們少,一定上前挑釁,不是嘲笑球技,就是吵著時間到了,想辦法把人家趕出去。
打彈子,誰不愛?我的桿法可準呢,看在狗弟他們眼裡就像根刺。所以定下規矩:要打球可以,但要先交五毛錢保護費。有錢才准打。我沒錢,就叫我滾一邊等著,不然就是拿桿子頂我弄我,或者擋在檯子邊,讓我不好出手,不然就是突然來個擠撞,桿歪手斜,白球亂滾洗袋,狗弟就帶頭鬼吼,又叫又笑。
我當然不爽,一定怒聲回嗆。那一票就一擁而上,拍頭捏臉,連推帶拉把我推倒地上,「我們是幸安聯盟,記住了。」我只想敲桿,不想磕頭,更不想繳保護費,偏偏雙拳難敵八手,只能鼻青臉腫,蹲在水溝邊生悶氣。
黑鵝雖然只是高中生,卻是我的偶像。看我蹲在水溝邊生悶氣,問清楚原委,就帶我走進彈子房,才進門就吆喝起來:「站好,給我站一排站好。」狗弟他們一夥看到高頭大馬的黑鵝,還真的安靜下來,慢慢走到球檯邊。
黑鵝拍拍我肩膀:「吳敦,別蹲了。過去敲一桿。放心,有我們在。」我們連同黑鵝的同伴只有四人,狗弟他們至少十人,可是黑鵝滿臉霸氣,狗弟只能眼睜睜看著我耍帥,看著我一桿清檯。
有黑鵝罩,我明白了出外靠兄弟的道理,從此就跟著他們,跑腿買菸,心甘情願好開心。我沒錢買菸,但有老爸在,我不用擔心。我爸吳家齊是國民黨忠貞黨員,常在家裡開小組會,開會時每位組員都會發菸。沒抽完的、囤備用的菸品我全偷來孝敬黑鵝。我這輩子使過的第一把武士刀,也是從黑鵝手上接過來的。
不過,躲進狗弟家樓梯下,才是我的復仇。我想憑一己之力,制伏狗弟。
我記仇,有仇必報,不達目的,絕不放棄。得罪我的,看不順眼的,我一定拚到底,第一次打不過,第二次還是打不過,我一定會再想辦法,三次四次五次沒完沒了,一定拚到對方討饒落跑為止。我會像鬼一樣神出鬼沒纏著你,走到哪,你都會看到我,知道我要幹嘛……我就是這麼陰魂不散,連鬼都嫌,所以後來人家才會叫我「鬼見愁」。
帶便當,就代表我準備長期抗戰,非幹倒狗弟不可。那晚,便當早嗑完了,窩在樓梯下方的水泥地上,屁股都僵麻了,阿狗才推著單車進來。聽見車聲,我立刻解開布袋,樓梯間暈黃的燈光已經夠讓我確認那人就是狗弟,便當一丟,翻過身,彈跳蹦起,抽出武士刀,大吼一聲朝他背上掃去。
聽見喊殺聲,狗弟急然回頭,眼神充滿了恐懼。他看見了我吳敦,知道我有仇必報。知道我會打他砍他,直到他躺下為止。
那是我頭一回舞弄武士刀。原本以為刀鋒俐落,偷襲得手,肯定刀落人倒,電影不都是這樣拍的嗎?錯了,刀鋒再利,掃過身子,最多破皮見血,微不足道的輕傷,真要留下難忘的回憶,刀鋒一定要先壓上對方身子,順勢用力扯拉,上下左右都好。關鍵不在砍,而是拉扯,用對力才會皮破見肉又噴血。
狗弟的恐懼眼神,是我拿下的第一個江湖獎杯。江南的茫然眼神,卻讓我接下來的人生完全變了調。
一聽見走下樓梯的腳步聲,我的左手趨前扶緊持搶的右手,這是來自大陸,當過解放軍的Jerry特別提醒我的射擊姿勢:「單手不穩,會抖,雙手才準。」我們在加州靶場射過烏茲衝鋒槍和M16長槍,純粹只是好玩,左輪才是用來防身與攻擊,這趟是狙擊,電光石火,千鈞一髮之際,一旦射偏了,可能就會賠掉自己小命,「手要穩,才會準!」
我清楚記得江南往下走了才五步,就停住了。手上拿著小紙箱的他,看到了站在暗處的我。愣了一下,眼神有些錯愕,應該是沒想到車庫有人,更沒想到是來索命的人。
我想他應該還不及看清楚我手上的槍,最多就只看到一抹紅光。
他沒見過我,不認識我,絕對不知道江湖道上叫我鬼見愁,更不知道我是特級射手,雖然以前都是拿槍唬人,這次才是第一次拿槍對著人開轟。而且,我沒打算讓他開口,眼神才剛對接,就扣下了扳機。
行動之前,我們做足了功課,掌握江南每天行蹤。知道江南太太早上八點左右會先開車送兒子上學,江南則是九點左右出門上班,九點十五分會到達漁人碼頭的藝品店,晚上六點半左右回家。
十月十四日晚上,大哥(陳啟禮)再次帶我們到江南家再走一趟,讓大家確認和熟悉行動和撤退路線,最重要的是確定江南在家,第二天才不會白跑一趟。當晚,我們看見江南家燈火通明,「好,就明天動手。」接下來,大哥再次要我們再看一眼江南的照片。這麼謹慎,就是避免殺錯人。
按照我們掌握的行蹤,此刻,江南老婆已經送完孩子回家,接下來就該是江南要去上班了,既然家裡只剩這對夫妻,這時從樓梯走下來的男人,絕對就是江南。
聽見樓梯腳步聲,我舉起了黑色的0.38左輪。
槍不沉不重,來舊金山前才在洛杉磯的靶場試過,好使得很。我在心中反覆告訴自己:「你是特級射手。三軍四校聯合開學典禮上表揚過的特級射手。」
車庫沒亮燈,加州陽光很豔,門外天光儘管只射到日產「達特桑(DATSUN)」跑車的車後燈,但已經夠讓我和小董(董桂森)看清楚車庫方位,我左他右,站定身,擺好陣勢,等他從樓上下來。
車庫裡頭很靜,左手邊的熱水爐??響著電磁聲。樓上有男女對話,夾雜著腳步聲、馬桶沖水聲。「不是該上班了嗎?」大約等了十分鐘,一直不見人影,我忍不住嘀咕起來。比較輕的腳步聲明明都走近了,卻又旋了回去,大概有東西忘了。
屏著呼吸,我等待。漫長的十多分鐘,這種安靜,我很熟悉。
三十年前,我也這樣等待過。
當時,還在讀小學,身高不到一五○公分的我,懷裡裡著武士刀和飯盒,乘著傍晚天色昏暗,一溜煙鑽進「狗弟」家樓梯下的小空隙裡。那是我的攻擊基地,就等著「狗弟」返家。
「狗弟」就是個最會仗勢欺人的屁,個頭跟我差不多,人一多就喳呼喧鬧,落單就靜得像老鼠,眼睛骨溜溜轉。本事沒有,就是一張嘴又賤又臭屁。他們幾位念初中的混在一起,有幾個大個兒有一點肌肉,滿能打的,號稱「幸安聯盟」,相互照應,囂張的很。
我就讀的台北市幸安國小那時還有國軍駐紮,幾位老芋仔在街角開了間彈子房,兩盞黃燈掛兩張球檯上,幾排板凳和兩塊黑板,設備簡陋得很,但吸引年輕人,「幸安聯盟」是常客,一來就霸著不放。他們很精,要比拳頭前會先比人數,就算是個頭高大的高中生進來,只要人數比他們少,一定上前挑釁,不是嘲笑球技,就是吵著時間到了,想辦法把人家趕出去。
打彈子,誰不愛?我的桿法可準呢,看在狗弟他們眼裡就像根刺。所以定下規矩:要打球可以,但要先交五毛錢保護費。有錢才准打。我沒錢,就叫我滾一邊等著,不然就是拿桿子頂我弄我,或者擋在檯子邊,讓我不好出手,不然就是突然來個擠撞,桿歪手斜,白球亂滾洗袋,狗弟就帶頭鬼吼,又叫又笑。
我當然不爽,一定怒聲回嗆。那一票就一擁而上,拍頭捏臉,連推帶拉把我推倒地上,「我們是幸安聯盟,記住了。」我只想敲桿,不想磕頭,更不想繳保護費,偏偏雙拳難敵八手,只能鼻青臉腫,蹲在水溝邊生悶氣。
黑鵝雖然只是高中生,卻是我的偶像。看我蹲在水溝邊生悶氣,問清楚原委,就帶我走進彈子房,才進門就吆喝起來:「站好,給我站一排站好。」狗弟他們一夥看到高頭大馬的黑鵝,還真的安靜下來,慢慢走到球檯邊。
黑鵝拍拍我肩膀:「吳敦,別蹲了。過去敲一桿。放心,有我們在。」我們連同黑鵝的同伴只有四人,狗弟他們至少十人,可是黑鵝滿臉霸氣,狗弟只能眼睜睜看著我耍帥,看著我一桿清檯。
有黑鵝罩,我明白了出外靠兄弟的道理,從此就跟著他們,跑腿買菸,心甘情願好開心。我沒錢買菸,但有老爸在,我不用擔心。我爸吳家齊是國民黨忠貞黨員,常在家裡開小組會,開會時每位組員都會發菸。沒抽完的、囤備用的菸品我全偷來孝敬黑鵝。我這輩子使過的第一把武士刀,也是從黑鵝手上接過來的。
不過,躲進狗弟家樓梯下,才是我的復仇。我想憑一己之力,制伏狗弟。
我記仇,有仇必報,不達目的,絕不放棄。得罪我的,看不順眼的,我一定拚到底,第一次打不過,第二次還是打不過,我一定會再想辦法,三次四次五次沒完沒了,一定拚到對方討饒落跑為止。我會像鬼一樣神出鬼沒纏著你,走到哪,你都會看到我,知道我要幹嘛……我就是這麼陰魂不散,連鬼都嫌,所以後來人家才會叫我「鬼見愁」。
帶便當,就代表我準備長期抗戰,非幹倒狗弟不可。那晚,便當早嗑完了,窩在樓梯下方的水泥地上,屁股都僵麻了,阿狗才推著單車進來。聽見車聲,我立刻解開布袋,樓梯間暈黃的燈光已經夠讓我確認那人就是狗弟,便當一丟,翻過身,彈跳蹦起,抽出武士刀,大吼一聲朝他背上掃去。
聽見喊殺聲,狗弟急然回頭,眼神充滿了恐懼。他看見了我吳敦,知道我有仇必報。知道我會打他砍他,直到他躺下為止。
那是我頭一回舞弄武士刀。原本以為刀鋒俐落,偷襲得手,肯定刀落人倒,電影不都是這樣拍的嗎?錯了,刀鋒再利,掃過身子,最多破皮見血,微不足道的輕傷,真要留下難忘的回憶,刀鋒一定要先壓上對方身子,順勢用力扯拉,上下左右都好。關鍵不在砍,而是拉扯,用對力才會皮破見肉又噴血。
狗弟的恐懼眼神,是我拿下的第一個江湖獎杯。江南的茫然眼神,卻讓我接下來的人生完全變了調。
一聽見走下樓梯的腳步聲,我的左手趨前扶緊持搶的右手,這是來自大陸,當過解放軍的Jerry特別提醒我的射擊姿勢:「單手不穩,會抖,雙手才準。」我們在加州靶場射過烏茲衝鋒槍和M16長槍,純粹只是好玩,左輪才是用來防身與攻擊,這趟是狙擊,電光石火,千鈞一髮之際,一旦射偏了,可能就會賠掉自己小命,「手要穩,才會準!」
我清楚記得江南往下走了才五步,就停住了。手上拿著小紙箱的他,看到了站在暗處的我。愣了一下,眼神有些錯愕,應該是沒想到車庫有人,更沒想到是來索命的人。
我想他應該還不及看清楚我手上的槍,最多就只看到一抹紅光。
他沒見過我,不認識我,絕對不知道江湖道上叫我鬼見愁,更不知道我是特級射手,雖然以前都是拿槍唬人,這次才是第一次拿槍對著人開轟。而且,我沒打算讓他開口,眼神才剛對接,就扣下了扳機。
行動之前,我們做足了功課,掌握江南每天行蹤。知道江南太太早上八點左右會先開車送兒子上學,江南則是九點左右出門上班,九點十五分會到達漁人碼頭的藝品店,晚上六點半左右回家。
十月十四日晚上,大哥(陳啟禮)再次帶我們到江南家再走一趟,讓大家確認和熟悉行動和撤退路線,最重要的是確定江南在家,第二天才不會白跑一趟。當晚,我們看見江南家燈火通明,「好,就明天動手。」接下來,大哥再次要我們再看一眼江南的照片。這麼謹慎,就是避免殺錯人。
按照我們掌握的行蹤,此刻,江南老婆已經送完孩子回家,接下來就該是江南要去上班了,既然家裡只剩這對夫妻,這時從樓梯走下來的男人,絕對就是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