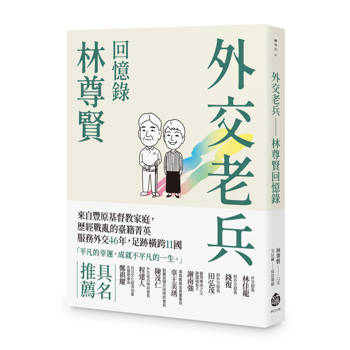▍第九章 駐韓國首任代表
──韓臺特殊情誼與斷交後的外交考驗,外交生涯的高潮與終止。
◆ 韓臺人民對日本的不同心態
韓國社會的氛圍至今仍然相當保守,男尊女卑的現象普遍存在。這種觀念深植於韓國的傳統文化之中,也受到中國儒家思想的深遠影響。長久以來,韓國人將中國文化視為中原正統,把中國人尊為「大哥」;相較之下,日本文化則僅被視為扶桑邊陲的產物,日本人頂多算是「小弟」。這種文化心態不僅是殖民仇恨的延續,更透露出韓國人對日本這個蕞爾小國,由心底生出的輕視與不服。
韓國人畫龍的方式就很有象徵意義:中國龍有五爪,韓國龍是四爪,而日本龍只有三爪。光從這種畫龍的細節,就能看出三國之間在文化層級上的微妙差異。
我還記得,有位韓國朋友曾問我:「同樣都曾被日本殖民,為什麼韓國人和臺灣人對日本的看法會差這麼多?」我想了想,回答他:「韓國是文化古國,本有自己悠久且優良的傳統,卻在近代被他們長期輕視的日本殖民,對韓國人而言,這是一種民族的奇恥大辱。反觀臺灣,只是一個被隨意割讓、清朝也未曾真正重視的邊陲之地。日本接手後卻用心建設,替臺灣奠定了現代化的基礎,因此許多臺灣老百姓對此心存感激。」
◆ 臺韓之間特殊的軍事與情報合作
蔣中正政府撤退到臺灣後復任總統,在他的任內僅有兩次出國訪問:一次是前往韓國釜山,另一次則是菲律賓碧瑤。這不僅顯示了韓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特殊關係,也反映出兩國當年的緊密連結。我想,這種深厚關係的淵源,與雙方領導者同樣是軍人背景有關;兩國政府都處於威權統治時代,因此軍事與情報上的交流格外頻繁密切。
那個年代,臺韓之間的政治合作不僅限於高層互訪,還包括許多實質的軍事與情報合作。舉例來說,金鍾泌是韓國中央情報部(KCIA)的首任部長,他與我政府關係深厚,多次來臺訪問,並與軍方高層保持往來。作為KCIA的創建者,他在韓國情報界的影響力極大,而我國的情報單位也與KCIA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
除此之外,兩國還進行過多次軍事人員的祕密交流與訓練。從一九五○到一九六○年代,韓國曾派遣軍官到臺灣接受陸軍官校的課程,而臺灣也多次派遣軍事顧問團赴韓,協助他們進行軍隊現代化的改革。
我記得,在我駐韓任內,臺灣前軍情局局長丁渝洲曾祕密訪韓,由我負責接待,但他具體的任務與行程安排,我並不知情。這種高度機密性,正是兩國軍事交流的典型特徵─往往只有極少數高層知情。丁渝洲返臺不久後被宣布接任國安局局長,更顯示他在情報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我後來曾專程到陽明山拜會他,受到極其隆重的接待,這也是我外交生涯中印象深刻的一段經歷。
◆ 金鍾泌的親民風範
蔣總統(蔣中正)過世時,韓國國務院總理金鍾泌以弔唁特使團團長的身分親自來臺,充分展現了韓國對中華民國(臺灣)的高度重視。我在外交部禮賓司擔任副司長,正是負責接待金鍾泌的窗口。記得那次,日本弔唁代表團的團長則是剛卸任總理職務的佐藤榮作。
金鍾泌先後在朴正熙與金大中兩位總統任內出任國務總理,雖然始終未能登上總統大位,但他從政生涯相對圓滿,並普遍受到韓國人民的尊重與愛戴。許多韓國友人與政情專家都曾告訴我,他心地溫和,作風並不強悍,因此少了些爭權奪勢的鋒芒,卻多了一份難得的平衡與穩重。
我與金鍾泌交談時多以日語為主,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球場上的舉止。每次與他打高爾夫,他總會事先準備許多小禮物,並在場上與桿弟、工作人員閒話家常,親手送上禮物。他這種親民、細膩的作風,讓人感受到他的溫暖與誠懇。對我而言,金鍾泌是我在駐韓期間特別懷念的一位人物。
◆ 韓臺斷交的衝擊與潘基文的靈活外交
前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原本是職業外交官出身,他在金泳三、金大中與盧武鉉三屆韓國政府中歷任外交要職,深受朝野倚重。一般來說,韓國職業外交官能升至「次官」已屬難得,但潘基文憑藉高超手腕化解多起外交危機,最終破格出任外交部長,這在韓國外交界可說是一大突破,也是對他能力的最高肯定。
我派駐韓國時,正值臺韓斷交不久。對於昔日兄弟之邦竟與我們翻臉斷交,國人內心自然難免感到痛心。斷交當天,韓國政府宣布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館人員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離境,並強制將原屬我國的大使館房舍、土地,全數移交給新建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如此,韓國政府更進一步要求首爾的僑團和僑校停止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甚至連大使館內的孫中山、蔣中正銅像也被迫搬遷到華僑中學。這種徹底翻臉、不留情面的作法,讓臺灣社會普遍感到憤慨,臺韓關係也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
◆ 臺韓斷交後的航權角力
一九九二年(民國八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臺韓正式斷交,對兩國關係造成了深遠影響。直到一九九三年(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韓國才設立「駐臺北韓國代表部」,以示對臺灣的尊重,並特別派任前駐中華民國大使韓哲洙擔任首任代表。臺灣則於稍晚的一九九四年(民國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漢城(今首爾)設立「駐韓國臺北代表部」。而我,已年逾六十四歲,被任命為首任駐韓國代表。我與韓哲洙私交甚篤,彼此都很高興又能再度有互動。
在兩國關係低迷、風雨飄搖的時期,潘基文奉金鍾泌之命,祕密前來拜會我。他主動提出希望每月能固定見一次面,雙方不帶祕書,並在市區飯店祕密會談。韓國對臺灣的貿易依賴很深,每年需向臺灣進口大量商品和工業設備,而臺灣的航線則是通往東南亞的重要樞紐。斷航後,韓國遭受極大經濟損失,旅客往來和貨物運輸都受到嚴重影響,因此我們每月會談多半圍繞在航權談判上。透過這些交流,我深刻體會到潘基文靈活巧妙、精明圓滑的外交手腕。
即便如此,雙方談判進展依然緩慢。主要原因在於我方堅持韓國必須先道歉,或至少表現出誠懇的態度。畢竟對臺灣而言,臺韓航線並非不可或缺;但對韓國而言,失去臺灣航線必須繞道飛行,將因此付出極大的經濟代價。韓方雖還不願意公開道歉,但內心深知對臺灣原有的兄弟情誼造成傷害。我剛赴韓就任代表時,韓國外交部長對我極為禮遇,經常私下邀我到官邸作客,據辦事處同仁觀察,他接待我的禮數甚至比有邦交時還要周到。
韓國一方面積極發展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另一方面又不願完全放棄在臺灣的利益。他們試圖在兩邊之間維持平衡,這本是國際現實中的利益權衡。無論彼此官方立場如何牽扯,最終仍要以人民的最大利益為依歸。但由於各方互不相讓又堅持己見,兩國航權談判還是一再拖延,直到二○○五年(民國九十四年)才正式恢復通航,自斷交以來雙方整整中斷航線十三年。
◆ 韓國官邸購置的緣起與巧合
當我剛派駐韓國時,起初先住在飯店裡。雖然飯店設施齊全、環境也算舒適,但畢竟不是自己的官邸,對外活動多少還是受到限制。後來外交部決定購置官邸,這也是當年的政策─重要駐在國的官邸應盡量避免承租,要以自購為原則。不過,由於部裡預算有限,每年只能編列一個駐在地的購屋經費,採購順序則由外交部統籌評估。
我剛到韓國的那一年,原本的購房預算是編給吉隆坡(馬來西亞)官邸使用的,但因馬來西亞屬於英國法系,不動產登記程序繁複,加上當地法律不允許直接登記在官方機構名下,僅能賣給私人,產權有風險,因此計畫作罷。這筆預算轉來用在韓國,而韓國代表處不動產能以「代表處」的名義登記,於是我們成了受惠者,代表處剛成立不久就能擁有自己的官邸。
透過我韓裔女婿朋友的介紹,我得知一位遠洋漁業老闆因經營困難,準備出售一處房產。那房子剛好位於青瓦臺後方的住宅管制區,房產交易必須經過韓國國安單位的核准才能過戶。經過幾番交涉,韓方認定臺灣代表處符合資格,最終官邸以三百萬美元成交。這座官邸占地五百多坪,環境清幽。據屋主說,他開出的價格只等於土地價值,原建築幾乎是「半買半送」。如今,這棟官邸的市值據說已經高達數千萬美元。
傳統上,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館的規模和編制都比一般大使館更大,也特別重視門面與排場。館內光是賓士車就有兩輛,在我任內,還有一輛凱迪拉克豪華房車被運回臺灣,成了禮賓司接待外國元首訪臺的專用座車。早些年,駐韓大使回國後經常就升任外交部長,所以,早期駐韓大使一直被視為極為重要的職位。我接任時,已是即將退休的「外交老兵」,雖然仍盡心履行職責,但這個職位已經不像往昔那般重要了。
據時任外交部長錢復先生告訴我,臺韓斷交後,他與房金炎次長商討接任人選時,兩人一致認為我是最適合收拾殘局的人選。錢、房兩位長官都是我在臺大政治系的學弟,也是外交部內多年的同事,對我的個性瞭若指掌。他們覺得我有「逆來順受」的耐性,不知這算不算是一種美德呢?
◆ 韓國人「世界第一」的志氣
韓國人做事向來講究氣魄,不論是煉鋼、造船還是汽車製造,只要確立了目標,就會下定決心「要做就做到世界第一」。我記得有一次參觀韓國現代造船廠,發現他們正在興建號稱全球最大的船塢。雖然那時陽明海運一口氣下了七艘貨櫃船的訂單,但距離填滿這麼龐大的產能仍差得遠。
同行的臺灣官員朋友覺得好奇就問:「你們造這麼大的船塢,真的有足夠的訂單嗎?」沒想到,帶領我們參觀的總經理頭也不回地回答:「放心,我們很快就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造船公司。」
這句話展現韓國人的決心與氣魄,或許在當下聽起來略顯誇張,但也徹底體現韓國人做事的風格─一旦目標確立,信念就絕不動搖。
◆ 四十六年路程,畫下圓滿句點
二○○一年(民國九十年)五月,總統陳水扁同意我告老還鄉。至此,我在外交部及各駐外館處服務累計已達四十六年,最後擔任首屆駐韓國代表也長達七年半。公務員職等早已晉升至最高簡任十四級以上的「特任」階級,外交生涯走到這一刻,總算能畫下完美的句點。
回首往昔,我自認沒有愧對國家與人民的栽培,這份心安讓我倍感欣慰。卸下公職後,我更期待能展開全新的生活,自由自在,去體驗另一種人生的節奏。
回顧這段旅程,我深知自己只是時代洪流中的一名小角色;然而,只要曾經為國家盡一份力,無論成就大小,都足以讓我的生命因此而更為厚實。
──韓臺特殊情誼與斷交後的外交考驗,外交生涯的高潮與終止。
◆ 韓臺人民對日本的不同心態
韓國社會的氛圍至今仍然相當保守,男尊女卑的現象普遍存在。這種觀念深植於韓國的傳統文化之中,也受到中國儒家思想的深遠影響。長久以來,韓國人將中國文化視為中原正統,把中國人尊為「大哥」;相較之下,日本文化則僅被視為扶桑邊陲的產物,日本人頂多算是「小弟」。這種文化心態不僅是殖民仇恨的延續,更透露出韓國人對日本這個蕞爾小國,由心底生出的輕視與不服。
韓國人畫龍的方式就很有象徵意義:中國龍有五爪,韓國龍是四爪,而日本龍只有三爪。光從這種畫龍的細節,就能看出三國之間在文化層級上的微妙差異。
我還記得,有位韓國朋友曾問我:「同樣都曾被日本殖民,為什麼韓國人和臺灣人對日本的看法會差這麼多?」我想了想,回答他:「韓國是文化古國,本有自己悠久且優良的傳統,卻在近代被他們長期輕視的日本殖民,對韓國人而言,這是一種民族的奇恥大辱。反觀臺灣,只是一個被隨意割讓、清朝也未曾真正重視的邊陲之地。日本接手後卻用心建設,替臺灣奠定了現代化的基礎,因此許多臺灣老百姓對此心存感激。」
◆ 臺韓之間特殊的軍事與情報合作
蔣中正政府撤退到臺灣後復任總統,在他的任內僅有兩次出國訪問:一次是前往韓國釜山,另一次則是菲律賓碧瑤。這不僅顯示了韓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特殊關係,也反映出兩國當年的緊密連結。我想,這種深厚關係的淵源,與雙方領導者同樣是軍人背景有關;兩國政府都處於威權統治時代,因此軍事與情報上的交流格外頻繁密切。
那個年代,臺韓之間的政治合作不僅限於高層互訪,還包括許多實質的軍事與情報合作。舉例來說,金鍾泌是韓國中央情報部(KCIA)的首任部長,他與我政府關係深厚,多次來臺訪問,並與軍方高層保持往來。作為KCIA的創建者,他在韓國情報界的影響力極大,而我國的情報單位也與KCIA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
除此之外,兩國還進行過多次軍事人員的祕密交流與訓練。從一九五○到一九六○年代,韓國曾派遣軍官到臺灣接受陸軍官校的課程,而臺灣也多次派遣軍事顧問團赴韓,協助他們進行軍隊現代化的改革。
我記得,在我駐韓任內,臺灣前軍情局局長丁渝洲曾祕密訪韓,由我負責接待,但他具體的任務與行程安排,我並不知情。這種高度機密性,正是兩國軍事交流的典型特徵─往往只有極少數高層知情。丁渝洲返臺不久後被宣布接任國安局局長,更顯示他在情報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我後來曾專程到陽明山拜會他,受到極其隆重的接待,這也是我外交生涯中印象深刻的一段經歷。
◆ 金鍾泌的親民風範
蔣總統(蔣中正)過世時,韓國國務院總理金鍾泌以弔唁特使團團長的身分親自來臺,充分展現了韓國對中華民國(臺灣)的高度重視。我在外交部禮賓司擔任副司長,正是負責接待金鍾泌的窗口。記得那次,日本弔唁代表團的團長則是剛卸任總理職務的佐藤榮作。
金鍾泌先後在朴正熙與金大中兩位總統任內出任國務總理,雖然始終未能登上總統大位,但他從政生涯相對圓滿,並普遍受到韓國人民的尊重與愛戴。許多韓國友人與政情專家都曾告訴我,他心地溫和,作風並不強悍,因此少了些爭權奪勢的鋒芒,卻多了一份難得的平衡與穩重。
我與金鍾泌交談時多以日語為主,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球場上的舉止。每次與他打高爾夫,他總會事先準備許多小禮物,並在場上與桿弟、工作人員閒話家常,親手送上禮物。他這種親民、細膩的作風,讓人感受到他的溫暖與誠懇。對我而言,金鍾泌是我在駐韓期間特別懷念的一位人物。
◆ 韓臺斷交的衝擊與潘基文的靈活外交
前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原本是職業外交官出身,他在金泳三、金大中與盧武鉉三屆韓國政府中歷任外交要職,深受朝野倚重。一般來說,韓國職業外交官能升至「次官」已屬難得,但潘基文憑藉高超手腕化解多起外交危機,最終破格出任外交部長,這在韓國外交界可說是一大突破,也是對他能力的最高肯定。
我派駐韓國時,正值臺韓斷交不久。對於昔日兄弟之邦竟與我們翻臉斷交,國人內心自然難免感到痛心。斷交當天,韓國政府宣布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館人員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離境,並強制將原屬我國的大使館房舍、土地,全數移交給新建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如此,韓國政府更進一步要求首爾的僑團和僑校停止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甚至連大使館內的孫中山、蔣中正銅像也被迫搬遷到華僑中學。這種徹底翻臉、不留情面的作法,讓臺灣社會普遍感到憤慨,臺韓關係也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
◆ 臺韓斷交後的航權角力
一九九二年(民國八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臺韓正式斷交,對兩國關係造成了深遠影響。直到一九九三年(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韓國才設立「駐臺北韓國代表部」,以示對臺灣的尊重,並特別派任前駐中華民國大使韓哲洙擔任首任代表。臺灣則於稍晚的一九九四年(民國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漢城(今首爾)設立「駐韓國臺北代表部」。而我,已年逾六十四歲,被任命為首任駐韓國代表。我與韓哲洙私交甚篤,彼此都很高興又能再度有互動。
在兩國關係低迷、風雨飄搖的時期,潘基文奉金鍾泌之命,祕密前來拜會我。他主動提出希望每月能固定見一次面,雙方不帶祕書,並在市區飯店祕密會談。韓國對臺灣的貿易依賴很深,每年需向臺灣進口大量商品和工業設備,而臺灣的航線則是通往東南亞的重要樞紐。斷航後,韓國遭受極大經濟損失,旅客往來和貨物運輸都受到嚴重影響,因此我們每月會談多半圍繞在航權談判上。透過這些交流,我深刻體會到潘基文靈活巧妙、精明圓滑的外交手腕。
即便如此,雙方談判進展依然緩慢。主要原因在於我方堅持韓國必須先道歉,或至少表現出誠懇的態度。畢竟對臺灣而言,臺韓航線並非不可或缺;但對韓國而言,失去臺灣航線必須繞道飛行,將因此付出極大的經濟代價。韓方雖還不願意公開道歉,但內心深知對臺灣原有的兄弟情誼造成傷害。我剛赴韓就任代表時,韓國外交部長對我極為禮遇,經常私下邀我到官邸作客,據辦事處同仁觀察,他接待我的禮數甚至比有邦交時還要周到。
韓國一方面積極發展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另一方面又不願完全放棄在臺灣的利益。他們試圖在兩邊之間維持平衡,這本是國際現實中的利益權衡。無論彼此官方立場如何牽扯,最終仍要以人民的最大利益為依歸。但由於各方互不相讓又堅持己見,兩國航權談判還是一再拖延,直到二○○五年(民國九十四年)才正式恢復通航,自斷交以來雙方整整中斷航線十三年。
◆ 韓國官邸購置的緣起與巧合
當我剛派駐韓國時,起初先住在飯店裡。雖然飯店設施齊全、環境也算舒適,但畢竟不是自己的官邸,對外活動多少還是受到限制。後來外交部決定購置官邸,這也是當年的政策─重要駐在國的官邸應盡量避免承租,要以自購為原則。不過,由於部裡預算有限,每年只能編列一個駐在地的購屋經費,採購順序則由外交部統籌評估。
我剛到韓國的那一年,原本的購房預算是編給吉隆坡(馬來西亞)官邸使用的,但因馬來西亞屬於英國法系,不動產登記程序繁複,加上當地法律不允許直接登記在官方機構名下,僅能賣給私人,產權有風險,因此計畫作罷。這筆預算轉來用在韓國,而韓國代表處不動產能以「代表處」的名義登記,於是我們成了受惠者,代表處剛成立不久就能擁有自己的官邸。
透過我韓裔女婿朋友的介紹,我得知一位遠洋漁業老闆因經營困難,準備出售一處房產。那房子剛好位於青瓦臺後方的住宅管制區,房產交易必須經過韓國國安單位的核准才能過戶。經過幾番交涉,韓方認定臺灣代表處符合資格,最終官邸以三百萬美元成交。這座官邸占地五百多坪,環境清幽。據屋主說,他開出的價格只等於土地價值,原建築幾乎是「半買半送」。如今,這棟官邸的市值據說已經高達數千萬美元。
傳統上,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館的規模和編制都比一般大使館更大,也特別重視門面與排場。館內光是賓士車就有兩輛,在我任內,還有一輛凱迪拉克豪華房車被運回臺灣,成了禮賓司接待外國元首訪臺的專用座車。早些年,駐韓大使回國後經常就升任外交部長,所以,早期駐韓大使一直被視為極為重要的職位。我接任時,已是即將退休的「外交老兵」,雖然仍盡心履行職責,但這個職位已經不像往昔那般重要了。
據時任外交部長錢復先生告訴我,臺韓斷交後,他與房金炎次長商討接任人選時,兩人一致認為我是最適合收拾殘局的人選。錢、房兩位長官都是我在臺大政治系的學弟,也是外交部內多年的同事,對我的個性瞭若指掌。他們覺得我有「逆來順受」的耐性,不知這算不算是一種美德呢?
◆ 韓國人「世界第一」的志氣
韓國人做事向來講究氣魄,不論是煉鋼、造船還是汽車製造,只要確立了目標,就會下定決心「要做就做到世界第一」。我記得有一次參觀韓國現代造船廠,發現他們正在興建號稱全球最大的船塢。雖然那時陽明海運一口氣下了七艘貨櫃船的訂單,但距離填滿這麼龐大的產能仍差得遠。
同行的臺灣官員朋友覺得好奇就問:「你們造這麼大的船塢,真的有足夠的訂單嗎?」沒想到,帶領我們參觀的總經理頭也不回地回答:「放心,我們很快就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造船公司。」
這句話展現韓國人的決心與氣魄,或許在當下聽起來略顯誇張,但也徹底體現韓國人做事的風格─一旦目標確立,信念就絕不動搖。
◆ 四十六年路程,畫下圓滿句點
二○○一年(民國九十年)五月,總統陳水扁同意我告老還鄉。至此,我在外交部及各駐外館處服務累計已達四十六年,最後擔任首屆駐韓國代表也長達七年半。公務員職等早已晉升至最高簡任十四級以上的「特任」階級,外交生涯走到這一刻,總算能畫下完美的句點。
回首往昔,我自認沒有愧對國家與人民的栽培,這份心安讓我倍感欣慰。卸下公職後,我更期待能展開全新的生活,自由自在,去體驗另一種人生的節奏。
回顧這段旅程,我深知自己只是時代洪流中的一名小角色;然而,只要曾經為國家盡一份力,無論成就大小,都足以讓我的生命因此而更為厚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