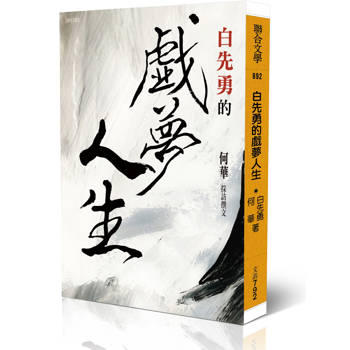前言:小說改編——電影、電視劇、舞臺劇/白先勇
上個世紀當電影這種結合科技與人文的嶄新藝術形式初問世的時候,馬上有人宣稱:小說已走到盡頭,將被電影取代。當然這是危言聳聽,其實,小說的生命依然旺盛,只是形式有所改變。的確,相較之下,有些場面,電影佔優勢。例如大型戰爭、崇山峻嶺的鏡頭,小說平面文字的描寫就不免吃虧。然而小說、電影還是以人為中心,小說對於人物塑造、人性刻畫、心理分析等等就要略勝一籌了。所以小說與電影相生相尅的關係一個多世紀以來糾纏不清,小說改編電影而且成為經典之作的比比皆是。早期如《魂斷威尼斯》,近期如《斷背山》,至於《亂世佳人》獲得十項金像獎,票房至今仍屬冠軍,是小說改編電影最成功的例子。
我從小愛看電影,念大學時,週末有時到西門町電影街去趕兩場,看完新生又去趕萬國,但那時期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部電影卻是在臺北戲院碰巧看到法國大導演亞倫•雷奈的《廣島之戀》。臺北戲院是個老電影院,座椅都是硬木板的,平常只放映日本片,如紅極一時的《請問芳名》。觀眾誤以為《廣島之戀》也是一部日本浪漫苦情片,看到一半,大概覺得不知所云,走掉大半。亞倫•雷奈這部經典之作扎扎實實讓我大吃一驚:原來電影可以這樣拍的!那時我們在臺大外文系辦《現代文學》雜誌,正好引介了詹姆斯•喬伊斯、威廉‧福克納、維珍妮亞•吳爾芙現代主義的作品,而這幾位小說家都是運用意識流內心獨白的高手,剛好與雷乃這部新潮流電影代表作《廣島之戀》接軌。這部電影完全是用女主角內心獨白意識流的手法貫穿全劇,敘述戰爭核爆給人類帶來的殘酷斲傷。德國侵佔法國,女主角卻不顧輿情與德國士兵戀愛,被視為叛國,剃光頭髮,德國戀人則被槍殺。電影故事開始,女主角到日本廣島參加拍攝一部國際反戰、反核爆的影片,與廣島一位已婚日男有一段一夜情,兩個受戰亂重傷的肉體靈魂,在片刻歡悅之間,相濡以沫,昇華了人世間的苦難。我沒有看過比這部更深沉、更哀傷的電影,但看完後得到的訊息和啓示卻是:人與人之間超越種族、國籍以及一切人為阻隔的愛,才是這個紛擾塵世唯一的救贖力量,最後這部電影提升了我們,給了我們精神正能量。
上世紀五○、六○、七○這幾十年,是美國好萊塢、歐洲、日本、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傑出導演、經典之作層出不窮,我在這段時間真是看了不少好電影,有形無形之間,我的成長以及創作,恐怕多少還受到這些電影的影響。五○年代,我在香港念初中的時候,白光、嚴俊主演的《血染海棠紅》上演,紅極一時。我在九龍快樂戲院看到這部電影,當時電影公司為了宣傳,敦請主角明星隨片登臺,我就在快樂看到了白光,她穿著一身火紅晶亮的旗袍,梳了一個鳥窩頭,樂隊敲打起來,白光便進進退退蹋著倫巴舞步,展開她那慵懶低沉的歌喉,唱了一首電影中的插曲:〈東山一把青〉。其實《血染海棠紅》只是一部黑道頭目與妓女之間恩怨情仇的社會寫實片,可是白光唱的〈東山一把青〉這首歌卻深深印在我的記憶里,慢慢醖釀,最後變成了《臺北人》中〈一把青〉那篇小說的源頭,歌詞中有一段:
今朝呀走東門
明朝呀走西口
好像那山水往下流
郎呀,流到幾時方罷休
這首歌好像講中了女主角朱青一生漂泊的命運。抗戰後,白光在上海,她的歌唱出了那個時代的滄桑與悲情,又帶著一點大都市的頹廢。德國籍的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法國巴黎的伊迪絲•琵雅芙(Edith Piaf),她們都唱出了二戰後時代的悲涼。戰爭摧毀了人類的文明,這幾位歌手替眾生發出了心底里無言的哀痛及惶惑。
我有幾篇小說改編成電影:《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玉卿嫂》、《孤戀花》、《孽子》,還有兩部大陸導演拍的《最後的貴族》(謝晉)、《花橋榮記》(謝衍)。《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因為是第一部改編,我差不多全程都參與了,我那時候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既然是由我的小說改編,那麼原著作者便有對電影製作的發言權。後來我才發覺版權一旦賣給電影公司,原著什麼事都不能管了,幸好導演白景瑞脾氣好,任由我攪和。女主角姚煒是我選定的,我在合約里定了一條:女主角人選不經原著同意,影片不得開拍。我知道這部電影全是女主角一個人的戲,人選不對,這部片子就砸掉了。我們選來選去,港臺女演員都排過一遍,還是選不出來。後來我偶爾在一部港片《夜來香》中看到姚煒,我憑直覺就說:就是她!後來姚煒果然把金大班演活了,看過電影的人都說「姚煒就是金大班」。我很慶幸,當初沒有看走眼。
電影最後的主題曲〈最後一夜〉也是我弄出來的,片末金大班跟一個小伙子共舞,想起了她跟第一個大學生情人月如的初戀,這時候襯底的音樂至關重要。我的朋友、新象樊曼儂推薦青年作曲家陳志遠,我們半夜三更到他家去,我跟他描述劇情,希望曲子是首華爾茲,有追憶失落初戀的情懷。陳志遠非常靈光,三天曲子便寫出來了,而且旋律正是我要的。歌詞請慎芝操筆。歌曲我堅持要蔡琴唱,因為她那低沉醇厚的嗓音非常合適這首歌的調子。後來電影上映,最後一場,蔡琴歌聲起處,餘味無窮,給電影大大加分。歌曲〈最後一夜〉爆紅,還得了金馬獎。
我其他小說改編的電影,我就沒有像《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這樣積極參與了。只有《最後的貴族》,導演謝晉非常認真,一九八七年,我第一次重返上海,在復旦大學做訪問教授,謝晉把我關到興國賓館兩個禮拜,討論劇本大綱。白樺的劇本初稿寫好後,謝晉又要我在美國把劇本從頭到尾重寫一次,最後他親自飛到加州聖芭芭拉與我詳細商討,才最後定稿。《最後的貴族》的女主角李彤本來決定是林青霞,林青霞倒是非常合適扮演這位孤高傲世、命運多舛的亂世佳人。林青霞已經飛到上海試過鏡了,可是當時兩岸剛開放,臺灣當局還是把林青霞擋了下來。否則,《最後的貴族》又是別有一番風貌了。
我也有幾篇小說改編成舞臺劇。《遊園驚夢》、《孽子》、《永遠的尹雪艷》、《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花橋榮記》,後三部是大陸導演導的。一九八二年,在臺北國父紀念館上演的《遊園驚夢》是我第一次參與小說改編舞臺劇,於是興致勃勃,不辭勞苦,製作全程大小事都有我一份。這齣劇由新象主辦,主創人員都是當時臺灣一時之選,導演是臺視黃以功、舞美燈光聶光炎、音樂許博允,劇本是我自己寫的。加上董陽孜的書法,滿堂生輝。女主角錢夫人的戲份最重,這個角色好像是專為盧燕量身打造的。盧燕在梅蘭芳家中長大,自幼耳濡目染,一身的京崑氣質,在舞臺上,一舉一動,一顰一笑,把崑曲名伶藍田玉活脫脫地敷演出來。其他硬裡子演員也十分了得:胡錦(天辣椒十三)、歸亞蕾(竇夫人桂枝香)、錢璐(賴夫人)、曹健(錢鵬志錢將軍)、劉德凱(鄭彥青參謀),這一堂演員個個精彩,把一齣三個鐘頭的大戲撐了起來。《遊》劇在國父紀念館演了十場,場場客滿。《遊園驚夢》這齣舞臺劇有幾項破天荒的紀錄,其一是臺灣兩家大報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同時支持資助一項文藝活動,這是前所未有的。其次是編導演全是義務,分文不取。我們當時的確付不起龐大的製作費,可是臺灣頂級的藝術家、熠熠發光的明星演員卻心甘情願為了一個戲劇藝術的理想,每個人都卯足了勁,為《遊》劇賣命。我看到大家那樣認真努力,由衷的感動,覺得臺灣文化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現在回想起來,八○年代的確是臺灣文藝復興的時期,各種藝術奼紫嫣紅開遍。
那時臺灣還在戒嚴時期,舞臺劇的劇本要經過審查的,一開始,《遊園驚夢》劇本審查被卡住了,據說有人指出《遊》劇有影射高層的疑慮。我們場地早已定好,兩個月前十場票兩萬多張一售而空,可是劇本遲遲通不過,我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幾經交涉,最後鬧到政戰部王昇主任那裡,才過了關。
《遊園驚夢》最後一場演完,我一個人獨自站在臺上,面對著兩千五百座位,只剩下四壁悄然的一個偌大戲院,心中不由得湧起一股曲終人散的惆悵。富麗堂皇的舞臺馬上就要撤掉了,一刻鐘前臺上鑼鼓笙簫,衣香鬢影,還是個錦繡世界,頃刻間人去樓空,繁華落盡,真是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孽子》舞臺劇我也涉及頗深,我是該劇的藝術總監兼編劇。劇本是我和施如芳共同創作,臺語部分由她執筆,其餘全是我的構思。我們一開始就做了一個關鍵性的決策:把舞蹈融入劇中,因為《孽子》文本人物眾多,情節複雜,在舞臺劇有限空間時間內難以說得明白,例如新公園孽子們的滄桑史、龍鳳血戀,如果用舞蹈來表現,可以以簡御繁,抽象觀念得以落實,尤其是龍鳳冤孽式的愛情,光靠對白說不清楚。我跟出自雲門的舞蹈家、資深編舞者吳素君仔細商量過後,決定用六段各種不同的舞蹈,因時制宜插入劇中。音樂也是本劇重要構成,我們有陳小霞、張藝這些臺灣重磅級的音樂人掌舵,主題歌是香港林夕寫的詞。整體來說《孽子》舞臺劇具有近乎話劇加歌舞劇的結構。後來《孽子》舞臺劇演出獲得巨大成功,得助於舞蹈、音樂的地方不少,龍鳳血戀那一段舞蹈成為全劇的亮點。我們很幸運找到一位飾演阿鳳的舞者張逸軍,他畢業於北藝大,在太陽馬戲團四年,是「太陽」的明星演員。張逸軍徹頭徹尾就是個野鳳凰,在《孽子》舞臺劇中表現出色。
《孽子》舞臺劇有兩個版本,二○一四年是初版,曹瑞原導演,創作社製作。製作人李慧娜,舞臺設計王孟超,一九八二年舞臺劇《遊園驚夢》我們便合作過,三十二年後,我們再度合作製作一齣大戲,我們三個人的戲緣確實非淺。這一版突出的地方是楊教頭轉性讓唐美雲串演,唐美雲知名度高,帶進不少觀眾。二○二○年,《孽子》舞臺劇第二版上演,這次是由和碩董事長童子賢先生資助的。除了第一版的老演員外,又增加了許多生力軍,龍子由周孝安飾演、阿青由張耀仁飾演,阿鳳還是不可取代的張逸軍。楊教頭還原了原來的性別由廖原慶扮演。吳素君手下的一群青春舞者又換了一批人。素君把龍鳳血戀那場舞蹈加碼升級,一場彩帶舞讓龍鳳一起飛向天空,觀眾大為驚艷。《孽子》這齣戲有一個極不平常的現象,一開幕好像臺上就傳下來一股電流,觸到了觀眾,有幾場觀眾不分族群、老少、性別,一同看得聲淚俱下。劇本是我寫的,我也參加過排演,連我自己也忍不住掉下淚來。其實《孽子》舞臺劇講的是天倫人倫:父子、母子、兄弟、情侶,觸動了基本人性人情,是一首「天倫歌」。奚淞說得好,他說《孽子》是借他人的靈堂,哭自己的滄桑。連他也哭了。導演曹瑞原、編舞吳素君都同時淚崩。二○二○版,從高雄、臺中演到臺北,場場如此。那一堂演員個個稱職,把他們最好的功夫拿了出來。本來三月就要上演,因新冠疫情來襲,延到九月,多出半年排演,共一百場,演員都入戲了,執行導演黃緣文把場次又重新調動了一下,節奏更加緊湊。臺北共演四場,最後一場落幕,所有的演員及主創人員,驟然感到悲欣交集,一方面《孽子》獲得觀眾如此熱烈的反應,當然覺得萬分興奮,但一年多的相處下來,大家休戚與共,已生感情,現在戲演完了,即將拆伙,自然不勝依依。阿鳳張逸軍是性情中人,竟然撲倒在龍子周孝安懷裡痛哭起來,龍子也陪著掉淚,兩人難分難捨,不可開交。其他演員個個都紅了眼眶,《孽子》這齣戲把臺上臺下都「電」到了,我從來沒有看過一齣戲發揮了這樣巨大感人的力量。
我有幾篇小說也改編為電視劇、舞劇、越劇,其中改編形式最多的是《玉卿嫂》。一九八四年,《玉卿嫂》初次拍成電影,張毅執導,楊惠姍主演。這是我的小說改編電影中藝術成就最高的一部,張毅擅長用電影語言塑造人物,心理刻畫細膩深刻,四次照鏡,用鏡子影像把玉卿嫂的內心變化歷歷表現出來。楊惠姍因此片獲得亞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獎。有一次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放映我小說改編的電影,其中包括《玉卿嫂》,楊惠姍受邀出席,她發言道:我演過一百部電影,人家以為我只演過《玉卿嫂》一部。《玉卿嫂》的確是楊惠姍的代表作。電視劇《玉卿嫂》有兩個版本,臺灣版導演是黃以功,女主角徐貴櫻;大陸版也是黃以功導的,女主角是蔣雯麗,慶生一角我推薦範植偉。《玉卿嫂》還改編成舞劇,舒巧編舞。上海徐俊導演把《玉卿嫂》改編成越劇,方亞芬主演。電視劇還有幾部:《孽子》、《孤戀花》、《一把青》,這三部劇的導演都是曹瑞原。每部都得過金鐘獎,其中,以二○○三年《孽子》電視劇的社會影響最大,因為收視率高,公視一連重播五次。大約二○○一年底或二○○二年初,我約了朋友在遠東大飯店樓下咖啡廳見面,朋友遲到,突然曹瑞原走過來跟我打招呼,我那時並不認識曹導,他單刀直入便跟我說公視要他拍一部電視劇,他正在考慮《孽子》改編的畫面,突然在玻璃窗上反映出我的影像來,他本來還以為我人在美國,要設法聯絡我呢,這番巧遇成就了《孽子》這部戲。陳世傑和王詞仰是編劇,劇本大綱我和曹導都參加討論。因為電視劇《孽子》題材敏感,而且是八點檔,社會影響大,拍得不好會破壞同志形象,茲事體大,我對曹導說:如果《孽子》失敗,大家一起去跳海吧!幸虧《孽子》電視劇成功了,非常感人。觀眾的反應正面居多,這是臺灣影視界第一次以同志為主題的二十集長劇。成功的要素之一又是選角選對了。曹瑞原選範植偉飾第一男主角阿青,氣質形貌完全合乎小說人物,其他楊祐寧、張孝全、金勤各有所長。阿鳳馬志翔是我推薦的,同時我也推薦老一輩演員柯俊雄(飾李父)、王珏(飾傅老爺子)。後來《孽子》獲金鐘獎十四項提名,共獲獎七項。導演、劇目都得獎,飾李母的柯淑勤表現優異,獲最佳女主角。范宗沛的音樂非常有名,引起觀眾共鳴。在熱播時,有一位父親因兒子是同志,父子衝突決裂,父親在電視螢幕的跑馬燈上呼籲兒子回家和解。據說,這部八點檔的電視劇影響了許多家庭。
我曾參加好幾次小說改編電影、電視劇、舞臺劇,而深深體會到小說改編成其他藝術形式,欲求其完整精准,太不容易。小說創作是作家一個人的「獨角戲」,是一條孤獨的單行道。影視舞臺作品卻是集體創作,幕前幕後、臺上臺下的工作人員,少則幾十,多則上百,這麼龐大的團體要求人人稱職,難上加難,有時還得碰運氣。我參加製作的一九八二年《遊園驚夢》和二○二○年《孽子》,兩齣舞臺劇運氣好,碰到一群兢兢業業優秀的舞臺工作者、一批出類拔萃燦爛發光的演員,把這兩臺戲演得轟轟烈烈。當年的過程雖然有這樣那樣的挫折焦慮,可是結果如此成功,回想起來,心中還是感到欣慰的。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於臺北
上個世紀當電影這種結合科技與人文的嶄新藝術形式初問世的時候,馬上有人宣稱:小說已走到盡頭,將被電影取代。當然這是危言聳聽,其實,小說的生命依然旺盛,只是形式有所改變。的確,相較之下,有些場面,電影佔優勢。例如大型戰爭、崇山峻嶺的鏡頭,小說平面文字的描寫就不免吃虧。然而小說、電影還是以人為中心,小說對於人物塑造、人性刻畫、心理分析等等就要略勝一籌了。所以小說與電影相生相尅的關係一個多世紀以來糾纏不清,小說改編電影而且成為經典之作的比比皆是。早期如《魂斷威尼斯》,近期如《斷背山》,至於《亂世佳人》獲得十項金像獎,票房至今仍屬冠軍,是小說改編電影最成功的例子。
我從小愛看電影,念大學時,週末有時到西門町電影街去趕兩場,看完新生又去趕萬國,但那時期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部電影卻是在臺北戲院碰巧看到法國大導演亞倫•雷奈的《廣島之戀》。臺北戲院是個老電影院,座椅都是硬木板的,平常只放映日本片,如紅極一時的《請問芳名》。觀眾誤以為《廣島之戀》也是一部日本浪漫苦情片,看到一半,大概覺得不知所云,走掉大半。亞倫•雷奈這部經典之作扎扎實實讓我大吃一驚:原來電影可以這樣拍的!那時我們在臺大外文系辦《現代文學》雜誌,正好引介了詹姆斯•喬伊斯、威廉‧福克納、維珍妮亞•吳爾芙現代主義的作品,而這幾位小說家都是運用意識流內心獨白的高手,剛好與雷乃這部新潮流電影代表作《廣島之戀》接軌。這部電影完全是用女主角內心獨白意識流的手法貫穿全劇,敘述戰爭核爆給人類帶來的殘酷斲傷。德國侵佔法國,女主角卻不顧輿情與德國士兵戀愛,被視為叛國,剃光頭髮,德國戀人則被槍殺。電影故事開始,女主角到日本廣島參加拍攝一部國際反戰、反核爆的影片,與廣島一位已婚日男有一段一夜情,兩個受戰亂重傷的肉體靈魂,在片刻歡悅之間,相濡以沫,昇華了人世間的苦難。我沒有看過比這部更深沉、更哀傷的電影,但看完後得到的訊息和啓示卻是:人與人之間超越種族、國籍以及一切人為阻隔的愛,才是這個紛擾塵世唯一的救贖力量,最後這部電影提升了我們,給了我們精神正能量。
上世紀五○、六○、七○這幾十年,是美國好萊塢、歐洲、日本、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傑出導演、經典之作層出不窮,我在這段時間真是看了不少好電影,有形無形之間,我的成長以及創作,恐怕多少還受到這些電影的影響。五○年代,我在香港念初中的時候,白光、嚴俊主演的《血染海棠紅》上演,紅極一時。我在九龍快樂戲院看到這部電影,當時電影公司為了宣傳,敦請主角明星隨片登臺,我就在快樂看到了白光,她穿著一身火紅晶亮的旗袍,梳了一個鳥窩頭,樂隊敲打起來,白光便進進退退蹋著倫巴舞步,展開她那慵懶低沉的歌喉,唱了一首電影中的插曲:〈東山一把青〉。其實《血染海棠紅》只是一部黑道頭目與妓女之間恩怨情仇的社會寫實片,可是白光唱的〈東山一把青〉這首歌卻深深印在我的記憶里,慢慢醖釀,最後變成了《臺北人》中〈一把青〉那篇小說的源頭,歌詞中有一段:
今朝呀走東門
明朝呀走西口
好像那山水往下流
郎呀,流到幾時方罷休
這首歌好像講中了女主角朱青一生漂泊的命運。抗戰後,白光在上海,她的歌唱出了那個時代的滄桑與悲情,又帶著一點大都市的頹廢。德國籍的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法國巴黎的伊迪絲•琵雅芙(Edith Piaf),她們都唱出了二戰後時代的悲涼。戰爭摧毀了人類的文明,這幾位歌手替眾生發出了心底里無言的哀痛及惶惑。
我有幾篇小說改編成電影:《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玉卿嫂》、《孤戀花》、《孽子》,還有兩部大陸導演拍的《最後的貴族》(謝晉)、《花橋榮記》(謝衍)。《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因為是第一部改編,我差不多全程都參與了,我那時候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既然是由我的小說改編,那麼原著作者便有對電影製作的發言權。後來我才發覺版權一旦賣給電影公司,原著什麼事都不能管了,幸好導演白景瑞脾氣好,任由我攪和。女主角姚煒是我選定的,我在合約里定了一條:女主角人選不經原著同意,影片不得開拍。我知道這部電影全是女主角一個人的戲,人選不對,這部片子就砸掉了。我們選來選去,港臺女演員都排過一遍,還是選不出來。後來我偶爾在一部港片《夜來香》中看到姚煒,我憑直覺就說:就是她!後來姚煒果然把金大班演活了,看過電影的人都說「姚煒就是金大班」。我很慶幸,當初沒有看走眼。
電影最後的主題曲〈最後一夜〉也是我弄出來的,片末金大班跟一個小伙子共舞,想起了她跟第一個大學生情人月如的初戀,這時候襯底的音樂至關重要。我的朋友、新象樊曼儂推薦青年作曲家陳志遠,我們半夜三更到他家去,我跟他描述劇情,希望曲子是首華爾茲,有追憶失落初戀的情懷。陳志遠非常靈光,三天曲子便寫出來了,而且旋律正是我要的。歌詞請慎芝操筆。歌曲我堅持要蔡琴唱,因為她那低沉醇厚的嗓音非常合適這首歌的調子。後來電影上映,最後一場,蔡琴歌聲起處,餘味無窮,給電影大大加分。歌曲〈最後一夜〉爆紅,還得了金馬獎。
我其他小說改編的電影,我就沒有像《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這樣積極參與了。只有《最後的貴族》,導演謝晉非常認真,一九八七年,我第一次重返上海,在復旦大學做訪問教授,謝晉把我關到興國賓館兩個禮拜,討論劇本大綱。白樺的劇本初稿寫好後,謝晉又要我在美國把劇本從頭到尾重寫一次,最後他親自飛到加州聖芭芭拉與我詳細商討,才最後定稿。《最後的貴族》的女主角李彤本來決定是林青霞,林青霞倒是非常合適扮演這位孤高傲世、命運多舛的亂世佳人。林青霞已經飛到上海試過鏡了,可是當時兩岸剛開放,臺灣當局還是把林青霞擋了下來。否則,《最後的貴族》又是別有一番風貌了。
我也有幾篇小說改編成舞臺劇。《遊園驚夢》、《孽子》、《永遠的尹雪艷》、《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花橋榮記》,後三部是大陸導演導的。一九八二年,在臺北國父紀念館上演的《遊園驚夢》是我第一次參與小說改編舞臺劇,於是興致勃勃,不辭勞苦,製作全程大小事都有我一份。這齣劇由新象主辦,主創人員都是當時臺灣一時之選,導演是臺視黃以功、舞美燈光聶光炎、音樂許博允,劇本是我自己寫的。加上董陽孜的書法,滿堂生輝。女主角錢夫人的戲份最重,這個角色好像是專為盧燕量身打造的。盧燕在梅蘭芳家中長大,自幼耳濡目染,一身的京崑氣質,在舞臺上,一舉一動,一顰一笑,把崑曲名伶藍田玉活脫脫地敷演出來。其他硬裡子演員也十分了得:胡錦(天辣椒十三)、歸亞蕾(竇夫人桂枝香)、錢璐(賴夫人)、曹健(錢鵬志錢將軍)、劉德凱(鄭彥青參謀),這一堂演員個個精彩,把一齣三個鐘頭的大戲撐了起來。《遊》劇在國父紀念館演了十場,場場客滿。《遊園驚夢》這齣舞臺劇有幾項破天荒的紀錄,其一是臺灣兩家大報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同時支持資助一項文藝活動,這是前所未有的。其次是編導演全是義務,分文不取。我們當時的確付不起龐大的製作費,可是臺灣頂級的藝術家、熠熠發光的明星演員卻心甘情願為了一個戲劇藝術的理想,每個人都卯足了勁,為《遊》劇賣命。我看到大家那樣認真努力,由衷的感動,覺得臺灣文化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現在回想起來,八○年代的確是臺灣文藝復興的時期,各種藝術奼紫嫣紅開遍。
那時臺灣還在戒嚴時期,舞臺劇的劇本要經過審查的,一開始,《遊園驚夢》劇本審查被卡住了,據說有人指出《遊》劇有影射高層的疑慮。我們場地早已定好,兩個月前十場票兩萬多張一售而空,可是劇本遲遲通不過,我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幾經交涉,最後鬧到政戰部王昇主任那裡,才過了關。
《遊園驚夢》最後一場演完,我一個人獨自站在臺上,面對著兩千五百座位,只剩下四壁悄然的一個偌大戲院,心中不由得湧起一股曲終人散的惆悵。富麗堂皇的舞臺馬上就要撤掉了,一刻鐘前臺上鑼鼓笙簫,衣香鬢影,還是個錦繡世界,頃刻間人去樓空,繁華落盡,真是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孽子》舞臺劇我也涉及頗深,我是該劇的藝術總監兼編劇。劇本是我和施如芳共同創作,臺語部分由她執筆,其餘全是我的構思。我們一開始就做了一個關鍵性的決策:把舞蹈融入劇中,因為《孽子》文本人物眾多,情節複雜,在舞臺劇有限空間時間內難以說得明白,例如新公園孽子們的滄桑史、龍鳳血戀,如果用舞蹈來表現,可以以簡御繁,抽象觀念得以落實,尤其是龍鳳冤孽式的愛情,光靠對白說不清楚。我跟出自雲門的舞蹈家、資深編舞者吳素君仔細商量過後,決定用六段各種不同的舞蹈,因時制宜插入劇中。音樂也是本劇重要構成,我們有陳小霞、張藝這些臺灣重磅級的音樂人掌舵,主題歌是香港林夕寫的詞。整體來說《孽子》舞臺劇具有近乎話劇加歌舞劇的結構。後來《孽子》舞臺劇演出獲得巨大成功,得助於舞蹈、音樂的地方不少,龍鳳血戀那一段舞蹈成為全劇的亮點。我們很幸運找到一位飾演阿鳳的舞者張逸軍,他畢業於北藝大,在太陽馬戲團四年,是「太陽」的明星演員。張逸軍徹頭徹尾就是個野鳳凰,在《孽子》舞臺劇中表現出色。
《孽子》舞臺劇有兩個版本,二○一四年是初版,曹瑞原導演,創作社製作。製作人李慧娜,舞臺設計王孟超,一九八二年舞臺劇《遊園驚夢》我們便合作過,三十二年後,我們再度合作製作一齣大戲,我們三個人的戲緣確實非淺。這一版突出的地方是楊教頭轉性讓唐美雲串演,唐美雲知名度高,帶進不少觀眾。二○二○年,《孽子》舞臺劇第二版上演,這次是由和碩董事長童子賢先生資助的。除了第一版的老演員外,又增加了許多生力軍,龍子由周孝安飾演、阿青由張耀仁飾演,阿鳳還是不可取代的張逸軍。楊教頭還原了原來的性別由廖原慶扮演。吳素君手下的一群青春舞者又換了一批人。素君把龍鳳血戀那場舞蹈加碼升級,一場彩帶舞讓龍鳳一起飛向天空,觀眾大為驚艷。《孽子》這齣戲有一個極不平常的現象,一開幕好像臺上就傳下來一股電流,觸到了觀眾,有幾場觀眾不分族群、老少、性別,一同看得聲淚俱下。劇本是我寫的,我也參加過排演,連我自己也忍不住掉下淚來。其實《孽子》舞臺劇講的是天倫人倫:父子、母子、兄弟、情侶,觸動了基本人性人情,是一首「天倫歌」。奚淞說得好,他說《孽子》是借他人的靈堂,哭自己的滄桑。連他也哭了。導演曹瑞原、編舞吳素君都同時淚崩。二○二○版,從高雄、臺中演到臺北,場場如此。那一堂演員個個稱職,把他們最好的功夫拿了出來。本來三月就要上演,因新冠疫情來襲,延到九月,多出半年排演,共一百場,演員都入戲了,執行導演黃緣文把場次又重新調動了一下,節奏更加緊湊。臺北共演四場,最後一場落幕,所有的演員及主創人員,驟然感到悲欣交集,一方面《孽子》獲得觀眾如此熱烈的反應,當然覺得萬分興奮,但一年多的相處下來,大家休戚與共,已生感情,現在戲演完了,即將拆伙,自然不勝依依。阿鳳張逸軍是性情中人,竟然撲倒在龍子周孝安懷裡痛哭起來,龍子也陪著掉淚,兩人難分難捨,不可開交。其他演員個個都紅了眼眶,《孽子》這齣戲把臺上臺下都「電」到了,我從來沒有看過一齣戲發揮了這樣巨大感人的力量。
我有幾篇小說也改編為電視劇、舞劇、越劇,其中改編形式最多的是《玉卿嫂》。一九八四年,《玉卿嫂》初次拍成電影,張毅執導,楊惠姍主演。這是我的小說改編電影中藝術成就最高的一部,張毅擅長用電影語言塑造人物,心理刻畫細膩深刻,四次照鏡,用鏡子影像把玉卿嫂的內心變化歷歷表現出來。楊惠姍因此片獲得亞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獎。有一次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放映我小說改編的電影,其中包括《玉卿嫂》,楊惠姍受邀出席,她發言道:我演過一百部電影,人家以為我只演過《玉卿嫂》一部。《玉卿嫂》的確是楊惠姍的代表作。電視劇《玉卿嫂》有兩個版本,臺灣版導演是黃以功,女主角徐貴櫻;大陸版也是黃以功導的,女主角是蔣雯麗,慶生一角我推薦範植偉。《玉卿嫂》還改編成舞劇,舒巧編舞。上海徐俊導演把《玉卿嫂》改編成越劇,方亞芬主演。電視劇還有幾部:《孽子》、《孤戀花》、《一把青》,這三部劇的導演都是曹瑞原。每部都得過金鐘獎,其中,以二○○三年《孽子》電視劇的社會影響最大,因為收視率高,公視一連重播五次。大約二○○一年底或二○○二年初,我約了朋友在遠東大飯店樓下咖啡廳見面,朋友遲到,突然曹瑞原走過來跟我打招呼,我那時並不認識曹導,他單刀直入便跟我說公視要他拍一部電視劇,他正在考慮《孽子》改編的畫面,突然在玻璃窗上反映出我的影像來,他本來還以為我人在美國,要設法聯絡我呢,這番巧遇成就了《孽子》這部戲。陳世傑和王詞仰是編劇,劇本大綱我和曹導都參加討論。因為電視劇《孽子》題材敏感,而且是八點檔,社會影響大,拍得不好會破壞同志形象,茲事體大,我對曹導說:如果《孽子》失敗,大家一起去跳海吧!幸虧《孽子》電視劇成功了,非常感人。觀眾的反應正面居多,這是臺灣影視界第一次以同志為主題的二十集長劇。成功的要素之一又是選角選對了。曹瑞原選範植偉飾第一男主角阿青,氣質形貌完全合乎小說人物,其他楊祐寧、張孝全、金勤各有所長。阿鳳馬志翔是我推薦的,同時我也推薦老一輩演員柯俊雄(飾李父)、王珏(飾傅老爺子)。後來《孽子》獲金鐘獎十四項提名,共獲獎七項。導演、劇目都得獎,飾李母的柯淑勤表現優異,獲最佳女主角。范宗沛的音樂非常有名,引起觀眾共鳴。在熱播時,有一位父親因兒子是同志,父子衝突決裂,父親在電視螢幕的跑馬燈上呼籲兒子回家和解。據說,這部八點檔的電視劇影響了許多家庭。
我曾參加好幾次小說改編電影、電視劇、舞臺劇,而深深體會到小說改編成其他藝術形式,欲求其完整精准,太不容易。小說創作是作家一個人的「獨角戲」,是一條孤獨的單行道。影視舞臺作品卻是集體創作,幕前幕後、臺上臺下的工作人員,少則幾十,多則上百,這麼龐大的團體要求人人稱職,難上加難,有時還得碰運氣。我參加製作的一九八二年《遊園驚夢》和二○二○年《孽子》,兩齣舞臺劇運氣好,碰到一群兢兢業業優秀的舞臺工作者、一批出類拔萃燦爛發光的演員,把這兩臺戲演得轟轟烈烈。當年的過程雖然有這樣那樣的挫折焦慮,可是結果如此成功,回想起來,心中還是感到欣慰的。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於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