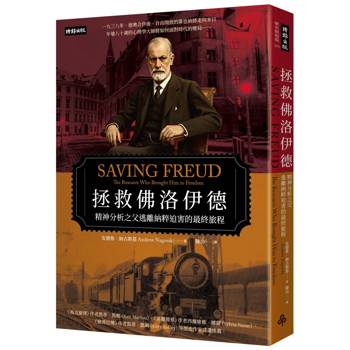第一章 在自由中死去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也就是德軍越過國境進入奧地利三天後,阿道夫.希特勒現身維也納霍夫堡皇宮的陽臺上。在二十五萬民眾的熱烈歡迎下,他宣布奧地利的分離狀態徹底結束了。「從今天起,德國最古老的東部邦,將成為德國最年輕的壁壘。」他這樣說道。「德奧合併」:即把他出生的國家併入第三帝國,是他經常掛在嘴邊的夢想。如今這個夢想終於成為現實,現場的民眾也表現出一片狂喜。從希特勒的軍隊跨過邊境的那一刻起,絕大部分奧地利人民都在歡呼雀躍。
但不是所有人都在為此高興。德軍進入奧地利後,立即展開大規模搜捕,被捕的都是被蓋世太保認定為反納粹分子的人。與此同時,他們還掀起了一波反猶太暴力運動。當地的猶太人慘遭毆打、殺害,他們的商店被洗劫一空,更有不少人選擇了自殺。彼時正在維也納的德國劇作家卡爾.楚克邁耶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整座城市變成了傑洛姆斯.波希畫筆下的夢魘……他們在維也納釋放出了洶湧的嫉妒、仇恨,以及盲目的、惡毒的復仇心……這是屬於暴徒的女巫安息日。人類的所有尊嚴在此被統統埋葬。」
當時的西格蒙德.佛洛伊德正住在伯格街十九號,那裡既是他多年來的居所,也是他的辦公場所。德軍佔領剛開始,佛洛伊德就在日記中寫下一句話:「奧地利的末日。」這位精神分析之父在四歲之後就一直生活在這座奧地利的首都。如今,眼看著八十二歲生日即將到來,佛洛伊德卻發現自己身處一個逐漸展開的噩夢之中。身為一名猶太人,他自然面臨著危險。精神分析被大部分納粹官員譴責為是猶太偽科學,而作為這一學科的代表人物,沒人知道等待他的會是什麼。
佛洛伊德第一時間成為了被騷擾了對象。就在希特勒在附近做演講的同一天,納粹暴徒同時闖進了佛洛伊德的公寓和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這家出版社位於離佛洛伊德住所不遠的伯格街七號,專門出版佛洛伊德及其同事的作品。在公寓裡,面對這群不速之客,佛洛伊德的妻子瑪莎試圖以禮服人,她掏出手頭僅有鈔票遞給他們說:「先生們,請自便吧。」隨後,佛洛伊德夫婦最小的女兒安娜又把「客人們」領進另一個房間,取出了保險箱裡全部的六千先令(約合八百四十美元),並全數交給他們。
突然間,佛洛伊德出現了。他一言不發,只是怒視著闖入者。暴徒們顯然被他的威嚴鎮住了,他們稱呼他為「教授」,然後帶著戰利品撤出了公寓,臨走時還不忘叫囂他們會再次光顧。在他們離開後,佛洛伊德詢問,那幫人拿走了多少錢。得知答案後,佛洛伊德泰然自若,只是半開玩笑地說:「我出一次診都拿不到這麼多錢。」
但是這裡發生的事情並非可以一笑了之,在附近的「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也是一樣。當時,佛洛伊德的大兒子馬丁正在出版社銷毀一切可能被納粹當作罪證以迫害他父親的檔案。馬丁後來回憶稱,十幾名「打扮寒酸」的暴徒突然闖進來,用步槍抵著他的肚子,把他囚禁了幾個小時。其中一名男子還耀武揚威地掏出一把手槍大喊:「咱們幹嘛不斃了他?咱們應該當場斃了他!」
在混亂開始的第一天,這些闖入者似乎不太確定自己的任務是什麼,也沒人知道他們是聽從誰的命令。馬丁以肚子痛為由說要上廁所,並趁機把好幾份檔案沖進了馬桶,他們居然都沒有發現。直至當天傍晚,所有的納粹才全都撤走,並叫囂下次再來徹底搜查。
馬丁回到公寓,和父母與妹妹團聚,一家人這才稍微鬆一口氣。安娜表現得尤其悲觀。她問父親:「要是我們一起自殺會不會更好?」佛洛伊德一針見血地告訴大家,他完全沒有這種想法。他說:「為什麼?那豈不是讓他們得逞了?」
但是他面臨的困境--以及極為不明朗的前景--讓人不禁好奇:佛洛伊德為何心甘情願留在這個水深火熱的環境之中?他為什麼沒有在可以離開的時候及時離開維也納?
以及,為什麼在三月十五日,當這幫納粹強盜離開他的住處並叫囂著還會回來時,佛洛伊德依然不願意採取行動?馬丁在出版社被釋放後,便立刻回家查看父母的情況。他寫道:「儘管遭遇嚴酷考驗,但我不認為父親有任何離開奧地利的念頭。」。相反,佛洛伊德希望能「挺過風暴」,期待「社會秩序能夠恢復,本分之人能夠遠離恐懼,重回正常生活」。
諷刺的是,佛洛伊德應該最清楚邪惡勢力正在把他的世界一步步推向屠殺與毀滅。在一九三○年的著名文章〈文明及其不滿〉中,佛洛伊德就探討了人類的「殘忍與侵略性」,它「會自發地表現出來,展現出人類其實是野獸,而憐憫同族才是異常的行為」。他特別提到猶太人經常為他人「提供服務」,扮演這種原始欲望的發洩對象。
彼時,佛洛伊德的人生已經經歷了奧匈帝國的滅亡、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二戰之前的肅殺,因此,他對於政治動盪和反猶太主義絕不陌生。對他來說,反猶太主義不是什麼湧動的暗流,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態。一方面,他深知這種不穩定的狀態隨時可能爆發,威脅著他和家人的安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拒絕接受現實。因為長年嗜抽雪茄,佛洛伊德的下頜患上癌症,令他苦不堪言。他很清楚自己時日無多,因此迫切渴望能夠在平靜的生活中度完餘生,而不想要四處輾轉、顛沛流離。
但是,阻止他逃離的不只是衰老與疾病。佛洛伊德對維也納有著深厚的感情。因為數百年來,維也納一直是歐洲的文化生活中心,同時也是一個猶太人中心。在這個蓬勃發展的猶太群體中,出現了像古斯塔夫.馬勒和阿諾.荀伯格這樣的作曲家,也有像史蒂芬.茨威格、弗朗茨.韋爾弗和約瑟夫.羅特這樣的作家,以及各式各樣的物理學家、醫生,當然,還有其他同時代的頂尖心理學家。這些人當中,絕大部分佛洛伊德都認識或者至少接觸過。
佛洛伊德的世界中心就是伯格街十九號。在這裡,他和瑪莎把六個孩子撫養成人。也是在這裡,他接診病人、寫文章、寫書,並且在每週三晚和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成員定期見面。他有許多數十年如一日的老習慣,比如晚上在環城大道散步,或是去市裡最有名的咖啡館裡抽雪茄、看報紙。簡而言之,他既是一名革命性思想家,同時又恪守德國人所說Ordnung muss sein,翻譯過來的大致意思就是「必須要有秩序」。放在第三帝國的語境下,這句話可能會有極其邪惡的含義,但是在戰前的維也納,它是可以和包容的社會環境以及佛洛伊德對禁忌話題的不懈探索共存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也就是德軍越過國境進入奧地利三天後,阿道夫.希特勒現身維也納霍夫堡皇宮的陽臺上。在二十五萬民眾的熱烈歡迎下,他宣布奧地利的分離狀態徹底結束了。「從今天起,德國最古老的東部邦,將成為德國最年輕的壁壘。」他這樣說道。「德奧合併」:即把他出生的國家併入第三帝國,是他經常掛在嘴邊的夢想。如今這個夢想終於成為現實,現場的民眾也表現出一片狂喜。從希特勒的軍隊跨過邊境的那一刻起,絕大部分奧地利人民都在歡呼雀躍。
但不是所有人都在為此高興。德軍進入奧地利後,立即展開大規模搜捕,被捕的都是被蓋世太保認定為反納粹分子的人。與此同時,他們還掀起了一波反猶太暴力運動。當地的猶太人慘遭毆打、殺害,他們的商店被洗劫一空,更有不少人選擇了自殺。彼時正在維也納的德國劇作家卡爾.楚克邁耶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整座城市變成了傑洛姆斯.波希畫筆下的夢魘……他們在維也納釋放出了洶湧的嫉妒、仇恨,以及盲目的、惡毒的復仇心……這是屬於暴徒的女巫安息日。人類的所有尊嚴在此被統統埋葬。」
當時的西格蒙德.佛洛伊德正住在伯格街十九號,那裡既是他多年來的居所,也是他的辦公場所。德軍佔領剛開始,佛洛伊德就在日記中寫下一句話:「奧地利的末日。」這位精神分析之父在四歲之後就一直生活在這座奧地利的首都。如今,眼看著八十二歲生日即將到來,佛洛伊德卻發現自己身處一個逐漸展開的噩夢之中。身為一名猶太人,他自然面臨著危險。精神分析被大部分納粹官員譴責為是猶太偽科學,而作為這一學科的代表人物,沒人知道等待他的會是什麼。
佛洛伊德第一時間成為了被騷擾了對象。就在希特勒在附近做演講的同一天,納粹暴徒同時闖進了佛洛伊德的公寓和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這家出版社位於離佛洛伊德住所不遠的伯格街七號,專門出版佛洛伊德及其同事的作品。在公寓裡,面對這群不速之客,佛洛伊德的妻子瑪莎試圖以禮服人,她掏出手頭僅有鈔票遞給他們說:「先生們,請自便吧。」隨後,佛洛伊德夫婦最小的女兒安娜又把「客人們」領進另一個房間,取出了保險箱裡全部的六千先令(約合八百四十美元),並全數交給他們。
突然間,佛洛伊德出現了。他一言不發,只是怒視著闖入者。暴徒們顯然被他的威嚴鎮住了,他們稱呼他為「教授」,然後帶著戰利品撤出了公寓,臨走時還不忘叫囂他們會再次光顧。在他們離開後,佛洛伊德詢問,那幫人拿走了多少錢。得知答案後,佛洛伊德泰然自若,只是半開玩笑地說:「我出一次診都拿不到這麼多錢。」
但是這裡發生的事情並非可以一笑了之,在附近的「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也是一樣。當時,佛洛伊德的大兒子馬丁正在出版社銷毀一切可能被納粹當作罪證以迫害他父親的檔案。馬丁後來回憶稱,十幾名「打扮寒酸」的暴徒突然闖進來,用步槍抵著他的肚子,把他囚禁了幾個小時。其中一名男子還耀武揚威地掏出一把手槍大喊:「咱們幹嘛不斃了他?咱們應該當場斃了他!」
在混亂開始的第一天,這些闖入者似乎不太確定自己的任務是什麼,也沒人知道他們是聽從誰的命令。馬丁以肚子痛為由說要上廁所,並趁機把好幾份檔案沖進了馬桶,他們居然都沒有發現。直至當天傍晚,所有的納粹才全都撤走,並叫囂下次再來徹底搜查。
馬丁回到公寓,和父母與妹妹團聚,一家人這才稍微鬆一口氣。安娜表現得尤其悲觀。她問父親:「要是我們一起自殺會不會更好?」佛洛伊德一針見血地告訴大家,他完全沒有這種想法。他說:「為什麼?那豈不是讓他們得逞了?」
但是他面臨的困境--以及極為不明朗的前景--讓人不禁好奇:佛洛伊德為何心甘情願留在這個水深火熱的環境之中?他為什麼沒有在可以離開的時候及時離開維也納?
以及,為什麼在三月十五日,當這幫納粹強盜離開他的住處並叫囂著還會回來時,佛洛伊德依然不願意採取行動?馬丁在出版社被釋放後,便立刻回家查看父母的情況。他寫道:「儘管遭遇嚴酷考驗,但我不認為父親有任何離開奧地利的念頭。」。相反,佛洛伊德希望能「挺過風暴」,期待「社會秩序能夠恢復,本分之人能夠遠離恐懼,重回正常生活」。
諷刺的是,佛洛伊德應該最清楚邪惡勢力正在把他的世界一步步推向屠殺與毀滅。在一九三○年的著名文章〈文明及其不滿〉中,佛洛伊德就探討了人類的「殘忍與侵略性」,它「會自發地表現出來,展現出人類其實是野獸,而憐憫同族才是異常的行為」。他特別提到猶太人經常為他人「提供服務」,扮演這種原始欲望的發洩對象。
彼時,佛洛伊德的人生已經經歷了奧匈帝國的滅亡、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二戰之前的肅殺,因此,他對於政治動盪和反猶太主義絕不陌生。對他來說,反猶太主義不是什麼湧動的暗流,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態。一方面,他深知這種不穩定的狀態隨時可能爆發,威脅著他和家人的安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拒絕接受現實。因為長年嗜抽雪茄,佛洛伊德的下頜患上癌症,令他苦不堪言。他很清楚自己時日無多,因此迫切渴望能夠在平靜的生活中度完餘生,而不想要四處輾轉、顛沛流離。
但是,阻止他逃離的不只是衰老與疾病。佛洛伊德對維也納有著深厚的感情。因為數百年來,維也納一直是歐洲的文化生活中心,同時也是一個猶太人中心。在這個蓬勃發展的猶太群體中,出現了像古斯塔夫.馬勒和阿諾.荀伯格這樣的作曲家,也有像史蒂芬.茨威格、弗朗茨.韋爾弗和約瑟夫.羅特這樣的作家,以及各式各樣的物理學家、醫生,當然,還有其他同時代的頂尖心理學家。這些人當中,絕大部分佛洛伊德都認識或者至少接觸過。
佛洛伊德的世界中心就是伯格街十九號。在這裡,他和瑪莎把六個孩子撫養成人。也是在這裡,他接診病人、寫文章、寫書,並且在每週三晚和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成員定期見面。他有許多數十年如一日的老習慣,比如晚上在環城大道散步,或是去市裡最有名的咖啡館裡抽雪茄、看報紙。簡而言之,他既是一名革命性思想家,同時又恪守德國人所說Ordnung muss sein,翻譯過來的大致意思就是「必須要有秩序」。放在第三帝國的語境下,這句話可能會有極其邪惡的含義,但是在戰前的維也納,它是可以和包容的社會環境以及佛洛伊德對禁忌話題的不懈探索共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