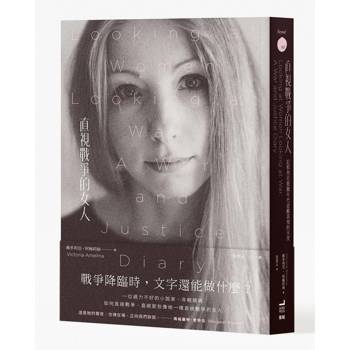我剛在利沃夫市中心買了人生第一把槍。我聽說,每個人都有殺人的能力,而那些說自己沒有殺人能力的人,只是還沒遇到對的人罷了。持槍進入我的國家的陌生人,很可能就是那個「對的人」。
我的新槍躺在床上,既漆黑又危險,擺在我所有的泳衣和鮮豔的夏裝當中。之後回來時可能會需要它。但現在還不用。現在,我要去埃及度假一週。
「我們會在2月24日回到烏克蘭,然後我就會開始練習射擊。」我向我兒子解釋。以他的年紀來說,他在過去幾個月看了太多新聞,但一點也不害怕入侵。
我把槍放進保險箱,把泳衣放入行李箱。
*
返回烏克蘭的班機預計於2022年2月24日早上七點起飛。當我們搭計程車前往機場時,埃及的天空還很黑。在幾乎有一半是空房的海邊旅館,所有人似乎都還安然睡著,我決定不倚靠行李箱的輪子,而是提起行李箱走過未開燈的平房,如此一來就不會有人被我吵醒。也或許我只是想聽聽世界的寧靜,彷彿我知道世界將永遠改變。
埃及和烏克蘭現在都是凌晨四點。我抬頭一看:天空清澈,大熊座在頭頂上閃爍光芒。其他星座也是如此,我只是不認得。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星空是在盧甘斯克,那年我五歲。我們當時住在利沃夫,那裡的光害太嚴重,無法看清星星,也無法學會辨認星座。在盧甘斯克,我們拜訪的親戚住在一棟房子裡,那棟房子位處一條夜色黑到可以看見天上所有星星的街道。當時在盧甘斯克,有人帶著五歲的我去看了大熊座。或許那人是我媽媽。總之滿是星星的天空成了我對這座城市的回憶。星星代表我的童年和盧甘斯克。我長大,盧甘斯克在2014年被俄羅斯占領,世界改變了,但我還沒有學會辨認其他星座。2月24日也不是什麼學習星座知識的好日子。
我叫我兒子動作快點。如果我們錯過班機,就會被困在埃及──埃及很美,但對於不懂阿拉伯語的家庭來說,旅行起來可不容易。
穿越沙漠途中,我嘗試讀新聞。網路還是很差,幾乎連不到。儘管盡了一切努力,我只收到一則訊息,很簡短,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線傳回的電報。上面只寫著:「基輔發生爆炸。」
我倒抽一口氣。這一定是搞錯了。當你害怕的時候,許多聲音聽起來都像是遠方的爆炸聲。那如果這些只是煙火,只是某人開的玩笑呢?我們最近讀到太多可怕的新聞,我們不再仰望星星,而是看著落在碎磚堆裡的玩具。我們想盡所有錯誤的事,許下了錯誤的願望。爆炸也可能有各種解釋。如果是瓦斯氣爆呢?氣爆還有可能發生,轟炸歐洲國家的首都則否。我的意思是,再也不可能了。永遠不再,對吧?
「看得到窗外的星星嗎?」我問我兒子。
「看不到。」他回答。他太睏了。
「我可以看到大熊座喔。」我說了謊,才讓他繼續嘗試觀看星座,儘管我的手機螢幕在窗上投下刺眼的光,而我試著聯絡我們在烏克蘭的家人與朋友。我不太記得我傳訊息或打電話給誰了,反正大多沒有成功。沙漠一望無際。
「噢,我看到了!」我的孩子對著大熊座喊道。
我們向司機道謝,接著衝進機場航廈。我們到家之後,一切都會明朗。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一進到航廈,埃及的地勤人員就這麼問我。我沒有馬上回答,所以他不斷重複詢問,好像在幫助我了解:「你不能回你的國家。」
「你不能回你的國家。」
我想我能,而且我會。我急忙看向藍色螢幕上的起飛時間。這將暫時是我最後一次於這樣的螢幕上看到烏克蘭的城市:利沃夫、基輔、哈爾基夫。我會在每座機場的藍螢幕上尋找,希望這場噩夢終將結束。
一小時後,我們是唯一還留在埃及馬薩阿拉姆小機場沒走的旅客。一群絕望的烏克蘭人離開了航廈,前往旅行社安排的巴士。這些烏克蘭人要被帶往隨機挑選的旅館,如此一來他們就不會妨礙那些來自更快樂國家的旅客登機。我自行訂了旅館和航班,也沒有和任何旅行社簽約。因此當所有人登上巴士時,我們留了下來。機場人員要求我們離開。
「你們不能待在這裡。」一位穿著機場人員制服的男人又說了一次。顯然,他喜歡說重複的話。
我解釋我們沒有其他地方可去,但他似乎並不明白。
「好吧,你們可以坐在入口這附近。」
我向他道謝,接著坐在地板上,開始查詢航班。
當你知道無情的敵人正在攻擊你所愛的城市,自己卻被困在空無一人的異國機場裡,會是什麼感覺?我的感覺是混合了憤怒、悲傷和⋯⋯如釋重負。是的,我也感到如釋重負。有這樣的感覺似乎很可恥,但又無可避免,而我為自己辯解,想著自己不是唯一一個在末日戰爭開打時,除了絕望或憤怒之外,還懷抱其他感覺的作家。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生於立陶宛的波蘭詩人,同時也是諾貝爾獎得主,他曾描述自己在1939年納粹德國與蘇聯攻擊波蘭時的感受。「不再需要說些無意義的話了,」他寫道,「長久以來令人懼怕的滿足感讓我們擺脫了自我安慰的謊言、幻想與詭計;不透明的事物終於變得透明了。」
我曾經在克拉科夫(Kraków)碰巧買下米沃什的書,而我現在正拚命地找尋飛往那座城市的票,坐在空無一人的航廈地板上。米沃什如釋重負的原因和我不一樣,但我同意他的主要論點:不再需要說些無意義的話了。
*
要找到從埃及起飛出發的機票並不容易,即使我不太在意目的地,只要是歐洲就可以。最終,我找到了飛往布拉格的機票。雖然機票貴得離譜,但我一天也不想多待──棕櫚樹、游泳池,以及全然放鬆的氣氛,與烏克蘭的現況反差太大。我需要回家。
在機場,來自歐盟國家的公民辦理布拉格航班的登機手續,並前往管制區。與此同時,所有的烏克蘭公民都被要求等候。我能認出夾雜在捷克人當中的烏克蘭人,不用看他們的護照,也不用聽他們說話。我們看起來不再像觀光客了。我們都已經是另一類人:難民、軍人,或者介在兩者之間的某種人。我們還不知道自己是誰。
我們嘗試在報到櫃檯解釋,烏克蘭人多年來都可以免簽證前往歐盟國家。因此,我們可以像如往常般進入捷克共和國,就像觀光客。但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們不再是觀光客。
夜晚的機場並不是解釋「烏克蘭是歐洲一部分」的好地方,而這個用於烏克蘭尊嚴革命的口號也許便是俄羅斯入侵的根本原因。這論點行不通。沒有人必須讓我們進去。
與此同時,第一批難民從烏克蘭越過陸地國界,前往波蘭、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摩爾多瓦。但我對此一無所知。我們等待布拉格的決定約一小時,討論有關某位烏克蘭人的謠言,那人在當天早些時候不被允許登上飛往德國的航班。
「如果他們不讓我們進去呢?」我十歲的兒子問我。
我不知道答案。我記得我看過的所有關於不被歡迎的難民新聞和紀錄片,以及2004年由湯姆・漢克(Tom Hanks)主演的美國喜劇電影《航站情緣》(The Terminal)。漢克所飾演的角色就被困在紐約的約翰・甘迺迪機場的航廈裡,既無法返回故鄉,也無法進入美國,被困在兩者之間,就像我們一樣。
一小時之後,我們收到了判決:「你們可以登機了。」
我仍然擔心著陸後的邊境管制問題。但被困在布拉格機場可能會比在埃及容易一點。我們的語言相近,而且據我記憶所及,布拉格的航廈內有許多咖啡店。
在布拉格機場,邊境管制人員是一名年輕女性,她瞥了我的護照一眼,接著就一直盯著我看。比起我護照上的資訊,她似乎對我臉上的表情更感興趣。也許她是新到職的,也從未見過他人的國家遭到轟炸。也許她不是在看我,而是在看戰爭。她在我們的護照上蓋章,沒有問任何問題。我點了點頭,也一聲不吭地接過護照。我無法說出「謝謝」這兩個字。我在抽泣。
「媽媽,你為什麼在哭?」我兒子問。
「因為我們到家了。」我說。
「但這裡不是烏克蘭。」他困惑地說。
「這裡是歐洲。」我回答,就好像「歐洲」一詞是個能向我兒子說明一切的通關密碼。當然,不是這麼一回事。接下來幾天內,所謂「歐洲」將被重新定義。世界正在轉變,詞彙的意義也在改變:從我說不出「戰爭」這個字、我兒子的安靜,以及捷克邊境管制人員的目光中,我感受到了這一點。我哭泣不只是因為我們被放行,而是因為人們在看我時,開始看到的似乎不是我,而是戰爭。我就是戰爭。我們烏克蘭人都變成了戰爭。關於我們的一切現在都不重要了,只有戰爭──那剛剛才發生的災難。
我買了前往波蘭的火車票。穿過憂慮的歐洲,我要回烏克蘭的家。在那裡,我會是身處戰爭之中的人,而非戰爭本身。
當然,我的兒子不會跟我一起走。我們將要分別。但他還不知道這件事。
我的新槍躺在床上,既漆黑又危險,擺在我所有的泳衣和鮮豔的夏裝當中。之後回來時可能會需要它。但現在還不用。現在,我要去埃及度假一週。
「我們會在2月24日回到烏克蘭,然後我就會開始練習射擊。」我向我兒子解釋。以他的年紀來說,他在過去幾個月看了太多新聞,但一點也不害怕入侵。
我把槍放進保險箱,把泳衣放入行李箱。
*
返回烏克蘭的班機預計於2022年2月24日早上七點起飛。當我們搭計程車前往機場時,埃及的天空還很黑。在幾乎有一半是空房的海邊旅館,所有人似乎都還安然睡著,我決定不倚靠行李箱的輪子,而是提起行李箱走過未開燈的平房,如此一來就不會有人被我吵醒。也或許我只是想聽聽世界的寧靜,彷彿我知道世界將永遠改變。
埃及和烏克蘭現在都是凌晨四點。我抬頭一看:天空清澈,大熊座在頭頂上閃爍光芒。其他星座也是如此,我只是不認得。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星空是在盧甘斯克,那年我五歲。我們當時住在利沃夫,那裡的光害太嚴重,無法看清星星,也無法學會辨認星座。在盧甘斯克,我們拜訪的親戚住在一棟房子裡,那棟房子位處一條夜色黑到可以看見天上所有星星的街道。當時在盧甘斯克,有人帶著五歲的我去看了大熊座。或許那人是我媽媽。總之滿是星星的天空成了我對這座城市的回憶。星星代表我的童年和盧甘斯克。我長大,盧甘斯克在2014年被俄羅斯占領,世界改變了,但我還沒有學會辨認其他星座。2月24日也不是什麼學習星座知識的好日子。
我叫我兒子動作快點。如果我們錯過班機,就會被困在埃及──埃及很美,但對於不懂阿拉伯語的家庭來說,旅行起來可不容易。
穿越沙漠途中,我嘗試讀新聞。網路還是很差,幾乎連不到。儘管盡了一切努力,我只收到一則訊息,很簡短,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線傳回的電報。上面只寫著:「基輔發生爆炸。」
我倒抽一口氣。這一定是搞錯了。當你害怕的時候,許多聲音聽起來都像是遠方的爆炸聲。那如果這些只是煙火,只是某人開的玩笑呢?我們最近讀到太多可怕的新聞,我們不再仰望星星,而是看著落在碎磚堆裡的玩具。我們想盡所有錯誤的事,許下了錯誤的願望。爆炸也可能有各種解釋。如果是瓦斯氣爆呢?氣爆還有可能發生,轟炸歐洲國家的首都則否。我的意思是,再也不可能了。永遠不再,對吧?
「看得到窗外的星星嗎?」我問我兒子。
「看不到。」他回答。他太睏了。
「我可以看到大熊座喔。」我說了謊,才讓他繼續嘗試觀看星座,儘管我的手機螢幕在窗上投下刺眼的光,而我試著聯絡我們在烏克蘭的家人與朋友。我不太記得我傳訊息或打電話給誰了,反正大多沒有成功。沙漠一望無際。
「噢,我看到了!」我的孩子對著大熊座喊道。
我們向司機道謝,接著衝進機場航廈。我們到家之後,一切都會明朗。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一進到航廈,埃及的地勤人員就這麼問我。我沒有馬上回答,所以他不斷重複詢問,好像在幫助我了解:「你不能回你的國家。」
「你不能回你的國家。」
我想我能,而且我會。我急忙看向藍色螢幕上的起飛時間。這將暫時是我最後一次於這樣的螢幕上看到烏克蘭的城市:利沃夫、基輔、哈爾基夫。我會在每座機場的藍螢幕上尋找,希望這場噩夢終將結束。
一小時後,我們是唯一還留在埃及馬薩阿拉姆小機場沒走的旅客。一群絕望的烏克蘭人離開了航廈,前往旅行社安排的巴士。這些烏克蘭人要被帶往隨機挑選的旅館,如此一來他們就不會妨礙那些來自更快樂國家的旅客登機。我自行訂了旅館和航班,也沒有和任何旅行社簽約。因此當所有人登上巴士時,我們留了下來。機場人員要求我們離開。
「你們不能待在這裡。」一位穿著機場人員制服的男人又說了一次。顯然,他喜歡說重複的話。
我解釋我們沒有其他地方可去,但他似乎並不明白。
「好吧,你們可以坐在入口這附近。」
我向他道謝,接著坐在地板上,開始查詢航班。
當你知道無情的敵人正在攻擊你所愛的城市,自己卻被困在空無一人的異國機場裡,會是什麼感覺?我的感覺是混合了憤怒、悲傷和⋯⋯如釋重負。是的,我也感到如釋重負。有這樣的感覺似乎很可恥,但又無可避免,而我為自己辯解,想著自己不是唯一一個在末日戰爭開打時,除了絕望或憤怒之外,還懷抱其他感覺的作家。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生於立陶宛的波蘭詩人,同時也是諾貝爾獎得主,他曾描述自己在1939年納粹德國與蘇聯攻擊波蘭時的感受。「不再需要說些無意義的話了,」他寫道,「長久以來令人懼怕的滿足感讓我們擺脫了自我安慰的謊言、幻想與詭計;不透明的事物終於變得透明了。」
我曾經在克拉科夫(Kraków)碰巧買下米沃什的書,而我現在正拚命地找尋飛往那座城市的票,坐在空無一人的航廈地板上。米沃什如釋重負的原因和我不一樣,但我同意他的主要論點:不再需要說些無意義的話了。
*
要找到從埃及起飛出發的機票並不容易,即使我不太在意目的地,只要是歐洲就可以。最終,我找到了飛往布拉格的機票。雖然機票貴得離譜,但我一天也不想多待──棕櫚樹、游泳池,以及全然放鬆的氣氛,與烏克蘭的現況反差太大。我需要回家。
在機場,來自歐盟國家的公民辦理布拉格航班的登機手續,並前往管制區。與此同時,所有的烏克蘭公民都被要求等候。我能認出夾雜在捷克人當中的烏克蘭人,不用看他們的護照,也不用聽他們說話。我們看起來不再像觀光客了。我們都已經是另一類人:難民、軍人,或者介在兩者之間的某種人。我們還不知道自己是誰。
我們嘗試在報到櫃檯解釋,烏克蘭人多年來都可以免簽證前往歐盟國家。因此,我們可以像如往常般進入捷克共和國,就像觀光客。但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們不再是觀光客。
夜晚的機場並不是解釋「烏克蘭是歐洲一部分」的好地方,而這個用於烏克蘭尊嚴革命的口號也許便是俄羅斯入侵的根本原因。這論點行不通。沒有人必須讓我們進去。
與此同時,第一批難民從烏克蘭越過陸地國界,前往波蘭、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摩爾多瓦。但我對此一無所知。我們等待布拉格的決定約一小時,討論有關某位烏克蘭人的謠言,那人在當天早些時候不被允許登上飛往德國的航班。
「如果他們不讓我們進去呢?」我十歲的兒子問我。
我不知道答案。我記得我看過的所有關於不被歡迎的難民新聞和紀錄片,以及2004年由湯姆・漢克(Tom Hanks)主演的美國喜劇電影《航站情緣》(The Terminal)。漢克所飾演的角色就被困在紐約的約翰・甘迺迪機場的航廈裡,既無法返回故鄉,也無法進入美國,被困在兩者之間,就像我們一樣。
一小時之後,我們收到了判決:「你們可以登機了。」
我仍然擔心著陸後的邊境管制問題。但被困在布拉格機場可能會比在埃及容易一點。我們的語言相近,而且據我記憶所及,布拉格的航廈內有許多咖啡店。
在布拉格機場,邊境管制人員是一名年輕女性,她瞥了我的護照一眼,接著就一直盯著我看。比起我護照上的資訊,她似乎對我臉上的表情更感興趣。也許她是新到職的,也從未見過他人的國家遭到轟炸。也許她不是在看我,而是在看戰爭。她在我們的護照上蓋章,沒有問任何問題。我點了點頭,也一聲不吭地接過護照。我無法說出「謝謝」這兩個字。我在抽泣。
「媽媽,你為什麼在哭?」我兒子問。
「因為我們到家了。」我說。
「但這裡不是烏克蘭。」他困惑地說。
「這裡是歐洲。」我回答,就好像「歐洲」一詞是個能向我兒子說明一切的通關密碼。當然,不是這麼一回事。接下來幾天內,所謂「歐洲」將被重新定義。世界正在轉變,詞彙的意義也在改變:從我說不出「戰爭」這個字、我兒子的安靜,以及捷克邊境管制人員的目光中,我感受到了這一點。我哭泣不只是因為我們被放行,而是因為人們在看我時,開始看到的似乎不是我,而是戰爭。我就是戰爭。我們烏克蘭人都變成了戰爭。關於我們的一切現在都不重要了,只有戰爭──那剛剛才發生的災難。
我買了前往波蘭的火車票。穿過憂慮的歐洲,我要回烏克蘭的家。在那裡,我會是身處戰爭之中的人,而非戰爭本身。
當然,我的兒子不會跟我一起走。我們將要分別。但他還不知道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