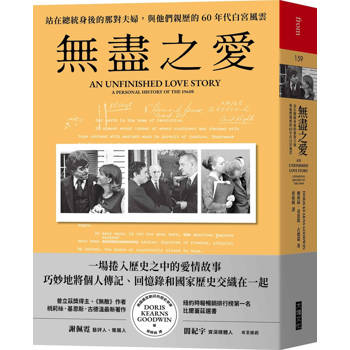序章(節選)
一九七二年六月某天早晨,當我踏進哈佛大學奧本山街(Mt. Auburn Street)七十八號的辦公室時,整個房間洋溢一股興奮的氛圍。理查.「迪克」.古德溫(Richard “Dick” Goodwin)剛在我們那棟老舊的黃色建築三樓租了一間辦公室,準備完成一本書。我們都知道他是誰:他二十多歲時曾在約翰.甘迺迪(John Kennedy) 政府任職,並在「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計畫鼎盛時期擔任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 的首席文膽。後來羅伯特.「巴比」.甘迺迪(Robert “Bobby” Kennedy)在加州遇害身亡時,他也在場。一位認識他的人說,他是其見過最聰明、最有趣的人,但有時也顯得輕率、善變且傲慢─總之,他是一名耀眼且難以捉摸的人物。
我剛在樓梯盡頭的辦公室裡坐下,迪克便閒晃進來,一屁股坐在我給學生準備的椅子上。他的外表立刻引起我的注意:一頭蓬亂的黑色捲髮、濃密而凌亂的眉毛、滿臉的坑疤,幾根大雪茄從他的休閒襯衫口袋探出頭來。他自我介紹後,問我是否是研究生。「不,我是助理教授。」我反駁道。「我在教一門關於美國總統的課程,還主持研討會和輔導課。」
「我知道,我知道!」他笑著舉起雙手打斷我。「我只是逗你玩呢,我知道你在我離開後為詹森工作。」
就這樣,我們展開長談,話題從詹森、六○年代、寫作、文學、哲學、科學、天文學、性、演化、八卦、紅襪隊(Red Sox),一直延伸到天底下的各種話題─這場對話將在我們生命接下來的四十六年間持續下去。我們在白宮錯過了三年時光。我在一九六八年加入詹森的白宮幕僚團隊,迪克則在一九六五年秋天退出,當時他就已經擔心越戰升級將耗盡「偉大社會」計畫的資源。
遠離華府後,他對國內政策資金萎縮和關注度下降的擔憂,逐漸被對越戰的強烈不安取代。迪克首次公開發表反戰聲明時,遭到政府外交政策單位的批評。國家安全顧問邦迪(McGeorge Bundy)對他說,他既然離開白宮,就不該如此高調,應該保持沉默,把異議藏在心裡。無任所大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的指責更令人費解,說他反咬餵過他的人一口。
「你怎麼回應的?」我問。迪克陷入回想,眼底泛起漣漪。「我告訴他,林登哪有餵過我?我靠自己吃飯。」我不確定他的語氣是否含帶諷刺幽默,或懷有真心的不屑。
我們連續聊了五個小時。他身上帶著幾分鋒利的叛逆氣息,也格外沉穩、歷經世事,但在機智犀利之餘,舉止與眼神裡仍看得見溫柔。
他提議我們晚上在波士頓燈塔山(Beacon Hill)的一家餐廳繼續談天說地。我們剛坐下並選好一瓶酒,他便靠近我。「告訴我,」他開口道,「你的抱負從何而來?你的父母是什麼樣的人?你談過幾次戀愛?」他那認真和急切的神情打動了我。在他的引導下,我開始滔滔不絕地分享。
我告訴他,我在一九五○年代的紐約郊區洛克維爾中心(Rockville Centre)長大。鄰居之間就像一個大家庭,街坊裡有十幾個和我同齡的孩子,我們整天在彼此的家中進進出出,街道就是我們的遊樂場。我還和他分享了父母和姐妹的故事,談到我對歷史和布魯克林道奇隊(Brooklyn Dodgers)的熱愛,還有我上學時有多麼快樂。
迪克有幾次打斷了我,但都僅是為了進一步詢問我父母的情況。我的母親在我十五歲時去世,父親則在一個月前剛剛辭世。最後,我深吸一口氣,意識到他巧妙掌握了話題的主導權。通常,與人見面時,主導提問的總是我。
晚餐結束後,他開始講述自己在麻薩諸塞州布魯克萊恩(Brookline)長大的經歷,以及在塔夫茲學院(Tufts College)和哈佛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的日子。他的敘述比我的簡潔得多。羅伯特.甘迺迪去世不久後,他搬到了緬因州的鄉村,最近才回到麻州的劍橋。他六歲的兒子小理查(Richard Jr.)即將升上一年級,他希望孩子能在波士頓地區上學。他幾乎沒有提到他的妻子珊卓(Sandra Leverant Goodwin)。珊卓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曾就讀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和法國索邦大學(Sorbonne),但她長期受精神疾病困擾,住院治療多時,他們也因此分居多年。
顯然,故事遠不止於此,但他突然轉換話題:「你覺得紅襪隊怎麼樣?」─儘管他對這支棒球隊情有獨鍾,卻一輩子都覺得他們會輸球;在布魯克林道奇隊拋棄我之後 ,我搬到了麻薩諸塞州,也成為紅襪隊的球迷。
他送我回家時,輕捧起我的臉說:「桃莉絲.基恩斯(Doris Kearns),現在起我們是朋友了。」他擁抱我,並道晚安。由於迪克的辦公室和我在同一棟樓裡,我們後來確實變成了摯友,這段友情也成為我人生中最深刻的一段。
◄◊✶◊►
第一章:成長的模樣(節選)
我常常問迪克他年輕時是什麼樣的人。
對於這種問題,他總是翻白眼並聳聳肩說:「我怎麼會知道,我年輕時是什麼樣子?我那時正顧著當那位年輕人。」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四十歲,我二十九歲。我纏著他問:「如果我在你二十幾歲時遇見你,我還會愛上你嗎?」
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曾幻想能夠見到我研究的總統們在成長階段的模樣,因為在那段時間所做的選擇決定了他們未來的道路。多年來,我深入挖掘他們生命中的每一個蛛絲馬跡,鑽研日記和信件,並仔細斟酌他們相識之人的回憶,最終是同理心和想像力幫助我形塑出一種直覺,讓我感受到他們年輕時可能是什麼樣子。
曾在哈佛求學的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的宿舍瀰漫著甲醛(formaldehyde)氣味,到處散落動物剝製標本的毛皮和羽毛,他古怪、傲慢,但活力四射,彷彿隨時準備跳一支踢踏舞。而尚未被小兒麻痺症擊倒的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會打網球、打高爾夫、游泳,還能像「一隻令人驚嘆的公鹿」般躍過溪流。身材瘦長的詹森,將捲曲的黑髮整齊地向後梳,看起來迷人又霸氣,然而在德州科圖拉(Cotulla)初次任教時,他花了第一個月的大半薪水去照顧貧困的墨西哥裔兒童。還有,誰不會夢想在伊利諾州新賽勒姆(New Salem)的雜貨店裡流連,觀察那位擅說故事吸引每位路人駐足的奇特年輕店員林肯(Abraham Lincoln)呢?
想來有趣的是,我與林肯、老羅斯福、小羅斯福和詹森幾位總統共度的時光,比我與生命中的其他男性(除了我丈夫)還要多。沉浸於研究這些人物十多年後,我對他們產生了深厚、持久且複雜的親近感。我常常在公開場合開玩笑說這些人是「我的夥伴」,但考慮到我在他們身上投入的情感和智慧,我發現這個說法已不僅僅是玩笑。
不過,長期史調挖掘總統「夥伴」的檔案與我現在的研究之間,仍然存在顯著差異:這次我研究的檔案,屬於正坐在房間另一端的「我的老伴」,我結婚四十年的丈夫。雖然我的老伴最初在幫我重現少年迪克方面幫助不大,但我們開始研究不久,我發現了一頁迪克二十歲時在塔夫茲學院開始用打字機寫的日記,讓我感到非常興奮。我心想,終於能「見到」年輕時的迪克了: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日。開始寫日記就像是建立一段新的親密友誼。起初必須慢慢來,有些謹慎地吐露自己的想法與思緒,你需要確信─紙張如同朋友一樣,將會接納你所表達的一切。因為,沒有什麼比期待得到理解卻未能如願,還要傷人的了。當然,寫信與交友還是有差別的,在友誼當中,你必須信任他人;而在日記裡,你必須信任自己。
我現在被許多相互矛盾的渴望和想法撕扯著。活動壓得我喘不過氣。個人事務迫在眉睫,卻因疏忽處理而變得更糟。同時,我的學業也遠遠落後,負擔越來越重。我不知道自己在最後一刻衝刺的習慣能否應付得來。所以我之後要採取一個新辦法。每當有新的想法,我就要躺下來休息半小時。可能做不了太多事情,但肯定能得到很多休息。
我剛把這段日記大聲朗讀給迪克聽,他立刻開始挑剔自己年輕時的文筆。他說:「真是個一本正經的少年,還以為有後人會來品評他呢。」
「他才二十歲!」我反駁道,「而且已經展現出直接、真摯的情感,還帶點自嘲和幽默感。」我認為這個開頭很有潛力,迫不及待想繼續讀下去。然而,才寫這麼一頁,迪克的日記戛然而止,直到十多年過去,甘迺迪遇刺後的幾天才又重新開始。
迪克中斷的日記讓我想起了,一本我在高中二年級二月某天剛開始寫就停止更新的日記。我十五歲,母親去世了。日記上簡單的一句話,卻道盡了一切。我自覺無法用文字表達心中情感,於是闔上日記本,再也沒有提筆。
◄◊✶◊►
第二章:沒有前途(節選)
我從未親眼見過甘迺迪本人。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我們那台二十五公分(十英寸)的黑白電視螢幕上。事實證明,透過電視來領略他的魅力是最好的。我當時十三歲,那是一九五六年八月的一個星期五下午。我正在臥室裡閱讀,母親叫我下樓,見證即將發生的重大時刻。我很高興聽到她罕見的激動聲音。她告訴我,民主黨總統提名人史蒂文生(Adlai Stevenson)出乎意料地將副手提名交給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而且目前看來,她所支持的那位來自麻薩諸塞州的英俊年輕天主教參議員很有可能勝出。
從小螢幕傳來一陣陣的歡呼和嘈雜聲,成千上萬人喧鬧著,彷彿是一場盛大的體育賽事。很快地,我蜷縮在母親椅子旁的沙發上,試圖在一塊大海報板上記錄得分。評論員不斷重複,奪勝的魔術數字是六八六又二分之一。這場比賽的規則比我習慣的井然有序的棒球比賽要奇特得多,與父親一起觀看棒球時,我們是根據每一球、每一次出局、每一局進行計分。在這裡,隨著各州揮舞旗幟和高喊計票結果,數字迅速變化,支持率在短短十五到二十分鐘內就在不同候選人之間來回波動。
當時,我對全國代表大會幾乎一無所知。我的父母並不是特別熱衷政治,餐桌上討論政治的頻率不比金錢或性還多。唯一能感受到的是,我的母親平時很少表現出那天下午民主黨大會進行時的那般,充滿活力和興高采烈。她小時候曾患風濕病,導致心臟受損,三十多歲時開始出現心絞痛,三年前的一次嚴重心臟病發作更對她的身體造成了永久傷害。但那一天,她的眼神充滿明亮,聲音也很洪亮。
她向我解釋,儘管田納西州的參議員艾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在第一輪投票領先(我以前從未聽過艾斯蒂斯這個名字,更別說基福弗了,這讓我覺得很有趣),但甘迺迪展現了驚人的勢頭,排名第二,超越了參議員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和老高爾(Albert Gore Sr.)。果然,在第二輪投票中,我母親的年輕愛爾蘭王子超越了基福弗,她也興奮地跳起來歡呼。
第二輪投票中場,紐約州為甘迺迪灌入大量票數之後,我第一次見到那位身材高大、有著一雙大耳的身影,那是詹森。他握住麥克風,高喊德克薩斯州將把所有選票投給甘迺迪。布條在空中揮舞,呼喊甘迺迪的聲音此起彼伏。此時,甘迺迪的得票數已經超過基福弗,距離勝利僅差二十又二分之一,會場和我們家的緊張氣氛也隨之升高。
接下來的發展讓我感到不合理。田納西州的老高爾參議員要求撤下他的名字,以支持基福弗。突然間,甘迺迪的勢頭被徹底遏制。隨後,許多州一個接一個地將原本屬於甘迺迪的選票轉到基福弗手上。這情景很荒謬,就像我的布魯克林道奇隊在一局中得了兩分,卻在下一局突然遭取消,把得分轉給洋基隊(Yankees)。很快,基福弗的得票數遠超過魔術數字六八六又二分之一,我母親失望得幾乎要流下眼淚,而我憤怒於完全不可理喻的事態。
就在這時,敗選的副總統參選人走上講台。我和母親都安靜了下來。他與其他演講者不同,身材瘦削、非常年輕,還有一頭濃密的頭髮。他的臉上帶著疲憊神情,我能感受到他的悲傷。面對失敗,他依然保持誠懇且優雅的風度。他感謝來自全國各地的支持者,並稱讚史蒂文生將副總統提名人選交由全國代表大會投票決定是「英明之舉」。最後,他請求代表們以鼓掌表決的方式為基福弗獲提名喝采。當基福弗伴隨著〈田納西華爾茲〉(Tennessee Waltz) 43的旋律和人群的歡呼聲走入會場中央時,電視畫面卻切換到甘迺迪的特寫鏡頭,他在失敗後振作起來,站得筆直,為基福弗鼓掌。甚至,他表現出的那份脆弱與寬宏大量,將我母親的悲傷化作驕傲,也將我內心的憤怒和困惑轉化為新萌芽的好奇心。
在和母親一起觀看甘迺迪敗選演說的六十多年後,我透過YouTube重溫了那一天的情景。經過這麼多年,我逐漸理解當年代表票數跌宕起伏的變化。我明白當老高爾參議員退選,且中西部和洛磯山脈地區的州堅定支持基福弗時,甘迺迪的支持度已達極限;一旦局勢明朗,支持基福弗的跟風效應便開始顯現。沒有人願意在大勢已定後,還站在失敗的一方。
在隨後的幾十年間,我研究並撰寫了關於甘迺迪和詹森的文章,發現與甘迺迪對於史蒂文生「英明之舉」的讚譽相比,在詹森看來,讓全國代表大會表決副手「實在是只有白癡政客才會幹出的蠢到爆的事」。我在網路上重看那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影片時,仔細聽了詹森宣讀德州票數時的發言:「德州驕傲地把五十六票投給那位身經百戰的戰士,勇敢的參議員甘迺迪。」我不禁莞爾,因為這些讚美之詞與詹森在牧場私下對這位年輕參議員的評價大相逕庭。他曾形容甘迺迪是「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弱不禁風,一副有病的樣子」,「在參議院裡連個像樣的提案都沒有,什麼事都不幹」。現在我明白了,詹森對甘迺迪的批評其實無關緊要。對德州代表團而言,任何人都比直言不諱的自由派基福弗更合適。而詹森相信甘迺迪是最有機會擊敗基福弗的人。此外,在這個電視興起的政治時代,連詹森也不得不承認:「甘迺迪在該死的電視螢幕上太好看了。」
那個夏天的午後,我和母親獨自在家看電視,但甘迺迪給我們兩人留下的印象,也同樣觸及了全國各地的數百萬人。我最近重溫那場全國代表大會時,最深刻的體悟就是:電視的力量能在瞬間點燃一個人的魅力,將一位年輕參議員轉變為全國知名的政治人物,傳遞出活力四射、令人振奮和充滿希望的形象,並在未來歲月中持續深化。
一九七二年六月某天早晨,當我踏進哈佛大學奧本山街(Mt. Auburn Street)七十八號的辦公室時,整個房間洋溢一股興奮的氛圍。理查.「迪克」.古德溫(Richard “Dick” Goodwin)剛在我們那棟老舊的黃色建築三樓租了一間辦公室,準備完成一本書。我們都知道他是誰:他二十多歲時曾在約翰.甘迺迪(John Kennedy) 政府任職,並在「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計畫鼎盛時期擔任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 的首席文膽。後來羅伯特.「巴比」.甘迺迪(Robert “Bobby” Kennedy)在加州遇害身亡時,他也在場。一位認識他的人說,他是其見過最聰明、最有趣的人,但有時也顯得輕率、善變且傲慢─總之,他是一名耀眼且難以捉摸的人物。
我剛在樓梯盡頭的辦公室裡坐下,迪克便閒晃進來,一屁股坐在我給學生準備的椅子上。他的外表立刻引起我的注意:一頭蓬亂的黑色捲髮、濃密而凌亂的眉毛、滿臉的坑疤,幾根大雪茄從他的休閒襯衫口袋探出頭來。他自我介紹後,問我是否是研究生。「不,我是助理教授。」我反駁道。「我在教一門關於美國總統的課程,還主持研討會和輔導課。」
「我知道,我知道!」他笑著舉起雙手打斷我。「我只是逗你玩呢,我知道你在我離開後為詹森工作。」
就這樣,我們展開長談,話題從詹森、六○年代、寫作、文學、哲學、科學、天文學、性、演化、八卦、紅襪隊(Red Sox),一直延伸到天底下的各種話題─這場對話將在我們生命接下來的四十六年間持續下去。我們在白宮錯過了三年時光。我在一九六八年加入詹森的白宮幕僚團隊,迪克則在一九六五年秋天退出,當時他就已經擔心越戰升級將耗盡「偉大社會」計畫的資源。
遠離華府後,他對國內政策資金萎縮和關注度下降的擔憂,逐漸被對越戰的強烈不安取代。迪克首次公開發表反戰聲明時,遭到政府外交政策單位的批評。國家安全顧問邦迪(McGeorge Bundy)對他說,他既然離開白宮,就不該如此高調,應該保持沉默,把異議藏在心裡。無任所大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的指責更令人費解,說他反咬餵過他的人一口。
「你怎麼回應的?」我問。迪克陷入回想,眼底泛起漣漪。「我告訴他,林登哪有餵過我?我靠自己吃飯。」我不確定他的語氣是否含帶諷刺幽默,或懷有真心的不屑。
我們連續聊了五個小時。他身上帶著幾分鋒利的叛逆氣息,也格外沉穩、歷經世事,但在機智犀利之餘,舉止與眼神裡仍看得見溫柔。
他提議我們晚上在波士頓燈塔山(Beacon Hill)的一家餐廳繼續談天說地。我們剛坐下並選好一瓶酒,他便靠近我。「告訴我,」他開口道,「你的抱負從何而來?你的父母是什麼樣的人?你談過幾次戀愛?」他那認真和急切的神情打動了我。在他的引導下,我開始滔滔不絕地分享。
我告訴他,我在一九五○年代的紐約郊區洛克維爾中心(Rockville Centre)長大。鄰居之間就像一個大家庭,街坊裡有十幾個和我同齡的孩子,我們整天在彼此的家中進進出出,街道就是我們的遊樂場。我還和他分享了父母和姐妹的故事,談到我對歷史和布魯克林道奇隊(Brooklyn Dodgers)的熱愛,還有我上學時有多麼快樂。
迪克有幾次打斷了我,但都僅是為了進一步詢問我父母的情況。我的母親在我十五歲時去世,父親則在一個月前剛剛辭世。最後,我深吸一口氣,意識到他巧妙掌握了話題的主導權。通常,與人見面時,主導提問的總是我。
晚餐結束後,他開始講述自己在麻薩諸塞州布魯克萊恩(Brookline)長大的經歷,以及在塔夫茲學院(Tufts College)和哈佛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的日子。他的敘述比我的簡潔得多。羅伯特.甘迺迪去世不久後,他搬到了緬因州的鄉村,最近才回到麻州的劍橋。他六歲的兒子小理查(Richard Jr.)即將升上一年級,他希望孩子能在波士頓地區上學。他幾乎沒有提到他的妻子珊卓(Sandra Leverant Goodwin)。珊卓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曾就讀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和法國索邦大學(Sorbonne),但她長期受精神疾病困擾,住院治療多時,他們也因此分居多年。
顯然,故事遠不止於此,但他突然轉換話題:「你覺得紅襪隊怎麼樣?」─儘管他對這支棒球隊情有獨鍾,卻一輩子都覺得他們會輸球;在布魯克林道奇隊拋棄我之後 ,我搬到了麻薩諸塞州,也成為紅襪隊的球迷。
他送我回家時,輕捧起我的臉說:「桃莉絲.基恩斯(Doris Kearns),現在起我們是朋友了。」他擁抱我,並道晚安。由於迪克的辦公室和我在同一棟樓裡,我們後來確實變成了摯友,這段友情也成為我人生中最深刻的一段。
◄◊✶◊►
第一章:成長的模樣(節選)
我常常問迪克他年輕時是什麼樣的人。
對於這種問題,他總是翻白眼並聳聳肩說:「我怎麼會知道,我年輕時是什麼樣子?我那時正顧著當那位年輕人。」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四十歲,我二十九歲。我纏著他問:「如果我在你二十幾歲時遇見你,我還會愛上你嗎?」
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曾幻想能夠見到我研究的總統們在成長階段的模樣,因為在那段時間所做的選擇決定了他們未來的道路。多年來,我深入挖掘他們生命中的每一個蛛絲馬跡,鑽研日記和信件,並仔細斟酌他們相識之人的回憶,最終是同理心和想像力幫助我形塑出一種直覺,讓我感受到他們年輕時可能是什麼樣子。
曾在哈佛求學的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的宿舍瀰漫著甲醛(formaldehyde)氣味,到處散落動物剝製標本的毛皮和羽毛,他古怪、傲慢,但活力四射,彷彿隨時準備跳一支踢踏舞。而尚未被小兒麻痺症擊倒的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會打網球、打高爾夫、游泳,還能像「一隻令人驚嘆的公鹿」般躍過溪流。身材瘦長的詹森,將捲曲的黑髮整齊地向後梳,看起來迷人又霸氣,然而在德州科圖拉(Cotulla)初次任教時,他花了第一個月的大半薪水去照顧貧困的墨西哥裔兒童。還有,誰不會夢想在伊利諾州新賽勒姆(New Salem)的雜貨店裡流連,觀察那位擅說故事吸引每位路人駐足的奇特年輕店員林肯(Abraham Lincoln)呢?
想來有趣的是,我與林肯、老羅斯福、小羅斯福和詹森幾位總統共度的時光,比我與生命中的其他男性(除了我丈夫)還要多。沉浸於研究這些人物十多年後,我對他們產生了深厚、持久且複雜的親近感。我常常在公開場合開玩笑說這些人是「我的夥伴」,但考慮到我在他們身上投入的情感和智慧,我發現這個說法已不僅僅是玩笑。
不過,長期史調挖掘總統「夥伴」的檔案與我現在的研究之間,仍然存在顯著差異:這次我研究的檔案,屬於正坐在房間另一端的「我的老伴」,我結婚四十年的丈夫。雖然我的老伴最初在幫我重現少年迪克方面幫助不大,但我們開始研究不久,我發現了一頁迪克二十歲時在塔夫茲學院開始用打字機寫的日記,讓我感到非常興奮。我心想,終於能「見到」年輕時的迪克了: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日。開始寫日記就像是建立一段新的親密友誼。起初必須慢慢來,有些謹慎地吐露自己的想法與思緒,你需要確信─紙張如同朋友一樣,將會接納你所表達的一切。因為,沒有什麼比期待得到理解卻未能如願,還要傷人的了。當然,寫信與交友還是有差別的,在友誼當中,你必須信任他人;而在日記裡,你必須信任自己。
我現在被許多相互矛盾的渴望和想法撕扯著。活動壓得我喘不過氣。個人事務迫在眉睫,卻因疏忽處理而變得更糟。同時,我的學業也遠遠落後,負擔越來越重。我不知道自己在最後一刻衝刺的習慣能否應付得來。所以我之後要採取一個新辦法。每當有新的想法,我就要躺下來休息半小時。可能做不了太多事情,但肯定能得到很多休息。
我剛把這段日記大聲朗讀給迪克聽,他立刻開始挑剔自己年輕時的文筆。他說:「真是個一本正經的少年,還以為有後人會來品評他呢。」
「他才二十歲!」我反駁道,「而且已經展現出直接、真摯的情感,還帶點自嘲和幽默感。」我認為這個開頭很有潛力,迫不及待想繼續讀下去。然而,才寫這麼一頁,迪克的日記戛然而止,直到十多年過去,甘迺迪遇刺後的幾天才又重新開始。
迪克中斷的日記讓我想起了,一本我在高中二年級二月某天剛開始寫就停止更新的日記。我十五歲,母親去世了。日記上簡單的一句話,卻道盡了一切。我自覺無法用文字表達心中情感,於是闔上日記本,再也沒有提筆。
◄◊✶◊►
第二章:沒有前途(節選)
我從未親眼見過甘迺迪本人。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我們那台二十五公分(十英寸)的黑白電視螢幕上。事實證明,透過電視來領略他的魅力是最好的。我當時十三歲,那是一九五六年八月的一個星期五下午。我正在臥室裡閱讀,母親叫我下樓,見證即將發生的重大時刻。我很高興聽到她罕見的激動聲音。她告訴我,民主黨總統提名人史蒂文生(Adlai Stevenson)出乎意料地將副手提名交給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而且目前看來,她所支持的那位來自麻薩諸塞州的英俊年輕天主教參議員很有可能勝出。
從小螢幕傳來一陣陣的歡呼和嘈雜聲,成千上萬人喧鬧著,彷彿是一場盛大的體育賽事。很快地,我蜷縮在母親椅子旁的沙發上,試圖在一塊大海報板上記錄得分。評論員不斷重複,奪勝的魔術數字是六八六又二分之一。這場比賽的規則比我習慣的井然有序的棒球比賽要奇特得多,與父親一起觀看棒球時,我們是根據每一球、每一次出局、每一局進行計分。在這裡,隨著各州揮舞旗幟和高喊計票結果,數字迅速變化,支持率在短短十五到二十分鐘內就在不同候選人之間來回波動。
當時,我對全國代表大會幾乎一無所知。我的父母並不是特別熱衷政治,餐桌上討論政治的頻率不比金錢或性還多。唯一能感受到的是,我的母親平時很少表現出那天下午民主黨大會進行時的那般,充滿活力和興高采烈。她小時候曾患風濕病,導致心臟受損,三十多歲時開始出現心絞痛,三年前的一次嚴重心臟病發作更對她的身體造成了永久傷害。但那一天,她的眼神充滿明亮,聲音也很洪亮。
她向我解釋,儘管田納西州的參議員艾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在第一輪投票領先(我以前從未聽過艾斯蒂斯這個名字,更別說基福弗了,這讓我覺得很有趣),但甘迺迪展現了驚人的勢頭,排名第二,超越了參議員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和老高爾(Albert Gore Sr.)。果然,在第二輪投票中,我母親的年輕愛爾蘭王子超越了基福弗,她也興奮地跳起來歡呼。
第二輪投票中場,紐約州為甘迺迪灌入大量票數之後,我第一次見到那位身材高大、有著一雙大耳的身影,那是詹森。他握住麥克風,高喊德克薩斯州將把所有選票投給甘迺迪。布條在空中揮舞,呼喊甘迺迪的聲音此起彼伏。此時,甘迺迪的得票數已經超過基福弗,距離勝利僅差二十又二分之一,會場和我們家的緊張氣氛也隨之升高。
接下來的發展讓我感到不合理。田納西州的老高爾參議員要求撤下他的名字,以支持基福弗。突然間,甘迺迪的勢頭被徹底遏制。隨後,許多州一個接一個地將原本屬於甘迺迪的選票轉到基福弗手上。這情景很荒謬,就像我的布魯克林道奇隊在一局中得了兩分,卻在下一局突然遭取消,把得分轉給洋基隊(Yankees)。很快,基福弗的得票數遠超過魔術數字六八六又二分之一,我母親失望得幾乎要流下眼淚,而我憤怒於完全不可理喻的事態。
就在這時,敗選的副總統參選人走上講台。我和母親都安靜了下來。他與其他演講者不同,身材瘦削、非常年輕,還有一頭濃密的頭髮。他的臉上帶著疲憊神情,我能感受到他的悲傷。面對失敗,他依然保持誠懇且優雅的風度。他感謝來自全國各地的支持者,並稱讚史蒂文生將副總統提名人選交由全國代表大會投票決定是「英明之舉」。最後,他請求代表們以鼓掌表決的方式為基福弗獲提名喝采。當基福弗伴隨著〈田納西華爾茲〉(Tennessee Waltz) 43的旋律和人群的歡呼聲走入會場中央時,電視畫面卻切換到甘迺迪的特寫鏡頭,他在失敗後振作起來,站得筆直,為基福弗鼓掌。甚至,他表現出的那份脆弱與寬宏大量,將我母親的悲傷化作驕傲,也將我內心的憤怒和困惑轉化為新萌芽的好奇心。
在和母親一起觀看甘迺迪敗選演說的六十多年後,我透過YouTube重溫了那一天的情景。經過這麼多年,我逐漸理解當年代表票數跌宕起伏的變化。我明白當老高爾參議員退選,且中西部和洛磯山脈地區的州堅定支持基福弗時,甘迺迪的支持度已達極限;一旦局勢明朗,支持基福弗的跟風效應便開始顯現。沒有人願意在大勢已定後,還站在失敗的一方。
在隨後的幾十年間,我研究並撰寫了關於甘迺迪和詹森的文章,發現與甘迺迪對於史蒂文生「英明之舉」的讚譽相比,在詹森看來,讓全國代表大會表決副手「實在是只有白癡政客才會幹出的蠢到爆的事」。我在網路上重看那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影片時,仔細聽了詹森宣讀德州票數時的發言:「德州驕傲地把五十六票投給那位身經百戰的戰士,勇敢的參議員甘迺迪。」我不禁莞爾,因為這些讚美之詞與詹森在牧場私下對這位年輕參議員的評價大相逕庭。他曾形容甘迺迪是「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弱不禁風,一副有病的樣子」,「在參議院裡連個像樣的提案都沒有,什麼事都不幹」。現在我明白了,詹森對甘迺迪的批評其實無關緊要。對德州代表團而言,任何人都比直言不諱的自由派基福弗更合適。而詹森相信甘迺迪是最有機會擊敗基福弗的人。此外,在這個電視興起的政治時代,連詹森也不得不承認:「甘迺迪在該死的電視螢幕上太好看了。」
那個夏天的午後,我和母親獨自在家看電視,但甘迺迪給我們兩人留下的印象,也同樣觸及了全國各地的數百萬人。我最近重溫那場全國代表大會時,最深刻的體悟就是:電視的力量能在瞬間點燃一個人的魅力,將一位年輕參議員轉變為全國知名的政治人物,傳遞出活力四射、令人振奮和充滿希望的形象,並在未來歲月中持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