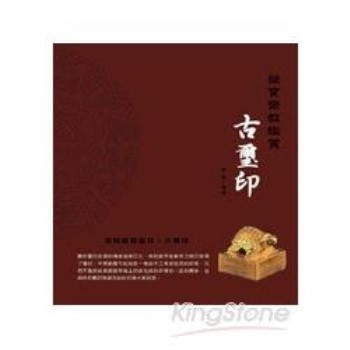中國古代璽印各部位的名稱,一直以來都比較統一,少有分歧。其中有的名稱來自於歷史文獻依據,有的則是長期以來約定俗成的稱呼。瞭解這些名稱,對中國古代璽印做進一步的研究就有了參照的標準,避免了敘述上的混亂。
1.印面:一般位於印章底部,是通過鈐印來顯現印文或圖形之處。單面印的印面向下,雙面印的印面相背,多面印的印面除向下者外,印臺四周乃至印鈕上均有印面,如戰國時期的五面印與東晉時期的六面印。
2.印臺:又稱印身,一般指印鈕以下部分。有的多面印常在印臺上做出印面。戰國秦漢以來,印臺上已有作動物裝飾紋樣者,特別是漢代私印印臺側面刻鑄「四神」圖像的紋樣頗為盛行。隋唐之後,印臺上部即印背部分,多具備款識。但據考古發現,東漢時期已經有銅印章在印臺側面鑄款制銘了。
3.印鈕:印臺以上部分,隋唐以前印章的鈕多有穿孔,為繫綬帶處。唐代及其以後,官私印章多見有未加穿孔的鈕制,但穿孔的印鈕也有不少。印鈕具有裝飾或表示等級的用途,其中後者的作用偏盛於漢魏南北朝。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4.印綬:綬本是璽印的繫帶,並無特殊含義。自漢而後,印綬的顏色被賦予政治等級意義,例如東漢光武帝時規定:公侯紫綬,中二千石以上青綬,千石至四百石以上黑綬及黃綬。諸侯一旦遺失或丟棄印綬,將受到除國或免職的處分。對印綬的製作也有嚴格規定,民間所織印綬不合制度則以不敬罪名收押入監,且二千石以上的印綬,便禁止民間織作。因為絲織品易於腐朽,故很少見到古代印綬實物。故宮博物院藏傳世東漢「琅邪相印章」龜鈕上的銀圓環以及陝西岐山縣博物館藏曹魏政權頒發給氐族佰長的官印駝鈕上所套梯形銅活環、新見「通」字白文印鼻鈕上所附銅鏈環,顯然亦具有相似於印綬的功用。
5.款識:最早見於東漢私印印臺側面的紀年鑄款,但迄今所見尚屬孤例。隋唐之後,官印常在印背、印側刻款,其內容有記印文內容、記時、記鑄造頒發官署、記序號,在鈕頂部往往有為防倒蓋的「上」字等。官印的刻款雖對後來明清流派印章的款識有很大影響,但與其藝術本質的追求是截然不同的。南京出土南宋「張同之印」四側均有篆體款識,內容為「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與予同生,命之日同。」具有自敘性質,而以篆書製款,則當是宋代金石學昌盛的標誌(圖1)。汪偽時期有專門的印鑄局,彙集了陳巨來、石學鴻、談月色等技藝精湛、功力深厚的篆刻家,由他們設計鑄造的汪偽政權官印,亦多採用篆文刻款,頗為精整有致,但氣息似較細弱。
6.印囊、印函:從戰國到兩漢,有些官私印配以絲織「印囊」,又稱「印衣」。考古發掘中有時得見痕跡,墓裡隨葬的「遣冊」中也往往有對印囊的記錄。南京大廠區牟尼峰漢墓曾出土銅質「黃饑私印」1枚,印體與印面黏附絲織品遺痕,或即為印囊殘跡。有些官私印配以木製、金屬或骨角「印函」,即「印盒」。如青海西寧發現的十六國「淩江將軍章」與河南偃師唐代李存墓出土「渤海圖書」印皆有印盒。其中,凌江將軍章印盒為角質,外形似一半球形,腹部依次刻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頂部亦作龍虎圖像,下部有17個未穿透的孔,頂部亦分布有6個呈梅花狀的未穿透的孔,推測原來曾鑲有綠松石。印盒內按銅印形狀雕空,在龜首部位有一斜向圓洞與外部貫通。唐代渤海圖書印盒的盒蓋為攢尖頂,兩側有長方形貫耳,另兩側有搭扣和轉軸,盒內殘存紅色絮狀物,當是用於保護印面的。此外,1958年浙江紹興出土唐「會稽縣印」、1968年浙江安吉出土「金山縣印」(圖2)、1984年廣西隆安出土「武夷縣之印」等唐代官印,也都附有與之形制相類同的印盒。1978年湖南臨澧出土元代「董壽」八思巴文銀印,亦附有銀印盒。
1.印面:一般位於印章底部,是通過鈐印來顯現印文或圖形之處。單面印的印面向下,雙面印的印面相背,多面印的印面除向下者外,印臺四周乃至印鈕上均有印面,如戰國時期的五面印與東晉時期的六面印。
2.印臺:又稱印身,一般指印鈕以下部分。有的多面印常在印臺上做出印面。戰國秦漢以來,印臺上已有作動物裝飾紋樣者,特別是漢代私印印臺側面刻鑄「四神」圖像的紋樣頗為盛行。隋唐之後,印臺上部即印背部分,多具備款識。但據考古發現,東漢時期已經有銅印章在印臺側面鑄款制銘了。
3.印鈕:印臺以上部分,隋唐以前印章的鈕多有穿孔,為繫綬帶處。唐代及其以後,官私印章多見有未加穿孔的鈕制,但穿孔的印鈕也有不少。印鈕具有裝飾或表示等級的用途,其中後者的作用偏盛於漢魏南北朝。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4.印綬:綬本是璽印的繫帶,並無特殊含義。自漢而後,印綬的顏色被賦予政治等級意義,例如東漢光武帝時規定:公侯紫綬,中二千石以上青綬,千石至四百石以上黑綬及黃綬。諸侯一旦遺失或丟棄印綬,將受到除國或免職的處分。對印綬的製作也有嚴格規定,民間所織印綬不合制度則以不敬罪名收押入監,且二千石以上的印綬,便禁止民間織作。因為絲織品易於腐朽,故很少見到古代印綬實物。故宮博物院藏傳世東漢「琅邪相印章」龜鈕上的銀圓環以及陝西岐山縣博物館藏曹魏政權頒發給氐族佰長的官印駝鈕上所套梯形銅活環、新見「通」字白文印鼻鈕上所附銅鏈環,顯然亦具有相似於印綬的功用。
5.款識:最早見於東漢私印印臺側面的紀年鑄款,但迄今所見尚屬孤例。隋唐之後,官印常在印背、印側刻款,其內容有記印文內容、記時、記鑄造頒發官署、記序號,在鈕頂部往往有為防倒蓋的「上」字等。官印的刻款雖對後來明清流派印章的款識有很大影響,但與其藝術本質的追求是截然不同的。南京出土南宋「張同之印」四側均有篆體款識,內容為「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與予同生,命之日同。」具有自敘性質,而以篆書製款,則當是宋代金石學昌盛的標誌(圖1)。汪偽時期有專門的印鑄局,彙集了陳巨來、石學鴻、談月色等技藝精湛、功力深厚的篆刻家,由他們設計鑄造的汪偽政權官印,亦多採用篆文刻款,頗為精整有致,但氣息似較細弱。
6.印囊、印函:從戰國到兩漢,有些官私印配以絲織「印囊」,又稱「印衣」。考古發掘中有時得見痕跡,墓裡隨葬的「遣冊」中也往往有對印囊的記錄。南京大廠區牟尼峰漢墓曾出土銅質「黃饑私印」1枚,印體與印面黏附絲織品遺痕,或即為印囊殘跡。有些官私印配以木製、金屬或骨角「印函」,即「印盒」。如青海西寧發現的十六國「淩江將軍章」與河南偃師唐代李存墓出土「渤海圖書」印皆有印盒。其中,凌江將軍章印盒為角質,外形似一半球形,腹部依次刻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頂部亦作龍虎圖像,下部有17個未穿透的孔,頂部亦分布有6個呈梅花狀的未穿透的孔,推測原來曾鑲有綠松石。印盒內按銅印形狀雕空,在龜首部位有一斜向圓洞與外部貫通。唐代渤海圖書印盒的盒蓋為攢尖頂,兩側有長方形貫耳,另兩側有搭扣和轉軸,盒內殘存紅色絮狀物,當是用於保護印面的。此外,1958年浙江紹興出土唐「會稽縣印」、1968年浙江安吉出土「金山縣印」(圖2)、1984年廣西隆安出土「武夷縣之印」等唐代官印,也都附有與之形制相類同的印盒。1978年湖南臨澧出土元代「董壽」八思巴文銀印,亦附有銀印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