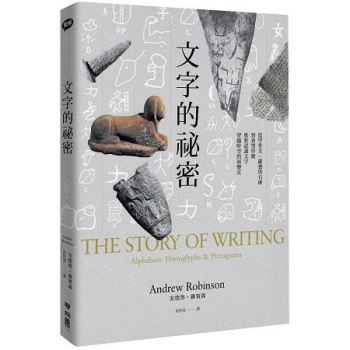發現羅賽塔石碑
王名框一詞是1798年隨拿破崙入侵埃及的法國士兵所發明。銘文中包圍多組象形文字的橢圓形,讓他們聯想到槍中的彈藥筒(法文為cartouche)。
所幸,這支遠征軍對文化的興趣不亞於攻城掠地。一批法國學者與軍隊同行,後留在埃及三年之久。也有多名藝術家隨行,為首的是多明尼克.韋馮.德儂(Domenique Vivant Denon,上圖)。1809至1813年間,他畫了《埃及記述》(Description De L’egypte )一書,而整個歐洲都對古埃及的奇蹟驚嘆不已。
右圖描繪了底比斯城,後為路克索神廟的廊柱,前為精雕細琢的方尖碑。牆上的雕刻描繪了加低斯戰役中,乘雙輪馬車的弓箭手奉拉美西斯二世之命向西台人衝鋒的場景。拿破崙的軍隊為此深感震撼,據目擊者表示,「他們不禁停下腳步,不由自主,放下手中武器」。
1799年7月中旬,一個班的拆除部隊發現了羅賽塔石碑,那可能嵌在尼羅河一條支流河畔拉希德(羅賽塔)村裡一面非常古老的牆中,距海不到幾英里。班隊主
官認為此石碑非同小可,遂下令立刻將它搬到開羅。畫家臨摹後,摹本在1800年送交歐洲學者。1801年,石碑被運往亞歷山卓,避免被英國軍隊擄獲。但它最終還是落入英軍之手,被送往英國,在大英博物館展示,此後就一直沒離開過。
解讀開始
羅賽塔石碑是一塊密實的花崗岩板,有750公斤重、114公分高、72公分寬、28公分厚。
從發現的那一刻起,專家學者皆清楚,石碑上刻有三種不同的文字,最下面是希臘文、最上面(毀損嚴重)是帶有明顯王名框的埃及象形文字,兩者之間則是當時無人認識的文字,明顯不像希臘文,倒和上方的象形文字有某種程度的類似,但沒有王名框。今天我們知道那是象形文字的草寫體,通稱世俗體文字。
解讀碑文的第一步顯然是翻譯希臘文字。內容原來是西元196年3月27日,埃及王托勒密五世(Ptolemy V Epiphanes)加冕週年當天,來自埃及各地的教士齊聚孟斐斯城召開總理事會所通過的一道教令。之所以用希臘文寫是因為當時埃及的統治者不是埃及人,而是馬其頓希臘人:亞歷山大大帝一名將領的後裔。托勒密、亞歷山大、亞歷山卓等人名皆出現在碑文中。
接下來學者將注意力轉向世俗體(象形文字部分因毀損太過嚴重,看來希望渺茫)。他們從希臘文部分的一句聲明中得知,三部分的碑文雖非「逐字」翻譯,但意義相仿。所以他們開始搜尋托勒密之類的名字:在和希臘碑文托勒密出現處大致相同的位置,挑出重複出現的世俗體符號。找到那些符號後,他們發現用世俗體寫成的名字似乎是用字母拼寫,跟希臘碑文一樣。因此他們繪了一張試驗性的世俗體字母表。其他某些世俗體文字,諸如「希臘」、「埃及」、「神廟」等,現在可用這套字母表鑑定出來。由此觀之,世俗體說不定全是字母文字。
可惜不是。第一批學者無以為繼,因為他們執著於世俗體是一套字母的概念──反過來說,他們又認為象形文字全是非表音,其符號就像赫拉波羅解釋的那樣,是表達想法的。象形文字和世俗體符號外觀上的差異,加上背負文藝復興以來對埃及象形文字的傳統觀念,使學者相信這兩種文字:象形文字和世俗體,背後的運作原理截然不同。
字形的重要性
我們已經明白,所有文字都透過表音符號和表意符號運作。文字也透過字形,即符號的形狀來傳達意義。字母使用者通常會忽略字形的重要性,因為他們感受不到個別字母的意義,雖然他們確實認為字體不同,傳達的意義也不同。(因此羅馬體、斜體、哥德體等字體各有含意。)相對來說,中文字的使用者似乎就太過強調字形的象徵,因為每一個字,不同於字母,都有其意義,而有些字看起來就很像其代表的意義。寫中文字的人喜歡說中文字不需聲音介入,就能「直接和心靈交談」。
這句話雖然言過其實,但中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確實有額外的意義面向。這兩種系統,如果精心演繹,可以產生彷彿有生命的文字。右頁的大字意謂佛祖。對今天的基督徒來說,在字母前面祈禱是極不尋常的事:無論中世紀的僧侶把英文字母裝飾得有多漂亮,那就是沒有中文字那樣的象徵力與生命力。
僅有少數中文字一看就知道是什麼意思。但外國人在獲知字義後,常覺得中國字的外形切合意義,於是有人發明視覺記憶法來幫助學習字形字義。但我們切莫誤入陷阱,以為視覺記憶法「說明」某個字是從圖像一路演變而成。的確有一些中國字原為圖形──例如「女」和「田」──但絕大多數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