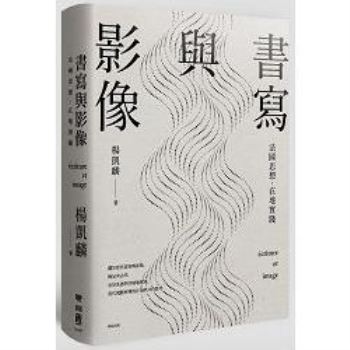駱以軍,游牧書寫者──《西夏旅館》的運動─語言與時間─語言
前言:駱以軍時空
從許多方面來看,47萬字的《西夏旅館》對於當前華語文學版圖都是一記摔碑裂山的重手。在文學形式與語言皆已山窮水盡的今日,吾人驚駭地發現駱以軍仍猱身欺近文學創作的基底,意圖以撼人的書寫意志力搏早已蔫然昏瞶的文學現況。在穿越洶洶旭旭的龐大故事字團之後,渾厚難解的二冊《西夏》已然是與文學固執締結的「黃金盟誓之書」,一座未來或許將被命名為「駱以軍時空」的文學特異空間確切地在作品自身上自我奠立。在此,文學不再只是諸異質故事噴湧如繁花迸放的天方夜譚(如《第三個舞者》),也不只是乖張的戲劇場景所犬牙交疊的怪奇誌異(如《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或其加強版),內建在這些表面上已多少嶄露於先前作品的故事結界,《西夏》並不只是群星賀歲式的簡單「集大成」,不只是工匠辛勤勞動後的「技巧更形純熟」。《西夏》所從事的遠比這些更多,或更少,或許一點都不重要。因為重點已不在此,其直抵致使前者成為可能並作為殘酷核心的創造性時空條件!或者不如說,在所有先前的作品中,儘管已有許多篇幅專注於小說形式(或形上學)的高難度操演,並迫使書寫一再成為一種自我朝自我摺曲並內在揭露的技藝,在《西夏》出版後,駱以軍的讀者才愕然發現先前以為已催逼至底的故事存有狀態(mode d’être),原來僅是其雛形,是完全變態之前的幼蟲,吾人誤以為早已探底的小說形上學實驗最終竟需歷經《西夏》折返後才可能真正理解。
什麼是作為小說殘酷核心的「駱以軍時空」?在故事總是蜂擁而至並引發時空錯亂的文學暴動中,必須質問的恐怕不是附屬於故事的歷史脈絡與地理位置(不論其是否明確設定),不是去拼湊、重整並意圖復原小說的內在時間順序或外在地理參照,相反的,我們問:如果故事在此文學空間中總是迅猛地席捲而來,如果迫使故事強度化的意志在此凌駕一切(甚至取代對角色或情節一致性的要求),究竟什麼是一再促使其成為如此的無上條件?換言之,我們要探究的不是《西夏》的時空(不論其如何怪異與破碎),而是致使其總是如是的文學條件。
《西夏》創造了一個致使自身得以誕生的特異時空,其不屬於書中任何被確切描述的時間與地點(1038至1048年的西夏或20世紀末的台北?),亦不是任何經驗所可給予的歷史場景,而是由一種被特性化的「時間─語言」所強勢迫出的文學空間,其被駱以軍命名為「西夏」或「旅館」。重點或許不太在於《西夏》發生了什麼事(內容),而是作者從事了何種語言操作、配置了何種文學布置(表達)以致《西夏》這個怪異、「脫漢入胡」的空間激生而出?簡言之,促使《西夏》(駱以軍時空)得以誕生的時間性與空間性是什麼?一、故事的再結界與後─斷裂狀態
1. 故事的入口
駱以軍的作品從不曾與一種故事的矯飾主義分離。這種總是將過度修飾、強烈失衡與神經質觀點鋪展於故事時空的風格化書寫,使得其作品一律飽滿充盈,有一種與當前存有狀態相符的俗麗凌亂,小說幻化為一幅吞食各種華麗故事的地獄變。從敘事的觀點來看,這種書寫模鑄了各式當代知識或經驗的複式疊層,意圖以一種軟骨文字在最小面積中凹摺最多故事。在電視、報紙、電影、小說等經驗異質勾連、褶皺的小說平面上,我們見識到的是一種專注於各式激烈動態、轉變、衝突、意外與頓挫的超敏感語言。這種或許可以稱為「運動─語言」(或感覺─運動連結[encha])的書寫形式,從荷馬、塞萬提斯到薩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光怪陸離的故事仍如先前作品般一逕在紙頁上噴吐狂洩,「像上百個凹窪孔格的蜂巢,每一個格子裡都有一條白糊糊的蜂蛹在扭動著」(101)。然而,窮盡運動─語言機巧的故事儘管扣人心弦,《西夏》書寫的賭注卻遠不在此。故事的「田徑運動時期」似乎已經終結,運動─語言的純粹操演最終並不能滿足「虛構」的無上要求。在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波赫士、侯伯.格希耶(Alain Robbe-Grillet)之後,文學早非諸故事的簡單填塞或拼接,作者也不再可能是天真的「說故事的人」(即使是「故事系」作者)。於是不無弔詭的,應說故事卻無有故事,因為故事職人對自身技藝的嚴苛遠超乎想像,所有的故事(破碎的、錯愕的、歷史的、情色猥瑣的)最終都僅在於摸索摳弄某個魔幻的「故事的入口」(30),為了尋覓一個朝虛構開敞的裂罅,一片得以穿透並進入異托邦的纖薄鏡面。
如果小說不免以運動─語言來鋪陳(故事的田徑運動),各種生命經驗(性、酒精、藥物、愛情、家族、創傷……)透過語言平面上的複式微調分身千百億,從一種必要的創造性來看,這些難以細數的故事儘管有優劣之分,卻不無類似。其較量的似乎是語言的細微修飾或情節的剪接鋪陳,否則便是一種怪奇驚駭故事間的赤裸角力。其中,作為故事載體的語言平面僅被簡單等同於一種次要元素,書寫無非是「尬」故事,文學作者坐化為一束束故事過敏的神經叢。然而,說故事的困難並不在故事本身,不在於能否總是揉捏模塑一串怪奇精采、懾人心弦的文學奇遇。對當代職人而言,一切的困難恐怕更在於如何由鋪天蓋地的運動─語言網羅中逃逸,從故事的慣性裡解套。成敗其實已不取決於故事本身(文學史上的故事達人難道還少嗎?),而是繫於一切故事尚未定型、混沌尚未解離的「入口」。然而,故事的入口也不完全是《水滸傳》裡洪太尉揭起的楔子,因為即使群魔出匣、風雲色變,《水滸傳》仍然停留在一種由運動─語言所構成的文學之中,天罡地煞一○八梁山好漢再怎麼逞凶鬥狠殺人如草,也僅是日常生活的變形、誇張或激凸,或者僅是某種偶然、機緣或命運的機巧算計,畢竟離不開由感覺─運動連結所限定的物理慣性。
在故事綻放如漫天花雨的文學傳統裡,素人式的「說故事」已被職人式尋覓「故事入口」所怪異置換。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無疑地便是這種關於「故事入口」的龐大文學布置。就其內容而言,巨河長流寫出的小說篇幅並不真是作品本身,而僅是普魯斯特懸置其社交生活到真正進入文學書寫前的過場,是一個既非作者本人空蕪生活亦非真實文學作品的中介空間;而作品的「真正」啟動,「故事的入口」,其實始於《追憶》一書的最後幾頁。但普魯斯特在此戛然停筆,書中所懸絲一命的真正作品因此從未真正出現。《追憶》僅是故事正式進場前的漫長準備,是「我要說故事喔」的繁複冗雜宣告,是一代宗師正式較量前凌空虛點的起手式。
「這種如同在鏡中可以觀看卻從無法觸及的中介空間、虛擬空間,正是這個擬像空間(espace de simulacre)賦予普魯斯特作品其真實積體」(Foucault, 1964: 7)。
文學似乎怪異地等同於文學自身的擬像,「說故事」從此被「說故事的姿態」所取代,作品不在任何具體述說的內容而是被遙指卻總是缺席的客體=x;或者不如說,如果文學書寫等同於某種騙術(波赫士或大江健三郎)、幻術(駱以軍)或巫(朱天文),最高明的書寫者不是那些赤身裸體(或鳳冠霞帔)投身於砌築故事者,而是徹底地將幻術召喚本身都化成另一層幻術,在語言的撥花穿霧中將整個文學空間騰空、翻摺成絕對的擬像空間;而這個空間的虛擬跨幅,其藉由語言的牽絲攀藤所亟欲拉扯出的中介距離,這個以實際作品與文學作為光譜二極的虛構間際,正是作品的「真實積體」,「文學語言的深邃存有」(Foucault, 1964: 7)。跋(節錄)
越界的地域哲學與就地游牧思考
以中文實踐法國哲學,這意謂什麼?這可以做為一個哲學問題被提出並成為在歐洲之外從事哲學的人回返自身的質問嗎?難道這個問題不該僅停留於幕後,而非如同正式問題被嚴肅地提出來?問題似乎沒這麼簡單。因為這並不涉及一種哲學理論的單純引進,也不是由一種哲學理論到另一種之間的化約比較。確切來說,這個問題想問的是:做為一個亞洲人以他的母語來述說法國哲學時究竟該有什麼效果產生?這些效果,哲學或非哲學的,首先應該是語言論述上的。企圖重複法國哲學的效果,但卻不是在法文語境而是在中文平面上,如果意識到語言學轉向、後殖民論述與全球化理論所給予的啟示時,問題將變得非常複雜與困難。對於思想運動而言,真正重要的並不在於原典的粗糙移植與僵化複製。以中文從事法國哲學研究時,必須召喚的是一種純粹重複。這裡採用的是德勒茲在《差異與重複》一書的意義,重複並不召喚同一性(identité)與一般性(généralité),相反的,重複總是離不開一種稀有的差異。這種對差異與重複的要求並不是一種偶然,在德勒茲那裡我們看到了差分(différenciation)與微分(différentiation),在德希達那裡我們看到了延異(différance),在李歐塔那裡我們看到了紛爭(différend),在傅柯那裡我們看到了異質拓撲學(hétérotopologie)。
在法國思想的核心中,與其展現僵化乾枯的忠誠,涉及的更是一種創造性的背叛跟無窮的越界,其從一開始便不斷地更新與革命思想本身。因此當我們試圖要在一個有別於法文的環境裡實踐這種不斷自我越界且越界一切事物的思想時,問題將變得非常危險與狡獪。我們應該去要求忠實於誕生在它自身的背叛與它自身越界中的思想嗎?這裡沒有任何辯證法的可能,因為這門哲學僅能被再生產於這種極端的條件下。簡言之,去解釋、評論這種思想是遠遠不夠的,相反的,必須去從事一種超越練習(exercice transcendant),其允許我們實踐這種哲學的就地經驗。
這是什麼經驗?一種思想的活體經驗。它首先在法語中被給予,然後現在將在中文中重複。問題並不在於這種獨特經驗是否可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而在於這種異者性(étrangéité)是否早已內在於作為思想基本元素的經驗裡面。以中文述說法國哲學將置身於雙重的異者性中,其中之一是思想本身的內在性條件,其不止息的自我解疆域化,另外之一則源自兩個不同世界的相遇,這是界限及域外條件。這裡較不涉及其中之一對另一的佔有,或者對已知事物的合法化,而是企圖在語言中召喚雙重的異者性,同時解疆域化思想與既有的語言。尼采曾說,古希臘的第一批哲學家就如同「去國家化的異者」(des étrangers dépaysés),即使到今天這仍然是哲學家的身分:我是異者。哲學家在自己國家中的「去國家化」並不只是地理學的,而且透過他們所述說的異者語言來定義。但這並不意謂他們只是說著有別於國人所認識的語言,因為哲學家就是那些述說自己母語卻如同是奇怪或異者語言的人。用德勒茲的話來說,就是在語言中發明新的語言。哲學家迫使他的語言重置於流變之中。他好像是異者化的土著(autochtone étranger),操作一種就地思想運動,一種母語的流變─異者(devenir-étranger)。因此,並不是從某一思想中攫取與另一思想共有的普遍性,也不是將它們共置於四不像的比較與會通之中。內在的異者性是哲學的基本元素之一。法國哲學毫無疑問是亞洲的異者,但並不只因為它是西方思想,而是因為它自身就誕生在自己的異者性裡,誕生在它自己的解疆域化作用中。去國家的國家,解疆域化的領土,未知的土著,異者化的母語……。從事法國哲學時,這便是必須被給予的效果。
異者並不是某種跟我無關之物,而是就地解疆域化者,如同德勒茲與瓜達希所說:「在其自己的語言中如同一個異者」。每次我們企圖要消解某一哲學的異者性,必然成為摧毀其思想強度的災難。必須相反的,在一種異於這個思想的語言中重新誕生哲學的異者性,換言之,它的解疆域化運動必須在這個也是異於此哲學的語言中再度激起。
這是純粹的問題化場域,我們意圖解疆域化一種自我解疆化的思想。換言之,與其簡化思想的異者性,必須將其倍增與加乘,將異者性置入一種雙重鏡像的遊戲之中。將異者性放進自身的循環裡,這就是以中文從事法國哲學的效果。如果德勒茲與瓜達希肯定哲學是一種地域哲學(géophilosophie),這是因為思想必然會將自身抽離到距自己最遠之處的這個意義之下。不只是離自身最遠,而且成為一種去國家的異者以利於就地誕生的嶄新思想。用傅柯的語彙來說,這就是異質拓撲學,它奠立在一種將內部置於外部且反之的強度性操作之中。
地域哲學是一種內在性的異質拓撲學,概念在此透過一種碎形關係相互連結以達成它們的無窮解疆域化作用。地域哲學因此較不是一種可定位與向量化的地理學,而是一種促使思想從宇宙一端逃離且在另一端冒出的超越練習,一種由域外到域內,由內部到外部,由比所有外在更遙遠到比所有內在更深邃的思想運動。一種流變為大寫異者的大寫土著邏輯。透過對傅柯思想的分析,德勒茲寫到:「就域外(「抽象風暴」)闖入觀看與述說之縫隙而言,思考隸屬於域外。對域外的召喚是傅柯一再重現的主題,而且這意謂思考並非一種天生能力之運作,而是必須突然闖進思想中。思考並不取決於一種能結合可視與可述的優美內部性,而是產生於能凹陷出間隙與逼迫、肢解內部性的域外入侵。」毫無疑問的,不只是對於傅柯,這個作為異者與解疆域化作用的抽象風暴正是法國思想的必要條件,而同樣也基於這個理由,幾年後德勒茲與瓜達希再度強調:「對自身,且對自己的語言與國家流變為異者,這個就是哲學與哲學家的本性,他們的風格。」
哲學地促使自身流變為異者,或許這就是法國思想最弔詭的命題,且正是在此湧現哲學的獨特強度。如果異者性是這種思想的核心,則愈強化異者性就愈哲學。然而,異者性並不由地理意義上的陌生思想所引起,而是大寫土著的流變─異者。在中文裡這個由思想力量所給予的原初異者性必須被引導到另外一種異者性,其特屬於中文這個環境,在此同樣涉及一種流變的問題。
然而,什麼是這種在中文思想裡的流變─異者?重要的並不是我們能否去解釋作為某種理論的法國哲學,而是能否在中文鋪設一塊思想平面,其允許土著思想的流變。一方面,這是這個異者思想的現實化,另一方面,這個思想則透過解疆域化觀念及其語言來「反實現」(contre-effectue)中文的哲學場域。
在中文從事思想的流變─異者,這是一種必須一再被從事的思想實驗。其涉及異者思想與華語之間的相遇,但並不是以華語同化異者的思想,也不是企圖將其收編(incorporer),而是「以嶄新、獨特、有趣取代真理的表面性,且其比後者更苛刻」(Deleuze & Guattari, 1991: 106)。嶄新性、創造性與改變總是比表面真理所要說的更為重要。至於哲學史通常是平淡無奇的,「它僅是一種幾近負面的條件整體,其促使某種逃離歷史的實驗成為可能」(Deleuze & Guattari, 1991: 106)。以中文從事法國哲學因此並不是去述說其歷史,而是去促使這個實驗在中文成為可能,去發現且創造一個介於異者思想與土著母語間不可區分的場域。從事哲學,並不是去透過一般性意見促使其變得可以被理解,而是去促使動搖、位移、改變、激怒,以及使陳腔濫調閉嘴,以利於流變。「是為了刺痛他們,如同牛虻刺痛一匹馬一樣」,蘇格拉底說(Platon, 1997: §30e)。
前言:駱以軍時空
從許多方面來看,47萬字的《西夏旅館》對於當前華語文學版圖都是一記摔碑裂山的重手。在文學形式與語言皆已山窮水盡的今日,吾人驚駭地發現駱以軍仍猱身欺近文學創作的基底,意圖以撼人的書寫意志力搏早已蔫然昏瞶的文學現況。在穿越洶洶旭旭的龐大故事字團之後,渾厚難解的二冊《西夏》已然是與文學固執締結的「黃金盟誓之書」,一座未來或許將被命名為「駱以軍時空」的文學特異空間確切地在作品自身上自我奠立。在此,文學不再只是諸異質故事噴湧如繁花迸放的天方夜譚(如《第三個舞者》),也不只是乖張的戲劇場景所犬牙交疊的怪奇誌異(如《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或其加強版),內建在這些表面上已多少嶄露於先前作品的故事結界,《西夏》並不只是群星賀歲式的簡單「集大成」,不只是工匠辛勤勞動後的「技巧更形純熟」。《西夏》所從事的遠比這些更多,或更少,或許一點都不重要。因為重點已不在此,其直抵致使前者成為可能並作為殘酷核心的創造性時空條件!或者不如說,在所有先前的作品中,儘管已有許多篇幅專注於小說形式(或形上學)的高難度操演,並迫使書寫一再成為一種自我朝自我摺曲並內在揭露的技藝,在《西夏》出版後,駱以軍的讀者才愕然發現先前以為已催逼至底的故事存有狀態(mode d’être),原來僅是其雛形,是完全變態之前的幼蟲,吾人誤以為早已探底的小說形上學實驗最終竟需歷經《西夏》折返後才可能真正理解。
什麼是作為小說殘酷核心的「駱以軍時空」?在故事總是蜂擁而至並引發時空錯亂的文學暴動中,必須質問的恐怕不是附屬於故事的歷史脈絡與地理位置(不論其是否明確設定),不是去拼湊、重整並意圖復原小說的內在時間順序或外在地理參照,相反的,我們問:如果故事在此文學空間中總是迅猛地席捲而來,如果迫使故事強度化的意志在此凌駕一切(甚至取代對角色或情節一致性的要求),究竟什麼是一再促使其成為如此的無上條件?換言之,我們要探究的不是《西夏》的時空(不論其如何怪異與破碎),而是致使其總是如是的文學條件。
《西夏》創造了一個致使自身得以誕生的特異時空,其不屬於書中任何被確切描述的時間與地點(1038至1048年的西夏或20世紀末的台北?),亦不是任何經驗所可給予的歷史場景,而是由一種被特性化的「時間─語言」所強勢迫出的文學空間,其被駱以軍命名為「西夏」或「旅館」。重點或許不太在於《西夏》發生了什麼事(內容),而是作者從事了何種語言操作、配置了何種文學布置(表達)以致《西夏》這個怪異、「脫漢入胡」的空間激生而出?簡言之,促使《西夏》(駱以軍時空)得以誕生的時間性與空間性是什麼?一、故事的再結界與後─斷裂狀態
1. 故事的入口
駱以軍的作品從不曾與一種故事的矯飾主義分離。這種總是將過度修飾、強烈失衡與神經質觀點鋪展於故事時空的風格化書寫,使得其作品一律飽滿充盈,有一種與當前存有狀態相符的俗麗凌亂,小說幻化為一幅吞食各種華麗故事的地獄變。從敘事的觀點來看,這種書寫模鑄了各式當代知識或經驗的複式疊層,意圖以一種軟骨文字在最小面積中凹摺最多故事。在電視、報紙、電影、小說等經驗異質勾連、褶皺的小說平面上,我們見識到的是一種專注於各式激烈動態、轉變、衝突、意外與頓挫的超敏感語言。這種或許可以稱為「運動─語言」(或感覺─運動連結[encha])的書寫形式,從荷馬、塞萬提斯到薩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光怪陸離的故事仍如先前作品般一逕在紙頁上噴吐狂洩,「像上百個凹窪孔格的蜂巢,每一個格子裡都有一條白糊糊的蜂蛹在扭動著」(101)。然而,窮盡運動─語言機巧的故事儘管扣人心弦,《西夏》書寫的賭注卻遠不在此。故事的「田徑運動時期」似乎已經終結,運動─語言的純粹操演最終並不能滿足「虛構」的無上要求。在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波赫士、侯伯.格希耶(Alain Robbe-Grillet)之後,文學早非諸故事的簡單填塞或拼接,作者也不再可能是天真的「說故事的人」(即使是「故事系」作者)。於是不無弔詭的,應說故事卻無有故事,因為故事職人對自身技藝的嚴苛遠超乎想像,所有的故事(破碎的、錯愕的、歷史的、情色猥瑣的)最終都僅在於摸索摳弄某個魔幻的「故事的入口」(30),為了尋覓一個朝虛構開敞的裂罅,一片得以穿透並進入異托邦的纖薄鏡面。
如果小說不免以運動─語言來鋪陳(故事的田徑運動),各種生命經驗(性、酒精、藥物、愛情、家族、創傷……)透過語言平面上的複式微調分身千百億,從一種必要的創造性來看,這些難以細數的故事儘管有優劣之分,卻不無類似。其較量的似乎是語言的細微修飾或情節的剪接鋪陳,否則便是一種怪奇驚駭故事間的赤裸角力。其中,作為故事載體的語言平面僅被簡單等同於一種次要元素,書寫無非是「尬」故事,文學作者坐化為一束束故事過敏的神經叢。然而,說故事的困難並不在故事本身,不在於能否總是揉捏模塑一串怪奇精采、懾人心弦的文學奇遇。對當代職人而言,一切的困難恐怕更在於如何由鋪天蓋地的運動─語言網羅中逃逸,從故事的慣性裡解套。成敗其實已不取決於故事本身(文學史上的故事達人難道還少嗎?),而是繫於一切故事尚未定型、混沌尚未解離的「入口」。然而,故事的入口也不完全是《水滸傳》裡洪太尉揭起的楔子,因為即使群魔出匣、風雲色變,《水滸傳》仍然停留在一種由運動─語言所構成的文學之中,天罡地煞一○八梁山好漢再怎麼逞凶鬥狠殺人如草,也僅是日常生活的變形、誇張或激凸,或者僅是某種偶然、機緣或命運的機巧算計,畢竟離不開由感覺─運動連結所限定的物理慣性。
在故事綻放如漫天花雨的文學傳統裡,素人式的「說故事」已被職人式尋覓「故事入口」所怪異置換。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無疑地便是這種關於「故事入口」的龐大文學布置。就其內容而言,巨河長流寫出的小說篇幅並不真是作品本身,而僅是普魯斯特懸置其社交生活到真正進入文學書寫前的過場,是一個既非作者本人空蕪生活亦非真實文學作品的中介空間;而作品的「真正」啟動,「故事的入口」,其實始於《追憶》一書的最後幾頁。但普魯斯特在此戛然停筆,書中所懸絲一命的真正作品因此從未真正出現。《追憶》僅是故事正式進場前的漫長準備,是「我要說故事喔」的繁複冗雜宣告,是一代宗師正式較量前凌空虛點的起手式。
「這種如同在鏡中可以觀看卻從無法觸及的中介空間、虛擬空間,正是這個擬像空間(espace de simulacre)賦予普魯斯特作品其真實積體」(Foucault, 1964: 7)。
文學似乎怪異地等同於文學自身的擬像,「說故事」從此被「說故事的姿態」所取代,作品不在任何具體述說的內容而是被遙指卻總是缺席的客體=x;或者不如說,如果文學書寫等同於某種騙術(波赫士或大江健三郎)、幻術(駱以軍)或巫(朱天文),最高明的書寫者不是那些赤身裸體(或鳳冠霞帔)投身於砌築故事者,而是徹底地將幻術召喚本身都化成另一層幻術,在語言的撥花穿霧中將整個文學空間騰空、翻摺成絕對的擬像空間;而這個空間的虛擬跨幅,其藉由語言的牽絲攀藤所亟欲拉扯出的中介距離,這個以實際作品與文學作為光譜二極的虛構間際,正是作品的「真實積體」,「文學語言的深邃存有」(Foucault, 1964: 7)。跋(節錄)
越界的地域哲學與就地游牧思考
以中文實踐法國哲學,這意謂什麼?這可以做為一個哲學問題被提出並成為在歐洲之外從事哲學的人回返自身的質問嗎?難道這個問題不該僅停留於幕後,而非如同正式問題被嚴肅地提出來?問題似乎沒這麼簡單。因為這並不涉及一種哲學理論的單純引進,也不是由一種哲學理論到另一種之間的化約比較。確切來說,這個問題想問的是:做為一個亞洲人以他的母語來述說法國哲學時究竟該有什麼效果產生?這些效果,哲學或非哲學的,首先應該是語言論述上的。企圖重複法國哲學的效果,但卻不是在法文語境而是在中文平面上,如果意識到語言學轉向、後殖民論述與全球化理論所給予的啟示時,問題將變得非常複雜與困難。對於思想運動而言,真正重要的並不在於原典的粗糙移植與僵化複製。以中文從事法國哲學研究時,必須召喚的是一種純粹重複。這裡採用的是德勒茲在《差異與重複》一書的意義,重複並不召喚同一性(identité)與一般性(généralité),相反的,重複總是離不開一種稀有的差異。這種對差異與重複的要求並不是一種偶然,在德勒茲那裡我們看到了差分(différenciation)與微分(différentiation),在德希達那裡我們看到了延異(différance),在李歐塔那裡我們看到了紛爭(différend),在傅柯那裡我們看到了異質拓撲學(hétérotopologie)。
在法國思想的核心中,與其展現僵化乾枯的忠誠,涉及的更是一種創造性的背叛跟無窮的越界,其從一開始便不斷地更新與革命思想本身。因此當我們試圖要在一個有別於法文的環境裡實踐這種不斷自我越界且越界一切事物的思想時,問題將變得非常危險與狡獪。我們應該去要求忠實於誕生在它自身的背叛與它自身越界中的思想嗎?這裡沒有任何辯證法的可能,因為這門哲學僅能被再生產於這種極端的條件下。簡言之,去解釋、評論這種思想是遠遠不夠的,相反的,必須去從事一種超越練習(exercice transcendant),其允許我們實踐這種哲學的就地經驗。
這是什麼經驗?一種思想的活體經驗。它首先在法語中被給予,然後現在將在中文中重複。問題並不在於這種獨特經驗是否可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而在於這種異者性(étrangéité)是否早已內在於作為思想基本元素的經驗裡面。以中文述說法國哲學將置身於雙重的異者性中,其中之一是思想本身的內在性條件,其不止息的自我解疆域化,另外之一則源自兩個不同世界的相遇,這是界限及域外條件。這裡較不涉及其中之一對另一的佔有,或者對已知事物的合法化,而是企圖在語言中召喚雙重的異者性,同時解疆域化思想與既有的語言。尼采曾說,古希臘的第一批哲學家就如同「去國家化的異者」(des étrangers dépaysés),即使到今天這仍然是哲學家的身分:我是異者。哲學家在自己國家中的「去國家化」並不只是地理學的,而且透過他們所述說的異者語言來定義。但這並不意謂他們只是說著有別於國人所認識的語言,因為哲學家就是那些述說自己母語卻如同是奇怪或異者語言的人。用德勒茲的話來說,就是在語言中發明新的語言。哲學家迫使他的語言重置於流變之中。他好像是異者化的土著(autochtone étranger),操作一種就地思想運動,一種母語的流變─異者(devenir-étranger)。因此,並不是從某一思想中攫取與另一思想共有的普遍性,也不是將它們共置於四不像的比較與會通之中。內在的異者性是哲學的基本元素之一。法國哲學毫無疑問是亞洲的異者,但並不只因為它是西方思想,而是因為它自身就誕生在自己的異者性裡,誕生在它自己的解疆域化作用中。去國家的國家,解疆域化的領土,未知的土著,異者化的母語……。從事法國哲學時,這便是必須被給予的效果。
異者並不是某種跟我無關之物,而是就地解疆域化者,如同德勒茲與瓜達希所說:「在其自己的語言中如同一個異者」。每次我們企圖要消解某一哲學的異者性,必然成為摧毀其思想強度的災難。必須相反的,在一種異於這個思想的語言中重新誕生哲學的異者性,換言之,它的解疆域化運動必須在這個也是異於此哲學的語言中再度激起。
這是純粹的問題化場域,我們意圖解疆域化一種自我解疆化的思想。換言之,與其簡化思想的異者性,必須將其倍增與加乘,將異者性置入一種雙重鏡像的遊戲之中。將異者性放進自身的循環裡,這就是以中文從事法國哲學的效果。如果德勒茲與瓜達希肯定哲學是一種地域哲學(géophilosophie),這是因為思想必然會將自身抽離到距自己最遠之處的這個意義之下。不只是離自身最遠,而且成為一種去國家的異者以利於就地誕生的嶄新思想。用傅柯的語彙來說,這就是異質拓撲學,它奠立在一種將內部置於外部且反之的強度性操作之中。
地域哲學是一種內在性的異質拓撲學,概念在此透過一種碎形關係相互連結以達成它們的無窮解疆域化作用。地域哲學因此較不是一種可定位與向量化的地理學,而是一種促使思想從宇宙一端逃離且在另一端冒出的超越練習,一種由域外到域內,由內部到外部,由比所有外在更遙遠到比所有內在更深邃的思想運動。一種流變為大寫異者的大寫土著邏輯。透過對傅柯思想的分析,德勒茲寫到:「就域外(「抽象風暴」)闖入觀看與述說之縫隙而言,思考隸屬於域外。對域外的召喚是傅柯一再重現的主題,而且這意謂思考並非一種天生能力之運作,而是必須突然闖進思想中。思考並不取決於一種能結合可視與可述的優美內部性,而是產生於能凹陷出間隙與逼迫、肢解內部性的域外入侵。」毫無疑問的,不只是對於傅柯,這個作為異者與解疆域化作用的抽象風暴正是法國思想的必要條件,而同樣也基於這個理由,幾年後德勒茲與瓜達希再度強調:「對自身,且對自己的語言與國家流變為異者,這個就是哲學與哲學家的本性,他們的風格。」
哲學地促使自身流變為異者,或許這就是法國思想最弔詭的命題,且正是在此湧現哲學的獨特強度。如果異者性是這種思想的核心,則愈強化異者性就愈哲學。然而,異者性並不由地理意義上的陌生思想所引起,而是大寫土著的流變─異者。在中文裡這個由思想力量所給予的原初異者性必須被引導到另外一種異者性,其特屬於中文這個環境,在此同樣涉及一種流變的問題。
然而,什麼是這種在中文思想裡的流變─異者?重要的並不是我們能否去解釋作為某種理論的法國哲學,而是能否在中文鋪設一塊思想平面,其允許土著思想的流變。一方面,這是這個異者思想的現實化,另一方面,這個思想則透過解疆域化觀念及其語言來「反實現」(contre-effectue)中文的哲學場域。
在中文從事思想的流變─異者,這是一種必須一再被從事的思想實驗。其涉及異者思想與華語之間的相遇,但並不是以華語同化異者的思想,也不是企圖將其收編(incorporer),而是「以嶄新、獨特、有趣取代真理的表面性,且其比後者更苛刻」(Deleuze & Guattari, 1991: 106)。嶄新性、創造性與改變總是比表面真理所要說的更為重要。至於哲學史通常是平淡無奇的,「它僅是一種幾近負面的條件整體,其促使某種逃離歷史的實驗成為可能」(Deleuze & Guattari, 1991: 106)。以中文從事法國哲學因此並不是去述說其歷史,而是去促使這個實驗在中文成為可能,去發現且創造一個介於異者思想與土著母語間不可區分的場域。從事哲學,並不是去透過一般性意見促使其變得可以被理解,而是去促使動搖、位移、改變、激怒,以及使陳腔濫調閉嘴,以利於流變。「是為了刺痛他們,如同牛虻刺痛一匹馬一樣」,蘇格拉底說(Platon, 1997: §3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