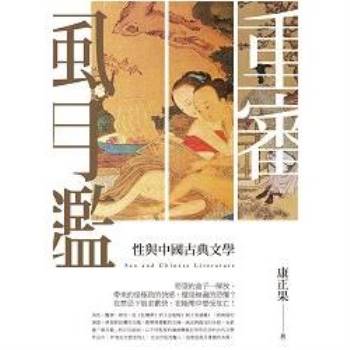《金瓶梅》中的性描寫遠比《肉蒲團》節制,敘述者的聲音也遠比《肉蒲團》隱蔽,然而《金瓶梅》的色情感染力卻明顯比《肉蒲團》厲害。「笑笑生」的語言富有彈性,他筆下的性場景彌漫了肉欲的氣息,色情的意象、淫蕩的動作和猥褻的對話,全與人物沉溺的狀態相表裡,因而有其特殊的魔力。李漁的語言過於油滑,他在造詞創意上的尖新常常讓人覺得太饒舌,他筆下的性場景大都是一些粗俗的色情漫畫,與其說它們富有刺激,不如說全都顯得很可笑。同樣誇張陽具的威力,西門慶的陽具被寫成了一個「活物」,是西門慶的化身,它和西門慶本人一樣狂妄、專橫,最後與西門慶同歸於盡。未央生的陽具只是一個純粹工具化的東西,因為它已經被改造成非人的器官。李漁越是誇張它的功效,便越顯得它完全麻木,猶如死物。他並沒有像「笑笑生」那樣用誇張的字眼和擬人化的手法把陽具寫得神氣活現,對於未央生腰間那個打滿了補釘的怪物,他很少作特寫鏡頭式的描繪,而更多的是以數量的計算來突出它的妙用。從後來未央生的多次漁色歷險可以看出,李漁顯然喜歡把這一妙用導向一個他認為最富於刺激的場景:如何使一個女人多次達到高潮或使更多的女人依次達到高潮。這是古代色情小說的一大特徵,它與房中書所強調的「閨中佳境」有一定的聯繫。因為房中書完全從養生的角度考慮女性在性交中的興奮程度,更多地激發女性的陰氣始終被描述為有益於男性採補的過程,因而對女子在這一過程中的一系列反應均有詳細的記載,其中特別強調了所謂「淫津流溢」。其次,房中書向來把陰道分泌物視為女人的陰精,甚至把它列為「三峰大藥」之一。對這種津液的神化也導致了某些房中書文本對它的誇張描寫,以致大肆渲染津液流溢成了表現女子達到高潮的描寫程式,比如在〈大樂賦〉中,有關的描寫已達到了製造刺激的程度。高潮的另一個反應是發出興奮的呻喚,說一些甜言蜜語,即〈大樂賦〉所謂的「姐姐哥哥,交相惹諾」。這兩種自然的反應在《肉蒲團》中完全被敷演成有意製造的效果,性行為的目的,交歡者證實自己享受到快感的依據,甚至是敘述者固執地強加給人物的主觀嗜好。從未央生新婚之初希望妻子「叫死叫活,助男子的軍威」(第三回),到賽昆侖大談「婦人口裡有三種浪法」(第四回),直到花晨向未央生解釋「聽騷聲」的樂趣(第十七回),李漁幾乎利用一切表現手段突出了他自己對於淫聲浪語的感受和見解,因為在這部自稱旨在誡淫的小說中,他更關心向讀者灌輸享樂的方法。未央生與賽昆侖的對話被描述為一問一答的授課,他與眾佳人的狂歡則如互相切磋的實習,各種有關性的奇談妙論使《肉蒲團》更像一部色情的教科書。
《肉蒲團》中的佳人幾乎沒有絲毫獨特的個性色彩。她們全都被寫成了只關心滿足淫欲的女人。豔芳對行房之事的樂趣精打細算,在初次與未央生通姦的晚上,她先讓鄰婦暗中做替身,以驗證是否值得同他交鋒。香雲與未央生姘居數日之後,感到非常滿意,她立即召來她的兩個姊妹,與她們分享快樂,因為她想讓她們「也知道天地之間有這一種妙物,大家賞鑑賞鑑」。(第十二回)而她的兩個姊妹―瑞珠和瑞玉―一聽到她的誇耀,便對未央生其人充滿了好奇,「一句遞一句的問他,就像未考的童生遇著考過的朋友,在試館門前扯住了問題目一般」。(第十五回)後來,三姊妹的好事被她們的親戚花晨發現,這個年長的寡婦更是後來居上,在四女一男的盛會中占盡了風騷。所有的佳人既無貞節觀念也沒情感的需求,她們結交未央生的共同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兩件寶貝湊在一處」。(第十二回)在她們的眼中,未央生與其說是個情人或姘夫,不如說只是「一幅活跳的春宮」。(第十六回)她們之間也不存在《金瓶梅》中眾淫婦的勾心鬥角和拈酸吃醋,因為未央生並不是她們共事的主子,她們更傾向於把他當成可以共享的「天下之寶」。她們與未央生的關係被描繪為一種純粹的性關係,其中排除了任何經濟的、社會的和精神的因素,雙方都拼命地追求快感,把自己作為寶貝出讓給對方,同時盡情享受對方的寶貝。在她們的丈夫全都不在場的情景中,在這個暫時從人倫的背景中抽離出來的春宮世界裡,李漁讓他筆下的眾佳人全都表現出一種虛假的性解放姿態。如果把小說中未央生漁色歷險的諸場景比成一系列床上的運動比賽,眾佳人就是幾個大同小異的運動員。相比之下,她們的形象顯然比《金瓶梅》中的淫婦們膚淺、單薄,儘管後者的身上有更多可厭的東西。西門慶的姬妾和姘婦沒有一個表現出自己獨特的性要求,性行為主要是她們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是她們為討得西門慶的歡心而屈身奉承的事情。在「笑笑生」的筆下,她們的快感更多地表現為忍痛、受虐,為滿足西門慶的嗜好而幹任何卑賤的事情,她們往往不是在享樂,而是辛苦地為他人服務。因此,她們總是很關心報酬,西門慶也從不吝嗇於獎賞。即使像潘金蓮這樣使盡手段奪專房之寵的淫婦,她在交鋒時幾乎要把西門慶完全吞沒的衝動也不完全是性欲,而或多或少是與其他女人爭奪地位的一種變態反應,是對西門慶的一種消耗。她們的表現儘管很醜惡,而唯其醜惡,正顯示了她們的奴化之深。她們自甘卑賤和屈辱的行為也正好說明,女人在受男人豢養、被男人當作佔有物的處境下,在必須以自己肉體為本錢去謀取只有男人才能賜予她們的其他利益時,她們是不可能有自己獨特的性要求的。李漁向來在小說中不關心表現人物的處境,他的人物幾乎都是他製造戲劇效果的木偶,人物的對話和敘述者的議論不管多麼新奇、精闢,他全都是當作噱頭處理的。總的來說,《肉蒲團》中的眾佳人全都是作為未央生欠下的一筆筆淫債陸續出現的,未央生從她們身上得到的所有歡樂則是他預支的消費。他自己的妻子緊接著就要為他的偷竊和揮霍付出代價。
李漁絲毫也不懂得男女之間自由的性關係,眾佳人的肆意踐踏禮法只是他製造的一場鬧劇,為了完成她們的丈夫狠狠報復未央生的結局,他有意設計了她們縱淫的場景。她們仍然被視為各自丈夫的佔有物和丈夫們之間的交換品,因為一方的妻子被另一方所偷,偷竊者就得拿自己的妻子償還。不管是欠債還是討債,所兌現的總是妻子們的肉體,這就是李漁在《肉蒲團》中宣揚的「陽報」。作者的另一個代言人孤峰長老在小說一開始便向未央生宣佈了故事的既定格局:「淫人妻者,妻亦為人所淫;汙人女者,女亦為人所汙。若要脫套,只除非不姦不淫則已,若要姦要淫,少不得要被套話說著。」(第二回)未央生蔑視孤峰長老的套話,企圖僥倖占漁色的便宜,結果仍未跳出報應的老套。李漁並不迴避在他的小說中採取這個老套,他所自負的創新是把報應推到極點,讓故事的結局圓滿到「無一人不報,無一事不報」。(第十八回評語)
《肉蒲團》中的佳人幾乎沒有絲毫獨特的個性色彩。她們全都被寫成了只關心滿足淫欲的女人。豔芳對行房之事的樂趣精打細算,在初次與未央生通姦的晚上,她先讓鄰婦暗中做替身,以驗證是否值得同他交鋒。香雲與未央生姘居數日之後,感到非常滿意,她立即召來她的兩個姊妹,與她們分享快樂,因為她想讓她們「也知道天地之間有這一種妙物,大家賞鑑賞鑑」。(第十二回)而她的兩個姊妹―瑞珠和瑞玉―一聽到她的誇耀,便對未央生其人充滿了好奇,「一句遞一句的問他,就像未考的童生遇著考過的朋友,在試館門前扯住了問題目一般」。(第十五回)後來,三姊妹的好事被她們的親戚花晨發現,這個年長的寡婦更是後來居上,在四女一男的盛會中占盡了風騷。所有的佳人既無貞節觀念也沒情感的需求,她們結交未央生的共同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兩件寶貝湊在一處」。(第十二回)在她們的眼中,未央生與其說是個情人或姘夫,不如說只是「一幅活跳的春宮」。(第十六回)她們之間也不存在《金瓶梅》中眾淫婦的勾心鬥角和拈酸吃醋,因為未央生並不是她們共事的主子,她們更傾向於把他當成可以共享的「天下之寶」。她們與未央生的關係被描繪為一種純粹的性關係,其中排除了任何經濟的、社會的和精神的因素,雙方都拼命地追求快感,把自己作為寶貝出讓給對方,同時盡情享受對方的寶貝。在她們的丈夫全都不在場的情景中,在這個暫時從人倫的背景中抽離出來的春宮世界裡,李漁讓他筆下的眾佳人全都表現出一種虛假的性解放姿態。如果把小說中未央生漁色歷險的諸場景比成一系列床上的運動比賽,眾佳人就是幾個大同小異的運動員。相比之下,她們的形象顯然比《金瓶梅》中的淫婦們膚淺、單薄,儘管後者的身上有更多可厭的東西。西門慶的姬妾和姘婦沒有一個表現出自己獨特的性要求,性行為主要是她們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是她們為討得西門慶的歡心而屈身奉承的事情。在「笑笑生」的筆下,她們的快感更多地表現為忍痛、受虐,為滿足西門慶的嗜好而幹任何卑賤的事情,她們往往不是在享樂,而是辛苦地為他人服務。因此,她們總是很關心報酬,西門慶也從不吝嗇於獎賞。即使像潘金蓮這樣使盡手段奪專房之寵的淫婦,她在交鋒時幾乎要把西門慶完全吞沒的衝動也不完全是性欲,而或多或少是與其他女人爭奪地位的一種變態反應,是對西門慶的一種消耗。她們的表現儘管很醜惡,而唯其醜惡,正顯示了她們的奴化之深。她們自甘卑賤和屈辱的行為也正好說明,女人在受男人豢養、被男人當作佔有物的處境下,在必須以自己肉體為本錢去謀取只有男人才能賜予她們的其他利益時,她們是不可能有自己獨特的性要求的。李漁向來在小說中不關心表現人物的處境,他的人物幾乎都是他製造戲劇效果的木偶,人物的對話和敘述者的議論不管多麼新奇、精闢,他全都是當作噱頭處理的。總的來說,《肉蒲團》中的眾佳人全都是作為未央生欠下的一筆筆淫債陸續出現的,未央生從她們身上得到的所有歡樂則是他預支的消費。他自己的妻子緊接著就要為他的偷竊和揮霍付出代價。
李漁絲毫也不懂得男女之間自由的性關係,眾佳人的肆意踐踏禮法只是他製造的一場鬧劇,為了完成她們的丈夫狠狠報復未央生的結局,他有意設計了她們縱淫的場景。她們仍然被視為各自丈夫的佔有物和丈夫們之間的交換品,因為一方的妻子被另一方所偷,偷竊者就得拿自己的妻子償還。不管是欠債還是討債,所兌現的總是妻子們的肉體,這就是李漁在《肉蒲團》中宣揚的「陽報」。作者的另一個代言人孤峰長老在小說一開始便向未央生宣佈了故事的既定格局:「淫人妻者,妻亦為人所淫;汙人女者,女亦為人所汙。若要脫套,只除非不姦不淫則已,若要姦要淫,少不得要被套話說著。」(第二回)未央生蔑視孤峰長老的套話,企圖僥倖占漁色的便宜,結果仍未跳出報應的老套。李漁並不迴避在他的小說中採取這個老套,他所自負的創新是把報應推到極點,讓故事的結局圓滿到「無一人不報,無一事不報」。(第十八回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