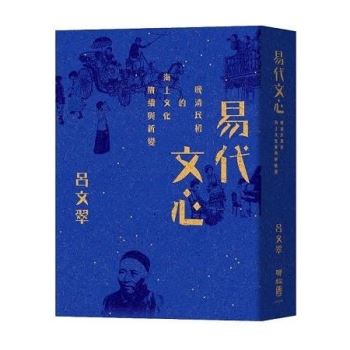第五章
五詳《紅樓夢》,三棄《海上花》?──張愛玲的人情文學系譜
前言
本章討論張愛玲穿越晚清、五四與整個二十世紀,於一九六○年代開始《紅樓夢》考證、透過英譯及國語註譯研究《海上花列傳》,熨帖闡釋社會文化易代的晚清「文心」,讓韓邦慶的文學遺產復活於當下時空。與魯迅將《海上花列傳》類分為「狹邪」小說一脈的觀點互異,她認為韓邦慶《海上花列傳》與《金瓶梅》、《紅樓夢》乃一脈相承的人情文學系譜。小說中的妓家人際關係亦人之常情,且歷經層疊世變後,在晚清主流小說中充滿活力,持續影響民初《歇浦潮》為代表的社會小說浪潮。易代的張愛玲闡明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在王韜開拓的歷史文化迴廊上,添置了華洋雜處的新風景。故深入分析張愛玲與《紅樓夢》、《海上花》間的文學傳承與相互闡釋的複雜關係,可梳理出張愛玲自覺建構自身文學定位的曲折心理脈絡,更得窺晚清民初都市文學《歇浦潮》如何賡續衍異人情小說系譜的豐饒內涵。
一、從「石頭」說起:「對照」「詳夢」與自我詮釋的生命文本
(這兩部書)在我是一切的源頭,尤其紅樓夢。
著筆於一九六○年代,張愛玲生前從未發表的幾部自傳體中英文小說無疑讓張迷興奮異常:二○○九年在台灣率先出版,銷售火紅與迴響熱烈的《小團圓》(一九七六年完成);動筆於一九五七年,完成於一九六三年龐然巨冊一分為二的兩部英文自傳小說《雷峰塔》(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於二○一○年四月在港、台出版,由鄭丕慧翻譯的中文版緊接著於該年九月推出。評者有言,這三部自傳小說,可從她的自傳式中英文散文以及《對照記:看老照相簿》(一九九三年出版)找出故事的素材與人物原型。
因此不論題材或情節上,這幾部自傳小說中絕大多數的內容對「張迷」而言早已是琅琅上口的典故,了無新意。王德威於是重提他在二○○四年對張愛玲晚期風格的詮釋:重複、迴旋與衍生的敘事學,以此解釋日後出土的《小團圓》、Fall of the Pagoda與The Book of Chang依然適用。然而,就如王德威受訪時所言,對於這三部生前終未發表的自傳小說,也許張愛玲的態度是「但願大家不要找到我」。
不管這不斷重寫的衝動是自我療癒或自我陷溺,讓張愛玲最終放棄出版的原因固然是顧慮讀者怎麼讀,更毋寧是自己怎看(「張看」)的根本問題,過不過得了自己這一關尤其要緊。除了《小團圓》中邵之雍與九莉間的情愛糾葛與現實中的胡張戀勢必再度掀起諸多話題與爭議外,這部「坦率得嚇人」的自傳小說中展現張愛玲眼中不堪回首復又糾結縈繞的家庭羅曼史或許更是她躊躇再三的關鍵因素。
讀者看《小團圓》,每每訝異小說中九莉與母親蕊秋間的愛恨情結,如第四章曾分析過的,張迷們不免對號入座地想像真實人生中黃素瓊的行徑:離婚後各國男友源源不斷,警戒及不無忌妒地提防更年輕的女兒出落長成後壓倒她的風采……;《雷峰塔》藉童女沈琵琶之眼,進一步揭露出家族祕辛:舅舅楊國柱的身世可疑,是鄉下村婦的骨肉偽裝而成的世家遺腹子、輪廓洋化的弟弟沈陵可能是母親楊露與義大利歌唱教師的孽種,而姑姑沈珊瑚則與表姪羅明有了亂倫戀情,為了資助羅明打官司營救因貪污案入獄的父親,使一向親密的姑嫂因財務問題而產生無法彌合的裂痕。更有甚者,《易經》的少女琵琶與母親楊露的親情戰爭,乃是楊露在牌桌上一夕之間賭光了女兒的獎學金(八百元港幣)後正式爆發,琵琶認定楊露懷疑這是港大歷史教授付給琵琶的一筆夜度資,故不惜將這筆來路不明的鉅款輸光,如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母女溫情終於銷毀殆盡。凡此種種,皆構成《易經》中幽深無望的主題之一:人與人間溝通的不可能,親人彼此誤解與互相提防的心理鬥爭,盤根錯節地構成無法直面的精神創傷,終其一生如幽魂般縈繞迴盪在作家的生命史與作品中。
讀者終於明白曹七巧(《金鎖記》)、霓喜(《連環套》)等人的惡母形象從何而來。這種赤裸裸的曝現筆法,若對照一九九三年出版也引起騷動的《對照記》,張愛玲筆觸中處處流露對母親的孺慕之情,其中相距何止以道理計!
我記得的那件衣服是淡藍色薄綢,印著一蓬蓬白霧。T字形白綢領,穿著有點傻頭傻腦的,我並不怎麼喜歡,只感到親切。隨即又記起那天我非常高興,看見我母親為這張照片著色。一張小書桌迎亮擱在裝著玻璃的狹窄的小陽臺上,北國的陰天下午,仍舊相當幽暗。我站在旁邊看著,雜亂無章的桌面上有黑鐵水彩畫顏料盒,瘦瘦的黑鐵管毛筆,一杯水。她把我的嘴唇畫成薄薄的紅唇,衣服也改填最鮮豔的藍綠色。那是她的藍綠色時期。
我第一本書出版,自己設計的封面就是整個一色的孔雀藍,沒有圖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點空白,濃稠得使人窒息。以後才聽見說我母親從前也喜歡這顏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淺的藍綠色。我記得牆上一直掛著她的一幅靜物習作靜物,也是以湖綠色為主。遺傳就是這樣神秘飄忽──我就是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氣死人。
參看年譜,這部她在世時最後一部「欽定」出版的自傳式圖文集(相簿)是讓張愛玲有「天長地久」之感的姑姑張茂淵逝世(一九九二)後隔一年旋即付梓出版的,與當時張迷們引頸期待的自傳小說(即《小團圓》)千呼萬喚始終「只聽樓梯響」而久久不見下聞(文)的狀況恰恰相反,皆非偶然隨意之舉。
宋以朗曾經提及,The Fall of the Pagoda完成於一九六三年,《小團圓》寫於一九七六年,《小團圓》很多內容都是從The Fall of the Pagoda中譯過來的,也許可以說,張愛玲在漫長的雙語互換、重複書寫自我與家史的過程中,《對照記》的溫暖回憶筆調終究取代了《小團圓》的直白坦露與譴責之聲。彷彿這本老相片簿的出版,是年過耳順之年的張愛玲對姑姑與母親、姑姑與自己之間異常堅固的「姊妹」情誼(sisterhood)回眸致意。她挑選出代表母親黃素瓊一生各個階段的相片:我們看見三寸金蓮的深閨少女,庭園中掌壺宴茶的嫻靜少婦,在倫敦、法國、北京、西湖的雍容婦人,以及海船上側映夕陽餘暉的時髦翦影──踏著三寸金蓮橫跨兩個時代的「摩登女性」──一九五○年代末葉客死英倫,她的遺物(整箱骨董)留給了女兒。
五詳《紅樓夢》,三棄《海上花》?──張愛玲的人情文學系譜
前言
本章討論張愛玲穿越晚清、五四與整個二十世紀,於一九六○年代開始《紅樓夢》考證、透過英譯及國語註譯研究《海上花列傳》,熨帖闡釋社會文化易代的晚清「文心」,讓韓邦慶的文學遺產復活於當下時空。與魯迅將《海上花列傳》類分為「狹邪」小說一脈的觀點互異,她認為韓邦慶《海上花列傳》與《金瓶梅》、《紅樓夢》乃一脈相承的人情文學系譜。小說中的妓家人際關係亦人之常情,且歷經層疊世變後,在晚清主流小說中充滿活力,持續影響民初《歇浦潮》為代表的社會小說浪潮。易代的張愛玲闡明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在王韜開拓的歷史文化迴廊上,添置了華洋雜處的新風景。故深入分析張愛玲與《紅樓夢》、《海上花》間的文學傳承與相互闡釋的複雜關係,可梳理出張愛玲自覺建構自身文學定位的曲折心理脈絡,更得窺晚清民初都市文學《歇浦潮》如何賡續衍異人情小說系譜的豐饒內涵。
一、從「石頭」說起:「對照」「詳夢」與自我詮釋的生命文本
(這兩部書)在我是一切的源頭,尤其紅樓夢。
著筆於一九六○年代,張愛玲生前從未發表的幾部自傳體中英文小說無疑讓張迷興奮異常:二○○九年在台灣率先出版,銷售火紅與迴響熱烈的《小團圓》(一九七六年完成);動筆於一九五七年,完成於一九六三年龐然巨冊一分為二的兩部英文自傳小說《雷峰塔》(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於二○一○年四月在港、台出版,由鄭丕慧翻譯的中文版緊接著於該年九月推出。評者有言,這三部自傳小說,可從她的自傳式中英文散文以及《對照記:看老照相簿》(一九九三年出版)找出故事的素材與人物原型。
因此不論題材或情節上,這幾部自傳小說中絕大多數的內容對「張迷」而言早已是琅琅上口的典故,了無新意。王德威於是重提他在二○○四年對張愛玲晚期風格的詮釋:重複、迴旋與衍生的敘事學,以此解釋日後出土的《小團圓》、Fall of the Pagoda與The Book of Chang依然適用。然而,就如王德威受訪時所言,對於這三部生前終未發表的自傳小說,也許張愛玲的態度是「但願大家不要找到我」。
不管這不斷重寫的衝動是自我療癒或自我陷溺,讓張愛玲最終放棄出版的原因固然是顧慮讀者怎麼讀,更毋寧是自己怎看(「張看」)的根本問題,過不過得了自己這一關尤其要緊。除了《小團圓》中邵之雍與九莉間的情愛糾葛與現實中的胡張戀勢必再度掀起諸多話題與爭議外,這部「坦率得嚇人」的自傳小說中展現張愛玲眼中不堪回首復又糾結縈繞的家庭羅曼史或許更是她躊躇再三的關鍵因素。
讀者看《小團圓》,每每訝異小說中九莉與母親蕊秋間的愛恨情結,如第四章曾分析過的,張迷們不免對號入座地想像真實人生中黃素瓊的行徑:離婚後各國男友源源不斷,警戒及不無忌妒地提防更年輕的女兒出落長成後壓倒她的風采……;《雷峰塔》藉童女沈琵琶之眼,進一步揭露出家族祕辛:舅舅楊國柱的身世可疑,是鄉下村婦的骨肉偽裝而成的世家遺腹子、輪廓洋化的弟弟沈陵可能是母親楊露與義大利歌唱教師的孽種,而姑姑沈珊瑚則與表姪羅明有了亂倫戀情,為了資助羅明打官司營救因貪污案入獄的父親,使一向親密的姑嫂因財務問題而產生無法彌合的裂痕。更有甚者,《易經》的少女琵琶與母親楊露的親情戰爭,乃是楊露在牌桌上一夕之間賭光了女兒的獎學金(八百元港幣)後正式爆發,琵琶認定楊露懷疑這是港大歷史教授付給琵琶的一筆夜度資,故不惜將這筆來路不明的鉅款輸光,如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母女溫情終於銷毀殆盡。凡此種種,皆構成《易經》中幽深無望的主題之一:人與人間溝通的不可能,親人彼此誤解與互相提防的心理鬥爭,盤根錯節地構成無法直面的精神創傷,終其一生如幽魂般縈繞迴盪在作家的生命史與作品中。
讀者終於明白曹七巧(《金鎖記》)、霓喜(《連環套》)等人的惡母形象從何而來。這種赤裸裸的曝現筆法,若對照一九九三年出版也引起騷動的《對照記》,張愛玲筆觸中處處流露對母親的孺慕之情,其中相距何止以道理計!
我記得的那件衣服是淡藍色薄綢,印著一蓬蓬白霧。T字形白綢領,穿著有點傻頭傻腦的,我並不怎麼喜歡,只感到親切。隨即又記起那天我非常高興,看見我母親為這張照片著色。一張小書桌迎亮擱在裝著玻璃的狹窄的小陽臺上,北國的陰天下午,仍舊相當幽暗。我站在旁邊看著,雜亂無章的桌面上有黑鐵水彩畫顏料盒,瘦瘦的黑鐵管毛筆,一杯水。她把我的嘴唇畫成薄薄的紅唇,衣服也改填最鮮豔的藍綠色。那是她的藍綠色時期。
我第一本書出版,自己設計的封面就是整個一色的孔雀藍,沒有圖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點空白,濃稠得使人窒息。以後才聽見說我母親從前也喜歡這顏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淺的藍綠色。我記得牆上一直掛著她的一幅靜物習作靜物,也是以湖綠色為主。遺傳就是這樣神秘飄忽──我就是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氣死人。
參看年譜,這部她在世時最後一部「欽定」出版的自傳式圖文集(相簿)是讓張愛玲有「天長地久」之感的姑姑張茂淵逝世(一九九二)後隔一年旋即付梓出版的,與當時張迷們引頸期待的自傳小說(即《小團圓》)千呼萬喚始終「只聽樓梯響」而久久不見下聞(文)的狀況恰恰相反,皆非偶然隨意之舉。
宋以朗曾經提及,The Fall of the Pagoda完成於一九六三年,《小團圓》寫於一九七六年,《小團圓》很多內容都是從The Fall of the Pagoda中譯過來的,也許可以說,張愛玲在漫長的雙語互換、重複書寫自我與家史的過程中,《對照記》的溫暖回憶筆調終究取代了《小團圓》的直白坦露與譴責之聲。彷彿這本老相片簿的出版,是年過耳順之年的張愛玲對姑姑與母親、姑姑與自己之間異常堅固的「姊妹」情誼(sisterhood)回眸致意。她挑選出代表母親黃素瓊一生各個階段的相片:我們看見三寸金蓮的深閨少女,庭園中掌壺宴茶的嫻靜少婦,在倫敦、法國、北京、西湖的雍容婦人,以及海船上側映夕陽餘暉的時髦翦影──踏著三寸金蓮橫跨兩個時代的「摩登女性」──一九五○年代末葉客死英倫,她的遺物(整箱骨董)留給了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