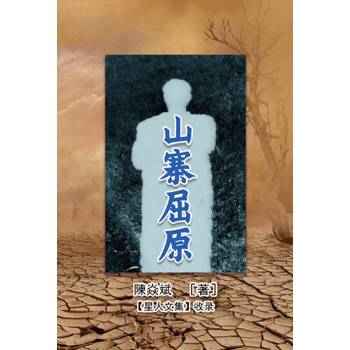【開篇:山脊松林】
1976年9月22日。天已擦黑,烏雲遊移。欒山尾脊松林裡,一位老者拄著手杖佇立在秋風中。他凝望著山下那條江、那架橋、那座城。颼颼涼風吹佛著他那件碩長的風衣,城裡點點燈火映襯在他的鏡片上,遮住了眼眸的迷茫。
良久,一位樵夫路過,跟老者打聲招呼,好奇地打量。端詳一會兒,忍不住問道:“天色不早噠,何解還一個人在山上?”
“路過,歇腳。”。老者答道。
“從哪裡來?”。樵夫又問。
“那邊。”。老者朝江的上游嚕了嚕嘴。
“看你該身打扮,斯斯文文的,是教書的吧?”
“嗯… 不!”
“那邊那個單位?”
“學校。”
“我就猜你是教書的吧。‘中南’,‘江麓’,還是‘師範’?”
“‘江麓’。”
“哦,‘江麓’啊!”。樵夫似乎有些感慨。
樵夫放下柴擔,擺出一副打算聊天的架勢,邊找地方坐邊對老者說:
“來來來,看你腿腳不方便,莫總是站噠,坐下來策哈子噻。”
“嗯…”。老者一臉不情願的樣子。
樵夫坐下,觸到了地上的一件東西,提起,沉甸甸的。借著微光打量,是個帆布背包。再仔細看,包的反面下方有三個用蔴線絞成的字,歪歪斜斜,好不容易才辨認出來:陳 炎 文
“該是你的包吧,你叫得‘陳炎文’吧?!”。虧得樵夫認得字。
“包裡裝的是些麼子傢伙囉?該麼打秤。”。樵夫委實好管閒事。
“行李。”
“哦,你到哪裡克?”
“那邊。”。老陳朝江的下游嚕了嚕嘴。
“‘那邊’是哪裡?”。樵夫是個“包打聽”。
“很遠~,很遠的地方。”。老陳的話音拖得好長。
樵夫見他不想細說,也就忍住不再追問。扭過頭來,另開了個話題:
“老陳呐,望噠你該副斯文相,就想起我那個大崽。我崽伢子細時候好聽話的,學習成績好得不得了,政治上也表現得冇空話港,一直是班幹部,期期被評為優秀學生,入隊,入團,順順暢暢;高中畢業後在隊上作田,勤快,積極,人緣好,還冇得兩年就當噠團支部書記、生產隊長、民兵班長;再過一向子,入噠黨;又過一向,就當噠大隊黨支部書記,民兵排長。你要曉得,那時候他還冇滿二十呢!”
樵夫緩了口氣,從上衣口袋摸出一包皺巴巴的煙絲和一疊舊日曆,邊捲煙邊繼續嘮叨:
“他那個時候好是有蠻好,不過呢,我還是想他做個讀書人,以後成為斯文人。嘿,就像你該個樣子哪。我要他莫作田噠,莫做官噠,上大學克。開始他還不情願丟嘎他那個得意的排場,不聽勸,還是搭幫他那個姓姚的同學,也是我們公社另一個大隊的,情況跟他差不多。小姚動員我那個蠢崽還是多讀點書好,講噠一通讀噠書將來就會如何如何的道理,總算把我的崽伢子勸通噠,於是乎他白天做事,晚上溫習。一年後,那是1965年吧,居然被他考取噠。我們望欒公社就在欒山的背後,崽伢子跟他那個同學當然報考‘江麓大學’囉,就是你那個學校哪。入校後學校裡看他們先前表現得好,還是社隊幹部,就讓他們擇個喜歡的專業。崽伢子選噠個叫麼子‘土木系’的,你港是叫得該個名字擺?我實在搞不懂有那麼多好聽的牌子的行當不要,他何解偏要學麼子泥木匠,也只隨得他囉。他那個同學選得好,學化工,‘化工系’,好聽得很!總而言之不管何是,反正我屋裡是‘祖墳開岔’噠!”
樵夫瞥了一眼一聲不吭的老陳,把卷好的“喇叭筒”點上火,猛吸幾口,吐出陣陣青煙,瞬間不見面目。待煙霧散去,乾咳兩聲,接著講他的故事:
“那年頭,港是港讀大學,其實是‘三分之一搞運動,三分之一搞勞動,三分之一搞文化’,我冇港錯吧?‘三分之一搞運動’呢,就是管教那些在學校裡勞動改造的‘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叫得麼子‘四類分子’還是‘五類分子’還是‘七類分子’還是‘九類分子’還是‘二十一種人’吧,哎呀,莫港我該個粗人策不清,就算洽政治飯的人只怕也懵懂。’
“才讀得一年,‘文革’開始噠,搞運動的時間越來越多。寫大字報,貼標語、扯橫幅,開大會,批鬥麼子‘牛鬼蛇神’哪,今天‘保該個’,明天‘滅那個’哪。學生伢子搞‘運動’上噠贏,成立噠叫得麼子‘高司’的組織。崽伢子那個小姚同學是‘江麓司令部’的‘司令’,我崽伢子當‘參謀長’,跟社會上有個叫得‘紅聯’的組織搞在一起,整個不讀書噠。’
“後來,社會上又冒出個叫得麼子‘工聯’的組織,港自家是‘造反派’,‘造反有理’;港‘高司’是‘保皇派’,‘保皇有罪’;港‘高司’實際上是站在‘無產階級司令部’對立面的反革命組織,是保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所以呢,為噠捍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必須跟‘高司’作‘你死我活的鬥爭’。起頭雙方還是叫得麼子‘口誅筆伐’,後來又時興‘文攻武衛’,就是一路罵一路打囉,棍棒梭鏢砍刀叮鐺響,時不時有人頭破血流。1967年,到處打得一塌糊塗。有一天,崽伢子一瘸一拐地回來,邋遢死噠的,癡癡呆呆地,只港學校怕是守不住噠,要開闢新戰場。我跟他娘佬子勸他莫回克噠,反正學校已經不是學校,成噠戰場,不但讀不到書,還要打打殺殺,還是保命要緊,老老實實回來作田吧。他就是不服,只港他在捍衛‘革命路線’鬥爭中不能當逃兵,不能撇開一個戰壕裡的戰友不管,要共同戰鬥到底。總之不聽勸,修養幾天又回克噠。該一克就再也冇回來。”
講到這裡,樵夫把目光移向橋那邊的城市,那座城市遠一些的某個地方。
“老陳呐,你曉得原來的‘中蘇友好館’吧,就在五一路上,靠東頭那邊。1967年6月,‘高司’占噠那裡做‘指揮部’,聚噠百把人在裡頭‘辦公’。那個什麼‘工聯’的,還有個什麼“六號門”的,還有個什麼‘青近’的,還有個什麼‘風雷’的,幾百號人攻打那棟樓:搬雲梯丟磚頭啦,打彈弓啦,放鳥銃啦,放火燒啦,噴農藥啦,用消防龍頭沖水啦,斷水斷電啦,圍困噠好多天,裡頭的人實在熬不住噠,我崽伢子自告奮勇做談判代表,想討個‘優待俘虜’,才出樓下門口就被一遭拳腳一頓亂棍給打死噠。”。樵夫嗚咽了起來。
老陳嘟噥道:“那件事,有的說死了人,有的說沒死人;有的說是慘案,有的說是勝利。”
“冇死人?還是勝利?那就得看港該種話的都是些麼子人囉!我跟你港囉,就是在那天,6月6號吧,我崽被打死後,‘工聯’、‘六號門’的人沖進樓裡,打死七八個,打傷幾十個,要不是解放軍趕來制止,還不曉得會死好多人呢。該些事情是幾年後小姚回來跟我港的。”。樵夫憤然。
老陳忽然有一種莫名的感覺,不禁問道:“你兒子叫什麼名字?”
“丁輝,你認得不?”
“哦,丁輝。校方說他失蹤了。”。老陳心裡一陣酸楚,又喃喃道:
“自古都是‘勝者王,敗者寇’,強勢面前無理論,受難終是斯文人。”。老陳感歎。
“是囉,是囉。斯文人就應該做斯文事,老老實實做學問,莫克關心‘政治’‘時事’那些東西,你的道理有人聽嗎? 搞得不好要治罪的! 更莫跟什麼‘路線’哪‘鬥爭’哪攪和,你們該些書生鬥得過別個嗎? 做該些事情,那幫人是裡手,他們就是靠搞該些名堂起家的。心血來潮的時候騙你一把,搞事的時候用你一把,搞定以後甩你一把,不順眼就鬥你一把,覺得有威脅就乾脆殺你一把… ”。老丁既“世故”又“覺悟”。
“別說了,別再說了!”。老陳感觸萬千,趕忙打斷老丁的話,此刻他的心裡已不是酸楚,而是痛楚了。
老丁歎了口氣,冷靜下來,緩緩說道:“我是有些激動,大意噠,好在冇得人聽見,你總不至於克告發我擺?!我看你是斯文人,又是‘江麓’的,才跟你策些我那可憐的崽伢子的事,你莫在意噢。”。老丁已緩過神來。
老陳苦笑。凝視著遠處淩波蕩漾的江水,好似無意地問道:
“老丁哪,你說這汐江裡現在還有大魚嗎?”
“有還是有的,只不過比以前少得多噠。你曉得不,大魚最多是什麼年代?只怕你一世都猜不到。告訴你囉,該條江裡魚最多的時候是武鬥期間!那個時候,江裡連常有死屍,冇得人管,魚們就連常聚餐囉,長得滾豬爛壯的。’
“尤其到發大水的時候,漂下來的死屍就比平日多些,聽港多半是從桂林從道縣漂過來的。上游那邊打得蠻厲害,有些是鬧派性打仗被打死的,有些是翻舊賬搞報復被打死的。唉~,我就搞不懂何解要搞該麼大的運動要打死該麼多人呢?! 哈是鄉里鄉親何解要下狼心自相殘殺噻?!”
老丁一臉傷感。稍頓,緩口氣接著說:“該些年江裡乾淨得多噠,那些魚的日子冇得從前好過也就冇得幾條大魚噠。嘿嘿~。’
“何解,你想改行打漁啦?”。老丁乜眼瞟著老陳。
“想喂魚!”。老陳喃喃。
“喂魚?你是做學問的,又冇得池塘,養麼子鬼魚囉,神經病!”。老丁不屑。
“哎,老陳呐,太晚噠,堂客還等噠我的柴火搞飯呢,靠得住會挨駡。你也快走吧,烏昏黑暗的,只怕就要落雨噠,你腿腳不利索,注意安全,保重身體,有機會碰面再策,再會了!”。老丁起身挑起柴擔緩緩下山去了。
陳炎文不能回應“再會”這個告別詞,這個人之常情的詞彙,他在14年前與妻兒離別的時刻就回避過一次了。
他緩緩站起身來望著老丁漸漸遠去的背影,回味著老丁的話語,感慨萬分,歎了口氣,搖了搖頭。
此時,山風越來越緊,松濤越來越響,真的有點飄毛毛雨了。
他抬頭望瞭望陰沉沉的天空,轉過身子,面朝東方慢慢坐下,撫摸著那個沉甸甸的背包,再把目光移回那條江、那架橋、那座城,開始實施來到這片山脊松林的計畫 - “放電影”,再放一遍這部攝於他自己62年滄桑歷程的“紀錄片”。多少年來,他無數次試圖把自己放在旁觀者的視角來觀看這部“影片”,但每次卻還是不知不覺地融入了角色,總也逃避不了。
這回可是他最後一次當“放映員”,也是最後一次做唯一的“觀眾”了。
他神情遲疑,猶豫了好一陣子。然,還是狠狠心“打開鏡頭”,一幅幅不甚分明的畫面映上了陰沉的夜幕 ……
1976年9月22日。天已擦黑,烏雲遊移。欒山尾脊松林裡,一位老者拄著手杖佇立在秋風中。他凝望著山下那條江、那架橋、那座城。颼颼涼風吹佛著他那件碩長的風衣,城裡點點燈火映襯在他的鏡片上,遮住了眼眸的迷茫。
良久,一位樵夫路過,跟老者打聲招呼,好奇地打量。端詳一會兒,忍不住問道:“天色不早噠,何解還一個人在山上?”
“路過,歇腳。”。老者答道。
“從哪裡來?”。樵夫又問。
“那邊。”。老者朝江的上游嚕了嚕嘴。
“看你該身打扮,斯斯文文的,是教書的吧?”
“嗯… 不!”
“那邊那個單位?”
“學校。”
“我就猜你是教書的吧。‘中南’,‘江麓’,還是‘師範’?”
“‘江麓’。”
“哦,‘江麓’啊!”。樵夫似乎有些感慨。
樵夫放下柴擔,擺出一副打算聊天的架勢,邊找地方坐邊對老者說:
“來來來,看你腿腳不方便,莫總是站噠,坐下來策哈子噻。”
“嗯…”。老者一臉不情願的樣子。
樵夫坐下,觸到了地上的一件東西,提起,沉甸甸的。借著微光打量,是個帆布背包。再仔細看,包的反面下方有三個用蔴線絞成的字,歪歪斜斜,好不容易才辨認出來:陳 炎 文
“該是你的包吧,你叫得‘陳炎文’吧?!”。虧得樵夫認得字。
“包裡裝的是些麼子傢伙囉?該麼打秤。”。樵夫委實好管閒事。
“行李。”
“哦,你到哪裡克?”
“那邊。”。老陳朝江的下游嚕了嚕嘴。
“‘那邊’是哪裡?”。樵夫是個“包打聽”。
“很遠~,很遠的地方。”。老陳的話音拖得好長。
樵夫見他不想細說,也就忍住不再追問。扭過頭來,另開了個話題:
“老陳呐,望噠你該副斯文相,就想起我那個大崽。我崽伢子細時候好聽話的,學習成績好得不得了,政治上也表現得冇空話港,一直是班幹部,期期被評為優秀學生,入隊,入團,順順暢暢;高中畢業後在隊上作田,勤快,積極,人緣好,還冇得兩年就當噠團支部書記、生產隊長、民兵班長;再過一向子,入噠黨;又過一向,就當噠大隊黨支部書記,民兵排長。你要曉得,那時候他還冇滿二十呢!”
樵夫緩了口氣,從上衣口袋摸出一包皺巴巴的煙絲和一疊舊日曆,邊捲煙邊繼續嘮叨:
“他那個時候好是有蠻好,不過呢,我還是想他做個讀書人,以後成為斯文人。嘿,就像你該個樣子哪。我要他莫作田噠,莫做官噠,上大學克。開始他還不情願丟嘎他那個得意的排場,不聽勸,還是搭幫他那個姓姚的同學,也是我們公社另一個大隊的,情況跟他差不多。小姚動員我那個蠢崽還是多讀點書好,講噠一通讀噠書將來就會如何如何的道理,總算把我的崽伢子勸通噠,於是乎他白天做事,晚上溫習。一年後,那是1965年吧,居然被他考取噠。我們望欒公社就在欒山的背後,崽伢子跟他那個同學當然報考‘江麓大學’囉,就是你那個學校哪。入校後學校裡看他們先前表現得好,還是社隊幹部,就讓他們擇個喜歡的專業。崽伢子選噠個叫麼子‘土木系’的,你港是叫得該個名字擺?我實在搞不懂有那麼多好聽的牌子的行當不要,他何解偏要學麼子泥木匠,也只隨得他囉。他那個同學選得好,學化工,‘化工系’,好聽得很!總而言之不管何是,反正我屋裡是‘祖墳開岔’噠!”
樵夫瞥了一眼一聲不吭的老陳,把卷好的“喇叭筒”點上火,猛吸幾口,吐出陣陣青煙,瞬間不見面目。待煙霧散去,乾咳兩聲,接著講他的故事:
“那年頭,港是港讀大學,其實是‘三分之一搞運動,三分之一搞勞動,三分之一搞文化’,我冇港錯吧?‘三分之一搞運動’呢,就是管教那些在學校裡勞動改造的‘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叫得麼子‘四類分子’還是‘五類分子’還是‘七類分子’還是‘九類分子’還是‘二十一種人’吧,哎呀,莫港我該個粗人策不清,就算洽政治飯的人只怕也懵懂。’
“才讀得一年,‘文革’開始噠,搞運動的時間越來越多。寫大字報,貼標語、扯橫幅,開大會,批鬥麼子‘牛鬼蛇神’哪,今天‘保該個’,明天‘滅那個’哪。學生伢子搞‘運動’上噠贏,成立噠叫得麼子‘高司’的組織。崽伢子那個小姚同學是‘江麓司令部’的‘司令’,我崽伢子當‘參謀長’,跟社會上有個叫得‘紅聯’的組織搞在一起,整個不讀書噠。’
“後來,社會上又冒出個叫得麼子‘工聯’的組織,港自家是‘造反派’,‘造反有理’;港‘高司’是‘保皇派’,‘保皇有罪’;港‘高司’實際上是站在‘無產階級司令部’對立面的反革命組織,是保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所以呢,為噠捍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必須跟‘高司’作‘你死我活的鬥爭’。起頭雙方還是叫得麼子‘口誅筆伐’,後來又時興‘文攻武衛’,就是一路罵一路打囉,棍棒梭鏢砍刀叮鐺響,時不時有人頭破血流。1967年,到處打得一塌糊塗。有一天,崽伢子一瘸一拐地回來,邋遢死噠的,癡癡呆呆地,只港學校怕是守不住噠,要開闢新戰場。我跟他娘佬子勸他莫回克噠,反正學校已經不是學校,成噠戰場,不但讀不到書,還要打打殺殺,還是保命要緊,老老實實回來作田吧。他就是不服,只港他在捍衛‘革命路線’鬥爭中不能當逃兵,不能撇開一個戰壕裡的戰友不管,要共同戰鬥到底。總之不聽勸,修養幾天又回克噠。該一克就再也冇回來。”
講到這裡,樵夫把目光移向橋那邊的城市,那座城市遠一些的某個地方。
“老陳呐,你曉得原來的‘中蘇友好館’吧,就在五一路上,靠東頭那邊。1967年6月,‘高司’占噠那裡做‘指揮部’,聚噠百把人在裡頭‘辦公’。那個什麼‘工聯’的,還有個什麼“六號門”的,還有個什麼‘青近’的,還有個什麼‘風雷’的,幾百號人攻打那棟樓:搬雲梯丟磚頭啦,打彈弓啦,放鳥銃啦,放火燒啦,噴農藥啦,用消防龍頭沖水啦,斷水斷電啦,圍困噠好多天,裡頭的人實在熬不住噠,我崽伢子自告奮勇做談判代表,想討個‘優待俘虜’,才出樓下門口就被一遭拳腳一頓亂棍給打死噠。”。樵夫嗚咽了起來。
老陳嘟噥道:“那件事,有的說死了人,有的說沒死人;有的說是慘案,有的說是勝利。”
“冇死人?還是勝利?那就得看港該種話的都是些麼子人囉!我跟你港囉,就是在那天,6月6號吧,我崽被打死後,‘工聯’、‘六號門’的人沖進樓裡,打死七八個,打傷幾十個,要不是解放軍趕來制止,還不曉得會死好多人呢。該些事情是幾年後小姚回來跟我港的。”。樵夫憤然。
老陳忽然有一種莫名的感覺,不禁問道:“你兒子叫什麼名字?”
“丁輝,你認得不?”
“哦,丁輝。校方說他失蹤了。”。老陳心裡一陣酸楚,又喃喃道:
“自古都是‘勝者王,敗者寇’,強勢面前無理論,受難終是斯文人。”。老陳感歎。
“是囉,是囉。斯文人就應該做斯文事,老老實實做學問,莫克關心‘政治’‘時事’那些東西,你的道理有人聽嗎? 搞得不好要治罪的! 更莫跟什麼‘路線’哪‘鬥爭’哪攪和,你們該些書生鬥得過別個嗎? 做該些事情,那幫人是裡手,他們就是靠搞該些名堂起家的。心血來潮的時候騙你一把,搞事的時候用你一把,搞定以後甩你一把,不順眼就鬥你一把,覺得有威脅就乾脆殺你一把… ”。老丁既“世故”又“覺悟”。
“別說了,別再說了!”。老陳感觸萬千,趕忙打斷老丁的話,此刻他的心裡已不是酸楚,而是痛楚了。
老丁歎了口氣,冷靜下來,緩緩說道:“我是有些激動,大意噠,好在冇得人聽見,你總不至於克告發我擺?!我看你是斯文人,又是‘江麓’的,才跟你策些我那可憐的崽伢子的事,你莫在意噢。”。老丁已緩過神來。
老陳苦笑。凝視著遠處淩波蕩漾的江水,好似無意地問道:
“老丁哪,你說這汐江裡現在還有大魚嗎?”
“有還是有的,只不過比以前少得多噠。你曉得不,大魚最多是什麼年代?只怕你一世都猜不到。告訴你囉,該條江裡魚最多的時候是武鬥期間!那個時候,江裡連常有死屍,冇得人管,魚們就連常聚餐囉,長得滾豬爛壯的。’
“尤其到發大水的時候,漂下來的死屍就比平日多些,聽港多半是從桂林從道縣漂過來的。上游那邊打得蠻厲害,有些是鬧派性打仗被打死的,有些是翻舊賬搞報復被打死的。唉~,我就搞不懂何解要搞該麼大的運動要打死該麼多人呢?! 哈是鄉里鄉親何解要下狼心自相殘殺噻?!”
老丁一臉傷感。稍頓,緩口氣接著說:“該些年江裡乾淨得多噠,那些魚的日子冇得從前好過也就冇得幾條大魚噠。嘿嘿~。’
“何解,你想改行打漁啦?”。老丁乜眼瞟著老陳。
“想喂魚!”。老陳喃喃。
“喂魚?你是做學問的,又冇得池塘,養麼子鬼魚囉,神經病!”。老丁不屑。
“哎,老陳呐,太晚噠,堂客還等噠我的柴火搞飯呢,靠得住會挨駡。你也快走吧,烏昏黑暗的,只怕就要落雨噠,你腿腳不利索,注意安全,保重身體,有機會碰面再策,再會了!”。老丁起身挑起柴擔緩緩下山去了。
陳炎文不能回應“再會”這個告別詞,這個人之常情的詞彙,他在14年前與妻兒離別的時刻就回避過一次了。
他緩緩站起身來望著老丁漸漸遠去的背影,回味著老丁的話語,感慨萬分,歎了口氣,搖了搖頭。
此時,山風越來越緊,松濤越來越響,真的有點飄毛毛雨了。
他抬頭望瞭望陰沉沉的天空,轉過身子,面朝東方慢慢坐下,撫摸著那個沉甸甸的背包,再把目光移回那條江、那架橋、那座城,開始實施來到這片山脊松林的計畫 - “放電影”,再放一遍這部攝於他自己62年滄桑歷程的“紀錄片”。多少年來,他無數次試圖把自己放在旁觀者的視角來觀看這部“影片”,但每次卻還是不知不覺地融入了角色,總也逃避不了。
這回可是他最後一次當“放映員”,也是最後一次做唯一的“觀眾”了。
他神情遲疑,猶豫了好一陣子。然,還是狠狠心“打開鏡頭”,一幅幅不甚分明的畫面映上了陰沉的夜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