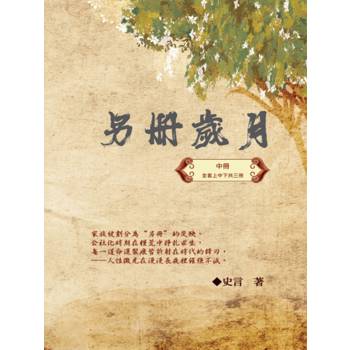26
總算要開學了。陰曆二月十一,天還“嗡黑”,周恆順告別了奶奶和洪秀表姐,挑上自己鼓鼓囊囊的書包,鋪蓋卷兒和兩個星期的煎餅,去上學了。當太陽從東方天際低矮的,平鋪沓的,蒼青色的山脊背後升起來的時候,他已經走出二十多裡路了。他有點累了,但還是快馬流星地急走。課業,學校的情況,班主任和任課老師的變化,徐靜茹和別的他尊敬並熱愛的老師的命運都讓他懸著心,他想早一步到學校,早一點知道些情況。一九五八年的早春,也許是受了政治氣候的影響,氣溫上升得格外快,頭兩天,剛下了一場雨,花草樹木,地裡的莊稼苗不管人間在頭年發生過什麼事情,全都在爭先恐後地,急不可待地忙著復蘇,萌生和成長。太陽在當頭頂上暖烘烘地照著,周恆順覺得自己身上冒汗了,刺刺撓撓的。他趕在中午開飯前進了一中大門。他不知道是自己心情使然,還是像運動中批判右派分子戴著“有色眼鏡”看社會現實的緣故,進校來,周恆順覺得學校沒有了往日的親切,溫馨,撲鼻的書香和斐然的文采,變得陌生,冷漠,甚至陰森可怖,幾乎認不出了。廣播喇叭裡播送的不是優美動聽的抒情歌曲,也不是活潑歡快的兒童歌曲,而是反右派鬥爭中剛出現的《社會主義好》,調子激昂,吐字像跟人爭吵,辯論,一聲聲像滾滾波濤往人耳朵裡灌,一條大紅的橫幅長龍般橫亙在校門上空,像紅色的閃電灼人眼睛,上邊寫著金黃色的大字:“熱烈慶祝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迎接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高潮!”校園裡,大字報蓆帳子還沒拆,三扯兩裂,躬腰凹肚,像曬得半乾的死牲口皮,蓆帳上,辦公室、教室的牆壁上各種顏色紙張的大字報、大標語經過風雨的剝蝕,淋漓,有的在脫落,抖抖挲挲,像窮人家幼兒的尿布,死趴趴地緊貼在上面的也已經字跡漶漫,混合上底紙紅黃綠各種顏色,顯得醜陋,怪異,慘不忍睹,路上的爛紙被風吹得和行人追逐,像調皮孩子搞惡作劇,這種景象,讓人想到激戰過後,硝煙散去,狼籍無狀的戰場。就連校園裡的花木,也不像往年春天那樣亮麗,動人,親切,而帶了些蠻不在乎,旁若無人,肆無忌憚的野性,好像在說,管他呢,咱長咱的。到處是垃圾,以及被冬天的雪,春天的雨漚成灰黑色的枯枝敗葉,路上見到的人都有點兒愣愣青青,像趕集的,像夢遊者,像打愣了的雞,像掐了頭的螞蚱,空氣中似乎飛舞著用各種筆跡寫的大大小小的“亂”字,讓人躲閃不迭。
周恆順先上了宿舍,宿舍裡的床鋪被住在這裡“反右”的人給搬得亂七八糟,幾個先到的同學正忙著搬動,復位。一個個陰沉著臉,肚子裡有氣,但是嘴上不說,像夏天河溝子裡肚子鼓鼓卻不叫喚的氣蛤蟆。周恆順放下行李,趕緊參加抬床板,拿了笤帚掃地。張峰有點異樣,虎著臉,從周恆順手裡要過笤帚,扔到一邊,說:“先不慌掃,人來齊了,弄好了鋪,打總掃,現在掃了,還得髒。”周恆順覺得經過這個五十多天的假期,同學們之間沒有因為分別而變得親熱,反倒顯得生分了,疏遠了,連素來寬厚、友善,大哥哥般的張峰也緊皺著眉頭,對人冷冷的。大家在宿舍裡收拾了一陣,有同學去伙房抬來了開水,各人舀了開水,拿出煎餅或窩頭,就著疙瘩鹹菜,吃午飯。同學們開始互相交換鹹菜,宿舍裡這才開始有了點活躍的氣息。那種窮學生,苦孩子之間惺惺相惜,親和友愛的情愫才開始慢慢地顯露,擴散,像酵母菌在發面盆裡孳生,膨脹。
午飯後,張峰帶領同學們到教室裡收拾桌椅,寒假期間,教室裡也搭了地鋪,必須重新收拾。大家到教室裡一看,更是一片狼籍。桌子椅子靠牆堆著,桌子上羅著腿兒朝上的桌子,頂上橫七豎八放著椅子,像拙劣的雜技疊羅漢,又像傻小子擺瞎了的積木,男生女生陸陸續續都來了,像是人多勢壯膽氣足了,有的同學開始大呼小叫,從上邊往下拿椅子的同學不時地叫喊:“好好接著,這又一個‘傷號兒’。”不少椅子被弄得缺胳膊少腿,張峰安排女生送到學校木工房去修。有人說:“在這裡住的都是當老師的,不知道愛護公物。”有人說:“可能是有人朝咱這裡的傢俱撒惡氣吧?”有同學“噓”一聲,說:“別胡扯了,新班主任老師來了。”大家都沉默了,因為他們已經知道,徐老師犯錯誤了,成了“右派分子”,正在勞動改造,不能再教課,更不能當他們的班主任了。據說,新換的班主任是去年剛從城關完小調來,教《生理衛生》的,名叫方向榮,大家知道這個消息後,都覺得心裡彆扭,但像黑夜中被人打了一悶棍,找不著人撒氣,又像吃飯碗裡有蒼蠅,想噦又噦不出來。他們為換掉徐老師心中不快,但是誰也不說,誰也不敢說。換這個方向榮來當他們的班主任,他們覺得是受了歧視,甚至是羞辱,是受徐老師牽累而受的懲罰。因為即使不考慮傳統上班主任一般由主課——語文、數學或外語老師擔任,即使退而求其次,讓副課老師當(班主任),也不應該是這個方向榮。因為此人是初師畢業,在小學教書,靠上盧正人以後,先調到城關完小,又調到一中,別的課教不了,教《生理衛生》,因為在課堂上形象地描述大腸的蠕動,引得同學們哄堂大笑,弄得一個嬌氣的女生當場嘔吐,一時傳為笑談。而且這個方向榮形象也太差,上不得臺面,個子矮,身子粗,像油簍,像麻袋,像磨墩子,或者像齊頭鑽子,長了個扁扁的,歪七扭八的腦袋,臉黑不溜丘,額頭凸起,眼窩深陷,兩隻小眼睛,賊不幾的。兩隻招風大耳朵,往前罩罩著,有人說他像《世界歷史》課本上那個鎮壓巴黎公社的梯也爾,說話公鴨嗓子,聽著讓人心煩乾噦。如果說,他們原先的班主任徐靜茹老師是美的極致,那這接替他的方向榮就是醜的樣板。這中間的落差太大,同學們一時適應不了,順不過勁兒來。這方向榮老師來到班裡,就扯開公鴨嗓子,裝腔作勢地發號施令,同學們也沒人搭理他。他不指揮還好些,同學們悶著頭收拾,他指揮了,大家乾脆停了下來,他急哧白裂地說:“怎麼回事,怎麼停了?”這人有個毛病,說話時往外噴唾沫星子,站在他旁邊的女同學慌忙躲開。同學們還是不動,張峰說:“方老師,我帶著同學們抓緊收拾,打掃,你先回辦公室,這邊弄完,你來驗收,你放心,保證不耽誤今晚上自習,更不用說明天上課了。”方向榮氣咻咻地說:“你們這個班,過去中毒太深了,今後要好好學習,加強改造。”張峰說:“那以後慢慢來。”方向榮說:“今晚上,全班在教室裡集合,我來講話,盧老師也來,組織好。”說完,晃著他的大腦袋,甩開他兩條短而粗的腿,像圓桶一樣磨遊磨遊地走了。教室裡不知誰怪叫了一聲,很多同學都笑了。張峰說:“笑什麼?有什麼可笑的?快點收拾。”周恆順祗覺得心裡彆扭,更覺得沒什麼值得一笑,另外,他“不擔事兒”,在種情況下,也不敢笑,一直沉著臉,站在那裡接椅子,再傳給別的同學。同學們見張峰不但沒笑,還生了氣,也就覺得剛才的情況並不可笑,而是可悲,也就不再傻笑了。
總算要開學了。陰曆二月十一,天還“嗡黑”,周恆順告別了奶奶和洪秀表姐,挑上自己鼓鼓囊囊的書包,鋪蓋卷兒和兩個星期的煎餅,去上學了。當太陽從東方天際低矮的,平鋪沓的,蒼青色的山脊背後升起來的時候,他已經走出二十多裡路了。他有點累了,但還是快馬流星地急走。課業,學校的情況,班主任和任課老師的變化,徐靜茹和別的他尊敬並熱愛的老師的命運都讓他懸著心,他想早一步到學校,早一點知道些情況。一九五八年的早春,也許是受了政治氣候的影響,氣溫上升得格外快,頭兩天,剛下了一場雨,花草樹木,地裡的莊稼苗不管人間在頭年發生過什麼事情,全都在爭先恐後地,急不可待地忙著復蘇,萌生和成長。太陽在當頭頂上暖烘烘地照著,周恆順覺得自己身上冒汗了,刺刺撓撓的。他趕在中午開飯前進了一中大門。他不知道是自己心情使然,還是像運動中批判右派分子戴著“有色眼鏡”看社會現實的緣故,進校來,周恆順覺得學校沒有了往日的親切,溫馨,撲鼻的書香和斐然的文采,變得陌生,冷漠,甚至陰森可怖,幾乎認不出了。廣播喇叭裡播送的不是優美動聽的抒情歌曲,也不是活潑歡快的兒童歌曲,而是反右派鬥爭中剛出現的《社會主義好》,調子激昂,吐字像跟人爭吵,辯論,一聲聲像滾滾波濤往人耳朵裡灌,一條大紅的橫幅長龍般橫亙在校門上空,像紅色的閃電灼人眼睛,上邊寫著金黃色的大字:“熱烈慶祝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迎接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高潮!”校園裡,大字報蓆帳子還沒拆,三扯兩裂,躬腰凹肚,像曬得半乾的死牲口皮,蓆帳上,辦公室、教室的牆壁上各種顏色紙張的大字報、大標語經過風雨的剝蝕,淋漓,有的在脫落,抖抖挲挲,像窮人家幼兒的尿布,死趴趴地緊貼在上面的也已經字跡漶漫,混合上底紙紅黃綠各種顏色,顯得醜陋,怪異,慘不忍睹,路上的爛紙被風吹得和行人追逐,像調皮孩子搞惡作劇,這種景象,讓人想到激戰過後,硝煙散去,狼籍無狀的戰場。就連校園裡的花木,也不像往年春天那樣亮麗,動人,親切,而帶了些蠻不在乎,旁若無人,肆無忌憚的野性,好像在說,管他呢,咱長咱的。到處是垃圾,以及被冬天的雪,春天的雨漚成灰黑色的枯枝敗葉,路上見到的人都有點兒愣愣青青,像趕集的,像夢遊者,像打愣了的雞,像掐了頭的螞蚱,空氣中似乎飛舞著用各種筆跡寫的大大小小的“亂”字,讓人躲閃不迭。
周恆順先上了宿舍,宿舍裡的床鋪被住在這裡“反右”的人給搬得亂七八糟,幾個先到的同學正忙著搬動,復位。一個個陰沉著臉,肚子裡有氣,但是嘴上不說,像夏天河溝子裡肚子鼓鼓卻不叫喚的氣蛤蟆。周恆順放下行李,趕緊參加抬床板,拿了笤帚掃地。張峰有點異樣,虎著臉,從周恆順手裡要過笤帚,扔到一邊,說:“先不慌掃,人來齊了,弄好了鋪,打總掃,現在掃了,還得髒。”周恆順覺得經過這個五十多天的假期,同學們之間沒有因為分別而變得親熱,反倒顯得生分了,疏遠了,連素來寬厚、友善,大哥哥般的張峰也緊皺著眉頭,對人冷冷的。大家在宿舍裡收拾了一陣,有同學去伙房抬來了開水,各人舀了開水,拿出煎餅或窩頭,就著疙瘩鹹菜,吃午飯。同學們開始互相交換鹹菜,宿舍裡這才開始有了點活躍的氣息。那種窮學生,苦孩子之間惺惺相惜,親和友愛的情愫才開始慢慢地顯露,擴散,像酵母菌在發面盆裡孳生,膨脹。
午飯後,張峰帶領同學們到教室裡收拾桌椅,寒假期間,教室裡也搭了地鋪,必須重新收拾。大家到教室裡一看,更是一片狼籍。桌子椅子靠牆堆著,桌子上羅著腿兒朝上的桌子,頂上橫七豎八放著椅子,像拙劣的雜技疊羅漢,又像傻小子擺瞎了的積木,男生女生陸陸續續都來了,像是人多勢壯膽氣足了,有的同學開始大呼小叫,從上邊往下拿椅子的同學不時地叫喊:“好好接著,這又一個‘傷號兒’。”不少椅子被弄得缺胳膊少腿,張峰安排女生送到學校木工房去修。有人說:“在這裡住的都是當老師的,不知道愛護公物。”有人說:“可能是有人朝咱這裡的傢俱撒惡氣吧?”有同學“噓”一聲,說:“別胡扯了,新班主任老師來了。”大家都沉默了,因為他們已經知道,徐老師犯錯誤了,成了“右派分子”,正在勞動改造,不能再教課,更不能當他們的班主任了。據說,新換的班主任是去年剛從城關完小調來,教《生理衛生》的,名叫方向榮,大家知道這個消息後,都覺得心裡彆扭,但像黑夜中被人打了一悶棍,找不著人撒氣,又像吃飯碗裡有蒼蠅,想噦又噦不出來。他們為換掉徐老師心中不快,但是誰也不說,誰也不敢說。換這個方向榮來當他們的班主任,他們覺得是受了歧視,甚至是羞辱,是受徐老師牽累而受的懲罰。因為即使不考慮傳統上班主任一般由主課——語文、數學或外語老師擔任,即使退而求其次,讓副課老師當(班主任),也不應該是這個方向榮。因為此人是初師畢業,在小學教書,靠上盧正人以後,先調到城關完小,又調到一中,別的課教不了,教《生理衛生》,因為在課堂上形象地描述大腸的蠕動,引得同學們哄堂大笑,弄得一個嬌氣的女生當場嘔吐,一時傳為笑談。而且這個方向榮形象也太差,上不得臺面,個子矮,身子粗,像油簍,像麻袋,像磨墩子,或者像齊頭鑽子,長了個扁扁的,歪七扭八的腦袋,臉黑不溜丘,額頭凸起,眼窩深陷,兩隻小眼睛,賊不幾的。兩隻招風大耳朵,往前罩罩著,有人說他像《世界歷史》課本上那個鎮壓巴黎公社的梯也爾,說話公鴨嗓子,聽著讓人心煩乾噦。如果說,他們原先的班主任徐靜茹老師是美的極致,那這接替他的方向榮就是醜的樣板。這中間的落差太大,同學們一時適應不了,順不過勁兒來。這方向榮老師來到班裡,就扯開公鴨嗓子,裝腔作勢地發號施令,同學們也沒人搭理他。他不指揮還好些,同學們悶著頭收拾,他指揮了,大家乾脆停了下來,他急哧白裂地說:“怎麼回事,怎麼停了?”這人有個毛病,說話時往外噴唾沫星子,站在他旁邊的女同學慌忙躲開。同學們還是不動,張峰說:“方老師,我帶著同學們抓緊收拾,打掃,你先回辦公室,這邊弄完,你來驗收,你放心,保證不耽誤今晚上自習,更不用說明天上課了。”方向榮氣咻咻地說:“你們這個班,過去中毒太深了,今後要好好學習,加強改造。”張峰說:“那以後慢慢來。”方向榮說:“今晚上,全班在教室裡集合,我來講話,盧老師也來,組織好。”說完,晃著他的大腦袋,甩開他兩條短而粗的腿,像圓桶一樣磨遊磨遊地走了。教室裡不知誰怪叫了一聲,很多同學都笑了。張峰說:“笑什麼?有什麼可笑的?快點收拾。”周恆順祗覺得心裡彆扭,更覺得沒什麼值得一笑,另外,他“不擔事兒”,在種情況下,也不敢笑,一直沉著臉,站在那裡接椅子,再傳給別的同學。同學們見張峰不但沒笑,還生了氣,也就覺得剛才的情況並不可笑,而是可悲,也就不再傻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