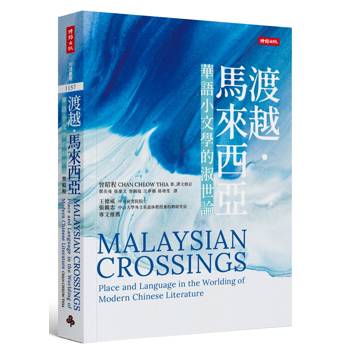「文」生在世與「家園」情懷:馬華文學及其研究的南方境遇
(一)馬華文學存世的祈願
本書英文原著以Malaysian Crossings: Place and Language in the World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為題,於2022年歲末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推出,眼下譯為《渡越.馬來西亞:華語小文學的淑世論》面世。書名由數個關鍵詞串連而成,正文將一一剖析其中的指涉,於此我則希望分享與課題緣起及發展相關的思想際會。回首研究的初衷,我一直非常好奇:一個華語文學社群何以能在資源和關注如此匱乏的情況下堅持創作,不斷交出亮眼的作品,並且也能根據社群?的論辯,制定一套關乎其歷史定位、美學考量和書寫倫理的自我認識?
猶記得讀博期間,我曾依循臺灣文學的論述先例,將文本生產和知識社群之建立所共同撐起的整個跨域文化構形(formation)稱作「文學馬來西亞」(Literary Malaysia); 但由於我的關注面更多集中在馬來亞和馬來西亞的華語文學,「文學馬華」的稱說應更為適切。隨著學術探索的延展,專書的追問變成:「文學馬華」是怎樣的一種存續樣態?從某種意義上說,馬華文學的處境類如新加坡在現實世界中的地緣政治處境。言及島國的生存境況,歷史學家陳大榮將之形容為「不受約束的渺小」(smallness unconstrained)。在他看來,「渺小雖然是新加坡歷史的中心主題,卻沒有限制它作為城市、作為國度和作為民族國家的進化」。而我以為「不受約束的渺小」亦適合用來理解在世界華語文學空間裡面對多重限制的馬華文學。經年累月後,這個文化構形在創作方面已取得醒目的建樹:有作家贏得國際性的專業讚譽(例如,張貴興獲頒2023年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有作家還開拓了廣大的市場(例如,黎紫書2020年的長篇小說《流俗地》在中國大陸兼具口碑與銷量),而學界更藉助馬華文學來重繪現代華語文學生產的全球圖景。
然而,與其說《渡越.馬來西亞》探究馬華文學「成功的祕訣」,毋寧說它關注的是如何開掘新的角度,來思考馬華文學複雜起伏的現代歷史經驗。專書包含了我長期閱讀馬華文學與追蹤相關論述後的想法,主要闡述「文學馬華」所涵納的一種頗具弔詭意味的創作抱負與進路:馬華文學的作家多能深刻省思他們在世界華語文學空間裡的邊緣性,亦十分懂得善用相關的糾結進行創新。換言之,儘管文化資源稀缺,寫作生命也一直不穩定,但馬華作家並未因此退縮。對高度自覺的他們而言,位處邊緣不是難以自拔的境遇,而是切實可行的創作常態。
上述的中心論點也許會被看作在事實上無法周延,但類似的觀察非我獨有。言及它流通的局限,黃錦樹就曾評斷:「作為失敗的商品讓它?按:馬華文學?在市場經濟處於邊緣倒有一個預想不到的好處:可以讓生產者死心塌地的讓文學維持它古老的手工業身分,不管是為文學自身的道義,還是『以詩存史』的歷史道義」。換個說法,反正外界有太多不可控制的面向,馬華作家無須對缺乏書市認可的現象進行過度的分析,而只需認真、專注地做好創作的本分。
再者,如起首的引文所示,董啟章曾透過黎紫書的首個長篇實踐辨識,馬華文學是一種希冀「見證自身在時光中的存在和不滅」的文學,儘管極不起眼,所在之處也十分隱蔽,卻?含存世與傳世的欲望。十年後,黎紫書再有長篇問世,即便業已打開中國市場,並自我期許成為「世界性的中文作家」,但她仍保持對個人創作出身的清醒認知。根據她自己的表述:「當一個馬華作家,你就知道自己追求的肯定不是那種世俗眼中的成功,比如說賣得很好,或是成為很火的作家,因為馬來?按:馬來西亞?的文學市場就那麼大……而想要享受寫作帶來的樂趣,就必須不斷地超越和挑戰自我。」
從一個非國家的地域尺度出發,林建國則提到大山?(Bukit Mertajam)文學的現代主義起源離不開各種物質和文化資源的不足。他進而不僅斷言「貧窮,外加困頓決定了大山?文學的色澤」,更擴大貧窮的再現意義,將之視作馬華文學現代性的文本症候:「我們往往不知道馬華文學在寫什?。好不容易拉出一個省視距離……方才驚覺,很多時候我們寫的是貧窮」。民生困蹇的再現原來業已變成整個文學構形繁衍再生的觸媒,以及具代表性的標記。而相對於林建國以國家內部的場址(site)進行詮釋,張錦忠依循斷代的分析加以引申,闡述馬華作家如何不約而同地展演一種集體向上、各自努力的創作趨向:
馬華文學自「有國籍」以來,在共同體?按:國家?之?的無所作為,以迄於今。但是「自強」(strong)的個體,在共同體裡頭自能「?立雞群」,或突圍而出,像暗夜或荒野中的巨人那樣孤獨、清醒、成長、進擊。因此,這也解釋了何以七?年代以來,商晚筠、潘雨桐、李永平、張貴興、陳大為、黃錦樹、黎紫書、鍾怡雯、賀淑芳等人能夠卓然脫穎,因為他們在共同體之外書寫,成為自己的書寫主體。顯然從共同體的終結到個體的茁長,才是「文學」的誕生。
在張錦忠筆下,馬華作家自1970年代起以退為進的取態,可謂包含了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描述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意即「一種現時在場的,處於活躍著的、正相互關聯著的連續性之中的實踐意識」,凝結了馬來西亞建國以來華人的集體社會經驗和社會關係,具有「新興性、聯結性和主導性」,並「賦予某一代人或某一時期以意義」。從張錦忠的角度審視,在馬華文學的語境裡,真正的「共同體」的鍛造在馬來西亞獨立後不久即不再依賴國家,轉而於民間以「個體」的邏輯找到另造和維續的方式。
不謀而俱述,賀淑芳在另一場合猶如連?了威廉斯所謂的「作為感受的思想觀念和作為思想觀念的感受」,以便為馬華作家代言,並經由勾畫馬華文學與國家體制的互動協商,體現了張錦忠論及的「感覺結構」。配合其短篇小說集《湖面如鏡》的英譯本出版,她在向新讀者引介馬華文學時,娓娓道出作家在接受其身分處境遇後的創作對策:
(一)馬華文學存世的祈願
本書英文原著以Malaysian Crossings: Place and Language in the World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為題,於2022年歲末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推出,眼下譯為《渡越.馬來西亞:華語小文學的淑世論》面世。書名由數個關鍵詞串連而成,正文將一一剖析其中的指涉,於此我則希望分享與課題緣起及發展相關的思想際會。回首研究的初衷,我一直非常好奇:一個華語文學社群何以能在資源和關注如此匱乏的情況下堅持創作,不斷交出亮眼的作品,並且也能根據社群?的論辯,制定一套關乎其歷史定位、美學考量和書寫倫理的自我認識?
猶記得讀博期間,我曾依循臺灣文學的論述先例,將文本生產和知識社群之建立所共同撐起的整個跨域文化構形(formation)稱作「文學馬來西亞」(Literary Malaysia); 但由於我的關注面更多集中在馬來亞和馬來西亞的華語文學,「文學馬華」的稱說應更為適切。隨著學術探索的延展,專書的追問變成:「文學馬華」是怎樣的一種存續樣態?從某種意義上說,馬華文學的處境類如新加坡在現實世界中的地緣政治處境。言及島國的生存境況,歷史學家陳大榮將之形容為「不受約束的渺小」(smallness unconstrained)。在他看來,「渺小雖然是新加坡歷史的中心主題,卻沒有限制它作為城市、作為國度和作為民族國家的進化」。而我以為「不受約束的渺小」亦適合用來理解在世界華語文學空間裡面對多重限制的馬華文學。經年累月後,這個文化構形在創作方面已取得醒目的建樹:有作家贏得國際性的專業讚譽(例如,張貴興獲頒2023年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有作家還開拓了廣大的市場(例如,黎紫書2020年的長篇小說《流俗地》在中國大陸兼具口碑與銷量),而學界更藉助馬華文學來重繪現代華語文學生產的全球圖景。
然而,與其說《渡越.馬來西亞》探究馬華文學「成功的祕訣」,毋寧說它關注的是如何開掘新的角度,來思考馬華文學複雜起伏的現代歷史經驗。專書包含了我長期閱讀馬華文學與追蹤相關論述後的想法,主要闡述「文學馬華」所涵納的一種頗具弔詭意味的創作抱負與進路:馬華文學的作家多能深刻省思他們在世界華語文學空間裡的邊緣性,亦十分懂得善用相關的糾結進行創新。換言之,儘管文化資源稀缺,寫作生命也一直不穩定,但馬華作家並未因此退縮。對高度自覺的他們而言,位處邊緣不是難以自拔的境遇,而是切實可行的創作常態。
上述的中心論點也許會被看作在事實上無法周延,但類似的觀察非我獨有。言及它流通的局限,黃錦樹就曾評斷:「作為失敗的商品讓它?按:馬華文學?在市場經濟處於邊緣倒有一個預想不到的好處:可以讓生產者死心塌地的讓文學維持它古老的手工業身分,不管是為文學自身的道義,還是『以詩存史』的歷史道義」。換個說法,反正外界有太多不可控制的面向,馬華作家無須對缺乏書市認可的現象進行過度的分析,而只需認真、專注地做好創作的本分。
再者,如起首的引文所示,董啟章曾透過黎紫書的首個長篇實踐辨識,馬華文學是一種希冀「見證自身在時光中的存在和不滅」的文學,儘管極不起眼,所在之處也十分隱蔽,卻?含存世與傳世的欲望。十年後,黎紫書再有長篇問世,即便業已打開中國市場,並自我期許成為「世界性的中文作家」,但她仍保持對個人創作出身的清醒認知。根據她自己的表述:「當一個馬華作家,你就知道自己追求的肯定不是那種世俗眼中的成功,比如說賣得很好,或是成為很火的作家,因為馬來?按:馬來西亞?的文學市場就那麼大……而想要享受寫作帶來的樂趣,就必須不斷地超越和挑戰自我。」
從一個非國家的地域尺度出發,林建國則提到大山?(Bukit Mertajam)文學的現代主義起源離不開各種物質和文化資源的不足。他進而不僅斷言「貧窮,外加困頓決定了大山?文學的色澤」,更擴大貧窮的再現意義,將之視作馬華文學現代性的文本症候:「我們往往不知道馬華文學在寫什?。好不容易拉出一個省視距離……方才驚覺,很多時候我們寫的是貧窮」。民生困蹇的再現原來業已變成整個文學構形繁衍再生的觸媒,以及具代表性的標記。而相對於林建國以國家內部的場址(site)進行詮釋,張錦忠依循斷代的分析加以引申,闡述馬華作家如何不約而同地展演一種集體向上、各自努力的創作趨向:
馬華文學自「有國籍」以來,在共同體?按:國家?之?的無所作為,以迄於今。但是「自強」(strong)的個體,在共同體裡頭自能「?立雞群」,或突圍而出,像暗夜或荒野中的巨人那樣孤獨、清醒、成長、進擊。因此,這也解釋了何以七?年代以來,商晚筠、潘雨桐、李永平、張貴興、陳大為、黃錦樹、黎紫書、鍾怡雯、賀淑芳等人能夠卓然脫穎,因為他們在共同體之外書寫,成為自己的書寫主體。顯然從共同體的終結到個體的茁長,才是「文學」的誕生。
在張錦忠筆下,馬華作家自1970年代起以退為進的取態,可謂包含了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描述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意即「一種現時在場的,處於活躍著的、正相互關聯著的連續性之中的實踐意識」,凝結了馬來西亞建國以來華人的集體社會經驗和社會關係,具有「新興性、聯結性和主導性」,並「賦予某一代人或某一時期以意義」。從張錦忠的角度審視,在馬華文學的語境裡,真正的「共同體」的鍛造在馬來西亞獨立後不久即不再依賴國家,轉而於民間以「個體」的邏輯找到另造和維續的方式。
不謀而俱述,賀淑芳在另一場合猶如連?了威廉斯所謂的「作為感受的思想觀念和作為思想觀念的感受」,以便為馬華作家代言,並經由勾畫馬華文學與國家體制的互動協商,體現了張錦忠論及的「感覺結構」。配合其短篇小說集《湖面如鏡》的英譯本出版,她在向新讀者引介馬華文學時,娓娓道出作家在接受其身分處境遇後的創作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