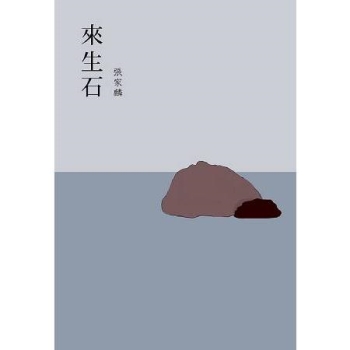淡水觀音坐
汗水
變成一種
最濃的膠水
把左手與右手
緊緊黏在一起
我的右手妳的左手
不再分開
緊貼在一起的春天
上弦月的唇
與下弦月的唇
吻成一個滿月的圓
月亮橙色的笑容
是生命豐腴的盤子
生活如飛鳥的夜
安靜的翅膀
圓的鑼聲圓的鼓
淡水安靜的午後
週一的河水
如課堂安靜的學生
喧鬧躲起來
帆影藏在樹蔭下
貓輕輕的走著
咖啡煮沸的香味
是妳貼在我胸前的髮絲
坐著
觀音山臥著
笑看我們的禪坐
無須語言
水沒有痕跡移動
海在足尖
輕推著小舟
遠方很近是太陽的汗珠
兩個肩膀重疊
變成海鷗的翅膀
拉高一種凝視的印象
把安靜變成一張雙人素描
安置在淡水的海岸線上
紅樹林的螃蟹有了家
雕塑時光
我們沉睡了相擁了
輕輕的清清的蝶
輕輕的吻
清清的手
在老榕樹鬚根
飛揚的午後
飄在圖書館的牆角
想等天暗
再送妳回南門
古城牆邊的燈下
那時校園悠悠
讀余光中的詩
看張曉風的散文
想王尚義
野鴿子的黃昏
那個時代很笛卡兒
總想學徐志摩
想把妳這片雲帶走
不曾揮手
雲仍然隨著風走
我不屬於風的信子
而妳是蝶
再用妳的名字寫詩
也只能遠望
蓮池潭
那朵睡蓮的秋天
巷子口
拿著糧票
領米領麵領黃豆
領油鹽還有
媽媽們賣糧票的聲音
爸媽離不開這個島
總把紐約當成子女的天堂
或者另外一個國
都是一種家庭的驕傲
我們在骨子裡被形塑一種
旅行的基因
當〈梨山癡情花〉在那個年代
被唱響那魯灣時
我無法當勇士
守住那隻
輕輕的清清的蝶
飛遠竹籬笆的土牆
南門的圓環
怎麼轉
只能找到小時的米粉羹
土孩子望著蝶
輕輕的清清的
永遠的吻
累了我們會等妳回來
撿骨
跪在這條白線的外端
棺槨面對著爐門
裡面有一千度的火
電動的按鈕即將壓下
法師念著經
讓我們說
火來了快跑
希望肉身烈火羽化
而魂魄不被赤焰帶走
火來了快跑
棺木奔向烈火
靈魂在我們的唇邊
是否真的能逃得了
我們跪在白線的外端
總有自己跨越的
烈火選擇
等待炎熱與降溫
秋天是膝蓋旁的睡蓮
黑色晶體的骨灰罈打開
一盤涼的白骨推出
今生所有的豔彩
都擺在總結的淚水中
沒有舍利子的佛身
只是懷念慈悲歲月
從腳到腿到身
最後一塊頭骨
天靈蓋的封頂
仍然擺成一個人
盤坐的形體
封膠鎖緊
這一生終於抖落
孝衣的滄桑
來世為什麼還要來
不來了
不要烈火不要這
小小罈子的幽閉長子
就應該承擔
掛在脖子上的袋子
把罈子放在胸口
抱緊再抱緊
不捨仍然要捨
送進一個更幽閉的格子
法師打著羅盤
方位可以庇佑子孫
我們在遠方流浪
歸向的動因
不是方位不需羅盤
而是愧疚的懷念
紐約東京台北上海的夜
都有格子都有烈火
都有這天靈蓋
最後的觸摸與淚水
來世不來了
暈眩的旅行箱
前面飛行的標籤
還沒有撕掉
新的標籤
又貼上旅行箱
每次都匆匆的撕掉
又急切的貼上
不曾想留下任何記錄
不像一些旅行者
喜歡貼滿旅行的標籤
顯耀腳程的痕跡
而我只是撕下貼上
暈眩在空間與時間追逐
旅行箱我的沉默
永遠找不到一個落腳處
如雲端的雲
搖曳在旋轉之中
經常
在夢中醒來
不知道自己究竟
在哪個城市
快速變遷
讓意念不能夠休息
陀螺靠著繩子的力量
我是旋舞的陀螺
卻沒有繩子
臉不認識自己的臉
十年
繞了赤道五十圈
標籤貼滿眼睛
旅行箱的輪子滾薄了
我的翅膀很疲倦
眼睛和輪子都睏了
明天
還要貼上新的標籤
每一個機場
都是焦慮的迷宮
滾動的輪子穿梭
膚色和語言
變成一種梵音
想找一口銅鐘
把自己封印在裡面
一千年後
再打開
打開一千年後
輪子不再轉動
沒有我的標籤
沒有高與低的疼痛
不再有風箏與線的等待
萬千年的甦醒
有些白的霧
有些黑的霾
夾雜著黃和灰的厚度
把這個城市覆蓋
包圍在低度的空間中
壓抑窒息
感覺幽閉在無數條
吐信纏繞的蛇群中
不敢觸摸
霧霾如蛇舞
我們也有一種舞蹈
和牠對抗
雪不再下了
厚衣服嚴實的口罩
露出無奈的眼神
歲末北京
壓低頭
我們移動在
萬千年
地下屍體腐化
黑色昇華的噴油中
燃燒萬千年
森林碳化的火焰
溫度改變了
天的眼睛
地的呼吸
北京
這個霧霾的週末
忙碌在黑色的希望中
萬千年的甦醒
其實天本是藍的
水綠山也青
白色的炊煙
是童年單純的夢
我們追逐複雜
讓自己成熟
總想山水變色
把足跡踏遍征服的
一種紅色信念中
享受
手臂張開如鐵翅
鋼輪如滾動的蹄
交換著蓮花的舌
偽裝如戲台主角
變換面具的紛飛
然後給自己
一種虛偽的定義
把豐富典藏祖先的魂
當成享受的燭光
照亮眼睛火熱的聚光
讓霧成為詩
讓霾唱成歌
然後懺悔在白髮的
霧霾季節
想綠與藍與白
遙遠的日子
觸動祖靈的祭日
我們回歸
北京霧霾的圖騰
寧靜的蹲下與彎腰
汗水
變成一種
最濃的膠水
把左手與右手
緊緊黏在一起
我的右手妳的左手
不再分開
緊貼在一起的春天
上弦月的唇
與下弦月的唇
吻成一個滿月的圓
月亮橙色的笑容
是生命豐腴的盤子
生活如飛鳥的夜
安靜的翅膀
圓的鑼聲圓的鼓
淡水安靜的午後
週一的河水
如課堂安靜的學生
喧鬧躲起來
帆影藏在樹蔭下
貓輕輕的走著
咖啡煮沸的香味
是妳貼在我胸前的髮絲
坐著
觀音山臥著
笑看我們的禪坐
無須語言
水沒有痕跡移動
海在足尖
輕推著小舟
遠方很近是太陽的汗珠
兩個肩膀重疊
變成海鷗的翅膀
拉高一種凝視的印象
把安靜變成一張雙人素描
安置在淡水的海岸線上
紅樹林的螃蟹有了家
雕塑時光
我們沉睡了相擁了
輕輕的清清的蝶
輕輕的吻
清清的手
在老榕樹鬚根
飛揚的午後
飄在圖書館的牆角
想等天暗
再送妳回南門
古城牆邊的燈下
那時校園悠悠
讀余光中的詩
看張曉風的散文
想王尚義
野鴿子的黃昏
那個時代很笛卡兒
總想學徐志摩
想把妳這片雲帶走
不曾揮手
雲仍然隨著風走
我不屬於風的信子
而妳是蝶
再用妳的名字寫詩
也只能遠望
蓮池潭
那朵睡蓮的秋天
巷子口
拿著糧票
領米領麵領黃豆
領油鹽還有
媽媽們賣糧票的聲音
爸媽離不開這個島
總把紐約當成子女的天堂
或者另外一個國
都是一種家庭的驕傲
我們在骨子裡被形塑一種
旅行的基因
當〈梨山癡情花〉在那個年代
被唱響那魯灣時
我無法當勇士
守住那隻
輕輕的清清的蝶
飛遠竹籬笆的土牆
南門的圓環
怎麼轉
只能找到小時的米粉羹
土孩子望著蝶
輕輕的清清的
永遠的吻
累了我們會等妳回來
撿骨
跪在這條白線的外端
棺槨面對著爐門
裡面有一千度的火
電動的按鈕即將壓下
法師念著經
讓我們說
火來了快跑
希望肉身烈火羽化
而魂魄不被赤焰帶走
火來了快跑
棺木奔向烈火
靈魂在我們的唇邊
是否真的能逃得了
我們跪在白線的外端
總有自己跨越的
烈火選擇
等待炎熱與降溫
秋天是膝蓋旁的睡蓮
黑色晶體的骨灰罈打開
一盤涼的白骨推出
今生所有的豔彩
都擺在總結的淚水中
沒有舍利子的佛身
只是懷念慈悲歲月
從腳到腿到身
最後一塊頭骨
天靈蓋的封頂
仍然擺成一個人
盤坐的形體
封膠鎖緊
這一生終於抖落
孝衣的滄桑
來世為什麼還要來
不來了
不要烈火不要這
小小罈子的幽閉長子
就應該承擔
掛在脖子上的袋子
把罈子放在胸口
抱緊再抱緊
不捨仍然要捨
送進一個更幽閉的格子
法師打著羅盤
方位可以庇佑子孫
我們在遠方流浪
歸向的動因
不是方位不需羅盤
而是愧疚的懷念
紐約東京台北上海的夜
都有格子都有烈火
都有這天靈蓋
最後的觸摸與淚水
來世不來了
暈眩的旅行箱
前面飛行的標籤
還沒有撕掉
新的標籤
又貼上旅行箱
每次都匆匆的撕掉
又急切的貼上
不曾想留下任何記錄
不像一些旅行者
喜歡貼滿旅行的標籤
顯耀腳程的痕跡
而我只是撕下貼上
暈眩在空間與時間追逐
旅行箱我的沉默
永遠找不到一個落腳處
如雲端的雲
搖曳在旋轉之中
經常
在夢中醒來
不知道自己究竟
在哪個城市
快速變遷
讓意念不能夠休息
陀螺靠著繩子的力量
我是旋舞的陀螺
卻沒有繩子
臉不認識自己的臉
十年
繞了赤道五十圈
標籤貼滿眼睛
旅行箱的輪子滾薄了
我的翅膀很疲倦
眼睛和輪子都睏了
明天
還要貼上新的標籤
每一個機場
都是焦慮的迷宮
滾動的輪子穿梭
膚色和語言
變成一種梵音
想找一口銅鐘
把自己封印在裡面
一千年後
再打開
打開一千年後
輪子不再轉動
沒有我的標籤
沒有高與低的疼痛
不再有風箏與線的等待
萬千年的甦醒
有些白的霧
有些黑的霾
夾雜著黃和灰的厚度
把這個城市覆蓋
包圍在低度的空間中
壓抑窒息
感覺幽閉在無數條
吐信纏繞的蛇群中
不敢觸摸
霧霾如蛇舞
我們也有一種舞蹈
和牠對抗
雪不再下了
厚衣服嚴實的口罩
露出無奈的眼神
歲末北京
壓低頭
我們移動在
萬千年
地下屍體腐化
黑色昇華的噴油中
燃燒萬千年
森林碳化的火焰
溫度改變了
天的眼睛
地的呼吸
北京
這個霧霾的週末
忙碌在黑色的希望中
萬千年的甦醒
其實天本是藍的
水綠山也青
白色的炊煙
是童年單純的夢
我們追逐複雜
讓自己成熟
總想山水變色
把足跡踏遍征服的
一種紅色信念中
享受
手臂張開如鐵翅
鋼輪如滾動的蹄
交換著蓮花的舌
偽裝如戲台主角
變換面具的紛飛
然後給自己
一種虛偽的定義
把豐富典藏祖先的魂
當成享受的燭光
照亮眼睛火熱的聚光
讓霧成為詩
讓霾唱成歌
然後懺悔在白髮的
霧霾季節
想綠與藍與白
遙遠的日子
觸動祖靈的祭日
我們回歸
北京霧霾的圖騰
寧靜的蹲下與彎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