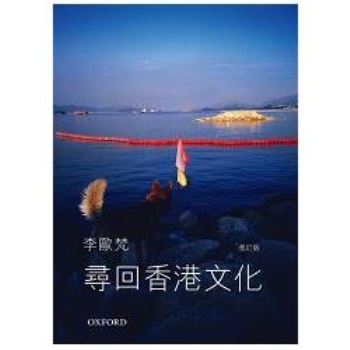─尋回香港文化
香港回歸五週年有感
香港回歸五年,從文化意義而言,是否可以斷言已經回歸了祖國文化?「一國兩制」的制度,是否仍然適用於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文化?最近香港政府提出的口號──香港成為「亞洲」的國際都市,其文化意涵是甚麼?是否要超越「祖國」的國際大都市──如上海?這一連串的問題,是我個人在回歸五週年前夕所能想到的,卻不一定能夠提出充份的解答方案。不過,既然已經提出了命提,不妨也試着演繹一番。
記得九七年回歸的前夕,香港人最關心的認同問題:香港人的身份究竟是甚麼?將來有何變化?而這種認同焦慮的背後因素,當然是政治和歷史。
然而,曾幾何時,認同問題已經沒有人討論,似乎也不成問題了。香港人已經認命,乖乖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區公民,持特區護照和回鄉證,但往返祖國與外國,卻比祖國人民更方便,這不得不說是「一國兩制」之賜。
但香港人似乎也不再討論英國殖民的歷史遺產。作了一百多年的英國殖民地公民,他們竟然可以在一夜之間搖身一變,從「女皇」改認「同志」(這個典故來自當年羅大佑的一首名歌《皇后大道中》);從英國米字旗(英國曾有「大不列顛世界永不日落」的殖民口號)改升中國五星旗;從「親英」突然變成「親中」(特別見之於香港的富豪和高官),這個現象,似乎也沒有人作更深層的討論。
我認為這是英國殖民主義最典型的特色,它和法國殖民主義最大的不同,就是對殖民地的統治只重制度和經濟,不重文化。影響所及,英國殖民地的人民對於英國王子的文化並沒有深刻的認識,當然也沒有依戀。
誠然,不少其他英國殖民地的精英,如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V.S.Naipaul),在留學英國後沾染了不少英國人的習慣,甚至比英國人更「英化」,但他們的心理也較香港人複雜,對英國主子的愛恨交織,遠較香港人為深。我想原因無他,大部份香港人的文化深層結構,本來就是中國式的,而且根深蒂固,即使有外來文化侵入,馬上可以將之「漢化」,變成自己的東西,香港茶餐廳的奶茶即是一例。所以,香港華人當中,雖然也有不少「假洋鬼子」,但畢竟是假的,對英國文化的了解,僅止於皮毛而已。
然而,這種皮毛現象也產生了另一種悖論:一般香港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也不深,僅止於人類學所說的文化──日常生活中的風俗習慣和行為舉止而已。而且這種文化的基礎,基本上是嶺南文化。回歸以後,我覺得香港人似乎較從前更「本土化」了,也就是更加執著於多年來賴以為升的嶺南文化。香港人甚至把珠江以北的所有中國地區,都稱之為北方,把大陸人稱之為北佬,大陸妓女則稱之為北姑等等。
這種心理上的南北區分,當然也是一種自我保護的假象。但是影響之下,使得香港人學習普通話更感困難;面對以北京為主的祖國文化,似乎也抱着愛理不理的被動心態,這在香港的大學生中,表現得最明顯。我甚至認為,香港年輕人對日本通俗文化的嚮往,遠在對祖國文化之上。如果這個推斷屬實,將會造成一個不大不小的危機。
這個危機,其實已經漸露端倪,可以見之於最近電視上的猜獎節目。關於中國文化的猜獎題目,有的很深,參加比賽的學生答不出來,情有可原。但是,有一位學生竟然不知道唐代的長安,就是今日的西安,而錯認是北京,就不可原諒了。這也反映了一種政治掛帥的單純心理:反正歷史上各朝首都都在北京(其實只有明清兩朝,香港學生的歷史之是可能僅止於明清),所以長安一定就是北京!
上週,幾位香港理工大學的學生來訪問我,他們問我如何看待祖國文化,我不知道他們的問題原因何在。或許是他們剛從大陸西北遊歷回來,對祖國文化開始感到興趣;也許他們覺得香港的教育政策開始認同祖國文化,因此向我這個「北人」(我雖祖籍北方,其實不一定是北人)請教。我的回答可能使他們感到意外,我堅持中國的文化本來就是多元的,而且是擴散式的。文化不能大一統,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所選擇和認識;可以認同廣義的中華文化傳統,但是,也要承認這個大傳統在經過現代化的轉化以後,早已經四分五裂。這也構成了一個當代華人文化的多元現象。香港人其實可以在這個華人文化的離散(diasporic)版圖中,重構自己的文化,甚至有所建樹。
當然,我的這一番話語,目前只能算是高調,這也不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訪問我的年輕學生當然不會了解,回歸的政治意義雖然是統一,但在文化意義上,代表的可能是離散和多元──這又是一種悖論。而離散式的中華文化版圖,當然較祖國的政治和地理版圖,要大得多。
為香港打氣
一
此次返港,我住的時間較長,有較多的機會接觸、觀察和體驗香港的文化生活,也感受到這一年來港人的「低迷」心態。這種心態,當然是因為經濟低迷的情勢而起,形之於色,則是一般怨氣無處發,從的士司機到高級知識分子,個個都在抱怨。抱怨最多的似乎是各報的專欄,我從大大小小的印刷空間感受到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態,因為專欄是香港報紙的特色,深入討論的大塊文章少,小小的不平之鳴比比皆是,積少成多,聲音大了起來,同仇氣愾,變成「倒董」。
從一個外來人(現已成為半個香港人)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世上沒有一個大城市的文化生活和經濟生活像香港一樣聯繫得如此緊密,似乎印證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生產動力和關係決定一切,特別是「上層建築」。其實這種庸俗的說法已受挑戰,甚至在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範疇內也早已修正,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就認為:文化生產本身就是一種基層動力,即文化絕非經濟的被動反映,它有其獨立性,也可和經濟生活互動。
而香港目前的現實不能印證這種修正後的文化理論,卻似乎不由自主地充當馬克思主義的代言人。果真經濟決定一切?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我當然不服氣。撇開理論不談,即使從個人經驗層次來觀察,我也覺得港人在文化生活方面有點「人在福中不知福」,不知福的後果就是文化的動力低落,因而對自身更短視,自我批評和抱怨更厲害。外人如果為香港說幾句好話,港人並不領情,甚至還會怪罪外人不了解香港;如果外人批評香港,則港人更憤怒,認為局外人既然不能與港人共甘苦,自然更無權批評。這種矛盾心態近來又因上海崛起而更變本加厲。上海越發達、在國際上越出風頭,港人則越不安,於是媒體就開始炒作:上海是否已趕上香港?中國入世後,香港的地位是否更低落?這兩個城市的競賽甫開始,香港是否已居劣勢?上海何時會取代香港?愈炒愈熱之餘,港人似乎也有點愈墮落愈不快樂。作為半個外來客和半個本地人,我理應為香港打打氣。當然,我有自知之明,已下列舉的皆會被港人批得一文不值,說我無知、不了解內情。也罷,我既為香港作了不少承擔,還是要繼續說。邊批評,邊打氣。
迄今為止,我仍認為香港的「文化資產」相當雄厚,只是沒有善加利用和發揮。我所謂的文化資產,至少有兩面:一是資金相當充足,決不遜色於台灣;就我較熟悉的大學教育研究經費而言,在比例上就比台灣多。不知是否有人對港台的博物館、電影資料館、大學等文化機構每年經費作比較,若再加上香港各地區的文化節慶的用費,我想調查結果必不會令港人失望。其二是所謂「硬體」(硬件)。近年香港就有設備第一流的文化博物館、中央圖書館和電影資料館落成開幕。最近我到圖書館和電影資料館參觀,對其電子技術的先進,十分佩服。各大學新落成的建築物也不少,來開學術會議的外國學者也對各校會議室的先進設備讚不絕口(只不過覺得冷氣太冷,無法促進思想上的熱身運動);而且更遠超過中國大陸各大學。除文化資產外,香港文化的服務水平也是第一流,從大酒店的待客服務到中央圖書館為使用者提供的種種方便,上海和北京無可比擬。在這方面,香港或受常年經濟消費掛帥之賜,一切皆為消費者服務,然後才得以賺取利潤。然而,文化消費又和經濟消費不盡相同,後者純為慾望的滿足,前者除慾望(包括求知慾)滿足外,還應產生潛移默化的功用。我認為這才是目前香港文化的致命傷:大批資金和不動產(或曰硬體)投下後,好像還未產生太大的潛移默化之效。香港的文化和學術活動不少,但總的成果仍不理想,這就牽涉到文化「硬體」(軟件),即人才、制度和各種課程節目及活動的設計等不易一目了然的未知數。
以學術研究為例,我認為目前的政策處處以硬體和官僚的方式處理軟體,層層建構而後核實,卻往往在過度制度化和嚴密程序中使學者,特別是人文學者喪失思考和獨創的自由空間。其他文化方面的情況頗類似,文化政策冠冕堂皇,但制度繁多、人事複雜,大批錢投下,文化上的建樹仍難和台灣相比。甚至一般市民的文化生活也受過多的建制之累,而失去其自動自發性。所以我所謂「人在福中不知福」的弔詭意義就是:若沒有主動的原創力、自由思考和想像空間,資產再多,可能也會變成「負資產」。
二
近日重遊上海,短短五天之中,腦海裏不時浮現的卻是香港。也許,這個「雙城記」的觀念,我算是始作俑者之一,所以,不少人問我對這兩個城市的印象,甚至逼我作個比較。我一向反對惡性競爭的論調,總覺得這兩個城市應該「互動」而不互相取代,如此才可以相得益彰。
然而,香港人的信心危機似乎日益嚴重,甚至覺得上海已經──或正在──取代香港。為了安慰香港的人心,且讓我先批評上海幾句:
‧浦東的建築物大而無當,APEC會議的會址更是如此,為「全球化」的批評者提供了另一個證據:「硬體」的「接軌」並不足以代表中國可以和世界並駕齊驅;上海的都市建築和失去了「世貿雙樓」以後的紐約在文化意義上相差甚遠。
‧虹橋機場(我還沒有去過浦東機場)仍然雜亂無章,甚至無法和香港的舊啟德機場相比。‧上海的街道仍然在「開發中」,單車不時走上行人道;汽車疾駛不讓人;而人過馬路更對周圍車輛視若無睹。當然無法和香港交通的秩序相提並論。
‧上海的「成功人士」和「白領階級」,在文化消費上仍然擺脫不了暴發戶的習氣。而貧富兩極化的現象可能比香港更嚴重。
‧上海的文化消費生活雖然顯得日益多采多姿,但文化資訊遠遠落在香港之後。上海的文化人雖時常上網,但外文報刊和港台刊物仍然很難看到──甚至連我在衡山路的咖啡店見到台北的《中國時報》都會感到一陣意外的驚喜,更不必提《紐約時報》、《紐約客》,或倫敦《泰晤士報文藝副刊》(TLS)。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對於這些唾手可得的文化資訊,大不份人仍然不聞不問。
這一切都是浮光掠影的表面現象,當然微不足道。從表面看來,目前的上海都市文化尚沒有到「世故」(sophisticated)的程度。世故需要涵養,而涵養需要知識和經驗的累積,作人如此;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的老上海,在外觀上似乎無法和今日的上海相比,但我認為它仍然較現在更「世故」,因為它涵蓋了中西文化多年在上海互動後的成果,而這個歷史上的文化資源仍然可以為今所用。所以,我每次到上海,都感受到一種文化氣氛,它雖然未成型,但在街頭巷尾隨處有形跡可尋。散布在衡山路附近的幾家餐館和酒吧──特別是翻修後的老房子──幾乎每家都有一個「前世」的故事,而這一種歷史的陰魂,在我眼中正代表了上海的魅力。即使經過多年滄桑,在革命和現代化的輪番摧殘之下,仍然陰魂不散,令我着迷。
我認為這才是上海對香港的最大挑戰。香港的世故,完全奠基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它表現於各種經濟消費時尚和品味,然而香港的歷史卻逐漸被這種消費生活所抹殺了。我在香港的餐館、咖啡店和大酒店中感受不到在上海所感受的氣氛,雖然其服務還是第一流的。香港的文化記憶,似乎在嶄新的博物館中也無法保存。我只能從西環的街市或赤柱的墳場中去找尋。香港的空間有限,寸土必爭,似乎對於文物的保護也毫不在意。最近有幸結識香港文物保護委員會的主席劉華森先生,對於他的義務努力,不勝欽佩。然而香港仍然製造不出上海的「新文化」──這個以里弄為基本元素的空間設計,最近甚受各國遊客──包括俄國總統普京和法國大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寵愛,當然也受部分上海本地人的譏諷,稱之為「偽古典主義」。我為了好奇,特別去參觀了兩次,並和一位在該地任職的建築學家傾談,經她指點迷津之後,我感受更多。
「新天地」是由香港的一位商人投資、波士頓的一位名建築師構思設計、新加坡的一家建築公司參與建設,並與上海市的黨政當局積極合作而完成的。這個計劃本身似乎就代表了某種「全球化」的意義。但更引起我的興趣的卻是它對上海里弄文化記憶的處理。它不能算是文物保存,因為當年的里弄房屋幾乎全被拆除,而拆除後重建的小廣場和小天井,和原先的里弄格局也相差甚遠;真正住過里弄房子的人,都說與原來的真實氣氛大相徑庭;原先的里弄是陰溼的、壓抑的,這在王安憶的小說《長恨歌》的第一章中有極精
采的描述。但是這個「新天地」卻是一個開放的遊樂場(只不過常去遊樂得人多屬白領階級和外國遊客);它有點像香港的蘭桂坊,但比蘭桂坊更有氣氛。且不論這個略帶懷舊的新建築是真是偽,它畢竟製造了一個文化的想像,它也沒有抹除歷史──中共「一大」的會址仍然保存,但被「邊緣化」了。
為什麼香港不能重闢新天地?原因之一是香港沒有發現足夠的歷史,而香港人似乎也不再回憶自己的歷史。
三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明報》「生活副刊」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上海陰影下的香港歷史」,開頭一段頗發人深省:
「九七年回歸前後,有陣香港歷史應景出版熱,紅過一陣子,三、四年輾轉下來,出版界的朋友說:如果以中國城市為座標,今天的焦點必然屬於上海。只要跟上海有關,或在標題上安插了『上海』二字的出版,都會賣個滿堂紅。這是五十年未曾發生過的事。新時代的香港故事,要活在新上海的陰影下。」這段話中有一句至為關鍵:「如果以中國城市為座標。」也許,有些香港人會問:如果不以中國城市而以世界或亞洲其他城市為座標呢?幾年前,名建築師──也是哈佛建築設計學院的教授──庫哈斯(Rem Koolhaas)寫過一篇名文,現在廣被引用,題目叫作「通屬城市」(Generic City),恰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答案。庫哈斯說:這個國際都市的新模型在亞洲尤其明顯,它的特徵是:一切「通屬」,兼容並有;無都市計畫可言──而且計劃了也沒有用,徒費錢財和人力;也沒有歷史的自覺,其實歷史的缺席不值得惋惜,人類發展太快,「過去」在我們的心目中也越變越小;如果以共有歷史作為文化認同的依據,這一個論點本身就註定失敗,況且歷史本身在屢被濫用以後,也變得可鄙而無意義。庫哈斯又說:這種「通屬」城市的馬路只供行車,摩天大樓遍地皆是,互相也無甚麼結構關係,而行人被高架通道引入迷津(猶如在遊樂場);無所謂「地方特色」,少許地方文物保存也只是為了遊客;每一個「通屬城市」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機場和酒店,前者容納大量旅客和工作人員,幾乎自成一城;後者幾乎是「通屬城市」最常見的生活標誌。而且酒店裏有商場,人住在裏面可以不必進城購物,所以酒店文化也最足以代表這種都市生活。
庫哈斯的這一套理論也發人深省。也許不少香港人會反對,但目前的香港似乎正逐漸接近這個「通屬城市」的模式,比上海尤有過之。上海還在發展,它的歷史和文化記憶仍然處處為其所用;換言之,還沒有發展到「通屬城市」的地步。香港呢?香港應該走哪一條路?是否仍有選擇?
香港回歸五週年有感
香港回歸五年,從文化意義而言,是否可以斷言已經回歸了祖國文化?「一國兩制」的制度,是否仍然適用於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文化?最近香港政府提出的口號──香港成為「亞洲」的國際都市,其文化意涵是甚麼?是否要超越「祖國」的國際大都市──如上海?這一連串的問題,是我個人在回歸五週年前夕所能想到的,卻不一定能夠提出充份的解答方案。不過,既然已經提出了命提,不妨也試着演繹一番。
記得九七年回歸的前夕,香港人最關心的認同問題:香港人的身份究竟是甚麼?將來有何變化?而這種認同焦慮的背後因素,當然是政治和歷史。
然而,曾幾何時,認同問題已經沒有人討論,似乎也不成問題了。香港人已經認命,乖乖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區公民,持特區護照和回鄉證,但往返祖國與外國,卻比祖國人民更方便,這不得不說是「一國兩制」之賜。
但香港人似乎也不再討論英國殖民的歷史遺產。作了一百多年的英國殖民地公民,他們竟然可以在一夜之間搖身一變,從「女皇」改認「同志」(這個典故來自當年羅大佑的一首名歌《皇后大道中》);從英國米字旗(英國曾有「大不列顛世界永不日落」的殖民口號)改升中國五星旗;從「親英」突然變成「親中」(特別見之於香港的富豪和高官),這個現象,似乎也沒有人作更深層的討論。
我認為這是英國殖民主義最典型的特色,它和法國殖民主義最大的不同,就是對殖民地的統治只重制度和經濟,不重文化。影響所及,英國殖民地的人民對於英國王子的文化並沒有深刻的認識,當然也沒有依戀。
誠然,不少其他英國殖民地的精英,如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V.S.Naipaul),在留學英國後沾染了不少英國人的習慣,甚至比英國人更「英化」,但他們的心理也較香港人複雜,對英國主子的愛恨交織,遠較香港人為深。我想原因無他,大部份香港人的文化深層結構,本來就是中國式的,而且根深蒂固,即使有外來文化侵入,馬上可以將之「漢化」,變成自己的東西,香港茶餐廳的奶茶即是一例。所以,香港華人當中,雖然也有不少「假洋鬼子」,但畢竟是假的,對英國文化的了解,僅止於皮毛而已。
然而,這種皮毛現象也產生了另一種悖論:一般香港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也不深,僅止於人類學所說的文化──日常生活中的風俗習慣和行為舉止而已。而且這種文化的基礎,基本上是嶺南文化。回歸以後,我覺得香港人似乎較從前更「本土化」了,也就是更加執著於多年來賴以為升的嶺南文化。香港人甚至把珠江以北的所有中國地區,都稱之為北方,把大陸人稱之為北佬,大陸妓女則稱之為北姑等等。
這種心理上的南北區分,當然也是一種自我保護的假象。但是影響之下,使得香港人學習普通話更感困難;面對以北京為主的祖國文化,似乎也抱着愛理不理的被動心態,這在香港的大學生中,表現得最明顯。我甚至認為,香港年輕人對日本通俗文化的嚮往,遠在對祖國文化之上。如果這個推斷屬實,將會造成一個不大不小的危機。
這個危機,其實已經漸露端倪,可以見之於最近電視上的猜獎節目。關於中國文化的猜獎題目,有的很深,參加比賽的學生答不出來,情有可原。但是,有一位學生竟然不知道唐代的長安,就是今日的西安,而錯認是北京,就不可原諒了。這也反映了一種政治掛帥的單純心理:反正歷史上各朝首都都在北京(其實只有明清兩朝,香港學生的歷史之是可能僅止於明清),所以長安一定就是北京!
上週,幾位香港理工大學的學生來訪問我,他們問我如何看待祖國文化,我不知道他們的問題原因何在。或許是他們剛從大陸西北遊歷回來,對祖國文化開始感到興趣;也許他們覺得香港的教育政策開始認同祖國文化,因此向我這個「北人」(我雖祖籍北方,其實不一定是北人)請教。我的回答可能使他們感到意外,我堅持中國的文化本來就是多元的,而且是擴散式的。文化不能大一統,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所選擇和認識;可以認同廣義的中華文化傳統,但是,也要承認這個大傳統在經過現代化的轉化以後,早已經四分五裂。這也構成了一個當代華人文化的多元現象。香港人其實可以在這個華人文化的離散(diasporic)版圖中,重構自己的文化,甚至有所建樹。
當然,我的這一番話語,目前只能算是高調,這也不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訪問我的年輕學生當然不會了解,回歸的政治意義雖然是統一,但在文化意義上,代表的可能是離散和多元──這又是一種悖論。而離散式的中華文化版圖,當然較祖國的政治和地理版圖,要大得多。
為香港打氣
一
此次返港,我住的時間較長,有較多的機會接觸、觀察和體驗香港的文化生活,也感受到這一年來港人的「低迷」心態。這種心態,當然是因為經濟低迷的情勢而起,形之於色,則是一般怨氣無處發,從的士司機到高級知識分子,個個都在抱怨。抱怨最多的似乎是各報的專欄,我從大大小小的印刷空間感受到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態,因為專欄是香港報紙的特色,深入討論的大塊文章少,小小的不平之鳴比比皆是,積少成多,聲音大了起來,同仇氣愾,變成「倒董」。
從一個外來人(現已成為半個香港人)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世上沒有一個大城市的文化生活和經濟生活像香港一樣聯繫得如此緊密,似乎印證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生產動力和關係決定一切,特別是「上層建築」。其實這種庸俗的說法已受挑戰,甚至在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範疇內也早已修正,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就認為:文化生產本身就是一種基層動力,即文化絕非經濟的被動反映,它有其獨立性,也可和經濟生活互動。
而香港目前的現實不能印證這種修正後的文化理論,卻似乎不由自主地充當馬克思主義的代言人。果真經濟決定一切?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我當然不服氣。撇開理論不談,即使從個人經驗層次來觀察,我也覺得港人在文化生活方面有點「人在福中不知福」,不知福的後果就是文化的動力低落,因而對自身更短視,自我批評和抱怨更厲害。外人如果為香港說幾句好話,港人並不領情,甚至還會怪罪外人不了解香港;如果外人批評香港,則港人更憤怒,認為局外人既然不能與港人共甘苦,自然更無權批評。這種矛盾心態近來又因上海崛起而更變本加厲。上海越發達、在國際上越出風頭,港人則越不安,於是媒體就開始炒作:上海是否已趕上香港?中國入世後,香港的地位是否更低落?這兩個城市的競賽甫開始,香港是否已居劣勢?上海何時會取代香港?愈炒愈熱之餘,港人似乎也有點愈墮落愈不快樂。作為半個外來客和半個本地人,我理應為香港打打氣。當然,我有自知之明,已下列舉的皆會被港人批得一文不值,說我無知、不了解內情。也罷,我既為香港作了不少承擔,還是要繼續說。邊批評,邊打氣。
迄今為止,我仍認為香港的「文化資產」相當雄厚,只是沒有善加利用和發揮。我所謂的文化資產,至少有兩面:一是資金相當充足,決不遜色於台灣;就我較熟悉的大學教育研究經費而言,在比例上就比台灣多。不知是否有人對港台的博物館、電影資料館、大學等文化機構每年經費作比較,若再加上香港各地區的文化節慶的用費,我想調查結果必不會令港人失望。其二是所謂「硬體」(硬件)。近年香港就有設備第一流的文化博物館、中央圖書館和電影資料館落成開幕。最近我到圖書館和電影資料館參觀,對其電子技術的先進,十分佩服。各大學新落成的建築物也不少,來開學術會議的外國學者也對各校會議室的先進設備讚不絕口(只不過覺得冷氣太冷,無法促進思想上的熱身運動);而且更遠超過中國大陸各大學。除文化資產外,香港文化的服務水平也是第一流,從大酒店的待客服務到中央圖書館為使用者提供的種種方便,上海和北京無可比擬。在這方面,香港或受常年經濟消費掛帥之賜,一切皆為消費者服務,然後才得以賺取利潤。然而,文化消費又和經濟消費不盡相同,後者純為慾望的滿足,前者除慾望(包括求知慾)滿足外,還應產生潛移默化的功用。我認為這才是目前香港文化的致命傷:大批資金和不動產(或曰硬體)投下後,好像還未產生太大的潛移默化之效。香港的文化和學術活動不少,但總的成果仍不理想,這就牽涉到文化「硬體」(軟件),即人才、制度和各種課程節目及活動的設計等不易一目了然的未知數。
以學術研究為例,我認為目前的政策處處以硬體和官僚的方式處理軟體,層層建構而後核實,卻往往在過度制度化和嚴密程序中使學者,特別是人文學者喪失思考和獨創的自由空間。其他文化方面的情況頗類似,文化政策冠冕堂皇,但制度繁多、人事複雜,大批錢投下,文化上的建樹仍難和台灣相比。甚至一般市民的文化生活也受過多的建制之累,而失去其自動自發性。所以我所謂「人在福中不知福」的弔詭意義就是:若沒有主動的原創力、自由思考和想像空間,資產再多,可能也會變成「負資產」。
二
近日重遊上海,短短五天之中,腦海裏不時浮現的卻是香港。也許,這個「雙城記」的觀念,我算是始作俑者之一,所以,不少人問我對這兩個城市的印象,甚至逼我作個比較。我一向反對惡性競爭的論調,總覺得這兩個城市應該「互動」而不互相取代,如此才可以相得益彰。
然而,香港人的信心危機似乎日益嚴重,甚至覺得上海已經──或正在──取代香港。為了安慰香港的人心,且讓我先批評上海幾句:
‧浦東的建築物大而無當,APEC會議的會址更是如此,為「全球化」的批評者提供了另一個證據:「硬體」的「接軌」並不足以代表中國可以和世界並駕齊驅;上海的都市建築和失去了「世貿雙樓」以後的紐約在文化意義上相差甚遠。
‧虹橋機場(我還沒有去過浦東機場)仍然雜亂無章,甚至無法和香港的舊啟德機場相比。‧上海的街道仍然在「開發中」,單車不時走上行人道;汽車疾駛不讓人;而人過馬路更對周圍車輛視若無睹。當然無法和香港交通的秩序相提並論。
‧上海的「成功人士」和「白領階級」,在文化消費上仍然擺脫不了暴發戶的習氣。而貧富兩極化的現象可能比香港更嚴重。
‧上海的文化消費生活雖然顯得日益多采多姿,但文化資訊遠遠落在香港之後。上海的文化人雖時常上網,但外文報刊和港台刊物仍然很難看到──甚至連我在衡山路的咖啡店見到台北的《中國時報》都會感到一陣意外的驚喜,更不必提《紐約時報》、《紐約客》,或倫敦《泰晤士報文藝副刊》(TLS)。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對於這些唾手可得的文化資訊,大不份人仍然不聞不問。
這一切都是浮光掠影的表面現象,當然微不足道。從表面看來,目前的上海都市文化尚沒有到「世故」(sophisticated)的程度。世故需要涵養,而涵養需要知識和經驗的累積,作人如此;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的老上海,在外觀上似乎無法和今日的上海相比,但我認為它仍然較現在更「世故」,因為它涵蓋了中西文化多年在上海互動後的成果,而這個歷史上的文化資源仍然可以為今所用。所以,我每次到上海,都感受到一種文化氣氛,它雖然未成型,但在街頭巷尾隨處有形跡可尋。散布在衡山路附近的幾家餐館和酒吧──特別是翻修後的老房子──幾乎每家都有一個「前世」的故事,而這一種歷史的陰魂,在我眼中正代表了上海的魅力。即使經過多年滄桑,在革命和現代化的輪番摧殘之下,仍然陰魂不散,令我着迷。
我認為這才是上海對香港的最大挑戰。香港的世故,完全奠基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它表現於各種經濟消費時尚和品味,然而香港的歷史卻逐漸被這種消費生活所抹殺了。我在香港的餐館、咖啡店和大酒店中感受不到在上海所感受的氣氛,雖然其服務還是第一流的。香港的文化記憶,似乎在嶄新的博物館中也無法保存。我只能從西環的街市或赤柱的墳場中去找尋。香港的空間有限,寸土必爭,似乎對於文物的保護也毫不在意。最近有幸結識香港文物保護委員會的主席劉華森先生,對於他的義務努力,不勝欽佩。然而香港仍然製造不出上海的「新文化」──這個以里弄為基本元素的空間設計,最近甚受各國遊客──包括俄國總統普京和法國大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寵愛,當然也受部分上海本地人的譏諷,稱之為「偽古典主義」。我為了好奇,特別去參觀了兩次,並和一位在該地任職的建築學家傾談,經她指點迷津之後,我感受更多。
「新天地」是由香港的一位商人投資、波士頓的一位名建築師構思設計、新加坡的一家建築公司參與建設,並與上海市的黨政當局積極合作而完成的。這個計劃本身似乎就代表了某種「全球化」的意義。但更引起我的興趣的卻是它對上海里弄文化記憶的處理。它不能算是文物保存,因為當年的里弄房屋幾乎全被拆除,而拆除後重建的小廣場和小天井,和原先的里弄格局也相差甚遠;真正住過里弄房子的人,都說與原來的真實氣氛大相徑庭;原先的里弄是陰溼的、壓抑的,這在王安憶的小說《長恨歌》的第一章中有極精
采的描述。但是這個「新天地」卻是一個開放的遊樂場(只不過常去遊樂得人多屬白領階級和外國遊客);它有點像香港的蘭桂坊,但比蘭桂坊更有氣氛。且不論這個略帶懷舊的新建築是真是偽,它畢竟製造了一個文化的想像,它也沒有抹除歷史──中共「一大」的會址仍然保存,但被「邊緣化」了。
為什麼香港不能重闢新天地?原因之一是香港沒有發現足夠的歷史,而香港人似乎也不再回憶自己的歷史。
三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明報》「生活副刊」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上海陰影下的香港歷史」,開頭一段頗發人深省:
「九七年回歸前後,有陣香港歷史應景出版熱,紅過一陣子,三、四年輾轉下來,出版界的朋友說:如果以中國城市為座標,今天的焦點必然屬於上海。只要跟上海有關,或在標題上安插了『上海』二字的出版,都會賣個滿堂紅。這是五十年未曾發生過的事。新時代的香港故事,要活在新上海的陰影下。」這段話中有一句至為關鍵:「如果以中國城市為座標。」也許,有些香港人會問:如果不以中國城市而以世界或亞洲其他城市為座標呢?幾年前,名建築師──也是哈佛建築設計學院的教授──庫哈斯(Rem Koolhaas)寫過一篇名文,現在廣被引用,題目叫作「通屬城市」(Generic City),恰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答案。庫哈斯說:這個國際都市的新模型在亞洲尤其明顯,它的特徵是:一切「通屬」,兼容並有;無都市計畫可言──而且計劃了也沒有用,徒費錢財和人力;也沒有歷史的自覺,其實歷史的缺席不值得惋惜,人類發展太快,「過去」在我們的心目中也越變越小;如果以共有歷史作為文化認同的依據,這一個論點本身就註定失敗,況且歷史本身在屢被濫用以後,也變得可鄙而無意義。庫哈斯又說:這種「通屬」城市的馬路只供行車,摩天大樓遍地皆是,互相也無甚麼結構關係,而行人被高架通道引入迷津(猶如在遊樂場);無所謂「地方特色」,少許地方文物保存也只是為了遊客;每一個「通屬城市」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機場和酒店,前者容納大量旅客和工作人員,幾乎自成一城;後者幾乎是「通屬城市」最常見的生活標誌。而且酒店裏有商場,人住在裏面可以不必進城購物,所以酒店文化也最足以代表這種都市生活。
庫哈斯的這一套理論也發人深省。也許不少香港人會反對,但目前的香港似乎正逐漸接近這個「通屬城市」的模式,比上海尤有過之。上海還在發展,它的歷史和文化記憶仍然處處為其所用;換言之,還沒有發展到「通屬城市」的地步。香港呢?香港應該走哪一條路?是否仍有選擇?